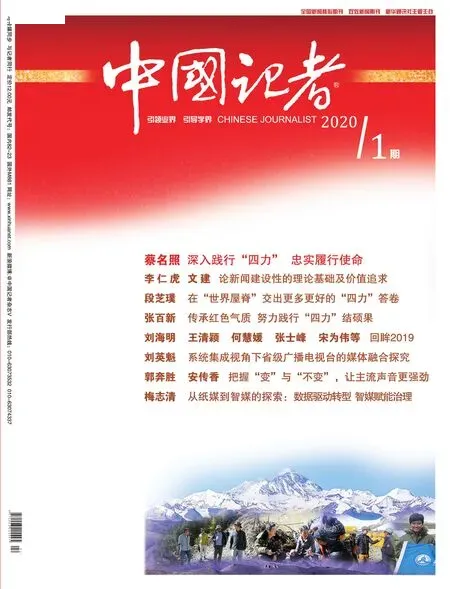意识形态偏见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选择框架
□ 王润泽 徐诚
内容提要 在近期涉港问题报道中,部分西方媒体以“不客观”“不平衡”的报道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媒体的报道偏见深植于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常常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置于“他者化”的新闻框架,以报道的“双重标准”造成新闻内容的失衡。本文从报道的理论分析出发,对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梳理,并联系公共舆论安全讨论了媒介报道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应对策略。
2019年夏秋以来发生在香港的修例风波、极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暴力行为的严重性、香港这一地域的重要性与敏感性使得涉港问题报道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铺天盖地的报道使新闻事件延伸至更为宏观和政治化的层面,部分西方媒体的报道从双重标准出发,以偏概全、主题先行,引发新闻报道“偏见压倒客观”的质疑。西方媒体对涉港问题的报道在实践层面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框架与意识形态偏见,报道失衡、不客观、有失真实的“倾向性新闻”成为西方媒体在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服务于舆论战的工具。
一、问题的提出:意识形态偏见与西方媒体涉港问题报道
“对那些在自我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冲突的人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新闻框架的倾向性研究中,意识形态被视为促使报道产生媒介偏见与新闻倾向性的要素之一,在新闻实践中媒介偏见与新闻倾向性主要体现在新闻事件的选择框架与报道方式上。[1]沃尔特·李普曼将“刻板印象”与媒介偏见相联系,“一篇报道是知情者和已知的事实的混合产物,观察者在其中的作用总是带选择的,而且通常是带想象的。”[2]媒介偏见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夹带偏见的新闻报道无法全面反映新闻事件,妨碍了受众对真实情况的了解,同时,媒介偏见导致新闻事件中某一部分群体受到不平衡、不公正的报道,这将造成社会团体、族群的隔阂,引发社会动荡,危及社会安全。在国际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中,媒介偏见更加明显,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常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他者化”框架,将其与落后、混乱、人权问题等联系在一起,报道基调呈现出负面内容大于正面的现象。作为现代理性精神的对立面,“他者”被视为异端,与愚昧、混乱、邪恶、肮脏等联系在一起,为的是证明与维护“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3]例如,在涉藏报道上西方媒体就以显著的选择框架对新闻事实进行加工,中国被视为西方社会的对立面,大量的西方报道对涉藏问题的新闻事实进行歪曲,显示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4]
香港发生修例风波、暴力破坏活动后,大量的西方媒体报道将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建构成为彼此对立的两派,以非常鲜明的选择框架将香港警察、中国大陆建构为一个与之敌对的“他者化”形象,这些报道往往以偏概全、主题先行,在选择框架背后隐藏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偏见。美国媒介分析家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宣传模型”的概念,指出宣传模式导致了“舆论同化”现象。[5]在对华报道中,特别是在对西藏问题、香港问题等的报道上,西方媒体以其“东方主义心态”显示出强烈的媒介偏见,使得西方新闻界标榜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的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6]例如,英国《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媒体2019年7月30日报道了一则消息:香港警察用抢指着抗议群众,并配有图片或者剪辑过的现场视频,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断章取义地将新闻标题定为“警察拿枪指着抗议人士”。据《中国日报》调查,7月30日晚,在香港葵涌警署外,一群“黑衣人”号称“和平示威”,但却用砖头砸、激光笔照、棍棒打等攻击警察。现场拍摄的完整视频也显示,两名落单警察被近百人围住并殴打,暴徒向警察投掷不明物体,还用激光笔试图使落单警察丧失防卫能力。在此情况下,一名警察挥舞警棍自卫,一名白衣警察迫于无奈举枪。31日,前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陈祖光回应记者采访,当晚的情势下该警察举枪完全没有问题。
传统的新闻框架理论围绕媒体新闻报道的倾向性,认为新闻记者在报道过程中主观地构建了一个社会“真实”,这一框架受到记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就概念的理论内涵而言,新闻框架的构建围绕新闻内容的选取与舍弃,主要包括了“选择”“凸显”“遗漏”与“包含”等内容。[10]例如,在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日的报道中,报道称香港的抗议者为与警察作斗争不得不采取创新手段,如设立路障、使用激光笔(镭射枪)等。实际上,这种激光笔具有攻击性的事实被西方媒体报道有意“遗漏”,报道也因此具有了明显的选择框架。据《中国日报》调查,自6月以来,香港示威者多次在冲突中使用激光笔照射警察眼睛,已导致多名警察受伤与不适。8月7日香港警方在记者会上现场演示经激光笔照射后的情况。现场一名戴着黑色防护镜的人员手持银色激光笔,近距离照射纸张,大约十秒,纸张上出现白烟,继续照射后,纸张被烧穿起火。
从文字、图片与视频的展示都能看到,西方媒体对涉港问题的报道已经从各个方面建立了选择框架,这种框架使得新闻报道出现了清晰的价值判断,将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置于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事实上,回顾此次事件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西方媒体的报道存在明显的“选择”,报道出现明显的失衡。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香港暴力事件的导火索,《逃犯条例》的修订旨在处理有关香港居民涉嫌在台湾杀人案件的移交审判问题,同时堵塞香港现有法律制度的漏洞。香港特区政府于2019年4月向立法会提交了《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以使香港可与尚无长期司法互助安排的司法管辖区展开个案合作。但是无论是报道展现的香港问题具体细节,还是在对香港暴力活动的报道上,西方主要媒体的报道都显示出很强的同化性,这一现象展示出西方话语对“香港问题”独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方面,西方话语中的香港具有殖民地色彩,在这一情境中,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刻板印象与意识形态偏见强化了西方媒体报道的倾向性,破坏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概言之,在大众媒体、西方话语和东方主义刻板印象的综合作用下,舆论放大了公众对于香港问题的偏见,使得西方媒体在迎合读者的商业诉求驱使下构建出倾向性明显的新闻框架,近乎一致地选择新闻议题,报道体现出更为明显的偏见。
新闻选择框架的倾向性研究存在一个前提,即多数媒体主张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并认为新闻工作者存在客观报道的义务。与新闻的客观性相区别,框架理论认为记者在报道过程中所建构的“真实”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个“框架”是记者主观意志的体现。因此,就西方媒体涉港问题的具体报道而言,新闻框架的构建更加显著,凸显了中西方报道差异,这背后是西方话语中心对香港问题的巨大意识形态偏见。在文字报道中,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英国星空电视(SkyNews)始终用争取民主的抗议者(Protester)来称呼那些破坏公共秩序和设施的暴徒,更为鲜明的是图片报道和视频的选取,网络与社交媒体的传播中西方媒体对文字、图片、视频的选取都说明西方媒体的涉港问题报道已经从各方面凸显了选择框架。
二、西方媒体新闻报道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原因分析
中西方媒体报道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涉港、涉藏问题的报道上,西方媒体在报道基调上展现出一贯性与一致性。在新闻实践中,西方话语往往将中国建构为一个敌对的“他者化”形象,充满了落后、混乱和人权问题。从新闻框架的理解看,中西方媒体报道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为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偏见催生了西方媒体所使用的选择框架。另一方面,受到商业化运作和西方客观报道准则的影响,西方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偏见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一)意识形态偏见与“他者化”框架
新闻报道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其意义在于对原本的社会事实进行意义化和选择性重构,借助意义化的过程将事实的叙述条理化,以此构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世界。在围绕2019年涉港问题报道中,中西方媒体报道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差异性,而出现这些报道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媒体都将中国的国家形象矮化,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落后、混乱和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在近期的涉港问题报道中,西方媒体构建的针对中国新闻报道的双重标准存在明显的“妖魔化”中国的倾向,折射出意识形态的偏见;其二,在全球经济下行、西方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的情况下,西方媒体急需构建一个“他者”的形象。在近期涉港问题的报道中,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被西方媒体描述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报道内容将中国大陆刻意建构为一个与中国香港敌对的“他者化”形象,激化社会矛盾,为实现这一目的,报道的客观性最终流于形式和表面化。
国际新闻传播中西方媒体报道构建选择框架的目的之一即是以宣传模式促进“舆论同化”,体现出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英国哲学家约翰·汤普森认为,“把一种观点称为‘意识形态’,似乎就是已经在含蓄地批评它,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似乎带有一种负面的批评意义”。[11]当前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去意识形态化、淡化意识形态的声音层出不穷,然而就西方媒体在涉港、涉藏报道上的表现而言,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性显而易见:一方面,诸多西方媒体在近期涉港问题的报道上对事实进行歪曲,报道偏颇,另一方面,具备强大传播实力的西方媒体在涉港报道上与中方媒体一度开展争夺话语权的竞争。从传播过程看,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选择框架具有一致性,其报道基调体现了西方社会遏制中国的意识形态霸权。
西方媒体报道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他者化”新闻框架构建可以认为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典型体现。在传播学理论中,“霸权”是某个社会群体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领导权,西方媒体在涉港问题报道上的表现正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它不仅需要媒体的作用,还需要文化工业与国际舆论对其的认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媒体借助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与西方社会舆论之间达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建构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偏见。在跨文化传播中,权利关系模式与“他者化”表征紧密相连,新闻媒体成为主导权力的鼓噪者,将带有偏见的报道卷入权力运作,以更为多样的形式干预政治。因此,在西方媒体的新闻实践中,围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报道内容更多聚焦于负面问题,新闻信源和内容都呈现失衡状态,大量体现西方价值观的象征符号被运用,中国被塑造成为与西方社会相对立的“他者”。在近期涉港问题报道中,西方媒体将香港警察建构成敌对的“他者”,歪曲报道香港警察依法执法、止暴制乱,污蔑警察过度执法,同时对暴徒用易燃液体焚烧无辜市民、企图抢夺警察佩枪、威胁警察生命安全的罪行进行蓄意包庇和美化。
(二)商业化与新闻客观性的内在悖谬
在商业化运作模式的驱动下,西方媒体需要以“戏剧性”刺激读者对媒介文化产品的消费欲望,而这种“戏剧性”与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存在矛盾之处,在西方媒体对涉港问题的报道中客观、平衡地展现各方声音的报道几乎没有,一些报道甚至断章取义、夸大其词,为在香港进行暴力、破坏、恐吓活动的暴徒唱赞歌。另一方面,在近期涉港问题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媒介偏见的体现进一步验证了西方新闻界客观性神话的破灭,这些夹杂偏见的新闻内容体现了西方媒体报道的“表面客观性”或“伪客观性”。
新闻客观性借助记者的新闻实践而得以建立,包含一套新闻采访与报道的技术标准。客观报道与新闻内容的传播效果、受众的阅读态度紧密相关,深刻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趋向。作为一种报道的手法,客观报道发源于新闻事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国学界长期将新闻客观性视为资本主义新闻业的理论内容,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引入。就新闻客观性与客观报道的概念解读而言,中国和西方新闻界对客观报道有不同的理解。作为客观报道的对立面,报道偏见很难被完全消除,记者在选择事实的过程中不免受到来自国家与民族利益、阶级与种族意识、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记者等新闻工作者反映与理解现实和新闻事件的框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彻底摆脱报道偏见,实现完全的客观性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对报道客观性的怀疑一度使美国的新闻报道走向反面,即完全的主观性。例如,美国新闻史上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新新闻主义”就将小说创作的手法运用于新闻写作,不但包揽了新闻要素,还以“解放媒介”为口号对新闻内容进行大规模改写,细致地描写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并表达写作者的评论与意见,然而“新新闻主义”对客观报道的完全抛弃并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可,记者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负责。中国新闻界对客观报道的接纳与实践较早体现在消息与通讯写作上,胡乔木在其《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中认为“最有力量的意见,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12]在新闻实践中,中国新闻界认为“客观报道不等于也不可能没有倾向性”,客观报道并不是自然主义,也应有立场,坚持“用事实说话”。[7]
在西方新闻界,客观报道常被认为是“一个有经验的职业记者的标志”,是“新闻工作的一项标准”,客观报道以“平衡”的原则作为新闻客观的“操作定义”,要求报道内容“务求不偏不倚,尽可能把正反双方的事实和意见并陈,让读者自己评理。”[8]就新闻报道的网络传播情况而言,网络新闻一方面常以社交媒体特有的方式进行新闻信息的交流,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网络新闻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常彼此纠缠,部分断章取义、主观解释、夸大其词的报道以“真实性”为幌子,蒙蔽了新闻客观报道的准则。[9]回顾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报纸由登载船期的广告纸逐渐演化为政党党同伐异的舆论武器,消息发布的系统开始集中化,到了商业化时代,新闻客观报道原则的衍生与资本主义的商业利益相互结合,平衡、客观地报道才成为报纸从业者牢固的职业准则。深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则不难发现,新闻客观性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历史背景,在新闻实践中新闻客观性要求新闻报道反映“普遍利益”。私人资本所掌控的商业化媒体将代表工人阶级意识的劳工新闻边缘化,将资本利益视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将资产阶级主流价值和统治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共识”。同时,西方新闻客观性还与商业化媒体相互依附,政治与经济动因互为表里,共同构建了客观性在新闻实践层面的意义。因此,在西方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下,西方媒体报道呈现出鲜明的“表面客观性”或“伪客观性”,客观报道准则成为粉饰新闻内容的“幌子”,帮助媒介偏见暗度陈仓,制造隔阂与对立。[13]
三、研究意义:意识形态偏见与公共舆论安全的深层关联
在近期的涉港问题报道中,西方媒体为争夺话语权,维护西方文化霸权,在报道中采取“双重标准”,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些偏见通过宣传模式与新闻框架制造共识,促进“舆论同化”,威胁公共舆论安全。按照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对意识形态的分类,媒介偏见也可以被纳入“有机的意识形态”与“任意的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中:一部分媒介偏见由社会结构决定,很难避免,另外一部分媒介偏见存在于受众的头脑中,受到各种认知过程的影响,集中表现在文化因素中,具有随意性与非理性的特质。[14]简而言之,媒介机构受到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影响,在新闻报道的框架设置上就具有倾向性,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报以明显的有机的意识形态偏见,同时西方国家的观众与读者已经在其文化想象中接纳了这一偏见,这种偏见有受众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特殊的环境因素作用,两者互为表里、皮毛相依,共同作用于社会心理,对公共舆论安全造成深刻影响。
公共舆论具有鲜明的倾向性、集合性与表层性,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始终处于一种混沌、冲动和非理性状态,容易受到摆布与控制,通过舆论传播平台传递信息以作用于受众。舆论战是“宣传战的一种重要方式,属于心理战的宣传心理战范围。即是指以敌集体心理为目标,通过大众宣传工具对其心理施加压力和影响,以期达到改变敌方观念和意识形态,削弱敌方士气和瓦解敌军的作战方式”。[15]在舆论战中,“交战双方依托新闻媒体展开的全方位的攻心划谋的特殊作战样式,已成为现代战争敌我对抗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强调要与心理战、信息战高度融合,创造性地运用新闻传播的方法和技巧,使新闻资源的战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政府和军队的宣传机构控制、操控、策划、利用各种舆论工具,以网、视、声、文、图等为武器,进行旨在压制对手、赢得公众的较量”。[16]社会舆论事关意识形态安全,西方国家近年来动用各方力量参与舆论斗争,媒体机构以舆论为武器,通过利用各种传播工具和信息资源对重大问题进行导向性宣传的舆论对抗活动。
夹带意识形态偏见的新闻报道危害着公共舆论安全,这种报道内容的“失衡”无助于缓解现代化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反而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制造障碍。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实现了媒体内容的全球化,为西方媒体制度和自由主义媒体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销文化霸权铺平道路。因此,受制于以上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多重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媒介偏见很难消除,作为它的对立面——新闻客观性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具有相对性与虚伪性。如此而来,客观报道充当记者压制主体性的一层表象,不仅为记者争取了相对于政府与资本的独立性,还掩盖了新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例如,西方媒体认可的所谓“普遍利益”仍旧是西方新闻界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利益之间关系的反映。[17]
意识形态偏见使得报道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导向性,这一点使得新闻报道成为宣传舆论战的重要工具。从国际传播或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在近期涉港问题报道中西方媒体偏见的背后隐藏的是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偏见,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方之间的认同壁垒与文化共识的阙如同时也对西方媒体报道的框架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主导的媒体如何取舍新闻内容,如何灵活使用客观性等职业规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媒体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与新闻价值观。在近期的香港问题报道中,媒体利用倾向性明显的报道孤立中国大陆并将其塑造为一个敌对的“他者”,这不仅验证了新闻客观性的相对性与虚伪性,也是西方媒体媒介偏见的一个代表案例。近期发生在香港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主权问题,还藏有更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隐忧。西方媒体带有偏见的报道不仅对公共舆论安全造成显见的影响,还为中国媒体如何在香港问题的报道中争取主动权带来严峻挑战。概言之,简单的中西方二元对立实际上无助于解决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夹带偏见的报道只能掩盖问题,探索与寻求全球化视角才能正面由现代化、经济快速增长与少数族群的多元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
四、结语
在香港暴力事件升级的情况下,西方媒体涉港问题报道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体现了明显的媒介偏见,中国在西方媒体的话语建构中多呈现出一种负面的“他者化”的刻板印象。从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看,西方新闻界的客观报道准则所强调的“普遍利益”具有明确的立场,记者、编辑等新闻工作者经由主观经验的加工,在新闻报道中移植新闻的选择框架与媒介偏见。
在近期的涉港问题报道中,西方媒体这种制造对立的“他者化”新闻框架筑起了香港民众对中国大陆的认同壁垒,激化了社会矛盾。“他者化”新闻框架的设置强化排他性认同,根源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媒介偏见与公共舆论互相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心理,危及公共安全。对此,中国媒体一方面应善于设定议题,利用媒介事件引导舆论,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应避免处于解释、抗议、声明等被动状态,应与外国媒体展开合作,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避免意识形态偏见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注释】
[1]《新闻框架的倾向性研究》,杰拉德·马修斯、罗伯特·恩特曼著,韦路、王梦迪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2).
[2]《舆论学》,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3]跨文化传播在各种思潮和文化冲突的裹挟之下,聚焦“他者的表征”,发展了颇具反思性的“他者化”概念。认同制造了他者化,他者化又制造了“我们”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强化排他性认同。参见《跨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他者化难题》,单波、张腾方,《学术研究》,2016(06).
[4]《西方传媒“3·14”事件报道的选择框架与意识形态偏见》,周庆安、卢朵宝,《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03).
[5]《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爱德华·S·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著,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著,沈荟、周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7]《客观报道与对外报道》,唐润华著,收录于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研究室编:《对外宣传工作论文集》,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332页.
[8]《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约翰·赫尔顿著,刘有源译,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9]《网络新闻传播学》,董天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10]Entman,R.M.Framing:Towardclassificationof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ofCommunication,1993(4):51-58.
[11]《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约翰·B·汤普森著,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2]《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13]《简论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偏见——以西方媒体新闻报道为例》,徐琴媛、杨卓颖,《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10).
[14]《狱中札记》,安东尼奥·葛兰西著,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15]《传播技术发展与舆论战的嬗变》,刘燕、陈欢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16]《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舆论战法》,杨堂珍,《军事记者》,2004(7).
[17]《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赵月枝,《新闻大学》,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