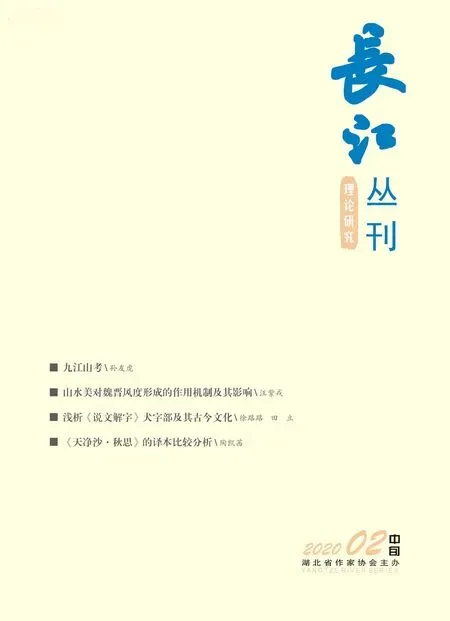山水美对魏晋风度形成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
■汪紫戎/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一、前言
魏晋时期属于历史长河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的人,思想方面,摆脱了汉代儒学思想统治的禁锢,汲取道教的思想内核;政治方面,朝代的快速更迭,残酷的选官标准;社会方面,动乱、疾病、灾荒以及后期的“八王之乱”等一系列繁复而宏阔的时代背景,促使魏晋名士对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进行深层次发掘,并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表征于文学上就是由被动转变为自觉和文学创作个性化突出,文学自觉贯穿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才最终形成。魏晋风度也由此产生,李泽厚先生曾说:“药、酒、姿容、神韵,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才构成魏晋风度。”[1]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倾注下,才塑造出遗世独立的魏晋风度,多种因素中山水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在山水美影响下的魏晋风度对后世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历史大背景促使文人寄情山水
山水情怀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早在《诗经》中已有描写自然山水的诗句,孔子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阐发儒家思想。山水一词真正以独立形式出现是在魏晋时期,左思《招隐诗》中的“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顾恺之《论画》中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2]山水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运用于各个领域。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史无前例,汉末战乱频繁、三国乱战、“八王之乱”、宋、齐、梁、陈朝代更替产生的战乱等,使得整个魏晋南北朝充满了战火的硝烟,许多人命丧沙场、农田上没有充足的劳动力、沉重的赋税、战乱带来的人口大规模逃亡和瘟疫疾病的发生,在这三百多年几乎没有停息的时候,混战和分裂的字眼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符号。曹操的《蒿里行》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选拔官员的制度由汉代按察制演变为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门阀统治权倾天下,后期愈演愈烈,甚至演变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极端局面,阻断了有知识、有抱负的寒门名士官宦之路,黑暗的政治环境也打消了诸多名士入仕愿望。传统儒学在此背景下也逐渐式微,摆脱两汉经学的思想束缚,吸取老庄的成分,魏晋玄学由此产生,为魏晋之人思想上注入了更多自然、随性德特点。敏感的文人作家们受制于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难免感怀人生转瞬即逝、命运颠沛流离、时事难于把控,报国无路、入世无门的文人们转而将自身难以释怀的情绪寄情于山水自然之中,希冀在“自然”和“名教”之间寻找平衡点。
三、山水美在艺术形式中的体现
(一)山水美寓于诗歌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人墨客历来喜好游览山水、吟诗寄兴。不同于传统文人欣赏山水时的比德模式,魏晋文人更多的将个人的情感意志自由挥洒。王羲之的传世名作《兰亭序》正是记载他们一行人因修禊习俗集于兰亭,游览山水的乐事,感发山水之中纵情挥洒,标志着诗人对山水审美开始留心注意。创立田园诗的陶渊明,在他诸多田园诗中都描绘了山水之美。历史上因遭遇政治上的打压的诗人谢灵运,第一位极力书写山水诗山水成为真正独立的审美对象。为后世开创新的文学题材,一直延续至今。
(二)绘画中的山水美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魏晋玄学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魏晋名士仰观宇宙繁盛,低头俯察万物,山水本无意,观者有心尔,于是出现了潇洒玄远的山水画。山和水作为绘画素材历史深远,直到魏晋时期才真正成为独立的画种。这一时期关于山水画的理论与著作层出不穷,顾恺之《论画》是涉及山水画的最早理论著作。还提出了“迁想妙得”“传神”“以形写神”等对后世绘画创作特别是山水画产生深刻影响的理论主张。
(三)追寻自然的魏晋书法
宗白华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出的。”[3]魏晋士人以高度的自觉意识追寻文艺发展的步履,书法是自由精神人格最恰当的艺术载体,由此衍生出草书、行书、楷书等新书体。受老庄玄学影响,士人精神得到极大的解放,魏晋书法讲求自然的韵味,摈弃质朴古趣,转向追求率性自然。书法家常于山水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传世名作,如“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
四、追寻自然的魏晋名士
(一)于山林中长啸
魏晋名士善啸,歌啸、吟啸、讽啸、长啸成为他们纵情山水、眷恋人生的种种逸态。[4]阮籍、陶渊明、嵇康等名士都有诗句直接描写自己啸歌并赞美啸歌带来的种种好处。啸歌不需假借外物,是名士自我娱乐、自我排解心中郁结、抒发高雅情趣的有效方式之一。登高长啸,超然物外,面对的是自然界的山川河流,是人与自然间独有的交流方式。
(二)自然与人物品藻
中国美学正是出自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魏晋士人注重自我形象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时代,如《世说新语》从文学、容止等三十六个方面来品评人物,容止在这一时期作为评判一个人物的准绳之一。在评赏人物时,常用自然界事物作为形容词比拟人物,夏侯玄被称为“玉树”,呈现出“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的美,王衍神姿“如瑶林琼树”,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5]以优美的树木、日月、云彩、蛟龙形容人是当时的风尚,这对于崇尚自然的魏晋名士是一种极高的评价。
(三)追寻隐逸的魏晋名士
魏晋南朝时期,归隐是诸多名士的追求,在当时甚至成为一种风尚。彼时政治混乱,士人仕途坎坷,动荡的时局是滋养隐士的土壤,追寻自然成为当时士人的向往。不论出于何种心境和意图,许多士人选择回到山水田园中,亲近大自然。陶渊明曾三仕三隐,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山林,披星戴月地耕作,在田野上劳作时悠然见南山,为世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田园画卷,勾勒出令人憧憬田园生活。
(四)喜好游历山川
七贤曾遍历太行山水,畅游太行竹林,不仅是为躲避灾祸,也是对于自我品格的坚持和塑造。兰亭名士常集会于山林之中,赋诗、挥墨、饮酒、啸歌,是在自然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陶渊明归隐是淡泊明志追求田园宁静的表征。同时,服散在当时成为众多名士的爱好,他们追求药散带来的形神合一的快感和得道成仙和长生不老,因此进入山林寻找草药制成药物也是当时名士走进山川,游历风景因素之一。山水美景为名士提供了解放天性、寻找自我的绝佳场地。
五、魏晋风度下山水美对后世的影响
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亲近自然,环抱山水方式的熏陶,在这一过程中,山水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意象,并被运用在诗歌、绘画、书法等多样艺术形式中,由此开创了独立的新题材,如山水诗、山水画等,为后世文艺创作开拓全新的形式,新书体流传使用至今,成为书法爱好者学习的源头。魏晋名士向外感知了自然,向内发现了情感,而自然正是产生和抒发情感的绝好场地和对象,自然成了他们生命价值的源泉和凭据,由此追寻自然的神韵是这一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共同追求,山水成为后代文人创作的常青题材之一。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乃至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vi魏晋风度贴近自然、追求自然的审美情趣,“风神潇洒,不滞于物”成为后世仰慕的人格范式。唐代的王勃、李白、宋代的苏轼都是追寻自然,喜好游历大山大川的名士。山水美不仅滋养了魏晋风度的生长,更为人们寻找自我、感知自我、发现自我提供了绝佳场地,这或许也是魏晋风度经久不衰,备受历代文人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