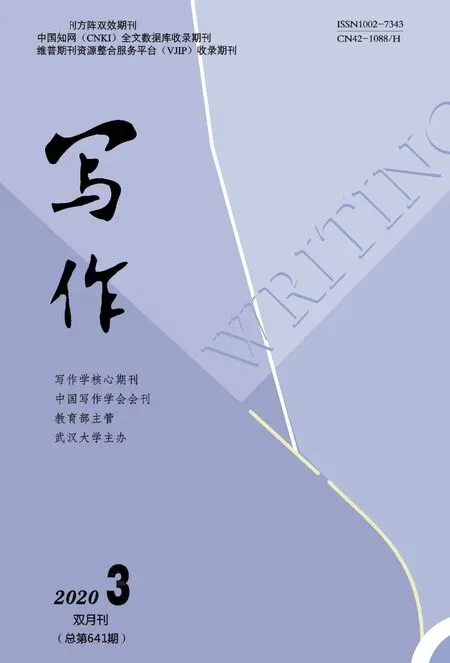“把握住他者”与“重建整体”
——读达恩顿《屠猫狂欢》
唐小林
达恩顿被誉为“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专家之一”①[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他于196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曾和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共同主持史学与人类学的专题研究课,《屠猫狂欢》便是从那门课发展而来的。《屠猫狂欢》展示出达恩顿对人类学化历史的研究兴趣,他将这项研究看成是“一项看来冒险有加的写作计划”②[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页。。这种“冒险”性体现在研究方法、理论视野与历史关怀等多个方面。他对“自下而上”不同阶层的文本个案进行研究,涉及18世纪法国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多个维度,最终试图“探讨十八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③[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页。。达恩顿由此展示出超越新文化史学的一般研究范式,并尝试对历史进行总体性理解的努力。
《屠猫狂欢》属于心态史研究。事实上,达恩顿在1968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采取的便是心态史研究路数。他提出这本书的“大目标”是“旨在考察大革命前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心态,看看他们的世界在被大革命颠覆之前是什么样子的”④[美]罗伯特·达恩顿:《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周小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如果说在《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中类似科学期刊、宣传手册和私人信件等零散的材料还只是达恩顿描述历史所利用的线索,那么他在《屠猫狂欢》中则更加注重对材料本身的“阅读”,某种意义上走的是文学研究的路径,只不过他的阅读对象是警察的报告手稿、农民版的童话故事,甚至是一份私人的购书单等。他尝试通过对材料个案的阅读与诠释,勾勒出历史的丰富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屠猫狂欢》显示出人类学视角下的阅读形态,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说:“阅读的概念乃是串连所有篇章的一贯之道,因为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①[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325、9页。对达恩顿而言,他在《屠猫狂欢》中所进行的探究性工作,是通过文本阅读来观察18世纪法国“自下而上”各阶层的人如何看待并阐明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讨论他们如何感知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的变更,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与认知。达恩顿通过阅读与诠释来理解一个异己的文化,以“把握住他者”的方式来重建讨论18世纪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参照谱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屠猫狂欢》为我们作出了一种独特但颇具可操作性的“跨学科”式的“阅读—诠释”的研究示范。
一、探索文本中的幽暗处与进入陌生心灵
《屠猫狂欢》分为六章,分别涉及农民、工人、资产阶级、警探、哲学家和读者等社会群体。尽管各章的内容看似关联性不大,但背后却隐含着达恩顿的总体性视野,即试图以“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通过描绘这些群体的精神世界与价值观念,呈现出以往有关18世纪法国史研究中未能显影的部分。正因如此,《屠猫狂欢》中所选取的文本个案都是“最为暧昧难懂的材料”。达恩顿追问的是诸如农民版的小红帽故事为什么充满了暴力和非理性的因素,杀猫对当时的工人来说为什么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等问题。正是因为“暧昧难懂”,这类材料才鲜明地显示出历史与当下的差异,而理解其他文化的这种异己性质,便有可能使自己的研究脱离一般的现象描述,从而寻找到理解历史的新方式。用达恩顿自己的话来说,他之所以选取这些特别的材料,是因为这些材料背后存在着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意义系统,因此“把握住他者”、理解这些异己的文化的最佳途径是“探索文本中的幽暗处”。他认为“探索途中最让人给予厚望的时刻可能最令人感到困惑。碰上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或许就是撞上了进入陌生心灵的有效切入点”②[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325、9页。。
达恩顿自言,他所阅读的这些文本“不可能拿来代表十八世纪的思想,当作敲门砖却绰绰有余”③[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325、9页。。由此看来,达恩顿无意再去阐释抽象哲学观念本身的含义,而是试图站在18世纪法国社会中寻常人的立场,去观察他们思考和组织现实的途径,以及他们理解自身所处世界的方式。达恩顿充分重视以往宏大历史叙述中不那么受关注的面向,通过对这些面向的梳理与理解,试图重新激活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空间。
达恩顿认为,实现他历史研究目标的最佳方式是理解寻常人的“市井之道”。他特别赞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即“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用抽象的概念来思考”,而是“以具体之物进行思考”,所谓思想就是“具体之物的科学”④[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达恩顿在“具体之物的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出“市井之道”的观点,关注寻常人如何生成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也是达恩顿理解历史与展开具体研究的重要前提。今天人们的思考与感受方式已经受到过诸多观念价值的重新塑造,几个世纪以前人们的思考方式可能已经外在于我们当下的认知框架,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认识这些陌生的世界观,是达恩顿处理的核心问题。
《屠猫狂欢》首先启发我们思考所谓“心态史”研究的可能性问题。达恩顿质疑法国年鉴学派的三大假定,认为他们“以计算来衡量心态”的研究方式并不能真正观照到社会变迁背后的“心态”层面,而所谓“心态”问题往往关乎文化客体如何被制造出来,文化意义如何表达自身等。他强调“探索文本中的幽暗处”,主张以此来代替“计算”,而文化及其关联的世界观,要通过解读才能揭示出来。达恩顿对法国年鉴学派研究方式的反思,为他在《屠猫狂欢》中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参照系,展示出某种超越性的史学研究视野。
达恩顿以“进入陌生心灵”来进行历史研究的方式具有一定“浪漫化”的特点。他的基本前提是过去人们的具体处境、另一种文化和经验世界,是可以被理解、认知和重新感受的,因此“心态史”研究必然包含着想象与建构的成分。达恩顿在《屠猫狂欢》中的“心态史”研究无意颠覆已有的对18世纪法国历史的认识,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他找到了18世纪法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与当时人们“心态”的结合点,并从中看到18世纪法国人如何思考现实并表达自身。从这个意义上看,《屠猫狂欢》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也在于它提示我们要关注理解一种文化的角度与视野,并从中找到打开历史褶皱并进入历史深处的途径。
二、历史学家如何了解这样的一个世界?
《屠猫狂欢》的第一章“农民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使用的材料来自德拉吕和特内兹合编的三册《法国民间故事集》。他举出《小红帽》原始的农民版本,关注这个原始版本中包含着的非理性成分,思考为何我们的祖先会用这样一个充满暴力与性因素的故事来哄自己的孩子睡觉。进言之,达恩顿思考的是18世纪的法国人为何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以象征的方式来掩饰自己要传递的信息,而是赤裸裸地描述一个阴森森的野蛮世界?归根结底,达恩顿在这章提出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历史学家如何了解这样的一个世界?”①[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3、70、4、168、169页。
事实上,这也是全书关注的核心话题,即今天的历史学家如何了解18世纪的法国,如何通过理解当时的法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和表达去生成一个新的历史认知图景。因此,达恩顿重读鹅妈妈的故事,指出这些故事中非理性内容中的写实成分,并不是为了重新印证社会史学家们已经考证过的近代法国初期农民残酷的生存状况。达恩顿重读农民版鹅妈妈的故事的真正关怀,是为了重新理解近代法国初期的农民和他们的心理世界,从中发现旧制度时期“农民社会的热情、价值、兴趣与态度”②[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3、70、4、168、169页。这类属于心态范畴内容的变化。他试图用这样的研究表明,社会历史的变迁与人类心态之间有着诸多幽微而绵延的关联点,今天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依然可以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到答案。
达恩顿在 《屠猫狂欢》的修订版序言中提出,“历史无非是要理解别人如何理解人类所处的情境”③[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3、70、4、168、169页。。因此,在第二章《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狂欢》中,达恩顿研究的重点便是要掌握对猫展开大屠杀的笑点所在,分析的是工人如何通过一种通俗仪式传达他们的世界观;第三章《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关心的是“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如何阅读旧制度之下的城市”④[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3、70、4、168、169页。。达恩顿通过对一个中产阶级市民所写的《1768年所见蒙彼利埃市现况》的解读,揭示出“对于现实的认知,它塑造了现实本身,而且即将形塑随后百年的法国历史,那一百年不只是马克思而且也是巴尔扎克的世纪”⑤[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3、70、4、168、169页。,为我们重新认识观念、民众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第四章《警探整理他的档案:文坛解剖》,将一个警察的报告手稿中的作家“纪事”,当作有意义的故事来解读,试图通过破解警察和他所监看的这些文人所共享的“符码”与“预设立场”,来呈现知识分子群体在法国兴起的历史线索。如果《屠猫狂欢》中这些被解读的文本可以看作是折射当时社会文化的镜子,那达恩顿的兴趣绝不止于从镜中窥探过去社会文化的一般面貌,他更关心的是这些镜子本身选择何种方式,以及为何是“这种”方式来再现现实。达恩顿并非遵循观念逻辑的线索来寻找其中的关联,而是考察一种意义表达的生成过程与传达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对历史进行重新理解。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达恩顿在《屠猫狂欢》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要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在他的理解中,书籍和阅读构成了认知生成、观念沟通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达恩顿从阅读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读者对卢梭作品的接受和反应,勾勒出过去人们的阅读经验和方式。达恩顿在这章特别强调,“阅读的卢梭主义变体应该视为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而且不应该跟目前的阅读混为一谈,因为旧制度的读者住在一个当今几乎想也想不到的心灵世界”①[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08、262页。。通过分析《新爱洛漪丝》的两篇序文,达恩顿发现卢梭在引导读者如何阅读他的小说,在这个过程中他重塑了阅读的功能。达恩顿认为阅读是在“沟通体系之内积极进行意义的整合”②[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08、262页。,而卢梭和他的读者共同落实了沟通模式的变化。借助阅读史的视角,达恩顿发现卢梭的思想如何渗透到读者的日常世界,以及旧制度读者感受人生的方式如何通过阅读而发生改变。
达恩顿的这种研究路径,为我们理解作者、文本、读者与现实四个层面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然而,从一个普通读者的书单、信件与作者的序言之间建构起意义的桥梁,并从中窥探一个正在变动着的社会结构和沟通模式,这种做法多少有些“冒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通过历史诠释得到的开放性结论是否足够使人信服,是否还可以得到另一种结论?达恩顿未必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因此他在每章之后都附上自己所“细读”的原始文本。有论者指出这种有意的安排,“充分体现了他将《屠猫记》一书所作的研究作为一项实验性的探索,更多的是强调方法和手段,而并不强求读者在结论上同作者达成完全的一致”③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但无法否认的是,在达恩顿的研究视野中预设了诸多认知前提,这些前提“预示”了他的结论。如达恩顿相信人和现实世界之间通过意义的建构能够获得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动,同时也有其延绵的一面,而通过历史研究可以揭示出这种复杂暧昧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达恩顿强调要“理解别人如何理解人类所处的情境”,其实就是要理解别人如何与他们所处的现实建立起关联,理解他们如何为了认识和应对现实社会而建构起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意义世界。
三、“重建整体,重建全部的内在关联”的方式
如果说达恩顿在《屠猫狂欢》以及他的其他研究著作中有某种贯穿性关怀的话,那么首先体现在他始终对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这类经典问题的关注。他认为对18世纪法国的研究,要“重建整体,重建全部的内在关联”,以此来重新理解“旧制度分崩离析和大量的革命能量在1789年被释放出来的方式”④[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19页。。《屠猫狂欢》所选取的材料或许如达恩顿自己所言不那么具有“典型性”,但他聚焦各个阶层的社会群体,“自下而上”最终进入启蒙运动的研究领域,则不得不说是一种有意味的安排,背后隐含着“重建整体”的意图。达恩顿颇具独创性的解读,其实并没有跟以往有关启蒙运动的研究相冲突,他“更没有想要揭穿哲人的观念或者是一般而论的观念”⑤[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19页。。在《屠猫狂欢》中,尽管他选择的都是个性化的文本,但是他的解读依然建立在已有的认知范式基础上,他并不质疑启蒙运动思想与观念的经典论说,而是在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开拓他的研究思路。因此,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达恩顿在《屠猫狂欢》中试图对18世纪法国社会作出某种总体性描述的尝试,那么他通过阅读与诠释这类“暧昧难懂的材料”,最终能否生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历史图景,能否真正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认知方式?
达恩顿强调寻常人的观念和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但他们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层又一层的塑造,达恩顿试图揭示出其中复杂的“传播”图景。从这个角度来说,《屠猫狂欢》也体现了达恩顿历史研究的抱负。尽管他在《屠猫狂欢》中选择的是“心态史”的研究方式,但这依然内在于他所谓的“观念的社会史”视野中,最终要探索的是“观念在旧制度下的社会中旅行并‘生根发芽’的方式”①[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达恩顿深受人类学观点的影响。人类学家认为,要“把握住他者”,需要有一个提前性的假定,即“象征是共享”②[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22、323、323、324页。的。在达恩顿的研究视野中,“象征”显示出个人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以“意义系统”呈现出来。因此,他在《屠猫狂欢》中选取的这些“暧昧难懂的材料”,其实鲜明地凸显出了另一个有别于我们当下的“意义系统”,达恩顿所做的便是通过文本诠释的方式,将这个“意义系统”勾勒并呈现出来。历史文本所包含的各种符号、仪式影射着这些文化信息,而《屠猫狂欢》关注的“思考方式”本身也关乎“象征”如何形成、怎样对现实发挥作用的问题。正如他通过工人的屠猫仪式发现了其中隐藏的信息,这些仪式本身意味着一整套传达方式的形成。文本诠释的工作依赖于社会文化的象征系统,正如达恩顿所言,“我们再也犯不着牵强附会探究文献如何‘反映’其社会环境,因为那些文献全都嵌在既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③[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22、323、323、324页。。
达恩顿尝试通过《屠猫狂欢》的研究来“重组两个世纪以前解体了的象征世界”④[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22、323、323、324页。,他的研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意义何在等根本性问题。达恩顿深受格尔茨“深描”理论的影响。格尔茨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⑤[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29页。。格尔茨借助吉尔伯特·赖尔有关“深描”的讨论,发展出自己的“深描”理论,强调意义诠释的方法,“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⑥[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29页。。事实上,达恩顿在《屠猫狂欢》中展开的便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的工作,同时借助“意义系统”“象征世界”等中介,尝试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启蒙运动这类问题进行一种系统性的研究。从达恩顿的研究脉络来看,近年来他更加注重书籍史、阅读史领域的研究,从“传播”的层面来破除从观念到观念的固化认知模式,最终致力于描述并重建一个具有整体感的文化系统。他从自己的研究对象法国大革命的传播方式中获得新的启发,认为要实现对一种文化的理解,必须要“重建整体,重建全部的内在关联”。这不仅是指包括“观念旅行”在内的传播体系,也指的是一种理解文化、认识历史的整体性视野。《屠猫狂欢》的写作包含着这样的研究抱负,他对各个阶层、群体的关注,将人类学与历史学进行结合,以及从文本诠释到意义系统的揭示,无不在试图以一种“敲门砖”的方式重组并激活一个过去的具有整体感的象征世界。但令人不满足的地方或许在于,不论是第一章重读鹅妈妈的故事,还是最后一章对阅读经验的讨论,达恩顿重启了历史进程中那些“陌生心灵”的丰富世界,但却未能生成一个新的历史认知图景,尚未通过这种“个案”研究找到通往整体性历史理解的道路。
余论
达恩顿这类研究观念、方法以及视野,曾在历史研究学界引起过争议,这些“争议”甚至在1998年还集结为《达恩顿之争》一书。事实上,达恩顿也意识到自己“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这两方面的难题”⑦[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22、323、323、324页。。他展开研究的大部分文献材料都来自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以这部分有限的资料来进行研究,难免使自己的视野受到局限。达恩顿在《阅读的历史》中指出:“书籍历史学家早就挖出大量阅读的外在历史信息。他们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解答很多关于‘是谁’、‘读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的问题,这有助于回答更困难的‘为什么’及‘如何做到’等问题”①[美]罗伯特·达恩顿:《阅读的历史》,《新史学》第4辑,陈恒、耿相新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因此,他努力寻找的是关于“为什么”以及“如何做到”的理解,更加关注接受观念的一方的认知方式和心态变化。达恩顿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具体论证,以诠释建构的方式来处理他所关注到的文本,因此《屠猫狂欢》这类研究也呈现出较多的“文学趣味”。
达恩顿“观念旅行”的研究路径,重点落实在“旅行”上面,而对“观念”本身并未作出重新解释。“旅行”关乎的是传播问题,本身是一种重新连接、打通“上下”的整体建构的尝试。但同时,《屠猫狂欢》中各章的研究都体现出相似的思路,也就是将文本个案尽可能地放在一个经过严谨考证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展开阅读,这些文本个案与已有的社会历史文献形成了某种“互文性”关系。达恩顿基于此来把握某种历史根源性的东西,试图更深入地对历史进行描述,但背后其实依然隐约可见史学家和哲学家们所建立起来的既有历史认知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达恩顿展开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开拓性意义和局限性都鲜明地凸显了出来。
在达恩顿的历史研究视野中,“大写的‘真’(Truth)是一个让历史学家们不太自在的词,似乎它带有实证主义或者某种形而上学的意味”②[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03页。。因此他提出以小写的“真(truth)”来回答某些历史问题,并从中获得有意义的理解。他的这种研究志趣深受人类学家的“移情”观念的影响。达恩顿认为各个文化体系具有特殊性,如果要实现对另一个文化的有效理解,则应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研究:“就每一个文字作品体系自身、并从亲身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它,而不是以像是经济学家所偏好的某种共同的外在标准来对它加以考量。”③[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03页。因此,他更加关注寻常人的思考方式,以及观念形成的过程。但是他基于大写的“真”(Truth)而提出的小写的“真”(truth)的研究路径,依然受限于二元化的框架。因此,他在《屠猫狂欢》中所“深描”的这些文本个案,最终的诠释结论几乎都必须依赖所谓大写的“真”(Truth)来印证。尽管达恩顿的个案诠释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颇具启发性,但他的最终结论依然内在于现有的历史认知框架中。他所特别重视的小写的“真”(truth)尚未能生成新的理解18世纪法国史的认知方式,依托于文本个案诠释的历史谱系因此也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在达恩顿以及其他新文化史研究者那里,如何在历史研究中“重建整体”依然是一个待被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