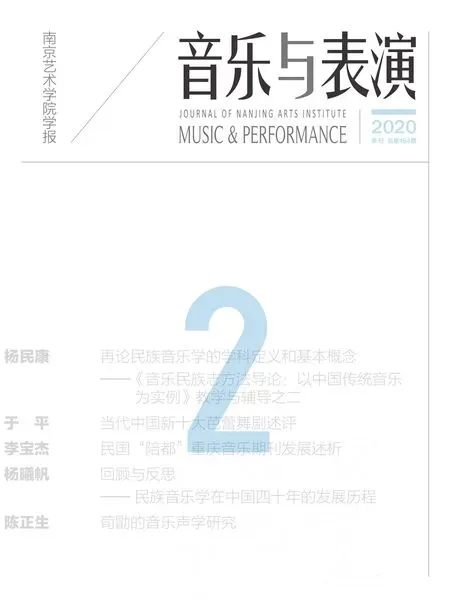如画的舞台
—— 论“日本主义”对日本巡演剧团在20世纪早期西方的受容的塑造
高 洋(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200040)
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30 年代,先后有三个日本剧团在美国和欧洲诸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巡演活动。在整个海外巡演期间,这些剧团的舞台表演不断掀起轰动性的热潮并激发了从普通观众到艺术界人士在内的广泛的西方公众的热烈讨论和品评。
1899 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戏剧剧团①早在幕末时期,就陆续有一些日本人组建的剧团前往西方世界进行舞台表演。但是这些日本剧团的成员并不是来自戏剧界,而是杂技演员。关于日本杂技团的海外巡演情况的详细信息,参看宮岡謙二.異国遍路芸人始末書[M].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78; 宮永孝.海を渡った幕末の曲芸団:高野広八の米欧漫遊記[M].東京: 中央公論新社, 1999; 三原文.日本人登場:西洋劇場で演じられた江戸の見世物[M].東京:松柏社, 2008.踏上了前往西方巡演的征程。这个剧团的创建与领导者是日本的著名新派剧②“新派”(shimpa)这个词通常指代的是从19世纪末起陆续出现在日本的一系列致力于西化改良的新型现代戏剧样式。与这个词汇相对应的是“旧派”(kyūha)一词,它被一些日本现代戏剧人用来指称作为日本传统戏剧样式代表的歌舞伎。演员川上音二郎(1864—1911)。川上音二郎的妻子川上贞(1871—1946)——以艺名“贞奴(Sada Yacco)”闻名于西方,是这个剧团的另一名核心成员。可以说,川上剧团能够在西方巡演的所到之处受到观众们的狂热青睐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贞奴在舞台上的卓越演技。
时间来到1902 年,当川上剧团于这一年完成了他们第二轮的海外巡演时,③川上剧团先后进行了两轮海外巡演。第一轮巡演始于1899年5月,先在美国的旧金山、西雅图、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纽约等地巡演,然后于1900年4月前往欧洲,先后在伦敦和巴黎进行演出,最后于1901年1月返回日本。第二轮巡演开始于1901年4月,第一站是伦敦,然后前往巴黎,继而在波兰、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等东欧国家的城市中演出。1902年3月川上剧团进入俄国,先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演出。俄国巡演后,川上剧团前往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演出。1908年8月川上剧团结束第二轮海外巡演回到日本。一个娇小的日本女人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个本名叫太田久(1868-1946)却以艺名“花子”(Hanako)被人所称道的女人与她的演员同伴们所组建的剧团进行了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都跨度极大的西方巡演之旅。花子演艺生涯的几乎全部时间都挥洒在了西方世界的舞台上,让那里的观众为其如痴如醉超过了十五个年头之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花子的存在是她的剧团得以建立并在西方世界取得巨大成功的唯一基石。
1930 年,在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沉寂之后,另一个日本戏剧团在演员筒井德二郎(1881-1953)的带领下开启了新一波的海外巡演之旅。自从花子于1921 年结束了其海外演出事业返回日本后,西方世界一直热烈期盼着能有机会再次一睹由日本人所组建的剧团所带来的日本舞台艺术。因此,筒井剧团在西方舞台上的出现可以说适时地维持与促进了由川上剧团与花子剧团所开创的日本戏剧演出在西方世界传播的潮流。
鉴于上述三个日本剧团在西方世界的巡演横跨了巨大的时间与空间范围,能够接触到他们的巡演活动的西方观众必然在阶层、职业、教育程度、经济状况以及艺术鉴赏能力等方面有着很丰富多样的构成。尽管如此,在西方公众对于日本巡演剧团的受容中似乎又潜藏着一种共通的认知构造,而这种认知构造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日本主义”(Japonisme)——一种从19 世纪中叶开始就席卷西方世界的文化艺术热潮——所规定和塑造的。
正如戏剧学者苏珊·班尼特(Susan Bennett)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标识……指定与支持了戏剧在一个特定社会的存在方式”。[1]作为一种在西方世界勃兴并长久存续的社会文化现象,“日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标识”(cultural marker),它深刻地形塑与影响了西方公众对于日本文化与艺术的认知心态与模式,而这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西方公众对于上述三个日本巡演剧团的受容方式。诚如萨义德所言,西方对东方的表象不是“作为对东方的‘自然’描写”,而是一种强加于东方的外在性与想象性的表述;在这里,重要的既“不是表述的正确性,也不是其逼真性”,而是一系列诸如“风格、修辞、置景、叙述技巧”[2]式的表象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主义”对于日本文化与艺术的外部性表述自然与日本的现实情况拉开了距离:西方世界中所流行的与日本相关的文化与艺术意象只有通过那些借助于“日本主义”所提供的各种表象技巧所进行的想象性论述才能得以彰显。就像萨义德所指出的,“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负担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2]可以说,尽管日本巡演剧团在整个海外公演的过程中总是试图将他们的演出打造成一种对于日本固有戏剧文化的自我表述,他们仍会发现自己有时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到一种可以称之为“自我异国情调化”(self-exoticization)的尴尬境地中。而日本巡演剧团利用这种“自我异国情调化”来修正与修饰对日本的戏剧性表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要服从与迎合“日本主义”在西方人的思维中所培植的认知框架。
有鉴于此,探究“日本主义”如何形塑与规定了西方公众对日本巡演剧团的受容模式与特征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首先必须要对“日本主义”这一文化现象在西方社会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一种历史性的回溯考察。
一、“日本主义”在西方的流变
“日本主义”这个概念最早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法国艺术评论家菲利普·布尔蒂(Philippe Burty,1830-1890)。布尔蒂于1872 年在艺术杂志《文学与艺术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首次创制了“Japonisme”这个词汇来指代“对于日本的美术与天才的研究”。[3]作为一名有重要影响力的日本美术工艺品的收藏者与推介者,布尔蒂与法国内外的西方艺术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关联。正因为如此,他创造的这个特定的法语词汇后来很快地被接受为一种通行的术语,用以指代日本美术与手工艺的各种样式在欧洲受到的狂热青睐与追捧以及其对于欧洲艺术发展的巨大影响。①法语“Japonisme”一词在其他欧洲语言中有一系列的对应词汇。例如德语中的“Japonismus”和英语中的“Japonism”或“Japanism”。但是,在整个西方的文化书写语境中,“Japonisme”得到了最普遍的使用,即使在英语国家其使用频率也要远高于“Japonism”或“Japanism”。参看川添優.日本人になってみる、日本をやってみる[C]//演劇のジャポニスム.神山彰, 編.東京:森話社, 2017: 37.
“Japonisme”这个词语的创制缘起清楚地揭示了“日本主义”一开始乃是美术领域内的一种日本文化现象,它既包含绘画与雕塑这样的“纯美术”(pure arts)体裁,也囊括诸如陶器、瓷器、漆器以及室内装饰这样的手工艺美术形式。②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出版于“Japonisme”这个词汇诞生后没多久的一些法语词典对于此词条的解释中。例如,在出版于1877年的《十九世纪环宇大词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的第一扩展版中,“日本主义”被定义为“对于日本事物的美术装饰性的探究”。在其1890年出版的第二扩展版中,“日本主义”被理解成一种对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美术领域的喜爱与追求。转引自寺本敬子.パリ万国博覧会とジャポニスムの誕生[M].京都:思文閣出版, 2017: 210.当然,随着“日本主义”这一文化现象在西方世界的展开与演化,在更广的涵义上“日本主义”已经不能仅仅被局限在美术这一范畴内,其意涵的外延已经在不断的进化中得到极大的拓展。事实上,正如美国艺术史学者加布里埃尔·韦斯伯格(Gabriel P. Weisberg)所指出的,“日本主义”的存在形态可以说是“无穷尽的” (inexhaustible),因为“对所有日本事物的鉴赏”都可以被纳入到“日本主义”的范畴中。[4]日本美术史学者高阶秀尔同样认为在形式、内容、风格、技巧、主题与动机等方面存在着“多元日本主义”。[5]在其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主义”在各个文化层面都保持一种强劲的扩张势头,快速地从美术领域扩展到建筑、音乐、服装时尚和文学等的领地之中。在地理空间上,“日本主义”从其起源地法国首先播散到西欧各国(英、德、奥、西、荷、意等),进而进入北欧诸国与中东欧(捷克、波兰与俄国),然后跨过大西洋直抵新大陆。在受众上,从精英文化人与知识人(艺术家、美术收藏家、日本学家等)到一般普罗大众,可以说西方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沉浸在“日本主义”所酝酿的对于日本文化与艺术的狂热迷恋氛围中。
尽管“日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演进历程中已经在内涵与表现形态上变得极为丰富多元,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主义”这一文化现象的最核心构成仍然是日本美术的传播与受容。从19 世纪后半叶开始,在西方公众,特别是艺术家与文化人的圈子中兴盛的对于各种样式的日本美术工艺品(浮世绘乃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的收藏、展示与鉴赏在当时西方人的思维结构中潜移默化地培植了一种强有力的认知日本文化与艺术的美术视角。即使时至今日,这种美术视角在对“日本主义”的定义、理解与研究上仍然是最经典的评价准则。①例如,在2000年后出版的日本词典,比如《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2001年)、《大辞林》第八版(2006年)、《广辞苑》第六版(2008年)所收录的“日本主义”(日语:ジャポニスム)词条中,“日本主义”仍然被狭义地定义为对于日本美术的收藏与鉴赏趣味以及特定的日本美术样式对诸如新印象派与拉斐尔前派等欧洲近代艺术思潮与运动的影响。参看川添優.日本人になってみる、日本をやってみる[C]//演劇のジャポニスム.神山彰, 編.東京:森話社, 2017: 36.在川上剧团于19、20 世纪之交开始海外巡演旅程之前,“日本主义”的热潮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席卷多年并在19 世纪晚期达到其热度的最顶点。在某种意义上, “日本主义”通过形塑和规定西方人理解与认知日本文化与艺术的方式与视点为日本巡演剧团在西方舞台上的出现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文化与社会土壤。因此,当西方公众第一次接触到由日本巡演剧团所带来的日本舞台艺术时,由于对这种全新而陌生的戏剧上演形式在感性上的猎奇以及理性上的知识匮乏,由“日本主义”在西方公众的认知构造中所培育的关于日本文化与艺术的美术视角似乎便成为了他们理解与评价日本剧团的巡演活动的唯一标准。
二、“日本主义”所孕育的美术视角
如果历史地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戏剧与美术在西方文化中有着很亲密的关系。英国学者安吉莉卡·古登(Angelica Goodden)认为在西方的历史上,戏剧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发展的时期总是与那些重视“现实的艺术视觉化”的时期相重合。[6]39相较于文学这样的,主要是诉诸于读者的内在的情绪、思想与情感的语言艺术所具有的间接性,以绘画为代表的视觉艺术由于能通过形象直接作用于观者的视觉感官,因而被认为更具有艺术感染力。[7]在这个意义上,戏剧艺术——特别是当以演员的身体表象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时,便具备了一种能与绘画的视觉效果相媲美的“视觉奇观性”(visual spectacularity)。②例如,17世纪的法国画家查尔斯·迪弗雷纳(Charles Dufresnoy,1611-1668)在其题为《论图像艺术》(De art graphica)的著作中讨论了哑剧表演者的身体姿势与绘画表现之间的相似性。参看アンジェリカ·グデン(Godden, Angelica).演劇·絵画·弁論術: 一八世紀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パフォーマンスの理論と芸術[M].譲原晶子,译.つくば: 筑波出版会, 2017: 103.除了身体表现,戏剧的“如画性”(picturesque quality)同样体现在服装③古登指出要求绘画中的人物穿戴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相符的服饰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新古典主义戏剧的演出中对角色戏服的历史准确性的追求。同上书。与舞台装置上;后者(舞台装置)则生动地反映了绘画艺术与戏剧演出在时空构成上的亲缘性。④正如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1922-1998)所指出的那样,“绘画与戏剧的相似性首先体现在通过对艺术造型的有意识地的视觉表达来组织场面这一点上。这是因为舞台文本的展开并不是一种模仿非艺术世界中的时间流动的连续流,而是一个整体;它可以被清晰地分解成一系列被共时地加以组织的单个‘静态’(stills),每一个‘静态’就像一幅画被镶嵌到画框中那样被置于到布景之中”。Yuri M. Lotman, Boris A. Uspensky. Type of Culture [M]. Milan: Bompiani, 1973: 278.事实上,绘画艺术在空间构成上的诸多理论长久以来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戏剧演出的舞台布景设计之中。这一点生动地体现在写实主义戏剧演出中的幻觉式舞台布景的设计理念上。⑤正如英国戏剧学者基尔·伊拉姆(Keir Elam)所指出的那样,在写实主义的布景设计上,“采用透视法的绘画被加以使用,以此来试图幻觉式地复原丢失的空间深度,并因此创造了一种奇特的‘元模拟’(meta-mimetic)游戏。这场游戏之中,三维的空间被一种伪装成三维空间的二维空间所伪装”。Keir Elam. The Semiotics of Theatre and Drama [M]. London: Methuen, 1980: 61.由于戏剧与绘画之间的这种鲜明的可类比性,历史上曾有西方戏剧演员通过研究绘画作品中人物的神态举止来打磨和改良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通过模仿这些画中人物的身体仪态,这些演员试图营造出某些经典绘画作品中的场景在舞台上“活起来”(come to life)的幻觉效果。[6]106-110反过来讲,绘画艺术的世界中同样可见戏剧式的隐喻。①举例来说,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出席在沙龙举办的画展被称为“逛剧院”,而画家则被比作“演员”。参看アンジェリカ·グデン(Godden, Angelica).演劇·絵画·弁論術: 一八世紀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パフォーマンスの理論と芸術[M].譲原晶子,译.つくば: 筑波出版会, 2017: 110-112.
鉴于西方文化传统中戏剧与美术之间的这种亲和性,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日本主义”所营造的对于日本美术工艺品的狂热爱慕的文化氛围下,西方公众在日本戏剧与日本美术之间想象出一种亲密的关联性就是一件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通过比较日本戏剧的假定性特征与日本美术的美学特性,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将日本戏剧的风格特征与日本美术的风格特征进行关联是一种……欧洲评论家在分析(川上)剧团的演出时频繁援引的类比。” Shelley C. Berg. “Sada Yacco: The American Tour, 1899-1900” [J]. Dance Chronicle, 1993 (16.2): 187.一些西方人似乎在表现原则方面在日本戏剧与日本美术之间找到了一种共同的基础。例如,英国评论家凯瑟琳·鲁夫(Katherine Roof)认为,日本美术所传达的乃是事物的本质,而不仅仅是模仿“生活的表象”,这是因为,“一位日本美术家所表现的菊花是菊花的精神与灵魂,因而显得无限真实而又极有灵性”。[8]6在鲁夫看来,川上剧团演员的表演借助于“克制与冷静的情感表现”,同样可以在舞台上传递登场人物的精神实质。[8]10
在日本美术的所有体裁中,浮世绘木版画被西方人认为是与日本戏剧有着最强类比性的美术形式。有学者指出,尽管绝大多数的西方浮世绘爱好者从来没有到过日本,但是他们中的一些却似乎能够对日本戏剧有比较准确的认识,究其原因在于,这些西方人所具备的关于浮世绘版画的抽象表现的知识能够让他们比较容易地理解日本戏剧的样式化演技特征。[9]这种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将浮世绘与日本戏剧进行类比的现象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大量以歌舞伎演员为主题的浮世绘作品流入西方市场的缘故。这些浮世绘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无疑是由充满神秘色彩的日本浮世绘画师东洲斋写乐所创作的一系列描绘著名歌舞伎演员的肖像画作品。某种意义上,这些盛行于西方的,以歌舞伎演员为主题的浮世绘作品极大地塑造与强化了西方公众对于日本巡演剧团演员的个人与艺术形象的“如画性”的认知。
当川上剧团于1900 年在巴黎世博会期间进行公演时,“日本文化(在法国)主要是由浮世绘和字画挂轴这样的日本美术品所表象的。鉴于‘日本主义’已经在这里酝酿多时,对于日本戏剧的评价必然要建立在它的影响之上”。[10]法国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一个孤例,可以说整个西方在19 世纪末20 世纪早期都浸染在由“日本主义”培育的这种以美术视角认知日本戏剧的历史与文化氛围中。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为数众多的西方评论家会把自己对于日本巡演剧团的论述与评价建立在与日本美术有关的各种意象与词汇的基础上。
总体上来说,西方评论家普遍认为,可以在日本巡演剧团的演出中发现日本美术很深的影响痕迹。举例来说,有人在评述筒井剧团的表演时感叹:“日本的绘画艺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戏剧技巧施加了强烈的影响”。[11]5苏格兰戏剧评论家威廉·阿彻(William Archer,1856-1925)认为,川上剧团的表演浸染了“他们自己国家的绘画艺术的优雅与精致,以及时常表露出来的生动活力”。[12]一些评论家则倾向于将这些日本巡演剧团的舞台演出视为对日本美术的一种戏剧化的表征。例如有评论家就认为,川上剧团的舞台作品“实现了浮世绘彩色版画为我们所编织的梦想”。[13]
更具体而言,这种与日本美术相关联的视角在各个层面上浸润到了西方人对于日本巡演剧团的认知之中。首先,在表演者个人形象的层面上,日本巡演剧团的演员经常被视为日本美术的“活化身”(living incarnation)。在一些西方评论家的眼中,这些日本演员在舞台上展露的身体性特质以及每一个具体的姿态与动作都给人一种好像浮世绘版画或者其他日本美术工艺品中所表现的人物“活起来”的幻觉。例如,一位评论家曾经这样评价川上剧团的演员在舞台上的风貌:
他们的面部与喉咙被涂上一层充满死寂感与无法释怀感的石膏白,乌黑的头发以各种精巧的弧度与弯度悬在这些无表情的脸谱之上,步伐则缓慢而又流畅。这使得他们好似那些从平板的绘画中活起来的人物。[14]
在川上剧团的所有成员之中,贞奴可能是最频繁地被西方评论家拿来和日本美术的各种意象作对比的人物。在这些评论家的比喻里,贞奴时而是“从一把日本扇子或一个日本陶壶中移植下来的一抹印花”;[15]时而是“一只活的日本瓷器”;[16]有时又变成了“画中所描绘的艺伎的活的复制品”。[17]就花子剧团的演员而言,一名评论家认为,这些表演者的面部酷似“东方世界的扇子、花瓶与屏风中的人物面庞……只不过之前不曾见到它们活过来的样子”。[18]另一名评论家则将花子剧团的演员称为“活的萨摩烧①萨摩烧是一种日本著名的代表性瓷器,发源于九州南部的萨摩藩。”,其表演给人以“画在一只花瓶上的正在寻找看不见的仇敌的狂怒武士已经活了过来”[19]的印象。与贞奴的情况相似,在花子剧团中,花子本人被认为是最具美术性色彩的人物。有评论家称她“呼吸着日本扇子与版画的精神,……就像艾莎道拉·邓肯②艾莎道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7-1927):美国著名女舞蹈家,现代舞(modern dance)的创始人。这名伟大的舞者是希腊陶瓶的活的体现那样,她用同样的方式诠释了北斋③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浮世绘画师。”。[20]即使花子在舞台下的姿态在某些评论者的眼中也散发着一种强烈的绘画性氛围。④例如,一名评论家评论道:“看看她的体态,她那精巧的小手,长而尖的指甲,贴放在前额上的手腕,这一切就像是在鉴赏一幅优雅的东方画卷”。 Authorless. “Madame Hanako —Tragedy Queen in Miniature: The Japanese Duse Explains Something of the Art which She Has Brought from Tokio to New York” [N]. New York Times, 1907-10-27 (10).至于筒井剧团,它的那些“如画的东方表演者”[21]则被视为“一系列活的日本版画”。[22]
其次,在舞台表演的层面上,日本巡演剧团演员的身体表现中所蕴含的样式化特征同样能激起西方观众对于日本美术的联想。例如,花子剧团演员的“传统姿态”(conventional gestures)被认为传递出一种“令人想起日本版画”[23]的感觉;这其中,花子的舞蹈“在每一个体态上都构成了对一幅日本版画的暗示”。[20]一位评论家则认为,筒井剧团演员的“装饰性”(decorative)演技“在舞台上永远是一幅画,一幅异常美丽的画,而且(至少在我们西方人的眼中)永远是一幅饶有兴味的画”。[24]除此之外,有些评论家在日本巡演剧团演出中的某些舞台调度与场面构成上也感受到了绘画效果。例如,有论者认为,贞奴在某些表现死亡的舞台场景中所展现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歇斯底里状态酷似东洲斋写乐的浮世绘作品;[25]另一名评论家则认为,川上剧团作品中那些伴随着贞奴所饰角色的死亡的最终场面可以与某些表现悲剧题材的浮世绘版画相仿佛。[26]在谈到筒井剧团演出中的武打场面时,一位评论家指出:“重要的是,在这些周而复始的打斗中,演员做出并维持的姿态以及持剑的角度乃是整体设计中的重要一环。这些群像与日本版画的强劲有力之间的相似性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11]4另一名论者则称,筒井剧团的舞台作品在场面调度上的整体效果是“一连串静止的图画”,它们令人联想到“那些广重⑤歌川广重(1797-1858):日本浮世绘画家。或者北斋创作的版画”。[27]
在演员的个人形象与表演之外,日本巡演剧团在演出中使用的舞台装置与戏服由于其所具有的华丽视角效果同样被西方人从日本美术的视角加以审视。例如,川上剧团在某些舞台作品中所使用的布景就被认为其“真实性与如画性就像日本美术那样令人愉悦和理想”;[28]有论者甚至认为,这些布景图“应该像普通画作那样被悬挂在画廊里”。[29]而花子剧团舞台布景的如画性则被认为,来源于“帷幔,其中有一些极为美丽,此外还有那些散布在各处的看似不起眼却极富效果的‘小道具’,诸如一株樱树或者一道篱笆”。[30]至于筒井剧团演员的戏服,有评论家认为,他们身披华丽服饰在舞台上的表演就好似“画中人物”一般;[31]这些“五彩的服装,在如画的背景的衬托下,给人一种日本版画活起来的感觉”。[32]
与一般公众与评论家不同,一些曾亲身见证过日本巡演剧团海外公演的西方戏剧人主要是从舞台实践的专业立场出发来理解与评价这些剧团的演出活动。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西方戏剧人同样会表露出一种以美术视角诠释这些剧团演出的倾向。例如,被誉为法国现代戏剧之父的著名导演安德烈·安托万(André Antoine,1858-1943)曾经在1900 年的巴黎世博会期间观看过川上剧团的表演。在谈到对贞奴在川上剧团的标志性舞台作品《艺伎与武士》(The Geisha and the Knight)中的表演的印象时,安托万称贞奴是“一名能让人联想到挂轴中的人物的女演员”。[33]另一名著名的法国戏剧导演雅克·科波(Jacques Copeau,1879-1948)则在与筒井德二郎的交谈中称赞筒井剧团的表演揭示了一种“如画的美感”,这种美感被科波认为是戏剧美学精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4]
在众多的西方戏剧人中,英国著名的戏剧导演与舞美设计家戈登·克雷(Edward Gordon Craig,1872-1966)对于贞奴和花子的表演的评论可以说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些西方戏剧人对于日本巡演剧团的受容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日本主义”培育的美术视角的影响。对于“日本主义”在西方的流行, 戈登·克雷似乎抱有一种警惕感。在他看来,“日本主义”通过煽动和满足人们对异国情调事物的猎奇欲望来实现其商业主义的功利目的,本质上具有一种极为浮躁与喧哗的氛围。在戈登·克雷眼中,贞奴和花子这样的日本女演员在西方舞台上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主义”带给日本戏剧的一种“创新”(innovation),但是这种“创新”的目的并不是以提高日本戏剧的艺术性为着眼点,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经济动机。[35]
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戈登·克雷其实与“日本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其青年时代,戈登·克雷就通过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1834-1903)这样的印象派画家接触到了以葛饰北斋为代表的日本浮世绘大师的作品并为之倾倒。戈登·克雷在其一生中曾经创作过众多的木版画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收录在他自己编辑的名为《册页》(The Page)的杂志上。日本版画在色彩、线条和构图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样式美与象征美给予了戈登·克雷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启发,并且鲜明地反映到了他日后的舞美设计中。相较于在日本美术领域所具有的丰富知识,在亲自去观看川上剧团在伦敦的演出之前,戈登·克雷实际上对日本戏剧的舞台呈现并没有第一手的直观认知,其关于能剧、文乐等日本传统戏剧样式的认知主要是间接地获取自西方学者和艺术家编纂或撰写的介绍性书籍。这种在日本美术和日本戏剧的知识结构上的不均衡使得戈登·克雷有时也和普通大众一样,不自觉地用看待日本美术作品的眼光来审视贞奴和花子的表演。例如,他就曾这样评价过花子的表演:“在日本绘画中,正如北斋所教导过我们的那样,形式与彩色完全不是靠一种人为的意图来实现的。北斋一定会非常憎恶花子(的表演)”。[36]这种基于绘画标准的评价方式很难说具有戏剧本体论层面上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结 论
曾经有研究者针对日本戏剧在19、20 世纪之交西方的传播特征发表过如下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许多在当时对日本戏剧抱有兴趣的重要人物,其关于日本戏剧的知识却是从一些对其所要“介绍”的戏剧样式完全不了解的信息源那里获得的。[37]
诚如斯言,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无论是在一般公众层面还是在戏剧艺术界,这种对日本戏剧的无知是普遍存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主义”孕育出的美术评价视角能够主导人们对于日本巡演剧团的认知与理解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评论家们常常惊讶于他们无法对贞奴的表演进行适当的归类……许多作者则试图通过与他们(至少略微)懂得多一点的视觉艺术形式进行关联来定义她”。[38]这就是说,受限于“日本主义”所孕育的美术认知视角的西方人始终对日本巡演剧团的表演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判断,在他们眼中,这些剧团的演出形象始终处在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中。
最终,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一般西方公众也好,还是像戈登·克雷这样的西方戏剧人也好,他们在“日本主义”这一文化语境下展开的对日本巡演剧团的受容过程中始终抱有这样一种认知心态,即他们并不是从戏剧艺术的本体论出发来对这些日本剧团的演出艺术水准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毋宁说,对一般大众和戏剧实践者两方而言,日本巡演剧团的表演始终体现的只是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他者性”(Otherness)。正是这种“他者性”充当了满足这些西方人东方主义式的猎奇心与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 而“日本主义”所建构的关于日本文化与艺术的认知想象无疑就是生产这些隐喻的强有力装置。[37]这便是这些日本巡演剧团站在西方舞台上时所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文化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