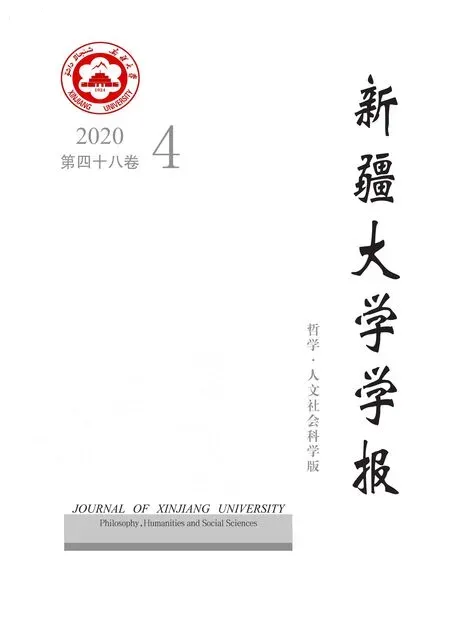文学友于·政治阋墻:论萧绎的“曹植情结”*
林宗毛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中古时期,文学是世族巩固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此期历史上涌现出众多拥有“家风”或“家学”的家族,南兰陵萧氏便是其中较著者之一。萧梁开创者萧衍及其子萧统、萧纲和萧绎凭借政坛优势入主文坛并成就斐然,此种情况在稍前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即建安时期的曹氏父子,正如林文月所云:“梁代萧氏父子、兄弟在文学史上与魏之曹氏父子、兄弟皆以政治的领导者兼具文坛之领导者地位,而且其宫廷文士集团的附庸唱和亦直追邺下风流。”[1]这样的巧合,南兰陵萧氏或早已发觉,因为就现存文献来看,萧衍父子都有过自比或被他人比做曹氏父子的记载。①仅就萧衍一人而论,正如曹道衡先生云:“萧衍以萧纲比曹植,萧续比曹彰,显然是比萧统为曹丕,比丁贵嫔为卞太后。”萧氏比附曹氏之风借此一例即知大概。参见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7页。在诸多萧氏比附曹氏的文献之中,萧纲和萧绎比附曹植的几条文献稍引注目,因其文献呈现了一个颇值细绎的矛盾。
一、“曹植之誉”的矛盾及成因
萧绎,生于南兰陵萧氏家族,萧氏在齐梁时期取得南方统治权的同时,也在文学上臻于鼎盛,尤其是萧衍及其子萧统、萧纲和萧绎,四人在文学史上享有“四萧”的美誉。“四萧”与前此的“三曹”旌旗相望,故时人就有将萧梁比于曹魏的意识,如吴均《赠别新林诗》云“但令寸心是,何须铜雀台”[2]1735,“铜雀台”典出曹氏,吴均以此比况萧梁,其用意已相当明显。此后的评论家更是多将“三曹”和“四萧”进行对比,如张溥云:“昭明简文同母令德,文学友于,曹子桓兄弟弗如也。”[3]209又赵翼云:“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魏父子固已旷绝百代。……至萧梁父子间,尤为独擅千古。”[4]曹操身为建安文坛和政坛的双重领袖,萧衍以其自诩固无争议,而曹丕身为曹氏嫡子且善于文学,亦非萧统不能比。因此,曹植和萧纲或萧绎的匹配自然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无论就文学成就或家族长幼而论,萧纲和萧绎都与曹植吻合,且就现存文献来看,萧纲和萧绎都有被时人比做“曹植”的记载,如《梁书·简文帝纪》载萧衍称赞萧纲为“吾家之东阿”,而萧纲《与湘东王书》则径称萧绎为“子建”。若从权威角度而论,萧衍评定的“曹植之誉”自当更具官方性,但是细揣萧纲得誉之由又不免使人觉得权威性评论背后的不足,因为萧衍仅仅是基于惊讶萧纲“早就”且“御前面试,辞采甚美”一事而下的评语,他的立论依据显然是《三国志·陈思王植传》中曹植为了证明自己的“善属文”并非“倩人”而“援笔立成”使得曹操“甚异之”的记载。①据《南齐书》所载与萧衍同族的齐武帝萧赜曾对王俭称赏其子萧子隆为“吾家东阿也”,然萧赜仅仅因萧子隆“能属文”而有是誉,其立论之据较诸萧衍更显单薄。参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10页。至于萧纲对于“萧绎”的“曹植之誉”,虽不免掺有手足情谊,但更多的是兄长对于弟弟才华的由衷钦佩,这一点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表达的至为显豁,其云:“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5]116显然,萧纲认为萧绎是当时文坛的“领袖”,故以“子建”称之最为合适不过。②萧梁一代,文人除以萧氏兄弟比于曹氏兄弟外,亦以曹氏兄弟比附萧梁皇室其他成员,如张缵《怀音赋》云“感平原之爱客”,即是将邵陵王萧纶比于曹氏兄弟。然而较诸将萧氏兄弟比于曹氏兄弟者,仅此一例而已,故臆此当为萧梁早期之事,萧梁后期则萧氏兄弟比于曹氏兄弟渐渐为时代共识。
二、让誉与受誉——文学友于下的政治阋墙
据《梁书·简文帝纪》可知,萧纲受到梁武帝“吾家东阿”的赏誉在天监七年,是年萧纲六岁,萧绎出生。而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据吴光兴《萧纲萧绎年谱》考证作于中大通三年③参见吴光兴《萧纲萧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0-172页。,是年萧纲二十九岁,萧绎二十四岁。据此而论,萧纲是萧梁皇室内部第一个得到“曹植之誉”并经权威认可的,故无论就时间性还是权威性来说,萧纲远比萧绎更具比拟曹植的资格,虑及曹植在当时文坛上的诸多美誉,萧纲应无慷慨让弟的理由。吊诡的是,萧纲并未对自己拥有“曹植之誉”过于自矜,因为在他现存的著述中不仅未对曹植多有溢美甚至还在《答张缵谢示集书》表达了对曹植的不满,而最为关键的是中大通三年他将这个于他而言实至名归的个人荣誉让给了萧绎,从而顺利解决了“曹植之誉”的专属问题。
萧纲让誉的举动如果仅仅从手足情谊方面考虑本无多奇,但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或许能体会此举的深意。中大通三年,萧统薨逝,储位之争乍起,梁武帝最终因“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6]1313的顾虑作出立萧纲为太子的抉择。对于梁武帝的决定,当时“朝野多以为不顺”[7],甚至萧纲故吏周弘正也以“让王之道”对其提出了“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谁”的期许,萧纲表面虽“不能从”,但心中恐早已对自己“以庶代宗”的行为讳莫如深了。而萧纲在未立太子前获取的“曹植之誉”就俨然成为其为非“嫡长子”的标签,因为“曹植之誉”虽就文釆而言,但难免启人将曹植的身份地位等方面与受誉者两相对应。况且稍溯前代,那些拥有“曹植之誉”的人在时人的观念里皆才堪为藩王而非储君,如王俭赏誉萧子隆为“东阿重出,实为皇家藩屏”[8]。显然,“曹植之誉”在萧纲立为太子后于萧纲身份而言已成矛盾,出于政治考虑,萧纲必须舍弃,但是如何舍弃又是难题。就《与湘东王书》来看,正是在他太子身份与“曹植之誉”矛盾始现的中大通三年,他将自己享有二十三年之久的“曹植之誉”让给了萧绎,这难免使人觉得过于巧合。或许萧纲的意图正是想试探性地给萧绎传达某种政治消息,因为在萧统薨后按照顺位继承的原则萧纲自然成为长子,出于政治的需求他更希望“挟有曹丕之资”[3]271,这种强烈的意识在他立为太子后所作诗文中频繁的标榜曹丕即可窥知④如《上大法颂表》“曹丕从征之赋,刘坦游侍之谈”、《谢敕赉善胜威胜刀启》“曹丕先荷其一”、《谢敕赉益州天门冬启》“曹丕之爱落英”、《饯别诗》“行乐出南皮,燕饯临华池”、《望月诗》“空闻北窓弹,未举西园觞”。。实际上,萧纲对于曹丕的追慕在其立为太子前就有流露,据《南史·陆罩传》载:“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连璧》,……以比王象、刘劭之《皇览》焉。”[6]1205这里,萧纲既将萧子显等三十人比做王象和刘劭,又将《法宝连璧》比做《皇览》,则自比曹丕之意不言而喻。但此时的萧纲“尚在雍州”而未立太子,所以只能暗示而不能道明,直到中大通三年其入主东宫后,这种暗示的心理才名正言顺起来。
然而在为自己正名的同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储位,萧纲忧虑萦心,其《蒙华林园戒诗》自云“居高常虑缺,持满每忧盈”[2]1936。可以说,萧纲对目前的处境是不适的,因为他本性“特是厌逢迎”[2]1936,而现在的处境自然使他想过“方愿遣樊笼”[2]1935。但是现实却是一旦接替了兄长的储位,他就必然要和曾经“我本逍遥趣”[2]1966的自己永别,因为这是父亲萧衍的安排。为了回应父亲的“深慈”,他或许已经准备好要以一个储君固有的政治心思去“监抚宣王事”[2]1967,所以他才会在《阻归赋》中自云“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汉而自通”[5]85。生在帝王之家,储君内心的政治意识一旦生成就必会忌惮其兄弟,萧纲固不例外,⑤王夫之于此似有先发之明,其《读通鉴论》云“简文弱而忌”。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5页。况且“梁武八男,唯豫章性殊,余各有文武才略”[3]209更使他忧虑萦心,其《蒙华林园戒诗》中便云:“执圭守蕃国,主器作元贞。昔日书银字,久自恧宗英。”[2]1936虽然“宗英”是萧纲对于萧氏兄弟的泛指,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宗英”典出汉河间王和萧绎在萧氏兄弟中正是以河间王自比且亦被他人比做河间王的这两个背景,①自比河间王如萧绎《金楼子》中共提及汉河间王4次,皆是对河间王文学、德行的赞赏,其中更有从藏书丰富的角度认为自己堪为“河间之侔”。被他人比做河间王如庾肩吾《和刘明府观湘东王书诗》云:“陈王擅书府,河间富典坟。”则不难推知萧纲所指实为萧绎一人。萧纲的顾虑不无道理,因为唯有萧绎的才能不在其下。当然除了才能之外,萧绎所镇的荆州和所督的湘州亦足以使萧纲忌惮,荆州“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9],加之自东吴以来南土即有“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10]1168的谶语,故自江左以来据此作乱之事常有发生②傅乐成云:“荆州一地,在中国史上南北分裂时期南方政权之领土中,无论对内对外,均占极重要之地位。……所谓‘三吴之命,悬于荆江’。……纵观六朝兴衰,可知荆州一地,关系六朝政局者甚大。”参见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93-94页。。湘州地位虽不及荆州重要,但自刘宋以来就有“湘州出天子”[2]1331的民谣。除了地理区位之外,萧绎湘东王的藩号或也引起了萧纲的警戒,因为刘宋时刘彧以湘东王的藩号举兵称帝的前朝故事犹在耳目。③萧绎初封湘东郡王,普通七年出任荆州刺史,坐镇江陵,并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此正与上述三点暗合,萧纲忌惮固在情理之中。凡此种种之故,萧纲“非弟而谁”的期许,或在暗示萧绎要成为文学第一人而非政治第一人。④梁末动乱,萧纶写信求援于萧绎也同样使用了“非弟而谁”,其云“弟英略振远,雄伯当代,唯德唯艺,资文资武,拯溺济难,朝野咸属,一匡九合,非弟而谁”?不过这一次萧纶“非弟而谁”的期许是希望萧绎为要成为政治第一人而非文学第一人。其实,萧纲此举渊源有自,因为当年曹丕在当上太子后就是通过写作《典论·论文》来劝告曹植安心舞文弄墨而不要争权夺利。⑤参见徐正英《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28页。如此看来,萧纲的让誉之举实有双重效果:一是借兄弟友于的表面来达到其政治意图;⑥据吴光兴《萧纲萧绎年谱》考证萧纲的《蒙华林园戒诗》和《与湘东王》是中大通三年萧纲立为太子后并示萧绎的,其《蒙华林园戒诗》既有以文学寓政治的目的,则《与湘东王》亦应如是。二是此举难免使时人想起曹丕故事从而达到再次暗示自己匹配曹丕的政治现状。
萧绎此时已被父亲萧衍任命掌管荆州钱粮重镇,与镇守扬州的萧纶、雍州的萧续和南徐州的萧欢形成对新储萧纲的拱卫之势,武帝如此安排的用意,凭借萧绎的政治嗅觉自当心领神会,⑦正如劳干对于梁武帝这种对于“太子之子和太子之弟大量封王并给以军队和封地”的政策性质总结“对付”,即是一切为了巩固新太子萧纲的地位。参见劳干《魏晋南北朝简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0页。况且就他对于术数的熟稔而言想必早已知道自己所镇的荆州较诸其他兄弟确实更惹远在扬州建康的萧纲忌讳,因自东吴以来就有“望气者云荆州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10]1166的谶语。故而这个素来“与简文相得”的弟弟此后便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将萧纲比做曹丕来为其政治造势⑧如《皇太子讲学碑中》就运用“南皮太子”的典故以比萧纲,《谢东宫赐白牙镂管笔启》中更是以曹植自比来暗示萧纲为曹丕,《法宝连璧序》则不仅以“我副君”称萧纲而且还称颂其“业迈宣尼,声超姬发”。。此时的萧绎并未对皇位有过多觊觎,坦然接受“曹植之誉”既能向萧纲传达自己无意储位之意又能满足自己“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6]243的妒才心理,萧绎自然乐于接受。
其实,关于萧氏兄弟间让誉与受誉的玄机,他们的文学侍臣庾肩吾、刘孝绰等人早已洞悉,因为他们均在自己的诗文中将萧纲比作曹丕而将萧绎比做曹植。⑨笔者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梁诗》统计,庾肩吾此类诗歌共五首,除下文提及的两首外,尚有《侍宴应令诗》《和刘明府观湘东王书诗》《侍宴饯湘东王应令诗》,三诗中第一首将萧纲比做曹丕,另外两首均将萧绎比做曹植。综观庾、刘等人诗文可以发现,他们或在诗文中直接将萧纲和萧绎分别比做曹丕和曹植,如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诗》“副君德将圣,陈王才掞天”[2]1983、王训《奉和同泰寺浮图诗》“副君坐飞观,城傍属大林”[2]1717,或通过运用“西园”“南皮”“应刘”的典故来暗示萧纲为曹丕⑩这些与曹丕有关的典故在萧纲立为太子前一直为文人们所使用来形容萧统,如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至于宴游西园,祖道清洛。”就连彼时的萧绎也如此,如《太常卿陆倕墓志铭》:“南皮朝宴,西园夜游。”而这种典故的暗示在萧纲自己的文章中或有先启之嫌,如《萧临川书》:“清夜西园,眇然为尅。”,如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宴湘东王应令诗》“副后西园游”[2]1984、刘孝绰《赋得照棋烛诗刻五分成》“南皮弦吹罢”[2]1840、庾肩吾《侍宴应令诗》“无以厕应刘”[2]1983。他们如此默契般行文,既有为萧纲作政治宣传的目的,也有着二萧兄弟现实名位的考虑。
综綮言之,中大通三年是一个节点,此前,比附曹植依然对于萧纲适用,此后,萧纲的文学侍臣开始有意识地将萧纲与曹植割裂而去比附曹丕。
三、人生与文学——萧绎“曹植情结”的表现及其影响
(一)念兹在兹的曹植
萧绎现存著作中多次提及曹植,如《金楼子》一书就提及10次,而《全梁文·元帝文》只提及1次,《全梁诗·梁元帝萧绎》则未提及。试将萧绎现存提及曹植的文献与萧绎经常拿来与其并举的陆机作一衡量,可以发现其对曹植关注之切。据萧绎现存著作统计,其《金楼子》提及陆机共6次,而《全梁文·元帝文》则只提及2 次,《全梁诗·梁元帝萧绎》则未提及。可见曹植是萧绎经常提起的文人,萧绎念兹在兹,仰慕之情至为明显。这里需注意的是《金楼子·立言篇》中有两处关于曹植文学成就的评论,一为:“陈思之文,群才之隽也。”[11]892一为:“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更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11]966通观两论,足见萧绎对曹植文学成就的尊崇,此种尊崇固有时代风气的影响,但萧绎并未一味附和,而是有自己对于曹植文学的独家见解,因他指出了曹植文章前人未有论及的特色,他之所以能得出新解,与他对于曹植其人及其文学的独特观照密不可分。
(二)合辙的人生轨迹——藩王政治与贵胄文学
萧绎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曹植,仅因欣赏曹植文学而有是举则难以使人信服。其实翻开《三国志》和《梁书》《南史》,我们会发现曹植在人生轨迹上与萧绎有着诸多合辙之处。曹植为曹操第三子,而萧绎为萧衍第七子,魏武、梁武虽以杀伐取天下,但二人之子却都有“仁”的一面,如曹植“天性仁孝”[10]562,萧绎更是“性颇尚仁,每宏解纲”[11]872。曹植、萧绎同为幼子出身,这无疑使他们通过正规程序走上皇位机会渺茫。政治上既然触摸不到最高权力,于是他们便凭借贵胄身份借助优渥的条件转入文学。《三国志·陈思王传》便云曹植“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文章绝伦”[10]557-562,而曹植对于自己的作品是颇为自负的,其《前录自序》云:“故君子之作也,……与雅颂争流可也。”[12]《梁书·元帝纪》也称赞萧绎“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13]135,萧绎同样也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其《金楼子·立言篇》云:“神其巧惠,笔端而已。”[11]966出色的文学成就除了外界因素之外也与自身努力分不开,曹植为学十分刻苦,据《太平御览》引《魏略》载:“陈思王精意著作,饮食损减,得反胃病也。”[14]而萧绎为学刻苦亦不亚曹植,据《金楼子·自序篇》载萧绎“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沉痼,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11]1357。二人出色的文学是建立在同样勤学之上的,巧合的是二人都因勤学而染疾,更为巧合的是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恰好也记载了曹植“反胃”的逸闻,从中或可窥见萧绎对于曹植此举的认同,那么我们可以大胆臆测萧绎习文至勤或受曹植影响。
中古世族的生活,文学之余,便是政治,而曹植与萧绎在此点上的合辙更为明显。曹植在争储失败后便处于“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10]567的困境。即使如此,曹植的政治热情并未消减。首先,他在明确自己藩王身份后认为“藩位任至重,旧章咸率由”并警戒自己的职责是“作藩作屏”而不能“恃宠骄盈”[2]446。他曾多次在自己的文字中流露过报效家国的意愿,如《薤露行》“输力于明君”[2]422、《圣皇篇》“糜躯以报国”[2]427。而萧绎作为武帝第七子,幼年为藩而出镇外州,在他看来藩王的责任是“终然慙励精”[2]2039,同时萧绎也认为藩王是天子的臣属要“示不忘臣礼”[11]443。随着政治气候的成熟,“夙有匡时志,早怀经世方”[2]1812的萧绎的政治热情也歘然而起,他曾多次在诗文里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志向,或云“终当抚期运,伐罪吊苍生”[2]2053,尽忠尽力,以报国家,此吾之上愿焉”[11]810-811。当然为藩一方的首要任务是“留心在庶绩”[2]1812,在内政方面二人同样用心。曹植自云“劬劳五年,左右罢怠,居业向定。园果万株,枝条始茂”[15]152。可见曹植很好的完成了他的职责。同样,萧绎外镇期间也取得了很好的政绩,尤以主政丹阳期间为最著,时人裴子野亲撰《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以颂其绩。
(三)文章、诗歌的传承与观念的分歧
1.以为典范的曹植文
曹植的作品,萧绎谙熟于心,仅据陈志平《金楼子研究》可知萧绎读过曹植作品约可考者有《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乐府诗》《表》《汉二祖优劣论》,①参见陈志平《金楼子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9-230页。借此可窥萧绎对于曹植作品的谙熟程度。萧绎“善属文”,每值行文构思之际,都会想起曹植的作品用来作为自己规模的典范。如《金楼子·杂记篇》云:“曈昽日色,还想安仁之赋;徘徊月影,悬思子建之文。”[11]1283作为文人之外,萧绎又是当时著名的评论家,当时京师就盛传“议论当如湘东王”[11]1283。作为评论家,时常会遇到评论今古文人得失的情况,据《金楼子·说藩篇》载:“余谓《水仙》不及《洛神》,《拟古》胜乎士衡矣。”[11]654曹植、陆机是中古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家,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就将二人并举,可见二人在萧绎看来不分轩轾,但是当二人文学地位面临今人挑战时,萧绎的选择就显示出了孰轻孰重。首先,他并没有一味地否定今人创作不可齐驾古贤,而是选择放弃陆机作品的权威性,但是仍然坚持强调曹植作品的不可比拟性。①刘宋时,曹植地位似有动摇,如孟棨《本事诗》载宋武帝非常欣赏谢庄的《月赋》并对颜延之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又宋明帝时有吴迈远,每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可见刘宋时期,曹植无论在统治者还是一般文士心中地位都未绝对化。萧绎如此强调,或有重塑曹植作品典范地位之意。这样的抉择,显示曹植作品在萧绎心中的绝对典范性,这也符合萧绎一贯认为“陈思之文,群才之隽也”的评价。如此看来,萧绎虽然认为陆机文学地位很高,但并未绝对化,这种潜意识也时常在他别的作品中有所流露,如《与萧挹书》就认为萧挹“文藻相晖,二陆、三张,岂独擅美”[5]183。结而言之,萧绎虽在文学上并举曹、陆,但这种潜意识的存在证明了曹植的文章在萧绎心中的绝对典范地位。
2.浓郁的“拟曹”诗味
萧绎现存诗歌据罗宗强统计共123首诗,具体分为“写妇女或男女情怀的22首,应令5首(不包括涉及男女情怀的应令诗),其他(包括宴游、闲适、登临等等)62首”[16]。尤为注意的是,萧绎的诗歌有着明显的模拟曹植诗歌的痕迹。首先,最为典型的当为萧绎的《紫骝马》一诗有着浓厚的曹植《白马篇》的诗味。《古今乐录》曰:“《紫骝马》古辞云:‘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盖从军久戍,怀归而作也。”[17]可见《紫骝马》从汉至梁多表怀人思归之情。而萧绎的《紫骝马》却丝毫不觉有怀人之意,反而洋溢着昂扬奋发的豪情,较于曹植《白马篇》,虽在内容上未有“边塞征战之状”②左克明《古乐府》云:“白马者,见乘白马而为此曲,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曹植‘白马饰金羁’,鲍照‘白马骍角弓’,沈约‘白马紫金鞍’皆言边塞征战之状。”萧绎模仿《白马篇》而成的《紫骝马》,不仅打破了《紫骝马》固有词汇、情感的局限,同时也不拘泥于《白马篇》的固有情感,这是一种双突破。参见左克明编撰《古乐府》,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09页。,在立意上也未有“言人当立功为国,不可念私”[18],但诗中少年风姿却基本相类,这是因为萧诗中大量运用了曹诗中形容少年的语辞来对自己诗歌中的少年形象进行再创作,如“金络”源于“金羁”,而“幽并”“西北”“连翩”更是径袭曹诗语辞。萧诗除了《紫骝马》受曹诗《白马篇》影响外,另有《去丹阳尹荆州诗》一诗也有曹诗《赠白马彪诗》的痕迹,尤其将萧诗中的“谒帝朝承明”句与曹诗“谒帝承明庐”句并观,因袭之迹尤著。师其“辞”是个人学习的初级阶段,此外,萧绎另有师其“技”的表现,如萧诗中的部分宫体诗对于“女性形与色的外在美的精细描绘”[19]就与曹诗中细腻精致地描写女子的技法颇为相似,如曹植《妾薄命行》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一位艳丽的佳人形象,这得益于曹植不厌其烦的描摹女子的服饰之丽和体态之美。在萧绎写女子的诗中也时有类似笔法,如《看摘蔷薇诗》“横枝斜绾袖,嫩叶下牵裾”[2]2047、《咏歌》“汗轻红粉湿,坐久翠眉愁”[2]2055。除了对女子服饰精细描写外,萧绎还沿袭了曹植诗中对失意女子的人文关怀,如其《闺怨诗》“知人相忆否,泪尽梦啼中”[2]2051。
3.三萧对曹植的认可度与各自文学观差异的关系
萧统、萧纲和萧绎,虽“文辞竞美,增荣棠棣”[3]212,但他们的文学观却同中有异,正如曹旭云:“三萧是三个圆圈,萧统在前,萧纲在后,萧绎居中,居中的萧绎的文学观与萧统重叠的部分多,与萧纲重叠的部分少,可知萧绎的文学观虽与萧纲有相似的地方,但比较而言,更接近萧统。”[20]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涉及到三人的成长经历、心理变化等诸多方面。③如曹道衡先生认为“萧绎从小所受的教育,显然和萧统、萧纲等人大不相同”,因为萧绎的母亲“阮氏为了保持她自己和儿子的地位,显然也会把那种韬晦、伪装和谄媚的手法传授给她的儿子”。参见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8页。然而,如果从他们对曹植的认可度来解释或许也能有所裨益。
萧统虽无对曹植的直接评价,但可借助《文选》的收录情况来分析。《文选》共收诗532首,录曹植诗25 首,总数仅次于陆机和谢灵运。从诗的分类来看,《文选》分诗24 类,而曹植诗却横跨8 类,在这8类中又多收曹植的赠答诗、杂诗和公宴诗。以此推知萧统是充分肯定曹植诗歌创作及其艺术价值的。又《文选》收曹植书、表各2篇,赋、七、诔各1篇,文共7篇,量虽不多,但仍可看出萧统对曹植多种文体的肯定。而从所收各体文章的数量来看,萧统是更加肯定曹植的书表而非它体文章。萧纲对于曹植的直接评价有三处,其《与湘东王书》云:“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5]115这里萧纲肯定了曹植的文学创作继承了《风》《骚》传统。其《答张缵谢示集书》云:“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5]114针对曹植肯定“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的偏狭文体观,萧纲是颇为不满的。其《答新渝侯和诗书》云:“跨摄曹、左,含超潘、陆。”[5]115他认为萧暎的宫体诗已经超越了曹植,可见曹植在其心中地位并非高不可攀。萧绎对于曹植的评价,前文已详述,他高度肯定曹植文学成就并认为曹植文学地位不可企及。合而观之,三萧兄弟对于曹植的接受程度以萧纲为最低,萧统居中,萧绎最高,而这样的接受程度正暗合于三人文学观的同异程度,这不能不说明二者之间或有某种联系。
萧统自幼深受儒家教育的熏习,故而主张文质彬彬,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5]216而曹植的诗文恰是“体被文质”。萧纲前期身为藩王,各方面的禁锢远少于萧统,他的宫体诗继承了永明体声律论的衣钵而有所新变,其协律程度和用典精切均胜过曹植。当然最大的分歧点在于萧纲的宫体诗继承的是“诗缘情”的道路。而曹植却是“坚守诗学传统,其诗以‘言志’为主,兼顾‘抒情’,体现以志帅情之特征”[21]。所以尽管曹植对于五言诗写作技巧贡献颇多,但在追求“缘情非雾縠”[2]1932的萧纲看来则略逊一筹。较诸两位兄长,萧绎则是完全接受曹植的,而他的出发点和萧统颇类似,在他的心中“诗言志”要大于“诗缘情”。首先,萧绎怀有立言不朽的观念,其《金楼子序》就坦露其“以为一家之言”的希望,这恰与曹植的“聘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的夙愿不谋而合,因而萧绎大力称赞曹植。萧统的《文选》收曹植表、书各2篇,赋、七、诔各1篇。其因何侧重书表而忽视赋、七、诔,这大概和书表的文体性质分不开,《文心雕龙·章表篇》云:“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22]据此可知,刘勰认为书和表是实用文体,是除去诗歌以外“言志”的文体,所以借此又可发现萧统对于“言志”文体的认可。而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却申讨曹植对赋体的偏狭之见,表面上是批评曹植狭隘的文体观,其实是对曹植“言情”之赋的肯定和对其“言志”之文的否定。从萧纲对宫体诗“性情”的追求来看,不难理解这种追求跨越了文体的界限,使其对一切“文”的好坏的衡量标准首先局限在了“情”上。萧绎在《金楼子》中多次评价曹植文章,原因在于曹植的文章里涌动着“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15]160的志向,而萧绎同怀此志。萧绎庶出的卑贱身份和失明的生理缺陷使其逐渐养成了猜忌、阴狠的性格,也激起了他争位的欲望。可以说帝王之志在萧绎心中暗滋已久,在梁祚未頽之前,身为皇位第七顺位继承人的他距离皇位还很遥远,所以只有通过“文”的途径来抒发自己的志向,而这点在曹植的身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三萧对于曹植的肯定程度与他们的文学观差异联系密切,曹植的作品在“言志”与“缘情”的严格区分下被三萧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评价。
四、个人价值的凸显——“曹植情节”不足与突破
天监八年萧纲得誉“东阿”,而此年恰逢萧绎生年,虽然从《金楼子》《梁书》《南史》等记载来看萧绎在青少年时期被梁武帝誉为“孙策”而非曹植,但此番巧合无疑给了少來“伎能之事,无所不该”的萧绎以某种遐想,①尤为巧合的是与萧绎同出南兰陵萧氏的南齐武帝萧赜之子萧子建封爵恰为湘东王,我们无法考知萧衍后来在封萧绎为湘东王时是否想到此点,但此巧合却足以使受封者萧绎产生某种遐想。更何况在萧纲身上还有一个“此子与冤家同年生”[23]的不利谶语。中大通三年萧纲继承储位,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让誉于弟更使萧绎“曹植情结”得到确认。此后,无论萧氏家族内部或是外界都对于萧纲、萧绎与曹丕、曹植的对应关系十分了然并用各自擅长的方式来加以强调。②最为典型者当为萧氏兄弟共同文学侍臣庾肩吾,其现存诗歌中就有五首涉及,这恐非出于偶然而当是有意强调,可见时人于此认知之一斑。随着萧绎自身“曹植情结”的逐渐成熟,他的人生、文学等诸多方面都受其影响。
但是萧绎毕竟不是曹植,虽怀有“曹植情结”但也时有突破“情结”干扰而有体现其本质的行为,这集中表现在他政治个性方面较于曹植的不足与政治成就方面对于曹植的超越。曹植虽不受重用,但他却“志在擒权馘亮”[15]149,于此可见曹植希望自己能够结束天下三分的局面。但萧绎在江陵即位后却通聘魏、齐,可见其应无结束分裂之意,所以在志向上远不如曹植宏大。同为身处乱世的藩王,曹植唯愿做好藩王本分而已,然而萧绎却在侯景乱中“拥众逡巡,内怀觖望,坐观国变,以为身幸”[13]151。虽然有此不足,但是萧绎却在政治上取得了曹植毕生未曾染指的成就,曹植后期备受帝王猜忌而赍志以殁,而萧绎却在侯景乱中备受重用进而“握图南面,光启中兴,绍兹宝运”[13]136。如此看来,萧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弥补了曹植未能“争雄于宇内”的缺憾,因此明人张溥评论云:“挟陈思之才,攘子桓之坐,眇僧化身,固一神物哉!”[3]275可谓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