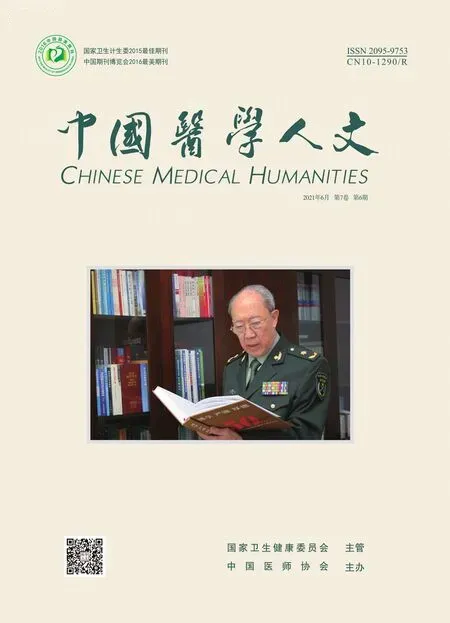沟通不只是一纸知情同意书
文/黄 越 黄学武 余 玲
怀着好奇的心,订购了《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这本书,拿到它时,我并没有立即翻开,而是仔细揣摩了封底推荐者写的话,他们从不同角度大致剖析了这本书的内容或结合自己的人生体会,告诉大家这本书值得一读!
死亡是每个人人生的终点,从一出生,我们就不断向其靠近。大多数人不愿主动提及“死亡”二字,仿佛一提就会晦气,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一般。就像我平时无意中提及诸如“死亡”“生病”这些不吉利的字眼,奶奶就会很反感,立马制止我。这或许是迷信,但“死亡”这两字,确实在中国人的情结中,一提及就让人心里不舒服。疾病文化学家苏珊·桑塔格1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一书中提到,每个人都有两张公民身份证,一张代表健康国度的身份,一张代表疾病国度的身份,每个人都在两个国度居住。运气好的公民在健康国度居住的时间更长,而运气不好的公民可能长久待在疾病国度。每个人都会遭受疾病之苦,有些人因为得了绝症如癌症,会提前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很陌生,但作为医学生,在临床上我们离死亡又很近。
《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是一位临床医生,书中记录了十几个有关老年疾病和临终护理的故事。在这些通过医生视角展开的生命叙事中,葛文德反思了过度技术干预和死亡的医学化带来的困境,重新审视医学的本质,思考生命与死亡的真正意义。葛文德在书中提到:“在医学院读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包括死亡。教授们一门心思地教导我们如何挽救生命,以为那才是医学教育的目的。我们全力聚焦于知识的进步。虽然我们知道如何表达同情,但是完全不能确信我们懂得怎样进行恰当的诊断和治疗。我们上医学院是为了了解身体的内在运行过程、身体病理学的复杂机制,以及人类积累的阻止疾病的许多发现和大量技术。除此之外,不曾想过我们需要丰富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修养。”2
葛文德医生描述了现代医学的许多现象:作为医学生,我们都在努力学习医学知识,努力写好病历;患者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对症处理,患者需要抢救我们如何进行规范有效及时的抢救;患者需要签知情同意书,我们医生应该和患者及家属交代什么情况及后续治疗。我们以为签了字,谈了话,这样就算沟通过了。事实却是,患者和家属被我们医生牵着鼻子走。但是,这就是现实,现在医院的程序就是这样子进行的。
葛文德医生在书中提到三种医患关系:家长型、资讯型、解释型。最古老的也是最传统的关系是“家长型”。医生是医学权威,目的是确保病人接受我们认为对他/她最好的治疗。医生有知识和经验,负责做出关键的抉择。这是一种“医生最明白”的模式,虽然经常遭到谴责,但目前仍然是普遍的医患交往模式,尤其对于易受伤害的病人——虚弱的、贫穷的、老年的,以及所有容易听从指令的人。第二种“资讯型”关系,同家长型关系正好相反。医生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其他一切随患者来裁决。这是一种零售型关系,医生是技术专家,病人是消费者。医生的工作是提供最新知识和技术,病人的任务是做出决定。越来越多的医生成为这个样子,医生这个行当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我们对病人的了解越来越少,而对科学的了解越来越多。这种关系越来越受欢迎,因为患者和家属清楚风险和能采取的措施,他们拥有完全的自主。第三种关系是“解释型”,医生的角色是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专家把这种方式称为共同决策模式,医生会问“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你有些什么担心?”了解了患者的需求后,医生会告诉患者什么选择对其更能实现优先目标。但是解释型的医患关系并不普遍,很多医生似乎没有时间去思考和理解患者所要面对的痛苦,而患者则期望医生能够理解和见证他们的苦难3。
回想自己身边的例子,似乎也能明白医生有医生的苦衷,患者有患者的苦难。此前在肿瘤科轮科,听同学说组里有位病人比较难沟通,肺癌脑转移,常常独来独往,没有陪护也不请护工,抗拒治疗,这是我听到的关于这个人的评价。一次值班查房时没有见到他,我过后再去病房询问他的情况,没想到他打开话匣子聊起了自己的治病经历。我没有打断他,让他畅所欲言,原来他在治病过程中经历了外院误诊、用药过敏,所以他的“有所戒备”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正常的反应,而充分的沟通才能打开他的心扉,让医患双方都互相理解。
最近我在肾病科轮科,入科第二天新收了一位患肾终末期疾病CKD5期(指慢性肾脏病分期第5期,即肾衰竭)伴心力衰竭、右腹部剧烈疼痛的病人。我记得很清楚,当天入院就让他签了6个知情同意书,包括透析知情同意书、病重知情同意书、入住ICU知情同意书、深静脉置管同意书等。当带教老师和患者及家属谈完病情,我带着iPad(无纸化病历)去给患者和家属签字,我心想,若我是患者或家属,我能接受一入院还没治疗就签这么多知情同意书吗?其实说实话,我是担心和焦虑的。我战战兢兢,语气诚恳,语速放慢,签字前交谈,字里行间安慰和鼓励患者和家属,让他们了解这是必要的程序,心里很希望患者和家属配合医生和护士。我很幸运,患者和家属并没有过多地质疑,他们表示配合并且果断签字。签完字,我走出病房,心里松了口气。后来我一直关注这个病人的治疗进展,他住了半个多月,每次查房,他都会仔细和主管医生描述自己症状和感受的变化。从他的谈吐中,我发觉他很健谈,也很乐观,即便在被告知要终身透析或接受肾移植才有希望摆脱去医院透析时,他也冷静接受,表示会更积极配合治疗,求生的欲望也很强烈。他会积极主动和医生沟通,表达自己的期望和意愿。我在询问他的情况有无好转时,他向我表达了他的愿望是肾移植,摆脱医院的束缚。他的理由很多,他的孩子还小,他还很年轻,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他不想一辈子和医院绑在一起。他说希望和医生多沟通,让我们明白他的需求。我觉得他比我更懂得,当今医疗环境,医患更需要沟通,他作为患者,主动走出了这一步,也启发了我。如果医务人员能够注意给予患者关注与关怀,做到及时沟通、有效沟通,将会有利于改善和发展和谐的医患关系4。《卡尔曼医学教育史》一书中指出:“医生要让身处困境的人们感到有人在伸出援助之手,要倾尽其力,尽其所能。”5
当代医生兼作家亚伯拉罕·佛吉斯(Abraham Verghese)在与同行交谈时,这样说道:“作为医生,我们很容易卷入到患者的生命故事中,成为这些故事的参与者。我们的行为改变着叙事的轨迹,患者的故事渐渐变成我们话语的重复。”6刘端祺教授曾说,他接触最多的是肿瘤患者,发现他们的痛苦来源就是一点——“为什么是我?”患上肿瘤这一诊断会使患者惊觉,“我的世界垮了”“我不知道还能相信什么了”。面对一个逐渐开启的临终世界,身体、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三个层面的脱离,让他们经受着极端痛苦的心灵漂流过程。这个时候,如果患者主动提出灵性照顾的需要,而医护人员“顾左右而言他”“不接茬”,其结果可想而知。而倾听之后的真诚交谈,能让患者对病情的诊断、发展及治疗做到心中有数。虽然改变不了最终结果,但能改变患者的心态。对医生而言,则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以患者为师,感谢患者传授分享“人生秘籍”。
生命中最大的迷思有三:不可及(膏肓之间、盲人摸象)、不可测/测不准 (万物之灵)、不可知(混沌性)。它包含了诊疗局面的复杂(混沌)性、生死的偶然性、医患之间的主客间性、临床干预的双向性、医学认知的无限延展性,生命永远存在一个不可知的盲点,真理的彼岸不可终极抵达,刻舟无法求剑,也就是说疾病也不会在医学探索和技术拷打面前吐露全部秘密,医学总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全善7。但是我们需要和患者沟通,走进他们内心,明白他们在生命面临终点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而不是只靠签一张张冷冰冰的知情同意书,表示我们已经沟通过了,这不是真正的沟通。
《最好的告别》正是葛文德医生对生命尽头各种生命状态的记录与反思,书中一个个或成功、或失败、或令人欣慰、或留有遗憾的故事,堪称平行病历的范本。通过反思性写作,葛文德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脆弱、坚定与迷茫,以及面对衰老和生命的尽头时,医生、患者、家属各不相同的心境与选择;同时,对医学与生命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在生命濒临结束之际,到底是追求技术性突破的治疗更重要?还是让患者有意义地活着更重要?又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通过反思,葛文德提出医学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只是保证健康和生存,而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助人幸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