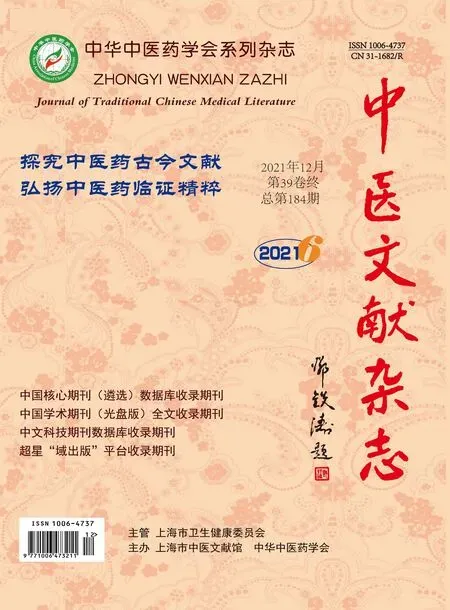《临证指南医案》眩晕证治探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200032)
《临证指南医案》为中医临床必读之书,是叶天士门人华岫云收集其临床治案辑录而成,为后世研究叶天士的学术观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叶天士不仅是温病大家,在眩晕等内伤杂病上亦颇有造诣。该书除专立“眩晕”门外,亦于“中风”“肝风”“虚劳”等30个疾病门共计78则医案中提及眩晕。这些病案反映了其对眩晕的分类、病因病机、证候及临证辨治用药特点的认识。本文拟就此作一探析,以期为现代中医临床诊治眩晕提供思路。
病因病机
对眩晕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殷商,出土的此代文物中有“疾王旋”等相关文字记述。[1]历代文献对此病证有多种称谓,仅在《临证指南医案》一书中的描述就不相同,如眩晕、目眩晕、头晕目眩、头眩目花、头眩、头晕等,虽描述各异,但总体还是沿用南宋陈无择提出的“眩晕”病名。《临证指南医案》中眩晕是指以眼目一时昏花或者发黑,头昏旋转,甚则猝倒而不可救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证,常兼见头额闷胀、目跳耳鸣、心悸等症状。正如华岫云所总结:“所患眩晕者,非外来之邪,乃肝胆之风阳上冒耳,甚则有昏厥跌仆之虞。”[2]
叶天士辨治眩晕从“阳化内风”立论,将其分为夹火、夹痰、中虚、下虚,认为眩晕的根本在于“肝风”,而引起肝风内动的原因,与脾胃、肾、心有关。叶天士治疗眩晕受到诸多前人学术观点的影响,但法古而不泥古,并多有创见。如肝阴易耗,肝阳易亢,虚风内生,扰动头目,则眩晕跌仆,主张从肝论治,此观点化裁于《黄帝内经》的“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若中焦脾土衰惫,肝失培养,则会导致肝气乘脾,久之引起运化失常,酿湿成痰,阻扰脑窍,则成眩晕,此看法实则是继承于张仲景“痰饮为病”和朱丹溪“痰火致眩”的学术思想;叶天士提出眩晕责之于肾,有“上实下虚”之证的观点,主要得益于张景岳提出的“无虚不作眩”,认为致虚的原因不外乎上气不足、髓海失养。
在此基础之上,叶天士进一步补充了眩晕有“阳升血热”之证。其病机为心血亏耗,阴不涵阳,心君之火夹厥阴相火上炎,扰乱神窍。虽然“阳化内风”最初是阐述“中风”的病机,但“中风”之前多有眩晕,因此叶天士也常以“阳化内风”来阐述眩晕病机。
辨证论治
叶天士根据前人论述,结合自己的认识,在眩晕证治方面多有创见。龚商年[2]在《临证指南医案》“癫痫门”中言:“人身亦一阴阳也,阴阳和则神清气定,一有偏胜,自致不测之疴。”人体阴阳与自然万物类似,一旦失去平衡,则百病由生。治疗疾病本质上是使用药物、针灸等手段来调整阴阳,平衡寒热,阴阳调和则疴疾自消,眩晕证治也是如此。本文试以阴阳寒热虚实为纲加以论述。
1.实证
风阳上扰 此证治以甘味息风。
案一:张 肝风内沸,劫烁津液,头晕,喉舌干涸。[2](《临证指南医案·眩晕》)
案二:梁 木火体质,复加郁勃,肝阴愈耗,厥阳升腾,头晕目眩心悸,养肝息风,一定至理。近日知饥少纳,漾漾欲呕,胃逆不降故也。先当泄木安胃为主。[2](《临证指南医案·肝风》)
此两案均为肝阳上亢、阴虚风动证。叶天士认为此类患者或因阳亢(如案二),或因忧思恼怒烦劳(如案二、“肝风”门沈案、“木乘土”门唐案),致雷火不潜,相火升腾,劫灼津液,肝风失去阴液之濡润,疏泄太过,内风上逆,扰动头目,故目跳头晕。
叶天士创立“阳化内风”学说,认为嗔怒动阳,阳化内风,扰动头目,发为眩晕。治疗“阳化内风”,善用甘味药以养肝阴,常用酒制首乌、枸杞子、黑芝麻以补肝肾、益精血,如本案用甘味之阿胶以滋阴补血,此即“甘味息风”;兼用天麻、钩藤、菊花等药以平抑肝阳。此外,叶天士言“肝风内沸,劫烁津液”,认为肝阳上亢,最易劫灼津液,耗伤阴精,因此治疗时常加入生地、天冬、麦冬以养阴生津,肝阴得以濡养,津液得复,则肝风自息,眩晕则止。
阳升血热 此证治以清热凉血、养血息风。
案一:吴 脉弦小数,形体日瘦,口舌糜碎,肩背掣痛,肢节麻木,肤腠瘙痒,目眩晕耳鸣,已有数年。此属操持积劳阳升,内风旋动,烁筋损液,古谓壮火食气,皆阳气之化。先拟清血分中热,继当养血息其内风。安静勿劳,不致痿厥。[2](《临证指南医案·肝风》)
此案为阳升血热证。操持积劳导致心血亏耗,一则阴血无以涵养肝阳,心君之火夹厥阴相火上炎,扰乱神窍,出现口舌糜烂、眩晕等症;二则营液内耗,无以充养肝血,致虚阳上亢,肝风内动。治疗前者,叶天士先用丹参、犀角、羚羊角、连翘、竹叶心以清热凉血,待阳升血热受挫后再予以养血息风,使用何首乌、白芍、黑芝麻、女贞子、墨旱莲、阿胶。针对后者,叶天士提出“养心气以通肝络”,使用小麦、炙甘草、阿胶、茯神等以补心气、养心血、安神定志,待心血充足,则肝血充盈,虚阳自潜。
痰浊上扰 此证治以土木同治。
案一:某 酒客中虚痰晕。[2](《临证指南医案·眩晕》)
案二:某 阳明虚,内风动,右肢麻痹,痰多眩晕。[2](《临证指南医案·中风》)
此两案均为痰浊致眩证。叶天士认为素喜饮酒、饮食不节等因素是眩晕的重要成因。案一患者素喜饮酒,酒家湿热,易酿痰饮,如《素问·厥论》篇所言:“酒气与谷气相搏,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酒辛大热,久则损伤中焦脾土,酿湿成痰,郁久化热,湿热内蕴,损伤胆腑,痰火上炎,扰动头目,故出现眩晕。
叶天士认为,眩晕乃风火痰合而为病,当胆胃同治(如“眩晕”门徐案、某案、汪案),此即“少阳阳明同治法”。他认为,饮食不节、久病劳倦、烦劳可损伤中焦阳气(“呕吐”门某案、“不食”门郑四三案等),致使脾胃衰惫。其一清阳不升;其二失于运化,痰湿内生;其三土衰木旺,肝气乘脾,造成湿痰夹肝风上扰清阳之象,且过亢之肝阳,又可横逆犯胃,引起胃失和降,循环往复,形成一个“阳愈亢土愈衰痰愈多风火愈旺的恶性循环”。[3]治疗上若是只镇肝息风,则会劫烁津液,使已伤之脾胃更加衰惫,故应当土木同治,健脾化痰与平肝息风相结合,如吴四五案中强调的“治痰须健中,息风可缓晕”。[2]因此,常用橘红、半夏、茯苓、薏苡仁、白术以燥湿化痰、健脾益气,此为从胃治;用羚羊角、黑山栀、花粉清泄上焦之火,此为从胆治;再佐以天麻、钩藤、菊花以平肝潜阳。
李东垣在《兰室秘藏·头痛》中言:“足太阴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疗,眼黑头眩,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除,其苗为定风草,独不为风所动也。”从叶天士的多个医案中可看出,叶天士宗东垣之法,治疗因痰致眩时常使用天麻、半夏以化痰息风。
血络瘀滞 此证治以辛香化瘀。
案一:钦 初产,汗出眩晕,胸痞腹痛。宜通恶露。[2](《临证指南医案·产后》)
此案为血络瘀滞证。如明代《仁斋直指方》所言 “瘀滞不行,皆能眩晕”。此案患者产后下血过多,元气大损,恶露乘虚上攻,眼花头晕,说明血络瘀滞亦是眩晕的病机之一。叶天士创立“久病入络”学说,认为“瘀”是其基本病理变化。因辛能散瘀、行气,直达络中,驱邪外出,故络病常用辛味药。叶天士治疗因瘀致眩时采用治络之法,以辛为治,如采用辛味之香附、延胡索、郁金调理气机,再配赤芍、牛膝以散瘀止痛,此即“辛香流气”之法。
2.虚证
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肝风》中言:“故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2]肝脏有赖于肾精、脾气、精血等精微物质的濡养。若肝阴失于上述精微物质的濡养,则肝阳易亢,虚风内生,扰乱清窍,发为眩晕。
血虚生风 此证治以辛甘化风。
案一:严四五 营虚,内风逆,心悸头晕。[2](《临证指南医案·眩晕》)
案二:陈四五 操持烦劳,五志阳气夹内风上扰清空,头眩耳鸣,目珠痛。但身中阳化内风,非发散可解,非沉寒可清,与六气火风迥异。用辛甘化风方法,乃是补肝用意。[2](《临证指南医案·肝风》)
此两案为血虚生风证。《证治汇补·眩晕》提出“眩晕生于血虚也”,或久病体虚,脾胃虚弱,气血化生无源,或外伤、妇女产后,失血过多,气随血耗,气虚则清阳不升,血虚则清窍失养,因此发为眩晕。
案一患者不知何因导致营血虚,心神失养、髓海失充,故出现心悸头晕。叶天士遵从巢元方“由血气虚,风邪入脑,而引目系”的观点,从“风、虚”立论来阐释眩晕的病机,认为营血亏虚,不仅血虚无以濡养脑窍,而且肝血亏耗,阴虚无以制阳,虚风内生,内风上逆,清窍被蒙,故出现头晕,这也是“阳化内风”学说的内容。治疗上,叶天士选用辛甘化风法,创立“养血息风方”和“枸杞桂圆方”以养血息风。此法化裁于“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说。如病案中使用甘味之品炒杞子、桂圆肉、柏子仁、川石斛以补养肝血,血充则风自息,再佐以生牡蛎、冬桑叶、甘菊炭以平抑肝阳。
脾胃阳虚 此证治以温补中阳。
案一:某 积劳伤阳,先已脘痛引背,昨频吐微眩,脉弱汗出。胃中已虚,肝木来乘,防有呃忒吐蛔。仿仲景食入则呕者,吴茱萸汤主之。[2](《临证指南医案·呕吐》)
此案为脾胃阳虚证。叶天士在多个医案中谈及积劳损伤阳气,且“卫外之阳内应乎胃”,卫阳与胃气相通应,阳气受损,一则清气不能上达,二则肝乘虚横逆犯胃,胃气上冲,再则脾虚则痰湿内生,浊阴上逆,故出现呕吐、眩晕。治疗上,叶天士化裁张仲景的吴茱萸汤,取辛热之吴茱萸、姜汁,以达温胃散寒、降逆止呕之功,佐以半夏、茯苓以燥湿化痰、增强止呕之效,再用粳米以顾护胃气。
肾精不足 此证治以滋水涵木。
案一:某二四 晕厥,烦劳即发。此水亏不能涵木,厥阳化风鼓动,烦劳阳升,病斯发矣。据述幼年即然,药饵恐难杜绝。[2](《临证指南医案·眩晕》)
案二:田二七 烦劳,阳气大动,变化内风,直冒清空,遂为眩晕。能食肤充,病不在乎中上。以介类沉潜真阳,咸酸之味为宜。[2](《临证指南医案·眩晕》)
此两案为肾精不足证。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生髓,脑为髓之海。《灵枢·海论》言:“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说明肾精耗伤,无以充养髓海,脑失濡养,则眩冒耳鸣。本案患者先天肾精不足,故幼年即发,病情久延,损伤肾精肾气,无以充养髓海;并且烦劳引动雷火,肝阳浮越,扰动清窍,发为眩晕。
《素问·五脏生成篇》载:“徇蒙招尤……上实下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叶天士继承此观点,认为眩晕之病,或因先天肾精亏虚,或因年高肾气衰,致肾精无以充养肝阴,厥阳化风鼓动,又遇烦劳,则肝阳上亢,变化内风,直冒清空,实为“根本虚在下,热化内风在上,上实下虚”[2]。
治疗上,叶天士宗“缓肝之急以息风,滋肾之液以驱热”之法[2],用熟地、阿胶、建莲、淡菜胶等药以补益肝肾、补血养血。在此基础上,常用灵磁石、龟板、牡蛎以镇肝潜阳,五味子、山萸肉等酸味之品以收敛固涩,补肝肾之阴,味咸之牡蛎与味酸之五味子同用,是为水生木,更辅以茯神、远志以达宁心安神之效。此两案与田二七案、“中风”门曾五二案均体现了叶天士治疗眩晕善用咸酸、味厚之药滋肾阴、潜肝阳。本证的根本病机虽为阴虚,但容易阴损及阳,故叶天士常用肉苁蓉、枸杞等柔剂代替刚燥之桂枝、附子来温补阳气。另外,叶天士认为久病不已,元气精血必伤,填补肾精时善用血肉有情之品,比之草木无情之药,其培补之力更宏,例如在案例中使用了龟板、淡菜胶、阿胶,亦值得学习。
肾气衰惫 此证治以温肾凉肝。
案一:李七三 高年颇得纳谷安寝,春夏以来头晕跗肿,不能健步。此上实下虚,肾气衰,不能摄纳,肝风动,清窍渐蒙。大凡肾宜温,肝宜凉,温纳佐凉,乃复方之剂。[2](《临证指南医案·眩晕》)
此案为肾气衰惫证。《临证指南医案·六气解》中言:“水土温和,则肝木发荣,木静而风恬;水寒土湿,不能生长木气,则木郁而风生。”患者年高,肾阳气渐衰,水寒无以温养肝木,木气生长缓慢,故内风起。叶天士在治疗上提出“温肾凉肝”法。肾阳衰惫,如“中风门”曾五二案中使用虎潜丸以扶助肾阳,而案一使用滋补肾阴之都气丸,是取张景岳“善补阳者,阴中求阳”之意,再加入附子以补火助阳,此即“温肾”;然而补阳之品多温燥,且肝阳上亢,温燥之品更易助阳,加重病情,因此去锁阳,取车前子、淡天冬、建莲之甘寒以养肝阴,此即“凉肝”。
叶天士虽取前人之法,但并不拘泥于古方而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常常在经典方药基础上稍作加减。每味药的使用均恰到好处,用药极轻灵,虽平淡,但效果更甚,正如华岫云所言:“案中治法,如作文之有平浓奇淡,诸法悉备。”[2]
结 语
《临证指南医案》为临证治疗提供诸多经验,如华岫云在“凡例”[2]中所言“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且“今观此案,其识证如若洞垣,所用法与方,皆宗前贤,而参以己意,稍为加减之”。说明识证是最为紧要之事,立法、用方只需遵循前人经验,根据病况稍加增减便可,此宗旨至今指导着中医临证。
叶天士博采众家之长并多有创见,从而形成一套眩晕诊疗体系。病因上,主张情志因素、饮食不节是眩晕发病的重要诱因,平时应当保持心情舒畅、饮食规律、防止跌仆以预防调护。病机上,明确提出“阳化内风”,强调肝肾阴虚、气血亏耗都是“肝阳化风”的重要成因,使眩晕病机的阐释趋于完善。治法上,开创性地提出了“温肾凉肝法”“辛甘化风法”“辛香流气法”等治法,丰富了眩晕的治疗思路,对后世治疗眩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