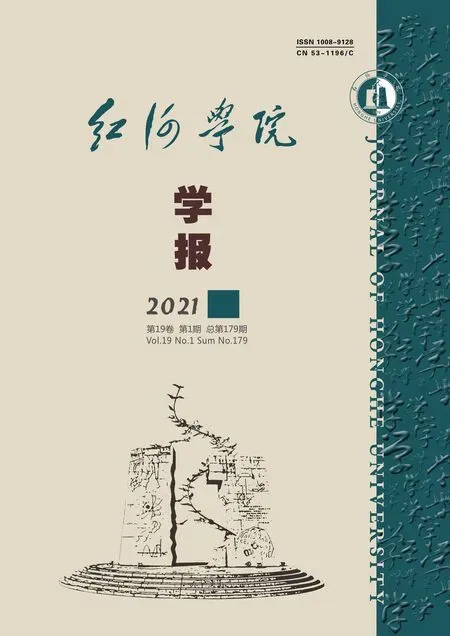麻山苗族的“归冢”意识:《亚鲁王》中的地理意象研究
李静静
(广西大学文学院,南宁 530004)
《亚鲁王》是一部涉及创世、战争、迁徙等诸多内容的苗族史诗,被誉为“苗族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多唱诵于麻山苗族的丧葬场所。目前,学界对《亚鲁王》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宏观文化环境及史诗文化内涵的探究,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从地理意象的角度出发,厘清麻山苗族的迁徙历史,探讨麻山苗族“归冢”意识在民族精神灵魂中的存在性显现,进而研究《亚鲁王》的美学价值。
一 地理意象与麻山苗族“归冢”意识的形成
《亚鲁王》立足于麻山苗族的历史变迁,以创世神话为创作源头,构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麻山苗族文化意象。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其迁徙范围之广,跨度之大,时间之长均为罕见。相传苗族是蚩尤的后代,蚩尤在河北涿鹿和黄帝交战,失败后不得不向南迁徙。“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苗族分布虽然很广,并且接近中原,有时还有由南而北内徙的势头,但当时苗族的聚居区是在武陵、五溪地区及相邻的鄂西、川东、黔东北一带。”[1]在秦汉、唐宋之际,尤其在安史之乱后,政治动乱,战争频繁,大批居于武陵、五溪地区的苗族被迫迁徙至贵州、川南、桂北和云南,形成了一个新的迁徙浪潮。“元朝统治者残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明王朝在黔东、贵阳、安顺等地大量设置屯堡,均强迫许多苗族人迁徙,操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的苗族就是这个时期在紫云的打郎、妹场、宗地、四大寨等地居住下来的。”[2]由于麻山地区地处偏僻,直至元初元廷在与宋遗民交战时路经麻山苗族的部分区域,这支苗族才被人们所知。
麻山苗族迁徙的过程在史诗《亚鲁王》中得到了印证。“关于亚鲁王的内容,是苗族先民从原武陵郡一带迁徙到目前的川西南、滇东北、黔西北靠近金沙江一带时产生的,其产生时间上限当在唐宋时期。”[3]史诗中记载的盐井之战有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为了争夺盐池而发动战争在苗族古歌中亦有叙述。结合史籍记载的盐井之战来看,麻山苗族的祖居地是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广袤的平原。由于战争因素,亚鲁王率领部落,由北向南迁徙,横渡若干江河,随后溯江河而上,形成自东向西的迁徙路径:
岜炯阴→哈榕冉农→哈榕冉利→哈榕呐英→哈榕呐丽→哈榕呗珀→哈榕呗坝→哈榕丫语→哈榕牂沃→哈榕卜稻→哈榕梭洛→哈榕饶涛→哈榕饶诺→哈榕咋唷→哈榕咋噪→哈榕卡比→哈榕比力→哈榕玛嵩→哈榕玛森→哈榕甲炯→哈榕哈占→哈榕泽莱→哈榕泽邦→哈榕呛且→哈榕甬农→哈榕嘿旦→哈榕崩索让→哈榕岜索久→哈榕麻阳→哈榕哈嶂→哈榕呐岜→荷布朵疆域(哈叠)。
史诗中亚鲁王带领族人自东向西迁徙,这是麻山苗族迁徙历史的曲折反映。在祖居地中,苗族裔民以经营集市、稻作生产和鱼虾养殖等为重要的谋生手段。正是这以固定的土地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成了苗族裔民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亚鲁王造田种谷环绕疆域,亚鲁王圈池养鱼遍布田园……亚鲁王开垦七十坝平展水田,亚鲁王耕种七十坡……亚鲁王对七十个王后说……我要领兵去做生意,我要率将来做买卖……我要在疆域开坝场,我得到领地建集市……你们得带兵种好糯谷,你们要领将养好鱼虾。”[4]101史诗以集市、鱼虾和糯谷等自然地理景观构建了一个富饶宜居的祖居地,呈现了以农耕为主,以集市交换为辅的苗族经济格局,蕴含着追求稳定和谐的价值取向。农耕民族所占据的地理空间具有稳定性,但麻山苗族由于历史因素被迫迁徙,现实状况与民族心理之间的冲突形成了麻山苗族强烈的“归冢”意识。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糯米、麻、鱼、集市等地理意象幻化为集体无意识,在时代变迁与地理迁徙中,依然根植于麻山苗族心理,成为了麻山后人“回家”的标志性符号。“蝴蝶”“马”“鱼”“糯谷”等地理意象至今仍存在于麻山苗族的丧葬仪式上。
由于战争因素,亚鲁王被迫从富饶宜居的祖居地迁徙至偏远贫瘠的麻山地区。“麻山位于贵州省黔西南自治州、黔南自治州和安顺地区的望漠、罗甸、长顺、惠水、紫云、平塘6县结合部,面积5000多平方公里,是苗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5]麻山地区属于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漠化严重,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由于耕地面积有限,粮食产量低下,麻山地区长期属于欠发达的区域,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在麻山苗族的集体记忆中,先民从富饶宜居的“大平原”迁徙至贫瘠的麻山腹地。恶劣的生存环境引起了麻山苗人“东方崇拜”和“魂归故里”的深层文化心理,由此产生浓厚的“归冢”意识。
二 地理意象与麻山苗族“归冢”意识的民族精神心理显现
迁徙,在史诗文本中不仅呈现为地理空间的置换,而且镜照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麻山苗族人民在历史上多次被迫迁徙,但其族群记忆感召麻山苗族人在迁徙途中建造与族源地相仿的地理空间,在丧葬仪式上吟咏祖源地,召唤亡魂回归故土,以圆满的心理空间弥合屡被进犯的家乡地理空间。
麻山苗族祖居地是一个平坦开阔、集市繁荣和盛产鱼米的“大平原”。河网密布,水池众多,利于渔业发展;土质肥沃,水源充沛,便于农耕;气候温暖湿润,草木茂盛,利于驯养家畜。“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6],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能够为人类生存提供基本食物保障及安全庇护。“东方故国”的整体地理景观结构满足人类长期居住的理想模式,亚鲁王在迁徙途中参照祖居地的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从水源、土地、安全等来考虑所定都的领地。亚鲁王带领苗族部落迁徙至哈榕冉农等诸多辽阔平坦的坝子,该地理位置水资源丰沛,粮草茂盛,但却难以使族群摆脱战争的阴影。亚鲁王只能携妻带儿跨上马背继续迁徙,走入了哈榕玛嵩等贫瘠的山地,该地虽具备地理优势以便躲避追杀,然而水源稀缺,不产丰盛的粮草。亚鲁王只得砸破家园拿上干粮继续上路,直至荷布朵疆域。“亚鲁王说,这是一片开阔的盆地,这是一处险要的山区。一条大河穿过盆地中央,大片田坝散在河的两岸。这里可逃避追杀,这儿能躲避战争。水源多多,粮草丰盛。亚鲁王说这里能抚养我儿女,亚鲁王讲这儿能养活我族人。”[4]226荷布朵疆域周围山势险峻,土地开阔,具备了水源充足、生态良好、安全庇护等条件。亚鲁王便将族人安置了下来,并以计谋夺取了荷布朵疆域,随后定都哈叠。
亚鲁王在艰难逃亡中定都哈叠,以祖居地为模本,重建亚鲁王国,展现了苗族的“归冢”意识。史诗《亚鲁王》以集市、糯米、鱼虾等地理意象构建了一个物阜民丰的祖居地。由于战争的因素被迫向西迁徙,在逃亡的过程中寻找新的家园,并定都哈叠。“羊天,成群的羊过江而来,大群羊逐浪跟随而到……稻谷种跟随而来,糯谷种尾随而到……青㭎树跟随而来,青㭎树尾随而到……万物跟随来了,万物尾随到了。万物跟随亚鲁王日夜迁徙来到哈叠。”[4]159亚鲁王定都后,史诗反复强调祖居地的动物、植物和粮种尾随而至,这既是麻山苗族携带家畜、粮种迁徙的曲折反映,也是麻山苗族“归冢”意识在民族精神灵魂中的存在性显现,更是麻山苗族反抗绝望的民族精神显现。亚鲁王定都后,派儿女到“勒咚”询问祖奶奶重建王国的经验,并得到“耶诺”“耶婉”指点,进行了“造日月、射日月”的工作,并先后派出蚯蚓祖先、青蛙祖先、牛祖先和老鹰祖先探索疆域。亚鲁王模仿先祖“开天辟地”,与儿女一同重组世界秩序,令士兵修筑长城,命将领守护王国。在亚鲁王的带领下,建立了龙集市、蛇集市、马集市、羊集市和猴集市等十二个集市,以此进行经商贸易。“我驻扎疆域带兵栽糯谷,我守护领地率将种小米。带儿女驻守疆域撒下麻种,领族人守卫领地种构皮麻。”[4]258亚鲁王还在新的地理空间重新种植糯谷、小米和构皮麻等植物,以构建起与先祖发详地相似的生态环境,以延续先祖的生存方式。苗族重建亚鲁王国,还原祖居地的整体地理景观结构,在新的地域上重建和“东方故国”一样符合人类居住的理想栖居地模式,这既是“回归故里”的心理补偿方式,也是族群身份认同的显现。
麻山苗族的“归冢”意识不但表现于史诗中,而且显现于麻山苗族的丧葬场所。“在麻山苗人的世界里,世间万物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山有山魂,树有树魂,各种动物都有灵魂,不能随意触碰,否则会受到罪恶的惩罚。”[7]形灭而灵魂不灭的灵魂观念是麻山苗族丧葬仪式的基石,也是麻山苗族祖灵信仰及送灵归祖仪式的发端和赖以长期维系、发展的前提,其观念信仰具体表现为“祖界观”和“三魂观 ”。在麻山苗族的信仰观念中,麻山苗族信仰灵魂不灭及人死后有三个灵魂。灵魂具有不同的归宿和存在的形态,一个住在坟墓里,一个回归到亚鲁王国与祖先相聚,一个守护在家中与子孙同吃住。在贵州省罗甸县、长顺县、望谟县和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等苗族地区,东郎在丧葬仪式上唱诵《亚鲁王》,通过追述先祖的坎坷经历和历史足迹,帮助亡灵穿越时空回到亚鲁王国。盖“芒就”仪式、竖桩仪式、征粮仪式和砍马仪式等均是为帮助亡灵回家而建构的文化行为。“芒就”是麻山苗人回归故里的“通行证”,其中蝴蝶意象、鱼意象、太阳意象、鸟意象和水稻意象是麻山苗族对亚鲁王国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强烈的精神回归生命意识。“芒就”由里外三层的三圈图案构成,最外围是由谷穗组成,中间层由蝶、鸟、鱼和鸡四种动物组成,最里层则是太阳及围绕于其间的太阳花。苗族先祖从东方故国迁徙至贵州麻山,太阳恰是从东方升起,因而以太阳象征着祖奶奶生活的祖居地。太阳花紧绕于太阳,寓为“太阳开花”,这是苗人对亚鲁王国的集体想象。鱼意象、鸟意象和蝴蝶意象反复出现于史诗文本及丧葬仪式上,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蝴蝶女祖宗从龙洞找回成千糯谷种,蝴蝶男祖宗从深坑寻来上百红稗种”[4]51,诸多动物在麻山苗族的历史中具有突出贡献,故苗族后人将蝴蝶等动物尊为先祖,将其绣在“芒就”上,于丧葬仪式唱诵中诉说它们的历史和丰功伟绩。亚鲁王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盛产糯米与鱼虾。丧葬仪式上,麻山人对糯米和鱼虾的使用十分讲究。孝子们以糯米供奉亡灵以及东郎的菜肴中必须有鱼等文化习惯,无不寄托着麻山苗人对故土的留恋。“芒就”作为回归故土的生命符号,蕴含着麻山苗人回归富饶和谐家园的期许守望。
《亚鲁王》以祖居地为依据重建亚鲁王国,体现了恒定的民族心理。富饶宜居的祖居地承载着麻山苗族文明的精华,镜照了民族区域的原始文化基因,蕴含着麻山苗族“归冢”的心理意识。麻山苗族以祖居地的地理景观构建全新但却同质化的地理空间,即通过周围相似的事物确立自我的身份认同和行为的合法性,以期达到与先祖沟通,以心理补偿机制实现身份认同。
三 地理意象与麻山苗族“归冢”意识的美学价值
“地理意象指具有显著地域特色和地理因素的外观之象进入到创作者的视野中,承载其主观情志并在代际演变过程中融合了接受者之‘意’所复合而成的文本中的‘综合体’;它作为文学文本的最小构成单元和元素,凝聚着创作者和接受者主体精神深处的地理基因与地域认知,并内化成文本中浓厚的地方情结,传递着创作者对于一个地域或超过地域的其他群体乃至全人类的精神观照。”[8]史诗的地理意象是苗族迁移历史与思想情志的主客观统一体,从中可以窥探出其浓郁的“归冢”意识。“归冢”意识是一个民族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不断被迫迁徙,但其集体无意识始终以族源地为灵魂旨归,是人类渴望过安定祥和生活的图式化显现。
《亚鲁王》以创世、迁徙与“回归”为线索,空间上形成了一个环形的叙事结构,蕴含着“建立家园”“失去家园”和“重建家园”的叙事意涵,贯穿着麻山苗族强烈的“归冢”意识。史诗以先祖开天辟地,创造世界为开篇,以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飞禽走兽等地理意象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地理生存空间。亚鲁王在和谐稳定的乐园上通过开垦田地、开辟市场、圈池养虾等进一步完善家园。集市意象、鱼意象、鸟意象和蝴蝶意象等构建了一个富饶宜居的祖居地。地理意象的流转引起了地理空间的流动,蕴含着强烈的“归冢”意识。由于外敌入侵,战争失败,亚鲁王在波丽莎、波丽露两人的掩护之下,成功带领族人迁出了含有不安定因子的居住地。亚鲁王带领族群迁徙多达30余个区域,先后走过哈榕冉农等辽阔平坦的坝子,走入哈榕玛嵩等山地,闯入哈榕崩索让等峡谷。地理意象的变化引起了地理背景的变换,通过详细罗列迁徙地名,构建起麻山苗族的迁徙路径,凸显迁徙历程的艰难性。史诗以重建家国大业为结局,“造日月、射日月”、探索王国疆域等情节的程式化表达,构成了史诗开篇与结尾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环形的叙事结构。史诗文本与演唱时空亦构成环形结构,并始终贯穿着“归冢”意识。史诗文本以亚鲁王带领苗族部落离开“东方祖居地”,自东向西迁徙为叙事内容,而麻山苗族的丧葬仪式则是为亡灵回归“东方故国”而构建的文化行为。在“吊唁”“砍马”和“节甘”仪式下,亡灵在东郎的引领下穿上草鞋,带上干粮,乘坐灵马,自西向东回归祖居地。史诗文本展现麻山苗族离开祖居地,而丧葬场合指向回归祖居地,二者之间相互补充,构成了环形结构。
地理意象构成了史诗文本空间,贯穿着浓郁的“归冢”意识,体现了沉郁悲怆的叙事风格。“亚鲁王携妻儿跨上马背,亚鲁王穿着黑色的铁鞋……亚鲁王带着撕碎了心的族群踏上了渺茫征程去前方路漫漫,亚鲁王领着裂碎了肺的族群踏上了浩瀚征程去前方路长长。”[4]157-158亚鲁王带领苗族部落一同迁徙,大人、小孩、老人齐上路,携带糯米饭,牵牛带马,背上粮种,他们深深眷恋着故土,但却被迫迁徙,产生了身心不一的撕裂感。每迁徙至一个新的地方,亚鲁王命人占卜,为新区域命名,传播民族文化种子。史诗高频重复唱诵动植物舍命相随,形成了语言上的回环婉转,深切表达了麻山苗人离开故土的无奈和辛酸。迁徙途中反复唱诵的祖居地动植物意象具有深刻的隐喻内涵,其集祖居地历史景观物质原型与麻山苗族主观“归冢”情绪宣泄于一体,杂糅了客观历史景观与认知主体主观意识。史诗中反复唱诵的“羊”“鸡”“狗”“猪”等动物意象,“稻谷种”“红稗种”“麻种”等种子意象及“青㭎树”“豆冠树”“五棓子树”等树木意象共同塑造一个充满乡愁记忆的叙事环境,将东方故国的归属感与迁徙流亡途中的漂泊感形成鲜明对照。人的行动被迫向西,灵魂却渴望往东,在灵与肉冲突、行为与意识相悖之下,显现了史诗沉郁悲怆的叙事风格。丧葬仪式指向了亡灵回归精神家园,体现了“向死而生”的乐观心态。在麻山苗族的观念中,死亡即是回归故里。“在麻山丧礼上是看不到悲哀的,大家欢快,也不讲究一定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大家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哭只是对亡灵的一个依恋,因为他离开了我们回家了,我们想念他,这个哭是短暂的离别而不是永久的离去。”[9]丧葬仪式上为亡灵准备草鞋、镰刀、饭箩、葫芦等“回家”物件,寄寓着生者祈盼逝者回归“东方祖居地”的美好期待,从而构成了悲喜交织美学特征。
综上,麻山苗族裔民理想的家乡在其祖居地,但因历史上历经多次战争而被迫迁徙,徙居之地的现状和浓厚的“归冢”意识的错位是苗族先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体现在《亚鲁王》这一史诗文本中。从史诗的地理意象的空间展演可以窥见麻山苗族大体上自东向西的迁徙路径,通过地理意象的叙事复现和印证了麻山苗族悲壮的迁徙史,表现了史诗沉郁悲怆的美学风格。“归冢”意识终极显现于史诗所操演的丧葬仪式上,苗族民众在死后魂归祖居地,虽对生命的逝去感到哀伤,但同时又对能魂归故土这一仪式感到幸福,展现了麻山苗族裔民特有的“向死而生”的文化心理,浓郁悲怆之极又蕴含着愉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