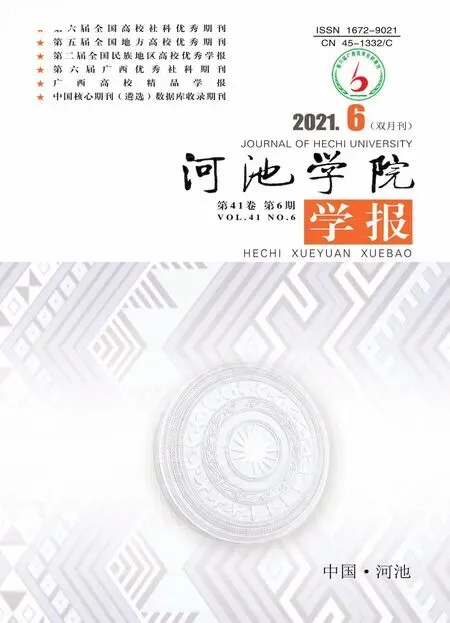文化象征·伦理困境·道德重建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张翎小说
张俊琦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聂珍钊于2004年“英美文学在中国: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文学研究方法,一经提出,便受到学界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推进。2014年,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出版使其系统精炼地展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1]5。在复杂的伦理关系中,“对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解剖,分析伦理选择的不同动机”[1]5,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经由聂珍钊的理论建构,刘建军作进一步生发,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瓦解使得“人处在一个由诸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要素编织的文化网络中,成为了卡西尔界定的‘文化人’……内外和谐是文化伦理之核”[2],从而指出现今伦理批评的主要形态是“文化伦理”,追求的是不同个体、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互补。
目前学界对张翎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伤、记忆、历史、女性、宗教、婚恋、家庭伦理、语言结构、意象分析等方面,明确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解读张翎小说,仅张建红《试论张翎〈金山〉中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3]一文。学界对于张翎小说家庭伦理方面的研究,虽未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导向,但其中所涉及的家庭伦理方面的论述给予笔者以启示。
伦理问题是张翎小说的关键症候。从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我们便可鲜明地感知到作品中复杂缠绕的伦理纠葛,到《金山》《余震》《交错的彼岸》《雁过藻溪》等小说文本,伦理更是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症结,同时也成为人物自我救赎的一把钥匙。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解读张翎小说,有助于发现张翎塑造“类型化”人物背后的文化寓意,而非仅仅将其当作叙事惯性的写作局限;同时,张翎将笔下的人物几乎都置于伦理两难的困境中,让其在极端的境遇中对道德与人性进行反复思考。人物历经“伤痛”,走向“救赎”的过程体现出作者怎样的道德倾向与伦理期待?
一、人伦关系的文化寓意
张翎出生于浙江温州,后赴加拿大留学,游走于多地而最后定居于多伦多市。于异国回望故乡,张翎以一段合适的审美距离,在中西双重精神资源的影响下,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自身与故土的关系”[4],对两地文化的差异与谐同处有更为理性的思索。张翎笔下的人物带有鲜明的文化象征性,被借以表达她对人类伦理本质的思考。
张翎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均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含义,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深受中国传统伦理和“五四”现代伦理思想的影响。《金山》中的六指是一个兼具中国传统与现代特质的女性形象。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伦理文化,在家庭伦理上提倡“三纲五常”。六指秉持传统伦理的道德教诲,以夫为纲,孝敬婆婆麦氏。六指与方得法“金山约”的承诺终生未得兑现,便是出于六指对麦氏根深蒂固的孝道伦理观念的影响,所以即便后来麦氏同意,六指也无法割舍这份伦理责任,让锦河替其赴约,同时达到减轻丈夫负担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山》中,“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在世俗普通家庭中并未走向极端,而更多地体现为亲亲之情。六指摒弃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糟粕而取其精华,维护了家庭的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六指身上的现代特质也是不可忽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力求打破封建伦理禁忌,主张男女平等,反抗包办婚姻,鼓励妇女解放,争取恋爱自由。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伦理环境中,六指不仅自己识文断字,而且要求方家众人都要如此,而这也是她与方得法情感关系的重要连接点。对知识的重视与传播体现了六指无形中所承担起的启蒙角色。六指拒绝包办婚姻,自断手指,将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已体现出现代独立女性的魄力。面对婆婆的刁难、误解和隔阂,六指小事忍耐,大事却不盲从,在碉楼事件中以血肉之躯感化婆婆,赢得麦氏的尊重。她被欧阳家族的后人称为“妇解分子”,足见其思想的超前性。
六指便是中国传统与现代伦理思想融合而成的一个象征符号,辐射至张翎其他众多作品也皆适用,如《交错的彼岸》中的阿九,她固执地将刚出世的金飞云从死亡之手中拯救回来,报答主母对她恩重如山的情意;在金家生意濒临绝境之时,她杀伐果断,以睿智的目光力挽狂澜,维护了家族产业;在教育上,她将金飞云送去公立学校读书;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上,她摈弃传统社会对封建女性的培养模式,使得金飞云从小便具备了现代思想和知识文化。阿九这种超前的思维方式,“关于女人修养方面的一些教诲,在不久之后的一个时代里,竟与某个伟人的想法不谋而合。”[5]36她们既承载着传统女性的坚韧、隐忍、感恩和孝道伦理思想,也具有现代女性独立、果敢、睿智的品质,是中国传统伦理和五四以来现代伦理思想的结合体。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大多来自西方,但理论经历旅行之后必定要适应中国本土的伦理环境,由此便生成新的伦理形态。从六指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张翎赋予其上的文化寓意:它是中西伦理思想和谐互补后的结晶,是新生成的一种既开放又有所约束的人伦关系,这也是作者所期待的理想伦理形态。
此外,张翎还将人物放置于他者的文化环境当中,在彼此的交流沟通中证明着当今世界伦理形态的核心,即不同个体、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互补,以霍米·巴巴的批评术语界定,便是文化的“混杂性”[6]113,这构成了张翎文学创作中鲜明的“第三文化空间”[7]的观察视角。张翎《羊》中的约翰在中国办学时收留了一个流浪的8岁女孩邢银好,后约翰以《圣经》中的路得为原型为其改名。在《圣经》中,路得一生虽颠沛流离,经历流浪与寡居,但始终未放弃丈夫的家园和丈夫所信仰的神。可见“路得”这个名字被赋予的文化内涵。邢银好与路得,中国名字与西方名字,隐喻着两种文化的糅合。路得在约翰身边成长,约翰将基督教的伦理思想播撒在了中国大地上,更种植在女孩的心灵当中。路得在约翰离开中国后接替约翰的事业,继任为鸿屋学堂的校长,且终生未嫁,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约翰所信仰的“神”。她身上的倔强、执著、博爱、救赎等思想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品格与西方基督教理念的融合。路得的教育奉献不仅点亮了约翰的后半生,也点亮了几代人的生命之路。她最后化为一座大理石雕像永存于人们心中。《邮购新娘》《劳燕》等篇章也有与之互文的意蕴表达。如果说《羊》代表的是西方伦理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那么《交错的彼岸》中,彼得与沈小娟的感情便象征着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书中这样描述彼得(韩弼德)初见沈小娟的情景:“看着小娟毫无粉饰干净光洁的脸,韩弼德心里突然动了一下。还处在中国蜜月情结里的韩弼德,那天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与心中景仰已久的劳工妇女形象完全重合的女人”[5]134,这个女人使他开始了小说《矿工的女儿》的构思。正是小娟那梳着两根辫子的质朴、“充满着感性世界的天真、尚未被理性世界的顾虑拘谨所污染”[5]201的中国革命儿女的美好品质吸引着彼得的目光,他甚至愿意为其加入中国籍,二人的结合是基于文化基础之上的人伦关系表征。
由此可见,张翎小说中的人伦关系均带有文化内涵,指向当今世界的伦理形态——文化伦理。张翎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描绘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互补、交汇杂糅,揭示了文化伦理的核心。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域出发,我们得以管窥张翎类型化人物塑造背后所寄予的伦理期待,而非仅仅将其当作创作局限予以批判;得以发现传统女性形象身上的复杂文化意蕴,而非将其当作固执守旧的封建女性、抑或仅仅是传统伦理文化的代表。她们也被张翎赋予了经由西方而来,历经理论旅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传播,而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的现代伦理思想。
二、伦理困境与道德追问
“斯芬克斯之谜”揭示了人的本质由理性(人头)与兽性(狮身)构成,善恶并存,二者的不同组合变化导致人物的不同行为表现,形成伦理冲突[1]36。张翎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处于大大小小的伦理困境之中,这构成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望月》涉及三角恋、同性恋、婚外情,《交错的彼岸》中的三角恋、母女隔膜,《金山》中的婆媳问题、锦河与亨德森太太的畸形性爱,《雁过藻溪》中的乱伦等伦理冲突屡见不鲜。通过分析小说人物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与他们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及伦理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世界的关怀和对道德与人性的思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相继暴露,人文精神的失落,信仰的缺失,以金钱与享乐为人生追求,欲望弥散整个社会。《望月》发表于1998年,时值“价值观念的混乱与退守,精神信仰的沦陷与坚持,生命体验的个人化与虚无感,成为世纪末和世纪初最重要的精神景观”[8]321。人们在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世界中沉沦,无所约束地追求物欲与情欲,道德理想也早已被束之高阁。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中理解《望月》,更可窥见作者的道德思考。当人性的无度扩张突破道德底线时,人性便需要被道德制约。亲情伦理的异化在《望月》中得以隐约呈现,卷帘费心帮妹妹望月办理移民事宜,目的是和律师分成赚取望月手中的费用,同时觊觎望月的钱财,希望妹妹可以与自己合伙创业。卷帘与黄明安的婚姻也不是基于感情之上,而是利益交换的结果。作品中的婚外恋更是屡见不鲜,似乎已成为生活常态。张翎还描绘出人对物质利益的无节制追求现象,颜开平超越道德底线,在他所承办的望月住宅区的修建当中,为赶工期而选择廉价建筑材料,结果阳台塌陷,导致一位儿童不幸身亡。颜开平最后家破人亡、一落千丈的结局象征着作者的道德警示。李方舟作为已婚男子,却与踏青暧昧沉沦:
若想拥有她,他需要打碎他过去拥有的一切。他的过去是已知的,他和她的将来却是未知的。在已知和未知中间,未知的恐惧便显得更为恐惧。哈姆雷特为了这个理由选择了生,他为了同样的理由选择了拖延——因为他吃准了她的死心塌地。因此,时不时地,他会提醒她,她的死心塌地绝对是她一厢情愿的。他在其中,原本是清白无辜的[9]173。
李方舟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在这段自白中显露无疑。张翎在这里将李方舟的内心独白与哈姆雷特作连接。出于理性意志,李方舟无法抛弃现有生活的一切:妻子、名誉、地位;但出于自然意志与自由意志,他也无法割舍与踏青之间的爱情。李方舟在这段关系中不断犹疑、徘徊、拖延,这是一出由伦理问题所引发的悲剧。在聂珍钊的解释中,哈姆雷特复仇拖延的本质原因是出于他在“杀父(继父)”与“为父复仇”之间所面临的伦理两难困境。可见,张翎以伦理为线将二者打通,同时作出她的道德警示。踏青的死亡终止了李方舟的懦弱与延宕,李方舟将永远生活在对两个女人的悔恨、愧疚与自责之中。这是一出由伦理酿造的悲剧,隐含着作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婚外恋问题的道德倾向。
此外,张翎还喜欢将人物放置于极端境遇中不断思考道德与人性的张力,“我喜欢这样的极致,极致是两端的极限的延伸,一端是飞翔的翅膀,一端是落地的双足。飞是一种伤痛,落地也是一种伤痛。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10]牧师由于其特殊的宗教伦理身份便成为张翎创造极端处境的典型代表。《羊》中的牧师约翰与女孩路得心意相通,但约翰却拒绝路得的告白,“约翰想告诉路得,他和她之间阻隔不是岁数,不是种族,也不是人群,站在他们中间的,只有一个威严的上帝。”[11]239“上帝”的阻隔便意味着约翰的理性意志控制住了自由意志,但他却终生陷入思念路得与自我忏悔的情绪之中。约翰对后人保罗说:“孩子,你知道当牧师的好处在哪里吗?你可以替你的朋友和你的敌人同时祈祷。你知道当牧师的坏处在哪里吗?你的朋友和你的敌人都同时忘了替你祈祷。”[11]236这段话反映出作者的道德倾向,牧师与普通人一样,有着相通的人性与“被祈祷”的渴望,但这重宗教伦理身份却阻碍了他们对正常人性的合理追求。除具有宗教伦理身份的人物外,张翎还将笔下的众多小人物放置于极端的伦理困境当中。如《金山》中亨德森太太深受病痛折磨,还要忍受丈夫的冷暴力,锦河便成为亨德森太太的救命稻草,由此发生“变形”的性爱。然而,作者并未对其进行道德谴责,而是极尽渲染亨德森太太的孤独处境,以及她和锦河相依为命的情感,并对这种异化的伦理关系表示同情和理解。《雁过藻溪》中末雁是百川的姑姑,有一定的血脉关联,二人却发生乱伦关系,面对女儿的质问,末雁解释道:“妈妈实在是,太孤单了”[11]123。历史遗留的创伤使末雁从小缺失亲情,内心敏感而又脆弱,有着对爱的极度渴望,但她对情感关系的隔阂使得婚姻最终走向破裂。孤独是末雁与亨德森太太甚至整个人类的永恒体验。“出于道德而反道德,构成的是叙事张力和对道德悖论的不断反思”[12],反映出作者对道德与人性限度的反复考量。
张翎在作品中为人物创设复杂的伦理困境,对道德与人性的关系问题进行辩证思考。张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便显示出她对社会现实、伦理道德的关怀。市场经济条件下,欲望的诱惑可能引发亲缘伦理、人际伦理,甚至政治伦理的异化。发表于1998年的这部作品便极具意味,有利于引起我们的道德反思。同时,道德准则也并非一成不变,人类有着共通的生命体验,比如孤独、流浪、对爱的追求等永恒的人生课题。牧师等宗教人物也无法免俗。此时,何为道德,何为反道德,便无法再作一刀切式的判断,但对个体的尊重与对温暖人性的呼唤则永远是张翎人性书写的道德旨归。
三、伦理救赎与道德重建
面对现代社会的诸多伦理困境,张翎将目光伸向历史的纵深处与大洋彼岸,试图寻求伦理救赎的窗口,发出道德重建的想象与诉求,作品中人物的伦理选择与情节构造反映着作者对未来的伦理期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些许负面影响,伦理危机与道德失范警醒着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经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张翎在《望月》中通过为人物创设伦理困境进行道德思考。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旋涡中沉沦、深陷伦理困境与伦理身份的危机而无处逃逸?通过《金山》,我们可以寻找到张翎的答案。艾米身处的是与《望月》共同的伦理环境,即现代社会欲望化的世界。方延陵携带着的沉痛的种族歧视记忆使得她对女儿艾米的教育缺乏中国文化的滋养,她力图将女儿打造为一个上等社会的精英,嫁给一个体面的白人。然而事与愿违,艾米“一辈子都在和一个又一个的无赖鬼混”[13]409,“根”的缺失使她无所归依、四处漂泊,流浪的感受始终与她如影随形。直到返归家乡,踏上“寻根”之旅,艾米才在体认家族历史的过程中确认了自我的伦理身份,从而牢牢抓住了自己的“根”之所在,消除漂浮之感,以自信的姿态立足于多元化的世界文明当中,最终选择在碉楼与外国男友马克成婚。也就是说,艾米通过“寻根”确认伦理身份,从而完成了自我救赎。《交错的彼岸》遵循同样的话语逻辑,历史的巨轮碾过金飞云与龙泉的爱情。黄蕙宁在目睹母亲与龙泉的偷情后面临亲缘伦理崩塌的危机,因此她选择逃离,将自己牢牢包裹起来,在爱情中平淡有余而激情不足,只是将他人作为停靠的港湾进行依附而不将真心全部地托付出去。然而,陈约翰如暗夜行路的火把照亮了蕙宁的心,她“明白了应该如何诠释善良和同情心”[5]253。但父母爱情的缺失,父亲原配的存在,母亲出轨的伦理禁忌始终如阴影般笼罩在蕙宁的身上,使她失去信任与爱的能力。因此,当蕙宁遇到陈约翰后,她本能地惧怕与逃避。“我多么害怕,那些短暂的光亮,还来不及让我们走入彼此就已经熄灭,把我们永远地隔绝在黑暗的水中。这种惧怕使我迟迟不敢迈出淌水的第一步路。”[5]253这是一出由伦理造成的悲剧,蕙宁面对这样的伦理困境,最终也是通过“寻根”的方式自我救赎。她从多伦多回到飞云江的怀抱,在与阿九小外婆的生死对话中寻找关于生命与爱情的答案。张翎在结尾处不无温情的书写暗示了蕙宁谅解历史、宽恕自我、打破心灵围墙的释然心态,而这一切是通过“寻根”才得以完成的伦理救赎过程。这从侧面反映了张翎处理伦理危机的方式,那便是回归中国传统,寻找民族之根,在“寻根”中确认自我。只有正视自己的过去,清楚地认识自己,才可以在纷纭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不至于迷失自我,而与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
张翎通过对人物伦理困境的创设、伦理危机的显现、伦理身份的迷失、“寻根”之旅的情节构造等方面,探寻自我救赎并从而进行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途径。由此再看《望月》,也可反证“根”之于张翎的重要性。《望月》中的人物尽管都面临大大小小的伦理困境,但中华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亲亲之情、孝悌思想、重义轻利等传统伦理观念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小人物。我们从作品中感受到更多的是望月、卷帘与踏青三姐妹相互支持的温暖,以及“荔枝阁”餐厅众人互相帮助、彼此理解的重义轻利的情感伦理关系,这支撑了他们在海外的生存与立足。
此外,张翎在向传统开拓的同时,也对西方伦理思想进行有价值的探索与汲取,这成为人物自我救赎的另一条途径。张翎小说有着明显的基督教伦理思想影响的痕迹。《望月》中的望月发现牙口是同性恋后,进入天主教堂,在“哈利路雅”“阿门”的呼声中寻求内心的平静与救赎。李方舟在与踏青发生伦理悲剧后,最终参加基督教无国籍医生组织的肯尼亚计划以救赎罪孽。《羊》中路得在约翰基督思想的引领下将爱遍施大地,终生在鸿屋学堂作无私的教育奉献;羊阳在约翰后人保罗的引领与开解中逐步扫除人生阴霾,拨开云雾见青天,实现自我救赎。
在对中西伦理思想的双重审视中,张翎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伦理期待,发出了道德重建的呼吁。首先是要建立健康和谐的亲缘伦理关系,对历史遗留下的创伤以宽恕、包容、谅解的心态去面对,重建新生活的信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亲亲之情、和谐思想,融汇道家、佛家对生命的理解和基督教“救赎的爱”的思想的有机结合。《雁过藻溪》中,黄信月将历史创伤传播至下一代黄末雁身上,亲情伦理的缺失导致末雁内心缺乏自信与安全感。她对于情感关系敏感而又脆弱,对爱的过度渴望与对亲密关系感到隔阂的矛盾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类似的意蕴在《余震》《空巢》等文本中也有体现。《空巢》中的李延安因童年亲情伦理的丧失导致她在婚姻中的不安全感,最终因对何淳安的误解而走向死亡。《余震》中王小灯因地震后母亲的一句“救小达”而留下一生的心理创伤。这是由于亲缘伦理的断裂造成的创伤记忆,影响着小灯未来的生活。她与丈夫、女儿关系隔膜,争吵不断,生理上总是伴随焦虑、头痛、失眠等症状,而这所有的一切痛苦都在小灯与母亲见面的那一刹那被治愈。因此,小灯人生的悲剧表面上是自然灾难造成的,实质上是因伦理问题而酿成的。由此可见张翎对中国传统亲缘伦理关系重要性的强调,即一个稳定、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对于子女的精神状态、心理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雁过藻溪》中的黄信月尽管受到藻溪乡民的伤害,但他们在其遭遇危难时仍给予帮助,使她和丈夫躲过了政治风暴并收获了藻溪人对她世世代代的感恩。信月过世之前交代女儿将骨灰带回藻溪,这意味着信月对历史的完全宽恕,也希望女儿可以宽恕自己,谅解那段历史。《余震》中的小灯在回国与亲人相见后实现了自我救赎,意味着她对亲人的宽恕。鼓励温暖和谐的亲缘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历史的和解与宽恕是张翎所要建构的道德方向,反映了张翎对人性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
其次,人际伦理关系应建立在真情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空巢》中的何田田将春枝对父亲的照顾、男友秦阳与自己的恋爱都当作一种利益关系加以防备,这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至上的道德观念,将人与人的关系都当成金钱关系加以理解,这将会导致信任危机的问题。张翎以情节构造反映自己的道德情感。何田田在电梯事故的极端困境中感受到了秦阳的真情相待,看到父亲和春枝其乐融融的生活画面。这种温情叙述表明了张翎的道德倾向,即否定现代人以利益衡量感情的存在方式,承认只有真情才可以感化一切冰冷坚硬的心灵。在《望月》中,所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婚姻都走向破裂,如卷帘为立足于加拿大而和黄明安结婚,后来却遇到了她爱慕的对象李方舟;望月对颜开平只有报恩之情而无爱情,二人的灵魂交流频频受阻。然而,作者还为我们呈现了以真情为基础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比如望月与宋世昌,二人同是艺术家,有着灵魂上的共鸣,彼此认同对方身上不沾俗世金钱气息的超脱气质和行为处事方式而成为灵魂伴侣。又如“荔枝阁”众人在各自遇到危难时不计利益的互相帮助。凡此种种,均呈现出中国人在异域没有被物质冲昏头脑,彼此真情相伴的独特伦理景观。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信任、尊重、和谐”是作者所要建构的现代伦理道德观念。
四、结语
伦理问题是张翎小说的重要症候。文化伦理是当今世界伦理形态的核心。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多元文化的滋养铸就了张翎伦理思想的形成。张翎笔下的人物是中国传统伦理、西方基督教伦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解放人性、独立平等的伦理思想的象征符号,体现了张翎多元、开放、平等的文化视域。张翎将人物置于伦理困境中,让其反复思考道德与人性的张力,探索人性的限度与道德僭越的可能性。张翎向内寻根,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如家庭伦理、义利之说等思想抵拒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金钱和利益为核心的人伦关系,警醒中国人在席卷而来的经济大潮中要保持理智,不要被金钱所异化,建构以真诚为核心的现代伦理关系,实现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转化,同时在寻根中明确自身的伦理身份,实现对历史的宽恕与对自我心灵的救赎,只有直面自我才可以更好地面向世界与未来。另一方面,作者向外开掘,吸收基督教伦理文化中的宽恕、谅解、博爱等思想,以温情脉脉的目光注视芸芸众生,探索人的终极意义与苦难救赎的可能性。张翎的伦理思想与道德思考体现了她对社会的关怀与对至善人性的呼唤,对现代人格真善美的形塑、人伦关系的和谐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