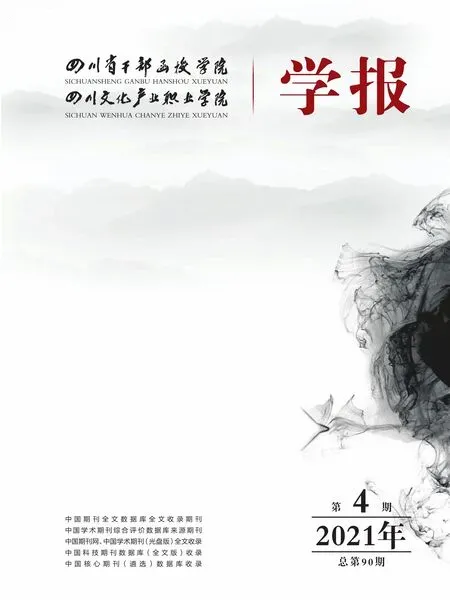音乐的景观:流行音乐视觉表征的分离与超越
◇ 王誉燃 ◇
美国理论家威廉·米歇尔在其著作《图像转向》中指出:“图像表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①魏毅东:《视觉殖民与审美听觉失聪——视觉文化语境下的音乐及其命运》,《人民音乐》2010年第11期。就连音乐这种纯粹的听觉体验,在今天也不可避免地为视觉形象所浸染。流行音乐与资本的关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在资本的推动下,流行音乐与视觉图像混杂在一起,“歌曲的‘文本’,也不仅包括词曲、演唱等声音,而且包括海报、宣传画、写真集、MV、现代光电舞台美术诸如此类的更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视觉表现形式”②张燚:《被观看的音乐——流行歌曲的视觉文化认知》,《人民音乐》2010年第5期。,后者可将其看作音乐的视觉文本。音乐的景观就是以音乐的视觉文本为物质基础,运用技术手段不断堆叠,从而成为延展到我们周遭的奇观场景。它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我们从未看见的、惊心动魄的、梦幻离奇的新兴事物。而本文所关注的则是景观背后的言说策略,即音乐景观的符号话语以及在奇观场景中看与被看关系背后的权力机制。
一、表征的建构:流行音乐的奇观世界
音乐的视觉表征既是对音乐的消解,也是对音乐的建构。从前者来看,音乐的视觉表征即中心不在场的文本,前者意义上的建构过程就是音乐传统的听觉审美逐渐消解的过程。从后者来看,其亦是一种视觉文化实践,是一种能够捕捉某种意义的在场,而这种意义的建构则是另一种兴起的、视觉的话语的建立过程。无论从解构还是建构的角度来看,音乐的视觉表征都不是关于音乐本身的再现,而是对不在场中心的再现。这种表征在当下更多地呈现为一种重复的奇观,数量庞大且形式各异。
在音乐视觉化发展态势的驱动下,太多的复杂因素使得流行音乐的视觉形象占据了主要地位,音乐本身的空间却被压缩。流行音乐不同于西方传统音乐追逐于音乐的形式,更多呈现的是对意义的表达。例如,摇滚音乐作为广义流行音乐的一种形式,它的主题大致可分为四类:情感的羁绊(尤其是爱情)、人生的困境、集体的记忆和日常的感悟。当一首歌曲的目的不在于“声音”,而在于“意义”的时候,那么视觉成分的加入的确是省时、省力且行之有效的。用MV等影像材料来帮助表达音乐的内涵是一种经典的方式,但是在视觉图像泛滥的今天,人们往往并不关注音乐本身,反而更关注MV,受众对音乐的感知和理解普遍处于依赖视觉影像的状态。因此,音乐本身留给听众的想象空间便被视觉影像塞满,听众对音乐的体验完全由官方“解读”引导,听众的感知自主性就这样被抹杀了。音乐的留白也许本身是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的,但由于影像的填充,这样的留白就并不起作用了。
摇滚音乐尚且有某种态度和意义的表达,一些网络热门歌曲则完全只是为了竞奇,一味吸引大众的眼球和流量。这些网络热门歌曲,因其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简单易懂,再加上搞笑、低俗的MV影像,红遍大街小巷。例如,筷子兄弟的《小苹果》MV讲述的是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在毒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的故事。在影像的呈现方式中,两位男主唱几乎全裸,重点部位闪烁着的马赛克欲盖弥彰。其中一位男扮女装反串夏娃,金色大波浪的假发、纤长浓密的假睫毛、鲜红的嘴唇、扭捏做作的表情以及浮夸的演技,实质是以丑化的方式来博得大众一笑,让人们在这些搞笑、恶俗的音乐画面中,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与烦恼。尽管这则MV是典型的叙事性文本,但本质上它是空洞且毫无意义的,更不要说许多歌曲的MV几乎就是演唱者的写真影像,永远都是场景、服装和动作的变换。
如果说影像只是音乐的视觉表征的平面形态,那么朝圣般的演唱会、“live house”等音乐现场则是主体亲身参与的视觉表征生产与消费的现场。那一束束缤纷繁目、璀璨迷离的灯光,将观众带入迷幻、兴奋的状态,令人陷入一阵又一阵的震惊和眩晕之中。就如同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描述的达达主义的艺术作品一般,“他们的目的是想耸动公共视听,以迷人的表演和声响来吸引观众耳目,惊世骇俗,冲击观者和听众,颇具杀伤力”①〔德〕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3页。。与其说光束扫射着台下的观众,不如说它是在“撞击”观众。这些强烈而刺眼的灯光,快速移动,一晃而过,被扫射到的观众因这“撞击”愈发兴奋。相比传统音乐会那样的深思冥想与美学判断,当下流行歌手的演唱会更像是布尔乔亚阶级欢乐的现场,是一种暴力的消遣,将音乐变成了绯闻。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音乐传播中的视觉元素从专辑封面、音乐海报、MV等二维影像发展到如今演唱会舞台上的虚拟现实、三维全息立体投影等模拟现实场景的出现,音乐世界看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是这些视觉经验都不是对音乐的再现,而是视觉霸权在音乐界的出场,并在音乐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璀璨夺目的奇观场景。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其音乐本身不是唯一主题,流行元素、时尚符号早已将其堆砌成一个形象的王国。
二、分离的产物:从音乐生产到形象诞生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①〔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第36-37页。整个社会生活成为一种表现,一种景观的巨大积累,真实与存在分离。在德波的分析中,“分离是景观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它包括工人与产品的分离、生产者之间直接交往的分离和非劳动时间的分离”②〔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第36-37页。。这里的分离最终走向的是人与真实世界的分离,人与其内心的分离。从某种程度上讲,流行音乐作为文化工业的产品,被制造出来的需求,亦是人与现实世界分离的产物,悄无声息地占据着人们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与形象纠缠不清,成为滥用的目光和虚假的意识的场所。
文化工业大行其道,流行音乐走向了异化的具体制造,其生产沦为一种片面的劳动。“大数据写歌”的创作模式让部分流行音乐似乎成为车间流水线生产的产品。一些文化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实时捕捉受众的听歌喜好,截取到最受听众喜爱的歌曲、旋律以及歌词信息,再将这些最受欢迎的歌曲作为模板,仿照着制作出一批新的歌曲。这种模式的构建不需要创作者绞尽脑汁、耗费心力进行创作,而是凭借大数据技术的演算规则来一步一步地生产。音乐的个性似乎在这样的制作过程中被消解了,完全沦为迎合大众的抽象商品。这样的音乐在城市中四处扩散,大街上、商场里随处都可听到,“音乐不再在安静中倾听,它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然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背景噪音,音乐不再具有意义”③〔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0页。。可以说,这样的音乐钝化了倾听,掩盖了真正的音乐,是一种对音乐的否定,走向了音乐的反面。
如果说依靠大数据技术制作出来的音乐是对音乐灵魂的消解,那么短视频里的背景音乐则是音乐被肢解的证据。现今在大众文化中极为流行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常常将一首完整的歌曲进行拆分,将最顺耳或是最热门的几句歌词和旋律(通常是副歌部分)截取出来,作为十几秒视频的背景音乐,在“视频流”里不断重复、重组,开场即高潮。在这里,音乐不被当作音乐,而是一种博人眼球的装饰。在表面个体性的情况下重新被组合,这是碎片化、匿名性和重复性的噪音音乐,而这种噪音又反过来“教化”着人们,侵占着人们劳动之余的休闲时间。
仅从音乐的角度观察流行音乐的景观只是冰山一角,在当下,流行音乐与形象才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形象并不仅指附着音乐的视觉制品,如唱片封面、海报等,更是指那些视觉制品所塑造的充满意味的形象:一个人、一件物甚至一件事。形象在这里只是一个能指,关键是其背后丰富的所指。
早在摇滚音乐盛行的年代,年轻人就将摇滚音乐视为喉舌,表达他们的叛逆、梦想与需要。由此,摇滚明星的形象成为无数青年所追随的对象,他们模仿歌手的穿着、发型、行为方式等,例如朋克风格的“鸡冠头”、衣服上的破洞、金属铆钉、黑色皮夹克等。直到现在仍然有年轻人穿着印着已故歌手形象的衣服,将有关他们的图像展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多数时候音乐并不在场,只有形象在场,他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由消费社会所诱导的、大众所共同认可的符号。
如果说早期的摇滚人物的形象尚有态度可表达,那么如今的流量明星则完全是资本市场所打造的虚假形象,是促进消费的工具。流行音乐的商业效益主要来源是视觉上的形象资本。这种形象资本主要投入对歌手外观的包装和宣传,以此来获取流量和关注,就如同杰姆逊指出的,“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①〔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除了歌手的服装、发型、身材管理等外部形象,关键在于“立人设”。歌手的出身、性格都是按照大众的喜好所设立的,例如《创造101》综艺选秀节目中的杨超越就有多个人设:“全村人的希望”——“草根人设”,业务能力较差但都顺利晋级——“锦鲤人设”等。这种“草根”“锦鲤”人设的建立拉近了她与观众的距离,因为大部分观众都是普通人,都有幻想过自己“走运”的时刻,而杨超越的出道就证明了这种希望可能实现。这种偶像文化和粉丝经济实质就是对音乐形象的一种炒作和包装,进而在互联网中创造新一轮的“精神信仰”。音乐在这里变得无关紧要,它已经成为形象的附属和赚取流量的工具,而重要的是“符号的劳作”。
景观建立在对精确技术理性进行不断展示的基础之上,“将人类权力流放到一个彼世的技术实现,它是人的内心已经完成的分离”②〔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页,第12页,第21页,第20页。。流行音乐作为景观的一部分、分离的产物,借着景观技术的“东风”,进行着精确的工业生产的扩张,建立起自身的形象王国。音乐的实质本是高度抽象化和秩序化的声音,在技术的催化下,变成了迎合大众口味的一种氛围、一种形象,从“被倾听”转变为“被观看”。人的身份亦发生了改变,从音乐“听众”变成音乐“观众”,从主动倾听转变为被动凝视。
三、拟像的超越:音乐景观的权力渗透
在《景观社会》中,德波意图宣告“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而今已经过渡到它所指认的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③〔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页,第12页,第21页,第20页。。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真实世界沦为简单的图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当然,这种表象化并不只是指现实社会中处处充满着图像,而是指人们用图像去把握世界,用形象表征实践,将图像看作真实本身。在流行音乐中,由于形象占据主体,人们忽视了音乐的声音输出,使得流行音乐中出现了很多传统音乐文化中没有的现象。
图像本是用作对音乐的宣传,如今反而主客颠倒,让音乐成为图像的拟像。宣传海报、音乐影像甚至歌手的形象都应该是为提升音乐的传播所做的努力,但是现在视觉占据主体,音乐反而成为一种氛围。“景象成了决定性的力量,景象控制欲望,欲望决定生产”④〔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页,第12页,第21页,第20页。。换言之,这些视觉图像、形象符号刺激着观众的需求,然而这种需求并不是对音乐的需求,而仍然是对图像的需求。由此,便构筑了“一个非生命之物的自主自足的自在运动”⑤〔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页,第12页,第21页,第20页。,即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人们原来意图用唱片来保存演出,而现在演出只是成功地作为唱片的拟像。”⑥〔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图像传播本是为音乐传播服务的,而如今在图像的自主运动中,音乐反而成为图像的附属。
景观的自给自足亦表现为一种实证性,或者说是教条性。在景观社会中,“出现的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①〔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第19页。,主体在景观中并没有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而是一个纯粹的接收者,并对此决然不知。例如,流行音乐的畅销排行榜并不是带有某种客观性或是中立态度的排名,而是一种对自身逻辑的合法性的证明。它就像景观社会中的指示牌,其意义本身并不是指向何方,而是看见它就证明了你存在于这个世界中,抑或是这个世界就是存在的。此外,畅销排行榜还掌控着流行音乐市场的秩序,它表明了什么样的音乐应该被生产,谁的歌曲应该被听。畅销排行榜创造销售,但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它为事物引导、选择以及赋予价值,否则这个物品将会一无是处,无处殊异,随即黯然流逝。
演唱会既是音乐再现的场所,同时也是“权力”出场的地方。在演唱会现场,人们以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沉醉地观赏着歌手制造和操控的景观性演出。一方面,舞台上的歌手,并不是作为个体出场的,而是作为一个有关其过往所有影像堆叠在一起的巨大形象,并且这个形象现场仍然在不断更新。新的场合、表请、动作、服装等,不仅吸引着现场观者目光的集结,更是通过视觉媒体将这一景观现场扩散得更远,其“权力”也随之扩散得更远。另一方面,处于黑暗之中的观众,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身份在进入场馆时都被消解了。在这里,贵宾座、嘉宾座、普通座等划分出新秩序,更是“权力”规则的分布。在这种区域划分下,观众目光可以纵向观赏到舞台中心的形象,却无法在横向间随意地交流。“景观的本质就是拒斥对话”②〔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第19页。,这种规则阻止了他们之间的意见交换,“因为观众是被组织起来的一个接受权力影响的整体,他们的权力被约束和消解在视觉机器中”③冯玲:《视觉文化时代的音乐“景观”——流行音乐的视觉化传播与审美互动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单位论文,2019年,第100页。。舞台上灯光绚丽夺目,而舞台下的昏暗一片,忽视了个体的存在。在景观的迷入之中,人们只能单向度地默从。
景观从来倡导的都是一种“不干预主义”,它引导视线,将权力一点一点渗透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平面广告、电子屏幕、摄影杂志、电视节目、演唱会、短视频、网络资讯等各种视觉媒体层出不穷地出现在眼前,人们难以说出一个“不”字。人们看似是在主动选择歌曲,但本质是每一种选择背后都有被操纵的痕迹。在流行文化所造成的广泛的、娱乐的迷惑之下,人们才是观看的对象,被“投喂”的群体。这种潜移默化的身份转变,即从观看的主体到观看的对象,就是视觉景观的权力逻辑。
结 语
流行音乐是文化工业的商业产品,沉溺于消费社会的运作逻辑中,这无可厚非,但是其接受对象是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其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在这个以形象、流量和利益来判断音乐价值的时代,音乐的本质逐渐被抛弃,“音乐已经成为一个人显露自己的素养的借口,而非一种生活方式”④〔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5页。,音乐成为装饰,其功能止步于氛围营造。这似乎消解了音乐最重要的性质,即艺术的本质——直抵人的内心深处。“视觉文化批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充满虚假意识的电视图像中呼唤价值理性的介入,在充满物质欲望的画面中要求人文精神的到场”⑤曲春景:《论视觉文化批评的当代价值》,《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而我们就是要呼唤音乐本质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