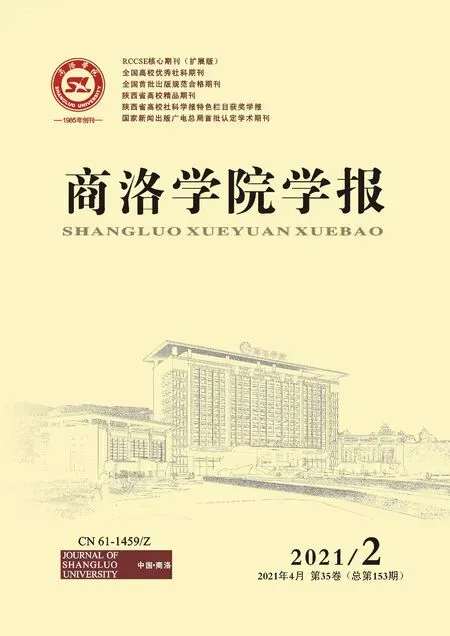基于六经辨治思想的慢性肾脏病诊治研究
黄笛,谭颖颖
(1.商洛学院 健康管理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2.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陕西咸阳 712046)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肾脏结构和功能进行性损伤,且病期超过3个月。该病威胁着全球大量人口的生命健康,有调查显示,至2017年,全球CKD患病人数为6.975亿,中国约1.323亿患有CKD[1]。CKD起病隐匿,呈慢性进展,最终必然出现肾小球硬化和间质纤维化改变,进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2-3]。临床上,该病的治疗多以对症治疗为主。至后期,随着病情加剧,患者不得不进行费用高昂的肾脏替代疗法。中医治疗慢性肾脏病有着临床效果明显、经济实惠的优点。传统中医认为慢性肾脏病属于中医的“水肿、癃闭、关格、虚劳”范畴,病机为“本虚标实”。本虚主要包括脾肾阳虚、肝肾阴虚、肺肾两虚等,标实主要表现为水湿、淤血、痰浊。治疗上标本兼治,内外治法同用。基于前人的理论,部分医家在张仲景所著《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下,推崇经方治疗CKD,并结合六经辨证,能够更加准确的辨证论治,取得较好的疗效。黄克基等将《伤寒杂病论》中具利尿之功的方剂分为“发表利尿剂”“和枢利尿剂”“温里利尿剂”,用以辨治肾病水肿[4]。杨霓芝教授在仲景《金匮要略·水气病》的指导下将肾性水肿分为“风水、皮水、正水、石水、黄汗”,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辨治方法[5]。王祥生教授以六经辨证为主要原则,治疗IgA肾病并取得确切效果[6]。杜雨茂教授在临床治疗慢性肾病的过程中,灵活运用六经辨证,并丰富了经方治疗慢性肾脏病的辨证方法和方药[7-8]。六经辨证是《伤寒论》的主要学术思想,是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以六经辨证的方式辨治慢性肾脏病,是中医治疗该病的理论创新,使辨证方式更加具体和系统,同时为临床治疗慢性肾脏病提供新的思路。
1 六经辨治慢性肾脏病的理论依据
1.1 六经辨证概要
“六经”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实谓三阴三阳经脉,即太阳、阳明、少阳和太阴、少阴、厥阴。按照六经的循行走向和脏腑所属,分为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手太阴肺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肾经、足少阴心经、手厥阴心包经、足厥阴肝经。《伤寒论》首创六经辨证理论体系,阐释了外邪入侵,从“外之藩篱”到“半表半里”,再入里进入阴经,最后传至“两阴交尽”,整个疾病过程的发展规律和证候特点,并提出相应的治法方药。六经辨证一经提出,便成为中医辨证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古至今应用于临床未病先防、治疗疾病和判断预后,已经发展成为相当成熟且极具古代哲学思维特色的辨证体系,体现了我国传统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和“阴平阳秘”的恒动观。后世医家深入探究了仲景六经辨证的深刻含义。祝味菊言:“太阳之为病,正气因受邪激而开始合度之抵抗也;阳明之为病,元气愤张,机能旺盛,而抵抗太过也;少阴之为病,抗能时断时续,邪气屡进屡退,抵抗之力未能长相济也;太阴少阴之为病,正邪相搏,存亡危急之秋,体工最后之反抗也(《伤寒新义》)。”时振声[9]、吴玲等[10]也认为六经辨证的全过程是疾病正邪消长的反应,说明六经辨证体现了人体正邪的消长,反应了疾病状态,为判断预后提供依据。徐宋斋[11]、张喜奎等[12]认为《伤寒论》辨证与辨病并重,表明六经辨证中辨证、辨病、辨症的关系,全书以经统病,按病析证,随症出方。宋远忠[13]、岳旭东[14]、张发艳[15]认为六经辨证是从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四时六气、六经运气的角度说明疾病的变化,六经辨证的思想实质上是基于人体与地理方位、自然气象变化规律间的关系。而今,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和现代医学的发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式发生变化,但仍然有许多医家运用六经辨证的方法辨治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内分泌疾病等,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临床效果。对于临床治疗缺少靶向药物的慢性肾脏病,六经辨证诊治慢性肾脏病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1.2 六经辨证对慢性肾脏病的认识
慢性肾脏病是一个病因复杂、起病隐匿、慢性进展的疾病,在整个病程中,临床表现随病情的变化而变化,且由于病理类型的不同,临床表现各异,故在辨证时,不可执着于少阴肾本脏本经,而应秉承仲景“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原则,精准辨证。慢性肾脏病由初期至末期,发生发展遵循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腑及脏的特点,辨证过程中,可将六经作为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杜雨茂[16]认为,慢性肾脏病的整个发病过程与《伤寒论》六经传变规律相符。慢性肾脏病的不同阶段,临床表现不同。CKD 1~3期患者可以无明显临床表现,部分患者表现为乏力、腰部困痛、夜尿频、易感冒等轻症。从六经辨证角度,该病始于太阳经,可见卫外失司、膀胱气化不利等相应病症;随病情进展,可进一步入阳明,见阳明腑实诸症;病入少阳半表半里,可见枢机不利、胆郁诸症。至CKD 4期,上述症状加重,可出现多尿、血尿、尿浊、水肿、眩晕、恶心呕吐等。依六经辨证,该期可对应少阳、三阴经证,阳气渐衰,虚寒渐盛,由阳转阴,由表入里,出现脾肾阳虚、寒湿内盛诸证。进展至CKD 5期,发展为终末期肾病,除了肾功能衰竭,还可出现心功能衰竭、严重的水、电解质紊乱、中枢系统障碍等,可危及生命。此时,该期已病入三阴经,阳气衰竭、阴寒内盛、预后极差,若失治误治,甚至发展为阴阳离决,上厥下竭的将死之证。慢性肾脏病的分期依据是肾小球滤过率这一指标,而同一时期病人的临床症状,仍有很大差别。而六经辨证主要依据临床症候、脉象、舌象等判断,因此,慢性肾脏病的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严格对应六经辨证中各经的证,具体临床运用因人而异,应具体分析。
1.3 慢性肾脏病的发病传变
《伤寒论》中,六经病的发病方式有六经单独为病;有两经或三经同时发病的“合病”;一经未罢,而另一经病又起的“并病”。基于《伤寒论》六经辨证分析慢性肾脏病的发病方式同样有单经发病、合病和并病。田子鹤[17]对172例慢性肾小球肾炎病人进行临床研究得出,单经病中以少阴病最为多见;二经合病中,太阴/少阴寒化证最多,其次为少阳/少阴寒化证、太阴/少阴热化证、少阳/太阴病。临床上,慢性肾脏病单经发病可见于不同时期,一般起于太阳,太阳经主一身之表,外邪入侵首犯太阳;也可直中太阴或少阴,来势凶险。合病也常发生在慢性肾脏病的病程中。如太阳与阳明合病,见慢性肾脏病初期,太阳受邪,见畏寒、发热、腰痛、脉浮,阳明合病,出现大便难、小便频数、潮热等症。太阴与少阴合病,在慢性肾脏病患者中十分常见,太阴脾病,己土不升,少阴肾虚,命门火衰,脾肾同病,则火不暖土,寒湿乃生,水木陷矣,临床上常见慢性肾脏病患者同时出现以食不下、腹痛下利、呕吐为症的太阴证和以畏寒肢冷、倦怠乏力为症的少阴证。慢性肾脏病也可见少阳与少阴合病,少阳三焦之火,温水脏,又“水之所以善藏者,三焦之火秘于肾脏也,此火一泄,陷于膀胱,实则下热而癃闭,虚则下寒而遗溺(黄元御《四圣心源》)”,故慢性肾脏病入少阳往往同时累及少阴,二者合病出现口苦、咽干、多尿或无尿等症状。并病最为常见的是太阳与少阴并病,见慢性肾脏病入少阴,肾气衰少,虚寒内盛,正气不足无以抗邪,感受外邪,外感风寒则见发热汗出、体痛、呃逆等太阳诸症。
《伤寒论》中,疾病的传变方式有循经传、越经传、表里传三种。循经传即按照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顺序传变;越经传是指传变时越过一经或两经;表里传是指互为表里经的两经之间的传变。从《伤寒论》六经辨治慢性肾脏病的方式看,慢性肾脏病的传变方式同样符合以上三种。循经传是慢性肾脏病较为常见的传变形式,该病呈慢性进展,且不可逆,从最初的太阳经轻证逐经传入,渐入三阴,最终发展为终末期肾病。越经传见于慢性肾脏病,如在患病初期未积极治疗,或在某些加重因素的作用下,如服用肾毒性药物、过度劳累、血压升高等,可迅速恶化,直接由慢转急,快速进展至终末期,这时即传入少阴、厥阴经,危在旦夕。表里经的传变见于慢性肾脏病,如一些慢性肾脏病始于急性肾盂肾炎,起初太阳膀胱经为病,水热互结,水气不利,见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若日久失治,形成肾间质纤维化,造成不可逆损伤,则转为慢性,由腑及脏,传至足少阴肾经,最终转变为慢性肾功能衰竭。了解慢性肾脏病的发病与传变能够在病及各经之时,根据六经传变规律“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做到“既病防变、已病防传”,对于慢性肾脏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2 六经辨治慢性肾脏病
2.1 辨太阳病脉症并治
太阳经主一身之表,病犯太阳者,外阳首当其冲。太阳病提纲:“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慢性肾脏病初期感邪而发,或急性肾病初得,风寒外侵,卫阳失守,肺失宣降,风水相搏,可见眼睑浮肿,恶寒、发热、头痛、脉浮。此期即慢性肾脏病病在太阳经,病情尚轻,表阳受邪而正气不虚。急性肾小球肾炎发病一般有前驱感染,常见于上呼吸道感染等引起的链球菌感染。素体阳虚者,外感风寒易伤及肾,患急性肾小球肾炎,病仍在太阳,见发热恶寒,身疼腰痛,眼睑浮肿等。该病可因失治误治,病情迁延不愈而转为慢性肾脏病。素体阳虚者,易感受外邪,感邪易损及阳气而患慢性肾脏病,初期卫气失司见畏寒、恶风。风邪易袭阳位,与水相搏,则颜面或眼睑浮肿;寒邪束表,经气不畅则体痛。
治疗上,以发汗解表为法,外窍通则经气行,内外调达,则病症可除。陈英兰等[18]以充足的理论依据证明了汗法治疗慢性肾脏病的可靠性,认为该法能够兼顾表里邪气,调和营卫气机,肺脾同治,助肾行水。肺为水之上源,肺失宣降则水液输布失常,与风相搏,而成浮肿;肺气不宣,则肾水难行,故宜发汗开通腠理行水道,疏解表肌行经气。麻黄汤是发汗解表的代表方剂,可在早期应用。方中麻黄、桂枝发汗解表,解肌祛风;杏仁降逆;甘草调和药性,兼培土建中,全方具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之功。程偲婧[19]用阿奇霉素尾静脉注射,腺嘌呤连续灌胃建立慢性肾脏病模型,以不同剂量麻黄汤灌胃治疗,结果表明该方能够改善慢性肾脏病模型大鼠肾脏的结构和功能,也表明了汗法开通玄府治疗慢性肾脏病的有效性。发汗的程度以“取微汗”为宜,汗不如法则阳气随汗液消耗,水液失制泛溢,水气凌心则心悸,水湿浸渍则筋肉跳动,上犯清阳则头眩,而表邪仍在,病在太阳。
另外,若太阳表邪不解,随经入腑化热,水热互结,则患急性肾盂肾炎,症见发热,小便短赤,渴欲饮水等。该病失治可由急转慢,发展为慢性肾脏病。治疗可选用猪苓汤化裁,猪苓、茯苓、泽泻能利水渗湿,茯苓又能补益脾肾;滑石利尿通淋,还能导热下行;阿胶具滋阴之功,全方育阴清热利水,可解急性肾盂肾炎之水热互结,阴液耗伤。岳沛芬[20]善治中老年女性泌尿系统感染,认为猪苓汤能够疏泄湿浊,又能滋润真阴而不留瘀滞;赵波[21]、邓伟[22]也分别采用猪苓汤加味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临床观察发现该方有明显的治疗效果。总之,太阳为病,虽肾阳受侵,但病邪轻浅,祛邪为主兼以扶正,可痊愈或控制病情发展;若不加重视,或治疗不当,则病情继续进展。
2.2 辨阳明病脉症并治
急性或慢性肾脏病病入阳明经,可因病邪直中阳明所致。《伤寒论》阳明病提纲:“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阳明经之慢性肾脏病,以热盛伤津为主要病机,特别常见于以糖尿病为原发病所致的糖尿病肾病;或是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感受外邪,未及时治疗,外邪进一步入里化热,呈现内外俱热之象,见发热、尿赤、小便频数、腹痛灼热、心烦口渴。治用白虎汤加味,既清阳明之热,又生津养阴。白虎汤组方中,石膏清热,知母润燥滋阴,甘草、粳米补中益气,制石膏、知母之寒凉。孔令海等[23]用白虎汤加味对30名肾病发热病人进行治疗,发现白虎汤治疗肾脏病发热具有显著疗效;李宇轩等[24]建立高尿酸血症肾病模型,以不同剂量的苍术白虎汤进行灌胃治疗,发现该方能够通过抑制XOD的活性及炎症因子的表达,起到保护肾脏的作用。慢性肾脏病患者素体肾阳亏虚,邪入阳明,燥热耗津,又肾水不济,易致阴津耗伤,白虎汤清热而不至寒凉伤胃;滋阴而不至滋腻碍脾,乃治慢性肾脏病病入阳明之良方。
《伤寒论》第180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慢性肾脏病患者若误汗伤津;或饮食不当,病情进展至阳明经,出现潮热、烦躁、尿赤、大便硬结或几日不大便等“胃家实”的症状。胃阳被伤,无以腐熟水谷,肠燥津伤,不能分清泌浊,出现实热之症。而实热郁积易生热毒,加重机体代谢负担,影响肾升清降浊,调节水液代谢的功能,可加速慢性肾脏病的进展。近代研究也表明,肠与肾直接有着密切的联系。宋尚明[25]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肾脏功能与肠道微生态平衡呈正相关;陶芳[26]认为肠道的代谢物质可以影响肾脏功能,可影响慢性肾脏病的发展和预后,并提出中药灌肠治疗慢性肾脏病的理论。病在阳明,治疗上以“通腑”为法,肠腑通则气机调,全身气机调达,则淤血得化,水湿得行。中医药治疗能够起到改善肠道通透性、建立免疫屏障、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27]。临床上常用中药灌肠等外治法进行通便排毒,具有相当肠道透析的作用。张九芝[28]对选取120例慢性肾脏病3~4期患者进行基础治疗、结肠透析,其中60例加用生脉承气汤治疗,结果发现生脉承气汤配合结肠透析能够改善慢性肾脏病患者临床症状、肾脏指标、改善患者营养状况。以“通腑”为治则同样可以内治,承气汤类具有通腑、行气、化瘀的作用。大黄降浊化瘀解毒,厚朴行气通腑,芒硝清热润燥,桃核可活血化瘀、行气散结,合方解慢性肾脏病之浊毒郁滞。林祥发[29]、马来[30]通过5/6大鼠模型,以桃核承气汤进行干预,表明以化瘀泄浊为治法的桃核承气汤能够明显改善肾脏功能,延缓肾纤维化的发展;赖昱宇[31]通过单侧输尿管结扎大鼠模型,证实桃核承气汤能够降低血清肌酐、尿素氮含量,减轻肾脏的形态学损害。
2.3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
慢性肾脏病病入少阳,可因外邪直中少阳,或表邪不解传入少阳而得。少阳病以“口苦,咽干,目眩也”为提纲。足少阳胆经主升发,具有升清降浊的功能,若正邪相争,休作有时,则气血运行不畅,枢机不利,胆火内郁,进而影响脾胃气机。慢性肾脏病病入少阳,可见口苦、呕吐、默默不欲饮食;少阳胆火上扰清窍则眩晕,手少阳三焦经具有运行水液的生理功能,《黄帝内经·素问》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慢性肾脏病病及少阳,三焦气化失司,水液代谢失常,津液输布失调则见水肿,津不上承,则口干渴。慢性肾脏病乃本虚标实之病,少阳相火降入肾水,肾水始温,而相火不降,肾水不温,出现脾肾阳虚等本虚之证[32];清浊逆乱可生实邪,胆失疏泄,脾土不达,可生痰涎;三焦水道不利,水液停聚,可生水饮、湿浊[33]。
治疗上主要以“和解少阳”为治则,临床上越来越多的医家开始重视“和法”治疗慢性肾脏病的意义。张令韶《伤寒直解》有云“……可与小柴胡汤,调和三焦之气。上焦得通而白苔去,津液得下而大便利,胃气因和而呕止。三焦通畅,气机旋转,身濈然汗出而解也。”柴胡、黄芩和解少阳,人参、甘草、大枣益气补中;生姜、半夏宣通散邪,全方攻补兼施、和畅气机,治疗慢性肾脏病之正气不足,湿浊、淤血阻滞恰到好处。于俊生教授,以小柴胡汤治疗慢性肾脏病,在和解少阳的基础上,根据症状特点化裁,或“泄浊解毒”,或“升降枢机”,扶正不留郁,祛邪不伤正[34]。饶向荣教授善以“和解少阳,通利三焦”之法治疗慢性肾脏病急性发作,证候主要以湿热弥漫三焦,少阳郁滞为主,治用小柴胡汤化裁[35];游梦祺[36]、黄秋华等[37]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发现,该法治疗慢性肾脏病急性肾损伤,能够保护肾脏功能,改善中医临床症状。
2.4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
肾藏命门之火,若命门火衰,火不暖土,则脾土虚寒。肾阳乃一身之元阳,其他脏腑之阳气皆本源于肾,肾阳虚衰,无以推动脏腑功能及温煦脏腑,则脾阳渐虚,寒湿内盛。而脾阳不足,气血生化无源,后天失养,病及先天肾阳,脾肾阳虚,则“脏有寒”,“自利不渴”也。李凯[38]通过对118名CKD 3~5期的病人进行临床观察,发现慢性肾脏病4期到5期的病人相当一部分表现出三阴病的脉证,其中以太阴病和少阴寒化证多见;慢性肾脏病病入三阴患者的分布与肌酐、尿素氮值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患者疾病的发生和进展与邪盛正衰及体质有关。太阴脾土乃“后天之本”“水中之州”,太阴为病则影响全身多脏。黄元御的《四圣心源》有云:“太阴主升,己土升则癸水与乙木皆升,……阳虚则土湿而不升,己土不升,则水木下陷。”太阴脾虚则运化失司,水液停聚,又肾阳衰弱,寒水相合,脾肾相干,阳气更衰,浊阴更盛。脾肾阳虚,寒湿内阻见腹胀、腹痛、呕吐;脾失运化,寒湿驱下则下利;正气不足,气血虚衰无力鼓动,见脉沉。慢性肾脏病传入阴经,乃由阳转阴,进入病情危重,预后不良的阶段。
治疗上,主要以“温补脾肾”为法。温补脾肾也是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慢性肾脏病的基本治法。张喜奎教授从“脾肾相关”论治[39];刘宝厚教授以“温肾健脾泄浊”法治疗慢性肾脏病[40];张琪[41]以调脾补肾治疗慢性肾脏病,创“调脾六法”:健脾益胃、升阳益气、益气养阴、健脾消满、益胃养阴、化浊泄热。《伤寒论》中一些温补脾肾的方剂,在临床治疗慢性肾脏病中得到广泛应用,如张晶晶等[42]的临床研究表明,以白通汤治疗脾肾阳虚型慢性肾脏病患者能够明显改善临床症状,并延缓病情进展。
2.5 辨少阴病脉症并治
慢性肾脏病入少阴,往往已发展至终末期肾病,阳衰更重,甚至阴阳俱衰,见“脉微细,但欲寐”。因肾不能主水行津,见水肿、腹水、胸水等水气泛滥的症候;阳气虚衰,失于温煦,阳气不振,见困乏、嗜睡、畏寒等症;阳气鼓动无力,肾精衰少,见脉微细。慢性肾脏病患者,多见素体阳虚,在病情发生发展过程中,也以肾阳虚耗为特点,故临床多见有少阴寒化证[38]。阳气衰微,火不暖土,则饮食入口即吐,下利清谷;阴寒内盛,寒饮上逆可见呕吐痰涎;若阴盛格阳则见其人反不恶寒、面赤、手足厥逆、脉微等阴盛格阳见症。
治疗上以回阳散寒,益气扶正为法。郭立中教授治疗终末期肾病以“扶阳泄浊”为法,临床观察发现该法能够缓解临床症状,改善肾脏功能[43]。在临床上,以温阳为主的四逆类方、真武汤、大黄附子汤等方剂,都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的常用方剂。附子乃回阳散寒的要药,在治疗慢性肾脏病具有重要意义。药理研究表明,附子有显著的抗炎、抑制氧化、抗凝血的作用,而慢性肾脏病的进展与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反应关系密切。杨洪涛教授善用附子治疗慢性肾脏病,提出“附子症、附子脉、附子舌”,认为用附子巧妙配伍,具有温阳通络、温阳疏利、温阳益阴、温阳利水等功效[44]。真武汤是治疗慢性脏病病及少阴的代表方剂,具温阳利水之功。《医宗金鉴》有云:“用附子之辛热,壮肾之元阳,而水有所主益;白术之苦燥,建立中土,而水有所制矣;生姜之辛散,佐附子以补阳,温中有散水之意;茯苓之淡渗,佐白术以健土,制水之中有利水之道焉。”附子能温肾助阳,散寒止痛;茯苓渗水利湿;白术健脾燥湿,培土制水;芍药不仅能柔肝止痛,还能滋阴舒筋;生姜能解表邪,又能温中散寒。真武汤已成为临床治疗慢性肾脏病的代表方剂,当代实验药理研究也充分表明了真武汤能够抑制各类炎症因子的表达,抑制肾间质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延缓慢性肾脏病的进程。周波[45]、邱模炎等[46],采用动物模型,以不同剂量真武汤干预,发现真武汤能够通过抑制细胞外基质的沉积延缓慢性肾脏病的发展;韩凌[47]、宋立群等[48]通过UUO模型从分子水平对真武汤治疗肾间质纤维化的机制进行探索,结果得出真武汤能够抑制各类炎性因子的表达;何岚等[49]研究表明真武汤能够下调肾组织血栓素B2、血管紧张素Ⅱ水平,进而改善肾脏血流和血管。少阴病期,肾阳衰微,积极治疗阳气回复,尚可延缓病情;若吐下不止,虚阳浮越,神志昏沉,则说明阳气不复,真阳继续耗损,阴精持续亏竭,终致阴竭阳脱的死候。
部分患者素体阴亏,随病情发展肾精亏耗;或在治疗中过用辛燥之品,或长期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致耗伤阴液,亦可引起肾阴虚而热化。临床可见阴虚燥热之症,如心中烦躁、失眠、手足心热,此乃肾水亏于下,不能上济心火;咽干、口渴,此乃阴液耗伤;燥热可下移膀胱,灼伤血络,引起尿血;燥热伤津,燥结成实,可致腹胀满不通。治疗上宜滋阴清热,方用黄连阿胶汤、猪苓汤等。黄连阿胶汤中,黄连、黄芩清心火,阿胶、芍药、鸡子黄滋肾水,全方具交通心肾,泄热滋阴之功。猪苓汤育阴清热利水,用治少阴病水热互结下利者,能止下利,存阴津。“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朱肱《类证活人书》),少阴热化证者,补阴而阳气乃存,若肾阴衰竭,则水竭土燥,阴阳离决,危及生命。
2.6 辨厥阴病脉症并治
“厥阴肝木,生于肾水而长于脾土,水土温和,则肝木发荣,木静而风恬,水寒土湿,不能生长木气,则木郁而风生(黄元御《四圣心源》)。”脾肾寒湿,终必伤及厥阴肝木,木为水火中气,土木郁迫,水火不交,则下寒上热。慢性肾脏病发展至厥阴经,多以上热下寒为主要病机。厥阴经提纲“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蚘,”反应了上热下寒之征象。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之间互相滋养和化生,肝肾之间藏泄互用,阴阳承制,若肾脏虚衰,精血亏损,可致肝血不足,肝脏失养。肝阴不足,肝阳上亢,风火上炎,致上热,见心中烦热、口燥咽干、舌红少苔等;肾阴阳两虚,无以温煦,则下寒,见四肢厥冷、腹泻、呕吐等。上热之脏不仅肝脏,心阳失于肾阴制约,水火不济,则心火亢盛;下寒之脏不仅肾脏,脾脏失于肾阳温煦,又被肝木所乘,则脾阳虚衰。《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厥阴乃“两阴交尽也”,孙云松[50]认为慢性肾脏病厥阴病的病机为“阴枢不利”,阴阳之气不相顺接则易寒易热、易虚易实、和风不升,木郁不达,故上愈热,下愈寒,从另一角度解释了慢性肾脏病病及厥阴出现上热下寒的由来。
治疗宜以清上温下为法,使阴阳平衡、气机条达。王金峰[51]以清上温下的代表方剂乌梅丸治疗肾系疾病,认为该方能够有效减少肾性蛋白尿、血尿,对于IgA肾病、紫癜性肾炎同样具有疗效。《伤寒论》厥阴病提纲中有“下之利不止”,提示医家在治疗中禁用苦寒攻下,防止脾阳更伤,下利可致阳气暴脱,病转凶险。慢性肾脏病患者始于肾虚,随病情恶化,逐渐累及多脏,出现厥阴郁火,冲心犯胃;下焦虚寒,血虚寒凝,上热下寒因病家体质不同,各有进退,终致阴阳阻格,危及生命。
3 结语
慢性肾脏病的治疗,目前临床上缺少有效的靶向药物,多以对症治疗为主,至后期患者不得不进行费用高昂的肾脏替代疗法。而根据《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慢性肾脏病从起病至发展为终末期肾病,整个过程亦是由阳经发展至阴经,由表证发展至里证的过程。从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层层递进,不同时期具有其相应的脉症和治法方药。慢性肾脏病病在太阳,见发热、恶风、畏寒,以汗法治之;病在阳明,见发热、不大便、尿赤,以通腑法治之;病在少阳,见往来寒热、呕吐、目眩,以和解法治之;病在太阴,见腹中痛、呕吐、下利,以温法治之;病在少阴,脉微细、但欲寐,寒化证以温阳法治之,热化证以清热滋阴治之;病在厥阴,上热下寒,以清上温下治之。
- 商洛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陕西旅游产业投融资模式及其对策
- 陕南循环经济体系中的产业生态化路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