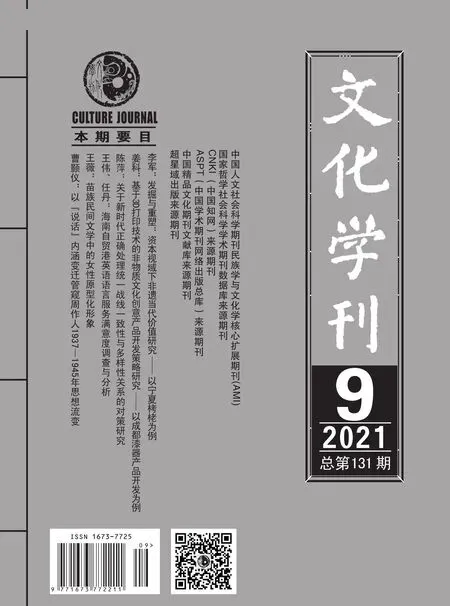“新农文化”视野下的非遗传承研究
——以“八仙戏”为例
陈晓宇
八仙戏,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处山东省淄博市齐国故都东北方向14公里的五路口村是八仙戏发祥地。作者在对鹧鸪戏的二十年田野调查过程中曾多次与八仙戏接触,也于2015年8月开始针对其展开详尽的田野调查研究,在研究其音乐形态本体的基础上逐步对八仙戏置存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展开研究,运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认识人类文化和人类艺术的方法论”[1],对八仙戏在“新农文化”视野下的传承创新进行了探讨。
一、传承创新的动力来源
八仙戏作为一个以乡村为背景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曲牌体戏曲剧种,完全靠剧团自己独立运营。在近五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整个剧团演员共计27人,王宝臣、李秀琴(夫妻)为八仙戏剧团负责人,夫妻二人以种植大棚蔬菜为主业,八仙戏演出为副业,同时亦协助周边同行进行帮演活动。2018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后,八仙戏这类有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八仙戏作为“新农文化”之一,是新时代的农村文化,乡村振兴的文化滋生的土壤,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
八仙戏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代表,是村民文化活动首选的内容。它与周边民间剧团演出的戏曲剧目的差异性在于戏曲音乐的结构体式。周边剧团演出的戏曲剧目是板腔体结构,易学易变,创作剧本者络绎不绝;八仙戏却是曲牌体结构,需要编剧、编曲等大量的专业人员,易学难变,虽有大量新剧本产出,但结果往往是换汤不换药,固定在一个似曾相识的套路中,给观众的感觉就是千篇一律,无任何新意。每当看到周边剧种的新编剧目推陈出新,他们那种渴望重塑与更新自身文化体系和传承体系的愿望就越发强烈。自媒体时代信息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更加刺激了“八仙戏”(乡村文化)的拥有者——五路口村民,他们是构成“乡村文化”的主体,在“新农文化”的视野下,需要根据村民新的生活环境中重新搭建精神沟通的桥梁,让本来远离的“乡村语境”再重拾回来。处在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消费文化、传播文化的环境里,八仙戏必须融入能够符合村民的利益、乡村文化传承维系动力的“新农文化”——乡村经济振兴战略中的载体中。
二、八仙戏与曲牌
(一)八仙戏现状
八仙戏共存有两个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手抄本,1869年抄本(共抄录《八仙戏》八出)、1960年初抄本(共抄录剧目十七出),是典型的外来说唱形式与本地文化相融合的曲牌体结构小戏。该剧种于2016年3月成功申请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2017年6月27日成立了演艺剧团,团长王宝臣(主演猴戏),在当地的节假日、大型民俗活动都有演出。现在常演的剧目多取材于《西游记》,如:《高老庄》《贾家庄》《白云洞》等,现存的演员有27人,最小的在40岁左右,演员全部为农民群众,只有在农闲时参与八仙戏的演出。场地与资金都是自行解决,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团长夫妇二人种植大棚的收益和租赁演出音响,偶尔参与对外演出交流时,临淄区文化馆及淄博市文化旅游局会拨付相应的政府补贴。剧团办公和排练场地为五路口村的幼儿园旧址,多数大型剧目的参演人员都是临时搭班或由相邻兄弟剧团(鹧鸪剧团、五音剧团、京剧团、吕剧团等)人员友情赞助。
(二)曲牌使用现况
在五路口村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东卷》中记载的曲牌应用与村民口述的曲牌应用有较大差异,集成中记载常用曲牌有八个:【驻云飞】【耍孩儿】【桂枝香】【号佛】【混江龙】【皂罗袍】【步步紧】【点绛唇】八支曲牌,而剧团成员和五路口村村民坚称该《集成》中叙述有误,据团长王宝臣介绍,实际此八支曲牌为他们当时能够记住的曲牌名称和大体旋律形态,常用的不过为【驻云飞】【耍孩儿】【桂枝香】3支,但还有9支曲牌(如:【双扣】【排神仙】等)他们有的曲牌连名称都遗忘掉了,只是在印象当中祖辈相传共有17支曲牌。为参演2020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在现有的7支曲牌(【皂罗袍】已完全遗忘)的基础上又恢复了两个唱腔曲牌【双扣】【排神仙】。从常用的3支曲牌,到恢复【双扣】【排神仙】在《白云洞》的应用,再到王汉亭(偶然采访)老人口中的【翻茉莉花】,这足以证明《集成》中所记载的8支曲牌不足以展示《八仙戏》的全部。
(三)八仙戏的文化生存环境
八仙戏虽是一个地方小型剧种,但它更多的承载了一定“乡村文化”意涵,是五路口村对外宣传、招商引资的有效文化载体。在山东,文艺汇演活动是衡量非遗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围绕各级文化单位给出的“主题”展开的一系列舞台实践活动,体现了山东本地民众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即能够随时随地地与国家的政策保持一致。八仙戏的语言华丽而不失地方特色,正面人物的唱腔、念白用普通话是它最大的特点,但因为该剧团演员长期在演出过程中仅会传统七出剧目,在音乐上创新非常少,从而在各类汇演中虽剧目有突破,但因唱腔重叠的缘故被观众逐步舍弃。
三、八仙戏的传承与“新农文化”视野下的重构
(一)社会功能的重构
2020年7月31日,本人接到淄博市戏曲创作研究所通知,要求协助八仙戏改良自己的唱腔和编曲,同时本人也与王宝臣、李秀琴夫妇进行沟通,在得到授权的前提下开始融入到八仙戏的编创中。在此,八仙戏的文化载体出现了两种社会形态,一个是由五路口村村民所组成:有机的团结(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因为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2]6,一个是由剧团成员和专业研究、创作人员组成:机械的团结(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2]7。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因为八仙戏知识上的不足造成的,一个从事大棚蔬菜经营的“非遗传承人”只是依靠本能来继承八仙戏,他们不足以应付非遗带来的各种应对,八仙戏的发展创新会只局限在他们的眼界中。
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八仙戏身处快节奏的当代社会环境中时,要想得以熟练掌握并传承下去,就需要它在时间行进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要根据当下进行重构。随着“新农文化”的推广,剧团原来的传承方式不能满足生存下去的需求,这就需要符合当下社会生存规律的传承创新。八仙戏如同其他传统非遗项目一样,单纯的传统节日和老百姓的婚丧嫁娶民俗事象中的应用越来越少,其大部分的社会作用发生了偏移,无论是省市级汇演还是江苏昆山的“百戏盛典”,它的社会功能已发生改变,已由原来的调和矛盾逐步过渡到发展经济,作为“乡民文化”的代表,在乡民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其精神生活也要得到满足,八仙戏的社会功能转变中基本上得到了乡民的一致认同,“认同不仅是沟通的过程,同时也是解蔽的建构,它最终表现为互动与交往的对象性和实践化”[3]。也就是说,原来单纯的精神娱乐已与经济建设相关联,根本功能发生了变化。
(二)“新农文化”视野下的突破
八仙戏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想要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更多地得到现代受众群体的审美认可,但是要想突破受众群体的审美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会局限在曾经的“惯性记忆”[4]中,创新传承要突破“惯性记忆”痕迹的局限,并不是去改变原有的音乐形态,而是要在创新的音乐形态中不能脱离原来的旋律形态,正是惯性记忆,阻碍了八仙戏的创新发展。
艺术节的展示突破,“艺术节是一个周期性、公众性节庆方式举办的并且容纳了人类丰富多彩的阶段性文学艺术实践成果的展演活动及娱乐行为”[5]。淄博通过自身形象和品牌,建立了一些多元化的文化载体,例如:齐文化艺术节、绿兰莎啤酒节、陶瓷琉璃艺术节等。但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八仙戏在艺术节展演的受众面较小,仅是一个“非遗”光环下的“属性特征”,并不能与艺术节功能构建相匹配,具有观赏性才是淄博城市文化所迫切需要的,而八仙戏最缺的就是观赏性。八仙戏由过去农闲娱乐到当今社会的“乡村振兴”,商品经济的影响力逐渐显现,商业演出和政府组织的宣传演出使得八仙戏在面对新时代经济的时候必须要进行重构,这不是坚守传统与否的问题,而是一种生存的需求。
(三)八仙戏的创新传承
八仙戏的创新传承能否建立在生理“记忆”的标准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群众的评价与八仙戏生存环境的改变所产生的社会记忆出现偏差,会导致八仙戏发展的道路出现过度偏移,本来安定传承的社会生活会在不断的争论中停滞不前,衡定八仙戏的标准怎样来构建是摆在王宝臣团长面前一个棘手的问题。八仙戏剧团是一群有组织的人群,但人员的匮乏、资金的不足,都需要王宝臣他们来维系和平衡。从以家族单位的传承利益到建立社团依靠团体利益维系的网络来言,“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2]49,在以淄博市戏曲创作研究所为中心牵头的八仙戏创作团队来看,从相互之间的学习到认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大家只是为了一个剧种的目的临时搭建的社会关系,那么“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2]61。相互之间专业的差异,社会经验的不同导致相互之间的认同会出现矛盾,团队成员都可以依靠“经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2]72。但相互之间的经验又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八仙戏新编曲目的价值难以判断。例如:参加江苏昆山百戏盛典的新编剧目因剧本的唱词跟曲牌的押韵不协调而放弃,后因传统剧目《白云洞》能够展示剧团所能够恢复的全部八仙戏曲牌才得以排演。戏曲创作研究所所长编剧,山东京剧团的导演,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的过场音乐编曲,演员还邀请了五音剧院、鹧鸪剧团、京剧团的专业演员,四种人员结构重新构建了八仙戏的社会关系,其剧目排演的稳定性完全取决于其“地缘”[2]102关系,王宝臣与这些成员之间的“人情”关系网,才是剧目排演是否成功的关键。八仙戏剧团自身配置不完善,此类情况由原来相互之间的吃饭、喝酒转变成为“货币”结算,“人情”变成“货币”,不得不说,这种国家资助的“民间艺术”又回到了起始源头——生存为目的,更像是一种商业契约关系,无论从剧本的创作、乐队的排练、演出的场地等都需要进行精密地计算,此时的非遗活动已被还原成最初的“商业活动”。
八仙戏要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纯的乡间演出活动并不能满足剧团的生存需求,他们开始有计划地让自己改变。“行为或是活动都是手段,是有所为而为的。”[2]107他们在进行传承创新时有意识地去让自己变成“国家级非遗”所需要的“文化”,这种有动机的行为导致八仙戏的创作和曲牌改编一切以获奖、获得演出机会、获得“非遗称号”为目的的欲望出现。王宝臣团长知道可以用手段和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所以他是理性的,“欲望经过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2]123,他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盲目实验也值得去关注。
八仙戏作为一个具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头衔的戏曲艺术,现在传承依然延续口传心承的老套路。在“新农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八仙戏剧团的成员重新招募本村村民,以八仙戏为纽带构成的新乡村文化经济能否为“乡村社会”提供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资源,传承者能否通过“历史记忆”和“惯性记忆”的判断来修订自身的传承创新道路,为那些纠结商业介入到其中能否保持传统问题的“非遗”提供一个良好的切入点,同时也为传统民间艺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