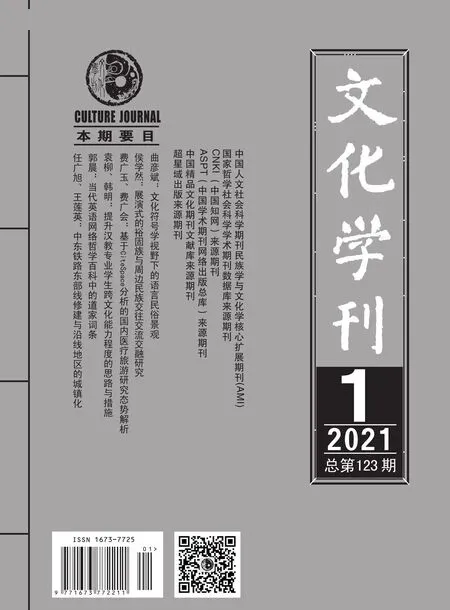基督教与蒙古地区的相遇
——19世纪西伯利亚传教士活动考
阿力更
19世纪是基督教在海外极大扩展的时期,在此期间,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传教士在海外地区的传教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派遣传教士前往西伯利亚的卡尔梅克蒙古族和布里亚特蒙古族中传教,是近代西方在蒙古传教活动中的一段重要历史。由于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信仰藏传佛教,因此传教士在西伯利亚的传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此外,传教士的真实记录和研究是西方对蒙古地区研究的雏形,对促进西方与蒙古地区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对该活动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丰富近代西方与蒙古地区交往的认识和理解。
一、西伯利亚传教活动的早期背景
最早来到西伯利亚传教的是摩拉维亚传教士,早在1742年他们就首次尝试在俄国的亚洲部落如蒙古和塔塔儿部落中传教。摩拉维亚传教士在俄国的传教活动于1765年开始并在贝加尔湖畔的萨拉普塔(Sarepta)建立了传教点,但是摩拉维亚人的传教活动并不如愿,只能被视作为后续的传教活动提供了一个范例[1]。真正给予在西伯利亚地区开展传教活动认真考虑的是英国重要的海外传教组织——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他们对俄国非基督教群体给予了极大支持,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进行传教,此次活动被称为“卡尔梅克行动”(Mission to the Kalmyks)。
18世纪末,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寻求精神慰藉的现象,罗马天主教、神秘主义、宗派主义等在这一时期都获得了极大发展,在各类宗教组织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俄国圣经会(Russian Bible Society)。1812年10月,在亲王戈利岑、罗伯特·平克顿神父和约翰·帕特森神父以及一些政府官员的协助下,经亚历山大一世允许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俄国圣经会。就在俄国圣经会成立一年多以后,居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蒙古族引起了伦敦会的注意,伦敦会决定派遣传教士到该地区传教。著名的蒙古学家施密特就是西伯利亚传教活动的核心人物,施密特不仅掌握了卡尔梅克蒙古语,还具有深厚的基督教背景,这些因素从多方面为在西伯利亚地区的蒙古族中传教提供了便利。从地理方位来看,西伯利亚的蒙古族聚居区处于中国和俄国中间地带,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传教士们穿过这片区域便可到达中国北疆。英国蒙古学家查尔斯·鲍登(Charles Bawden)就认为“卡尔梅克行动”不仅仅是有意向卡尔梅克人以及其他居住在西伯利亚的部落传教,传教士们还意图借此进入中国地区[2]。早在1807年,伦敦会就派遣了数名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但由于雍正登基后所颁布禁教令的限制,外来的传教士只能在澳门一带活动而难以进入中国内地,面对在中国境内传教的停滞局面,从位于中国北疆的蒙古地区进入中国内地不失为一种最优选择。因此,伦敦会于1814年决定派遣传教士进入西伯利亚地区的蒙古人聚居区中传教。
二、西伯利亚传教士在蒙古族聚居区的主要传教活动
西伯利亚传教活动于1814—1840年进行,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先后派遣了被称为“西伯利亚传教士”的四位神职人员前往西伯利亚蒙古族聚居区传教。首先派往传教的是英国人施德华(Edward Stallybrass)和瑞典人兰姆(Cornelius Rahmn)。施德华夫妇和兰姆夫妇分别于1817年6月和10月中旬到达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学习了几个月俄语后,他们在1818年3月到达传教点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施德华和兰姆跟随伊格诺夫(A. V. Igumnov)学习了一段时间蒙古语,但是由于周围居住的卡尔梅克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既无法向他们学习地道的卡尔梅克蒙古语,也无法向当地的卡尔梅克人宣传基督教,因此,施德华和兰姆决定采用帕特森神父的建议将传教点改为更加深入贝加尔湖区的色楞金斯克,并向居住在那里的布里亚特人传教。1819年7月,施德华一家和兰姆一家开始动身前往色楞金斯克,同年由于兰姆夫人重病,兰姆夫妇不得不离开色楞金斯克返回摩拉维亚传教士的传教点萨拉普塔,他们在卡尔梅克人中居住了4年并继续为伦敦会工作,直到1823年俄国政府禁止兰姆夫妇的传教活动他们才于1826年离开俄国。
两位苏格兰人史旺(William Swan)和尤里(Robert Yuille)是随后到达的传教士,他们分别于1818年7月和1819年下旬到达圣彼得堡。史旺在圣彼得堡学习了一年多的俄语,而尤里仅学习了几个月的俄语就被派往西伯利亚。1820年2月,史旺夫妇和尤里夫妇到达了色楞金斯克,同留在那里的施德华汇合。西伯利亚传教士的生活是艰辛的,在出生的13个传教士的孩子中,仅有8名儿童活到了成年[3]。对于传教士来说,除去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有来自心理的隔离。身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异乡,传教士要面对的是生活在拥有另一套意识形态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中,双方都无法理解彼此的信仰体系,这样的情况让这些传教士成为西伯利亚的孤岛。
西伯利亚传教士在传教点的活动有进行日常的祷告、传教,在他们的传教点或巡回传教的过程中分发印有《圣经》或部分《圣经》内容的小册子,翻译《圣经》,照顾病人[3]等,其中《圣经》的翻译和印发是传教士的重要传教活动。最早的有记录的蒙古语《圣经》的翻译活动出现于被派往忽必烈朝廷的方济会修道士蒙特科维诺(Monte Corvino)与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书信中[4],19世纪俄国圣经公会所支持的蒙古语《圣经》的翻译是此类活动的又一尝试。施密特是最早承担蒙古语《圣经》翻译的人,另外两位布里亚特宰桑布达纳(Badma)和那图(Nomtu)是施密特的助手,翻译的过程一般为施密特首先将《圣经》翻译为卡尔梅克语,再由两位宰桑修订并转写成为书面蒙古语。1815年,施密特首次出版了其翻译的卡尔梅克语《马太福音》,到1821年,施密特、布达纳和那图完成了卡尔梅克语和蒙古语《新约》的全部翻译。远在色楞金斯克的施德华和史旺也翻译了《圣经》,大概在1822年至1830年间他们完成了《旧约》的大部分和部分《新约》的翻译。在施德华和史旺返回英国后,1842年两人又向英国圣经公会申请完成剩余部分《新约》的蒙古语翻译,鉴于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境内传教的形势向好,英国圣经公会同意了施德华和史旺翻译《新约》的请求,施德华和史旺翻译的蒙古语《新约》于1846年完成并在英国伦敦出版。传教士不仅翻译了蒙古语《圣经》,还于1824年在色楞金斯克建起了印刷厂专门印刷翻译完成的蒙古语《圣经》。
建立学校是传教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传教士一般以自家住房为基础建立小型的学校,创建学校的目的有二:一是驱赶无知的阴云,二是选取年轻人充当学校教师和传教士[3]。四位西伯利亚传教士均在自己的住房里开设了学校,但其结果远不如传教士的预期,他们几乎没有收到固定前来学习的学生。尤里的学生旺奇科夫是传教士教授的学生中最为突出的一名,旺奇科夫于1821年进入尤里在色楞金斯克所办的学校,在此以后的6年中充当尤里学校里的学生、抄写员、翻译以及教师等,期间旺奇科夫在当地名声渐大,后于1827年离开尤里成为一位俄国官员的翻译和秘书,日后成为托斯高萨维斯克俄蒙军校的教师。
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伦敦会逐渐失去了俄国政府的官方支持,俄国圣经会于1826年解散,西伯利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受到了巨大挑战。1840年传教士在一封联名信中写道:“我们在对有意信仰基督教的布里亚特人进行洗礼这件事上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始终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让人心痛的现实不断地增加着我们内心的恐惧,这现实就是我们没有扮演好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3]在西伯利亚传教的艰难局面让传教士失去了继续传教的信心,终于在1841年年初,施德华和史旺离开了西伯利亚,并于1844年3月24日离开俄国首都莫斯科。施德华和史旺离开后,尤里又在西伯利停留了大概6年的时间,直到1846年才离开。
三、西伯利亚传教士对蒙古民族的研究
早期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往往一边宣讲教义一边对所在地区进行研究。19世纪初开始的这次英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虽然并未达到理想的传教目的,但它为西方世界了解蒙古族人的生活状况和宗教习俗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传教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以通晓蒙古语的欧洲人,他们为蒙古族文化进入西方提供了重要通道,是西方探索蒙古地区、研究蒙古民族的先驱。
在此次传教活动中,为西方研究蒙古民族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当属施密特。协助施密特进行《圣经》翻译的两位布里亚特宰桑从家乡带给了施密特《蒙古源流》这本书,随后1829年施密特在圣彼得堡将《蒙古源流》的蒙语原文及其翻译的德语版本以及注释一同出版,使得《蒙古源流》成为第一部呈现给西方世界的蒙古族编年史史书,此书的出版让施密特成为现代西方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施密特还对蒙古语言进行了深入研究,1832年其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欧洲首部《蒙古语语法》,1835年出版了《蒙古语、德语、俄语词典》。毋庸置疑,这次西伯利亚传教活动是西方蒙古学先驱者施密特的重要学术起点,在此期间施密特所出版的重要著作是近代蒙古学研究的基石。
除去施密特所编撰的字典外,西伯利亚传教士兰姆也编撰了一部名为《卡尔梅克语词典》(CorneliusRahmn’sKalmuckDictionary)的卡尔梅克-瑞典语词典,兰姆曾将部分《圣经》翻译为卡尔梅克蒙古语,他所编撰的字典极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圣经》翻译而准备的。兰姆的手稿现存于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共分为编号R162、R163、R164和用传统蒙古语写成的R165四部分。R162是《卡尔梅克语词典》的主体部分,囊括超过7000个卡尔梅克语单词,这些单词用传统的卡尔梅克文字写成,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大多数的卡尔梅克词汇都有瑞典语翻译,并经常伴有德语翻译。R163是《卡尔梅克语词典》的词汇表,可以被看作卡尔梅克语词典的索引。R164是兰姆用瑞典语写成的卡尔梅克语语法[5]。目前,兰姆的《卡尔梅克语词典》已由瑞典隆德大学语言文学中心的教授史万德森(Jan-Olof Svantesson)翻译和编辑,于2012年在威斯巴登的哈拉索维茨出版社出版。兰姆所编撰的《卡尔梅克语词典》为瑞典人研究蒙古语言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目前兰姆所编撰的《卡尔梅克语词典》仍隐于学界的视线外,但作为卡尔梅克语的早期研究成果,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施德华于1836年在伦敦出版了由其妻子撰写的《施德华夫人回忆录》(MemoirofMrs.Stallybrass,WifeoftheRev.EdwardStallybrass,MissionarytoSiberia),该书主要由施德华的第一任妻子萨拉的书信和日记组成,从中既可以见证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西伯利亚传教的艰难历程,又可以了解传教沿途布里亚特人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意识,书中第四章和第五章就集中记录了布里亚特人的习俗和宗教以及民间信仰。除了在书信和日记中记录布里亚特人的生存状态,传教士还重视收集和发掘蒙古语文献。19世纪,随着清政府对印刷业的推动,一些蒙古语文献得以流通,这些文献的手抄本和木刻版本是当时流通的主要形式。在西伯利亚地区流传的蒙文文献也引起了传教士的注意,他们尽可能收集和学习这些蒙古语文献,尤其是施德华收藏了许多蒙古族史诗、语言、历史和传说等方面的著作,现今存留下来的部分由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圣书公会图书馆保管[3]。
四、结语
在西伯利亚的传教活动中,西方和蒙古地区的文化交流始终处于不对等的位置,西伯利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从1814开始至1840年为止共26年间,几乎没有蒙古族人改信基督教,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受到传教士的影响极小,但与之相反的却是传教士对蒙古族文化的学习与研究,这一举动不仅奠定了西方学术界开展蒙古学研究的基础,还通过各类出版的著作使西方获得了大量关于蒙古的信息,很多学者甚至因此而对蒙古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传教士的手稿记录了19世纪前半期蒙古地区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状况,它们现在依旧是西方学界对蒙古地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