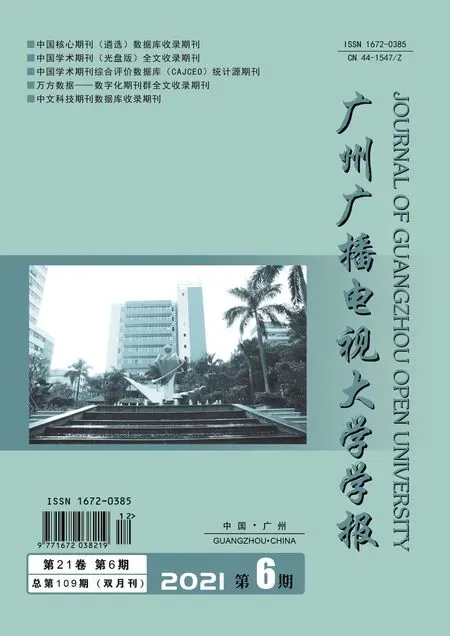论郁达夫小说《迟桂花》的空间叙事
刘城奕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二十世纪伟大的思想大师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不仅呈现静态的社会关系发展演变,还叠加着社会、历史和空间三重辩证的动态过程。空间作为人类生存和感知世界的维度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通过对郁达夫小说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发现研究者多重视郁达夫小说的时间性线索,而郁达夫小说所创设的具有丰富内蕴的空间却未被重视。事实上,郁达夫的小说结构单纯、空间特点明显,常借“零余者”在山水间浅吟低唱表现主人公的感情世界和心理状态。曾有研究者指出,郁达夫的小说“使人乐于回味的是‘自我’心灵律动和情绪起伏所构成的节奏和韵味,以及染上了主观感情的优美的写景片段。”[1]因此,本文从空间叙事角度探究郁达夫小说的艺术空间是有着一定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的。
学者方英在《文学叙事中的空间》一文中,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基础,整合索亚、科特等西方学者的理论,将文学叙事中的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等三种类型。本文结合方英的空间理论,将郁达夫小说《迟桂花》的空间分为自然空间、心理空间以及社会空间,并结合小说文本就具体空间形态展开论述。
一、清新绮丽的物理空间:情欲的净化
物理空间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人的知觉可以感知的空间。”[2]郁达夫善于在小说中营造自然空间已是学者们的共识。文艺理论家郑伯奇曾在《〈寒灰集〉批评》中对郁达夫“描写自然,描写情绪的才能”给予高度的肯定。郁达夫善于借助自身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大自然的光、形、色,在小说中体现为大篇幅的自然空间刻画与描写。自然空间的刻画不仅有对广袤自然空间浓墨重彩的渲染,也有轻描淡写的点染。因此,郁达夫小说中所构建的自然空间,不仅还原出自然景物的实际面貌,更是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向读者传递着人物独特的情绪感受。
在小说《迟桂花》的开篇,郁达夫以精妙之笔营造出了清爽怡人的物理空间:“在半山亭里立住歇了一歇,回头向东南一望,看得见的,只有些青葱的山和如云的树”[3]。青葱的山,如云的树,晴爽的秋天,处于幽深之处浓郁而撩人的桂花香。不仅点明了翁家山的地理环境,也呈现出了翁家山自然空间的诗意,并且这种如诗如画的氛围与文中翁家母子三人“沉静清澈的声气”“柔和的笑容”相互呼应,不禁让读者感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乃至融合。
小说文本对空间的建构不仅限于对物体静态的描写,而且包括对行动的描写。学者加布里尔·佐伦将空间问题的讨论建立在文本的虚构世界基础之上,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1984)中,他将“时空体空间”划分为叙事空间再现层次之一,认为空间中不仅包含静态的事物和关系,而且包含运动——在特定叙述文本中,空间发展轨迹受作者创作目的、情节阻碍、人物意图与行动等因素的影响。在小说《迟桂花》中,通过“我”(郁先生)与莲出游行动时的心境与行动轨迹,发现翁家山自然空间的特征产生了变化,而变化的结果是推动了“我”情欲的净化这一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且对小说主旨的升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我”和莲爬上了龙井狮子峰下一处平坦的山顶时,看到“在晴天下太阳光是躺着的杭州城市,和近水遥山”[4],但这原始的自然美景因“我”对莲的欲望的蓬勃而成为欲望的容器。“我”的心思除了用在了对莲丰满身体的想象之外,便是由这个风光美丽的原野而联想到德国作家延生笔下的小说《野紫薇立喀》和英国作家哈特生的小说《绿阴》中天真的女性。但是这种情欲空间没有持续太久,“我”由于受到莲天真的生命状态的观照,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道德感开始发挥作用:“我”的答语像是“被绞出来的”“难为情”“两颊潮热”,“我”久居城市所滋长的邪欲在人类原初混沌、懵懂的精神状态的对照中经受煎熬。最后在与莲的拥抱下,通过两性之间的互相感动“我”完成了自身情欲的升华:“眼睛里有点热”“心地开朗”。因而,当“我”与莲并肩站在五云山的山顶,翁家山的自然空间又回归到了清新绮丽的自然空间,这也是“我”由羞愧、自责转为感动,完成自我净化的过程。此时,在“我”的眼中,五云山的气概发生了改变。作者将它与颇负盛名的旅游胜地西湖进行对比,将西湖喻为一只锁在铁笼子里的白熊,而将五云山的景观比作一只深山的野鹿,精确地捕捉到了翁家山一带山峰与钱塘江水的天然野性,“一股自由奔放之情,却可以从它那里摄取得来”[5]渲染出了翁家山一带自然风光之幽与野趣盎然。
同时,翁家山自然空间特征的转变,也可以由主人公将丢失拐杖戏称“献祭”而得到佐证。“拐杖”是翁则生用过的,它是“我”走山路过程中的撑扶物,也是“我”完成了心灵净化行动后的“祭礼”。“我”把大自然当作了祭祀的对象,翁家山充满野趣的自然空间完成了它所承担的情欲升华功能。因而有学者认为,《迟桂花》表面上的情节是应朋友之托出游,实际是通过借助这一空间完成“我”潜意识中的抑郁与情欲的净化,突出了翁家山作为自然空间对人个体精神的洗涤作用。[6]郁达夫小说中的“我”通过回归到诗意的自然空间,重新体验到自然生命原初的活力与纯朴的人性美。
二、冰冷的社会空间:家道中落的写照
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空间不仅是小说表层呈现的具体的自然空间,还包括人物身处的社会环境,即社会空间——它是各种社会性元素投射于文本交织而成的空间。而在社会空间的建构中,建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建筑不仅圈定了人物活动的范围,同时也对人物的身份、角色、社会关系进行了界定,以此建构起了一定的社会秩序。
在小说《迟桂花》中,当拜访者“我”第一次踏入翁家时,“我”趁着翁老太太沏茶的空隙,在客堂内对翁家院落有过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深入的打量。翁则生家的院落整体是三开间有后轩后厢房的楼房,楼房前面是一块可以造厅造厢楼的大空地。据《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记载,自明清以来,浙东地区大中型民居以三合院为基本单位,翁家院落的占地面积在翁家村并不多见,规模可称得上是大户人家的规制。院落的气派不仅可以从占地空间看出来,而且可以从房屋所在的位置窥见一斑。翁则生家的院落前面虽然还有一排村民房屋,但是因为高度的优势,可以凌驾于这些平房,视野十分开阔。因而,站在翁则生家的空地上,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眺望前山、后山的山景。最能体现翁则生书香世家积淀的还属翁宅内的陈列,四壁挂着象征着主人志趣的书画,不仅琳琅满目,而且是件件精致,这些书画甚至连“我”这个留学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为之惊叹,足可以看出翁家先人饱读诗书的高雅情趣。因而“我”不禁发出感慨:“翁家的世代书香,只须上这客厅里来一看就可以知道了。”[7]
然而恰恰在这种拥有浓郁书香气息的房屋内,正充斥着家道中落的落魄感。翁父的早逝使翁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有出项没有进款,家底逐渐亏空。势力的亲戚族人冷眼旁观,不仅时不时地进行剥削,又在出卖田地山场的时候蚕食翁家的房产。等到翁则生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家中只剩下仅能维护衣食的住屋山场和几块荒地。不但家庭经济状况难以为继,翁家的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最富代表性的是翁则生被退婚一事。女家是杭城有名的旧家,在乡下的翁家明显在婚事上低人一等,幸而翁则生父亲在世时家中未败落,还有可观的不动产,翁则生又是出国留洋的读书人,将来恐有走上仕途的希望,暂时弥合了两家门第的差距。但是当翁家败落,翁则生染上肺结核回乡养病后,翁则生与杭城小姐的婚约被画上了休止符。媒人受女家之托,登门解除婚约,并且将定亲时候交去的红绿帖子、金玉如意一并还给了翁家。翁母登时目瞪口呆,虽在翁则生的劝说下含着泪将女家的回礼与八字帖交还给上门的媒人,但是她控制不住趴在翁父的坟前痛哭不已。在母亲和族人看来,经此退婚事件之后,翁家的颜面和名声彻底败落了。
院落作为个人所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嵌合着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和性格,使它成为社会文化与时代背景相交织的场所,也推动着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感的宣泄。在翁则生的书信营造的社会空间中,翁宅见证着翁家的兴衰变迁,院落今非昔比的幻灭感刺激着主人翁则生将人生的苦痛类推至积贫积弱祖国的屈辱地位,不仅表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被侵略国家知识分子孤独迷茫、郁闷无助、颓废沉沦的心境,也呈现了知识分子以民族兴亡为责的儒家传统道德伦理人格。可以说,翁则生“不平则鸣”的情感宣泄使得院落这个空间场所被赋予了文化与历史的意义。
三、意蕴丰富的心理空间:儒道人格的和谐交融
心理空间指涉的是小说文本内部的、主观的空间,是人根据外部世界的反应而投射于内心的空间。如果说,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为小说的空间叙事结构奠定了基本框架,那么由人的情感对外部世界过滤、编辑后所建构的空间——心理空间的营筑则拓宽了小说叙事空间的深度,对小说内蕴的传达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小说《迟桂花》中,郁达夫选取了独特意蕴的“迟桂花”意象,通过对其情感的投射而塑造了一个意蕴丰富的心理空间。在这层空间中,物理空间的静谧、祥和,社会空间的冰冷、残酷得到了暂时的弥合,也缓和了“我”作为被侵略民族的知识分子审美情趣与社会责任的分裂。就表层意象看,“我”初到翁家山时,漫山遍野盛开的桂花纯洁、馥郁,使“我”闻吸如醉。只有在翁家山的宁静空间中,“我”才闻到“迟桂花”的香气,因而,翁家山的“迟桂花”的香味被赋予了与城市桂花不同的表征,象征着“我”暂时地忘却城市的物欲横流后感受到的内心的平和、宁静。而后来,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迟桂花”所触发的心理空间发生了变化:文中第四次出现“迟桂花”是“我”在翁则生的婚礼中由“迟桂花”联想到友人迟来的婚姻与坎坷的命运,“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8]第五次则是“我”与翁氏兄妹告别时,“我”对他们的祝福:“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9]小说中第四、五次出现“迟桂花”的时候,由“迟桂花”触发的心理空间已经脱去了“迟桂花”物理的特性,而上升到了一种象征层面。虽然都曾有过不幸的遭遇,但是翁则生和妹妹都能以淡泊的心境坚韧地生活,如同“迟桂花”一般——尽管是迟开的桂花,但是却有着经久的品性,能经得起磨难的洗礼开出更加美丽的花。
在“迟桂花”所引发的心理空间中,不难发现郁达夫力图将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承载的责任感与传统儒、道理想人性的追求相调和。一方面,通过“我”对远离都市喧嚣的山村美景的赞美,作者把传统的道家思想注入“五四”时代精神,追求情欲与美德的双重满足,体现了郁达夫对个体情感需求与生命意志的肯定与尊重。另一方面,作家又通过翁则生兄妹顽强、坚韧品质的描绘,书写了乱世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体现了儒家道德伦理和启蒙精神引领下知识分子肩负的使命与责任意识。在小说《迟桂花》结尾处,“我”愉快地告别了翁氏兄妹,不再留恋于翁家山的美丽风景和隐逸生活,而是带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重新启程的勇气投入现实生活。作为承载着“我”丰富情感的载体,“迟桂花”意蕴特征的前后变化,也呈现了“我”作为一个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逐渐由前期的苦闷走向释然,由惆怅走向坚定的心境的转变。
四、小说《迟桂花》的空间叙事价值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身处于军阀混战、烽烟四起的动荡时代风云中,郁达夫在夹缝中艰难地寻找生存空间。从1927年发表的小说《过去》始,郁达夫小说的创作风格开始了明显的转变。而1932年底写成的《迟桂花》,不仅成为郁达夫创作风格转向的重要作品,而且以其独特的艺术性被学者普遍认为代表了郁达夫后期小说创作的最高艺术成就。
小说《迟桂花》的空间叙事价值首先在于对郁达夫叙事技法转变的推动。据郁达夫日记的记载,小说《迟桂花》是由郁达夫在现实生活中由情感触发,靠想象完成的创作。这表明《迟桂花》有别于其前期小说“自叙传式”的情绪倾泻,而是在想象与诗情的推动下营造三重空间写作而成的。在小说《迟桂花》中,无论是山中天朗气清的秋季,幽静的村落屋宅,还是枝头金黄灿烂的桂花,都以极为朴素与自然的面貌参与了小说的叙事与主旨的阐发。因而,在20世纪40年代便有论者指出《迟桂花》在郁达夫艺术探索中的特殊意义,认为小说借“迟桂花”一物诱发造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反复想象和品味的诗意世界,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和美学价值。[10]《迟桂花》以想象造境的审美方式,人与景物浑然天成的构制也为后来的小说如《边城》带来了叙事艺术上的启迪作用。
其次,小说《迟桂花》的空间叙事价值还体现为对作者情感与美学理想的诗意展现。在小说《迟桂花》中,郁达夫以远离城市喧嚣、山清水秀的翁家山为背景,借色、光、声等方面的细致描摹塑造了一个诗情画意的自然空间。同时,作者也没有完全回避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实冰冷的社会空间,在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迟桂花”这一特殊意象营造了一个意蕴丰富的心理空间。在“迟桂花”投射而成的这一心理空间中,从“我”最初来到翁家山闻到扑鼻的芳香,到“性欲”的冲动与净化,到最后告别翁家兄妹踏上归途,“迟桂花”淡雅的香味一直萦绕在文本叙事中,使得小说《迟桂花》叙事风格温馨明快,舒展有致,呈现着生命原初的自然之美与淳朴心灵,恬淡心境和理想人性、人情。正是在这种基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又超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心理空间的营造中,小说缓和了作为被侵略民族的知识分子审美情趣与社会责任的分裂,完成了由个人情欲暴露的感伤气息到回归自然的审美倾向的转变。
结语
从郁达夫小说《迟桂花》的三重空间形态来看,郁达夫的空间建构基于地域文化空间,通过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场景嵌入建构的空间中,融入到叙事主体表达的主题与意蕴中。在小说《迟桂花》三重空间的建构中,不仅诗意地呈现出了知识分子救国无门的苦闷与自卑,自然欲望的净化,对渺茫前途的勇敢追寻,也表现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走出了个人情欲书写的狭小天地,通过对理想人性的思考与歌颂使小说散发着“迟桂花”般耐久淡雅的香气,彰显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由早期的情感宣泄走向更为内敛、节制的成熟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