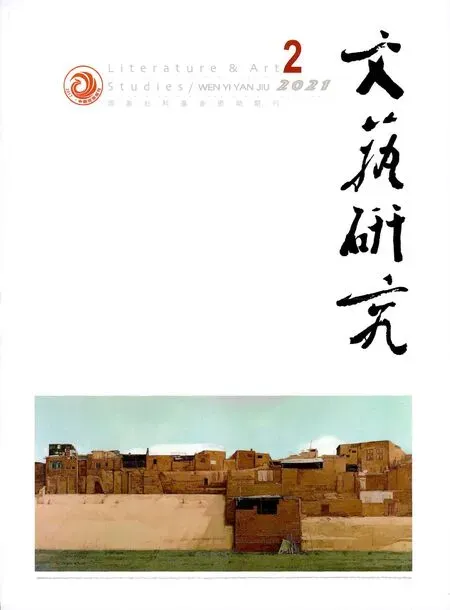探寻“与传统有关”的“现代化”
——朱自清的中国现代新诗论
李 怡
作为新诗批评家,朱自清有关新诗的全部文字只有《新诗杂话》和其他几篇不多的评论,加起来不过六七万字,论数量不及他的古典文学研究①,论声名不及他的散文创作,论在当时的影响可能还不一定超过他的语文研究。但在今天,朱自清评论中国新诗的视角、立场与方法却越发彰显出一种独特的、极具建设性的价值。尤其是对“新诗现代化”这个百年来争讼纷纭的诗学难题,他的讨论方式与提问过程,都与习见的徘徊于古今中西的“焦虑型”求索不同,洋溢着理性、宽厚却又不失立场的从容,历来搅扰人心的文化选择的困境,因为他富有耐性的观察、考辨最终化为乌有,在许多诗人眼中与传统对立的现代化问题获得了来自传统的助力,内在的支撑代替了自我的冲突,中外的融通化解了文化的隔膜,现代化敞开了其更为坚实、自信的面相。这样的理论阐述在“选择的焦虑”极具普遍性的现代诗歌界弥足珍贵,其历史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一
冯雪峰在《悼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用“时代的前进”和“文艺的进步性”来概括朱自清的文学批评②。在朱自清的新诗批评中,这种对“前进”和“进步”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他对“现代化”这个主导方向的集中阐述上。
一般认为,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化追求由来已久,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那里逐渐成熟,而系统阐述“新诗现代化”理论的则是40年代后期的袁可嘉。其实,第一个明确提出“新诗现代化”问题并反复论述的是朱自清。1942年,他在《诗与建国》一文中首先提及了“中国诗的现代化”诉求,比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 (1947)一文早了五年。在朱自清的新诗评论中,到处都留下了对现代化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关于现代生活与现代诗歌的关系,他说: “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些。”③关于民族形式问题,他指出: “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④“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 ‘民族形式讨论’的结论不错,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⑤论及白话、口语与现代化的关系,他认为: “新诗的白话,跟白话文的白话一样,并不全合于口语,而且多少趋向欧化或现代化。”⑥他还将这种变化与新文学发展联系在一起: “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⑦在概念的使用上,朱自清的“现代化”表述经常与“欧化”混用,多少令人想到梁实秋的著名判断: “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⑧就如同梁实秋“外国诗”这一用语一样, “欧化”一词大约最鲜明地标示出朱自清对新诗与新文学不应因循守旧,而要以求新、求变为使命的坚定主张。
回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原则时,朱自清说自己选诗只是由于“历史的兴趣”: “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⑨也就是说,挣脱传统的束缚,传达时代的新变是他观察中国新诗发展的重心。所谓“现代化”是一种反映时代要求的、区别于中国历史传统的社会形态、生活形态和艺术形态。毋庸置疑,中国新诗需要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区隔于自身的传统。朱自清就是以“重新估定价值”的态度定位这个时代的:“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对于一切传统,我们要重新加以分析和综合,用这时代的语言表现出来。”⑩因此,频繁使用“现代化” “欧化”概念的朱自清一度被某些学者视为反传统的“断裂论”者⑪。这种断裂主要表现在朱自清认识到西方诗歌之于中国新诗创生的重大意义。他特别强调外来的异质文化对新诗的特殊价值,指出新诗“不出于音乐,不起于民间,跟过去各种诗体全异”⑫,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 “外国的影响使我国文学向一条新路发展,诗也不能够是例外”⑬。 “在历史上外国对于中国的影响自然不断地有,但力量之大,怕以近代为最。这并不就是奴隶根性;他们进步得快,而我们一向是落后的,要上前去,只有先从效法他们入手。文学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之下,外国的影响是不可抵抗的,它的力量超过本国的传统。”⑭
当然,肯定新诗发展的现代化或欧化方向,在朱自清那里并非一种知识性的运用,而是出于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尊重。所有这些艺术判断都根植于他对诗歌艺术应该把握当下生活的确信:现代生活必然孕育出现代的诗。他宣称: “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⑮在这里,将“文学”作为“娱乐”就意味着这种表现当下精神生活的追求与貌似神圣的职业(知识的继承与建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朱自清进一步指出,职业性的知识建构也应当服务于当下精神生活的需要,主张把研究旧文学的成果用于创造新文学。据吴组缃回忆,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时,为该系确定的方针,就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⑯。虽然长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工作,但与当代人对国学的推崇不同的是,他旗帜鲜明地批判那些沉湎于复古的国学: “所以为一般研究者计,我们现在非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不可。我们得走两条路:一是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学术价值,二就是认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据我所知,现存的国家没有一国有‘国学’这个名称,除了中国是例外。但这只是‘国学’这个笼统的名字存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学问应包含现代的材料,则是无(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是现代的人,即使研究古史料,也还脱不了现代的立场;我们既要做现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杀了现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⑰在这里,基于“现代生活价值”的现代化是朱自清理解中国学术(包括传统学术)的一把标尺,将学术与“现代生活”联系起来是他清醒而独特的思想立场。
二
朱自清是“新诗现代化”概念的创立者和最早的讨论者,这当然不是要抹杀现代化理想之于中国新诗史由来已久的事实,不过,我们却可以透过中国新诗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见出朱自清诗学论述的独特之处。
当代西方学者倾向于将现代性视作“几乎是本世纪所有诗人的经历”, “现代性曾是一股世界性的热情”⑱,而反叛传统则被视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⑲。如果大体上认可这一判断的合理性,那么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如袁可嘉在1947年所言,仅仅是“四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现象⑳,它的理想早就萌生在近代的文学变革冲动中,而胡适等人的“诗体大解放” “文学革命”主张,当然更是现代化追求的正式登场。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传统诗歌最成功的挑战,其价值如闻一多总结的那样, “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㉑。 “与旧诗词相去最远” “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无疑体现了新诗创作的现代化取向。 《女神》之后的中国新诗先后沿着象征诗派的陌生化与左翼诗歌的现实反抗之路,与传统艺术拉开距离,可以说继续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到30年代《现代》创刊、现代诗派成型, “现代”一词第一次成为诗歌艺术高举的旗帜:“《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㉒20世纪30—40年代,戴望舒、废名、卞之琳、冯至、李广田及中国新诗派也都分别在创作或理论上,揭示出新诗承担时代命题可能的途径,而袁可嘉最后将“新诗现代化”归结为以戏剧化为特征的现实、象征与玄学等因素的结合,则进一步打通了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精神联系。
在这样一条现代化路径中,首创“新诗现代化”之说的朱自清居于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位置:前有近代以来走出传统模式的种种探索,后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样板的“现代化”诗学。需要朱自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真总结此前中国新诗左冲右突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提炼出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历史主题。施蛰存将现代诗理解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这里已经触及几个关键词,如“现代生活” “现代的情绪” “现代的词藻” “现代的诗形”等,其中“现代生活”概念在朱自清的“现代生活价值”那里有所呼应。但是施蛰存的定义缺少具体细节,只是几个概念的连缀,与其说是理性的概括,不如说是感性的描述。而朱自清的《新诗杂话》通过讨论诗歌的精神与形式、诗歌的发展规律、诗歌的感性与理性追求、诗歌的国家民族价值、诗歌的接受和释读、诗歌的翻译等,论述了“新诗现代化”问题,事实上奠定了未来进一步讨论的诗学轮廓,搭建起“新诗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对读五年后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一文,我们不难通过表格梳理出两者在一系列诗学主题上的连贯性:

诗学主题 朱自清 袁可嘉诗歌的精神与形式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真诗、诗的形式、诗韵、朗读与诗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新诗戏剧化、谈戏剧主义、诗与主题、诗与意义、诗与晦涩、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漫谈感伤等诗歌的发展 新诗的进步、诗的趋势 新诗现代化、“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诗与新方向诗歌的国家民族价值 抗战与诗、诗与建国、爱国诗 诗与民主、批评与民主诗的接受与释读 解诗 诗与意义、诗与晦涩、批评相对论、批评的艺术对当代西方诗学的借鉴 诗与公众世界(涉及与政治、大众的关系)从分析到综合、综合与混合、 《托·史·艾略特研究》 (书评)、 《新写作》(书评)
从上表可以看出,袁可嘉在朱自清论述的基础上,大大地深化和发展了“新诗现代化”理论的若干细节,他的核心话题“诗歌与民主”,其实早已出现在朱自清的诗论中。此外,两人分享着共同的西方诗学资源(如西方的语义学以及英国批评家瑞恰慈、燕卜荪等人的诗学理论),也都倾向于从西方诗论中获取思想资源。在“新诗现代化”的诗学理论史上,朱自清完成了关键性的理论筑基,为这一理论在40年代后期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思路。
朱自清不仅处在理论演变史上的关键位置,而且其讨论问题的方式也有值得注意的特点。中国现代诗人对新诗发展、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都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新诗创作势单力薄,遭遇来自传统诗歌的巨大压力,这包括诗歌史、文化史意义上的“经典”的压力,也包括这些辉煌历史所形成的欣赏接受习惯、氛围和读者需求的干扰和阻挠。朱自清就指出: “诗的传统力量比文的传统大得多,特别在形式上。新诗起初得从破坏旧形式下手,直到民国十四年,新形式才渐渐建设起来,但一般人还是怀疑着。”㉓也就是说,中国诗的现代化道路在一开始就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小径,现代诗人也就不得不竭力通过证明西方诗歌的价值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在引进外来诗学资源的同时批判和反抗古典诗歌传统。当然,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当刻意的反叛姿态并不能保证创作质量时,就会激发人们重新寻找和强调“传统”的价值,将创作的失败当作借鉴西方诗歌或现代化的恶果。这无疑加强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这种二元对立格外严重,几乎就是中国诗人的基本思维模式。平心而论,从胡适开始,实践中的中国新诗难以回避将外来的诗歌资源与古典传统相互融合的现实,但在相当多的诗学宣言、诗歌批评中,中外古今的资源还是处于彼此对立的状态,并常常通过批判对方来彰显自己的价值。当批判、对立的话语成了人们思维的某种出发点时,甚至对这种对立的怀疑也照样不能摆脱对立与焦虑的阴影,以致试图超越对立的努力也还是在对立的基础上立论。
例如,胡适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著名宣言: “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㉔真可谓是“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折衷之说,非但不知新,并且不知旧,非直为新界之罪人,抑亦为旧界之蟊贼”㉕。新世纪到来之际,郑敏对“五四”白话诗运动大加批评,指出“英国的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虽然也在19世纪初抛出他的《抒情歌谣序》,对新古典主义诗语进行了类似的抨击,开现代化英美诗语之风,铺平了18世纪新古典主义宫庭(廷)诗歌与现代英语诗歌之间的语言坎坎。但却没有像《逼上梁山》这类争论那种咬紧牙根决一死战的紧张与激动。从五四起中国的每一次文化运动都带着这种不平凡的紧张”㉖。有意思的是,郑敏虽然一针见血地批判了“五四”诗歌宣言中的“二元对立”,反思了“每一次文化运动”背后的紧张心态,但是她对“五四”新诗创立时的苦衷缺乏体谅,对隐藏在极端宣言背后的实践层面的复杂性也没有足够的理解,所以批判本身依然充满中国式的焦虑,二元对立思维清晰可见。另外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闻一多。他是“中西艺术交融”最早的提出者之一,其理想是“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㉗。不过,当闻一多怀有“宁馨儿”的梦想面对郭沫若的《女神》时,却陷入了肯定/否定的尖锐对立中,他以极大的热情盛赞《女神》的时代精神: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 《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㉘可以读出,闻一多对《女神》能够冲破传统束缚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激动,在这样的逻辑中, “旧诗词”理所当然站在了郭沫若诗歌的反面。但是,一周后发表的《〈女神〉之地方色彩》却对《女神》失去“地方色彩”的欧化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底狂癖,他们的创造中国新诗底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做成完全的西文诗。” “《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如何改变这一弊端呢?闻一多提出: “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㉙“旧文学”似乎又成了纠正欧化弊端的重要资源。显然,旧诗词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学与文化究竟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什么作用,对1923年的闻一多来说充满了不少矛盾和困惑。
在今天批判那个时代的诗人头脑中存在二元对立逻辑是很容易的,但发现和批评他者的二元对立其实并不意味着自我思想中不存在同样的逻辑。真正的宽容应该是考察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包括理论宣言与实践选择、历史的特殊处境等),体谅和理解中国新诗初创期面对的历史困境。在这方面,朱自清的诗学观点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新诗现代化”是朱自清诗学追求的核心主张,但这一明确的诗歌理想却并不妨碍他对各种诗歌实践的深刻理解和同情。西方诗学理论是他借镜的资源,古典文学塑造了他的诗学素养,古今中外的诗学资源在他的观察和陈述中往往是并置的,它们主要不是尖锐对立的存在,而是经常相互说明。对于身处现代学术体制中的研究者来说,朱自清这样的诗学批评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跨越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这很自然地在思维上打破和消解了文化的对立与隔膜。
朱自清对西方的语义学、新批评理论有过持续的关注,其“现代解诗学”就是对新批评理论的改造、转化㉚。不过,这些外来的理论在朱自清那里,并不只是用来研究新诗或证明新诗的合法性,他同时还将新批评理论运用到古典诗歌的解读中。1934年,他在致叶圣陶的信中说: “弟现颇信瑞恰慈之说,冀从中国诗论中加以分析研究。”㉛从1935年的《诗多义举例》、1936年的《王安石〈明妃曲〉》、1937年的《中国叙事诗的隐喻与引喻》,到1941年的《古诗十九首释》,朱自清的解诗之路一直在古典诗歌的世界中蜿蜒伸展。同样,他的新诗阐释,也不时借助古典诗歌的历史经验,摆脱了诗歌发展的历史羁绊。正如有学者归纳的那样: “朱自清一方面引进现代的(西方的)批评方法,以分析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文学;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他又发觉有必要以现代的眼光去理解古人的批评观念,认识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㉜
今天重读朱自清的诗论,让人不时感叹那份娓娓道来的自然与从容。的确,较之于现代文学研究中习见的现代化论述,朱自清的诗论让人感到举重若轻,而较少所谓“现代性焦虑”。他自由地往返于古今中外之间,能够在一种富有张力的历史考察中把握艺术发展的脉搏。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朱自清都不可能是诗歌历史的“断裂论”者,因为种种诗学资源在他的理解中本身就不是断裂的。
三
朱自清的诗论能够自如、从容地游走于中外古今,但我们却不能将这份从容视为没有原则的理论杂糅,将他看作丧失了独立认知的“和事佬”。朱自清评价新诗的原则是:新诗必须以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化方向为主导。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歌理想本身不会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力或古典诗学的魅力左右摇摆,最终走上一条没有立场也没有方向的折中主义道路(犹如一些中西诗学融会论者那样)。
那么,是什么让朱自清的诗学实践如此独特呢?那就是他作为一位清醒的文学史家所具有的历史意识。他认为: “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㉝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他有着远比一般新诗写作者更加自觉的历史意识,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观察局部的变化。因此,朱自清对中国新诗的讨论,总能将其放置在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使得他的研究能够跳出中外文化冲突造成的种种焦虑,以更加冷静、从容的姿态判断新诗的成就和问题。新诗作为中国诗歌的“局部”似乎已经不足以轻易左右诗家的情绪,一种更大的关怀充盈着他的心胸,使他能够超越一般的现实焦虑,自如地应对历史的难题。自然,这里体现出朱自清的理性和智慧,以此为基础,他的诗歌史判断也就是有原则和立场的, “现代化”依然是笃定的发展方向。用李广田后来的概括,就是“有一个史的观点”: “朱先生并不是历史家,然而近年来所写的文字中却大都有一个史的观点,不论是谈语文的,谈文学思潮的,或是谈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历史的演述,从简要的演述中,揭发出历史的真相,然后就自然地得出结论,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当前的任务。”㉞
用历史的眼光考察中国新诗的位置和价值,得益于朱自清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和他对中国诗歌史的深刻认知。王瑶说过: “朱先生是诗人,中国诗,从《诗经》到现代,他都有深湛的研究。”㉟这不是一位学生对授业恩师的简单赞颂,而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对另外一位同道的精准定位。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是“诗人”,它赋予朱自清特殊的艺术感知能力,使之能够在艺术的“内部”描述体验而非隔岸观火地猜测;二是“中国诗”,这里没有古今之别,共同以“中国”作为身份的标识,对于单纯的新诗而言,这是一种视野的扩大,也构成了一种新的艺术空间,它有助于将当下诗坛的矛盾与焦虑收缩为局部的遭遇,而不再遮蔽人们对整个中国诗歌史的长时段分析;三是“从《诗经》到现代”,这表明朱自清关注的是中国诗歌漫长的历史兴衰与转折演变,长时段提供了足够丰富的艺术经验,使研究者能更加自如地应对新诗遇到的新问题。
《诗经》是以研究国学为“职业”的朱自清的学术起点,他带着对千年诗史的独到认知考察新诗,将其视作这一历史脉络延伸向前的表现。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使得朱自清的新诗研究没有常见的戾气。因为从长时段来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冲击古已有之,并不值得让人大悲大喜、错愕莫名。于是,在毫不掩饰地高度评价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的基础上,朱自清明确宣布新诗诞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㊱。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古典诗歌对新诗的隐性影响。如何发掘出这些隐性影响与外来因素的微妙配合,才真正体现着一位研究“中国诗”的史家深远、精准的观察力和思想力。在肯定新诗发生主要来源于西方启示的同时,朱自清梳理了中国诗歌演变更幽微的内在规律,即民间音乐、民间歌谣的作用:
中国诗体的变迁,大抵以民间音乐为枢纽。四言变为乐府,诗变为词,词变为曲,都源于民间乐曲……按照上述的传统,我们的新体诗应该从现在民间流行的,曲调词嬗变出来;如大鼓等似乎就有变为新体诗的资格。㊲
照诗的发展的旧路,新诗该出于歌谣。山歌七言四句,变化太少;新诗的形式也许该出于童谣和唱本。像《赵老伯出口》倒可以算是照旧路发展出来新诗的雏形。但我们的新诗早就超过这种雏形了。这就因为我们接受了外国的影响,“迎头赶上”的缘故。㊳
总结、发现中国诗歌演变的内在机制,可以说是朱自清的重要贡献。将中国诗歌的内部演变基础与近现代异质因素介入的“突变”事实相结合,中国新诗诞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都得到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中国新诗史上,有胡适的宋元白话复兴说,有梁实秋的“中文书写外国诗”说,也有闻一多“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的断裂论,却很少有哪位诗家如朱自清一般,清晰地描述过中外诗歌资源究竟是如何交替生长、此伏彼起的。朱自清不仅发现了中外诗歌资源在实践中交替生长的复杂过程,而且对一些细微的中外诗学因素的生长、发展都有着耐心、诚恳的态度,拒绝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为历史的发展预留下足够的空间,这也是朱自清历史意识的深刻体现。在对中国新诗各种尝试的观察中,朱自清都尽量做到了理解和等待,并及时地把握其可能的合理性,对每一分成就都给予及时、充分的肯定。例如,对于已经不再被取法的歌谣,他提出: “新诗虽然不必取法于歌谣,却也不妨取法于歌谣,山歌长于譬喻,并且巧于复沓,都可学。童谣虽然不必尊为‘真诗’,但那‘自然流利’,有些诗也可斟酌的学;新诗虽说认真,却也不妨有不认真的时候。历来的新诗似乎太严肃了,不免单调些。”㊳“在外国影响之下,本国的传统被阻遏了,如上文所说;但这传统是不是就中断或永断了呢?现在我们不敢确言。但我们若有自觉的努力,要接续这个传统,其势也甚顺的。”㊵
关于其他传统诗歌体式,他也指出: “五七言古近体诗乃至词曲是不是还有存在的理由呢?换句话,这些诗体能不能表达我们这时代的思想呢?这问题可以引起许多的辩论。胡适之先生一定是否定的;许多人却徘徊着不能就下断语。这不一定由于迷恋骸骨,他们不信这经过多少时代多少作家锤炼过的诗体完全是塚中枯骨一般。”㊶
具体到诗人的创作探索,朱自清也独具慧眼、善于发现。他这样讨论俞平伯的诗:“平伯用韵,所以这样自然,因为他不以韵为音律底唯一要素,而能于韵以外求得全部词句底顺调。平伯这种音律底艺术,大概从旧诗和词曲中得来,他在北京大学时看旧诗,词,曲很多;后来便就他们的腔调去短取长,重以己意熔铸一番,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音律。我们现在要建设新诗底音律,固然应该参考外国诗歌,却更不能丢了旧诗,词,曲。旧诗,词,曲底音律底美妙处,易为我们领解,采用;而外国诗歌因为语言底睽异,就艰难得多了。这层道理,我们读了平伯底诗,当更了然。”㊷
此外,朱自清不仅能够发现传统诗韵在新诗创作中的微妙存在,而且能以开放的心态观察外来诗体在现代中国的实践,尽管自己未必立即认同。例如,他在评论冯至的十四行诗创作时指出: “十四行是外国诗体,从前总觉得这诗体太严密,恐怕不适于中国语言。但近年读了些十四行,觉得似乎已经渐渐圆熟;这诗体还是值得尝试的。”㊸这样的诗歌批评,充满了批评家自我反思、自我总结的精神。他没有预设历史,而是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可能性,不断完善自己对历史的观察。
深远的历史意识不仅让朱自清能够超越对立,将借镜西方思想、文学资源与对接中国历史脉络较为完善地结合在一起,其文学批评观也极具启发性。1934年,朱自清在为清华大学撰写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中提出,文学鉴赏与批评研究“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㊹。这是他探索已久的批评观,即注意辨析外来的批评话语、思维方式如何与中国历史现象的对接,包括“文学批评”这一外来概念本身也需要参照传统的“诗文评”: “‘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㊺在这里,朱自清绝不排斥外来的思想文化,但坚持认定“得将中国还给中国”,意识到传统中国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外来意念”最终必然与中国问题“打成一片”,中国文学研究者应时刻为此做好准备,迎接诗歌和文学史的无限可能。朱自清的诗学观念不仅内涵丰富,而且为诗歌的发展预留了极大的展开空间。
文学研究者大多认为“新诗现代化”的推动者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穆旦是实践者,而袁可嘉做了理论总结。应当说,中国新诗派主要接受欧美诗学的影响,对现代诗歌如何把握“时代经验”有着深刻的理解。而朱自清的新诗理论探索了如何以中国诗歌的自我演变为出发点,最终走上现代化道路。他结合中外诗歌资源的更迭、对接与交错影响的丰富过程,剖析了这一机制如何生成,又如何因为固有道路的受阻而另择新路的曲折过程。在这里,古体诗、近体诗至词曲的演变路径、传统歌谣的特殊价值、文人传统与民间传统的互动关系等都成为观察对象,中国诗歌自我展开和蜕变的面相轮廓分明,新的因素、外来因素在哪一节点上对接生长也都清晰准确。朱自清的探索表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问题不能通过对西方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简单的移植与模仿来解决,只有扎根于中国文学深厚的传统才能创造出新诗。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探索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关于中国新诗的论述中,朱自清总是一方面挖掘新的作品如何突破前人而有贡献,另一方面又不断将这种新的创造,特别是借鉴外来诗体的尝试纳入中国诗歌史的脉络,研究它们如何变成中国诗“自己”的一部分。他分析陆志韦、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以及冯至等人学习外国诗体的写作试验,考察种种尝试如何让中国诗歌的大河改道,最终又渐渐融化在中国诗歌的历史进程中。他告诉我们,新的元素为什么“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以及“这是摹仿,同时是创造,到了头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㊻等耐人寻味的现象。他的研究让我们相信: “大概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的变换,都与生活配合着,采用外国的标准也如此。表面上好像只是求新,其实求新是为了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广度。”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借镜异域的“求新”才完全成为自我发展的一部分,或者说,现代化才成了中国传统不断展开和延伸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中国新诗派的现代化开启的是以现代西方经验激活现代中国问题的可能,那么朱自清则提醒我们,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也最终必须“还给中国”,观察中国自身的传统在如何演变、转化,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与传统有关”的“现代化诗论”。朱自清极具独创性的探索向我们证明,谈论传统,并不就是保守,也不意味着无原则的折中,正如推动现代化并非我们常常担忧的那种与历史的无情决裂一样。
① 朱自清的古典文学研究获得较高评价,例如《诗言志辨》就被李广田视作“是朱先生历时最久、工力最深的一部书” (李广田: 《朱自清先生的道路》,朱金顺编: 《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② 冯雪峰: 《悼念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研究资料》,第238页。
③ 朱自清: 《新诗杂话·诗与建国》, 《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352页。
④⑫㉓ 朱自清: 《新诗杂话·朗读与诗》, 《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92页,第391页,第392页。
⑤⑬㊱㊳㊳ 朱自清: 《新诗杂话·真诗》, 《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86页,第386页,第386页,第386页,第386—387页。
⑥㊻ 朱自清: 《新诗杂话·诗的形式》, 《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400页,第398页。
⑦ 朱自清: 《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 《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64页。
⑧ 梁实秋: 《新诗的格调及其他》,杨匡汉、刘福春编: 《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⑨ 朱自清: 《选诗杂记》, 《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382页。
⑩ 朱自清: 《日常生活的诗——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序》, 《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12页。
⑪ 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在新诗的“现代化想象”史上,朱自清和卞之琳、戴望舒、穆旦等人“基本上被纳入现代主义或现代化的诗歌进化史”,而承认“新诗在新与旧的对抗中产生,意味着对传统诗歌的排斥,无疑属于 ‘断裂’的结果” (龙扬志: 《新诗现代化想象与重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⑭㊲㊵㊶ 朱自清: 《论中国诗的出路》, 《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288页,第288页,第292页,第292、293页。
⑮ 朱自清: 《那里走》, 《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243页。
⑯ 吴组缃: 《敬悼佩弦先生》, 《朱自清研究资料》,第277页。
⑰ 朱自清: 《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196、199页。
⑱ 奥克塔维奥·帕斯: 《受奖演说:对现时的寻求》,朱景冬译, 《太阳石》,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⑲ 哈贝马斯曾断言: “现代性依靠的是反叛所有标准的东西的经验。” (哈贝马斯: 《论现代性》,严平译,王岳川、尚水编: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12页)
⑳ 袁可嘉: 《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 《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㉑㉘ 闻一多: 《〈女神〉之时代精神》, 《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第110页。
㉒ 施蛰存: 《关于本刊中的诗》, 《施蛰存全集》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8页。
㉔ 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60页。
㉕ 汪叔潜: 《新旧问题》,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㉖ 郑敏: 《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 《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㉗㉙ 闻一多: 《〈女神〉之地方色彩》, 《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18页,第118、123页。
㉛ 较早剖析朱自清解诗学与新批评之关联的是孙玉石,参见孙玉石: 《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四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㉜ 朱自清: 《致叶圣陶》, 《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96页。
㉜ 陈国球: 《从现代到传统: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㉝ 朱自清: 《〈诗言志辨〉序》, 《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127页。
㉞ 李广田: 《最完整的人格》, 《朱自清研究资料》,第257页。
㉟ 王瑶: 《念朱自清先生》, 《王瑶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9页。
㊷ 朱自清: 《〈冬夜〉序》, 《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50页。
㊸ 朱自清: 《新诗杂话·诗与哲理》, 《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34页。
㊹ 朱自清: 《中国文学系概况》, 《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413页。
㊺ 朱自清: 《诗文评的发展》, 《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5页。
㊼ 朱自清: 《文学的标准与尺度》, 《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