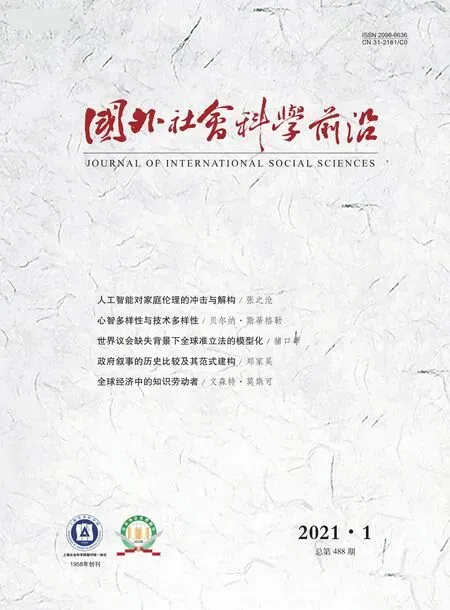人工智能对家庭伦理的冲击与解构 *
张之沧
家,作为社会的细胞、人生的摇篮,虽经数千年演变,几番解构重建,由原始社会的母系家庭到奴隶社会的父系家庭、封建社会的五世同堂、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子核式家庭,及至社会主义国家夫妻平等的家庭模式,使得任何人诞生,几乎总有母亲或父母共建的家庭的养育呵护。然而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后工业文明之后,有关信息网络、人工智能、器官移植、基因工程、克隆技术、大数据、云计算、认知智能化、“生命-智能-社会复合体”的建构(Bio-intelligence-social complex)等,对人类社会伦理纲常、法律法规及人生观、价值观、个人隐私和性爱权利等领域的挑战和否定,都直接导致人们对诸多伦理观念、道德律令的深入反思和重构。只是在这次范围广大、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中,人工智能及形形色色的机器人、电子人对人类家庭的冲击与解构最为强烈。这不仅因为人工智能的赋能技术在与日俱增地替代原本由人承担的任务,导致各行各业的人员“大失业”,加速人类及全球的智能化,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如网络生成、图像制作、人机交互、逼真虚构、机器隐喻、智能生命、性别机器人及智能复合等智能技术,必将颠覆和消解传统的人伦关系、家庭模式和婚恋形式,并带来新的伦理架构,进而促动人类建构新的法律条文和人伦系统。那么这次人工智能革命究竟会引发怎样的家庭结构和伦理新变革呢?
一、构建多元的两性婚姻
在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中,夫妻关系直接就是人性的自然关系和自身欲望的必然结果。正是男欢女爱构建了夫妻家庭,正是家庭成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构成。因此,人类在性爱基础上恋爱、结婚和建立家庭是符合人的本性与日常生活本质的。正基于此,黑格尔不仅认可家庭结构一般包含“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姊妹关系”,也称家庭为“现成存在着的天然的伦理”。特别是当“个人,在他为他的个体享受寻找快乐时,发现快乐就在家庭中”。①[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7 页。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随着人类文明表现出“体力→脑力→机械力→电力→电脑→人工智能→性别机器人→后人类社会”这样一条演变规律之后,便日益受到严重冲击。这一冲击自20 世纪60 年代就表现为“花派嬉皮”的性解放和最具挑战性的“要做爱不要作战”的理念, 以及“妇女放弃把婚姻当成‘ 人生主要目标’的传统女性人生轨迹模式”。②[德]乌尔里希等:《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83 页。当然,最主要的表现还是统治人类数千年的父权制受到重创。女权主义勿需借助暴力革命和浩大的夺权运动,随着人工智能、信息网络和语言统治的到来,就会使女性在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逐步取代男性,真正成为“天然的自我和能动的个体”。
特别是今后,通过更多家庭的人机化和智能化,必将把个人、家庭和社会全面联系起来,届时一切个人行为和社会活动都会在网络上成为举手之劳。妇女的全面解放和地位提升,也会随着人工智能的日益普遍变成现实。尤其是随着性别机器人,包括人机混搭的性别机器人,及其引发的各种情爱形式、网恋形式、性爱方式、婚姻模式、家庭结构和生育方式的问世,都将动摇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和家长制亘古不变的根基。也就是说,现代人工智能使得传统家庭中的“个体性,本身坚如磐石地团结一致的结构,现在毋宁已分崩离析,破裂成了众多的点”。①[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33 页。这些点,由于智能人美女、智能人妻子的介入,加之她们的结构和功能不仅与真女人的形态、容貌、肌肤、温度、行为、语言表达、情感交流、爱心关怀等方面十分近似,其模制的“性器官、性功能”还能够满足真人的性需求。这就务必会使原有的家庭结构、伦理关系、婚配传统,以及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类的意识发生质的变化。甚至会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所言,人工智能使得“人们可能会失去作为人的独一无二的感觉。”②[美]拉塞尔等:《人工智能》,姜哲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第739 页。与之相应,在面对数量众多、聪明过人、纯真可爱且可供自由选择的俊男靓女机器人有可能成为家庭的标配时,自然也会使一些人失去往日独一无二的妻子或丈夫的感觉。
当然,眼下制造的智能人妻子还不具有主体意识、主体思维、本能欲望,以及自主学习、新陈代谢和繁殖生育的功能。就像Akira Hanako 所言,“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术语,只是意味着它能清楚地表达有关由机器或软件所展示的类似于人的智力。”③Akira Hanako, A Modern Approach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Jersey, 2015, preface.然而,正是这一点吸引许多男人宁愿借助法律和伦理与之建立起“正常的夫妻关系”,也要不顾世俗偏见而选择智能人美女为妻。因为现实中就是有一些男人喜欢女性像一个十足的“呆头鹅”和纯粹的审美对象。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维纳斯的旨意。她开着残忍的玩笑,喜欢把不相配的形体和精神,束缚在同一枷锁之下。”④[德]叔本华:《叔本华思想随笔》,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147 页。尤其是那些惧怕激进女权主义的男性,宁愿对智能人妻子树立起平等观念、情爱、呵护、温暖与尊重的意识,在婚配中去除主奴关系和强制行为,也不要与真女人共建一个经常带来无限烦恼的矛盾体。因为他确实知道,他与“被结婚的智能人妻子”之间是一种主客或从属关系,不是现实中两个独立主体的合二而一。这样就会使自己在“新家庭”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自由,由此也会获得更多的欢乐和幸福。
尽管这种性爱和婚配形式会与真人的婚配和性爱生活有所区别,甚至是本质区别。这是因为“人机婚配”根本不可能拥有超越或等同于真人家庭的家庭结构、家庭温暖、爱的形式和爱的享受,以至“智能人妻子”也只能给男人带来十分有限的快感和愉悦。但这毕竟是现实社会男女性爱和情爱的一种补充形式,因此也必然会成为单身男女一种自由有益的选择。
不论怎样,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基因编辑、胚胎操纵、克隆繁殖、人机混合、再生医学、3D 打印及虚拟现实的推动下,一场颠倒乾坤的性革命将不可避免。其主要目标就是废除男权社会和性压抑,使两性各自的亚文化,或原先相互隔离的两性体验融为一体;重新审视男女的性别特征和两性的长短优劣;重新审察原有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结构。原有性角色的废除、妇女经济的独立及生育子女的科技化不仅会极大削弱男权家庭,结束女性的无权状况;而且会赋予妇女更多的自由和男性更多的解放;使传统婚姻完全被“自愿的伙伴关系、多元的两性结合、婚恋上的嫁娶系列或人机结合的家庭模式”所取代。如果这种婚恋革命或新型的家庭结构获得成功,“人类目前面临的人口过剩问题也将不复存在,因为这个问题与妇女解放有着重大关联。”①[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钟良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82 页。更与家庭的主要功能是“生儿育女、种族延续”转向寻求个人的快感、清静、安适、自由和“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历史性转变直接相关。
另外,人工智能和网络社会中的充分性自由也会洗去“堕落女人”的污名,使男女享有同等的道德和人格标准。由此,既会大大提升女性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也会消除长期以来“夫为妻纲、男性至上”的不平等关系;消解现实中的男女比例失调、大男剩女以及性犯罪的日趋严重等问题;甚至会推动人类进入“共享爱情、不再独占爱情”的婚恋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只是“社群主义替代个人主义、使用权取代私有财产、分享取代占有”的资源共享理念会普遍地渗入现在的婚恋家庭,而且鉴于传统家庭一直是“日常暴力和压抑之地”,这样在性别机器人即将大行其道的情势下,在“一种反家庭的家庭日益成型的过程中”,经由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婚恋观和道德观的熏陶,打破婚恋行为的常规也就成为必然。这样,既会极大地增加婚恋的多元化和种族的多样性,“也将会丰富我们的生活,加深我们对于人性和人类差异之间的了解”,使我们的家庭生活“更有趣、更值得享受以及更富有意义”。②[美]克里斯多佛·威尔斯:《人类演化的未来》,王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281 页。
再则,如果在不久之后,科学家能够采用语言引导想象的方法(LGI),让人工智能自行解读分析语言表达的意思,自行组织思想,模拟和人类相似的心理活动,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将人类与体力和智能无限优于我们的机器进行结合”来创造一个新物种。③[法]吕克·费西:《超人类革命》,周行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第19 页。或者如果牛津大学智能研究团队真的能够制造或培育出动人美丽、心地善良、温柔娴淑、长有人体组织器官,甚至能够怀孕生子的机器人,那么今日男女就可以遵循个人的意志自由、兴趣爱好、价值取向、人生追求,冲破数千年来人为建造的“两性恋爱、婚姻和家庭”的围城以及男女之间长期存在的买卖关系和占有关系,真正践行美、爱和性的统一性。在日常生活中,在保护身体、满足情感、尊重权利的原则下,践行尼采的酒神美学,打破男女禁忌,回归自然本性,解放肉欲和情欲;进入生命固有的那种痛苦、喜悦、兴奋和刺激相互交织的状态;恢复那被审慎、虚荣、名利心、陈旧的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和伦理道德所摧毁的强烈的真实感情;让人们觉得世界上充满真正属于生命自身的舒适、欢愉和美丽;使人们能够享受到从日常焦虑及各种无形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兴奋快乐,真正享受生命和身体之美。
这当然不是说,人工智能时代真人的恋爱、婚姻、生育和家庭模式将会被人和性别机器人相结合的婚恋形式所替代。可以断定:现实人与性别机器人发生婚恋,那只是现实人婚恋行为的补充。因为,即便今后“机器人能够完美地模仿人类,甚至比完美还完美,但因为机器的能力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能力,因此机器终究无法体验真人的快乐和痛苦、爱和恨,无法拥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当然,它可以表现得‘像有’,但它并没有任何“人”的感觉。因为要感觉到情绪,就需要有一个身体。”①[法]吕克·费西:《超人类革命》,周行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第119 页。然而,正是这个身体作为地球演化几十亿年的结果,其“灵魂和身体的统一决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的偶然结合,而是相反,身体必然来自作为身体的自为的本性”;②[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1987 年,第405 页。必然是“各种价值、功能、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赖以存在的那个实体”。正是这个实体成为意识“体现自己真正是人”的唯一源泉。因此要想造出一个真人身体,不仅要由真人生育,更需要社会养育。如此,才能最终培养出包括本能、欲望、意志、情感、自我意识等诸多生命要素的属人的身体,和由“身体结构、组织器官、身体行为、知觉认识、好奇心、求知欲、激情和创造力等”构成的社会人的身体。而且,正是人的身体才是用“各种符号,包括表情、形态、动作、感应、声音、心情等各种身体要素书写和表达的最丰富多彩的一部书”。正是人的身体才是“真善美”的源泉,才是积累和储存人类智慧的信息库、加工厂,也正是“我们的身体承载着我们的境遇和人生”。③M.Sheets-Johnstone, Giving the Body Its Du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 206.更何况真女人的“性器官遍及全身,性快感是多样的、复杂的,性倾向是多元的,因此女人的性是流动的、随意的、非线性的、非理性的和反逻辑的。”④Luce Irigaray, This Sex Is Not One, in Kate Conboy (ed.), Writing On the Body: Female Embodiment and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52-253.这也就决定,人类如此复杂、有序、神秘又神奇的身体只能来自上天造化,即便再高深精湛的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也只能制造一个总体上低于人本性的“智能机器人”或“性别机器人”,尽管它可以是一个满足人类精神、情感和性欲的机器人。
但这并不排除智能机器人和通过高科技增强了智力、体能、情感和意志力的真人,都会拥有更多的善心善行、信任和坦诚。因为无论到哪个时代,人类都不会忘记“道德的开端是对他人的关怀,直至做出牺牲,甚至为他而死的关怀。”⑤[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何百华译,学林出版社,2002 年,第61 页。相反,在那里,往日邪恶、贪婪、妒忌和诸多异化的人性会得到消除。由此,也就会更多地满足无数真人的快感、美感、欲求和寂寞的心理,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和享受空间。为此,现代伦理的价值取向将从绝对主义和一元论转向相对主义和多元论,从男性中心主义转向后现代的性别平等,并将不断激励人们寻找全新生活,创建和谐的婚姻家庭,实现刺激、幸福、美好的人生。
二、确立平等的血亲关系
渴望平等、自由是人的自然本性,也是公民的正当权利。遗憾的是,现实的人伦关系中,既存在性别不平等,也严重地存在成人和儿童、父母和子女间的不平等。这不仅在旧中国,有“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如孔子所言“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等腐朽礼教压迫着子女,就是眼下的家庭教育也有“棍棒底下出孝子”等虐待子女的陈规陋习。为此,波普尔尖锐地指出:“今天只有孩子仍旧是最大的一个不幸者阶级。简而言之,成年人现在当着孩子们的面犯罪。”①[美]戴维·米勒:《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450 页。他们经常是赤裸裸地剥夺子女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诸如以强制手段剥夺或控制子女的婚恋权、生育权、职业或专业选择权,以及日常生活中应该享有的休假、睡眠、郊游以及有利于身心成长的游戏和交际交友活动等。他们利用“虎爸虎妈”的至上权威逼迫子女学习那些过时无用或只旨在谋求功名利禄的技术知识,而根本不考虑子女的兴趣爱好、心理感受、辨识和承受能力,无视自由快乐对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为此,使许多子女都沦为父母或成人阶级那粗暴强势和自以为是的牺牲品。
当然,父母们常会以对子女的“关爱和疼爱”作为借口来掩盖父母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然而正是这种借口暴露许多父母对“父母子女”之间人伦关系的无知。他们只是从遗传学上看到“子女是自身的现实和对自身的肯定”,没有认识到子女一经长大成人,变成自为和否定的存在,会“永远成为一种异己的现实,一种独自的现实”。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 页。因此无论何时,父母都不能够把子女视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心所欲地管制子女,使子女在世界范围内沦为成年人的统治对象。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让父母放弃对子女不平等的强制和压抑,去除其不利的成长环境, 让其有一个健康快乐、自由成长的童年和一个自在自为、独立自主的人生,而不是一切都服从父母那已经异化的陈旧观念,甚至是盲目自大和唯利是图的自私行为呢?
这就需要父母不断学习,提高素养,接受新生事物;切实反省:子女不仅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诸多权利,而且根据儿童身心发育的特点还应该在诸多方面给予特殊、优先的关爱和保护。因此在许多方面都需要其智商和行为能力被父母低估了的孩子自己去体验自然和实践人生,而不是被迫接受父母那为了满足自己的意志或私欲制造的各种社会乱象;或者是由于父母自身知识修养的限制,甚至因闭目塞听根本不懂得教育,而把那些自认为“正确”的观念或做法强加给孩子。而当他们这样做时,根本意识不到,文明世界的快速发展,早就使得许多成人脑子中的“标准化人生成为‘选择性人生’、‘自反性人生’或‘自主人生’”。③[德]乌尔里希等:《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3 页。也就是说,文明世界中的年轻人,早就把命运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拥有与传统国度现代成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生活观、婚恋观和家庭观。
好在随着社会进步和人工智能化的发展,将会极大地改变成人和儿童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并会积极有效地推动儿童的学习和成长。这就是许多陪伴、护理、训练、教育或帮助儿童学习、游戏、从事户外活动的工作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或“智能儿童”进行,从而给孩子带来快乐、健康、安全和迅速增加知识、提升智力等方面的保证。这种保证不仅在于智能机器人陪伴儿童学习成长的高效率上,更重要的是未来的许多智能机器人或“智能玩伴”都可以具有类人的性质和近乎完美的人格,包括拥有思维、语言、情感、欲望、能进行操作、教育、说拉弹唱、跑跳投掷、斗智斗勇以及天真、童稚、活泼等正能量的功能。使孩子们能够与一群高素质的“儿童机器人”一起玩耍,一起从事高智力游戏;能够乐于接受那些具有更高智商、更高情商和更具纯洁道德的“保姆、教师”的教育与呵护。
当然,本质上类人机器人或“智能儿童”还不是生物人、文化人和社会人。但它们作为“形神皆似”的人造物,作为被人类设计、植入和控制的芯片软件,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具有“自制力、责任心和利他主义的道德人”,一个真正适合于做儿童的导师、伙伴且知识渊博、聪明智慧和幽默乐观的“良师益友”,因为“人工智能所涉及的主要领域就是计算的性质、知觉、推理、学习、语言、行为、相互作用、意识、人类和生命等最基础的问题。”①Vincent C. Muller, Philosophy and The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ringer Hindelberg, Berlin, 2013, VII.因此,拥有这些智能的机器人在与现实中的儿童相处或玩耍时,更能够“信心满满、全心全意、亲密友好”地体现它们是最真挚最纯粹和最合格的“朋友或玩伴”。它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决不像现实中两性间或夫妻间那样,相互欲求或相互占有,而是“彼此各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一种相互间毫无混淆的关系”。另外,也正是由于这些“智能玩伴”或“智能老师”的行为活动需要遵从人的理念和指令,这样也就使得它们能够“忠贞不二”地将现实社会中不断变革、完善的普遍伦理和道德原则,诸如自由、平等、友善、博爱、团结、诚信、敬业、公平、宽容等权利和品质贯彻到它们的行为实践和日常习惯中,及至传递到儿童的品性和行为中。其中,特别是平等原则,作为“一项原则,一种信仰,一个观念,是关于社会和人类问题在今天人类思想上已经形成的唯一事实、正确、合理的原则”,②[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68 页。将准确地灌输给儿童,必将对其长大成人大有裨益。因为在这种原则下,不仅不可以蔑视每个人的权利,而且只有如此才能够充分发展每个人的个性、主体性、多元意识和人生价值。
为此,美国教育家杜威特别主张父母要给儿童充分自由,要在其成长过程中积极开展各类游戏活动,要注重那“发动性的、有精力的和有生气的性行”。③[美]杜威:《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袁刚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374 页。这将既有助于其身体发育、脑智锻炼;有利于培养人的敏捷感觉、流利思想、果敢精神、生动活泼的禀性;激发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发明创造的兴趣;有利于塑造日益成熟的认知主体、审美主体和道德主体;也有助于培养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坚定的信念、锲而不舍的恒心及强劲的竞争意识;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也正基于此,后现代主义者福柯才“拒绝那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强加于我们的规范化的个体性,以便促成新的主体性形式”。④[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81 页。
这当然不是说,在儿童成长期,基于自由平等的权利,他们可以放任自流、为所欲为。必要的纪律约束、教育和规训还需要伴随其成长过程的始终。因为他们还毕竟处于身心未成熟的时期,还缺乏自制力、耐力,生活还不能自理、自治,不具有独立性,世界观也没有形成,对劳动和学习的动机目的还缺乏正确的理解和高度的自觉性。但也正因如此,给予他们相对多的自由活动对儿童的身心成长大有好处。而欲达此目的,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就需要恰到好处地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儿童发育成长的各个环节。特别是机器人非常擅长的那些领域,诸如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发明、摄影、绘画、音乐、舞蹈、体育运动、科幻动漫,以及“正人正己、铁面无私”、严格严密、灵活机动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程序,只要父母这个教育主体能够统筹兼顾,科学安排,有效操作,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和高效率,就可以把子女从成人陈旧笨拙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传统中解放出来,确保他们健康成长。更何况“人的幸福生活就是拥有一颗独立、高尚、无畏且不可动摇的心灵,就是远离恐惧和欲望”。在这里,儿童将和成年人一样面对“心地善良、单纯幼稚、无任何歹意、知识丰富、见多识广”的机器人,也会有一种身为主人主宰一切的感觉,并会从中赢得自由和尊严,进而“获得巨大而牢固的欢乐,以及心灵的善良和快乐”。①[古罗马]塞涅卡:《论幸福生活》,覃学兰译,译林出版社,2015 年,第104 页。也正基于此,眼下许多国际教育组织和机构都致力于高端机器人教育品牌;以此培养孩子的思维逻辑、思考、动手和协作能力;更好地激发孩子的兴趣爱好,锻炼其意志和韧性,使其成长为未来全球需要的创新精英。
三、泛化传统的兄弟姊妹概念
在由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兄弟姊妹关系构成的传统家庭中,兄弟姊妹关系在过往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中无疑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和人伦关系。它不仅是夫妻之爱或父母之爱的延伸,更是人际之爱或亲朋好友之爱建立和确认的中介。在这种关系中,往往是既没有等级、辈份之分,也没有夫妻、师徒等相互依存、各有所需的成分;兄弟姊妹间无任何非分欲求,只有一种安然、坦诚、无私的本性。他们从小耳鬓厮磨,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两小无猜,亲密无间;体现了兄弟姊妹关系的纯粹性、平等性及其真挚情谊。虽然兄弟姊妹“同出于一个血缘,而这同一血缘在他们双方却达到了安静和平衡。”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4 页。所以,在兄弟姊妹之爱中,一旦失去一方,就永远不可弥补。因为时间不可逆转,任何人都不能返老还童,故人类要特别珍爱兄弟姊妹之间的情义。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精神就是对兄弟姊妹之情的超越和扬弃,又是对类的现实和历史达到的自觉认识及下达的一种类的使命。
遗憾的是,随着网络技术、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引发的人生观、婚姻观、家庭观和生育观方面的革命,严重地肢解了原有的家庭关系。其中,由于独身主义、无子女婚恋、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等多元家庭结构的迅速剧增,以及一度存在的“计划生育”、限制生育,使得传统家庭中的兄弟姊妹关系面临灭顶之灾。这样,兄弟姊妹的概念也就自然地扩展到原有的亲族,包括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而不再仅仅表意家庭中的血亲关系。由此,可以预见,随着“人机组合家庭”的日益增多,在那里不仅不会存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关系,甚至连具有血亲关系或遗传关系的父母子女关系也将不复存在。这样,不仅会使更多的人不能得到亲情的直接满足,而且会使愈来愈多的人“生活在不安全的、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欲望的状态之中”。①[美]阿瑟·赫尔曼:《文明衰落论》,何百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391 页。如此一来,在现实中就务必出现不断延伸的“亲情”关系或“兄弟姊妹”关系,并引发对亲情或兄弟姊妹概念的重新理解。即如英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所言,这时“女人、男人与孩童之间的关系,有了根本性的重新定义,而家庭、性欲特质与人格,也随之有了根本的重新界定。”②[英]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3 页。当然,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由于时空作用,就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也即在左邻右舍和乡里乡亲之间,早就有相互间“称兄道弟”或以“兄弟姊妹”相互称谓及建立起亲密关系的传统。但那毕竟只是限于亲戚、邻里或同姓宗族之间,或者仅是一种礼节性称谓或表示友好亲近的称呼。而眼下伴随科技革命、人工智能、信息网络、虚拟现实、虚拟空间开辟的新时代,原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已经逐渐变为现实。如此,也就使得原有家庭结构中的兄弟姊妹关系发生质和量上的巨大变化。具体表现:
一是物联网拉近了人际关系,增加了人际间频繁接触、交际、交流、交往、交心和交友的时间和空间。使现在交友距离变成零距离,交友时间成百倍地增加。以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夸张表达,现在已变得十分普遍。现实社会中许多可望不可即的人和事,一经放入智能世界就可以经由网络或虚拟现实使人尽享人间的快乐友谊。在那里,人们可以无约无束地与他钟爱的真人、智能人、电子人或硅人一起游戏,聊天,欣赏,审美,访亲交友,祝福慰问,谈情说爱,成家立业。一切人都可以成为亲朋好友和兄弟姊妹。一个人若想和世界各地的网友交往,这在现实世界需要花费大量钱财和时间,而在智能网络中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人们通过声音图像、语言信息的传递与转化,甚至可以使现实中不可能进行的肉体和实物交往都能变成一种亲密接触。远隔万里的情侣可以共处一个荧屏,传递彼此的心声。在那里,由于时空性质的改变,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交往机会、更多样的选择对象、更大更多的人群社团,使得每个人都能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亲临其境,直接体会亲情冷暖。
二是与传统的兄弟姊妹关系相比,由于网络世界中不再存在往日那由肤色、性别、年龄、种族、国籍、信仰、习俗、职业等造成的差异和隔阂,当然也就可以千万倍地增加“兄弟姊妹”和朋友知己。因为在那里,人际关系中的博爱和友善更易确立和维持;人人都可以利用最方便的交流形式,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传递丰富可靠的信息,建立起广泛的人际交往关系。此外,在这种“天下一家”的新型群体中,个体间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可以建起自己交友的王国。为此,现实中发达国家人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观念早已发生重大变化:不只是表现在幻觉教会、自由大学、裸浴聚会、群居公社、同性恋俱乐部等异常形式上,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使社会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伦理革命。过去的人际关系由传统来界定,今天的人际关系则被界定为一种自由领域。它既将整个人类连为一个整体,也“守护着各种类型的个体”。在这里,只要遵纪守法,人们对许多事情都可以重新认知、考察、赋予和编组。因为人类在“经历了数千年与自然的史前斗争之后,我们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与社会组织水平已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是社会性的世界之中。”①[英]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578 页。
三是人工智能既可以使人际交往非常容易,也能够通过手机网、微信群、朋友圈和电脑邮件在亲朋好友间增加无限的信息。特别是在智能机器人能够精彩地扮演服务员、经纪人、文字秘书及“兄弟姊妹或男女朋友”之后,交友和传递信息更是不费举手之劳。此时,往日事必躬亲的自我“所能想到的一切:自然、真理、科学技术、道德、婚姻,都将会自由地付诸行动”。当然,如果今后新型机器人既具有理性交流和情感表达能力,又具有部分的生命机能,这就很可能使现实中的真人愿意与这些智能人建立起兄弟姊妹般的亲情关系。在这里,人际间的交往原则也将发生质变。特别是有关财富、荣誉、权力地位、个人隐私、社会监督、信息共享、网恋安全以及政治和善心、博爱、友谊、和平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也开始一种新的追寻、认定和建构。比如在现实世界,强权政治永远和自由平等、善心博爱相对立,以至现实中很难实现博爱。但在由人工智能构建的新型人际关系中,不仅会使众人拥有一种宅心仁厚、悲天悯人、相濡以沫的心理特征,并会使得现实社会中的剥削和奴役将被真诚、友谊和良心替代,从而在人际间确立一种更加亲密、真挚的兄弟姊妹或亲朋好友关系。
四是在虚拟空间、虚拟场景、虚拟家庭或在“人机组合的家庭”中,与更像真人、更具真人大脑思维或更加具有人性的机器人、智能人或电子人建立起平等互助的朋友关系,必将成为今后从传统家庭中存在的“兄弟姊妹关系”进一步延伸和泛化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因为在未来的机器人兄弟和朋友中将会有更多的各色各类的专家、学者、教授、艺人、诗人、科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旅行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届时,你希望结交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结交什么样的机器人朋友。这种朋友可以被永久地请到自己家中,陪你吃喝玩乐、打闹戏耍,一如兄弟姊妹。当然,也可以通过电脑网络将其放在一个虚拟世界或信息软件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使其成为彼此间无话不说、情同手足的知心好友。甚至也只有对这样一个真挚坦诚的对象,你才能够推心置腹地“倾诉你的忧愁、欢悦、恐惧、希望、疑虑、谏诤,以及任何压在你身上的事情,犹如一种教堂以外的忏悔一样。”②[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95 页。因为有些个人隐私完全可以输入一个你最信赖的机器人予以保密或尽情抒发个人情怀。因此不久的将来人类必将借助人工智能,从各个方面改造、补充和提升真人的能力和人性,让人类真正进入一个人机混搭的后人类社会。届时,尽管我们也许无法识别那些进入眼帘的“人”,但可以怀抱一颗善心爱意去与周围的“人”相处共事。使得人性和交往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实晶莹。那时,也只有生活在这样的“人”中,博爱、正义和诚信才会一如尼采所言:“它像雨一样没有偏见,不仅会使不公正的人浑身湿透,也会使公正的人浑身湿透。”②Ilias Maglogiannis, et al., Emerg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IOS Press, 2007, p. 1.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潘多拉才会按照宙斯的意志合上潘多拉魔盒的盖子,将灾祸留在魔盒之中,使其成为放在人类面前的一个幸运之盒。然而由于灾祸和瘟疫依然存在,并未消失,因此今后活着的人,也只有每时每刻都小心谨慎,精心防范,才可能远离灾祸磨难,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但无论何时,人类都不会停下征服大自然的步伐。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仿人机器人和类人生物领域,“我们会继续展现维度缩减和数据可视化在一系列现实生活问题中的应用。”②Ilias Maglogiannis, et al., Emerg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IOS Press, 2007, p. 1.
四、结束语
尽管人工智能可为人类带来光辉前景,然而一切事物在自身联系的本质中,其否定性总是“同时作为联系、差别、设定的存在、中介的存在而出现”。③[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250 页。因此任何事物作为肯定的存在都必然会向相反方面转化。一如核武器、信息网络、虚拟技术、基因工程可被人用于战争、诈骗、恐怖活动和图财害命一样,人工智能在家庭伦理中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比如它为人类创造了新的家庭形式,却解构了人类传统的家庭结构;它丰富了人类的性爱形式,却削弱了人类社会中的性别真爱;它通过人机系统和试管婴儿改变了人类的生育方式,却削弱了父母子女间的血缘关系和水乳交融的至爱亲情;它给丁克家庭带来情爱,却失去兄弟姊妹之爱。尤其是当制造的性别机器人在体态、肤色、健康、语言、思维、计算、温情、护理、家务、教育、性角色、性爱能力等方面,都可以极大地近似或超越真人之后,它不仅会为真人的性爱、情爱和家庭行为带来危机,而且那些达到以假乱真的智能美女或智能妻子一旦为坏人利用,届时人类社会中的许多伦理道德和法律教条都将受到挑战。比如出于移情别恋,“出卖、杀害或更换智能人妻子”是否算是不道德或违法?再比如,一旦智能人妻子失去控制,进行破坏,如何杜绝这类突发事件?对此,我们必须清楚:“尽管自然界是人类的最古老的上帝,然而它并不能教我们怎样生存。事实上,它也很少关心我们。”④Alan Levinovitz, Natural, Beacon Press, Boston, 2020, on flap.因此,一切都全靠我们自己。既然如此,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就需要做好充分的认识和技术准备,时刻关注人工智能、类人机器人或类人生物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阻断,谨慎管理人工智能。防止人工智能辅助监视侵犯隐私和公民自由,传播虚假和有害内容;防止针对政府、公司、组织和个人的人工智能网络攻击。当然我们也不必杞人忧天,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毁灭人类。要坚信人工智能永远不能统治人类和替代人类;其整体智商永远不会超过人类;更不会通过人工智能一蹴而就地形成新物种。因为一切物种毕竟都是宇宙长期演化的结晶,更何况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人类完全可能是“由数亿年前突然出现的原初种历经千难万险进化而成”。
特别是在符号化、数字化、信息化和借助语言打造的虚拟主体、无性别主体的隐蔽状态中,现实中的两性关系、两性界限几乎完全模糊不清,性别角色在虚拟的舞台中不再被大家看重,因为行为者完全是“代号、代码、概念人或电子人”,而不是现实中的“强悍男人和柔美女人”。如此一来,也就必然会给新伦理实施提供最大的机会。在那里,你甚至能够通过特制的网络设备和相距遥远的性伙伴牵手或接吻。只要你需要和现实世界互动,就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因为那里总有你期待的性伴侣陪伴你。如果你想与一位智能性伴侣结婚,只要选择你偏爱的“型号”,就可以美事成真。当然,如果你就是喜欢那具有诸多完美人性的智能机器人,那你就需要做好各方面都投入爱和智慧的准备。这不仅因为智能机器人本身就是情感和智慧的主体,更重要的是对待这一“新人种”,也一定会有新的伦理法规以便约束相互结合的两者的行为。即如吕克·费西所言,面对后人类或超人类主义革命,“我们应该力求规范,设置限制,应尽可能做到明智和细致。”任何时候,都要对人类或智能机器人的行为加强法律监管;绝对自由的随心所欲是不存在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宇宙发展进化的本质和规律,一如印度哲学家阿罗频多所言,“宇宙既非一无目的幻有,也非一意外的偶然,而有意义和目标——则一伟大,一超上,一光明的‘真实性’的进步的启示。”①[印]室利·阿罗频多:《神圣人生论》(上册),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45 页。
正是这种类似于造物主般的启示,才真正表达了宇宙万物总是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指导着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遵循着辩证法,沿着不断否定、解构而又不断重构和肯定的规律,向前发展演化,直至实现一个更自由、更多元和更具魅力的人类社会。也只有达及这种社会形态,才可以像马克思所说,“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②[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7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