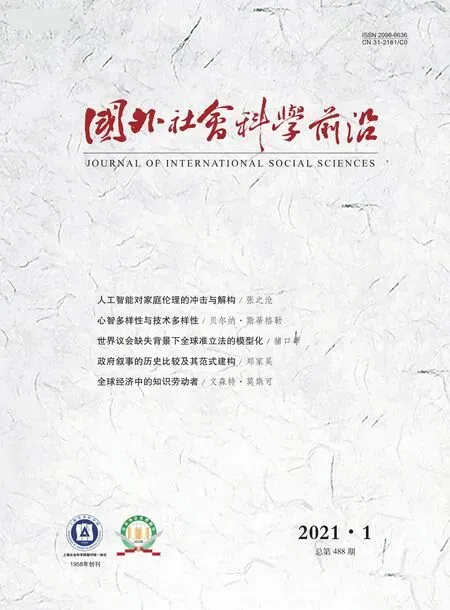心智多样性与技术多样性:建立在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上的新经济的诸要素*
贝尔纳·斯蒂格勒/文 陈明宽/译
[译者按] 斯蒂格勒认为,我们这个数字化时代正是充满技术所释放的毒性的人类世时代,而且正处于其毒性最大化的时期。他的这个论断正在为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影响全球各个国家的新冠疫情所强化。而当今人类世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局面,是因为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过于相信科学技术所致。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的进化是体外进化的模式,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存会不断地更加依赖外在于其躯体的技术和技术物体,也即斯蒂格勒所说的第三滞留。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以人工智能的诸种形式为伪装的数字技术,以异常强大的力量将人类躯体内器官的感知、知性、理性等心智功能不断地外化于人类躯体之外的所谓高新技术物之中。这些技术物如今已到处雷同泛滥,它们是提示记忆的第三滞留的最新形式。于是,雷同的提示记忆的方式导致了雷同的心智思维方式,而雷同的心智思维方式导致了系统性的愚蠢,导致了人类熵在全球范围内的急速增长。在此意义上,斯蒂格勒才说,人类世已经达到其毒性最大化的时期。当然,斯蒂格勒并非是完全贬斥技术的人,因为在他的理论中,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解药。当今数字化的科学技术导致了人类世毒性的最大化,但要化解这种毒性却依然需要依赖于这些数字科技。这也就是斯蒂格勒为什么在这里要重新反思理论计算机科学之基础的原因。只有主动地反思科学技术才能构建心智的多样性,才能认识到科学技术并不是唯一的技术形式,进而才能保护并发展技术的多样性。斯蒂格勒似乎将这场疫情看作是能够促使人类反思当下人类世状态的契机。可是,他本人却又对当下人类世的诸种状况非常地失望,他在这个大流行病的2020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家并非一定是相信自己哲学理论的人,也并非一定是勇于践行自身哲学理论的人。苏格拉底相信并践行了自己的哲学理论。那么,于斯蒂格勒而言,其为是耶?其为非耶?
一、“关于技术之追问”与对真理的考验
无论我们是谁,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关于技术之追问”①包括(甚至是经常)对此问题的否认以及默认其存在,此种否认和默认之态度的存在正是“关于技术之追问”的问题处于极端紧急状态下的征兆。②斯蒂格勒最近几年思考的关于技术的问题,许多是对海德格尔当年所思考的“技术座架”问题的回应。这里斯蒂格勒使用了“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的表达,对应于海德格尔同名的一篇论文,即“Fragenach der Technik”。中译版本可参阅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译者注的问题,并且现在(2020 年3 月29 日),我们必须在因新冠疫情而不能外出的情况下来面对这个问题。隔离迫使我们直面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虽然能够独处,但网络却又使我们彼此联系或者被迫联系起来。疫情似乎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开启了生物圈—技术圈之病理学意义上的体外因素(exosomatic factor)的问题。而这种问题正是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所谓的“体外进化”③A.Lotka, The Law of Evolution as a Maximal Principle, Human Biology, vol.17(3), 1945, p.192.意义上的体外化。
从这种情况来看,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重读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正常与病态》(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意识到,“生命政治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技术政治学。这是一种心智生命(noetic life)的政治学,当然也是动物、植物、细菌和病毒等生命的政治学,它能够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群岛(archipelago)结构。在“数字研究网络”协会(The Digital Studies Network)中,我们将其称为“生命有机体的群岛”(the archipelago of the living)。
计算技术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具体化在各种应用程序、服务、数据库、软件和算法中。而依靠计算技术所建立的一些主要平台实际上只掌握在两个国家手中。在此次疫情之前,我们所有人之所以都或多或少遭遇着“关于技术之追问”(Fragenach der Technik)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计算技术已经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种(西蒙栋意义上的)具体化导致一种技术—地理联合环境①G.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C. Malaspina and J. Rogove (Trans.), Minneapolis:Univocal, 2017, pp.57-58.②B.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ume 1: The Future of Work, D. Ross (Trans.), Cambridge: Polity, 2016, p.22.③联合环境这一概念是西蒙栋技术哲学中所使用的概念。西蒙栋认为,人类所生活的环境并非是只能使自身去适应的自然环境,人类也可以主动地营造使自身更舒适地生存的人工环境或者技术环境。而这两种环境联合起来的环境就是联合环境。参见G.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2017, p.49。——译者注的建立。构成这种联合环境的要素已经不是西蒙栋所研究的甘巴尔涡轮(Guimbal turbine)运行环境中的潮汐水域,而是由个体所供给的“人力资源”。个体成为了“信息有机体”(inforgs)④“ inforgs”,即的“informational organisms”的缩写,参见L. Floridi, Marketing as Control of Human Interfaces and Its Political Exploitatio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 32(3), 2019, p.379。——译者注,进而无数个这样的个体就构成了覆盖在地球之上的外在化的网络有机体(reticulated planetary exorganism)。但这种有机体是极度脆弱且具有危险的依附性。
未来,计算技术可能会对生存方式(但也不只是生活方式)做出更深一步的改变。对计算技术的功能、缺点、极限和危险的重新思考,必须成为我们要讨论的“希望后疫情世界的自然和文化会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的中心。同样地,这也是后数据经济世界的中心问题。数据经济建立在对机器的使用之上,并且正是通过机器,这种经济才能够利用服务于机器的人。但数据经济的发展正急剧地偏向它的深渊:熵。
二、病毒学与毒性:新的争论
在过去的27 年中,因普遍的网络化——根据阿梅利(Sophie Amsili)和莫雄(Florian Maussion)提供的数据,截止2019 年2 月,网络的普及已涉及44 亿人⑤S. Amsili and F. Maussion, L’usage d’Internet dans le monde in cinq chiffres, Les Echos, 9 Feb. 2019.——所带来这种改变引发了一系列无法化解的难题,如今又加上了病毒学的新难题。这些因而也成了有关毒性(virulence)的问题。毒性这个词从拉丁文“virulentus”而来,其最初的意思是“分泌毒液的、具有毒性的”。
正是从这个视角,我们应该阅读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对他的朋友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回应,阿甘本指责各国使用“与正常流感没有太大差别的东西”作为维持例外状态的借口。对此南希回应道:
例外事实上成了世界的规则。在这样的世界中,各种技术之间的相互连接(各种移植和传输)正达到一种迄今为止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前所未有的强度。同样,在富裕国家,人口增长伴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因此,老年人数量就会增长,总体上处于风险中的人口也会增长。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击中错误的目标:整个文明都处在问题之中,这是不用怀疑的。有一种病毒性的例外状态,即疫情;它同时是生物学的、信息论的和文化上的例外状态。政府只是冷酷严苛的执行者,对它们的攻击指责更像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惯用策略,而不是什么政治反应。
如果真有事实上的例外状态的话,南希对阿甘本的回应就是“一种病毒性的例外状态”。考虑到“关于技术之追问”以及技术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以下表述就包含着对真理的考验。我想在这里展示一下:
(1)尤其是疫情之后,对思想的挑战将总会是如何将技术(科技)所引起的难题(problems)转化为关于技术之追问(questions),即,将技术变为思想最切近的对象。
(2)事实上,例外状态的问题是本质的,同时也是中心的和边缘的。这个问题不仅要与卡尔·施密特、瓦尔特·本雅明、马丁·海德格尔和米歇尔·福柯等人思想放在一起考虑,而且要与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乔治·康吉莱姆和阿尔弗雷德·洛特卡等人的思想放在一起考虑;并且要将例外状态的问题当作熵、负熵和反熵(anti-entropy)之关系的问题来思考。
(3)至于就生命的心智形式而言,必须从洛特卡所发展的体外化视角出发,通过负人类学(neganthropology)的视野重新反思人类之现状,将反熵的问题转换为反人类熵(anti-antropy)①“antropy”是斯蒂格勒发明的一个概念,由“anthropos”(人类)和“entropy”(熵)这两个单词构成,因此我们这里将其译为“人类熵”。人类熵特指人类的愚蠢程度,相应地,反人类熵则是指人类的明智程度。斯蒂格勒在《休克状态:21 世纪的愚蠢与知识》(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2015)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愚蠢”问题。——译者注的问题。
(4)根本上,这些问题将会为建立在宇宙技术之技术全球化尺度(technospheric scale)上的政治经济学和由此产生的批判,构建新基础。当然,我们必须通过重新评估计算机科学和认知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来探索这些概念上和理念上的问题的意义。新自由主义如今已经变成了极端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论。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就要求从基础科学、哲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出发,为理论计算机科学建立新的基础,以便更好地去理解技术全球化时代(technospheric era)网络社会中的机器计算与自动化计算之功能的反人类熵和负人类学概念。
当南希说,“政府只是冷酷严苛的执行者,对它们的攻击指责更像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惯用策略,而不是什么政治反应”,但没有对他所说的“病毒性的例外状态”做进一步解释时,我不能确定我是否完全抓住了南希的观点。这显然不是“攻击指责”任何人的问题(正如尼采在很多年前警告我们的)。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这种药学之毒性的危机,同样也是体外化之病毒学的危机,这些当然不能使我们摆脱衰退。而衰退趋势燃起了民众对作为替罪羊的政府的愤恨之情,这愤恨之中隐含着潜在的(蓄意谋杀的)“罪恶”。我们只有通过塑造新的批判武器才能对抗这种“罪恶”。这种新的批判武器既包含科学权力、技术权力,更是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批判武器,因而也是政府以及那些服务政府的人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武器。
三、以“关怀、沉思”(pansements)①“ pansements”是“panser”的名词形式。“panser”是法语词,意为“包扎,敷药,(为马匹)梳理”,其词根为“panse”,也可以写作“pansée”。斯蒂格勒通过考证后认为,“panser”在18 世纪之前一直写作“penser”,后者具有“去思考,去关怀、去照料”的意思。斯蒂格勒在此使用“panser”一词,是为了说明“在精神上进行思考”与“在身体上进行照料”是一致的,这两种“关怀、照料”行为具有相同的起源。这也是斯蒂格勒以“What is Called Caring?”(见B.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pp.188-270)为标题作文来回应海德格尔的“What is Called Thinking?”(中译文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的《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135~151 页)一文的原因。在本论文中,我们将根据上下文具体环境,而将“panser”翻译为“沉思”、“关怀”、“照料”,将“pansements”翻译为“绷带”、“包扎”、“关怀、沉思”。关于斯蒂格勒对“panser”的考证,参见B.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pp.214-216。——译者注 的态度去重建理论计算机科学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与这种衰退趋势做斗争:
(1)首先,问题在于知道这种趋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那种声称可以客观地反思新冠病毒的思想。②这是斯蒂格勒在《国民阵线之药学》(Pharmacologie du Front national)中所研究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英译注这个问题部分地就是我所说的对心智绷带(noetic bandages/ pansements)的关怀沉思(careful thought/pansée)。但这种心智绷带最终总免不了被病毒所感染。③B. Stiegler, Qu’appelle-t-on panser? 1:L’immenseregression,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8.
(2)同时,这也是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反思的问题。无论是这些问题的上游还是下游,这种反思都会挑战上述那些政府,并将其置于质问之中(就像任何形式的哲学思考必须总是心智理疗或心智绷带一样)。对这些政府的挑战和质问将伴随对支持和操控政府的经济权力的挑战和质问,伴随着对那些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既积极又消极地与这些政府团结一致的人们的挑战和质问。
处于“消极团结”之中意味着参与进好人与坏人的“亲密无间”的角色扮演中,所有的角色都要努力成为这场表演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就既不用改变演员,也不用改变剧本,而只需重新安排布景和舞台。正是这种景象产生了所谓的“姿态”(postures)。
以这种方式妥协,就不再是坏人之腐败的问题,而变成了一个非常令人苦恼的心智之药学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会被迫周期性地落入这样的问题当中。因此,这种妥协就与我们每个人相关,尤其是与遵守学术原则的专业思想家相关。④妥协在此的意义是认识论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不过,要在这种妥协的不计其数的细微差别中划定其“近”与“远”,既是不可或缺也是漫长而又困难的,有时又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休克状态》(States of Shock)以及随后的一些作品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它在根本上涉及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讨论的问题,以及对海德格尔的“座架”问题的重新阐释。据我所知,德里达对此问题总是不可思议地保持沉默。
大体而言,学术在原则上(即在原理的层面上)具有普遍性;并且,在这种原则的名义上,即在专业的名义上,作为教授们的专业,它总是一种“信念(faith)的专业”。学术对社会(“政府”是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决断)的贡献(原则上始于arkhē[本原、基础]),被社会和政府所遭遇的难题所钳制。这些难题包括总是趋向于变得空洞的普遍性难题,它因此会成为消除多样性(diversal)的证据。这种多样性既可以是本地的(local),也可以是边缘的(如黄马甲、移民,等等)。
这个社会所遭遇的难题,首先就是它作为整体以及通过它自身的矛盾行为所挑起的问题。这些矛盾行为也是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的动态矛盾。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人文学科的公职人员”的学院思想家们必须要把这些难题当作既定的问题来看待。(并且,在这些既定问题出现的地方,已经根本不是重新恢复由“现代形而上学”所组成的“统治权”之形象的问题了,正如雅克·德里达的每位继承者都倾向于以守旧和狭隘的态度所相信的:他们倾向于去做法语中所说的“躲在某人的小拇指后面”之类的事情。)
理论计算机科学已经被关怀沉思(pensée qui panse)所抛弃,尤其是被欧洲哲学,以及作为马克思思想和精神分析的继承者的“法国理论”所抛弃,只有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是个例外。他们已经不会去关心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特殊面相,这些问题已经遗弃给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而这些人只会躲在建立在科学与量化研究(认知主义意义上)混淆之基础上的计算机伪科学的背后。这种事实的出现同时是由于:
(1)哲学不再实践数学;
(2)数学已经倾向于与数学物理学合并,并通过它与一种陈旧却专制的机制相结合。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胡塞尔已经将这种趋势追溯到代数化;
(3)这些受数学物理学启发并应用于算法的数学形式已经被初级阶段的、贫乏的控制论所挪用,已经被仅仅是拼凑起来的信息论所挪用,而且已经被那种消除对技术的任何思考、任何心智式的关怀沉思的对技术的使用所挪用。
于是,这种方式就取代了“关于技术之追问”。对技术的追问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这是我与许煜(Yuk Hui)展开所谓的(如今已只剩夕阳残照下、断壁颓垣中的)西方文明与(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中国文明之间对话的一种方式。
四、体外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熵增指向与哲学工程的失败
如果以我过去十年所发展的概念框架来分析当前的问题,我们会发现,科技引起的难题已经引发了体外化器官不同尺度上的药学问题:基于彼此关系的不同尺度间的相移是以不同层面间的差别为前提的,这就构成了从细胞到生物圈,再到环绕生物圈的外大气圈的不同尺度上的本地性(locality)问题。通过这种环绕着生命和人类的圆圈,就构成了技术圈(technosphere),而它们就像是一只巨大眼睛的虹膜和瞳孔。
今天,我们生存的各个维度上都因普遍的数字化而发生了改变,这种总体性自身引起了巨大的难以估量的问题。我们生存方式中那些已经完成或者正在到来的改变,似乎都正朝向一种单一的方向倾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每一天都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更具有破坏性:这种单一的方向正是不断地熵增。
数字化变革(digital change)如今已经被具体化为由网络效应、羊群效应、因而也是由病毒式传播(virality)——作为“模因”(memes)①在理查德·达尔文意义上。和“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②在彼得·泰尔(Peter Thiel)对这个由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提出的概念的使用意义上。——所主导的地球行星尺度上的网络化(planetary reticulation)③G. Longo, Letter to Alan Turing,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36(6), 2019, pp.73-94.过程。日复一日,越来越让人失望;在过去的20 年(大约自1985 年到2005 年)之中,每一天都让人感觉看不到希望。
这些现在看来反而是已经丢失的幻想的希望,最初出现在免费软件工程师这种有限的圈子中。这个圈子是一个以新知识产权为基础、基于知识共享的软件开发组织,其基本原则于1985 年左右形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它完全不同于古典劳动分工的工作模式。在亚当·斯密、马克思和涂尔干所关注的工业劳动分工专制霸权的两个世纪之后,只有安德烈· 高兹(André Gorz)从根本上看到了这种知识共享的软件开发组织的新基本特征。
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创建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该基金会孕育了基于“哲学工程”(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经常使用这一术语)的权利哲学的种子。该基金会介入10 年后,这些希望越来越普遍地被万维网的公共开发所分享——这也引发了“科技泡沫”和纳斯达克的“疯狂”投机行为。
然而,所有的这些都将被证明只是20 世纪70 年代早期最初由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④纳斯达克既是一种市场指数,也是一个自动化市场的组织。1990—1993 年,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成为纳斯达克主席,之后他(因金融诈骗)被判处监禁150 年。早在1971 年,麦道夫就是自动交易报价系统的创始人之一。所援助发起的自动金融化(automated financialization)运动的初步基础。毫无疑问,麦道夫最初的那些援助促成了金融化的进程,而金融化本身又为众所周知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革命”的新浪潮铺平了道路。
有两种“希望”开始衰落了:一是从发源于文化工业和愚蠢(Dummheit)——尤其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野蛮(barbarism)⑤Theodor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mund Jephcott(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2, p.xiv.——时代的“单向度的人”的境况(阿伦特意义上)中逃脱出来的“希望”;二是从已经建立的控制论—核能时代中逃脱出来的“希望”,这个时代占用了包含在网络去中心化与基于反馈回路和递归(recursivity)①我一般称之为“再发生”(recurrence)。再发生是我所说的“特殊文本”(idiotext)的动力学原理。关于“再发生”的一般认识,参见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S. Barker (Trans.),Stanford: Stanford UP, 2011, p.144;关于“特殊文本”的论述,参见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2: Disorientation,Stephen Barker(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9, p.64, p.243,以及B. Stiegler, Postface: 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 dans l’Anthropocène,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1-3. Paris: Fayard, 2018, pp.862-868。计算方法的万维网的可编辑化(editorialization)中的潜能。当与智能手机相连通的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s)开始终结社会网络(social web)——也即网络2.0,并一同终结网络(web)本身的逻辑时,所有这些“希望”就已经开始衰落,并且在事后看来,都会成为危险的幻觉。
这里让我们来澄清一下,艺术—工业协会(Ars Industrialis association)的成立首先是以上述科技内在固有的药学特征为前提假设的。在那些冲击了西方(及其货币与市场)的线性文字文码化(grammatization)②文码化过程是一种文码系统对某种连续流程离散之后,而使用其文码标准对之进行重新表达的过程。而所谓的“文码”(gramme)则是指包括文字、字母、基因、细胞符号、痕迹等一切可被重复引用的有限标准。典型的文码化过程,如,离散数学中的离散化过程:将物理世界中具体事件的某些节点用数据表示,然后根据这些数据建立起这个事件的离散模型的过程。不过,斯蒂格勒所说的文码化所涉及的范围要大得多,线性文字文码对口语这种连续流程的离散化,机械文码对躯体的肌肉骨骼的连续流程的离散化等,都属于文码化过程中的类型。对斯蒂格勒而言,他则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文码化过程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其标志是提示记忆的第三滞留的出现。目前对人类进化具有重要作用的文码化过程共有三个,即:书写技术文码化、印刷技术文码化和科学技术文码化。现在我们正处在科学技术文码化过程中的数字技术文码化阶段。关于斯蒂格勒的“文码化”思想,参见B.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1: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B. Norman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p.53-59;J.Tinnell,Grammatization,Bernard Stiegler's Theory of Writing and Technology, Computers & Composition, vol.37, 2015, pp.132-146;陈明宽:《技术替补与技术文码化——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的文码化思想分析》,载《自然辨证法通讯》第40 卷,2018 年,第128~134 页。——译者注和机械文码化(自动机器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过程发送之后,上述这些科技就成了文码化过程新阶段的标志。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社会正是使用了中国的印刷术、航海技术和火药等技术才可能完成自身的原始积累,正是这样,现代西方社会才能够将其对全球的支配力强加到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技术圈的世界上(而且,现在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去西方化的过程)。
“社会网络”的“终结”开始于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出现,随后与2008 年的金融危机结合在一起,进而导致了“平台化”(platformization)③D. Ross, Carbon and Silicon, Stiegler and the Internation Collectiv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ch.10.的迅猛加速。这些希望因此会走向幻灭,然后它们就会被自由主义或是超人主义运动大量地工具化。自由主义或者超人主义运动是定义了20 世纪末期之社会形态的撒切尔—里根保守主义革命(Thatcher-Reaganit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所引发的新自由主义的变种,此一变种通过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所说的“智能化”(smartification)④E. Morozov, 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3.过程而变得具体。
五、反乌托邦与不可能性
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不堪重负地(overwhelmed)清楚地相信,除非某些极端不可能之事发生,否则,这种似乎注定会每天变得更加“反乌托邦”的趋势将会持续地越来越系统化且无法扭转:直到断裂出现。并且,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目前的这种病毒性的元事件(viral archi-event)是否将以某种方式被证明就是这种断裂。当然,出现这种断裂并不必然就是好事,除非此次断裂能够引发大规模的重新发明(reinvention)。
关于数字化事态之当前现状的反乌托邦特征应归因于希尔特·洛文客(Geert Lovink)所说的“平台虚无主义”①G. Lovink, Sad By Design: On Platform Nihilism, London: Pluto, 2019.,以及我们在艺术—工业协会所说的“网络抑郁”(net blues)②B.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ume 1: The Future of Work, D. Ross (Trans.), Cambridge: Polity, 2016, p.13.。至于“断裂”在此次疫情状态下的意义,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是一次更新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所说的“休克主义”③N.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7.之涵义的机会,预示着一种朝向网络的、技术圈的利维坦的总体激进化的新跨越。如果这种休克主义存在的话,那么,它到底会是什么?它的相反学说又会是什么?
根据我自己早先的分析,在此,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在这个可能性(probability)计算的霸权时代,不可能性(improbability)意味着什么?此种不可能性是多样性,在此情况下,是指生物多样性、心智多样性。而可能性的(它总是相对于最可能而言④它是指从本土意义上(locally)临时地偏离而出现的相对性,比如,由某种秩序或者组织而构成的可能性。)则是指消除多样性的熵增趋势。然而,这种不可能性也是无法预知的、意料之外的,它是“黑天鹅事件”,也就是说,它是可能性之崩溃的起源处的缺陷(flaw)。
不堪重负的感觉尤其来源于这种清晰的事实: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建立在计算(calculation)之上的,而通过使用信息机器,计算本身已经成了霸权性的了。因为信息从功能上就是可计算的,那么,以此方式来构想信息(这种方式本身就是计算的结果),计算就获得了清除多样性的霸权。对多样性的清除也意味着是对有益的不可能性的清除,这种不可能性能够独立地延迟无法预见的、毒性的灾难性事件的增殖。
与“软件极权主义”(soft totalitarianism)的运算符(operators)通过其总体化强加计算于万事万物之上相反,计算本身并不能够计算所有的事物,它倒是能够引发那些灾难性的事情。而只有不能被计算的多样的不可能性才能够对抗这些灾难性的事情。这是重新开始进行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计划的出发点——不过,其中心论点在此就不再重述,它已部分地在《作为认识型和熵世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as Epistēmē and Entropocene)⑤B.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D. Ross (Tran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2018, pp.139-151.一文中提过了。这里,我只重述三点:
(1)资本主义是一种认识型(Epistēmē),它已经被资本构成的网络生产设备的固定资本所实现。这种认识型从功能上将计算工具整合为①在西蒙栋所描述的“功能整合”的意义上,此即为具体化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导致了西蒙栋所说的技术—地理的联合环境(associated techno-geographical milieus)的出现。关于对这种环境近期发展变化的论述,参见斯蒂格勒的《世界的再魅》(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2014)《自动化社会》《崩溃的年代》(The Age of Disruption, 2019),以及《克服熵世》(Au-delà de l’Entropocène)等书。西蒙栋生活年代的科技发展水平,使他没有机会来分析这种进化态势。统计、测量、仿真、建模、观测、生产、物流、移动、引导、文献计量、科学计量、市场营销和自我量化(“量化自我”)等过程的工具,进而专制地重新构造了所有的计算工具。
(2)信息是这种认识型的交换性的(allagmatic)②G.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s forme et d’information, Grenoble: Jérôme Millon, 2005,pp.529-536.运算符,它是一种能够完全与资本主义同质化的计算科技,然后迫使所有由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构成的交换服从市场计算法则。并且,这种信息计算基于认知主义建立了网络人工智能,而认知主义正是所有知识形式的普遍范式。
(3)然而,认知主义的认识型是一种反认识型(anti-epistēmē):它只有在彻底的无知化(generalized proletarianization)③此处的“彻底的无知化”是在艾伦· 格林斯潘的例子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我在《自动化社会》第一章中谈论了这个例子。④这里的“proletarianization”一词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化”。斯蒂格勒从马克思那里借用并发展了这一概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化”主要指的是“贫困化”(pauperization),而斯蒂格勒使用这个概念表示的则是“知识的丧失”(the loss of knowledge)。因此,这里我们将其翻译为“无知化”。在斯蒂格勒看来,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大生产对人类劳动的“异化”只是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所具有的“怎样去做”(how to do)的知识的剥夺,它是无知化的第一个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所具有的“怎样去生活”(how to live)、“怎样去思考”(how to think)的知识也会不断地被剥夺,即人类会继续地被无知化,直至成为彻底的无知者(proletariat),而达到这里所说的“彻底的无知化”。——译者注过程中才能够发展。例如,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ory)一文中提出的所谓“大数据”指导下的相关主义的(correlationist)神话,就是通过认知主义范式和市场营销,使得意识形态被重构的一个完美例子。⑤C. Anderson, 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Wired, 23 June 2008.而这种市场营销自身现在已经成了网络化的、拟态性的数据计算。⑥对意识形态与市场营销之关系的论述,参见B. Stiegler, Pharmacologie du Front national, Paris: Flammarion, 2013,p.11.
在剩下的部分中,我们将集中研究不可能性和体外化形式之关系的问题,尤其是与标准化相关的问题。同时,我们将尝试进入与许煜所写的涉及技术多样性和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论文的对话中。
六、“第三世界”的动态支撑与当前理性的分解
我们已经感知到,一种从系统上对多样性的清除正在发生,这一过程迫使所有事物都与科技、与可计算性联系起来。科技是被合理化的(rationalized),依靠着合理化,科技就内在地与计算联系在一起。经验性的技艺并不会与这种合理化联系在一起,合理化只会与“知道怎么去做”(know-how [savoir-faire])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这种清除过程使我们痛苦,但我们并不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它,而且因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那种允许我们沉思和关怀这种事实并因而将此种事实带到立法阶段的知识,仍旧没有发展出来。无论是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后果而言,还是对理论计算机科学的重建而言,这种知识的构建都将是关键的议题。
重启理论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计划需要从功能上将多样性的需求考虑在内,这就预设了对一种负人类学的建构,以便于对人类世时代向负人类世(Neganthropocene)的分叉(bifurcation)产生影响。这种负人类学的建立是以数码研究为前提的,其原则和主要目标已在2012 年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会议上提出过。它催生了一个非正式的网络——数字研究网络,以及一本书——《数字研究:知识器官学和认知技术》(Digital Studies: Organologie des savoirs et technologies de la connaissance)。
我在《自动化社会》和《技术与时间》的法语新版——这一版加了一个题目为《新系科冲突与诸种官能》(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①这个文本更早的版本有英文译本,见B. Stiegler, The New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and Functions: Quasi-Causality and Serendipity in the Anthropocene, D. Ross (Trans.), Qui Parle, 26(1), 2017, pp.79-99.的新后记——中曾讨论过这样的问题:自动化的可计算性能够将知性(understanding)的分析能力委托给自动化的滞留系统(retentional system),而这就会导致康德意义上的知性的过度增长和理性(reason)的退化。作为做决定的官能(faculty),理性是通过综合能力(也被称作判断力)而起作用的。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在他的后热力学的(post-thermodynamic)对康德这些问题的恢复过程中,重新复活了综合官能(synthetic function)的这种特殊性,即综合官能并不能分解为分析官能(analytical faculty)。而且,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中同样强调了他所说的“第三世界”②波普尔将跟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即三个世界:物理自然世界为“第一世界”,人类的内在主观经验世界为“第二世界”,承载人类思想内容和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所构成的世界为“第三世界”。参见 [英]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年,第78 页。波普尔的“第三世界”概念与斯蒂格勒所说的体外化的“第三滞留”概念非常接近,后者正是指承载人类所生产的各种记忆和知识的外在于躯体的技术和技术物体。——译者注和体外化(exosomatization)之间不可通约的联系。
这种对知性之过度生长的态度和对理性之官能的态度是从我在《技术与时间3》中所开启的讨论而来的。在那里,我认为,想象(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所定义的)和图式(schematism)(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所解释的),并不是心智(mind)的先验维度,而只是心智被配置出的经验结构(configurations)。这些心智结构通过提示记忆的第三滞留(hypomnesic tertiary retentions)①斯蒂格勒的“滞留”(retention)概念是从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而来。胡塞尔使用“第一滞留”表示当下的知觉,使用“第二滞留”表示对当下知觉的想象;并且,第一滞留决定了第二滞留。但胡塞尔从来没有使用过“第三滞留”概念。斯蒂格勒受到胡塞尔的启发,发明了“第三滞留”概念,指那些人类所创造的在人类躯体之外的技术和技术物体,比如燧石、斧头、弓箭、车船等。而随着人类的进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第三滞留,即这里所说的“提示记忆的第三滞留”。这种第三滞留是人类大脑记忆外在化的产物。斯蒂格勒之所以认为提示记忆的第三滞留最早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因为这个时期发现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岩洞壁画,这些壁画记载着人类过往社会的神话和历史事件,它们提示着人类社会过往的记忆。典型的是1940 年在法国发现的已存在1.5 万年之久的拉斯科(Lascaux)岩洞壁画。关于斯蒂格勒对“提示记忆的第三滞留”的论述,参见B.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pp.218-223。——译者注而被建造并处于亚稳定状态中。所有这些都与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相关:提示记忆的第三滞留正是此种第三世界的动态支撑。
通过自动化的知性来消解理性的特殊性,此种可能性的存在正构成了计算认知主义的基础。计算认知主义与所谓的分析哲学一道,并与数字化的推广同步,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的这种主导优势将被证明是与新自由主义完全同质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司马贺(Herbert Simon)在朝圣山学会(波普尔也曾经参加过这一学会)恢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过程中相遇,他们认为,市场是一种信息系统,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可以通过这种信息系统进行计算的东西。
然后,哈耶克和司马贺都将自由的观念规定为一种能够使信息自由流通的空间。但是,在这种空间中,所谓的自由实际上意味着是将所有现实(reality)都还原为可计算性的自由,也即,是将所有的现实化(realization)可能性(所有的未来)还原为市场之霸权规则的自由,是将所有的知识还原为这种熵增之条件的自由。不幸的是,波普尔自己在这场针对真正民主的政变中也妥协了。真正的民主总是保护,但不是对多数的保护,也不是对少数(这些是会计学概念)的保护,而是对多样性的保护。每个公民的内心中都必须培养起多样性的观念,因为它具有产生负人类熵(neganthropic)和反人类熵(anti-anthropic)的潜能。
七、为什么在人类世末期,技术多样性问题如此重要?
当许煜提出关于中国之科技的问题,并且首先将这种科技问题(在进入中国的技术问题之前)呈现为技术多样性的问题之时,他就将多样性这一观念作为挑战普遍的可计算性之霸权的方式。对下述两者进行安排(这些安排本身也是可计算的)的机器可以实现这种普遍的可计算性:
(1)一方面是这种机器以及它运行其中的技术系统,机器能够在此技术系统中同时成为计时器、储存器和中心单元,也即(作为处理单元的)运算符;
(2)另一方面是社会系统,同时还有生物系统和地理系统,作为彻底的计算技术系统的机器通过计算能够掌控这些系统,进而通过反馈回路就分解了这些系统。反馈回路能够连续不断地实时运行,能够将每一笔交易都还原为市场计算。反馈回路是基于递归函数而建立的,皮埃尔·利维(Pierre Livet)之前强调过它的困境。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1)认知主义者错误地将计算机定义为图灵机。计算机已经成了通过反馈回路来收集、处理和分配数据的计算网络的细胞元件(在计算机已经可以缩小为智能手机的意义上)。计算机反馈回路的运行速度要快于形成本地网络(local networks)的神经系统数百万倍。而这种本地网络则是依赖于文本、精神个体、公民或者消费者而形成的。
(2)随着卢西亚诺· 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所说的“信息有机体”——也就是心理—技术设备(apparatuses)——的聚集,技术圈就成了路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说的巨型机器(megamachine),进而以此方式,技术圈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复杂性更高的器官外化的有机体(exorganism)①B.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D. Ross (Tran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2018, pp.132-134.②B. Stiegler, Nanjing Lectures, D. Ross (Tran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2020, p.286.。在此有机体中,使用这种巨型机器的平台声称将用完全无视形式因、目的因和材料因的计算效率主权取代由其自身目的所定义的政治主权。
(3)正是在此背景下,今天,所有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都将被迫面临技术多样性的问题。然而,从许煜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首先是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并不能够被还原为西方。对西方而言,中国已经变成了它强大的挑战者。
在当前的形势下,比如就非常有必要回到莱布尼茨所密切关注的、构成中文书写条件的问题上来,这种条件可能包含了一种或许永远不会被西方思维所理解的精神的主权维度。③德里达《论文字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正是对此一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西方自以为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关注。许煜和我一直希望能够在中国组织一场关于这些问题的学术会议,可以冠以“通用表意文字、理论计算机科学和书写游戏”(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and Games of Writing)的名字。
现在作为踪迹工业(industry of traces)④“ 踪迹”(trace)是德里达和斯蒂格勒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重要程度几乎等同于“存在”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地位。对于德里达而言,存在从来不会在场,在场的永远只是存在的踪迹或痕迹。它们是对存在之不在场的替补(supplement)。形而上学家之所以遗忘了存在,是因为他们把存在的踪迹当成存在本身。斯蒂格勒这里所说的“踪迹工业”正是通过数字技术等手段试图捕捉人们日常生活踪迹,进而控制人们需求的工业。人们在各种程序软件中留下的数据踪迹,本身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没有这些程序软件就不会有这些数据踪迹。但这些数据踪迹一旦被捕获,“踪迹工业”就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对它们进行计算,模拟出人们的需求规律,进而制造和控制人们的需求。这种所谓的“数据经济”实际上就瓦解了人们主动地去思考什么是自身真正需求的理性能力。关于“踪迹”的论述,参见J.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A.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20-29;关于“踪迹工业”的论述,可参见B.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ume 1: The Future of Work, pp.22-26。——译者注的“数据经济”正在瓦解理性,不过,这一过程却是在20 世纪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而开始的。文化工业正在将理性替换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现代性(modernity)正是以此为代价成了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种字面上的分解和过度理性化的瓦解(逻各斯完全被作为算法的比值[ratio]所取代,因为在会计学的意义上,一种比值一旦出现,就是意味着一种算法的出现),就等同于普适性(universality)的这一概念的瓦解。并且,通过对机器这一概念的滥用,这种瓦解过程在今天已经完成。此种情况下,这里的机器概念就正是指阿兰·图灵已经理论化的抽象机器概念。
正是这样,西方的普世主义没有变成尊重人类之多样性的有助于解放的理性,而是成了根据其自身(即西方的)利益来异化一切资源的理性化过程。这个由认知科技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系列的数字科技构成了一种新的认知功能。我们将这种新的认知功能描述为一种理性之官能的躯体之外的外在器官发生。参见B. Stiegler, 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 dans l’Anthropocène.所强制实行的过程在完全不同于精神技术(spiritual technologies)②精神技术是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和他的传教士为回应路德派精神技术的传播,而实施的服务于精神修炼的技术。它首先是将《圣经》翻译为适合每一个人阅读的书,然后以此方式,将信仰和忠诚(fidelity)重新定义为一种阅读训练。之后,本杰明·富兰克林根据加尔文派的教义重新定义了这一方案。他将信仰和忠诚观念引向有“比率”(ratio)出现的记账簿中,并因而将“忠诚”(“fidelity”亦可翻译为“保真度,精确度”——译者注)重新定义为“计算”。的区域(register)上继续并完成了由文化工业③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本雅明之后也讨论了文化工业的问题,不过,他们没有完全理解本雅明所说的可复制性(reproducibility)的重要性。关于“什么是可复制性”,参见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ch.6.所开启的进程。
因此,所出现的问题正在于,现代性是否就意味着肯定或者否定西方历史过程中所发展出的,尤其是作为科技的那些趋势的普适性。科技的发展已经将普适的科学法则具体化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牛顿的物理学和可计算性的数学。为了接近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回到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的普遍技术趋势(universal technical tendencies)的概念,许煜在其《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一书中简要地重述了此概念的主要特征。④Y.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o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 pp.8-10.
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接近地球生物圈中的状态转变”(Approaching A State Shift in Earth’s Biosphere,巴诺斯基等人撰写)的签署国、2018 年11 月13 日李普尔(Ripple)等人在《生物科学》(BioScience)上所做的呼吁以及2020 年2 月1000 名法国科学家所召集的反抗活动“法国千名科学家的呼吁”(L’appel de 1000 scientifiques)等各方所宣称的:在人类世时代,上述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了获得解决的可能性。因为,因生物多样性和心智多样性的消亡而导致的极端危险在人类世时代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其中,这种消亡的运算符正是以普遍的数字文码化而运行的体外化的当前阶段。
在这个或多或少地有点末世论意味(非宗教意义上)的人类世阶段,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勒鲁瓦-古兰的普遍技术趋势之概念呢?
八、趋势与环境
我们是应该,例如,跟随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等加速主义者的观点吗?根据这种观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网络平台技术引导向正确方向,即引导向社会正义和重建经济合理性(rationality)的方向。或者,我们应该使技术—工业概念变得多样化?这有点类似于1987 年美国股灾之后的情况,当时,美国当局宣称,为了避免股票指数系统性强势下跌的趋势,股票交易市场的自动交易程序的“习惯化”(idiomatization)是必不可少的。①C. Distler, Réseaux globaux et marches financiers: les leçons du krach de 1987, Quaderni, 12,1990, pp.37-47.不过,根据此次事件之后的研究表明,当时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曾公开表示股价太高,此种言论反倒诱发了股价强势下跌的趋势。
许煜似乎并不同意勒鲁瓦-古兰和我的观点,因为我接受了勒鲁瓦-古兰关于普遍技术趋势的论证。②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许煜《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一书所坚持的“具体化过程”的立场。西蒙栋是就机器的生成过程而谈论具体化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西蒙栋使用“具体化”这一概念是为了回应维纳,以及他对机器与有机体之间的反馈问题的思考,也即递归的问题。递归是许煜最新的著作《递归与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London: Rowman, 2019)一书所探讨的主题。因此,为了理解技术多样性和许煜对此观念的立场,必须考虑到以下两点:
(1)勒鲁瓦- 古兰在《环境与技术》(Milieu et Techniques)中所提出的环境问题,以及作为“种族细胞”(ethnic cell)的环境的问题,它们总是已经在体外化的过程中被分割成了内在环境、技术环境和外在环境等彼此相互衍射的诸种环境。③以此方式,构成了体外化单体(exosimples)和体外化复体(exocomplexes)的体外化过程。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可参见G.Gilmozzi, et al., Localities, Territories and Urbanities in the Age of Platforms and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Anthropocene Era, Stiegler and the Internation Collective, ch.2,以及B. Stiegler, Qu’appelle-t-on panser? 3:Déconstruction et destruction,即将出版。勒鲁瓦-古兰以“外在化”(exteriorization)概念来表示“体外化”。这样的话,从来就没有单一环境(就像没有单一语言一样),有的只是从最开始就以某种方式被分割开来的诸种环境。这里,我们必须将环境与语言问题做一个对比:从来没有单一的语言,有的总是俗语、个人习语、方言、土语等诸种语言。
(2)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区分躯体之外的外在器官发生(exosomatic exorganogenesis)和外化记忆的体外器官发生(exomnesic exorganogenesis):外在记忆化(exomemorization)④B. Stiegler, Qu’appelle-t-on panser? 2:La leçonde Greta Thunberg,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20.是提示记忆之支撑物(hypomnesic supports)的生产过程;并且,从这些不同的延异之差异化(differently différant differentiations)过程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辨识出普遍技术趋势之表达的条件。普遍技术趋势包括诸多的趋势,除了在头脑中幻想之外,它们从来没有被完全表达出来过。勒鲁瓦-古兰从原则上指出过一种衍射过程,此种衍射能够摧毁从原则上制造负人类熵之衍射的所有东西,但西蒙栋在假设机器具体化(machinic concretization)之过程的时候却忽略了它。机器之具体化能够引导某种联合环境(associated milieus)的形成,此种联合环境凭借控制论扩张其网络范围,进而会构成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Gestell)。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对这两点内容进行评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九、什么是趋势?
普遍技术趋势之表达的条件会受到技术个性化(technical individuation)过程的限制和引导,因此,它的表达总是不完全的,它的条件会根据制造这些表达的外在记忆的文码化的类型而变化。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码化过程正是在此期间出现的)开始,体外记忆的文码化就已经产生了社会系统的提示记忆的支撑物。吉尔(Bertrand Gille)和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从萨满教到学院、研究机构、法院、行政辖区、国会等,再到教堂、寺庙和所有类型的神学组织,都是这种支撑物。准确地说,普遍技术趋势之表达的条件是根据先前的外在记忆化过程所产生的事物的类型而变化的,而此种过程与文码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什么使趋势成为趋势,并且仅仅是趋势?这首先是因为单一趋势是不存在的:趋势总是与其对立趋势相伴而存在,它们因此共同构成了一种同源二极性(bipolarity),并进而扩展了西蒙栋所说的不确定的二分体(the indefinite dyad)。此种二元性也是一种冲突性,它正是尼采通过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两种形象所构造出来的东西,也即“不和”(eris)。而且,这也是柏格森以其他术语所重新构想的内容:他把热力学和生命的特异性(singularity)放到“宇宙的热寂”过程中去思考。
趋势相对于另一种(对立)趋势而言,是一种(对立)趋势。在此趋势中,就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动态系统。此种动态系统在受到多重因素更强限制的作用下,会形成一系列的互导关系(transductive relations)。其中也会生成次级系统。比如,体内化生命(endosomatic life)①所谓“体内化生命”指的是一般的纯粹生命有机体,即病毒、细菌、植物和动物。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生命是“体内化生命”在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生命形式,因为根据勒鲁瓦-古兰的“外在化”思想和洛特卡的“体外化”思想,人类进化是逐渐地将其器官功能外在化于技术和技术物体之中而进化的,人类是“体外化生命”(exosomotic life),人类的出现是与纯粹生命的断裂。关于“人类生命与一般生命的断裂”的论述,可参见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The Fault of Epimetheus, R. Beardsworth and G. Collins(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8, pp.134-142。——译者注的有机体就是一种动态系统,它由器官构成,而器官则是由细胞构成。在人类生命中,什么又使得对立趋势成为对立趋势呢?这是由柏格森所提出的问题,他将其描述为一种在任何力学中都在发生的神秘的开放性(mystical opening)问题。②H. Bergson, 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Trans. R. Audra & C. Brereton (Trans.),Westport: Greenwood,1974, ch.4.此处所谓的力学,不仅包括牛顿力学及其“机械论”,也包括品达(Pindar)意义上的“机器”(mekhanē)。③B. Stiegler, The Age of Disruption: Technology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 D. Ross (Trans.), Cambridge:Polity, 2019, p.92, p.157, p.290.
在有时被称为“临界状态”(disruption)所诱导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技术多样性的问题就会出现。然而,技术多样性本应是作为抵抗单一趋势之事态而出现的。所谓单一趋势实际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因为它不再是一种趋势而只是一种状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状态,即我们所说的死亡,这里的问题就成了“文明的死亡”。而这种临界状态的特殊性实则是基于下述事实而出现的:体外化的科技和外在记忆的科技现在已被数学机器(mathematical machines)整合起来,这就形成了文码化的数字阶段,并因此建立了一个完全无法比拟的体外化阶段。
十、趋势与熵
这种整合正是基于算法的“平台”——正如弗兰克·帕斯奎尔(Frank Pasquale)所描述的——所具有的特征,这相当于这种新计算的“一般等价物”:它倾向于取代货币。但是,这种趋势迫使自身成为一种事实状态(state of fact),而不再仅仅是一种通过其历时化来扩展其共时化的趋势,它的“普适性”就产生了一种对生物圈和技术圈都非常致命的无法抵抗的人类熵。
这一挑战因此重新引入了在体外化和外在记忆化之间再建心智多样性之可变性的条件。很明显,心智多样性的可变性也是技术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可以培育能够阻止技术圈去破坏生物圈的生物多样性。这就要求从体外化视角和心智发生(noogenesis)的视角来重新反思“什么是心智”以及心智的官能和功能等问题。①B. Stiegler, Postface: 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 dans l’Anthropocène,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1-3.Paris: Fayard, 2018, pp.862-868.
体外进化是不同于体内进化的进化模式,我们在体外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体外科技(exosomatic technologies)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问题。西蒙栋将这些问题看作是机械学(mechanology)的问题,康吉莱姆则将其看作器官学问题;而在洛特卡之后,体外科技问题则属于我们应该以体外进化的视角来考虑的问题。体外进化确实会受到体内(器官构造)的束缚,康吉莱姆就曾在《正常与病态》一书中尝试分析过这个问题。但是体外进化会超脱这些束缚,即使并不能完全摆脱。举例来说,斯蒂芬·霍金正是在几乎摆脱内在器官束缚的处境下,进行自己的生活的,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因为,如果他在某种程度上完全超越内在器官之限制,他就不会死了。
说到这里,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来谈一下第三点。在《环境与技术》一书所做的定义的意义上,技术环境总是超越内在环境,并且,技术环境正是通过将自身贯通于与其他内在环境(其他“种族细胞”)所处的共同外在环境中,而与其他内在环境的技术环境之间发生共振,进而使自身与其他内在环境形成联系的。
今天,技术环境的贯通浸透于所有外在环境之中,以至于不再有任何外在环境;并且,除了其自身缺乏培育异质性之潜能并因此变得贫瘠的内在环境之外,也不再有任何东西。也就是说,技术环境会贯通和连接内在环境,与它们形成联系,并进而使内在环境本身崩溃。最终,技术圈不再有任何异质的成分,而只是一种单一的技术环境。
外在记忆化导致了三个层面上都出现的体外器官化(exorganization):
(1)生理层,比如与体内器官相连接的非提示记忆(non-hypomnesic)的体外化器官;
(2)神经层,它构成了体外化的、外在器官化的大脑的主要特征,并从提示记忆的意义上作为神经层而存在;所有这些都是以作为社会规则的教育模式(对神经层的塑造)为前提的;
(3)逻辑层,它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西方)是逻各斯(logos)、悠闲(skholē)和休闲(otium)的问题,但是,随着逻辑机器的出现(这种机器本身是基于物质的微观物理学特征而发明出来的),逻辑层的问题已经变成了科技问题。
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象征的体外器官化(exorganizations)(首先是习语)被编织起来。这三个层面的编排正是更高级的复杂体外化有机体(exorganisms)的特征。
这些问题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将会构成基于负人类学、以期到达负人类世时代的、为一种负熵经济服务的新的理论计算机科学。而在此科学理论的中心,将进行着贯彻整个想象过程的知性与理性之不可计算性和不可化约的延异过程。在这里,提示记忆的第三滞留构成着想象本身;在这里,勒鲁瓦-古兰的普遍技术趋势构成着技术—逻辑之图式(techno-logical schemas)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