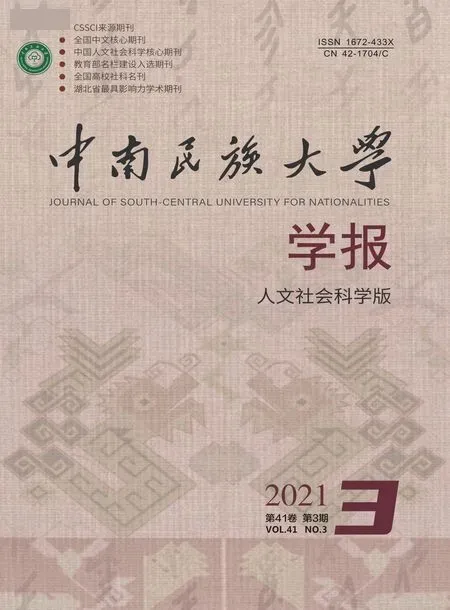清朝“直省-藩部”二元结构下的边疆治理经验
邓 涛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国古代大一统的集大成者,其在疆域范围内推行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府州县”制长期同札萨克制、军府制等具有一定自治权的边疆管理制度并存。清朝在边疆治理方式和效果上取得了超越过往朝代的成就,即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更具稳定性和持续性,其中的原因值得分析。同时也应当看到,清朝在不同藩部地区推行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段和不同区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而一些举措和体制由于未能因时制宜,弊端日益显现。
关于清代边疆治理的经验,以往有较多研究涉及,如张永江分析了清朝在藩部地区的不同治理模式[1];苏德毕力格分析了清朝对北方藩部治理的得失[2];邓涛从长城功能的角度分析了清朝边疆治理政策和效果[3];同时还持续研究涉及藩部与直省的关系[4]。而从“直省-藩部”二元疆域结构的角度分析清朝边疆治理的得失,还有待深入。
一、“直省-藩部”二元疆域结构下的不同治理模式
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之策,集历代边疆治术之大成,同时,清前期统治者励精图治、勤勉不怠,因此,清朝逐步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乾隆朝二十四年( 1759年)清朝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乱后,清朝的大一统局面正式形成且日益巩固。清朝“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版图结构更加稳定。第一部分即是直省地区。该区域大体实行府州县体制,由中央派遣的流官管理,官员俸禄、考核皆由地方和中央负责,地方的自主权十分有限,即如《清朝文献通考》所记载,当时“为省一十有八,分置各府,以领诸县”[5]243。第二部分为藩部地区,“至各边外之地,隶在舆图者,复以千万里计”[5]243。清朝在藩部地带实行札萨克制、驻藏大臣制、伯克制、将军制等特殊体制,对藩部地区实行差异化管理。关于“藩部”所指,广义的藩部指同清朝建立了封藩关系的部落,包括察哈尔八旗蒙古、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等归清朝直接管理的藩部地区,但不包含朝鲜等属国[1]24。本文研究所涉及的藩部含义为广义的藩部。
《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了乾隆朝大一统之后清朝的疆域:“北自大青山左右为蒙古诸部,至喀尔喀地……西南自四川境外为云南及青海、西藏地……其在天山北路则有乌噜木齐、伊犁等地,天山南路则有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5]243显然,清代的安南、朝鲜等朝贡国并未被纳入清朝的实际版图,仅作为名义上的臣服之地,而疆域内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则被视为清朝领土。关于藩部与清朝的关系,有研究认为:“不论它如何特殊,藩部与行省比较,都只能认为是一国之内统一主权之下的两种统治形式而已。”[1]260可见,虽然统治形式不同,但直省和藩部皆为清朝的一部分。
在蒙古地区,清朝将蒙古原有的鄂托克、爱马克体制改造为盟旗制,在部分盟旗地区又设立将军一职加以统帅,在给予自治权的同时实行分而治之。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制,在基本不改变西藏基层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加强对西藏上层宗教及世俗贵族的管理。清廷在不同藩部实行不同制度,兼顾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实际,其原因如学者所言,各民族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治理制度、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如在边疆地区强行划一行政制度、宗教信仰与社会习俗,势必引起各族的阻力而造成动乱”[6]63。此外,清朝针对不同藩部制定了不同的法律或制度,如《蒙古律例》等[7],在法律上对边疆地区进行差别化管理。
清朝在疆域范围内实行“一国多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对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民族习俗、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的差异化管理问题,在一定时间段内,对保持中央对藩部的统治、增强藩部对中央的向心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一国多制”的弊端也在逐步显现。到清末时,这些弊端影响到国家对边疆的稳定统治。
二、高度自治“札萨克”制度存在的问题
清朝在藩部地区的统治不同于直省,如在蒙古地区大体实行盟旗制,且掌旗官员多具有世袭性,在财权、人事权等方面有一定的自治权,也因此,相比直省地区,清朝对藩部的管理深入程度要弱一些。清朝给予藩部地区的高度自治,体现了清朝统治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特点,但由于清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朝代,因此,藩部地区具有相对自治权的体制,本质上是同清朝不断强化的专制体制及中央集权体制相矛盾的[1]260。综观整个清代,清朝对藩部地区的统治亦出现了一些波动。
1.札萨克制下的布尔尼反叛。清前期,在蒙古地区,清朝首先面对的便是来自原察哈尔大汗黄金家族嫡系后裔的反叛。明末崇祯朝,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病逝,其子额哲投降清朝后被晋封为和硕亲王,清朝虽然将其部众编为札萨克旗,但察哈尔蒙古地位居于蒙古诸部之首,具有较大的自治权。额哲去世后,袭爵的阿布鼐抵触清朝,故清朝将其囚禁,并命阿布鼐之子布尔尼承袭爵位,管理原有部众。但布尔尼具有反清和离心意识,最终的结果是“布尔尼之乱”的出现。布尔尼自视黄金家族嫡系后裔,对其父被囚禁十分不满,同时也不愿为清朝所管束,试图脱离清朝的统治。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后,清朝南北陷入动荡,清朝将部分察哈尔兵调入长城边内,以稳定局势。布尔尼见部众被分散、军力被削弱,更加不满,便积极准备叛清行动,“初察哈尔布尔尼乘吴逆作乱,欲谋劫其父阿布奈,兴兵造反,日与其党缮治甲兵”[8]694。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得知布尔尼有反叛之心,“欲遣人召布尔尼兄弟,以觇虚实”[8]694,但布尔尼拒绝入京,并囚禁了清廷派来的侍卫塞棱,于当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兵反清。清朝平定该叛乱之后,废除了察哈尔部的札萨克制,参照满洲八旗设立了察哈尔八旗,即直接由清朝中央管理察哈尔部众,且管旗官员并非世官,由清廷调任。可见,清朝废除察哈尔的札萨克制,即意识到札萨克制下中央对藩部的管控程度较浅,相对容易出现离心倾向。
2.哈密回部札萨克制弊端在清末日益显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朝统一哈密回部, “其地始内属,授为札萨克一等达尔汉,以旗编其所属,视各蒙古”[9]301。相比此后清朝在南疆实行的伯克制,清朝在哈密实行的是类似漠南蒙古的札萨克制,自治权更大。清末同治朝西北动乱之后,由于哈密首领忠于清朝,清朝保留了哈密的札萨克制,但该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清代时,哈密回部“所设官员,俱不支俸”[10]1791,即哈密回部的维吾尔官员薪俸由哈密首领自筹,而哈密回众为哈密首领的“属人”,哈密首领可以自己决定剥削程度,一旦剥削过重,便容易产生动乱。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哈密地区维吾尔部众因哈密首领剥削过重而反抗,曾参与处理暴动的杨增新提到暴动缘由:“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夏间,缠民千余人各持土砖,将王府兴门砌塞,意在逼迫回王改土归流。”[11]在札萨克体制下,中央无法直接管理藩部的普通民众,造成藩部首领自治权力的过大,也影响了藩部人民对中央的认同感。哈密札萨克制度的弊端最终遗留到民国时期全面爆发。1919年,哈密首领沙木胡索特去世后,民国新疆政府计划改土归流,但遭到哈密王府封建上层的强烈反对,原先的哈密统治阶级“既然有上述莫大之权利,一旦改设县治,归县管辖,不惟向有一切权利完全丧失,且须与一般缠民同赴县仓纳粮,自难甘心,于是乃捏造缠民世耕田地将拨汉民耕种,缠民妻女汉民要娶等种种谣言”[12],这些王府上层人员造谣煽动,引起了哈密暴动,进而引起了整个新疆持续数年的严重动乱。
三、直省与藩部隔离政策带来的不同效果
在清朝的北部边疆,由于明长城的存在,直省和藩部之间有较为明显的界限,即长城。清朝曾试图大体以长城为界限,隔离直省和藩部人民。
1.清朝以长城为依托实行双向民族隔离政策。综观整个清代,尽管长城的隔离功能日益弱化,很多民人(指直省民众)也开始越过长城在边外藩部地区繁衍生息,但直到清末财政危机前,清朝大体将长城视为直省和藩部的界限,管控两侧人民的自由交流。有研究认为,“清代视长城为分治蒙汉的天然藩篱,将出入口限制在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等关隘,另一方面严格管理通关文书票照的发放”[13],显示出长城的关禁和界限作用。
清朝的民族隔离政策,首先是限制民人出边至蒙古等地。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清前期人口增长较快,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北方民人开始越过长城到藩部地带耕种为生,但清前期清廷规定:“无印票可验者,不许私放出口……凡民人无票私出口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14]对民人出边到藩部地区,总体是限制的。同时,清朝还限制藩部人员入边进入直省。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针对青海蒙古入边事宜作了规定:“或有喜丧、煎茶、诵经等事进边,亦不得过百人。令该札萨克呈明办理,青海蒙古事务大臣查核,给予印票,守口官弁验票,始准行走,回日缴销。”[15]总体上禁止藩部人员大规模或随意进入直省地区。
2.隔离政策造成民族之间的陌生感。清朝民族隔离政策,对保护边外的自然生态、避免因民人大规模出边造成同藩部人员的矛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双向的民族隔离政策,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影响到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同时,由于双方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长城沿边官员对藩部地区有一种陌生感,他们对藩部地带同中央的关系认识不够清晰。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朝早已实现了对漠北蒙古、漠南蒙古的统一,但由于长城界限功能的存在,故彼时直省绿营同蒙古人因追捕马贼而产生矛盾时,直省绿营官员竟将察哈尔蒙古人视为敌人,因此,乾隆帝严厉批判了绿营官员,提到“竟视察哈尔蒙古如准夷……察哈尔蒙古,本属我朝世仆,张家口外牧群,现俱隶之太仆寺,安设台汛,不过稽查出入,以防私越耳”[16]678。可见,尽管长城已经不是王朝的边界,但由于清朝实行民族隔离政策,造成部分直省官员对“直省-藩部”二元疆域结构下藩部为王朝一部分这一现实的生疏,亦会影响藩部人员对直省和中央的认同感。隔离制度限制了直省地区民人同藩部地区民人的自然融合,也影响到了清朝对藩部地区的持续稳定统治。
3.直省民人融入新疆为清末新疆的稳定创造了条件。相比在蒙古地区实行民族隔离政策,清朝鼓励民众前往新疆耕种定居。乾隆朝时清朝统一了新疆,面对此前一直同清朝对抗的漠西蒙古地区,清朝为加强在该地区的统治,除了派遣八旗和绿营赴新疆驻扎生活外,还鼓励士兵携带家眷到北疆,鼓励民人前赴北疆定居,且将新疆作为流犯的重要发遣目的地。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在“敦煌等三县,招有情愿赴巴里坤种地民一百八十余户”[17]。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廷“令将甘省与新疆接壤居民,量其道路近便,迁移乌鲁木齐,俾资生有借,旷土愈开”[10]2502。大量民人迁徙至新疆,为清朝统一新疆之初当地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规定:“巴里坤兵丁差繁……明春即于沙州、安西、靖逆各营调兵四百名,千把总、外委四员,共合五百名,定额屯田。”[10]2550此外,被派至甘肃敦煌的遣犯,亦被清朝从敦煌调至新疆。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规定:“查沙州等营分发遣犯内,其年力精壮者,可得一百五十名,请就近拨赴巴里坤,随兵耕作。”[16]515无论是民人,还是士兵,或是遣犯,此后都成为新疆北疆开发的重要力量,促进了新疆多民族共生共存民族格局的形成。
直省民人迁入北疆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如同治朝时,新疆被阿古柏和沙俄所侵占,除了清朝驻扎在新疆的经制兵外,移民至北疆的民人也成为反抗侵略的重要力量,先后涌现了徐学功、孔才等保卫新疆、抵抗侵略的民团首领。清末民初时,新疆虽然距离中央政府最远,但由于此前大量直省民人前往新疆耕种定居,进而成为边疆稳定的依托,故在经历辛亥革命之后,新疆地区同民国政府依然保持了统属关系。
四、中央在藩部的驻军促进藩部地区的稳定
驻军是中央在藩部地区存在感和实力的体现,驻军在平时可以威慑离心和分裂势力,动乱时也可起到平定叛乱、反抗侵略、稳定地方的作用。清朝对藩部的治理,也因驻军情况的不同而带来了不同的后果。总体来说,驻军较多的地区相对稳定,驻军较少的地区不甚稳定,完全不驻军的地方最不稳定。
1.哈密回部的稳定离不开清朝的大规模驻军。新疆哈密回部归附清朝最早。哈密是中原通往新疆的通衢,“出嘉峪关外至哈密,分为南北二路”[18]。同时,哈密是南疆、北疆互通的交通要道,“南通吐鲁番,为天山南路之咽喉,北通巴里坤,为天山北路之冲要”[19]。也正因此,清朝在哈密驻扎了大量军队。
实际上,哈密主动归附清朝,除了清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之外,也离不开清朝强大的军事支撑。正是由于清朝击败了控制哈密的漠西蒙古噶尔丹,才使得哈密顺应历史大势归附了清朝。基于哈密的重要交通地位,清朝在该地驻扎了大军,将哈密视为经略新疆的前沿。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朝派兵至哈密,协助哈密抵御漠西蒙古。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增建哈密新城,为官兵驻防之所”[5]406,清朝在哈密驻军更加稳定。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时,清朝在哈密设立了提督,“派提督一员,驻扎哈密,节制两处驻防之总兵”[20]924。
清朝统一漠西蒙古和南疆之后,虽然裁撤了哈密提督,但保持了在哈密的长期驻军,“设哈密协副将以下将领八人,兵八百名”[5]280。清朝在哈密的驻军,是哈密回部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如雍正九年(1731年),有地方官员怀疑哈密回部私下投靠漠西蒙古,但雍正帝反驳道:“我之军力,能庇护哈密,哈密自不为贼人所用。”[20]380在雍正帝看来,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持藩部对中央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2.未驻军或驻军过少是清代西藏出现动荡的重要原因。顺治朝时,经清朝延请,在漠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的支持下,西藏五世达赖得以顺利赴北京朝觐顺治帝,清朝“赐以金敕、金印,授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21]。自此,清朝同西藏的关系除了朝贡关系,还多了册封关系。此后,清代历届达赖都需经清朝册封方才名正言顺。但顺治、康熙时,清朝并未在西藏驻军,故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得以插手西藏内部斗争,并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派兵占领拉萨,控制了西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遣兵进藏,立即讨平之”[9]666。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藏正式划入清朝版图,清朝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加强。限于当时西藏地区有限的生产力水平,西藏地方无法长期负担入藏清军的粮饷,故清朝不得不撤回在西藏的驻军,或在西藏仅保留少量驻军。综观清代西藏地方政局,清廷在西藏驻军的撤离或者削减,都或多或少地降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治能力,引起了西藏地方离心势力的加强,进而造成了西藏内部的动荡。
雍正初年,清朝撤回了驻扎在西藏的清军,原因便是后勤供应问题,即“恐屯扎日久,唐古特等供应繁费”[22]96。从西藏撤军之后,清朝在西藏实行了噶伦联合掌政制,“以贝子康济鼐总理其地”[23],以西藏贵族作为清朝管理西藏的代表。由于噶伦政府内前藏贵族和后藏贵族发生矛盾,雍正五年(1723年),后藏贵族康济鼐为前藏贵族阿尔布巴所杀,西藏出现动荡。在西藏局势平定之后,清朝又委任后藏颇罗鼐作为清朝管理西藏的助手,并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和驻扎绿营兵,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
乾隆帝继位之后,未能将驻军政策持续贯彻下去。乾隆四年(1739年),经清朝册封,颇罗鼐被封为多罗郡王,成为西藏爵位和政治地位最高的贵族。颇罗鼐执政期间,对清朝感恩戴德,配合中央在西藏施政,但颇罗鼐去世后,承袭爵位的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对清朝的忠诚度不如其父,并试图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藏王。
乾隆初期,清朝在西藏维持了约五百人的驻军。彼时,四川总督上奏:“西藏原驻兵五百名……兵止五百,然数年来安静无事,未始不赖乎此。”[24]在四川总督看来,西藏地方局势的稳定同清朝的驻军有着直接关系。遗憾的是,此后经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奏请,乾隆帝同意裁撤在西藏的驻军,使得驻藏大臣对珠尔默特的约束能力大大下降。乾隆十五年(1750年),珠尔默特反叛迹象日益明显,驻藏大臣同中央联络日益不畅,驻藏大臣傅清等不得不依靠仅有的一百名士兵,设计杀死了珠尔默特,但傅清等人亦被叛军杀死。此后,清朝开始在西藏维持了一定数量的驻军,一直延续到清末。
3.驻军战斗力下降影响到中央对西藏的治理。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内忧外患,对西藏的统治能力有所下降,驻藏绿营兵的战斗力也不断下降:一是“连年藏饷短绌”[22]1706,西藏驻军军饷短缺,衣食难保;二是三年一换的轮换制度遭到破坏,“迨后留防过多,更换日少……各弁兵日形苦累……倘偶有事端,难资得力”[22]1582。与驻军战斗力减弱相伴随的是英俄等侵略势力对西藏的日益染指。光绪三十年(1904年),即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之时,英国乘清朝无暇西顾,“剥削主权,边境益急”[25]72,派兵侵入西藏,占领了拉萨。此后,在清朝的交涉下,英军退出了西藏。
清朝为抵抗侵略,决定整理藏务,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向西藏派驻川军。这一举动,引起了十三世达赖等部分西藏上层的反对,但清朝认为若不在西藏驻扎足够军队,“任其一切自谋,则犹是独立之国”[26],既不能抵御外国侵略,也无法约束西藏的离心势力。宣统二年(1910年),由于西藏地方派兵抗拒中央增派士兵进入西藏,“四川协统钟颖率师西讨,累战至拉萨”[25]130,十三世达赖担心被清廷追责,便逃至印度。此前,如清朝在西藏保持强大的驻军,英国入侵西藏和西藏派兵抵抗中央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五、稳定而强有力的中央是藩部地区稳定的保证
清前期,清朝国力强盛,皇帝勤政有为,外部侵略势力尚无足够实力侵略中国,清朝得以集中精力统一北部边疆。清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用时超过一百年,最终统一了漠北蒙古、青海蒙古、阿拉善蒙古、哈密回部、漠西蒙古、南疆、西藏等藩部地带,实现了大一统。相比以往朝代,清朝对藩部的统治更为稳定。
1.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是藩部主动归附的重要原因。清朝实现对藩部的统一,或是对藩部地区实现稳定统治,其重要前提是中央自身的稳定和强大,正如学者所言:“清朝对边疆地区控制的程度如何,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6]61没有稳固的中央,边疆地区自然也难言稳定。
以清朝统一青海蒙古为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西征漠西蒙古噶尔丹,抵达宁夏,距离青海不远。彼时清朝军威正盛,康熙帝要求青海蒙古诸部来朝,在清朝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影响下,“青海四姓厄鲁特诸台吉,愿觐圣上”[8]952。此后,在康熙帝的安排下,康熙三十六年底(1697年),青海蒙古部分首领前赴北京朝觐康熙帝,康熙帝赐予亲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当年底,康熙帝邀请青海蒙古首领在北京西山观看了声势浩大的八旗兵火器演练。彼时,青海蒙古首领对清朝强大的军威印象深刻,“惊叹曰:天朝军威精严坚锐如是可畏也”[8]988。康熙帝通过阅兵,在宴请、封赐之余,向青海蒙古首领展示了清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增强了他们对中央的向心力。
2.从“王辅臣之乱”看清朝对藩部地区的约束力。相比流官治理的中原直省地区,中央政权对藩部地区的管理深度弱于直省地区。也因此,一旦清朝陷入内忧外患、自身实力减损进而对边疆的管控能力下降时,藩部地区容易出现动荡或离心力增强倾向。康熙前期,直省地区相继爆发了“三藩之乱”和“王辅臣之乱”,清朝南方和北方的陕甘地区陷入动乱,清朝不得不集中主要力量平叛,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自身实力。当时,清朝集中陕甘地区兵力平定王辅臣之乱,造成部分区域兵力空虚,而在清朝入关前即已臣服于清朝的漠南蒙古鄂尔多斯部乘机劫掠宁夏地区,原因是“宁夏与鄂尔多斯接壤,今乘内地有事,蒙古入边,侵掠宁花寨、平羌等堡”[27]。清朝得知情形,命理藩院派人前往鄂尔多斯部协调处理该事件,此后事件很快被平息。尽管这只是一场小冲突,且清朝对漠南蒙古的管控依然牢固,但反映了清朝自身实力衰弱时,对藩部地区的管控程度也会有所下降。
3.清朝国力下降与西藏局势的动荡。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珠尔默特之乱”后,清朝实现了对西藏较长时间的稳定统治,这一稳定局面的达成,除了驻军之外,也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威信和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支持。强有力的中央财政支撑了西藏局势的稳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西藏僧俗官员的津贴由清朝定期拨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规定:“西藏辅国公一员……札萨克台吉一员……噶布伦四员……戴琫六员……云骑尉一员……以上俸银、俸缎,均由户部径拨四川总督附解该处。”[28]二是盛世之下,清朝可以随时拨兵拨饷给西藏以抵御外来侵略。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帝以“现在后藏边境有廓尔喀与唐古忒因帐目滋扰之事”[29],决定派兵入藏反击廓尔喀,并迅速从四川等地调拨了饷银二百万两作为军费。但清末面临外国侵略和内部动乱,财政危机较重,中央对西藏的管控能力也随之下降。一是如前文所提到的,驻藏军队面临军饷短绌问题,驻军士气低落;二是由清朝中央政府承担的西藏僧俗官员津贴也不时拖欠,“赏番之款,多未发给,益怀怨望”[30]。这造成西藏地方官员对中央的不满和抱怨。
咸丰朝时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四川瞻对藏区也出现叛乱。由于清朝无力及时派兵平定瞻对叛乱,使得西藏地方得以乘机出兵瞻对。西藏地方在平定四川瞻对的叛乱之后,“索兵费银十六万两,秉章未允,藏人因据其地,设官兵驻守”[31]。这意味着西藏地方力量在瞻对地区的增强,随之而来的便是清朝中央政府对瞻对这一藏民聚居区管治能力的下降,反映了中央政权衰弱背景下藩部自主力量的增强。此外,由于清末国力衰弱,部分驻藏大臣能力欠缺、品行不佳,如“驻藏大臣奎焕到后,因其行止不检,商上更为藐视”[30],驻藏大臣逐渐被排斥在西藏地方的决策圈之外,西藏的自治和自主意识更加强烈。有研究认为:“清朝国势的衰落、在西藏某些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和驻藏大臣自身素质的每况愈下,使驻藏大臣衙门的权威严重下降。”[32]
光绪元年(1902年),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强迫清朝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其中即包括允许英国派探路队进入西藏,引起了西藏僧俗高层的反对。条约为西方侵略势力深入西藏创造了条件,如俄国乘机拉拢西藏高层,“许以有事救护,藏番遂恃俄为外援”[30]。清朝无力维护西藏权益,导致西藏地方对中央离心力的增强。
综上所述,直省和藩部之间的隔离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反而体现了民族交流和交融的重要性;中央政权在藩部地区驻军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央对藩部的稳定统治;而中央政权是否稳定,是否强大,也同藩部稳定密切相关。清朝在疆域范围内,针对不同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实行了不同的统治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实行差异化治理时,除了因地制宜,也应因时制宜。即一些制度和政策,在一定时段内是适应当时的形势的,例如清前期,清朝以强大的国力为支撑,在不同民族地区推行不同的治理模式,适应了不同地区的实际,但是随着清末清朝国力的衰弱,特别是随着外国侵略势力深入边疆,造成中央政权对藩部地带的管控能力下降。原本用以维护大一统局面的札萨克制等制度,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反而造成藩部地区离心倾向加强,成为清朝维持统一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影响到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央政权在藩部地区的稳定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