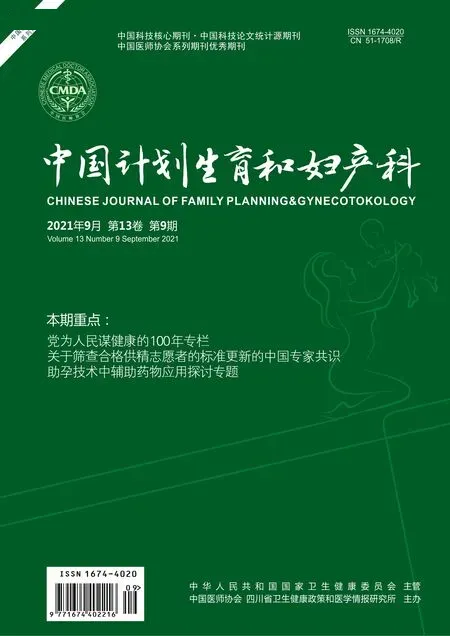集落刺激因子在助孕技术中的应用
白瑜,靳松,杨业洲
集落刺激因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CSF)是促进髓系祖细胞增殖、分化的一组生长因子,包括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M-CSF/CSF1)、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CSF2)、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CSF3)、多重集落刺激因子(multi-CSF/IL3)等,重组上市的商品化产品则称之为相应的形成细胞刺激因子。骨髓、间质细胞、成纤维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均可产生CSF,重组的GM-CSF、G-CSF、M-CSF在血液系统疾病和防治肿瘤放化疗不良作用等领域应用已经超过30年[1]。CSF与其受体(CSF-receptor,CSF-R)结合后发挥作用。已有研究发现,除髓系祖细胞、髓系白血病细胞、成熟的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一些T细胞和B细胞膜上表达特异性的CSF-R外,子宫内膜上皮细胞、胎盘细胞、滋养细胞和黄素化的卵巢颗粒细胞等许多非造血组织细胞亦可表达CSF-R。CSF与生殖相关细胞上表达的受体结合后,参与卵泡发育、成熟及破裂排出,促进子宫内膜的生长,介导母胎界面免疫调节,参与胚胎种植、发育及妊娠维持[2],已经发现的CSF中,除GM-CSF被用于胚胎培养成分来提高可利用胚胎形成率外,G-CSF在复发性卵泡黄素化不破裂综合征(luteinized unruptured follicle syndrome,LUFS)、胚胎培养、薄型子宫内膜、反复胚胎种植失败(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复发性流产(recurrent pregnancy loss,RPL)等生育障碍状态的治疗中得到了较多的试用。
1 卵泡黄素化不破裂综合征
连续的超声监测卵泡发育显示卵泡生长,出现黄体生成素(lnteinizing hormone,LH)高峰后卵泡持续存在,血孕酮水平达到正常黄体期水平,可判断为LUFS。在规律性月经周期中,LUFS的发生率为5%~11%,在不孕患者中,LUFS的发生率为25%~43%,且发生LUFS后的下一个月经周期,80%~90%的患者将再次发生LUFS。盆腔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手术等均可导致LUFS发生。前列腺素合成或功能障碍可能是导致LUFS发生的主要分子水平机制。研究发现,在卵泡发育过程中,主要由颗粒细胞产生G-CSF进入卵泡液,卵泡液中的G-CSF水平随卵泡增大而升高,卵泡晚期达到高峰[3],其作用是诱导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向卵泡聚集,促进单核细胞向巨噬细胞分化,巨噬细胞分泌蛋白酶导致卵泡壁破裂,卵-冠-丘复合体从卵泡中排出[4]。在确认LUFS后,应在下一个月经周期继续进行卵泡发育监测,卵泡直径达到15 mm时检测LH[5],LH出现峰值或在给予hCG后,连续2~4天的B超检查,卵泡持续存在,可诊断为复发性LUFS。对复发性LUFS,后续的促排卵应首选hCG,卵泡平均直径达到17~18 mm时给予尿源性或重组的hCG 5 000~10 000 IU。连续使用hCG促排卵3次均发生LUFS,最好建议患者接受腹腔镜手术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助孕。若患者坚持继续自然周期试孕或行人工授精,可在平均卵泡直径达到16~17 mm时给予G-CSF 100 μg皮下注射,24~48 h后给予hCG 5 000~10 000 IU[3],可将LUFS的发生率降低近3/4(4.3% vs 19.1%)[6]。
2 薄型子宫内膜
薄型子宫内膜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普遍认为是指卵泡晚期或使用雌激素准备子宫内膜超过10天,B超下子宫内膜厚度<7 mm。薄型子宫内膜周期取消率高,胚胎种植率和临床妊娠率降低,流产率增加。宫腔镜排除宫腔粘连等器质性病变后,可使用药物来增加子宫内膜厚度,临床常试用的方法包括增加子宫局部雌激素水平(加大使用剂量或阴道使用雌激素制剂)、每日加用75~100 mg阿司匹林、维生素E、西地那非或他达那非、左旋精氨酸、己酮可可碱、干细胞疗法、宫腔灌注富血小板血浆等[7]。G-CSF可能刺激子宫内膜干细胞或动员骨髓干细胞而刺激内膜生长,此外,内膜祖细胞及单核细胞中促血管生成基因的表达增加,促进了内膜局部血管生成[8]。控制性卵巢刺激下拟进行新鲜胚胎移植患者,若hCG扳机日的子宫内膜厚度<7 mm,可在hCG注射前6 h左右使用人工授精管或胚胎移植管将100~300 μg的G-CSF注入子宫腔内。采用自然周期或诱导排卵方案准备子宫内膜行冻融胚胎移植期间,若卵泡平均直径≥16 mm时的子宫内膜厚度<7 mm,当日可在宫腔注入100~300 μg G-CSF。行冻融胚胎移植应用雌激素准备子宫内膜期间,雌激素使用10天后的子宫内膜厚度<7 mm,当日可在宫腔注入100~300 μg G-CSF,2~3天后子宫内膜厚度增加不明显,可重复宫腔注入一次。临床报道显示G-CSF宫腔注入后,子宫内膜厚度较未使用该药人群增加1~4 mm,Meta分析后的OR值达到1.79(95%CI为0.92-2.67)[9],效果较为肯定。
3 反复胚胎种植失败
胚胎种植成败受诸多因素影响,胚胎质量、子宫内膜容受性、胚胎-子宫内膜界面的免疫学状况等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应对RIF的方法均从优化这些方面着手。G-CSF除改善子宫内膜厚度外,还可刺激胚胎分裂和囊胚形成以及滋养细胞生长,影响胚胎粘附于子宫内膜而参与胚胎种植过程,抑制胚胎-子宫内膜界面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免疫反应,抑制Th1细胞分化和功能,刺激Th2细胞增殖分化及其功能表达,产生母胎免疫耐受,维持持续妊娠[10]。对RIF患者,若准备进行鲜胚移植,可在控制性卵巢刺激注射hCG日或取卵结束后或胚胎移植前5~60 min使用G-CSF。自然周期或诱导排卵方案准备子宫内膜行冻融胚胎移植时,G-CSF使用时间点则定在LH峰值日或排卵日或胚胎移植前5~60 min。应用雌孕激素准备子宫内膜时,则在加用孕激素转换子宫内膜当日或在胚胎移植前5~60 min应用G-CSF。单次宫腔内注入G-CSF 100~300 μg,也可单次皮下注射G-CSF 300 μg,或每日皮下注射G-CSF 100 μg至确认妊娠或超声确认宫内活胎。Meta分析显示,对两次及以上胚胎移植后种植失败者,使用G-CSF后临床妊娠率是未使用该药者的2.11倍(95%CI为1.56-2.85)[11],效果肯定。
4 改善胚胎培养结局
自然妊娠时,胚胎先后经过输卵管、子宫腔和胚胎种植后发育阶段。在子宫内膜增殖期和分泌期,输卵管和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均可产生GM-CSF,在增殖晚期和分泌早期达峰值水平。胚胎种植后,母体的蜕膜细胞和胎儿的绒毛细胞也可产生GM-CSF。人胚胎中的内细胞团和滋养外胚层均可生成与GM-CSF结合的α受体(granulocyte-macrophage receptor α,GM-Rα)。鼠胚实验和人胚胎培养均观察到,GM-CSF可促进胚胎细胞增殖,增加抗凋亡基因及其蛋白表达而抑制胚胎细胞凋亡,增加不同发育时期的胚胎细胞数量,减少胚胎细胞碎片,增加优质可利用胚胎数。GM-CSF也促进桑椹胚和囊胚分泌τ干扰素(interferon τ,IFNτ),启动早期胚胎滋养细胞分化形成和生长,参与胚胎种植,维持胚胎及胎儿发育[12]。使用含2 ng/mL的GM-CSF胚胎培养液培养后,8细胞胚、桑椹胚、囊胚、扩张期囊胚形成率增加[13],非整倍体率和流产率呈下降趋势,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呈增加趋势[14]。
5 复发性流产
正常妊娠有赖于胎盘的正常发育和功能表达以及母胎界面免疫耐受的适时调整维持。胎盘的蜕膜细胞、细胞滋养细胞、合体滋养细胞、淋巴细胞等均可产生CSF。所有的CSF均促进胎盘的生长和细胞分化。M-CSF在妊娠后的血清水平增加2倍,子宫局部水平增加1 000倍。GM-CSF和G-CSF在子宫局部水平也显著增加[15]。GM-CSF促进细胞滋养细胞的迁移,促进桑椹胚和囊胚IFNτ分泌[16]。G-CSF增加蜕膜调节性T淋巴细胞和Th2细胞数量及其功能表达,增强RPL患者母胎界面免疫耐受,促进滋养细胞生成G-CSF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促进滋养细胞生长和血管形成[15,17]。对不明原因的RPL患者,可在排卵后6天或hCG检测确认妊娠后,接受胚胎移植者自移植日开始给予G-CSF,100~150 μg皮下注射,每天1次,或每周皮下注射2次,每次150~300 μg。妊娠满9~12周或发生难免流产时停药。RPL者接受G-CSF治疗后的流产率可降低2/3(17.2% vs 51.5%),活产率增加近1倍(82.8% vs 48.5%)[18]。
6 围妊娠期使用集落刺激因子的安全性
G-CSF是CSF中临床应用最多的药物,主要用于恶性肿瘤放化疗等导致的获得性粒细胞减少症。鼠和兔等动物实验显示,怀孕后使用人临床常用剂量2~10倍的G-CSF,可增加流产率,降低子代存活率,但不增加子代出生后的结构畸形[19]。恶性肿瘤放化疗期间应采取有效避孕措施,因放疗和化疗除对孕妇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外,还将增加胎儿发育异常及出生缺陷风险。妊娠期间发现的恶性肿瘤,是否实施放化疗,需根据疾病和妊娠期限等情况,本着“母亲优先”的原则决定。患者坚持继续妊娠且病情许可的情况下使用G-CSF治疗放化疗所致的粒细胞减少症,流产、死胎以及存活胎儿结构和功能缺陷风险增加,这主要与放化疗有关。单纯使用G-CSF对围孕期母儿影响的证据,来自使用G-CSF行外周血干细胞捐赠者。这些临床报道证据显示,围妊娠期使用G-CSF,不增加出生缺陷、流产、孕产期并发症和异常围生儿结局发生率[19-20]。辅助生殖技术、薄型子宫内膜、RIF和RPL等情况下应用G-CSF,使用药物种类较多,但使用G-CSF不增加该类人群不良反应发生率[11,21]。
GM-CSF目前仅见添加到胚胎培养液中的文献报道,对两篇低质量的RCT分析后显示,胚胎非整倍体率呈下降趋势(OR=0.32,95%CI为0.03-3.26),出生缺陷呈增高趋势(OR=1.33,95%CI为0.59-3.01)[14]。
7 用药注意事项
① G-CSF在助孕技术的应用为超药典及药品说明书适应范围用药,应该根据相关规定报医院药事委员会审定并获得该领域的临床试用备案。
② G-CSF为刺激粒细胞生成药物,非先天性或获得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患者可导致使用期间的粒细胞计数显著增加,同时增加凝血酶原片段F1+2、凝血酶原-抗凝血酶原复合物及D二聚体等促凝指标产物,增加深静脉血栓形成风险[22]。因此在用药前及用药后每3~7天必须进行包括粒细胞计数在内的血常规检查,一旦发现粒细胞计数超过20×109/L,立即停药,一般在停药后1周内下降至正常。
8 小结及建议
在卵泡发育及排出、子宫内膜增殖和转换、胚胎发育并在子宫内膜中成功种植、胚胎与胎盘生长、妊娠维持及分娩等过程中,来自卵巢、输卵管、子宫内膜局部和胚胎细胞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途径产生的细胞生长因子组成的网络发挥着关键作用。鉴于已有的临床实践,仅G-CSF在助孕技术尤其是薄型子宫内膜、RIF和RPL中应用较多,GM-CSF添加到胚胎培养液中并已经上市成品试剂。可检索到的多数文献报道中,显示G-CSF可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提高RIF临床妊娠率和RPL的活产率,但也有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G-CSF不能改善这些临床结局指标,但这些文献所提供的均为低或极低质量的临床证据[11],因此尚需经过严密设计、严格按设计方案施行的多中心大样本临床试验来确定其临床效果和安全性。在参考已经发表的文献来处理助孕技术中的相关问题时,使用包括G-CSF等药物辅助治疗,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专业组织制定的相关要求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