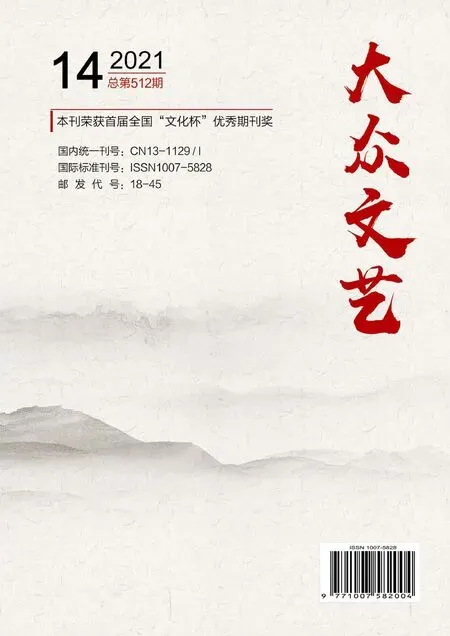华裔温哥华小说中的离散书写*
周风琴
(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淮安 223001)
一、引言
1858年首批华工经由美国西部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淘金,后因加拿大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越来越多的华工涌入,温哥华的唐人街因此兴旺起来。余兆昌(Paul Yee)的作品以纪实的方式书写了几代华人移民在温哥华的经历和唐人街的变迁。不同时代的华裔作家以温哥华都市背景创作的作品,同样呈现了华人移民在温哥华的历史变迁。本文尝试以这些不同时代的基于温哥华都市的作品为例,分析华裔温哥华小说的历史脉络,勾勒出小说关怀议题的传承与转向,论述华人移民与温哥华都市、都市居民及温哥华其他移民之间的关系。依据作家的出生年代、作品的出版年份以及作品所关怀的议题,华裔温哥华小说的历史书写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阶段,90年代的华裔温哥华小说与千禧年后的华裔温哥华小说。第一阶段小说主要议题为早期华人移民的悲苦经历,加拿大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及其造成的家族秘密与丑闻,家族内部冲突与和解。第二阶段小说逐渐摆脱二元对立的书写模式,关注全球性的议题,如疾病、战争,建构华人移民的全球离散网络。
二、90年代的华裔温哥华小说
早期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淘金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广东省三邑四邑县的因生活压力所迫的农民。尽管华人在加拿大的勤奋和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并未得到加拿大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白人以华人攫取就业岗位为由,试图把华人拒之国门外,华人遭受了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及白人的诋毁污蔑,如不断提高的人头税等。直至二战期间,因华人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华人在加国的地位才有所改善,但白人对华人的歧视偏见依然存在。书写加拿大华人移民的作品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笔名为水仙花姐妹的作品,但是华加文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早期的华加文学往往是集体创作的作品集,作品以“打破沉默”为目的,书写华人移民的家族史、打破沉默、挑战加拿大官方的论述。下文以崔维新的《玉牡丹》、郑蔼玲的《妾的儿女》和李群英的《残月楼》为例,分析90年代华裔温哥华小说所呈现的华人移民社群。
(一)第一代移民华人的沉默
上述三部作品中,第一代来加拿大的华人,基本上并不想永远留在加拿大,属于叶落归根型的。但是,因为国内的战乱或者无足够的归国路费,大多数第一代华人死在异国他乡,而运送华人尸骨回国也成为这一时期小说书写的共同点。为了能进入加拿大找到工作,第一代华人会伪造或购买他人的身份证,因非法的入境途径,第一代华人选择保守着其共同的秘密。《玉牡丹》中,女孩梁说“唐人街上那些三层和五层的家族建筑上的每一块砖都像长城般抵御着好事者。那些早年从中国来到海外的老人们在这些壁垒内隐藏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经历。留下的只有文件记载的经历,那是些与编造的故事混杂在一起的经历。”还有,因为语言的隔阂,无法与白人社会沟通,因此对于所遭受的压迫及不公正的待遇基本保持沉默。《残月楼》中面对1924年简妮特史密斯案发生时,老一辈华人的“本能的第一反应是把商铺的门窗都用木板钉死,在片打街口设下路障,储备足够的大米和咸鱼以资与他们的围困抗衡。”华人的沉默抵御方法揭示了华人在加拿大被压迫,无力抗击的被动处境。对于第一代华人来说,沉默也是他们得以存活下来的武器,因此第一代华人蜷缩在唐人街的空间内,选择默默守护着属于他们的秘密。华人移民选择沉默的另一原因是“很多华裔不愿提及,甚至宁愿忘掉过去那段屈辱的历史”。
在这封闭的唐人街空间,还有另外一群被压迫的群体,就是早期的华人女性群体。因加拿大对华政策,早期来加拿大的女性人数非常少,这些女性来到加拿大后,所面对不仅仅是陌生的环境,还有内心的孤寂与丈夫的冷漠,婆婆的刁难等。《玉牡丹》中梁的母亲在家中没有任何权力,自己亲生的子女竟随大房夫人的孩子称她为“后妈”。《妾的儿女》中的梅英来到金山时,丈夫陈山早已与此地的北京茶楼签了协议,“根据协议,梅英得待在这里工作,直到还清陈山把她弄到加拿大所花费的开销为止。”梅英愤恨不已,因为女服务员和妓女差不多,梅英沦为丈夫赚钱的工具。《残月楼》中,美兰于1911年来到金山时,噩梦就开始了,“美兰的噩梦就是孤寂。她来了,却发现这是个无声的世界。每当她试图走出去时,磐石般的沉寂就会把她撂倒……这儿一个女人也找不到。”同样地,八年后,美兰的儿媳妇凤梅发现,“除了几个陪伴服侍我的女人外,其他来宾全是男人。”因为婚后五年仍未生下子嗣,凤梅遭受婆婆的百般刁难而无人倾诉,为了保住王家少奶奶的地方,凤梅不得不求助于家中的男仆丁安,演绎一出借腹生子的桥段,凤梅为此不惜牺牲女儿的婚姻来掩盖这桩丑闻。华人女性成为加拿大对华政策和中国封建父权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
(二)第二代华人移民认同上的困境
这里的第二代华人移民是指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华人。第二代华人移民虽然出生在加拿大,但仍然无法获得加拿大主流社会的认可,处于“两域对立场景”(The Scene of Dual Territoriality),“指离散角色在母国与客国之间的抉择,在价值观上、生存空间上处于两国夹缝之中”。处于中国母国与加拿大客国的夹缝之中,既不被老一辈华人认为是真正的中国人,也不为白人主流社会所接纳。
第二代华人移民因出生加拿大,以接受西方教育为主,更倾向于认同加拿大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加之上一代华人移民刻意隐瞒过去及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假移民身份证件等等,造成第二代华人移民对中国母国并无实际的经验。《玉牡丹》中的三名加拿大本土出本的儿童叙述者皆有此迷惑,他们渴望成为加拿大人,却又面对不为白人社会接受、身为中国人的事实。女孩梁反驳婆婆“女孩没用”的封建观念,幻想能成为“秀兰•邓”那样的明星,告知婆婆“这是加拿大呀”,婆婆却提醒她,“梁,你不是加拿大人,你是中国人。”。三弟思龙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出生温哥华,每天给联合王国国旗敬礼,即便他的手是全加拿大自治领最干净的,而且一直在祈祷”,他还是中国人。因为思龙不能正确地称呼那些在金山的干公们,而被人们认为是“无脑”,是“没脑的孩子们,头脑里没有中国历史的孩子们。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加拿大人,生来就不懂得国界,生来就没头脑。”[这些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华人小孩,因为西化教育而忘却了中华文化,这令唐人街成年人担心不已。
《残月楼》中,加拿大本土出生的第二代华人移民同样遭遇加拿大主流社会的排斥,他们的才能和勤奋遭到否认;“老一代华侨为了抬高自己只值两分钱的身价,总是耻笑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不三不四不靠谱。”小说中,面对家族内部矛盾和白人主流社会的排斥,第二代华人移民对唐人街的态度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毕翠丝,基曼等为代表,外界的排斥加深了他们对温哥华唐人街的忠诚,这群唐人街土生土长的小伙伴因为生存的需要而结成死党,相互关照相互保护,他们不愿离开唐人街,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性而努力。另一类是以苏珊为代表的叛逆者,极力想要逃离不温暖的家庭、逃离唐人街,“跟一帮好赖不分的有钱人家子弟鬼混”,“做着叛逆的罗曼蒂克的梦。”。叛逆的苏珊碰上了叛逆的莫根,一切注定成为无法收拾的悲剧。
与上述两本小说相比,《妾的儿女》中,阿杏的遭遇更为不幸。上述土生土长的华人小孩至少还有一位疼爱她们的母亲,阿杏的母亲则是典型的重男轻女。阿杏的母亲一直渴望能有个儿子能够养老,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阿杏不仅得不到母亲梅英的指导,还天天被母亲抽打。贫穷悲惨的生活,母亲赌博、抽烟、喝酒,频繁地往返当铺间,这些令阿杏绝望和恐惧,但是阿杏并未因为向生活低头。学习成为阿杏逃离生活、逃离唐人街的唯一出路,她努力学习,用奖状和证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好成绩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也是改变生活的唯一办法。”然而,现实却更加残酷,对于华人阿杏,优秀的成绩并不能保证未来有份好的工作。阿杏试图逃离唐人街的失败也体现在她的婚姻上,在婚姻伴侣的选择上,华人移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童年的悲惨遭遇,阿杏一直处于创伤的阴影中,尽管如此,阿杏还是无法彻底地与母亲决裂,对于母亲,阿杏既恨又爱,无法寻求一完美的解决方法。阿杏与母亲梅英的关系反映了阿杏移民二代与中国既矛盾又无法隔离的关系。
(三)创伤的解决
20世纪50年代左右出生的第三代华人移民,也就是《妾的儿女》和《残月楼》中的叙述者,她们基本上完全融入了加拿大社会,她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一份不错的职业,嫁给了白人丈夫。面对家族的移民史,她们都采取了较广的书写视域,把华人的移民史、家族移民史置于中国与加拿大的历史大背景下,有助于读者对华人移民史有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这两部作品中,尽管早期华人移民的血泪史、家族的冲突与创伤在移民后代的身上得以改变,华人移民基本上完全融入了加拿大主流社会,但是两部作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融合。学者刘纪雯指出,“《妾的儿女》属传统的融合,而《残月楼》则为功能式融合,因为前者虽肯定自己的族裔背景,却对主流抗拒较少;而后者在加入主流的同时,颠覆主流的神话、形式、典律,企图改变主流之态度和文化。”《妾的儿女》中,叙述者的母亲阿杏的创伤最后似乎得以修复,但这是在中西对比之后,阿杏悟出的。阿杏原本以为自己是最可怜的、最孤单的,可是在对比自己在温哥华的遭遇与姐弟在母国的遭遇,阿杏得出自己能生活在加拿大,要比中国的亲人幸运多了。叙述者并没有谴责主流社会对华人移民所造成的创伤,表达的是一种进步的移民叙述模式,即加拿大的华人移民本着勤奋和努力,一代比一代幸福,直至最后的圆满结局。《残月楼》的叙述者凯对加拿大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异性恋作出了挑战,与身边的女性结成联盟,“我必须赋予这篇故事以一定的目的性”[4]332。小说结尾,凯放弃温哥华的高薪职位,离开感情不和的白人丈夫,选择前往香港,投奔同性恋女友贺米亚。凯的离开,不仅挑战了西方作为华人移民的理想国度的神话,而且打破了唐人街的封闭的空间。《残月楼》还开放了多重的可能性,打破了种族、阶层和血缘的界限,如钜昌与原住民的爱情,凤梅与仆人丁安的结合,摩根的不合法的血缘。血缘的纯洁性是加拿大白人和早期华人所竭力维护的,钜昌与原住民凯萝拉的跨种族结合打破了华人移民血缘的纯洁性,丁安成为王家不合法的儿子。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华裔移民离散网络
在多元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华裔加拿大作家们在创作中逐渐淡化族裔背景,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华裔作家本身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如新生代华裔英文作家黎喜年(Larrisa Lai)1967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成长于加拿大的纽芬兰。邓敏灵(Madeleine Thien)来自马来西亚华裔家庭,成长于温哥华。新生代华裔英文作家多元化的背景使得华加文学的书写超越华加两国的界限,华加文学呈现的空间不再局限于温哥华(加拿大)与中国,而是两国之间的多重往返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连接。华加文学的写作议题超越西方和东方、母国与客国二元对立的书写范式。下面将以黎喜年《千年狐》和邓敏灵的《确然书》为例说明华裔温哥华小说议题的传承和转向。
(一)《千年狐》跨越时空的女性结盟
学者傅友祥(Bennett Yu-Hsiang Fu)指出,“《千年狐》复活中西方历史,以建构一女性空间,处理离散、历史、性别、华加连字符等议题。”《千年狐》共有三个不同的叙述者,第一人称的狐狸,9世纪的中国女诗人鱼玄机,21世纪的加拿大温哥华少女阿尔忒弥斯,通过狐狸千年跨时空的形态变异,借由非线性,碎片,不完整性的故事、模棱两可的结尾,不断地穿越过去和现在,把9世纪的中国,21世纪的加拿大联结。通过狐狸跨时空的移动,文本既挑战主流社会,又怀疑母国的官方论述。狐狸、鱼玄机、阿尔忒弥斯皆属于边缘弱势群体。狐狸在中国的聊斋等故事中,是一群专门迷惑并祸害男子的狐狸,不可记入官方的正史。文本中的这只千年狐并不谋害男子,她喜欢女性,并帮助那些被社会或丈夫欺负的女性。鱼玄机因为其女性身份,在官方历史的记载上只有寥寥数笔,因打死婢女而被处死。狐狸为鱼玄机的死因寻找资料,但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阿尔忒弥斯是西方主流社会里的一有色人种,虽处处遭受冷落。这看似无关联的三位叙述者,因狐狸跨越时空的移动而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中西结盟的网络。
21世纪的温哥华是多族裔混杂的现代都市,不断飙升的房价,致使文本中的角色不断变换住所,如阁楼、地下室等。看似和谐的都市仍潜藏诸多危险,文本结尾处五名亚裔女性死者是这多元化都市冲突的必然结果。通过书写华人女性之间既冲突有结盟的友情和爱情,呈现了一多元西方华人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这些西方华人女性不再执着认同种族和族裔性,更关注当下的友情、爱情的联结。阿尔忒弥斯是一位被白人夫妇领养的华裔少女,她对自己的过去、亲生父母一无所知,也不想去了解。当黛安娜询问阿尔忒弥斯是否有想过亲生父母,阿尔忒弥斯回答,“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我知道我的父母是,我的朋友们是谁。”阿尔忒弥斯对亲生父母留下的小被子,对中国烹饪不感兴趣,但是因为黛安娜曾经使用过这被子,她突然觉得意识到这被子的价值和重要性,可见阿尔忒弥斯对当下友情和同性恋爱情的珍视。阿尔忒弥斯讨厌中国的烹饪,拒绝中国菜肴,但是为了吸引黛安娜的注意,阿尔忒弥斯乐意为她做中餐。明与阿尔忒弥斯拒绝过承认去相反,明处处彰显自己的有色人种身份以挑战白人主流社会,她不再使用之前的名字默茜•李,改为中文名字“明”,蕴含光明的意义。明的胳膊上文有龙、凤凰及阴阳等图案。黛安娜是这群华裔女性中较为复杂的角色,黛安娜叛逆,她骗取白人的信用卡。她和每位女性保持一定但并不固定的关系,且每位女性为她着迷。这些华人女性既相互帮助又有冲突。黛安娜因为古董外袍与阿尔忒弥斯发生矛盾,明认为阿尔忒弥斯对她不够关心而疏离阿尔忒弥斯作品的结尾处,因明的意外死亡,这群有冲突的华人女性角色又相聚在一起,暗示了华人女性群体结盟的可能。
(二)《确然书》的全球离散网络
相对于《千年狐》的跨越古今、跨越加拿大与中国的书写,《确然书》建构了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全球离散网络,呈现了全球化背景下,都市之间、都市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而都市中的移民角色成为连接都市的主要力量。《确然书》书写了父亲马修和女儿盖儿两代离散角色或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因为突发的疾病造成的死亡而备受创伤。以温哥华都市为中心,离散群体拓展可活动和交流沟通的空间,建立一种跨越亚洲、欧洲、澳洲和美洲全球离散网络。
第一代离散角色马修因二战造成的创伤而移民温哥华。马修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山打根,马修美好的童年和幸福美满的家庭,因日本的殖民统治而变得千疮百孔。马修的父亲因为替日本人服务而被村民所指责、唾弃。日本占领军撤退前,枪毙了马修的父亲,这一切被躲在灌木丛的马修亲眼看见。战争结束后,人们对马修和母亲视而不见,马修和母亲被迫离开家乡。直到十八岁,入大学前的假期,马修再次回到家乡,遇到了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安妮,并与之相爱。这期间,马修遭到一位乡民的指责,痛斥他父亲的罪状,并驱赶他离开。安妮意识到,他们两人如果待在山打根,必然没有好的未来。想不到更好地办法,安妮只能狠心撒谎拒绝马修的爱,并隐瞒了怀孕的事情。马修带着创伤再一次逃离山打根。后来,大学期间马修遇到了现在的妻子,盖儿的母亲克莱拉。为了逃避的创伤,马修与妻子移民加拿大,以为遥远的距离、新的环境能抚平他的创伤。然而,来到温哥华后,马修依然陷入以前的创伤而无法自拔。他无数次地梦到父亲,“在梦中,他试图告诉父亲,还有另外一条道路。”。面对昔日的创伤,妻子克莱拉的陪伴和都市行走成为化解创伤的良药。在盖儿小的时候,马修经常和盖儿一起行走,盖儿会记住所有的街道名称。“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父亲有个仪式。他每周日会把我们叫进汽车……他会连续不停地解说,自豪地向我和母亲指划某些事情,命名地标,希望我们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对于离散群体而言,都市不免对他们造成陌生感和距离,因此,缩短与城市的距离,客服陌生感是首要任务。透过行走于温哥华都市,马修和家人逐渐融入都市,命名地标的行为更进一步折射了马修对温哥华都市的认同,温哥华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三维空间,而是承载着情感、记忆与感受的载体”。
不同于马修的空间行走,第二代离散主角盖儿采取更为积极地方式,与都市进行对话。以盖儿、维德为代表的第二代离散角色更具有世界主义的关怀,关怀的对象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亲人。不仅如此,她俩艺术家性质的工作更具影响力与感召力,试图借由其艺术创作呈现当代全球化社会下断裂的历史、碎片,如,二战带给全球人民的创伤,人们面临的不可治愈的突发疾病。盖儿跨越不同的时空,联结两者所造成的创伤,主动建构都市人群渴望交流、被爱与爱的欲望。二代离散角色的离散路线更加多元化、多方向性,并非早期离散角传统的迁移路线:从殖民地移居到统治者的都市。透过彼此的爱,家人、朋友、邻居、陌生人跨越族群与空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个都市也因离散群体的越界与位移产生联结性,因年轻角色的加入、与都市进行对话而具有对话特性。
四、结语
华裔温哥华小说从书写早期华人移民的血泪史、非此非彼此的两难处境、家庭冲突到多元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离散空间,表明了离散不尽然是漂流移位的痛苦或创伤,也包含着跨越疆界的理想和视野;离散空间更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生产性与对话性的空间。在离散与流动的脉络中,离散角色可能重构身份认同,抗拒主流社会的压迫;也可能与都市联结,造就落地生根、融入都市的离散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