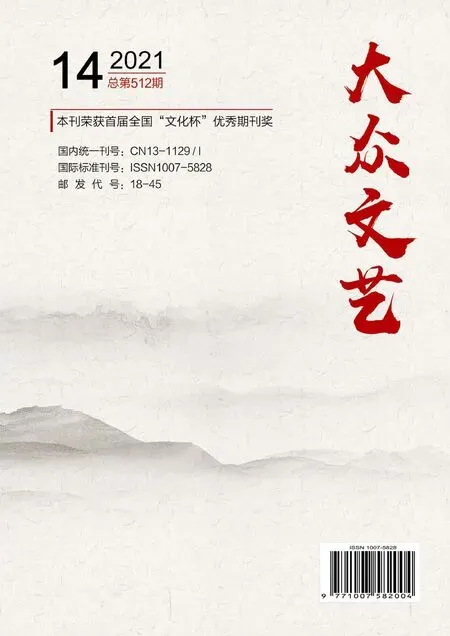李煜词中的女性形象与自我投射
李雅琪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00)
以李煜词风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亡国事件为转折,其前期多以宫廷场景为主,也有写男女之情,或者对于女性的描摹,风格多华美旖旎。后期词多抒发国破家亡的悲苦之情,悲愤凄清,字字带血,这一时期也是李煜词艺术的最高峰。本文依据《南唐二主词笺注》,对李煜前后期词中的女性形象与意象进行分析。
一、美人自喻的抒情言志传统
中国古代历来有以美人自喻的抒情言志传统,这种抒情言志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中,开创的“香草美人”的抒情传统。诗歌中的男女关系往往是君臣关系的符号象征,屈原也经常在诗歌中塑造一个孤洁的香草美人形象,以其为众女所妒而影射自身被群臣排挤的政治处境。诗词发展到唐代以来,诗歌中的女性书写已经遍布各种题材,女性形象成为男性书写中的符号化的意象,大量的闺怨诗、弃妇诗成了苦闷的象征,用以抒发在君臣关系中被冷遇的诗人的怀才不遇之情。其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是朱庆馀的《近试上张籍水部》,以女子自比,借“画眉深浅入时无”询问考官文章是否符合要求。
唐代的士大夫诗人以女子自喻,用以言自身的抱负、志向与心愿。如张籍以节妇自喻,表明自身对于唐王朝的忠心与贞洁;李白的《代赠远》《乌夜啼》也是借想象中女性的遭遇来抒发自身羁旅、怀才不遇之情。男性的文学中,女性成为男性意义认同的象征符号与自我表达的方式,女性是男性自我另一面的复制。
而词的发展晚于诗歌,词在隋唐起于音乐文学,随音乐而填词唱和,起源于市井,民间。在晚唐、五代时期逐渐发展,随着温庭筠、韦庄等人以及“花间派”的兴起,词进行了文人化书写的转向。至南唐李煜的时代,尤其是李煜的后期词作,已经完全不见艳情词的影子,转而是深沉悲怆的家国之思,对于人生遭际的伤感沉痛。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而李煜词中的“士大夫转变”,与李煜词中对女性的描摹到以女性自喻的书写转变有着紧密的关联。
二、李煜前期词对女性的书写
在对于女性的书写上,前期词受到花间词派的影响,此时的女性形象书写作为客观审美对象,多表现的是高贵风雅的宫廷审美情趣,也有反应女子的闺阁生活、相思别离的苦闷心情之作。
前期词中,宫廷诗、闺怨诗并未摆脱花间派对于女性的服饰、住所进行描写的传统。宫廷妇女身着的绫罗绸缎、所住的闺房深宫,都是词中着重描写的对象。而爱情诗中,作者擅长捕捉女子慵懒闲散的宫廷生活,男女幽会时的片段场景,注重书写实景,对于词中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则较为片面。
李煜前期词中的女性形象多以少女、少妇为主,这与他长期的宫廷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南唐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作为帝王的李煜生活奢华安逸,对于雍容华贵的宫廷生活和醉生梦死的歌舞宴饮见怪不怪,所以目之所及都是青春活力、面容姣好的青年女性。此时的李煜词风并未完全摆脱花间词派以来的艳情传统,词作者在语境中是置身事外的,换言之,读者并不能直接从词中窥见词作者明显的个人情感倾向。
三、李煜后期词中的女性自喻
李煜的后期词中,国破家亡的深悲剧痛成了他的词中永恒的主题。其风格多哀婉凄凉、深沉悲戚,内容上,多为书写梦中南国的旖旎奢靡与现实中绝望生活的鲜明对比。梦中的世界轻盈而高贵自由,现实却是残酷的血泪。两相对比下,词的语言艺术带有天然的张力,蕴含着一种悲剧的美感,同时也代表了李煜词的最高成就。而在后期词中,女性的书写也不再如同前期倾向对于年轻女性的书写,此时后主笔下的女性形象多为年老、哭泣、无能为力的形象。通过后期词中对于女性形象的书写,可以看出李煜对于故国的追思与怀念,对于物是人非的感慨。
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书写对象并非以女性为主,而是以女性作为词中的一个意象,来抒发自身的悲怆、亡国之叹。在作者所熟悉的宫廷事物中,明月依旧、雕栏玉砌、四季的流转都是照常进行的,而作为与他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却变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两句委婉地表达了李煜作为亡国之君对于故国的留恋,而“改”字则将宫娥妃嫔给予他的最后一丝告慰全部粉碎,也将残酷的现实全部托出。昔日的繁华和和平已经如同现在眼前的“朱颜”的青春一般完全停留在了过去,留给亡国之君的只有无尽的追忆。
这里的“朱颜”没有神态动作,没有内在的情感,也没有具体的指向,是完全被符号化的形象。符号存在的目的就是突出时空上的跨越,就是“犹在”与“改”的对比,是永远回不去的故国与成为阶下囚事实的强烈反差。字面意义上的“朱颜”是能指,但是此时词作已经摆脱了能指的表层意义,而背后的所指是跨越时空的家国愁思,就是最后这首词的落脚点,最后一句的“愁”字。词作摆脱了对于能指的描摹而转向抽象的情感,时空跨越所产生的陌生化,由此词的意境转向了更加辽远的空间。
再如《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中的“胭脂泪”,这首词当作于南唐灭亡之后,李煜作为两年之久的阶下囚的时期(975年)。“胭脂泪”同样也是符号化的书写,胭脂泪的主体不明,确有其人还是来自李煜本人的想象世界,读者也不得而知。“胭脂泪”,虽然写女性之泪,但是整首词并未出现对于女性的书写,反而更像是以“胭脂泪”来代言自身的“亡国之泪”。可以看出女性书写在这首词中是十分模糊的,只有一个“泪”字概括了女性的情绪和简单的动作。此时的女性书写,已经从前期词中的客观的他者的形象,逐渐转变成了作者的代言,情感的传声筒,女性不再是书写对象而是抒情主人公的自喻。
比起前期词中有着明确情态、服饰、情感、动作的女性形象,后期词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明晰,往往只有一个模糊的名称。此时女性的形象成了李煜书写自身心境的承载物,在悲戚愁苦的境地之中,李煜的词从华美旖旎逐渐实现了对人生遭际的伤感、故国的悼念。在情感上,亡国之君的悲愤无奈同士大夫怀才不遇、焦虑仕途的心境是相似的,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性在文本表现形式上也逐渐趋同。李煜词中的女性不再作为主角,而是成了处境悲凉的抒情主体的自喻,承载着自身的情感与寄托,往往是借女性书写表达自身的愁苦与亡国痛恨。王国维对李煜有评:“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中,词风更加偏向了对于个人命运的书写与痛失家国的悲情的流露,而这种血泪的控诉随着教坊“别离歌”的奏响,在最后一句“垂泪对宫娥”得到了集中的展现与爆发。宫娥作为词作者,就是李煜在词中情感流露直接承接的对象。李煜的后期词作中,对于女性的书写从写作的主体转变为了承载一定情感的意象,然而在另一种角度上,女性意象的出现作为作者在作品中传递重要情感的关键词。对于女性的书写不需要强调这位女性的容貌、服饰、性格与身份,而是把握了女性本身的一种特质:敏感的神经、易老的容颜,以及在女性群体中更为常见的特质。
李煜词从前期词到后期词词风的转变,首先是抒情主体的变化,前期以女性主人公或者咏物、悲春伤秋的缘情为主,而后期的抒情主体多为自身,抒发自我的离愁别恨、孤苦难挨的生命体验。其次,抒情主体的转变,导致女性书写从主体的位置走向众多集中表达较为固定情感的意象之一,对女性的客观书写转化成了自身言志抒情的表达,也是以亡国为节点,从“伶工之词”转变为“士大夫之词”,扩大了词的意境,将自身的个人生命体验转化成了能够获得广泛情感认同的能够引起共鸣的广泛体会。而在这种书写的转变当中,女性意象所承载的情感与经验,正是后主本人的生命体验,通过女性更为感性、容易伤感的情感特征,这种国破家亡、物是人为,以及旧梦幻灭与现实交错的折磨所带来的复杂细腻的情感得到了更好地传递。
同时,作为生长于宫廷,长期从宫廷生活汲取素材的词作者李煜而言,女性的意象是在词的创作中经常出现,并作为稳定的审美对象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持续出现的。而在命运转折的亡国之际,宫中女性作为这种悲剧转折的亲历者,不但能与作者感同身受,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词作者一定的慰藉。同时女性也是词作者南国旧梦,象征着他过去高贵自由、浪漫旖旎的创作与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远离了南国宫殿、江南水土的囚禁生活中,充当着能够给予他最直观的缅怀过去,回顾旧梦的关键词。但是越是温柔的梦与现实的残酷、血泪碰撞在一起,带给人情感上的落差就越能促使悲情的产生。女性意象作为触发这种悲情产生的直接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种情绪的酝酿与转化,也就成了词作者自觉将女性作为酝酿自身情感、承担一部分抒情作用,投射自我情感的意象。这也就完成了李煜词前期从客观审美对女性的书写道后期词女性作为意象承接自身情感投射的转变,完成了词意境更上一层的羽化。
四、结语
李煜被称为千古词帝,其词作中的女性书写,由于李煜的跌宕而悲情的人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前期他的生活浪漫高雅,其词作题材主要为女子情爱和宫廷之乐,女性的形象多柔美温婉,流露出轻柔典雅的美感;后期他被俘入宋,主要抒发亡国之悲和慨叹人生虚无,女性的形象大多苍老、凄怆、模糊,女性书写从单纯的客观书写转向了作者情感的自我投射,女性形象逐渐成为词作者本人情感传达的符号。由此,李煜词风的转变,可以看作是词作为一种当时新兴的文体,朝着士大夫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