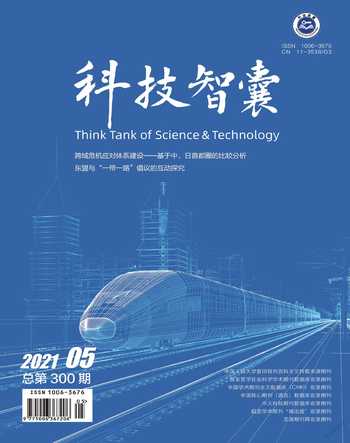人工智能环境下传播格局的重构
李丹 裴硕
摘 要:随着VR/AR、5G等技术的逐渐普及,各类终端媒介走向深度融合,万物互联、人机共存成为未来发展趋势,整个社会呈现出智能化倾向。文章在媒介环境学视域下,分别从感知环境与符号环境两个层面来理解人工智能,探究当前人与技术的共存关系、媒介与社会文化的共生关系、媒介与思想意识的共长关系。在这一新的媒介环境下,原有的传播格局被逐渐消解,新的传播格局正在形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引发传播形态的交互,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为复杂;二是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导致了传播内容的转变;三是这一新格局倒逼媒介管理者对自身角色做出改变,并完善传媒管理体系。
关键词:人工智能;传播格局;媒介环境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1.05.08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Pattern und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Li Dan1 Pei Shuo2
(1.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100024;2.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imary Education,Beijing,100048)
Abstract:With the gradual popularization of VR/AR,5G,and other technologies,various terminal media are gradually being deeply integrated,the interconnection of all things and human-machine coexistence have becom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the whole society presents an intelligent tend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this article understan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wo levels of the perceptual environment and symbolic environment respectively explores the current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y,the symbiosis between media and social culture,and the co-growth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ideology. In this new media environment,the origi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has been dissolved,and a new communication pattern has taken shape or is taking shape,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diversif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leads to the interaction of communication forms,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is more complex. Second,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 lead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Finally,this new pattern forces media managers to change their roles and improve the media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mmunication pattern;The media environment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随着5G、人工智能、VR/AR等媒体融合技术的发展,社会开启了智能化媒体的新时代。智能化媒体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1],其中尤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原有的以大众传播为主导的传播格局受到挑战,新的传播格局正在形成。
一、人工智能的媒介环境学分析
将媒介当作环境来研究是媒介环境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环境”包含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及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媒介环境学强调,人是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其研究重点是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2]1968年,波斯曼在公开介绍这一学科范式时指出,媒介是复杂的讯息系统,而媒介环境学则试图去揭示其隐含的、固有的结构,以及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麦克卢汉也指出,当社会的主导媒介发生变化时,其对应的符号系统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且这一变化又会致使人的感官发生变化。因此,将人工智能这一新时代媒介当作一种环境来研究,意味着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来理解它。
(一)作为感知环境的人工智能
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每一种媒介都对应着一套感官特征。例如,以阅读为主的印刷媒介是对视觉的延伸,需要用耳朵收听的廣播媒介是对听觉的延伸,看电视则是视觉与听觉延伸的结合。这种透过媒介过滤的感知环境即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在感官形貌发生变化的环境中,人们接收感觉资料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进而迫使人们重新理解和建构周围的世界。人工智能带领人类进入一个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感知环境,它延伸与扩展的不仅是某一感官或某几个感官的组合,而是人的智识。通过对人的意识及思维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与人共生共存,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接收感觉资料时,人们不会因一种感官的加强而导致其他感官的削弱,人们整体的感知系统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一种全身心地浸入式体验和参与。在这一仿真环境下,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交互,且二者的边界趋于模糊,这使得人们在理解世界时更易将虚拟世界当成需要付诸行动的真实世界,随之改变的是人类的行为习惯与思维模式。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人类的大脑首先获得了解放。在人与机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人类得以更为深入地了解自己。例如,人们可以运用自己最为熟悉的语言进行人机交互,而无须学习复杂的编程系统,因而可以更加自如地生存,同时,机器也可以识别和理解人类的情感,使其在需要表达或发泄情绪时获得“同伴”。人工智能环境下人与机器共同创设的人机共生共存,是对人的感官功能的解放,这也倒逼人类更谨慎地判断人与技术的关系。
(二)作为符号环境的人工智能
从符号层面来看,我们将人工智能设想为一种符号环境,且是由一套独特的代码及语法有序组成的符号环境。例如,为了能顺畅地阅读,我们需要掌握书面语的词汇与相关语法;为了能流利地看电影,我们需要对其构成元素有一定的了解。而在智媒时代,为了能够和谐地与机器共处,我们需要学习相关的数字代码,以了解其运作机制。当我们与媒介相互作用时,我们也融入媒介所构建的环境中,因这一环境正是媒介本身,这一点在人工智能的运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我们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真切地感知周围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又从其显示的智能化符号世界内部来思考和表征物质世界,而这一世界也成为我们所认为或了解的世界。因此,在万物皆媒的环境下,世界“感知起来”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终端,且我们就身处其中。具体来说,智能媒体所携带的符号结构,给我们的认知、意识及心灵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描写经验的方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固定的、无法修改的,而是可不断修改甚至扩充的。此外,更加依赖技术和系统的研判和决策,也会导致人类的认知能力与主动思考能力的下降,这警示我们在通过人工智能界定或建构描写经验的方式时,要对其符号结构持审慎的态度,不应忘记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
感知环境与符号环境是人工智能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两个方面,人们在交流与获取信息时,并不会有意识地区分这两个方面。但感知与符号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且人工智能这一全媒化的终端技术在这两方面都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深远的转变,所以笔者将人工智能分别当作两种环境来论述,以便我们能更为细致、全面地了解人工智能。此外,除从上述两个层面对人工智能进行理解外,还可以从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层面来对其进行研究,不同的媒介形式提供不同的传播结构,并影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由此,在微观环境与宏观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旧的传播格局被消解,新格局得以重构。
二、人工智能环境下传播格局的重构
人工智能环境下传播格局的重构体现在各传播要素的改变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以下将从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出发,通过探讨人与媒介之间关系的转变理解传播格局在新媒介环境下的重构。
(一)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引发传播形态的融合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更为智能、融合的数字化终端技术被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当前各类社交媒体的泛滥,使得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大众传播时代的传媒机构及其把关者,低门槛、自组织、去中心化、无管理主体的技术特性使更多以往边缘的、沉默的群体成为传播主体。尤其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及各类网络直播技术的平民化、大众化,使得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制作者、传播者。有人将传播主体划分为 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和OGC(Occupationally-Generated Content,职业生产内容)三类,也即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自媒体、营销组织、兴趣小组、个人等各种主体共同杂糅地参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活动,共同构成社会传播主体。[3]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构成了传播格局演变的根本诱因,由此导致了各类传播形态的博弈与相互融合。在互联网传播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及人际传播都被纳入其中,这消解了此前大众传播“一家独大”的局面,各类传播方式此消彼长间也在重构着传播的格局。例如,傳统媒体在发布新闻报道时更倾向于使用网络流行热词,即大众传播与群体传播在博弈的同时也在合作,以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各平台企业当前的直播带货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这是组织传播在借群体传播迅速、自发的聚合行为来获得更高的盈利;谣言传播的速度极快,公众舆论往往会迅速发酵等都是人际传播与其他3种传播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
技术赋权于民带来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并由此导致了4种传播形态之间的竞合,在这一集聚、交融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复杂。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人际关系逐渐淡化,以趣缘或业缘等为主要纽带的弱关系、浅关系、隐关系等逐渐增强。这些关系对个体的认知、态度及行为产生影响,反过来又加速了旧有的传播格局的消解,促进新格局的形成。
(二)信息系统的进一步融合导致传播内容的转变
在一个信息系统中,各类媒介因共同存在于其相互连接的网络中而形成所谓的媒介矩阵。对外,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对内,它们之间高度相关、联系密切。梅罗维茨在论述场景与行为的关系中认为,电子媒介所营造的开放场景,融合了印刷媒介时期互相隔离的信息系统,由此改变了社会信息获取的模式,并重塑了社会行为。在智媒时代,人工智能等智能化媒介的加入,拓展了这种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场景化、个性化。如果说电视、收音机、广播等电子媒介是对印刷媒介时期因物理场景的分隔而导致信息系统分隔的一种跨地域、跨场景融合,那么,物联网、VR/AR、人工智能等智能化媒介营造的则是一种跨思维、跨意识的融合,较之早期的融合更为深入。此外,早期信息系统的融合使场景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这种去场景化后新的媒介环境则又成为场景本身。因此,场景化和个性化成为人工智能环境的主要特征。
新媒介带来的信息系统结构变化,不仅直接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复杂,也对媒介传播的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原有各种不同类型内容的同化
将相对类似的材料暴露给所有群体是所有电子媒介的共同倾向,而社交媒体的泛连接性又易于将各种类型的信息在人们中间快速传递,这导致了媒介所设置的内容遵从一种既混合又富个性化的结构设置。由于群体间差异越来越小,所以做完全不同的主题节目不再具有意义。与此同时,个体的主体性越来越强,更多的类型群体逐步在这种融合性信息系统的包围下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小社群,形成新的区隔,并由此形成了以用户流量和用户黏性为主要目标的两种节目风格,而二者兼顾成为媒介主要的努力方向。
2.新的角色行为被描述为传播内容
信息系统的融合模糊了场景的前区与后区、公开与私下的界限,迫使角色调整其行为习惯,连接的广度、传播速度的即刻性,使得这种变化被呈现出来。例如,公务人员在公共场合的发言、公众人物在表演时的细节等都成为话题,在人际交互中被传播、解读。
3.旧有媒介以智能化媒介作为标准来决定“恰当的”内容
当前,人工智能等智能化媒介作为主要趋势的一个标志是,传统的大众化媒介常常与其所提供的信息种类与形式形成竞争关系。传统的印刷与大众电子媒介的使用在潮流趋势中维持或创造“个性”。例如,网络语言在书面语及视频化媒介中的应用,体现出旧媒介在描述事件时模拟人们可能在社交媒介等其他智能化媒介中所体验到的方式。这些媒介讯息的变化共同展现了信息系统结构与其内容之间的一种环形关系,信息系统的变化必定带来传播内容的变化。
(三)传播格局重构倒逼媒介管理者转变角色,完善传媒管理体系
任何改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及其社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新的传播格局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信息系统的深度整合,权威与普通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原有的神秘光环消失,信息发布者成为与民众一样的普通人,相应的“信任”问题便随之而来。此外,泛滥的信息引发了诸如商业平台的无序竞争、谣言的大范围传播、个人隐私被侵犯等媒介乱象,甚至新一轮的民粹主义、群体狂欢、群体孤独、社会冲突等都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媒介跨越时空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现代性中结构和行动的二元对立,令制度的作用凸显出来。[4]因此,当公众因手握技术而接触到更多以往被隔绝的内容时,也就相应获得了要求政府对各种事件进行回应和反馈的权利,而相关制度的改进也成为问题破解中最受关注的一环。在公众诉求的倒逼下,管理者首先需要调整自身角色、转变个人思想,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在新的传播环境下,管理者应通过接触和学习各类新媒介技术,关注普通大众日常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经常与公众互动和交流,增加个人亲和力,改善自身形象。
转变个人形象关键的一步是根据对当前环境的全方位认知,做出科学决策,以稳定人心。例如,当前人们对智能化技术是否会取代人的主导地位多有困惑和疑虑,相关技术部门应积极开展技术知识普及,祛除强加于技术之上的“魔力”,使之更好地与人类相处。
加强媒介管理法治化体系的建设,针对不同的传播主体,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在尊重、保护一般自媒体用户表达自由的同时,规范其言论自由;对以内容提供为主的自媒体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实时监管,并根据其所提供内容的不同形态,出台更为精准的网络著作权法,对原创内容及著作权进行保护;使作为内容和服务提供者的自媒体运营商,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打击各商家之间的恶性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针对当前网络环境中充斥的负面情绪,建立心理疏导机制,帮助网民进行情绪管理。例如,设立专业化、权威性的心理咨询机构,正确全面地认识情绪,有效合理地疏导情绪,尊重不同意见,减少社会的负能量,以降低社会风险,减少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促进理性的回归。
三、余论与反思
当前,智能化的发展及应用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捷和益处,其中最为突出的人工智能更是通過对人脑的模拟改变了人类经验世界的结构。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人工智能以及更多的智能化媒介技术还不能算是一项完善的技术,它们仍处于发展阶段,因而对其的认识与研究也有诸多局限。但无论如何,“一机一世界,一端一如来”已经构成了当前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并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共同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随着信息系统的进一步整合,从传播主体到传播内容,从人际交往到社会关系,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更多的传播主体从边缘走向中心、由“沉默的共同体”到“众声喧哗”,人与人的关系随之也变得更为复杂。传播模式的转变也导致了传播内容的改变与创新,更多适应新信息系统的内容应运而生,并与之共同构建了新的传播形态。新的传播格局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进而凸显了管理者及制度的作用,应积极针对不同类型的传播主体,制定相应的媒介管理政策,完善传媒管理体系。
一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伦理问题的探讨,在人工智能等智能化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在享受其便捷的同时仍需对其进行理性的反思。诸多学者都怀着人文主义式的关怀对此进行过探讨,媒介环境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芒福德在技术的膨胀中看到了人们所受的非理性驱动,他认为由于受到资本和利润的驱使,技术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在将人推向异化边缘的同时也使人性时刻面临着丧失的危险。芒福德提倡理性地思考,在其呼吁振兴有机论的意识形态里,潜藏着这样一种伦理:生命优先,生命的驱动力优先,也就是生存、繁衍和乐趣的优先。[2]因此,在与技术共生共存的进程中,要正确、辩证地看待技术对人的作用,在享有其成就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其对人的控制和奴役。
参考文献:
[1] 彭兰.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J].国际新闻界,2016,38(11):6-24.
[2]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
[3] 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8(11):114-134,204-205.
[4] 毛湛文.理解媒介融合的元理论:视野与路径——评延森的《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一书[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7(01):2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