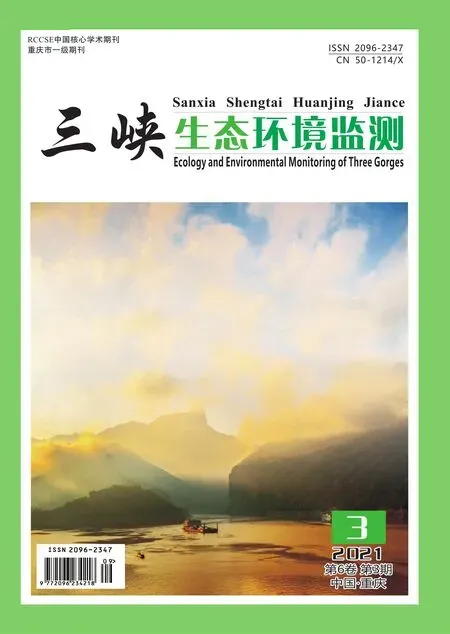三峡库区支流系统治理的问题和对策
任骁军,邹 曦
(1.水利部 三峡工程管理司,北京 100053;2.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武汉 430079)
三峡库区位于长江流域腹心地带,地跨湖北省西部和重庆市中东部,库区面积约5.8×105km2。全区地貌区划为板内隆升蚀余中低山地,地处我国第二阶梯的东缘,总体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山高谷深,岭谷相间。主要地貌类型有中山、低山、丘陵、台地、平坝。山地、丘陵分别占库区总面积的74.0%和21.7%,河谷平原占4.3%。库区内水系发达,江河纵横,三峡工程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1.0×106km2,占流域总面积的56%。库区除长江干流和嘉陵江、乌江外,区域内还有流域面积100 km2以上的支流152条,其中重庆121条,湖北31条。流域面积1 000 km2以上的支流有19条,其中重庆境内16条,湖北境内3条,主要有香溪河、大宁河、梅溪河、汤溪河、磨刀溪、小江(又名澎溪河)、龙河、龙溪河、御临河等,具有独特的地貌、环境、生态和水文条件。
自2010年10月试验性蓄水成功达到正常蓄水位175 m,三峡工程开始全面发挥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但由于历史、自然和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库区干支流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一是在入库污染负荷高的背景条件下,三峡工程蓄水运行使水流速度减缓,污染物滞留,局部水域富营养化加剧;二是在污染、捕捞和支流水电开发等影响的基础上,三峡工程蓄水运行导致水域生境和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生态系统结构不完善、功能下降;三是受水库水位大幅度(坝前高达30 m)、反季节涨落的影响,库周形成大面积消落区。
2011年6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三峡后续工作规划。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优化完善意见》,作为对规划的调整和补充,与规划一并实施。该规划将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列为三大任务之一,规划补助财政资金332亿元。规划实施围绕保护三峡水库水质、维护库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目标,通过加强“三带一区(库区水污染防治和库周生态安全保护带、城镇功能完善和城镇安全防护带、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和地质安全防护带、城镇移民小区)”建设,着力推进三峡库区库岸及消落区综合整治、水污染防治、造林绿化等工作,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一是库区污染治理能力和水平得到全面提高。生态屏障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二是库区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清漂机械化作业程度提高,基本实现辖区范围内漂浮物不出境,辖区水域“江清岸洁”的目标,库区干流水质总体保持在Ⅱ、Ⅲ类。三是生态屏障功能和消落区安全保障逐步增强。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森林覆盖率由29.5%提高到50%以上,城镇消落区及库岸安全保障增强,发生地质灾害的概率减小。四是库区新的“江湖”复合生态系统正在形成,生物多样性增加,鱼类资源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综上,通过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项目的实施,三峡库区重要生态屏障逐步筑牢,消落区生态功能和水环境质量整体得到改善,库区生态服务功能逐步显现。但是,规划实施以来,实施背景和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新的问题和难点凸显,也暴露一些薄弱环节。三峡库区20余条支流均发生过水华,部分支流河段存在水质超标问题,生态修复和环境系统治理措施少,三峡库区重要支流水体修复与水华控制项目实施进度缓慢,截至2020年底,仅开展13条支流水体修复和水华控制,支流富营养化问题尚未明显改善。需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布局,加强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分析三峡库区全部支流系统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布局,以重要支流为单元,以水系为脉络,以多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为导向,提出加强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促进水资源涵养、改善水环境质量、提升水生态功能的建议和措施。
1 研究区域
三峡库区有长江一级重要支流44条(其中湖北11条,重庆33条)(图1)。三峡工程蓄水运行后,支流回水区成为三峡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水区以上为水库重要影响区部分。因此,本文涉及的支流区域包含支流源头到入江口的全部支流范围。

图1 三峡库区主要支流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main tributari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2 三峡库区支流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
三峡工程采用一次建成、分期蓄水的建设方案,2003年6月三峡水库首次蓄水到135 m,2006年蓄水至156 m,2008年启动175 m试验性蓄水,2010年10月蓄水至175 m。自三峡水库蓄水特别是175 m试验性蓄水运行以来,多条支流富营养化程度加剧、发生水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2008—2017年库区38条主要支流77个断面处于富营养状态的比例为20%~37%,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图2)。从时空变化情况来看,回水区断面富营养化程度均高于非回水区,3—8月富营养化程度显著高于其他时段。2003年6月,三峡工程开始蓄水,同年9月巫山大宁河回水区首次发生水华,截至2018年,库区40条流域面积在90 km2以上的支流均发生过水华,2008年11条支流发生过水华,2012年发生水华的支流增加至22条,2017—2018年发生水华的支流维持在10条左右[1](图3)。

图2 2008—2017年三峡库区38条主要支流水体营养状况Fig.2 Water nutrition status of 38 main tributari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n 2008—2017

图3 2008—2018年三峡库区发生水华的支流数量Fig.3 The number of tributaries with bloom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n 2008—2018
依据各支流一河一策方案、支流生境调查项目成果、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监测系统成果、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水资源公报等,结合现场调研,我们发现库区支流在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和监管能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短板,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具体如下:
一是支流水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1)支流河岸植被覆盖率较低。库区支流河岸多为自然岸坡,局部河段岸坡建有防洪护岸,存在农业围垦种植等现象,但配套的岸线绿化工程与水土保持措施尚未开展,导致了河岸植被覆盖稀疏,存在水土流失隐患。
(2)支流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生境受损。20世纪80年代前,在三峡库区江段共有鱼类140~200种,其中分布有白鲟、中华鲟和胭脂鱼等珍稀特有鱼类40多种;三峡二期蓄水前后的2005—2006年,在库区共发现鱼类108种,其中白鲟、鳤、暗色东方鲀等鱼类在库区内已近绝迹,数量较多的胭脂鱼、岩原鲤、鳡、鳗鲡等鱼类的数量锐减;2010—2012年共在库区江段调查发现鱼类87种,相较2005—2006年的监测减少了21种,减少的种类包括鳗鲡、南方长须鳅、黄石爬、泉水鱼、胡子鲇、斑点叉尾、四川吻虎鱼等,多为适应急流、流水生境的种类[2]。受水库蓄水、河道渠化、大坝阻隔与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支流的珍稀保护物种栖息地破坏严重,珍稀保护鱼类与特有鱼类如白鲟、达氏鲟、铜鱼、胭脂鱼、岩原鲤、长薄鳅等资源量呈减少趋势;支流水坝建设不仅影响了鱼类洄游,造成洄游性鱼类和喜流水生活的鱼类资源下降,形成的静水环境和缓流态对部分鱼类栖息地产生较大影响,产漂流性卵鱼类产卵场消失或萎缩。
(3)支流水生态系统结构不完善,水华频发。三峡水库蓄水前,各支流均为典型的河流流态,2000—2002年13条支流总氮(total nitrogen,TN)浓度为0.35~9.34 mg/L,总磷(total phosphorus,TP)浓度为0.01~2.44 mg/L,高锰酸钾指数(CODMn)为0.81~23.39 mg/L,库区具备发生富营养化的条件。蓄水后库区部分支流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现象,受天气和水库水位调节的影响,库区支流发生“水华”现象,主要集中在3—6月[3-4]。一方面,三峡水库运行后,水位抬高、流速减缓、水文情势发生改变,水生生境结构简化、均质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发生演替;另一方面,蓄水后水体滞留时间较长,水体自净能力降低,加之流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入库污染负荷居高不下,水体污染物滞留导致局部水域富营养化加剧。水体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不完整,导致局部水域水华发生频繁[5-6]。
二是支流入库污染负荷较高。
(1)库区支流流域点源污染问题仍较为普遍。部分乡镇、村落污水收集管网设施尚不完善,污染收集处理效率普遍较低,部分区县现有的污水厂处理工艺选择和规模设计不尽科学,出水水质不稳定,脱氮除磷效果不佳,难以实现长期稳定运行、达标排放。根据初步统计,三峡库区已完工并投入运行的乡镇污水处理厂(站)660座、污水管网3 000 km,设计处理规模4.8×105t/d,实际处理规模2.5×105t/d,平均运行负荷52%[7]。部分支流流域内排污口众多,流域排污总量限制措施有待提升。部分支流流域内除存在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外,还存在一定数量工业、企业经过简单处理或未处理的污废水排放口,该类排口将直接导致流域水体被污染,对水体水质影响较大。
(2)支流面源污染仍然是库区入库污染主要来源。根据文献报道,三峡库区面源污染占总入库负荷的60%~80%,农业面源所占比例很大,主要污染物指标为TP、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BOD)、TN、重铬酸盐指数(dichro⁃mate oxidizability,CODCr)等。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为主要污染负荷产出源头,泥沙、TN、TP负荷分别达到库区总量产出的91.34%、76.26%和83.69%[8]。库区种植业结构不合理,整体水平不高,生产方式仍然比较粗放,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农药化肥流失污染、作物秸秆污染、养殖污染、农村生活污染等面源污染防治效果不佳;支流区域内浅丘较多,坡耕地分布广,部分区域在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遇到强降雨,水流夹杂泥土急流直下进入河道,对支流水环境影响较大。
(3)部分支流内源污染严重,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部分支流河道淤积,大量含有有机物、氮、磷、重金属等污染物质的底泥沉积造成内源污染;库区蓄水运行后形成大面积的消落区,消落区污染物随地表径流或水库水位上涨进入水域,也成为支流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
三是支流水资源保障不足。
(1)库区支流纵向连通性不足,生态流量难以保障。库区大部分支流均建有拦水坝、调节坝与水电站,导致河段水体纵向连通性下降。这类水电设施不仅改变了支流自然水文过程,切割了生境,隔断河流廊道系统的空间连通性,还对河流廊道在时间尺度上的自然动态造成严重干扰。同时,由于水坝蓄水,造成下游河流水量减少、河道淤积等现象,部分支流生态水量保障不足,且未确定合理的河流生态流量,导致支流河道在枯水期的生态基流无法得以保障,影响了水生动植物的栖息与生存,破坏了河流的生态环境。
(2)支流水源地保护不够,部分水源地水质不达标。库区部分区县制订了重要水源地达标建设方案,划定了水源地保护区范围。但部分区县水源地保护措施不完备,存在水源地保护区水质不达标、水体发黑等问题。部分饮用水水源地未设置警示标牌或警示标牌的建设仍达不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33—2015)的要求,且存在警示标牌损坏现象。部分水库型水源地未严格实行水源封闭式管理,并发现河流型水源地存在居民未搬迁,人群、牲畜在水源地附近活动造成水源污染等现象。
四是支流监管能力有待提升。
库区重要支流河长制信息化建设整体相对落后,支流流域内水资源管理与水质监测信息化建设程度普遍不高,对河流水质污染状况未做到及时的监控,取排水监测、垃圾堆放及非法采砂等行为未处理。各部门工作信息不互通,管理、巡查、监督、举报信息不到位,公众参与难度大,难以实现“高效、精准、科学”的河道执法监管模式。缺乏利用各类智能设备对库区支流流域内环境指标的动态感知与智能识别,不能确保准确、及时掌握支流生态环境变化情况。
3 对策与措施建议
在新形势下,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重要支流为单元,与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一河一策”综合整治方案、《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规财〔2017〕88号)、《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发改农经〔2020〕837号)等相衔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布局,以水系为脉络,以多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为导向,考虑库区支流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把生态修复放在首位,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进库区绿色产业发展,加强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促进水资源涵养、改善水环境质量、提升水生态功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9]。
一是把支流生态修复放在首位。
(1)开展陆生生境保护。通过植被绿化、生态湿地、生态护岸等措施,构建支流沿岸“自然连通”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健康稳定生态系统[9]。
(2)开展消落区保护与修复。对支流大部分农村消落区和部分城镇消落区,采取保留保护管理措施,以保留自然状态的方式保护其结构与功能。通过适度开展消落区植被修复、湿地多样性保护等措施,逐步恢复消落区湿地生态功能。
(3)开展水生生境保护。对没有防护要求河段,减少人为干扰,维持河流和河岸自然形态;因势利导改造渠化河道,重塑健康自然的弯曲河岸线,营造自然深潭浅滩和泛洪漫滩,恢复支流自然生境。加强重要水生生物栖息地保护力度,进一步完善支流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完整性和特有性,促进珍稀、特有物种种群恢复和遗传多样性延续,对流量较大、水域生境类型较丰富、分布有多种珍稀特有鱼类的重点支流生境,进行鱼类栖息生境重点保护与修复,开展辅助鱼类自然增殖的生物群落结构完善和生境结构优化建设,维持自然种群数量。
(4)开展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根据不同区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对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采取必要的辅助措施,保障补充群体数量,促进种群恢复和遗传多样性延续[10]。
(5)开展支流水华防治。针对三峡库区支流、库湾生态脆弱和敏感的特点,推进实施支流湿地建设、生境恢复、生物群落结构完善等措施,积极防治水华。配套建设藻类清除应急处置与安全处置设施,清除敏感水域水华;加强重要支流水环境的预警管理,为水华的适时控制提供支撑。
二是加强支流环境综合整治。
(1)开展点源污染防治。引导库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市场化运营,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及时征收污水处理费,尽快形成以用户付费为基础、中央及省(市)财政适当补助、县(区)财政兜底的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引入三峡集团长江绿色发展投资基金,健全三峡库区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提高支流流域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处理效果;实施支流流域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工程,完善乡镇、农村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提高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负荷和运行效率;明确库区产业发展的负面清单,严禁三高(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型产业进入库区,同时也继续加强工业污染排放管控,严格管控工业污水处理达标排放[7]。
(2)开展面源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主要从源头减量、过程削减、终端净化、循环利用等方面推进落实。加强库区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宣传培训,引导农民改进施肥方式、精准施肥,结合高效节水灌溉,实施水肥一体化,积极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使用高效低毒环境友好型农药品种,从源头控制面源污染产生量。采用生态沟渠、人工湿地等人工基质生物生态消减技术,结合支流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形成保护水库水质的生态屏障功能。围绕库区优势特色产业,优化和改善农业种植结构,建设高效现代农业园,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降低面源污染负荷。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居民点综合治理,完善提升农村环境卫生。根据各县(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对畜禽养殖场进行严格监管;开展规模化养殖场粪便无害化处理,对农村分散养殖实行区域性集中管理,集中解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建立完善的畜禽养殖农牧结合污染防治体系,构建畜禽养殖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畜禽粪污消纳模式[11]。
(3)开展内源污染防治。积极开展清理“四乱(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专项整治行动,逐步退还河流水域生态空间,对河道内阻水的淤泥、砂石、垃圾等进行清除,疏通河道,恢复河道功能,提高行洪排涝能力,增强水体流动性,同时可降低底泥内源污染,减少底泥污染物向水体的释放,改善水质。对清漂处理设施不够完善的部分县(区)配备漂浮物收集、装卸、转运等设施,促进建立三峡水库清漂长效保障机制。
三是实施支流水资源保护。
(1)开展水源地保护。对重要支流的集镇和农村集中居民点,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农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开展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因地制宜建设水源地防护设施,完善水源地标识标牌、监控设施建设。开展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护工程,清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章设施,综合防治保护区周边及上游河道污染。
(2)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取用水量,加强节水设施的建造,提升农业灌溉效率,合理回收利用工业废水,节约水资源。
(3)保障河流生态流量。加强三峡水库重要支流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生态水位)保障目标的确定,提出重要支流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加强生态流量监测预警。将生态调度与河流生态保护目标有机结合,制订生态流量调度方案,优化水库的蓄泄过程,并对生态调度效果进行监测评估。实施河湖水系连通工程,提高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增强水体自净能力,修复水生态功能。
四是支持支流流域绿色产业发展。
(1)发展库区生态农业。围绕三峡库区的柑橘、榨菜、茶叶、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路径,发展符合自身实际、主导产品突出、经营规模适度、经济效益显著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设计适宜的生态农业模式,优化和改善农业种植结构,实施化肥、农药施用量零增长行动,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利用和替代利用,加大测土配方施肥推广力度,引导科学合理施肥施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区和有机食品认证示范区建设,加快发展循环农业,推行农业清洁生产,提高秸秆、废弃农膜、畜禽养殖粪便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科学调控,实行现代集约化经营管理[12]。
(2)发展库区生态旅游产业。与库区各区县文化、旅游等规划相结合,分析各支流沿岸景观特征及现状利用情况,评价沿岸资源优势、生态基底以及存在的问题,构建以体验、教育和认知为主的生态友好型旅游模式。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围绕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深度挖掘农业功能,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新型业态,充分利用农村自然生态、田园景观、民族民俗文化等,积极发展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烈的乡村生态旅游产业[13]。
五是开展智慧河湖建设。
(1)加强智慧河湖监管能力建设。建立资源集约化的支流大数据中心,构建一体化智慧河湖管理系统,实现“透彻感知、互联互通、科学决策、高效智能管理”的智慧河湖管理体系,提高支流智能化管理和调度决策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河湖监督管理与公众服务监督平台,实现支流管理的信息化与现代化,为流域河长、流域档案、巡查日志与投诉建议等管理提供可靠依据与技术支撑。建立综合性发布终端,提供多渠道、全方位、无死角的信息监督服务。
(2)开展支流智慧化监测。借助现代化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创新技术,并利用各类智能设备对库区支流流域内环境指标的动态感知与智能识别,构建水资源、水岸线、水污染、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等要素感知与天地一体化的支流监测网络,实现对涉水信息的动态监测和全面感知,提升支流实时监测水平与风险预警能力。
4 结语
三峡工程蓄水运行后,干流水质总体良好,但部分支流出现富营养化状况,库区支流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三峡库区最主要的水环境问题。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要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治水思路,围绕保护三峡水库水质、实现库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创新思路和方法,进一步推进三峡库区支流系统治理。支流系统治理需考虑库区支流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系统性着眼,坚持重点突破,着力解决库区支流治山治水治林治田治湖治草治沙的空间协同问题,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监管等方面开展综合治理,促进支流水资源涵养,改善水环境质量,提升水生态功能,为保障三峡重要淡水资源库的水环境质量和水生态健康状态,全面发挥三峡工程综合效益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