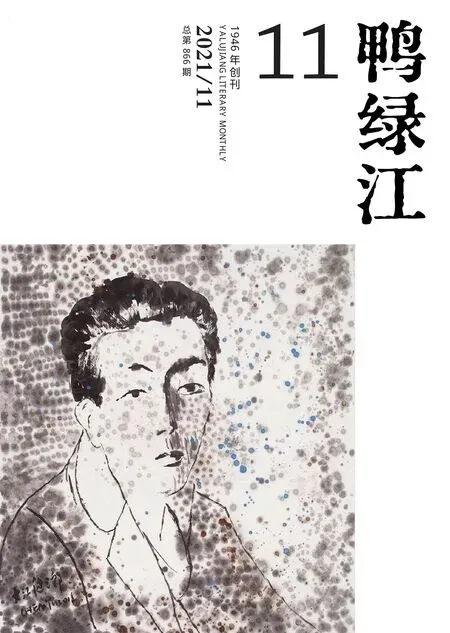溶液(短篇)
牛健哲
我开车带她来到弧城。弧城不远,因而我此前从没带她来过。以前我总是想,要带她出行就要走得足够远。
现在我们一起来了,我却像把她当了向导,问这问那。我们找到她上个月住过的旅馆,住进她那时睡过的房间。为了要这间房我在前台费了点口舌,但总算如愿了。从气象记录上看,一个月来这里的气温竟没什么变化,我相信街景和透射室内的光线也是。身上还有力气,出来原来不难。我含笑打量着一切,决意要把这次旅行的每一刻过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晚,明天一早自驾去郊游。明天已经是清新和亲密的了。
我让她舒展地躺在床上,我依傍在她身边。我要确保她身体放松。上次她初到时,一定是把自己扔在了床上,卸掉所有蛮劲、深深地呼吸后才流出眼泪。
“有时我真像个蠢货。”我用喉音替她再现上次所想。一个月前那天我刚刚从焦躁中抽出空来和她狠吵了一架,她便跑了出来。
她看着我点点头。她的嘴微笑,眼角却及时地渗出眼泪。
泪珠应该和一个月前一样圆滚,这想必是此行圆满的预兆。我要了点酒,我们喝起来。时隔这么久,她记不清上次酒的牌子了,这也说明这并不重要。如今翘了几次杯底后她一样喝醉了,昏睡过去。我抚摩了她的鼻翼和左腮。
次日早上,我给车加满油,把东西准备好,才换上车里那件休闲西装,回到房间门口敲门。她被吵醒,应该还不大舒服。
我问:“我看起来怎么样?”
她问:“这就开始了吗?”
我问:“早吗?”
她没回答,去梳洗。等她时我甚至有点心急。
她穿戴好后我牵着她下楼,回到车里,她可以闻到车里刚喷的古龙水味。
我开动了车,带她兜风,向城南行驶。弧城的路顺畅,路旁偶尔会有一两座古旧建筑或者石雕。这是一座小有名气的文艺之城。
它的确适合做某种回忆的背景。我的咀嚼肌鼓了鼓。
车行到那家美术学院门前,我转了进去,然后才想起补问一句:“进去转转好吧?”
让人在校园逗留总是很容易。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毕业作品展。我看似信步,其实担心这个展览上个月的有些展品如今不在了。还好,那个肚脐凸出的躯干雕塑还在,那螺壳里伸出的肥厚红唇也在。她经过它们时,我端起她的相机给她拍了照,并删除了上个月她在相同位置的留影。
一幅摄影作品里是重影层叠的人像。不同人的多张面孔叠加,远看是张模糊的脸,走近观看可见很多只眼睛很多张嘴,令人眩晕。作品题目是“溶”。我于是有点兴奋。来弧城前我对她说过,叠加即是消解。可现在我不能停步过久,她得像上次那样浏览下去,不该出离情境。
转过一组表现哭泣的摄像作品,我亲吻了她。这是一个被冷落的角落,附近故弄玄虚的作品被别处更加故弄玄虚的作品抢光风头。我使出了初吻或最后一吻的吸吮力。我想问她这力道像不像,但看她虚弱的样子我收住了傻话。
离开展馆,她告诉我可以从学校的另一个门出去。我有瞬间的恼火,把车提起了速度。
城南阳光充足,我的眼镜片变成深色。她头倚车窗闭上眼。顺着主路转弯后两侧尽是田野。我一度有点困倦,近来我睡得不多。我和她以不同的方式眯着眼。然而终于来到这一片树林旁时,我很快认出了它,停下车。很静,也很好闻。我们下车,迈过一些草石干碍,到林间深处漫步。高处的树叶极力拦住阳光,因而被照得通体明亮,脚下的草层暄软。水洼大概在林外一侧十几步远的坡下。
她走远一些,靠在树干上。树木其实比花更适合女人接近,不管它枝叶多青翠,都有一根粗糙的树干,女人靠上去会显得分外鲜嫩,至少是柔软。
我端详她靠着树扬起下颌的样子。
“在这儿他又亲你了吗?”她要继续走时,我不得不问。
“没有。”她边说边走开。她应该没有生气,我设计这次旅行时她湿腻着两眼,喉咙里拱动着大块的“对不起”。
追上她,我时而揽住她,时而任我们的肩膀和手臂频繁摩擦。我从她衣裳上摘掉几片叶子,又为她拨开拦路的树枝,这些显然是任何一个陪女人逛树林的男人都会做的。
我像猴子一样在林间呼吼时,她正处平静沉抑。我的第一声好像把她吓了一跳,然后我开始变换出几种声调。我推测一个精力过剩甚至有些亢奋的男人是会这样的,带着造作的清纯和模拟的爽朗。
惦念许久,我跑去采了一朵粉瓣白心的野花给她,上次她得到的花大概就是这种。我打开相机翻找照片,担心这花没有照片里的那朵醒目。上个月回去后,她冲印了持花的照片,镶进了相框里,我知道背面还写着“暂得一香”四个字。可现在在相机里找到原片后见得当时她手里的花幼小而色淡。我嗤笑着删去照片,还是握着她的手把我的花放在她鼻下,甚至杵到了她鼻孔里。我知道嗅觉对记忆的意义。
她的感官不会拒斥这情景。我拍下了她和我的花,又拍了几张树木间的她。
“该去钓鱼了。”我不想让这次漫步短于她上次的,更不想让这次比上次冗长乏味。
“你真的想那样?”她问。
“当然了,反正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好好陪你。”
我回到车处,拿出渔具、坐凳和食物。我坚持自己提拿所有的东西下坡,略有踉跄。她回头看了我一眼,似乎也瞥了瞥正在远离的树林。我又向她确认树林里是否发生过亲吻什么的,她又否认了。
鱼竿那套东西需要抽拉组接,并不很驯服。我背对着她鼓捣了一阵子。架竿时,我仔细问她上次垂钓的位置,微调几次,终于安置下来。相机取景委实与上次吻合,我甚至恍惚见到了上次他们的坐凳在水边泥地上留下的痕迹。坐下来的确舒服,阳光刚好晒不到,风把水味儿扫进鼻子里,几近解渴。视野少有地澄净,她的眼睛水样明润。
鱼钩甩进水里,我们安静了下来。野趣郊景中,她凝望着水面的两个倒影,我的映像随水波时聚时散。也许她眼里还会出现那个男人的样子,但一个月来她所受的魅惑可能已经开始松动含混了。
“我是该早点让你享受这些。”我望着浮漂说,“很美好,我也能感觉到。超离,懒散,还新鲜。身边的人是谁都这么美好。”
余光中她垂下了头。她知道我的意思,但心里还不舒服。我反复想过也对她讲过,恣意地过一天不是罪过,何况她一向记不牢新相识的面孔,一切都还可以解救。
总之我说了,我真的理解,而且我会处理好。
水边开始了一段沉默,这在意料之中。她什么时候这样都不奇怪,无论在那天之前还是之后。鱼漂动了一两次,但我们什么都没钓到。我可以弥补。后来她站起来,沿着水边走开,裙脚沾了泥水。水那边的野草显得比这边葱郁,其间那些窃窃弹动该是蛙类的蹦跳。
我收回她的鱼竿,俯身从桶水里捉起我早上买的活鱼,用力捏住甩摆的鱼身,把鱼钩穿进它的上颚。并不是很容易,场面也不大好看,鲜血涌流并飞溅。一条鱼怎么会流这么多血?我开始生鱼和垂钓运动的气。可使命感再次使我平和下来。进入同样的背景,叠加另一份印记,其过程是解题也该是审美,好比把第二种溶质搅进溶液,让人无法离析先后,只能欣赏再生的色泽和滋味。
我朝她的方向举起鱼,喊出欢畅的声音:“鱼!”
她回来的步子不快,我朝她使劲勾手。
见我把鱼递到身前,她还是有点紧张。我说有我呢,就把鱼嘴给她。她犹疑着伸手去摘鱼钩,我看见了她食指上留下的小小疤点,一个月前这里是一处小伤口,三十天间用拇指摩挲它成了她的习惯。她摘钩果然怯懦笨拙,动手帮她是很自然的事,我捏住钢钩也把持住她的手,隐敛地用钩尖又准确地戳破了她的疤点。她疼得叫了一声。
鱼像那次一样跌落,但还在泥地上扭动。我把它踢进水,同时把她的食指塞进嘴里,帮她吸吮鲜血。她的手冰凉,让我感觉嘴里的血更腥冷,由此也可知她能感觉到口腔的温热。
“上次是这样吧?”我问。这样可不合临床医护卫生标准。
她抽回手,额前的头发垂了下来,遮住了眼睛。那条鱼再笨,进了水洼也不见踪迹了。轮到我了。我只脱去外衣,面对水面上的自己竟可耻地打了冷战。
我明白我不同于那个人,可对她来说,一面之缘最堪记的,该是鲜明的环境和事件形态,而非特定的填充物。当日的欢愉畅快正听凭重演,她记忆里弧城伴侣的形象会两相变幻交溶融,我的模样和姿态即将荡漾其间。
念念有词地,我在泥地上蹬腿跳进水里。腾跃比预想的潦草短促,入水前我来不及吸气。拍进水面,身体当即被野水刷凉,扭拧了几番我才得以露出头,任几条水草挂在身上。不知道那个人在她面前戏水时是骁勇还是俏皮,上次他没捉到鱼,但一定像鱼一样放浪。我尽量学着那样子击水向远处游去,游到一簇挺水草茎之间才急迫地喘了几口。
回到岸上时,我当然累了。出水后的愿望就是脱掉湿水下坠的裤子。
“你不打算转过去吗?”我嗓音古怪地问她。她转身走开几步,我脱光了自己。接下来,我应该把外衣系在腰间,拧拧湿衣服,把它们晾在石头上。中午过后我们应该驾车回返,回到旅馆她应该让我赶紧洗个热水澡。然后我应该穿着浴衣与她相对,其时我们应该急着用嘴去找对方的嘴,应该连为一体倒在床上翻滚……这些都是已经规定了的。但在水边赤身裸体时,见她正走到一块圆润的大石旁,我突然有了另外的想法。
她从石头上收回眼风时,我已经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一手扣在她胸前,一手搂着她的小腹。
“在这儿是不是应该有一次?”
“胡说什么!”她想摆脱我的胳膊。
“你再想想,我们不能有疏漏。他在这儿脱了衣服。”
“没有,在这儿没有。”
我得给她讲讲她的经历,“我不是说你喜欢躺在石头上,但这种事都是凭心血来潮的。刚才那片树林其实是很好的铺垫,你说在那儿没怎么样,好,我信。但在这儿……怎么可能还没什么?”
不知不觉间我就使上力气,把她拥到石头上了。她则吭吭哧哧地试图推开我。我对她用这态度能否过好今天感到忧虑。
“你也知道,漏掉场景最不好办!”我压了上去,好像有两句央求。后来她不动了。
可能是因为疲劳和刚刚的冷水,我做事情费了些周章。我起身后,她在石头上躺了一会儿,也坐起来,抱紧胳膊裹起身体,开始掉眼泪。在家里她刚刚承认了事情之后,坐在我面前等我开口说话时,也是用两臂围裹身体,慢慢地哭了起来。
如果她开始哭泣,我就该承担更多了。今天还有很久要度过。我拿出吃的东西,发给她鱼罐头,又丢给她一个面包。我没找到给自己准备的牛肉罐头。从水里出来后,我领略到风的冷硬,一度有点腹痛。勉强完成了午餐,我在石头侧面靠坐良久。后来我发现她没吃多少东西,鱼罐头我忘了帮她打开。这不太好,她很少饿肚子。我开始喂她吃。她不看我,东西喂到嘴边才张一次嘴,如此重复,直到我觉得她吃好了。
午后返回时,我的衣裤根本就没晾干。我只套了外衣外裤,把其余衣物和渔具一起扔进了车后厢。弧城之行是我确证了情况后连夜安排的,拖延时令的话我现在也许会冷得打战。虽然我不是因为怕冷才雷厉风行的。当晚拖拖沓沓地交谈过后,我们都在床上静了下来。深夜我叫醒她,她的泪痕还在脸上,我讲给她那个原始部落的习俗——男人发现女人有了外遇从来顾不得打骂,而是即刻同她做爱,目的是用男性局部的蘑菇状结构尽多地掏刮女人身体里的外来精液,再把自己的精液捣进去,混合残留的那些,极力降低她被别人致孕的可能。多原始,又多理性。
“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晚我问。
她说她不会因为那天而怀孕的。她没懂我的意思。
“我在打比方,我说的是这儿——”我盘腿坐起来,指着脑袋告诉她,“我是说那些印象,在你脑子里赶不走的那些。我们应该去重新来一次,去搅拌去挤占那些印象。”
然后我讲了很多话,直到天亮。半宿里她脸上的眼泪干了好几次。
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一半任务吧。所谓的返回,其实是继续前行,绕弯子去找主路兜回市区。车子走得可以说磨磨蹭蹭,也可以说细致持重。到了那段土路,我望见了前面的另一片野水。她承认过发生在这儿的欢笑,眼下她不说话,我也不会略过。我熟悉相机里取景于此的那些照片,希望我能做好。
“准备好!”我说,然后加速,斜插水岸冲了过去。这片水开阔得多,水面有刚才水洼的十几倍大,有像样的岸,岸边野草过膝,腥气十足。刚刚望见的那些活动的斑点现了原形,变成一群野鸭惊飞起来,扑扑啦啦掠过车前窗。那些照片其实没拍好,有大片的模糊,我由此推测了车速。如果无知地慢慢推进,鸭群就会翻书一样三三两两地跳开,情景自然不会这么好看。
“哈!”用力笑了一声,我停下车。效果不错,除了末尾车在几个坑洼里颠了一阵子。她无动于衷,反倒眯起眼。
“我去后排躺一下,我累了,有点不舒服。”她去了后排座,侧卧下来。
我也不必保持欢快了。“上次在这儿你舒服吗?”
“也不太舒服,怎么了?”
“你拍了那些鸭子。”
“然后就没力气了。你知道,我有时有点晕车。”她声带松懈地说。
我下车拍照。出于模仿,我向水里抛石头,拍摄水花,动作让自己厌恶。受这方清幽勾引,我朝水里撒了一泡尿,风灌进外裤,直接粗鲁地刮擦腿根。我花了点时间排净。在车后门外,我透过车窗看她,看了好一会儿。她可以躺得那么柔软,我刚刚察觉。我翻过一些杂志,从中看过好些女人,有些面颊俊美皮肉明艳,但卧姿生硬。那些沙滩,那些床,毁了那些摄影模特该有的娇媚。
我拉开车后门,“怎么样,好点了吗?”同时我也跨进去,挤进后排。
她蜷了蜷腿,“干什么啊?”
“我是想说,刚才我也是推测——”我吞吞吐吐地凑到她腮前说,“也许你们不是那样,不是在石头上,而是在这儿,车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把事做周全……”
在后座她再次推搡了我,还兔子一样伸腿蹬我。
我相信我们的默契是深埋在内的,不依赖肢体协调,甚至会得到肢体失谐的烘托。
信念维系了许久。有一片刻,斜射的日光略呈棕色,吹进车里的风带来了些许蜇痛。
我们再起程时有些晚了。我有点急于摆脱土路,眼角也不舒服,行车又让她受了些颠簸。希望在她未来的记忆里她唇边和上臂的伤不是我弄的,是车座碰撞的。总之我没办法,这次更加力不从心,老早就气喘吁吁,从石头上到车里,腰肌也几近痉挛。我需要她停止扭拧。起初我怀疑是她暗示我别错过这里的,觉得她是不好说白,也怕破坏这一出的自发性,后来混乱中我糊里糊涂地动了手,她则嘶叫了几声。
“我没别的意思,这样总比……”
一本地图册从后座飞来,掠过我耳朵砸在车前窗上。车扭了扭,我把控住方向盘。接着说:“这样总比错过场景好些。”
我打开了车里的音乐。我肠胃又开始难受,认路困难,并开始担心又有什么幽静而引人逗留的地方出现。
回到旅馆,天色已经暗了。我们吃了点东西,我给她要了一碗汤,给自己要了一瓶酒。我们都没喝完,我猜我需要酒,但不知道需要喝多少。我最明确的任务来了。
进了房间,我佝偻着换鞋,不慎坐倒在地。我笑笑,嘟囔着说身上还有水草的气味,然后看着她的眼睛。
她开口说的居然是:“我们再谈谈行吗?”
“我想先洗个澡,不碍你事吧?”我连忙说。
在淋浴间里,我把水温调到接近烫人,扶着墙让花洒冲击头顶许久。皮肤由滑腻变得红嫩。翻洗下身时,我的手均匀地颤抖,手背竟是率先受不住水流浇烫的部位。或许这有帮助呢。
出来时我身上还泛着热气,浴衣敞露胸口,腰带松松地盘在腰间。她还站在窗口,没换衣服。从这个角度看,她的嘴角竟伤得不轻。我张了张嘴,看她的样子,事情不会很轻快。我吐一口气,坐在床上,前额的头发也垂了下来。
“对不起,在外边时我有点心急,尤其是在车里。”我想把话说得坦率又奏效。
她摇摇头,然后说:“我早想好了,这趟出来怎么都不怪你。”
我倒不希望她事先想好什么,不想她的预置心态让两次经历容易区分。她咬咬下唇,“我也没资格怪罪。只是今天我感觉,这不只是一个谁该怪谁的问题。”
“对啊,不是。我就是也这样觉得,才要这样过这一天的。”
“不是,现在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把脸转向窗外,外面已经是夜景了。她又哽咽了很久,才慢慢开口:“你不记得了吗?我们以前,很早以前,有一次就是在车里。”
我脸上的皮肉慢慢沉降下来。我想反问她什么,没能说出话来。那应该是一辆借来的车,我们去的是她家乡附近,那天我们好像很开心。在后排座位上,我拼命推拉座椅,同时对她说了些热烘烘的话。现在我可以记起这些,却不大敢继续回想那些声音和影像,它们随时会被淹浸,基调也会改变,变成我问她感觉如何,说我们要把事情做周全,然后让她别推我……
“大概也是这个季节吧,只是那时我们还都……”
“你提那些干什么?”我烦躁了。今天应该有所指向,我必须有所行动。我抓着她两条胳膊,把她往床上拉。她被我压在床上,这次连手臂都没挥动。
我独自忙乱一气。敞开浴衣后,我悬停在她上方,迟迟感觉不到自己可以继续做什么,终于绝望地倒在一边。
喘息过后,我对着天花板说:“看来这样不行。”
“你明白了就好,开始时我就想说的。”
“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早该想到的——我应该准备点药。”
她湿溻溻地笑,眼泪丰沛起来。
“那个人……不是陌生人。”她说,“我们认识他。”
我扭头盯着她,又似乎惧怕她的声音。
泪水从她眼角一股股涌出来,她用力说了下去:“我们都认识他,所以没那么简单,那天就是那天。”
有嗡鸣声在我颅内回荡,我听不清自己有没有问出那句换作谁都会问的话。
她说了一个名字,然后又重复了一次。我看见了她的嘴形。
“我们的确是偶然遇上的。他身边的女的走了。起初我们只是在聊你,他说他最了解你。后来……他也很后悔。”
她语音里开始有很多鼻涕声。我坐起来,像个耐不住平躺的心脏病病人,喘气成了唯一的活计。几分钟后我摆开浴衣,开始起身穿衣服,动作越来越坚决。
她看到我穿上了外衣外裤,正在潦草地拉拉链系扣子。她看上去前所未有地关切眼前,同时又被突如其来的呆愣攫住。
“我是想过早点告诉你的……”
我听到了她黏涩的声音。我拨掉桌几上的不少杂物,找到了车钥匙。
我们都清楚,那个人是我朋友,而以朋友相称,是因为我和他都觉得挚友不必唤作兄弟。
她拧身下床,想要拉住我,“这终究是我们俩之间的事,你厌恶我或者仇恨我都好……”
我边摆手边挡开她的手。
“其实路上我就感觉这样不对头了,但还在自欺欺人。”我克服了喉咙里的一阵不适,试着稳下声调,“现在好了。他不是别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不会不帮这个忙。”
她蠢笨,还没明白我们该做什么。
“我去找他,趁季节还对。我们三个一起来,什么细节都不会错,以后你的弧城就会有他也有我!”我去弯腰穿鞋,嘴里或许还余留着喃喃自语。他那里离得不远,我有几年没去,但心里一直记得,不需要怎么辨认道路。
我清楚他,在树林里他不会那样呼吼。我们一起混过几年,他足够知近,为人也足够体谅,当着他的面我可以吃几次药,她也不必噤声。
我腰身哆嗦着,拔脚往外走。她跌撞着跟到门口,还张皇地说着什么,就像我对她说的是另外一番打算似的。我只好摔上门纵步走开,让那声沉重的门响或者别的什么,把她封闭在这弧城最对的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