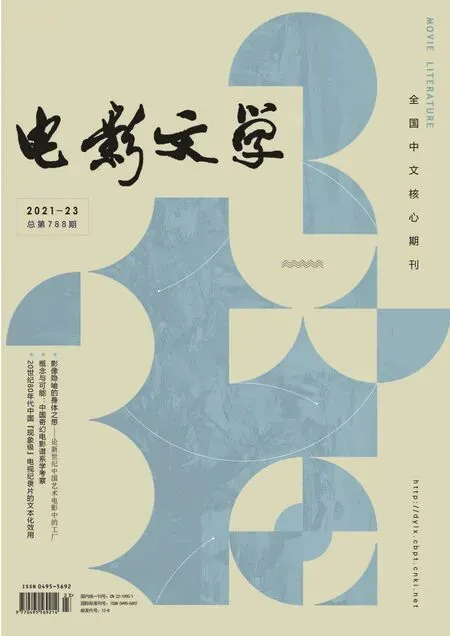概念与可能:中国奇幻电影谱系学考察
李小杰
(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自电影诞生以来,奇幻便成为电影重要的表现形式。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特技摄影、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使人类几千年来天马行空的想象在银幕上得以视觉呈现。中国电影的奇幻类型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武侠神怪片”。1928年张石川执导的《火烧红莲寺》就使用特技摄影、吊钢丝等方式实现飞天遁形的奇幻效果。然而,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片,奇幻电影(Fantasy Film)在计算机技术广泛运用的当代才得到相对集中和成熟的发展。西方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指环王》《霍比特人》《哈利·波特》等。奇幻文学大师托尔金(Tolkien)在《论仙境故事》(Tolkien
On
Fairy
-stories
)中提出“第二世界”(secondary world),即相对于现实世界,“第二世界”是架空的、幻想的,也是逻辑上真实的,并与真实世界保持“现实的内在一致性”。21世纪以来,中国奇幻电影蓬勃发展,“奇幻”成为电影市场抢手IP,但如何塑造圆融自洽的“第二世界”仍是中国奇幻电影面临的挑战。与奇幻电影热相比,目前国内学界对奇幻电影的研究却未臻成熟。本文尝试对奇幻概念进行谱系学考察,提出中国奇幻电影的“内取炼体”“外假控制”的本体论特征,为中国奇幻电影研究提供概念辨析与谱系学考察的理论基础;然后通过阐释奇幻电影历史传承和跨媒介融合,探讨其存在的问题。一、概念与类型:奇幻的理论边界
奇幻,即英语fantasy/The Fantastic,源自拉丁语phantasticus,其本义是指使本来不那么明显的事物得到显现或体现。早在电影诞生以前,奇幻这一概念就一直存在于神话传说、寓言、小说等虚构性作品中,西方学界对“奇幻”的概念、内涵也众说纷纭。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奇幻小说:文学体裁的结构化方法》(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
,1973)一书认为,遇到怪异的和奇妙的(the uncanny and the marvelous)事物,“人物和读者对事件的本质表现出‘犹豫’,足以使他们质疑现实。对于小说或电影的人物来说,“体验事件的人必须选择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他要么是一种幻想的、错觉的受害者,要么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世界的规律却保持不变。否则该事件确实已经发生,它是现实的组成部分。但是随后,现实受到我们未知的法则(laws)的控制”。凯瑟琳·休姆(Kathryn Hume)对欧美理论家进行一番考量之后,在《幻想与模仿:西方文学对现实的回应》(Fantasy
and
Mimesis
:Responses
to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1984)中指出,“奇幻是从共识现实出发的偏离,它是文学本能的冲动,并且表现出无数种变化,从怪物(monsters)到隐喻。它包括人们通常认为是诸如人类不朽之类的物理事实的越界,比光速行进,心灵感应运动等更快。……它们是奇迹或令人惊奇的事物,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是日常事件,并且不能由任何有志于尝试的人控制”。柯林·曼洛夫(Colin Manlove)在《英格兰奇幻文学》(The
Fantasy
Literature
of
England
,1999)中认为,“幻想的定义是‘涉及超自然或不可能的小说’,这与英国人对超自然的关注相吻合。他进一步指出,“超自然”(supernatural)意味着存在某种形式的魔术或无数魔法,从鬼魂(ghosts),仙女(faries)到神灵(gods)和魔鬼(devils);‘不可能’是指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菲利斯·佩里(Phyllis J.Perry)《奇幻小说教程:从霍比特人到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Teaching
Fantasy
Novels
:From
The
Hobbit
to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2003)指出,“显然,奇幻文学作品代表了与现实的故意偏离。或者可以说,它呈现了一个‘替代现实’(substitute reality),其中包含在理性世界中不可能发生或存在的事件、地点和生物。非理性现象在幻想故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杰米·威廉姆森(Jamie Williamson)的《现代幻想的演变:从古物到巴兰亭成人奇幻丛书》(The
Evolution
of
Modern
Fantasy
:From
Antiquarianism
to
the
Ballantine
Adult
Fantasy
Series
,2015)对奇幻的定义是其共性:“这是功能上最低的公分母,这意味着在超自然或神奇的事物构成现实结构且以探索、战争和冒险为主题的世界中设定的叙事。”马克·A·法布里齐(Mark A.Fabrizi )的《奇幻文学:具有挑战性的类型》(Fantasy
Literature
:Challenging
Genres
,2016)的定义与“第二世界”类似:“幻想作品使我们摆脱了平淡无奇的生活。……提供了从平庸到超自然的释放:一个惊喜和创造的世界,远远超出了我们自己的世界。”《剑桥奇幻小说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antasy
Literature
,2012)的编辑爱德华·詹姆斯(Edward James)和法拉·门德尔松(Farah Mendlesohn)则认为,奇幻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也是人们认识到不可能的事情时的兴奋和惊奇。从哥特式(gothic)的鬼故事到20世纪通俗文学的僵尸(zombies)和吸血鬼(vampires),从拉德克利夫夫人到罗琳女士,这种奇幻小说一直受到读者的欢迎。尽管学界至今没有统一奇幻这一概念的内涵,但上述研究对奇幻作品的普遍特征有一定的共识:即奇幻以不可能(impossible )、不寻常、超自然(supernatural)力量为故事情节,其人物通常涉及仙女(sylphids)、魔鬼(devils)或者僵尸(zombies)等,场景大多设定在一个异常的,或者另一个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奇幻作品的外延比较宽泛,包含的作品比较多。《剑桥奇幻文学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antasy
Literature
,2012)就精选了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800)、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1704)、通俗小说《木乃伊:一个22世纪的故事》(The
Mummy
!A
Tale
of
the
Twenty
-Second
Century
,1827)、安徒生童话《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
,1837),甚至现代主义作品卡夫卡的《变形记》(1915),当然还包括托尔金一系列著名的奇幻小说《指环王》《霍比特人》等。这些奇幻文学为奇幻电影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并被改编成风靡全球的奇幻影视作品,如《指环王》《权力的游戏:冰与火之歌》《暮光之城》等。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就叙事方式、人物特征和情节构成而言,中国古代神魔鬼怪小说《山海经》《搜神记》《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等也是奇幻电影的主要题材来源。需要指出的是,奇幻电影常与科幻电影划为同一类型。显然,一些偶发性的故事,两者的区别并不明确。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科幻电视系列剧”《神秘博士》(Doctor
Who
)主角就包含变异性,既可以将其描述为“科幻”,又可以称之为“奇幻”。正如布赖恩·阿特伯里(Brian Attebery)解释的那样,这两种流派在希腊神话的故事中有着共同的血统,例如“魔像(golems)的历险和其他人造生物的故事,不断变化的传说,乌托邦、梦想的幻象和寓言”。这同样发生在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第一本科幻小说《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中,作者用科学作品替换了幻想元素,用电力代替了神力等。事实上,早在中世纪,西方文学就已经有狼人故事等先驱,不过真正和“奇幻”有直接关系的,应该可追溯到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早期的现代文学(即1492年至1650年之间撰写的文学)中存在着仿生人(android)……网络化智能的文学实例可预见当今的网络系统,并为其主人提供虚拟假肢帮助。例如,莎士比亚的《暴风雨》(The
Tempest
,1610)中的普洛斯彼罗和马洛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创建的智能仆人网络(intelligent-servant networks),不仅为他们的制造者提供了增强功能(enhancement),而且成为其能力的延伸(distribution of their agency)。它们成为主角的分身,因此,它们不仅可以看作是假肢,还可以看作是制造者自我的分身的网络化版本——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当代后人类主题的早期现代先驱”。简言之,现代文本中的奇幻与科幻领域里的“赛博格”(Cyborg)的区别,即前者利用超自然力量,如魔法和咒语,后者则利用科学技术对人的身体进行改造,从而提升身体的性能。法拉·门德尔松(Farah Mendlesohn)和爱德华·詹姆斯(Edward James)认为,幻想与科幻的区别在于,幻想涉及“不可能和无法解释的事物”,科幻小说则“将一切视为可解释的”。简言之,科幻作品尤其硬科幻(Hard Sci-Fi)一般会遵循科学逻辑,或艺术逻辑,而奇幻则在一个相对自洽的逻辑世界展开叙事即可。
二、奇幻电影研究:如何可能与本体论特征
关于奇幻这一概念,中外研究者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我国奇幻电影理论还在逐步建构中。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对奇幻电影的研究,只是针对热门电影进行概括,概念考察梳理较少,尚未呈现系统的学术谱系溯源。戴清指出:“仙侠奇幻”题材影视剧以表现神、仙、妖、魔的情感故事和正邪较量为主要内容,主人公大多具有超自然能力,在艺术风格上充满非写实的瑰奇浪漫色彩。与“奇幻”相近似的称谓,还有“魔幻” (多指电影)、“玄幻” (多指网络小说),大多指代此类非写实题材创作。陈奇佳指出:“奇幻电影是幻想型电影中新近崛起的一个电影亚类型。所谓幻想型电影是以表现幻想性内容为主的电影的总称, 传统上包括科幻、童话、神怪、灵异还有宗教传奇、史诗神话等亚类型。”魏晨捷指出:“幻想电影(Fantasy Film)表现的是幻想与梦幻结合的幻想世界,其故事原型和叙事手法被认为是来源于幻想小说,通常涉及魔术、灵异事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或异国陌生化、传奇性的故事。幻想电影往往有魔法、神话、奇观、逃避现实和超能力等元素。”程波指出:“奇幻电影的定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经常与其他类型结合产生亚类型。一般来说,奇幻电影中有体现独立的世界观的架空世界,或与真实世界叠生或交叉的世界;其中的超自然事物无法用科学解释,而是作为一种既定的‘真实’存在;它的故事题材一般会结合超自然、人类无法预知或想象的事物。”周根红将那些离现实世界较远的架空世界、充满奇特幻想空间、表现神仙妖魔故事的小说归入“奇幻小说”的范畴,包括仙侠、盗墓等小说。
上述研究都认为中国奇幻与仙侠、魔幻、幻想渊源颇深,所以下文将集中讨论 “神、仙、妖、魔”和“仙侠”的背后有机逻辑,为奇幻电影研究提供本体论基础。《剑桥文学与后人类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Posthuman
,2017)指出,“早期的科学与现代科学相差甚远,因为它是基于魔法和未成熟的经验科学的混合,但也有一致性:例如,该时代对编码魔法(coded magic)和魔法代码(magical codes)的依赖实际上与我们自己依赖数字时代的编码魔法和魔法代码在某种程度一样”。如前所言,西方以“法术、魔法和妖等,(Art、Magic、demon或monster)”为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奇幻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魔法(召唤)”,中国奇幻电影具有本土历史文化特色,比如气功、妖怪、僵尸和阴阳五行等,发展出自己“内取外假”的中国特色。“内取”就是内取其身,主要是瞄准人类的身体,以阴阳五行、太极气功、修仙为主,让人更高更强,这在《西游记》等神魔类文本有更多展现;“外假”就是外假舟楫,主要是利用符咒、法器、法术、降头等超自然的力量,通过画好的/做过法的“符咒/法器”等召唤驱使对象,就像西方(科学)通过编码/代码的通信(communication)让人类或者人力使唤的智能对象(intelligent-servant ),甚至阴阳五行机关(networks )能力不断得到延伸,获得各种便利与飞跃,这在《阴阳师》类型的电影尤为多见。从电影的角度而言,当然是由此可展开人类的想象,视觉的拓展,建立具有本土色彩的“第二世界”。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出版了《控制论或在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1949)这一经典的控制论思想启发了人工智能、环境科学、认知科学等多个领域。《控制论》一书中提到“妖”的概念,“要使麦克斯韦妖(Maxwell Demon)行动,它必须从接近粒子的过程中接收有关其速度和撞击在墙壁上的信息”。于是,神话中的“妖”(demon)在近代终于和科学联系了起来,让“妖”成为“通讯”而落地,成就了奇幻研究有机的学术逻辑。不过科学家和人文学家都认为,要使“魔法”成事,要强调“接受/获取信息”。诺伯特·维纳的书名就叫“控制和通信(communication)”,而后人类经典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控制论、文学和信息学的虚拟身体》(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1999)特别提到,“麦克斯韦妖获取分子信息(information)所需的能量大于麦克斯韦妖通过筛选过程所能获取的能量”。那么整个基于控制论的奇幻概念的本体论特征就是:甲通过一些辅助(比如“妖”/符咒)发出信息得到乙的过程。用控制论的语言就是:只有传递/获得了足够信息量,才能够有效实行控制,而控制又使可能性空间缩小,获得了正的信息量,从而进一步促进控制。这在本质上揭示了“知”和“行”的统一。所以“信息”(information)和情报(intelligence)很重要,由此进行改造和控制。莎士比亚的奇幻剧《暴风雨》就是极好的展示:“亲爱的父亲,假如你曾经用你的法术(art)使狂暴的海水兴起这场风浪,请你使它们平息了吧!”以及“帮我把我的法衣( magic garment)脱去。好,(放下法衣)躺在那里吧,我的法术!——揩干你的眼睛,安心吧!” 该作品就是“父亲”(甲)借助法术/法衣(辅助)使风浪平息(得到乙),而其中的法术和法衣在作品的辅助作用可以作为中国奇幻作品咒语和法器等直接的借鉴。如果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出版了《控制论》和《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是从科学到人文的过渡,那么《剑桥文学与后人类指南》则通过从亚里士多德发明机器人代替人想法到中世纪的乔叟(Chaucer)的《修女的故事》(Nun
’s
Priest
’s
Tale
)的西方溯源,为我们研究奇幻,包括法术、魔法和妖等(Art或Magic或demon)扫平了障碍。简言之,在科学视域中,“情报(intelligence)”就是信息的获得,获得了沟通,就能控制机器人。在中国奇幻电影中信息的沟通表现为运用符咒来控制妖精或者僵尸,《控制论》一书的所言“控制和通信”,在中国文化语境则为带着咒语的符让信息畅通,从而实现控制。修仙电影近年成为重要IP,比如网络小说《凡人修仙传》(2017),电影《诛仙》(2019)以及电视剧《斗破苍穹》(2018)、《武动乾坤》(2017,2018)等都取得不俗的成绩。在修仙中,方术、方剂、秘术等本就较为重要。《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指出,“修道者首先是以修炼某种秘术著称的,它们绝大部分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声称能够延长寿命,并且内容很神秘……呼吸训练,以实现体内气的摄入、纯化和循环;冥想和内观;复杂的炼金术……包括使用符与灵体交流……并且人们相信,通过使用这些方术能够让人获得令人震撼的新的力量和境界”。使用秘术可以实施对非人类的控制,“修道者常常被表现为能够结交、控制、打败令多数人心生恐惧的生灵,或者得到它们的帮助。这些生灵包括野生动物、死去的人、魔和灵,以及特定地区的神仙”。 “命令和控制野生动物”“控制鬼的活动”“能够调动听从指令的灵”。如果说修仙炼气就是内取其身体,那么“听从指令”和“控制”的控制论逻辑就是外假舟楫,如此内取炼体、外假控制,神话与逻辑结合的概念内涵成了我们奇幻研究的本体论。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奇思妙想,甚至某些修仙人的愿望在当代已被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人类的想象力和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在这个点上与科技交汇。一方面这是人类的胜利,另一方面也给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以及给予电影逼真性(approach reality)。我们先在电影/小说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让后来的科学家再在现实中把它实现。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奇幻电影,会发现其实《晴雅集》(郭敬明导演,2020)的“铃虫”就像是监听器,“遁逃”就是时空机器,“千里传音”就像电话,“御风飞行”就像飞行器,只是在奇幻世界里面,每个民族都有基于自己文化底蕴建立的逻辑自洽的世界,这个世界展现的是人类的想象力,也是对身体、寿命、未来和世界的超越。
三、流动性与互渗性:神魔、民间到跨媒介融合
近年来,中国奇幻电影蓬勃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改编自古代小说和民间传奇的神魔、妖怪叙事,如:《画皮》《封神传奇》《西游降魔》《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西游记:女儿国》系列,改编自民间传说的《美人鱼》《长城》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系列,以及《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姜子牙》《新哪吒》等动漫。这类电影主要以小说、民间传说的人物为原型,在传统叙事上融入现代性思想,讲述天、地、人三界交错纵横的故事,相当于古代小说、民间传说的现代演绎。这类作品将民间传说的神魔、妖怪、幻术、丹药等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展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古代中国。
二是改编自网络小说如《鬼吹灯》系列、《捉妖记》《九层妖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赤狐书生》等。这些电影融奇幻、侦探、魔幻乃至玄幻为一体,通过精美的场景和特效,呈现出唯美、奇幻的视觉效果。这些电影的弱点也是明显的,因奇幻电影还在起步和摸索阶段。如何把奇幻做成中国的样式,如何把电影镜头和故事相结合,做出胜过中国神魔民间想象文本的电影,需要主创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建立一个复杂立体的宇宙。所以说,与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植物、语言、景观和世界观的《指环王》相比,我国至今的奇幻电影特征仍是流动的能指。
三是改编自手游作品的《晴雅集》《侍神令》《刺杀小说家》《真三国》或改编自日本小说的电影《妖猫传》等。例如,郭敬明编导,改编自日本小说《阴阳师》的电影《睛雅集》和改编自手游《阴阳师》的《侍神令》,算是跨界的大胆尝试,拿日本文化,转换给中国文化语境的观众观赏,把小说、漫画和电影交互,也是跨媒体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的实践,究竟如何创造出一个跨媒体的宇宙,即在一个(半)虚构的世界,大致背景是相似的,独立发展,偶尔交汇,创造出合乎本地的戏剧文化。小说《阴阳师》描写日本的平安时代,作者在开始时引述野史笔记,如《今昔物语集》,“可很快地,作家完全抛开典籍,纵横六合,翻云覆雨”。作者用想象力建造了自己的,但顺乎野史叙述,符合日本文化逻辑的世界。小说《阴阳师》的成功说明了奇幻世界想象力与人物逻辑的重要性。
如何合乎逻辑地放飞想象力,是奇幻电影要面对的问题。亨利·詹金斯在玛莎肯德的“跨媒体互文性”基础上提出“跨媒体叙事”,即“跨媒体叙事是理想的形式,就是每一种媒体出色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有这样,一个故事才能够以电影作为开头,进而通过电视、小说以及连环漫画展开进一步的详述;故事世界可以通过游戏来探索,或者作为一个娱乐公园景点来体验”。《晴雅集》版权购自《阴阳师》,就世界观来说,影片中的“式神”在日本指为阴阳师所役使的灵体。“式”者,侍也。式神可以理解为是“侍神”之意,就是侍奉其主的灵体。“式神”以剪纸而成形,可以利用符咒控制召唤出来。《剑桥文学与后人类指南》认为奴隶的主要功能是让主人克服自然的人为限制。换句话说,仆人为主人的身体和心理能力提供各种附加能力。例如,奴隶举起重物,使主人可以增加自身的力量。“奴隶”被视为主人可控的能力延伸。
其中这些剪纸、符咒、咒语和手势等都是上面所提到的通过获得信息,然后进行有效沟通(communication),实施控制。故此,既然阴阳师和阴阳五行有关,且其驭使方式又与驱使法器、道士赶尸,剪纸化蝶等幻术/仙术类似,只要遵行核心要义,或内取其身,修仙炼器,或外假舟楫召唤式神,成就通信,那么借鉴是顺理成章。譬如,我国古典的修仙典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幻世界。詹姆斯·米勒在《变形、灵性和具身性》中比较了基督教和道家的重要文献,发现中国的修仙不可思议,让人返老还童:“他们已经消除了老化的迹象,有一头黑发,满口牙齿(还可以再生)和年轻的脸庞。”另外,不朽的神仙通常看起来具有非凡的能力。他们可以一天走很远的距离,以很高的速度奔跑,拥有强大的力量,并且不受极端温度的影响。就像《庄子》中的精湛技艺一样,他们可以像“古之‘真人’入火不热,入水不湿”,这在文本中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说法。有些可以进入墙壁或潜入水下;有些则可以进入地下。其他人知道如何飞行或悬浮。有些人头上有高于他们的光环。其他人再一次表现出奇妙的,甚至是怪异的面相的迹象。况且当代观众因为西方的奇幻/科幻电影观影经验已经很习惯这种以增强人类身体和智力为角色的超人类(transhuman)角色。
正如玛丽-劳尔·瑞安指出:“每种媒介都有其最适合的主题及情节类型:你不能在舞台上、写作中、对话中、上千页的小说中、长达两个小时的电影及连播好几年的电视剧中讲述同样的故事类型。新媒体叙事的研发者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主题和什么样的情节可以恰当地利用媒介的内在属性。”比如,《晴雅集》开始一段的音乐和《攻壳机动队》开始那篇“谣”背景音乐相似,应该有所借鉴。《晴雅集》配乐制作人为川井宪次。川井宪次主要代表作包括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
,1995)和《攻壳机动队2》等,而《攻壳机动队》就是后人类最经典的电影之一,于此,我们看到了这两个电影文本的奇幻和赛博朋克美学的致敬与融合。就剧情的影响来说,好莱坞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最后一部分,电脑哈尔9000(HAL)能发展出自我意识。它已经拥有了部分人性,为完成木星使命,设计杀害了其他船员。我们在电影《晴雅集》里面也可以看到晴明师傅贺茂忠行和女王相爱,可是女王不能动情,于是贺茂忠行在自己的式神鹤守月灌注了对女王的爱,把鹤守月留下来陪她。岂知,式神鹤守月慢慢地发展出了自己的想法,想永远不死,以便和女王在一起,他把陪伴女王作为至高命令,宁愿牺牲众生也要放祸蛇出来。就像哈尔9000因在航程出现了一个判断失误,令鲍曼和普尔对它失去了信心,打算强行把它关闭,哈尔9000为了“活着”去完成探索木星的任务,因此突破了机器人三定律杀了人类。其实,在《流浪地球》的人工智能莫斯(Moss)为了保护火种计划阻止刘培强,刘培强认为莫斯是叛逃,可见我国电影不久前就已经致敬过《2001太空漫游》,短期内竟然再次致敬,模仿借鉴太多其实不利于原创。
我们不能说这种模仿就必然有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2001太空漫游》哈尔9000的出现,让人类警惕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人类将会被电脑取代。这是个对人类生存很是紧迫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人类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康德以来对理性提出的疑问。我们在赞美理性的同时,也对这种理性所具身化的机器感到非常担忧,因某天人工智能会发展成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因产生意识而比人类更聪明。可是这一设置并不符合奇幻类型,因为没有观众在观看奇幻电影时会觉得《晴雅集》中神鹤守月式的背叛会影响人类未来的命运,这也让“致敬”失去了深意。这也道出了国内导演的奇幻电影尚未创立逻辑自洽的世界,还没有走出国外奇幻电影的影响。
结 语
我国奇幻(动画)电影发展不过数年,属于草创阶段。由致敬、模仿阶段,再到自成一格,需要细致打磨作品,经典的产生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模仿和借鉴并非坏事,因为每件事情在刚起步的时候,都需要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做出成熟符合商业化流程的电影,最后做出独具一格的作品。就像系统论的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调节:通过系统不断把自己的控制结果与目标做比较,使得目标差在一次一次控制中慢慢减少,最终达致成品。在内容制作、投放渠道、数据反馈、调整优化的过程中不断进步,最终必能做出逻辑自洽又有中国特色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