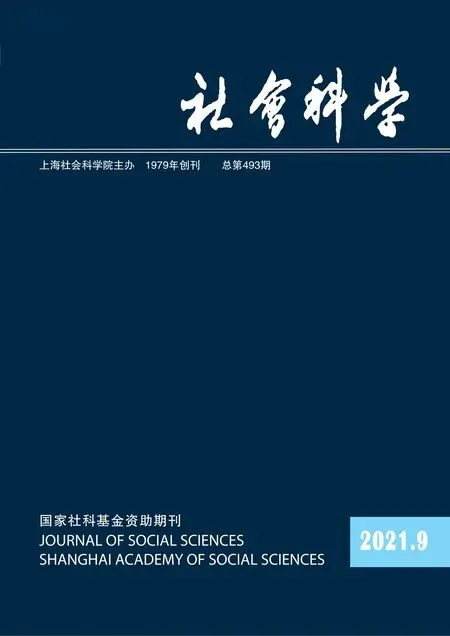人类增强的傲慢后果及其记忆之药*
杨庆峰
本文的写作有三个目的:其一是深入思考以往提出的问题。笔者曾经提出:在记忆哲学的视域中,构建一种指向人类增强理论与增强实践关联的理论框架;通过记忆哲学把握当代增强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1)参见杨庆峰《通过记忆哲学反思人类增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5日。本文就是要阐述清楚这个理论框架与关键问题。其二是回应增强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当属增强技术。从生命维度看,这种技术对于生命的控制达到了精准的程度。以神经元控制来说,光遗传学的出现使得人类对大脑的控制可以做到精准调控。现在的光遗传技术可以通过激活和抑制特定的神经元来调控动物的记忆、恐惧等行为。(2)关于光遗传技术对神经元进行精准调控的科学进展笔者曾做过专门梳理,很多具体的讨论可参见杨庆峰《记忆研究与人工智能》,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如同战争、灾难一样,增强技术也导致了某种时代情绪及哲学形态的出现。这种哲学准确地说与某种情绪关联,如果用一个情绪名称来概括增强技术条件下的普遍情绪,那么傲慢(hubris)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其三是为了回应包括笔者在内的四人新近出版的《技术有病,我没药》(3)参见杨庆峰、闫宏秀、段伟文、刘永谋《技术有病,我没药》,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一书的相关疑惑:此书为技术时代的危机提供了怎
样的药方?(4)2021年6月26日,在“人类增强与当代哲学”研讨会上,学界产生了三个相关争议:首先,断言了“技术有病”,这是否妥当?其次,“我没药”是否有种虚无主义的感受?第三,哲学能为技术时代开出何种药方?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书名是一个开放的话题,“我没药”并不是一个陈述式表达,而应该是疑问式表达。如果这样,那么本文的回应观点可以概括为“技术致病,我有药”,即增强技术导致了傲慢之病,而记忆是一种方法意义上的解药。下面本文将对这种普遍情绪加以阐述,并提供适当的缓解之道。
一、当前人类增强讨论的三个特点
人类增强技术讨论的第一个特点是遵循了从特殊到一般的基本逻辑。从个体角度看,对个体的身体功能和精神功能给予强化,会导致“超人”的出现。强化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如射线辐射、病毒感染、人机融合等。美国科幻电影塑造了强大的漫威超人群体,其讨论的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在看完电影之后进行思索。比如超人的能力与社会责任(蜘蛛侠)、团队协作与管理(美国队长)、超能力惩罚和超能力的合法运用(蝙蝠侠)等。在科学研究上,对技术的过度想象让人们感到恐慌。比如光遗传技术可以做到调控小白鼠的神经元,于是人们开始担忧这种技术一旦用于控制人体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对此科学家会说技术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关于这个逻辑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如从记忆的增强、智能的增强,推演到一般的意识增强。这种推演背后多少都有想象的因素。但是,总体来说,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是比较容易被日常讨论接受的方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会有很多特殊点的突破所带来新的增强案例,而哲学需要做的是从中把握哪些突破可以推演到一般?哪些增强技术会带来本体的改变?以感知和知觉增强为例,这种技术的发展往往会带来身体感知功能的提升,比如眼睛可以看到极其微小的东西,耳朵可以听到次声波现象。但是仅仅从器官功能提升的角度来讨论显然不够,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有趣的话题:什么样的对象会被构建起来?在新的增强技术下,并不是现成的对象被重新发现,而是新的知觉对象被构建出来。我们不妨构想一个思想实验:一个能够看到光速运动对象的状态的技术出现了,人类从此可以把握瞬间。这里,我们并不是看到瞬间,而是当条件具备的时候,技术与我们的知觉共同建构了瞬间这个新的对象,尽管我们的知觉器官可能猛然间并不适应这个新的由技术呈现的对象。
人类增强技术讨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出现了“泛增强”现象。“泛增强”讨论是指把所有的技术都看作是增强技术,然后讨论人与技术的关系。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把技术的实现目的即技术的功能从生活世界中抽象出来单独处理。这样一来,任何技术都可以看作是特定目的的增强或者实现。比如,椅子可以让人体感觉更加舒适;相对用手捧水喝,杯子可以提高喝水的效率;飞机可以提高我们从A到B的速度。但是,这种看法并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后果。“泛增强”讨论会使我们迷失在抽象的技术功能之中,而忽略了与之相应的社会语境,更使我们失去了对原有的人如何通过特定技术提升身体现有机能、实现完美性的考察。因此,“泛增强”讨论与本文的增强技术讨论之间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一般功能性“泛增强”讨论更多强调的是技术功能对于人体原有需求的满足,身体累了,想休息一下,找把椅子坐下来,这个过程对于身体的机能没有改变,只是让其从一个状态转换到另一个状态;但是,本文的增强技术却是指身体从原有的机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状态,也就是说身体的机能出现了改变。以身体增高技术来说,赛增这样的药品可以加大生长激素的分泌,这个加大就是对原有分泌量的提升,最终的结果是实现了每个月生长1cm左右的目标。
克服“泛增强”讨论的方法就是把增强技术放置在特殊的生活语境中。比如“新兴技术”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它把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技术类别中: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能够带来极大风险的技术类别,这样一来,日常讨论的技术物品就会被排除在外。然而,这种做法还是不足够的。在本文中,我们把增强技术放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之中。很显然,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与智能技术有关的可穿戴、虚拟与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会凸显出来;与生命改造有关的基因工程、合成生命技术与人机融合技术会被呈现出来;与生物体的控制有关的光遗传技术也会被带到当下。这些技术无疑符合“新兴技术”的规定性,但也有其他新的特性。
人类增强技术讨论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人类增强的伦理性讨论强于人文性讨论。目前增强技术讨论体现出明显的伦理特性,这种讨论将增强技术的观点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比如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5)易显飞:《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论主张及论争启示》,《世界哲学》2020年第1期。而人文性的分析并不足够。(6)2020年,增强技术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也说明了人文研究相对伦理研究来说比较缺乏,对这一话题的人文研究并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经典人文主义的立场,而是立足于数字时代新人文主义(比如阐述人类条件和体验)的研究,这一方式显然不同于从人性出发的做法。提升人体功能机能是当前讨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种讨论主要是科学主义的,即从科学的角度讨论人类的增强问题。诸多科学成果都是提升身体的某种特定机能,或者因为某种机能改变而影响到人类道德水平的提升。但是,身体或精神机能的讨论基础是自然主义,即把身体或精神看作是自然实体,对其属性进行增强。但人文主义的视野下的讨论会有新的基础,如人性(human nature)。人性这一概念曾经在哲学史上遭受多种批判,并因抽象性而受到质疑。所以当回顾语境的时候,人的语境、条件以及体验就会成为新的出发点。(7)笔者曾经指出,从现实条件出发,去探讨现实条件如何有利于个体的自我构成,不同于从人性路径(HN)出发。此外还有两条新的可能性路径:条件路径(HC)与体验路径(HE)。参见拙文《反思增强技术以增进人类福祉》,《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12日。这些出发点在哲学史上都有着深厚的讨论历史,需要加以挖掘。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些客观的出发点显然远离了真实的人们,沦为一个半真半假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寻求与人类体验有关的出发点,让人的体验成为增强技术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虚拟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交互式体验成为新的体验形式;增强现实也成为重要的问题。
此外,在人文性的要求下,人类增强技术的讨论会出现更多新的问题:与完美相反的缺憾的意义、与强大相反的弱小的意义会被重新审视,这是辩证思维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从哲学讨论来看,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缺憾、弱小也并不总是表现为上述增强现象的反面。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被束缚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事实上需要拓展这种考虑的方式了。(8)这种拓展已经在一些学者的思考中展现出来,如田海平指出,基于技术功能展现的“追求完美”“制造完美”与基于人性道德根据的“反对完美”总是如影随形,二者构成了人类增强的完美悖论。在他看来,走出完美悖论是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话语的价值方向或伦理旨趣之所在。他给出的方案是:寻求共识框架下人类增强的伦理安全是在完美悖论中借助伦理的“莫比乌斯带”(Mobius Band of Ethics),探讨“科技-人性”之相互生成、开放融合的可能。参见田海平《人类增强的完美悖论及其伦理旨趣》,《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在他看来,要跳出“制造完美”与“反对完美”的悖论,从正、反、合的三阶段找寻到科技与人性的开放融合之可能性。这一点应该说抓住了关键问题,但是不足之处在于悖论根基尚未澄清,笔者认为有三点需要注意:(1)真正的悖论依然是完美与缺憾的关系。“制造完美”的出发点是,针对人之脆弱性、依赖性或有限性,将缺陷看作不足;而“反对完美”也并不是基于肯定缺陷的本体论地位,而是防止增强技术的风险(桑德尔)。在这一悖论中,对缺陷的意义及其地位尚需进一步揭示。(2)还有一种路径就是对“科技-人性”的意义的阐发,这是一种融合意义上的,比如自然性与人工性的融合,比如植入人工心脏的人依然可以很好地生活,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这个路径不同于第一种立场,承认缺陷的意义,而是肯定了非纯粹自然性的地位。(3)是肯定改造后的人性之合理性,这很容易与传统的伦理观点产生较大冲突。举一个简单例子,记忆与遗忘的现象研究。无论是在日常生活领域还是在科学领域,遗忘通常会被看作是记忆的反面,因为记忆是保留,而遗忘是删除。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遗忘也具有主动性,生物进化与发展需要遗忘。此外,遗忘行为也是特定神经元回路的表达,与记忆一样。如此,一种思维上的固有框架不断遭受着科学事实的冲击。所以,对于诸如脆弱性、缺陷、有限性等的意义,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幸运的是,从利科的《可错的人》、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等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思考。这些思考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二、傲慢:增强技术导致的普遍情绪
上文已经指出,在新的人文性讨论的要求下,需要思考诸如脆弱、缺憾的意义,而不是完美、理性、进步、增强,但是这种思考也不能重新陷入二元的境地。这是后现代主义者已经完成了的任务,我们没有必要加以重复。本文准备从普遍情绪出发展开讨论。由此,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当代增强技术发展导致了怎样的人类普遍情绪?
这一问题很容易令人想到一本著作——《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阿诺德·盖伦在该书中以社会学和生物学为基础,提出了一套社会心理学理论来分析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但这本著作最终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悲观主义诊断”。(9)Shields, Mark A.,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2(2), 1983, p.244.在这篇书评中,马克·希尔德(Mark A.Shilelds)指出,盖伦对时代危机做出了与理性化、主体化和合法化有关的诊断。本文力图在此基础上前行,与该著作相同的地方在于,本文也将包括生物学在内的人工智能、虚拟增强等时代最新科技及其最新进展作为基础,与该著作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将普遍情绪看作是文化史中的恒定表达,力图实现一种合理的诊断。本文所指的普遍情绪是增强技术之下一种文化传承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傲慢(hubris)。hubris是一个古希腊概念,意思是傲慢和自大。在古希腊悲剧中,这个词是指导致悲剧英雄失落的致命缺点。但我们对这个词的考察不能仅仅通过词义来完成,还需要结合文化语境的不同。约书华·康哈达·杰克逊(Joshua Conrad Jackson)提供了“共词化”(colexification)的方法,他指出,在情感节点网络中存在着普遍结构。以傲慢为例,在英语中,我们找到了proud作为相近的表达;在印欧语系中,proud与bad和sad属于同一词群;而在其他语言中,proud和爱、希望、需要、喜欢等正面的词汇构成了同一词群。(10)Jackson, Conrad, J. et al, “Emotion Semantics Show Both Cultural Variation and Universal Structure”, Science, Vol.366, Issue 6472, pp.1517-1522,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6/6472/1517(2019-12-20)。在作者看来,许多语言都有一些指称生气和恐惧等情感词汇,然而在跨语言中这些情感是否具有相似的意义,或者为什么它们的意义会改变?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使用了一种“共词化”(colexification)方法来分析这一问题,共同化是指一种语言中的现象,即用相同的词来表示不同的语义关联的概念,比如英语fly,既指飞行的行为,又指苍蝇。此外,2020年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发布了最新版本的跨语言共词化数据库(Database of Cross-Linguistic Colexifications CLICS),涵盖了超过3100种语言的关联词汇。共词化方法可以使我们洞悉人类的感知、语言的演变。傲慢首先表现为文化性傲慢。从文化发展的符号中能感受到这一点。比如最初的神话中,神的傲慢经常在不同神话中出现。神的傲慢与人之卑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可以看作是文化性傲慢的原初形式,文化性的傲慢在理性时代通过理性被放大。“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生活是最尊贵的生活”“未加反思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等观念充分展示了理性傲慢。人始终想通过理性这一因素对人与动物加以区分,但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区分的缺陷。比如,在中国文化中,“孝”是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理性傲慢在科学决定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决定论看来,只要给出系统的初始条件,就可以计算出整个系统的未来状态。当前,傲慢这个概念成为哲学家分析我们时代问题的主要抓手。利科在2006年的《记忆、历史与遗忘》一书中专门提出了反抗理性傲慢的问题。“记忆现象,和我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为顽强地抵抗着彻底反思的傲慢(hubris)。”(11)[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与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桑德尔在2020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的访谈时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自由主义傲慢在美国衰落中扮演了重要地位。斯蒂格勒还提出了计算傲慢的形式。
技术性傲慢是指由现代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傲慢形态。麦克·海德(Mikael Hård)指出了科技傲慢的形态。“我们可以说,有时候科学以一种傲慢的方式打开了想象的领域:19世纪末尼采把超人越界与过度延伸概括为权力意志驱动的强人或者超人。”(12)Hård, M., Jamison, A., Hubris and Hybri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Routledge, 2005, p.53.“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对沉思适应于那个时代的价值有着极大的兴趣,那时人们对于弥漫在空气中的科技傲慢又爱又恨。”(13)Hård, M., Jamison, A., Hubris and Hybri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Routledge, 2005, p.101.这种形态显示了技术系统自身所表现出来的促逼本性,更准确地说是由技术逻辑运行导致的一种系统性结果。“在庆祝机器的时候,人们的乌托邦的一面发展出一类傲慢,借助它对于当前技术文明的文化评价有着强烈的需求。”(14)Hård, M., Jamison, A., Hubris and Hybri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Routledge, 2005, p.107.“相比其他形式,科幻电影更多被用来为科技傲慢的新产品和行动准备文化基础,例如把火箭送入外太空以及建造更加复杂的武器。”(15)Hård, M., Jamison, A., Hubris and Hybri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Routledge, 2005, p.163.
当前的技术性傲慢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数据化、网络化和算法化。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算法与网络显示出的力量是我们以前无法从单个的技术对象中认识到的。如今,算法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产生了一些新的行为模式。单个技术物无法导致傲慢的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与生活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会对技术物形成一种意义关联。长时间使用某物会形成对某物的情感依赖,“敝帚自珍”恰恰展示了这样一种文化认识。然而,现代技术发展的系统性关联使得技术物的个体性消失,技术物变成整个技术社会的网络节点。于是,个体性消失在系统性联结中。此外,技术系统并非将自身表现为对象性的存在,而是逐步构建着人类社会的技术架构。数据对象已经成为当前智能社会的技术框架,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中,智能对象会更多地嵌入这个框架之中,一种技术性共同体逐渐演化成形。现代技术导致的傲慢性是技术本身展现出来的,一种带有强大的功能性与去功能性的产物。马克思、海德格尔以及斯蒂格勒等哲学家已然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用“技术异化”、“技术促逼”和“技术工业化”等概念解释了技术性傲慢的展开逻辑。增强技术更是如此,其内在的提升机体的原有功能恰恰构成了技术性傲慢的内核。比如,在生命存在的期限上,增强主义者认为通过特定的手段可以实现生命的无限延长,也就是长生不老。虽然这终究是一种文化想象,但在延缓生命衰老上,科学研究却取得了显著成果。这实际也是技术性傲慢的一种样式,只是这种由理性带来的傲慢比较适度而已。
技术性傲慢并非孤立存在,它往往和心理性傲慢天然地融为一体。(16)作者还谈到了中国的科技傲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他看来,中国很少有动力和机会使科技傲慢在社会上变得显著。心理性傲慢是由人类强化自身或者基于进步主义的理性观念而确立起来的一种傲慢心态。这恰恰是一种亟须被揭示的普遍情绪。在战争、灾害、病毒等紧急状态下,生存会成为关键的问题,与之伴随的是生存主义哲学的兴起,战争背景下产生的普遍情绪当属生存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如雅思贝斯、萨特等人的哲学;在特大灾害背景下,如地震、火灾,人类更容易感受到自然的强大与自身的渺小,这种对比会让人产生无助、绝望等情绪;新冠疫情时期,长时间的隔离与缺少社交容易让焦虑、急躁、无聊成为普遍情绪。显然当技术取得飞速进步的时候,更容易滋生出心理性傲慢,尤其是在当前增强技术呈现出其特有的力量时产生的普遍傲慢情绪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人文主义哲学思考所要求的。
可见,在人类增强自身的前提下,傲慢的心态是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性的傲慢所指向的普遍情绪通过技术与心理等两种因素被放大,继而形成了技术性傲慢与文化性傲慢的形式。那么这种傲慢的技术基础是什么呢?
三、傲慢表征的技术基础
要理解傲慢得以可能的技术基础,首先应回答增强技术带来了什么?增强技术以何种方式表征出了傲慢?这是本部分要考察的问题。
(1)提高机能。很显然这是增强技术带来的成就之一。这也是2002年美国报告《用以增强人类功能的技术的汇合:纳米技术、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NBIC)》的显著成就,即通过上述汇聚技术提升人类的身体机能。同样的想法也渗透到欧洲。2020年一份欧洲报告《2020—2040科学与技术趋势:探索前沿》指出,利用遗传修饰、药理学制剂、机电设备和神经学接口增加人类生理和神经学性能,使其超出人体的正常生理和认知范围。这两份报告无疑都是通过各种最新技术来突破人体原有的机能,比如让身体力量增强、负载力加大等。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一种提升,所以足以成为自我展示的资本之一。
(2)精准控制。随着基因工程、光遗传技术的出现,人类对生命进行精准控制已经成为可能。卡尔·德赛若斯(Karl Deisseroth)指出,光遗传技术的核心是“在时空意义上的对细胞信号的精确的因果控制,有助于科学家发现神经系统的功能,甚至非神经系统的功能”。(17)Deisseroth, K.Optogenetics, “10 Years of Microbial Opsins in Neuroscience”, Nature Neuroscience, 18(9), 2015, pp.1213-1225.这种技术目前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在记忆研究、视力研究中已有成效。
(3)生命衰老的改变。改变生命延缓变老的药物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突破,比如谷歌公司下属机构Calico 已经公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干预人类身体老化的物质 ABBV-CLS-7262。谷歌称这种物质能在 3 天内逆转小白鼠大脑老化过程。目前该物质正进入I 期临床试验阶段。还有一些药物,如雷帕霉素、senolytics、二甲双胍、阿卡波糖、亚精胺、NAD + 补充剂和锂等,均可用于抗衰老。(18)Partridge, L., Fuentealba, M. and Kennedy, B.K., “The Quest to Slow Ageing Through Drug Discovery”, Nat Rev Drug Discov, 19, 2020, pp.513-532, https://doi.org/10.1038/s41573-020-0067-7.这些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令人兴奋的。可以想见,这样的药品如果合法上市,会引起怎样的社会效果,人类可以通过生物医药技术控制和改变衰老,又会滋生怎样的傲慢。
(4)跨物种跃迁。跨物种跃迁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是对人类增强的一种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于合理的技术想象。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人类增强是人类机能的提升。这个观点实际上也说明了人体机能的提升始终是量的累加,比如负载力。根据我国技术监督局1990年的一份报告《体力搬运重量限值》中的数据显示,男子单次搬运推拉物体的重量不能超过300千克,女性是200千克。(19)1990年4月23日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的李天麟、于永中起草该标准,1991年1月1号正式实施。这个国家标准是根据科学计算方式得出的。而通过外骨骼技术,推拉物体的重量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值。这种增强方式属于量上的增强,而并非质的飞跃。但是未来人类增强可能会出现跨物种跃迁的现象。人体增强会通过机体的结构性变化而使功能也发生极大变化,比如不借助望远镜,人可以看到很远的对象。
(5)增强的智能。这是出现在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朱迪·胡为兹(Judith Hurwitz)等人看来,所谓增强智能是指“一种使用人工智能来执行良好定义的任务,例如作为决策活动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人类与机器一同合作,人类需要评价自动任务的结果、在特殊环境中的决策以及评估由于商业需求的改变而导致数据必须被改变的情况”。(20)Hurwitz,J., Morris,H. Candace Sidner_ Daniel Kirsch, Augmented Intelligence—The Business Power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CRC Press, 2020, p.2.可以看出,这里的智能增强实际上是着眼于应用的,即自动机器参与到人类决策中。这个过程被称之为增强的智能。(21)作者分析了弱增强和强增强两种不同类型,在他看来,弱增强意味着将原先由人类劳动者执行的任务自动化;强增强使用AI技术,把AI与人类评估联合起来改变商业过程。
(6)社会关系的解体。关系论对人类本质的界定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的一面,这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技术增强。首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曾提出,“人从现实性上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成为社会学反思的重要基础。但这种反思过于宏观,让我们无法贴近人本身。相比之下,人与他者的关系显得更为根本。在这种关系中,自我的一切活动都会对他者形成影响,因而需要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调整自身。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利科提出的“自身、亲者和他者”中。来自第一人称的现象学视角要比第三人称的社会哲学视角更贴合人本身,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增强。其次,人是处于技术之中的存在者。正如维贝克在《将技术道德化》一书中提出的,人类总是在与他们使用的技术关系中形成自身。这并不是一种反思式的关系描述,海德格尔提出的“人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总是容易让人着迷,但却无法将二者之间的构成澄清。由于人是关系性的存在,那么技术增强对关系性存在产生的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
以上六个方面阐述了增强技术以何种方式表征出了傲慢。此外,傲慢是文化性现象,从神话、理性到科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傲慢不断增生的过程。这意味着现代科技并不是傲慢产生的原因,而是傲慢滋生的场域。
四、记忆:一种什么样的解药?
哲学史上,柏拉图最先把药以辩证法的方式予以讨论。他在《斐德罗篇》中谈到了书写技艺,并将这一技艺看作是药。他将写作(writing)看作是Pharmakon,这个词可以衍生出很多含义:处方、解药、良方、解救、拯救、毒药、诱惑、魅力、魔力、表象、欺骗、危害、威胁等。柏拉图认为,文字会让人产生依赖,从而忽略了记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像毒药一样,让人上瘾;但文字却能够让口语文化保留下来,让语言永恒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像解药一样,破解了语言容易消失的魔咒。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后来被法国哲学家充分发挥出来。利科在《记忆、历史与遗忘》中讨论了历史究竟是解药还是毒药的问题:“历史书写本身到底是良药还是毒药?这个问题同历史中所使用的诞生概念的歧义性一样需要受到重视。”(22)[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与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及后来的文章中也讨论了技术既是解药又是毒药的问题。与先验记忆相对,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作为傲慢出路的记忆。如果我们把傲慢看作“病态”——虽然这种看法多少有些问题——那么记忆是一种怎样的解药?缘何其摆脱了上述悖论?
前面展示了技术作为解药与毒药的双重性,于是从源头看,一切都变得清楚起来。我们发现,在不同民族文化中,技术都是英雄偷盗过来的东西,来自于神。这种起源说清楚地表明了技术是神性与物性的统一。物性体现的是事物本性以及加工之后的功能性。这种属性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比如眼镜让我们看清楚远处的东西。这个角度呈现出技术的解药的属性;但是另一方面,神性也是被忽略的东西。在传统社会中,与技术相伴随的文化、价值性与功能发生了抽离,换句话说,技术的功能性从价值性的场域中脱身而去,变成了孤立的存在。价值性对于现时代的人来说,无疑是毒药。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自动门的存在是为了显示神的伟大:神的力量可以让庙门自动打开。但是如今自动机器、智能机器的出现,其目的却仅仅局限于人类的需要。这无疑是过量服用了技术之药。由此可以看出,技术之药性与毒性并不是两种异质的东西。技术的功能性是其药性的根本,比如眼睛看不清楚,可以用眼镜来调整视力;抑郁症的人可以用神经元刺激技术或者药物来治疗。技术的毒性并不是来自这种功能本身,而是来自对这种药物的过分依赖。
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普遍情绪——傲慢,我们就可以理解其中的内在关联,技术可以解决人类自身面对的问题,并由此带来了文明和进步,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理性值得自傲的地方,这是技术的药性体现;如果从自然状态出发点来说,我们就会引入人类增强的范畴,在这一范畴下,技术的作用是提升和增强生命体的机能。但是,从增强本身来说,如果我们追问增强目的何在,那么主体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23)2018年,在世界哲学大会的“人类、非人类、后人类”分组讨论会上,伯根大学哲学系教授拉斯·弗·斯文狄森(Lars Fr.H.Svendsen)提出的观点和笔者有一些相似,在他看来,对“成为人”的最好理解是通过归属和认可去理解,这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表达。他认为,在未来非人类与人类、人类与后人类之间的界限将是模糊的。在笔者看来,社会关系会成为上述界限重建的根据,但是这一点尚需进一步论证。另外,这个会议的主题不足在于忽视了“常人”的讨论,因为在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窥见本真性的表达。尼采的超人理念会显示出人类的内在本性,意志本身就是在其增强过程中成为自身的。这是生命本身表现出来的必然性。至于后来唐娜·哈拉维等人提倡的赛博格、后人类形象等都是从形式上呈现了不同于“常人”(24)对于常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张志伟把“常人”理解为大众、公众;张汝伦将常人理解为引导此在之物,他分析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常人的六个特征:疏离、平均状态、抹平、公共性、解除存在负担和迎合。参见张汝伦《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的共在、此在、自我存在与在世存在?》,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f145dbb0102yuh2.html,2018-05-03;张志伟《海德格尔的常人和向死而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e510fe0102ww2i.html,2017-07-13。的样式。相比传统技术而言,增强技术的发展无疑会增进人类傲慢的表达。
如何应对傲慢这一普遍情绪呢?在傲慢的三种样式中,技术性傲慢显然无法提供有效的观念,无论是一般技术还是增强技术都是基于功能性之上,在工具论的理解中,技术功能性直接强化了傲慢的表达;而技术作为根据展现自身时,其实体性力量更是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傲慢本身。那么心理性傲慢如何呢?面对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事实状态,人类心理会发生变化是较容易理解的。无所不能的技术导致了傲慢的社会心理。我们可以从文化性傲慢中找到内在的克服之路,这就是记忆因素。利科的哲学提供了一个基础:通过记忆来对抗反思傲慢。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哲学史上的五个与记忆研究有关的重要人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胡塞尔、利科与斯蒂格勒。柏拉图的戒指印痕对记忆的保留特性做出了形象的比喻,这个思想影响到了后来的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中对记忆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关于回忆与记忆的区别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来胡塞尔的讨论。但这两位古典哲学家的研究最终都消失在知识海洋之中。后来胡塞尔对记忆的讨论将记忆的时间性给予了清晰的分析,可惜的是,这种分析后来迷失在知识论中;斯蒂格勒对记忆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胡塞尔色彩,他对滞留的分析成为第三记忆的前提。以上四位哲学家虽然在记忆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将记忆看作一种对抗的方法,而是把记忆纳入知识发生的维度中,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记忆附属论”。唯有利科将记忆看作是对抗反思傲慢的方法,这个观点将理性时代的病灶与病源揭示出来。可以说,记忆是对抗傲慢的有效方法,是医治傲慢病症的良药。
利科与斯蒂格勒同时从诊疗学的角度对记忆加以阐述分析。利科的批判是指向现代理性的,他将现代理性的傲慢反思特性剖析出来,从病理学-诊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25)他专门分析了自然记忆的滥用:被压抑的记忆、被操控的记忆和被过度控制的记忆,参见利科《记忆、历史与遗忘》,第87页。,并建立起了一个基于伦理-政治的规范视角,从而试图构建“负有责任的记忆”。斯蒂格勒的批判是基于药理学的,试图为“被计算的时代”开出药方。
综上所述,将记忆看作是克服反思理性傲慢的做法是有哲学上的根据的,利科的记忆哲学显然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其对傲慢的丰富性显然估计不足,正如本文所揭示的,在增强技术背景下,文化性的傲慢所指向的普遍情绪通过技术与心理等两种因素被放大,继而形成了技术性傲慢与文化性傲慢的形式。而在技术性傲慢和心理性傲慢的克服上,记忆作为一种克服之道也只是在奠基意义上成立,尚需进一步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