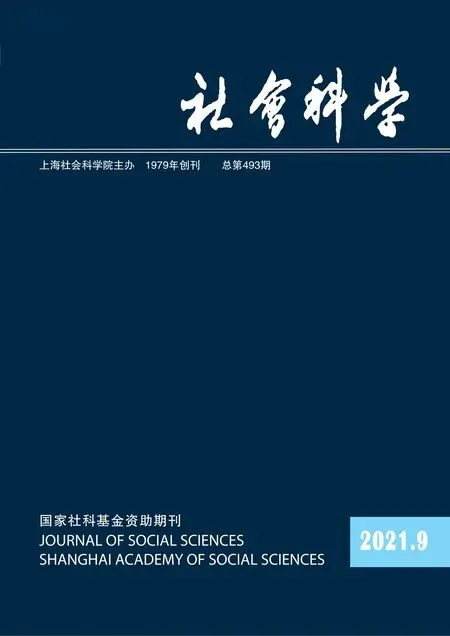论清代海塘技术选择背后的环境与政治因素*
王大学
以往水利技术史研究多关注技术本身,对技术传承、技术官僚和技术选择驱动力方面的探讨却不多。每次大型水利工程的技术选择除受客观环境影响外,更多受政治因素所左右。马俊亚认为,在河工问题方面水利史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史。(1)参见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夏明方强调水利史的政治维度,从“自然之河”走向“政治之河”。(2)夏明方《从“自然之河”走向“政治之河”》一文,是他为贾国静的专著《水之政治:清代黄河治理的制度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与《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所作序言。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政治史研究,需对决策和实施过程所涉历史背景、君臣想法以及相关人际网络进行综合分析。当涉及大型公共水利工程中的技术选择问题时,需增加政治与环境两个维度。技术是对客观环境的具体应对,但针对同一环境而进行不同技术选择时,往往受诸多政治、社会因素影响。这一现象在清代两浙海塘中间接护岸工程技术究竟采用石坝还是柴盘头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
陶存焕、周潮生初步研究了乾隆朝柴盘头与石盘头的争论,认为这是关于挑溜问题的技术性争议。(3)陶存焕、周潮生:《明清钱塘江海塘》,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3页。和卫国认识到范公塘一带石坝与柴盘头的争论是在乾隆“一劳永逸”的海塘追求遭到挑战后引起的又一异常波澜,对该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单地视为单纯技术性探讨,需从乾隆朝治水全局高度去审视和理解争论背后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在石坝和柴盘头的反复争论中,高宗君臣对治水问题的思考和处理越来越理性,尤其是经过反复辩驳之后得出石塘、石坝均属激怒水势、与水争地的结论表明君臣对钱塘江治水问题的思考再次升华。(4)和卫国:《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246页。但是,作者过于关注十八世纪清政府的“现代政府”特征而忽略了政治运作中的帝王心术和臣下应对,在没有搞清楚相关十二座石坝建设原因及过程的情况下便直接展开对这些石坝的讨论,再加上史料解读方面的问题,使得他的分析出现了偏差。
笔者拟对清代两浙海塘中范公塘附近石坝、柴盘头究竟谁挑溜更为得力问题的争论进行深入挖掘,分析范公塘各石坝建立的具体原因和过程,复原柴盘头取代石坝、石坝又取代柴盘头以及最后石坝被彻底废弃的宏观历史背景、人事因素及河工技术的潜在影子,展示水利史研究中技术、环境与政治因素的复杂交织。
一、技术性选择:石坝取代柴盘头
钱塘江河口动力强劲、复杂,河势变化无常,岸滩经常发生淤伸、坍退,海塘随着岸滩的变化而有时安全、有时危险。唐代以来的海塘以土塘为主,五代开始不断探索和改进塘型结构,直到元末,也只有钱塘江南岸部分地段在桩基上以长方形石料间层纵横叠砌为塘。(5)陶存焕、周潮生:《明清钱塘江海塘》,第11页。随着钱塘江大溜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岸滩变化,从明初开始在海盐一带险要地段改筑石塘,在塘岸崩毁之后,内筑新塘并保留旧塘作为外护保障,同时致力于探索改进塘身主体结构和砌筑工艺。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在晚明形成了五纵五横的鱼鳞石塘技术。(6)陶存焕、周潮生:《明清钱塘江海塘》,第20页。但是,鱼鳞大石塘技术耗资巨大且石料采运困难,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大规模展开。
随着康熙末年钱塘江主泓道全趋北大门,北岸险工地段的石塘建设方才又被提上议事日程。雍正朝的两浙塘工建设与他统治两浙的政治问题密切相关,他曾经有“吏治、海塘乃两浙第一要务”的说法。(7)王大学:《雍正朝两浙海塘引河工程中的环境、皇权与满汉问题探讨》,《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雍正末年的浙北鱼鳞石塘计划,到乾隆前期方才完成。随着乾隆十三年(1748)大溜重归中小门,两岸边滩平稳达十年之久。(8)王大学:《“天赐神佑”:乾隆十三年钱塘江“潮归中门”的过程及其政治意义》,《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此后,钱塘江大溜重返北大门,虽然第三、四次南巡中乾隆均想在浙北大修鱼鳞石塘,但是因为自然环境和钉桩技术的限制而只能以“维修柴塘”为主。(9)和卫国:《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第162-195页。从乾隆第五次南巡开始,才真正开始大规模兴建鱼鳞大石塘。鱼鳞大石塘有一套复杂的防御体系,其中柴盘头和石坝均是其间接护岸工程的一种,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范公塘石坝与柴盘头之争反映的是海塘间接性护岸工程的技术选择问题,其起因与钱塘江自然环境变化密不可分。乾隆四十三年(1779)以后,范家埠对面新涨阴沙离塘渐进,与北岸头围新涨阴沙夹峙,潮溜直射塘根,章家庵、范家埠成为险工。(10)范家埠石坝工程的自然环境变化的诱因,参见(清)琅玕纂《海塘新志》卷3《形势》,载《钱塘江文献集成》第1册《钱塘江海塘史料》(一),杭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169页。当时,在西北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乾隆帝,重新开始关注两浙海塘工程。此前,由于政府精力主要放在西北,乾隆暂时放松了对两浙塘工的大规模投入。乾隆四十五年(1781)第五次南巡时谕令:海宁绕城鱼鳞石塘内20余丈条块石塘、陈文港附近一百五六十丈石塘改建为鱼鳞石塘并添建坦水,石塘以上柴塘4200余丈中如有可改建石塘处即拨帑金赶紧兴筑。(11)(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载《钱塘江文献集成》第4册《钱塘江海塘史料》(四),第194页。
当时,除柴塘改建外,其他地方海塘的维护措施是柴塘修建盘头、石塘修护坦水。十月,由于范公塘是民间自筑土塘,塘身低薄且系活水流沙,巡抚李质颖补筑宿字号至天字号柴塘220丈,天字号以西老土塘添筑柴塘500丈。海宁西塘潮神庙以西调字号至往字号柴塘之外原准备建竹篓为外护,现塘外水势湍激,需改建木柜。这些地方均修筑木柜,共1080余丈。(12)(清)琅玕纂:《海塘新志》卷5《修筑二》,第184页。十一月,由于章家庵外中沙阻隔,在添字号以西添建柴盘头一座,添字号柴塘后建筑抢险条块石塘以西100丈、以东200丈。木字号柴塘间段拆镶280丈。十二月,在添字号柴塘增建抢险条块石塘的东西两侧各增建柴塘100丈。(13)(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195-196页。
此处所谓的柴盘头挑溜技术来自河工。柴盘头名为磨盘埽,又称丁厢,主要运用在正溜、回溜交注的地方。这种埽工大多是半圆式的,上水迎正溜,下水抵回溜,一工两用,主要运用在深水大溜。该埽体积比其他埽工大好几倍,“费料颇巨”。(14)《中国河工辞源》,载《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三),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622页。
很快,与以往主要运用柴塘和盘头相比,总督富勒浑借用了更高级、更有效但也更费钱的间接护岸工程技术。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富勒浑奏请建筑仁和范公塘挑水石坝一座。(15)(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196页。挑水坝是河工中一种重要的挑溜技术,又名顺水坝、鸡嘴坝或者马头,原来主要用在黄河迎溜之处。挑水坝长十余丈至二三十丈不等,伸至河心,能够挑溜,溜以下堤脚可免冲刷并能挂淤。如果险工太长,应做挑水坝数道,将空档排开,远近得宜,使上坝挑溜接住中坝,中坝挑溜接住下坝,可以保证堤岸安全。(16)《中国河工辞源》,载《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三),第640-641页。富勒浑选择采用挑水坝,主要是因为范公塘附近海岸坍塌难以处理,在乾隆重视海塘并将塘工看作自己不朽基业的情况下,务必用各种办法来保证塘工安全。
尽管开始出现挑水坝,但范公塘附近仍多采用柴盘头挑溜。正月二十六日上谕:除抢修石塘外,新筑的两座盘头的顶冲处的险情没有章家庵严重,建议在章家庵赶筑盘头一座,使溜势向外挑开。(17)(清)琅玕纂:《海塘新志》卷5《修筑二》,第185页。二月份,在黄字号大小赶筑盘头一座、章家庵盘头以西七十丈处添筑盘头一座,上下挑溜。(18)《清高宗实录》卷1124“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丙辰”条,第23册,第31-32页。这两座盘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三月份,章家庵东首新建盘头以来,溜势渐向南开。范家埠对面旧涨阴沙两块,北面小的一块已刷尽,南面大的阴沙刷低,盘头外渐有嫩沙。(19)(清)琅玕纂:《海塘新志》卷5《修筑二》,第187页。
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十六日,户部尚书和珅、兵部左侍郎曹文埴奏请在《一统志》中专列一卷,记载南巡时直隶、山东、江苏和浙江等省河工、海塘事务。(20)《清高宗实录》卷1151“乾隆四十七年二月癸未”条,第23册,第418-419页。此后,乾隆对海塘的重视又多了一层政治含义,保证塘工安全是彰显南巡效果的最佳方式。
十月,总督陈辉祖奏请修筑东西两塘的柴塘及坦水,范公塘首冲处接筑埽工140丈、建盘头一座,镶筑潮神庙、普尔兜和马牧港三处的柴盘头。陈辉祖还停修章家庵附近实践无效的木柜,建议仍照前任总督富勒浑的做法添建盘头、接筑护沙埽牛。(21)(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200页。随后,缓停范公塘前添建盘头。陈辉祖命人在仁和西塘头围江海交接处开挖引河750丈,范公塘一带溜势渐缓,贴近埽牛柴工间有沙淤,范家埠对面阴沙也有刷动。(22)(清)琅玕纂:《海塘新志》卷5《修筑二》,第190页。
乾隆四十八年(1783)正月十五日,上谕:明年正月南巡并指示河工、海塘的善后。因为上次南巡时亲自指示的高家堰石塘、徐州城外石堤矩工现在大功告成,浙江4200多丈柴塘改建为鱼鳞石塘的工程也将完成,“不能不亲为相度”。(23)(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201页。因而,海塘成为两浙关注的重中之重。
在此大背景下,范公塘第二座挑水坝是由乾隆遥控指挥并亲定地址的。当时,新任巡抚褔崧奏请在仁和县由民、灶人等呈请自修范公塘土塘1500余丈。(24)《清高宗实录》卷1172“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丁未”条,第23册,第725页。范公塘未建柴塘的地方离水甚近,先后已接筑柴塘300丈,该处埽牛被潮汐冲击,用竹篓木柜沉石下水但难以抵御,且不能签桩,容易被冲。该处埽工用五六丈的木船装满石块,沉到水底,块石叠压其上,堆出水面,藉护塘根。在第一座石坝挑溜基础上,拟于沉船处顶冲建挑水大坝一座。上谕:同意建挑水坝但觉得海塘图内所绘筑坝之处稍微偏北,朱笔标记改在迤南地方筑挑水坝;沉船维护塘根方法甚好,奇怪的是富勒浑、福崧此前并未奏及;沉船维护塘根并非一劳永逸之计,章家庵以东普建石工方能永保安澜,章家庵以西仅凭范公塘一道形势单薄,明年南巡时亲自阅视是否一律改建石塘。(25)(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202页。西塘范公塘的塘根危险仍没有彻底解除,四月,在范公塘埽工处又沉船8只,加上此前的沉船34只,总共沉船42只。(26)(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203页。
其实,乾隆已决定在范公塘改筑条块石塘。六月六日上谕:老土塘的塘根土性松浮,添筑柴工不能御潮,需一律改建石塘。修建条块石塘所需经费不过鱼鳞石塘的三分之一,明年南巡亲自勘察后再行筹办。次日,上谕:昨天谕令富将范公塘一带一律改建石塘。今年把物料准备齐全,明春南巡时现场视察后降旨开工,一年内即可完工,封疆大吏对于事关民生之事断不可心存畏惧。(27)(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203页。总督富勒浑、巡抚褔崧开始吹捧乾隆改建范公塘一带海塘的策略。(28)关豫编纂:《续修浙江海塘通志初稿》之《海塘三》,载《钱塘江海塘史料》(六),浙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92-93页。
但是,范公塘海塘改建难度大,因为江中新涨阴沙,大溜顶冲附近的维护是海塘改建的前提。七月,根据圣谕,巡抚福崧在第二座石坝以南添设一座挑水坝。坝基长11丈有余,宽10到12丈,接筑埽工470丈,接镶柴塘连接土堤170丈。截至六月底,共沉船73只,下石12000余方,计长106.8丈。(29)(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204页。八月,福崧奏请在西首柴塘以西首冲处建石坝两座,连前共筑石坝五座。在随后的四个月内,未经上峰批准,福崧每月建造一座石坝:九月,在第五座石坝外添建滚水石坝一座;十月,在第六座滚水石坝之外增建石坝一座;十一月,在第七座石坝外增建滚水石坝一座;十二月,在第八座滚水石坝之外增建石坝一座。私自增修石坝的做法为将来奏销埋下了隐患,因为这些都未按程序上报。(30)(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204-205页。
从技术层面看,这次密集建设的石坝中出现了滚水坝。滚水坝也叫减水坝,主要功能是分杀水势。坝基必须选择要害卑洼处坚实地基,先下地钉桩木,平下龙骨木,石底垒砌,雁翅宜长宜坡,跌水宜长,迎水宜短,均用立石栏门桩数层,其他钉桩均需要用悬硪钉下。连雁翅共长三十丈,坝身根阔一丈五尺,收顶一丈二尺,高一尺五寸,迎水阔五尺,跌水石阔二丈四尺。(31)《中国河工辞源》,载《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三),第694-695页。挑水坝和滚水坝的交替建设,组成了维护海岸与海塘的有机技术组合。
需注意的是,当时选择连续修筑石坝是客观自然环境、政治大背景与施工便利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福崧接连数月密集修筑挑水坝和滚水坝,是因为范公塘临水处有潮沟,沉船施工的同时必须用挑水坝、滚水坝来缓解潮势对石坝周边的冲击。当然,福崧此举是因为乾隆明确表示来年南巡要亲自视察范公塘并宣布此处改建石塘,在乾隆亲临范公塘之前必须保证此处万无一失。另外,当时在大规模修筑石塘,石料采运源源不断,利用石料建筑石坝相对容易。石料采运是一个综合的复杂工程,涉及石料开采、沿途运输、工所堆放等。在石料运输繁忙的同时,无暇从事柴薪运输,否则运石船和运柴船将在塘工附近随塘河上拥挤堵塞,也无充足空间堆放。
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中,乾隆对柴塘改建石塘的工作不满且把决策责任推给臣下,命令在范公塘改建石塘,五年内完工。(32)(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206页。三月二十四日,御制《南巡记》,强调自己历次河工、塘工决策的正确。(33)弘历:《南巡记(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见《清高宗实录》卷1201,第24册,第62-63页。因而,保证范公塘顺利改建是首要任务。福崧继续修筑石坝来挑溜。六月,福崧奏请在第九座石坝以西增建石坝一座,用石堆出水面并安置木柜,挑溜非常得力,又接筑埽工1005丈。(34)(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7《国朝修筑》,第206页。八月初一,上谕福崧回奏任内未经题请建设的塘工问题,其中包括范公塘以西的四座石坝。(35)《清高宗实录》卷1262“乾隆五十一年八月辛丑”条,第24册,第990-991页。
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巡抚琅玕上奏:章家庵以西接筑柴工1005丈,塘根临水,中段回溜冲激更厉害,应遵旨于朱笔圈记处添筑挑水大石坝一座,以挑溜南行。乾隆同意建设大石坝并强调抓紧办理原定急工。乾隆念念不忘范公塘改建条块石塘之事,让琅玕随时查勘,如果水势渐近,土塘难以抵御,即奏请接筑。如果该处沙涂依然宽阔,仍照前议停止。琅玕寻奏:范公塘外头围缓工现可停办,倘若水势逼近随时奏请兴工。得旨:若有此情形,即当速奏,一面备料请旨。(36)(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七《国朝修筑》,第207-208页。
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二月,琅玕奏报范公塘以东章家庵石塘工尾斜向西南至朱笔圈记处鱼鳞大石塘建成,共长2120丈。(37)(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七《国朝修筑》,第209页。
二、政治性考虑:从石坝改筑柴盘头到柴盘头改筑石坝
乾隆的本意是柴塘后面建设石塘,以柴塘为外护,既能保证石塘安全,又能避免因柴塘岁修而造成的柴薪价格上涨。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柴塘仍需岁修,这从侧面说明了乾隆决策的失误,他在无奈之下批准了柴塘的岁修专项银。(38)王大学:《制度背后的技术、环境与政治:以清代柴塘岁修专项银设立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3期。但是,对于间接护岸工程——坦水、盘头的选择,则产生了不小的风波。
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琅玕在京面奏:范公塘首冲之处旧设的十一座石坝不如柴盘头有益。石坝系用碎石沉入海边,叠出水面后用栅栏木柜装载碎石排列,再用碎石围绕堆护根脚,不能排钉木桩、无法用灰浆浇灌,潮大猛涌时易泼损,碎石入海难捞,运石重修费力且不能经久。经两年查勘筹划,将石坝与柴盘头对比后,发现柴盘头比石坝的效果更好。柴盘头钉木作桩根脚坚固,柴性柔软耐冲且与水性相宜,风潮大汛不致冲散,间有矬蛰可随时修筑,比较便利。现存十一座石坝中被冲损者改建柴盘头,尚属完固者待将来应修时按各处形势一律改建柴盘头,不必再做石坝。(39)《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四年三月浙江巡抚觉罗琅玕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3-1035-02。四月,乾隆允准。(40)《清高宗实录》卷1327“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条,第25册,第975页。
表面看来,此次用柴盘头来取代石坝是技术方面的考虑,其实,琅玕的这一举动有复杂的制度背景。乾隆五十一年(1786),经君臣反复角力,设立初次商息银,作为老盐仓以西柴塘岁修专项经费。(41)陶存焕、周潮生:《明清钱塘江海塘》,第44-45、119-121页。此时,石坝三年保固期限已过,如若继续维修石坝则费用高且报请手续麻烦,改成柴盘头则可以从柴塘岁修银中直接支出。
当年,乾隆要过八旬万寿,他认为自己一生功德圆满,尤其海塘、河工,是他极为骄傲的南巡功业。四月丁未,策试天下贡士,文曰:“海塘之筑一劳永逸,要未尝非疏沦与堤防并用。朕数十年临视图指,不惜数千万帑金以为闾阎计,大都平成矣。”(42)《清高宗实录》卷1327“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丁未”条,第25册,第956页。可见,海塘在无形中被赋予了更多政治含义。此后,乾隆对海塘更为关注。当海塘新涨阴沙有利于北岸海塘保护时,乾隆就把这归功于神灵保佑。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西塘潮神庙至乌龙庙随塘涨阴沙5700丈,宽200-1590丈不等。针对此,上谕:范公塘一带以西随塘涨出阴沙,以东一带自必逐渐涨长,对面南岸阴沙日渐坍卸,更足以保卫民生,此皆赖神灵保佑。于是,令琅玕亲到潮神庙虔诚告祭答谢神灵。(43)(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八《国朝修筑》,第213页。
本来,范公塘附近间接护岸工程之事已完结,但随着福崧重任浙江巡抚,石坝和盘头之争又起。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一月,福崧重任巡抚后旋奏:海塘近年岁修不善,柴塘、石塘泼损矬蛰之处甚多,前任巡抚琅玕并未亲自查勘据实奏报,目前预备分别缓急次第兴修。这对乾隆震动很大,因为柴塘专项岁修银设立说明乾隆此前海塘决策失误,只不过君臣对真相都秘而不宣。但是,这始终是他内心的一根刺。现在看到琅玕在海塘管理中玩忽职守,君心的震怒可想而知。上谕:塘工乃浙江第一应办要务,琅玕应随时查勘据实上奏,但安坐衙署并不前往阅视,对保卫民生之事全不关心。将福崧原折钞寄琅玕阅看。福崧务必将应办各工次第经理。(44)《清高宗实录》卷1367“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乙巳”条,第26册,第344-345页。次年(1791),福崧在范公塘首冲地方捐建挑水石坝一座,以确保头围老沙不被刷动。除修筑埽工盘头外,维修章家庵以西添字号、元字号盘头各一座。(45)(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8《国朝修筑》,第215页。按:和卫国认为,《海塘揽要》卷八中对于这座石坝修筑时间的记载有误,并根据录副奏折中长麟的奏折来反推该坝建造于乾隆五十六年而非五十七年二月(和卫国:《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第236页)。其实,仔细阅读杨鑅书中乾隆五十七年二月该条史料即可知道他说的是去年(乾隆五十六年)的事情,史料并无错误。
如前所述,琅玕担任巡抚时曾把褔崧修筑的多座石坝改为柴盘头,但现在褔崧又恢复自己的主张。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福崧奏称:范公塘一带水深溜急,不能钉桩下埽,故建筑石坝挑溜。后因石块容易冲失,经琅玕奏准修筑时改筑柴坝。停修以来石坝多有坍损,若改筑柴盘头需柴甚多,第二、第十大坝均为顶冲且挑溜极为得力,第二坝乃当年秉承圣意而建,坝基坚固,弃之可惜,率同司道将石坝如式捐修,以资捍卫。上年新筑之坝已经有效保护头围老沙,现按年修补,不用动项开销。其余坍损各坝现非顶冲,该处柴坦既然开始次第镶修且足资抵御,尚不用亟行改筑盘头。(46)(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8《国朝修筑》,第215页。
面对范公塘附近海塘间接护岸工程技术选择的再一次变化,乾隆心中疑云再起,委派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二月二十四日,上谕:关于范公塘一带石坝、柴盘头,琅玕主张放弃石坝而维修柴盘头,褔崧主张舍弃柴盘头而维修石坝;柴盘头易镶筑,遇潮水冲刷坍损不难修补,石坝以碎石堆积做基,难以钉桩护脚,不能持久,遇潮水冲卸石块沉入水底,无从查验,容易浮冒经费;柴薪为民间日用必需,改筑柴盘头需柴甚多,每年坝工多费一万斤柴薪则民间即少一万斤之用,会导致柴价上涨;建筑石坝需工料较多,承办之员会藉此开销浮冒。乾隆命令江苏巡抚长麟亲到杭州范公塘查勘石坝与柴坝各自的优缺点,绘图贴说据实覆奏;查勘建筑未久的十一座石坝为何多有坍损,是否从前经手各员办理不妥。(47)《清高宗实录》卷1397“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癸亥”条,第26册,第763-764页。
三月,长麟回奏说石坝利于挑溜且现在坝基稳固,停修以来坝顶木柜多有冲损,原建小坝顶上本无木柜,坝顶石块虽有汕刷但修补尚易。柴坝不宜施工,坍塌的石块仍在坝基左右,不能钉桩下埽,范公塘一带多有因保护塘根而沉船载石之处,难以在旧坝附近移建柴塘。长麟认为,与柴盘头相比,石坝具有以下优点:第一,石坝挑溜较柴盘头得力。柴坝深入水中最大不过五六丈,石坝入水二十丈,坝基愈长挑水愈远。第二,石坝的坝基比柴盘头巩固。海底沙性疏松,柴塘以桩埽为基,一经汕刷就需抢镶。石坝沉船载石为基,堆积石块增高出水,体重根牢,平时潮浪不能摇撼,风潮汹涌不过顶上木柜和浮置碎石易被冲损,不会全部漂没。原筑石坝过去多年而坝基稳固,柴塘一遇风排浪涌常常会被拔桩走埽,飘荡全无。第三,石坝主要使用石材而非像柴盘头那样使用柴薪,有利于民间柴薪的使用。不过,长麟修改了石坝上面木柜的形状,他认为水性宜顺不宜拂,挑水坝宜斜不宜直。现存坝基上窄下宽,坝基系圆形的坦坡式样,圆形有斜向之势,改变了潮水方向,原筑坝基不致全部坍损。坝顶木柜向系三面安设,排作四方形势,潮水由东而西,木柜面向正东,与水硬相冲抵,旧存木柜受损严重。全部改为圆形则担心可护塘而不能挑溜,最好将其改为三角形,侧身让水,尖形坝嘴挑水更远可更好地保护坝塘。(48)(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8《国朝修筑》,第216-217页。
据此,乾隆对琅玕异常恼火。三月二十日,上谕:范公塘一带大小石坝需略为修补,柴工不如石工,不知从前琅玕为何轻易更张改为柴工,改用柴坝后也不注意修理和维护,导致坝工坍损;传谕琅玕明白回奏从前奏请改石坝为柴盘头但又不修理的原因,抄寄长麟和福崧的原折给他看。(49)《清高宗实录》卷1399“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己丑”条,第26册,第783-784页。
次日,皇帝又下一道长谕,批评长麟在调查中刻意包庇琅玕。乾隆委派长麟前往考察,是希望全面总结两人所议得失,但是,长麟只声称宜用石坝而没有提及柴坝,也没有指出琅玕原办错在何处,明显是要回护调停。乾隆指出需要弄清楚以下问题:第一,琅玕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奏请将石坝改用柴坝至今已三年,是否将此项柴坝开工修筑;第二,福崧抵任一年有余,为何现在才将应行修筑石坝处具奏,任期内是否按照琅玕所办修理柴坝;第三,此项坝工既然是为挑溜护塘,无论用石或柴自应随时修整,为何两年内任其坍卸,若是无关紧要之坝就不该多此一举,徒滋靡费。(50)《清高宗实录》卷1399“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庚寅”条,第26册,第785-786页。
四月初五日,福崧上折解释修筑石坝的原因以及近几年的维修情况。乾隆五十一年(1786),石坝、柴坦均有沙涂拥护,无须动项兴修。五十四年(1789)琅玕奏准将冲损石坝改为柴坝,因潮神庙以西一带阴沙增涨而并未动工。五十六年(1791)五月梅雨较多,涨沙逐渐刷减,沙势坍涨靡常,备料防范。致字号埽工间段临水、江海神庙以东至朱笔圈记之石塘工尾旧筑埽工亦临水,此处紧接头围,抢筑时在顶冲处捐筑挑水石坝一座。本年正月,坝后1100余丈柴坦亟需镶修,见坝基坚固,废弃可惜,奏请捐修石坝。坝顶安设木柜是因块石堆出水面易被泼卸,将木柜连排安置填入石块,用铁鑻搭钉,“以期体重关拦”。(51)《宫中朱批-水利》,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五日浙江巡抚福崧奏,档号:04-01-05-0076-041。
结合褔崧、长麟的奏折,乾隆认为此前琅玕把范公塘石坝改为柴盘头的建议错误。四月十五日,上谕:此项石坝原为挑溜,琅玕在任时应于奏请后修理柴工,若是无关紧要之工就不应该妄议更张。琅玕在巡抚任内对海塘要工并未实心经理,传旨严斥并令其据实回奏,抄寄福崧原折给其阅看。(52)《清高宗实录》卷1400“乾隆五十七年四月癸丑”条,第26册,第810-811页。四月二十二日,皇帝再次命令琅玕回奏为何当年轻易奏请将石坝改为盘头、被谕允后未照章修补以致坝工现在有所坍损,把长麟、褔崧原折抄送给琅玕。(53)(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8《国朝修筑》,第218-219页。
面对乾隆的斥责,闰四月二十五日,琅玕上折承认不熟悉塘工并请求处罚。琅玕声称在任数年,因石坝上碎石堆积,木柜易于坍卸,需随时修补,看到章家庵一带原建柴盘头较耐冲刷,认为如果将石坝次第改建为柴工,水性相宜,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京陛见时奏请改用柴工,并声明冲损者改建柴盘头、尚属完固者待应修时一体改建。后来,西塘一带原涨阴沙高阜宽广,十一座石坝外面沙涂尤为宽广,坝身巩固。“臣糊涂之想”,既然涨沙拥护且该处非顶冲,完整者不用改建、间有冲损者可缓修,未敢改拆,待将来涨沙被冲刷再行改筑。从前请改石坝为柴坦是未曾通盘筹划即冒昧陈奏,阴沙外涨后未及时奏明暂缓改修,“以致上烦睿虑,糊涂错谬,实属咎无可辞”。(54)《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琅玕奏,档号:03-1038-026。
这道奏折有一点耐人寻味,表面看起来琅玕选择柴盘头代替石坝是简单对比的结果,琅玕忽略了潮势变化导致险冲地点的转移,是明显不懂塘工技术的表现。但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如前所述,当年琅玕奏请将石坝改为柴盘头,是因为当时奏销中批评石坝费用过大,改为柴盘头可以避免受到这种批评,而且利用柴塘专项岁修银报销起来更方便。令琅玕没想到的是,此事会出现这么大的反转,在被乾隆严斥的情况下,只能低头承认是自己的错误,以免因为自己强行争辩而招来更大的祸患。
闰四月二十七日,上谕肯定褔崧在范公塘修筑石坝的做法,同时乾隆修改了石坝做法。石坝常用碎石沉入海边,叠出水面,但碎石大小不等,恐根脚不能坚实,应捡取较大石块放入竹篓沉入海底,坝基更牢。此时的乾隆在两浙海塘问题上非常倚重福崧,福崧正月奏请来京陛见,批令略迟待数月,以便做好沿海塘工的防护抢修;福崧尚未起程的话,待伏秋大汛平稳后于十月间到京陛见;如在来京途中则不必转回,俟陛见后速回浙江。(55)(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8《国朝修筑》,第219页。五月初九,福崧上折逢迎皇帝:将竹篓较前放大装满石块沉入海底做挑水石坝的坝基,“洵为经久良法”。(56)《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初九日浙江巡抚福崧奏,档号:03-1038-024。
可惜,不久之后乾隆对福崧的态度便急转直下。五月十七日,五百里加急谕斥福崧速回浙江严审巡洋署守备林凤鸣插手民人争夺纲地一案并妥善处理海塘石坝事宜,如果福崧有紧要事务可上折奏明。福崧在奏报启程日期的奏折内声称并无要事,“因犬马恋主之心梦寐不能自己”,乾隆认为福崧并未在内廷行走也并非久未觐见,实在是自作多情。福崧原来曾在浙江巡抚任上犯错,被派到新疆效力赎罪。因一时没有合适人选,开恩让其回任。福崧此前对石坝的处理尚为留心,接到令其缓行陛见的谕旨后仍奏请面圣,实乃不知轻重缓急。接到本谕旨后,福崧必须立刻返回浙江。福崧原奏办理石坝必需将大块石料抛入,略小之石装入竹篓沉放海底,乾隆认为大块石料散抛水中仍有可能被冲失,建议将大石一并装入竹篓。(57)《乾隆朝上谕档》第十六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30页。因而,褔崧七月份在海宁城东西首冲处各建挑溜石坝一座。(58)(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8《国朝修筑》,第220页。
褔崧的为官艺术之低,在塘工方面一再暴露。乾隆对范公塘改建一直有决策失误方面的担忧,此时不宜再有塘工。可是,九月十一日,褔崧奏称:绍兴府萧山县荷花池、张神庙和闻家堰三处坐当顶冲,拟借项赶办并将海塘购办柴薪就近截留应用。这一不合时宜的举动,让乾隆勃然大怒,上谕:江潮大溜趋向萧山,此或南坍北涨的好机会,荷花池等处为何借项抢筑?北坍南涨需修塘工护卫省城,南坍北涨又在绍兴一带兴工,如果都像福崧这样,塘工修建永无结束之时,这可能是地方官藉词兴工冒销。(59)《清高宗实录》卷1413“乾隆五十七年九月癸亥”条,第26册,第1011页。十二月初八日,福崧上折:承认南岸塘工稳固,荷花池系西江塘工程,今年山水较大潮势旺盛,遂有冲坍。害怕民修迟缓,借项修筑,照例输还归款。(60)《宫中朱批-水利》,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浙江巡抚福崧奏,档号:04-01-05-0077-014。乾隆认为福崧所奏南岸工程系民修江塘,为江浙濒临江湖地方常有之事,与海塘工程不同,不宜混淆。(61)《清高宗实录》卷141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戌申”条,第26册,第1054-1055页。
这时候乾隆只是批评福崧塘工规划不合适,待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二月福崧等人侵挪盐政库项及福崧贪墨案爆发以及次年(1793)二月福崧被斩之后,(62)《乾隆朝惩治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70-3371页。石坝问题又起波澜。
三、技术、环境与政治交织的结果:石坝终被废
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月,新任巡抚长麟奏称:去年三月海潮大溜正走北岸,石坝挑溜得力,经奏明于五六月间将坍损的第二、三、九、十等坝捐修齐整,第一、四、五、六、七、八、十一等坝尚未兴修,六月在海宁镇海汛建石坝二座。今溜势南趋,无溜可挑,各坝维修暂缓,以节省经费。(63)《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抚长麟奏,档号:03-1068-003。值得玩味的是,福崧被斩后,石坝挑溜的做法被抛弃,长麟对范公塘首冲的防护是新筑埽工并修两道月堤。(64)(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8《国朝修筑》,第221页。
为保证范公塘持久稳固,七月二十四日,长麟奏称:范公塘头围沙涂刷动,应自原筑石塘工尾至乌龙庙筑石工2900余丈,需银约120余万两。但是,乾隆的塘工政策开始收缩。八月十八日,上谕:范公塘一带石塘,前经勘明涨沙宽阔,不必接筑石工,已降旨停办。该处旧涨阴沙存500余丈,自三官堂至乌龙庙尚有老沙1800余丈。前有三官堂新筑月堤,后有老土塘,即使三官堂以东至江海神庙涨沙刷减,形势稍觉单薄,不妨察看情形,或可以酌情把工程减半,章家庵石塘工尾接筑到三官堂的工段不过长麟原计划的三分之一,需银三四十万两即可,已在图内朱笔点出。海塘沙水靡常,如果三官堂以东现有新沙足资保固,此项塘工亦可缓办。如果必须筑堤,不可因此旨而惜费不筑。传谕长麟、浙江巡抚吉庆知之。(65)《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寅”条,第27册,第181-182页。当时长麟已升任两广总督。
九月初四,长麟奏请将范公塘原有十二座石坝以及镇海汛石坝的坝身收窄收低。旧坝连坦水直出宽十余丈至五丈不等、高二丈八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坝身木柜二层,太宽太高,不如收窄收低,水流顺轨直趋,不致迎激为患,并请将未修的七座石坝一律改为入水宽五丈围圆斜坡,比柴盘头约低四尺,顶上不安设木柜,类似滚水坝。每座石坝需银三四千两,费用不及大坝四分之一。如果收窄收低后的确有效果,此前已经维修的五座石坝将来修葺时亦照式改做。东塘镇海汛新建石坝二座尚未完竣但有泼损,坝身过于高宽,只要添筑滚水小坝即可。将此两座石坝收作入水五丈,围圆斜坡,收分到顶,身高较石塘低四尺,不必安设木柜。(66)《宫中朱批-水利》,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四日浙江巡抚觉罗长麟奏,档号:04-01-05-0076-039。该举措的实质是把挑水坝改为滚水坝。
对于这种技术上的变动,乾隆让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阿桂等认为:石坝乃护塘要工,最好不要轻易改动;长麟所奏系就目前情形而论,请饬令新任巡抚吉庆留心察看坝身收小后是否有效果,如果可行,就先将未修石坝七座奏明改修,已修五座将来修葺时照式改做。(67)《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八年大学士阿桂等奏,档号:03-1040-038。
按常理,经大学士、九卿议定后就由下面直接执行了,但乾隆不动声色地否定了众臣的建议。十月初五日,上谕:大学士、九卿议覆长麟奏酌减海塘石坝工程一折,从来治水之道以顺其性为要,若拦截抵御则水势激怒,不免泼损。建筑海塘原为保障滨海民生,柴、石塘工已属于与水争地,今添建石坝高二丈八尺至一丈五尺,直出十余丈至五丈不等。十二座石坝的长度累计不下百余丈,逼靠塘身,占水之地更多,导致水势直接冲击坝身,工程因而受损。此前福崧任巡抚时,不认真处理地方事务而只知婪索牟利,仅凭属员怂恿就添建石坝,筹办失当。长麟不熟悉塘务,恐亦无真知灼见,此处降低尺寸的做法不过是权宜之计;新任巡抚吉庆平日办事虽尚明白但并不熟悉塘工,谕令南河总督兰第锡、东河总督李奉翰到浙江勘察塘工。河海情形不同而水性相同,如何因势利导推类而知。现早过霜降,河工无事,李奉翰即日到京陛见,然后会同兰第锡、吉庆详细履勘后,迅速覆奏处理结果:此项工程应否照旧建筑,抑或按长麟所奏酌减丈尺,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办理。此次核议一折,待兰第锡、李奉翰等详勘覆奏后再降旨,以便坝工应修应停得有定见,以免无益工程激怒水势,屡有泼损。(68)(清)杨鑅辑:《海塘揽要》卷8《国朝修筑》,第223-224页。
这道上谕让兰第锡和李奉翰明白乾隆目前的塘工策略是维持现状和以小修小补为主,十一月十六日,兰第锡、李奉翰和吉庆上折彻底否定石坝并建议改回柴盘头。石坝既不签桩也不灌灰浆,碎石铺底,高出水面后排放二三层长宽各一丈、高五尺的木柜在碎石上面,然后将块石载入铺平顶面,每逢大汛风潮则木柜破损,碎石倾卸。十二座石坝内有九座现在并非迎溜,应听其废弃。长麟此前请修的七座石坝残损不堪,乾隆五十七年(1792)新修的五座也有破损,不过,其中的第二、十和十二坝地处迎溜,整体坚固,应暂存,将来大汛破损时则不必再修。柴盘头比石坝容易修理且节省经费,柴性柔软与水相宜,石坝横亘水中易激怒水势,一旦损伤不能随时修补,徒劳无益。三人奏请现存三座石坝将来坍损即改建为柴盘头,所需柴薪不多,尚不至于妨碍民用。东塘新建两座石坝均在迎溜,本年稍有泼损但紧靠石塘宽厚坚固,应暂保留,将来一律改建柴盘头。“塘外石坝办理本属周章,遇有风浪泼损,不能及时修整,实属无益。”(69)《宫中朱批-水利》,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南和总督兰第锡等奏,档号:04-01-05-0076-040。
虽然这道奏折揣摩圣意后否定了福崧以往修建石坝的做法,但乾隆仍不满意,他将此折交原议大臣议奏,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批评李奉翰并未领会圣意,李奉翰没有根据此前面谕将石坝是否与水争地以致冲激损工之处讲清楚。这十二座石坝均系福崧任巡抚时添建,后经长麟查勘后奏请收窄,石坝过于宽高,与水冲击后易被泼损。乾隆批评三人奏折中措辞模糊,容易误导人们认为长麟请修的七座残损石坝是长麟奏请修筑。乾隆把石坝决策失误的问题都归于福崧,认为福崧担任巡抚的时候只知道自己贪污谋私利,不亲自勘察海塘事务,受属员怂恿而轻率添建石坝。乾隆认为石工奏销重而柴工奏销轻,不用柴薪又可方便小民生计,福崧在利用施工谋取私利的同时,还博得了考虑民生而不用柴薪的美名。乾隆把矛头直指李奉翰,认为三人联合奏折中没有一字提及福崧从前草率建设石坝的事情,问题出在曾受面谕的李奉翰身上,兰第锡只是由其转告,吉庆不过随同查勘。李奉翰对面谕内容全未领会,不过联衔上奏就草率完事,传旨严斥李奉翰,将此旨交长麟阅看,“想长麟亦必当心服也”。(70)《清高宗实录》卷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壬子”条,第27册,第245-246页。
兰第锡等人奏折中并没有把责任推给长麟,但是,乾隆把石坝修筑的责任推卸给福崧并痛骂李奉翰等人没有批评福崧,皆因福崧再次触动了乾隆关于海塘决策的敏感神经。福崧在其贪墨案的供词中谈到赔偿塘工被罚银之事。除兰州案件赔付外,福崧更大部分的赔付与其浙江巡抚任期有关,尤其是海塘与仓库亏空赔付银占比很大,这无疑让乾隆对福崧在塘工中的事情更加关注。(71)《乾隆朝惩治贪污档案选编》,第3355-3356页。皇帝因厌恶福崧而恨不得否定其在塘工中的任何举动,以此来反证福崧该死。乾隆也从侧面打听了浙江地方对处斩福崧的看法。(72)《乾隆朝惩治贪污档案选编》,第3372-3373页。这两种举动的目的相同。
被乾隆痛骂后的长麟迅速复奏说石坝应尽废,承认自己未想到石坝与水争地的层面。长麟声称只是因为担心石坝废弃致柴工失去外护或有坍塌,所以奏请收窄收低石坝。顺着乾隆的意思,长麟说废弃石坝将不会与水争地,即使柴工因无石坝障护而稍有矬蛰,可以用修石坝的钱粮来修补柴工,节省经费且与修石坝相比患少益多。(73)《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两广总督觉罗长麟奏,档号:03-1041-010。
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月,看到长麟恳切承认错误并逢迎自己,上谕:长麟覆奏前次只议收窄收低石坝而未曾想到与水争地一层,恭绎谕旨,实为心服,可见从前多建石坝未免与水争地。海塘系浙省要务,必须筹划尽善,以资经久;巡抚吉庆要详查该处石坝是否应遵照前议酌减废去,断不可拘泥前旨,稍有迁就。(74)《清高宗实录》卷1445“乾隆五十九年正月乙卯”条,第27册,第281页。在这道上谕中,乾隆既肯定了建筑石坝做法的错误,又非常模糊地给了新任巡抚吉庆灵活处理这件事情的空间,这样就免除了将来自己出现决策错误的可能。其实,吉庆已揣摩到乾隆此前对石坝问题的真实态度及其原因,在此道上谕之前,正月十三日,吉庆疏称:范公塘十二座石坝内除第二、十、十二坝均系贴近要工挑护得力外,其余九坝听其废去;东塘海宁州石坝二座暂留,统俟应修时一律改作柴盘头。二月初五日,上谕:此折未绘图呈览,该处情形尚欠明晰,吉庆将此项石坝何处应留、何处应废及塘工溜势情形绘图贴说进呈。(75)《宫中朱批-水利》,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十三日浙江巡抚吉庆奏,档号:04-01-05-0079-034。吉庆复奏:西塘十二坝内第二、第十和第十二坝均系迎溜,其余九坝均在塘身弯进处且相隔甚近有占水势,听其废去;东塘海宁州石坝二座贴近州城左右,塘身突出,藉以保护,绘具图说进呈。(76)《清高宗实录》卷1446“乾隆五十九年二月癸亥”条,第27册,第288-289页。
此后,在海塘危险地方主要添设或修筑埽工,石坝被抛弃。这种间接护岸工程选择的变化,与其说是技术上的问题,毋宁说是政治因素所导致的人为的技术选择。
结 语
作为两浙海塘的主要间接护岸工程,以往一直被使用的柴盘头被石坝取代,与自然环境变化、海塘重新受关注密不可分。第五次南巡后,臣工知道乾隆希望借助塘工来建立不朽功业,因而,务必要保证塘工安全,范公塘附近石坝取代柴盘头就是表现之一。范公塘石坝的大规模建筑主要集中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因为乾隆明确提出将于次年第六次南巡,于是福崧接连修筑石坝以保此地万无一失。另外,当时在大规模修筑石塘,利用石料建筑石坝比较容易。琅玕奏请在石坝保固三年期满后,将石坝改为柴盘头,表面看起来是技术选择的变化,实质上是经费报销制度变化的后果。因为,乾隆本意是在柴塘后面建设石塘以图一劳永逸,但其决策失误,无奈批准柴塘岁修专项银,这样柴盘头的工费报销更便捷。
重任巡抚的福崧再次奏请废弃柴盘头而改用石坝,引起乾隆警觉,因为八旬万寿时的乾隆认为海塘是自己值得骄傲的功业,不允许塘工中有任何差错。作为钦差的江苏巡抚长麟调查后支持石坝,同时建议改变石坝上木柜的做法。乾隆痛斥琅玕轻易改弦更张,谕令改动坝基砌筑技术。福崧被斩后石坝挑溜的做法即被抛弃,新任巡抚长麟借助河工技术在险工地段增筑月堤,并奏请将原有挑水坝改为滚水坝。乾隆命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群臣认为缩小石坝形制要谨慎。不过,乾隆否定了众臣的建议,委派南河、东河两位河督亲自勘察。尽管两位河督揣摩圣意并彻底否定石坝,但乾隆仍不满意,痛斥两位钦差没有彻底指出福崧建设石坝的根本错误在于“与水争地”。柴塘改建石塘的决策错误乃君臣共知而未曾明言,乾隆趁机把胸中恶气全部撒到福崧身上。最终,石坝被废弃,这一持续十多年的柴盘头与石坝之争尘埃落定。
乾隆朝关于范公塘附近修筑石坝还是柴盘头更为适宜的问题之争,折射出古代大型公共水利工程建设中技术、环境与政治交织的复杂关系。有时候,技术选择背后的政治和制度因素比技术本身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