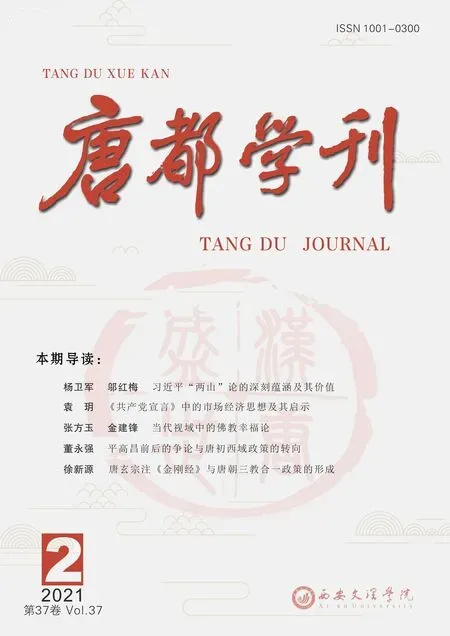金代诗人史肃的优游气度与诗歌创作研究
薛宝生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史肃,字舜元,京兆人。生卒年均不详,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进士(1)薛瑞兆先生据史肃《哀王晦》一诗“平生况且同年义”之句考得,参见薛瑞兆《〈中州集〉小传校札》一文,载于《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元好问所纂《中州集》卷5有传,云:“史御史肃……天资挺特,高才博学。作诗精致有理,尤善用事。古赋亦奇峭。工于字画。业科举,为名进士。……历赤县及幕官,入为监察御史,迁治书。出刺通州,大中党狱起,为所诖误,谪静难军节度副使。大安初,召为中都路转运副使,超户部正郎。复坐镌,降同知汾州事,卒官。舜元素尚理性之学,屏山学佛自舜元发之。晚年颇喜养生,谓人可以不死,尝欲弃官学道,而竟止于此,可哀也已。”[1]诗集《澹轩遗稿》不传,今存诗30首。以上为史肃生平及著述情况,关于其人其诗研究,除元好问“作诗精致有理,尤善用事”之论外,成果寥寥(2)薛瑞兆先生《〈中州集〉小传校札》对其生平事迹有补充研究。另外,侯震博士《金章宗明昌进士研究》一文从“记事抒情”“咏物抒怀”等方面将明昌进士诗歌创作进行了横向梳理,涉及史肃诗歌,然非专人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史肃诗歌中表现出的哲理思想、气度、意趣如何,亦鲜有关注研究者。
一、释、道兼蓄,而尤重禅
史肃平生思想,从上文所引“理性之学”“屏山学佛自舜元发之”“学道”等描述,可以略窥一二,大抵释、道兼修,前期喜释门之学,晚年笃信仙道之术。而观其仅存之诗,字里行间儒家之迹不显,而佛、道之痕颇彰。总体来说,其诗表现出借诗体禅或体道的倾向。
关于体禅,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诗中运用诸多佛家词汇、意象(如“明镜”“尘埃”“见性”“参禅”“比丘”等)来阐扬禅理。其《复斋》一诗云:“身似卧轮无伎俩,心如明镜不尘埃。”[2]389此处化用《坛经》(3)卧轮、神秀禅师分别云:“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慧能大师驳之曰:“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参见慧能《坛经》,丁福保笺注,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9、9、80、12页。中典故,言自性本清净如明镜,不受镜像(世事)纷扰。又《读传灯录》云:“处世若大梦,学禅犹小乘。早知文字悮,更用读传灯。”[2]387此处,颇能体现禅宗“不立文字”的宗旨。又《方丈坐中》云:“水底游鱼真见性,树头语鸟小参禅。”[2]386“见性”“参禅”,皆开悟之境,此处指因观鱼、鸟之自在而得自在,鱼、鸟“见性”“参禅”,即是人之“见性”“参禅”。又《登悯忠寺阁》云:“聚土闲童子,移山老比丘。能除分外见,寸木即岑楼。”[2]387“分外见”,即分别心。“寸木”句,语出《孟子·告子下》(4)《孟子·告子下》云:“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8页。,而假之以禅意,意谓人只要消除分别心,回归到本质上来看问题,方寸之木和擎天之楼在其根本属性上并无不同。
其二,禅与诗对举,而言诗思难成。《杂诗二首》其一云:“禅心已作沾泥絮,诗思浑如上水船。”[2]389“禅心”句取自参寥子“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风上下狂”[3]一联,意谓心性沉寂了悟不为外物所动而生种种念想。“上水船”,逆水而行之船,用五代姚洎事,喻诗思艰难迟钝。此处诗人自况,指于禅事修习已通透,而于诗事却一筹莫展。又《别怀玉》:“蜂腰鹤膝曾搜句,兔角龟毛不论禅。”[2]385“兔角龟毛”,语出《大智度论》,又见《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5)《大智度论》卷12云:“又如兔角、龟毛,亦但有名而无实。”见乾隆大藏经本,第78册,第335页。又《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1云:“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象,名为一切,汝不著者,为在为无,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乾隆大藏经本,第47册,第8页。。 “兔角”“龟毛”之属,虽无实,而有名,因而不可谓之真无。事实上,真无遍诸有。史肃此处用“蜂腰”“鹤膝”“兔角”“龟毛”之典,意谓为诗因忌犯“蜂腰”“鹤膝”之病而搜肠刮肚,苦于不得,亦如执着于“兔角”“龟毛”之虚无而不能悟得真无而达禅悟之境。
在禅心了悟之后,诗人“晚年颇喜养生,谓人可以不死,尝欲弃官学道”,表现在诗中则体现为道家“外形骸”式的生活状态。一方面是其“学道”所悟,另一方面也是对仕宦人生跌宕起伏的重新认识。
首先,对于学道,其诗中有所提及。根据“颇喜养生,谓人可以不死”,此“学道”似乎是修习道教炼丹长生之法。此论缺少充分材料支撑,仅元遗山片语如是说。此外,其《发脱》云:“衰发从今不须脱,少留衰白戴黄冠。”[2]389“黄冠”显然不是《礼记·郊特牲》中所谓“黄衣、黄冠而祭”[4]之祭祀所用服帽。结合其传“尝欲弃官学道”,此处当指道教修道之人的冠冕。而其诗中则更多地表现出道家思想的濡染。如《物化》一诗:
物化能忘我,天游不用心。膻香群蚁聚,树静一蝉吟。
败井劳深汲,荒庭阙近寻。枕书聊假寐,夕日半墙阴。[2]387
诗中多处化用《庄子》中的典故(6)《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庄周梦为胡蝶,……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外物》云:“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庄子·徐无鬼》云:“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羶也。”郭庆藩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2、935、864页。。如“物化”出自《庄子·齐物论》,天游出自《庄子·外物》,“膻香”句出自《庄子·徐无鬼》。此诗从题名到作意皆受《庄子》影响,意在消除嗜欲(即“膻”)而归于“静”,精神上消弭物我界限而为一(即“物化”),无所用心而与自然融汇共游(即“天游”)。
其次,对于人生的通透体悟,可以《放言二首》其二为例来说明。诗云:“清风明月无人管,茶鼎熏炉与客同。壮岁羞为褦襶子,而今却羡嗫嚅翁。”[2]388“褦襶子”原出晋程晓《嘲热客诗》“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一联(7)参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8页。,本意为衣着粗厚臃肿不合时宜的人。史肃此处却用陆游《夏日》诗中“褦襶”之意,指戴凉笠(褦襶)的渔翁(8)陆诗云:“孤舟正作笭箵梦,九陌难随褦襶忙。团扇兴来闲弄笔,寒泉漱罢独焚香。”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5页。言史肃用陆游诗,原因一,史肃“茶鼎熏炉”句与陆诗“寒泉漱罢独焚香”所言之事之趣相同,史言“茶鼎”,陆言“寒泉漱罢”;同谓饮茶,史言“熏炉”,陆言“焚香”;原因二,陆游生活在(1125-1210)间,而史肃主要活跃在明昌(1190)以后,且宋金使节往来频繁,兼之当时刻印出版发达(北宋苏辙使金,金人就曾言《眉山集》行于金地多时,详苏辙《论北朝事宜劄子》)。陆诗传至金地,自不在话下。故言用陆诗意。。“嗫嚅翁”,语出《旧唐书·窦巩传》(9)刘昫《旧唐书·窦巩传》云:“(巩)性温雅,多不能持论,士友言议之际,吻动而不发,白居易等目为‘嗫嚅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22-4123页。,史肃此处非徒羡巩氏“吻动而不发”般的“嗫嚅”,而是羡其久放外臣,远离政治权力斗争中心的处境。窦巩晚年在武昌有《放鱼》诗云:“金钱赎得免刀痕,闻道禽鱼亦感恩。好去长江千万里,不须辛苦上龙门。”[5]史肃的仕宦经历与窦氏此诗所言非常切合。史肃两次坐事罹祸,九死一生,故而羡慕窦巩所云“长江千万里”深隐之鱼,不愿纠缠仕途。《金史》卷12载:“八年春,……通州刺史史肃……坐于蒲阴令大中私议朝政,皆杖之。”[6]282-283又《金史》卷99:“尚书省奏其罪,铎进曰:‘昻等非敢议朝政,但如郑人游乡校耳。’上悟,乃薄其罪。”[6]2194可知,泰和八年(1208)这次获罪,非当时参知政事孙铎代为陈情,几于不免。再回头看史肃“壮岁羞为褦襶子,而今却羡嗫嚅翁”一联,从“而今”与“壮岁”对举可知,《放言二首》乃其晚岁之作,深明佛理而笃信道学,故于进退出处亦看通透。
从以上分析中,足见史肃用事婉转深密,正好印证元好问“精致有理,尤善用事”之言,然这只是抓住了史肃诗歌的显性特点,而关于其诗内容意趣以及诗中展现出的理想人生气度却并未囊括。
二、气度优游从容,有类宋儒
史肃诗深受释、道思想之濡染,其诗中也透露出一种颇类北宋士大夫般的情怀气度。这种气度突出地体现在其《方丈坐中》一诗:
纸本功名直几钱,何如付与北窗眠。诗书作我闲中地,风月知人醉里天。
水底游鱼真见性,树头语鸟小参禅。平生习气莲华社,一炷香前结后缘。[2]386
该诗后两联言禅事,而首联、颔联却是儒家士大夫积极用世外表下的精神内里写照。诗书、风月、美酒,自足自适,庶几曾点之适、颜子之乐。读到这首诗,便会使人很自然地想到北宋程颢的《秋日偶成》: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7]
此二诗既有很大相同处,又有些许不同处。相同之处在于诗中所描绘的从容面对生活的内容、方式及精神意趣;不同之处在于施行从容面对的主体范围。
从容面对的内容:“纸本功名”与“富贵贫贱”,此无需多言。从容面对的方式:“付与北窗眠”和“睡觉东窗”。“北窗眠”“东窗眠”无关乎休憩的方位,只代表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如元好问在评陶渊明诗时云:“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8]60无论“北窗眠”“东窗眠”“南窗眠”,都一样。未看透“纸本功名”“富贵贫贱”时,它是一种机械的生活方式。修养通透后,它是一种自适、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其《次韵安之饮酒》云:“日上南窗已数竿,醉头扶起不巾冠。”[2]386此处又作“南窗”,可见其乐在于“眠”所代表的这种生活方式,随处“眠”而可乐,可乐的时候还可以移床就景,管他哪个“窗”。如《夏夜》云:“移床就佳月,引袂纳凉风。”[2]387
精神上的优游与万物生息一般自得,无论“水底游鱼”“树头语鸟”,还是“四时佳兴”“风云变态”,不管是在禅理中解脱“见性”,还是在“理性”的从容中自得,都殊途同归。事实上,对于程颢,后人也多有儒表佛里之议。
所不同的是施行从容面对的主体范围:在史肃的诗中我们隐约看见一个人的自得,恍如陶渊明式的。如孙康宜所言,陶渊明居于喧嚣而能超脱,保持一种“和自己在一起”(being-with-oneself)的感觉[9]45。 在史肃的诗中,我们也能找到这种自传式的抒情模式,也能体悟到诗人“和自己在一起”的感觉。这一点我们从其《杂诗二首》其一便可窥得:“春江日暖舞清涟,客舍萧萧一缕烟。幽鸟隔林招我醉,小桃当户为谁妍。禅心已作沾泥絮,诗思浑如上水船。却是官闲得无事,一帘红雨枕书眠。”[2]389诗中描写了一幅从容萧散的生活情境:春江日暖,烟随风起,鸟儿纵情歌唱,桃花灼灼绽放,世事已然悟透,所事唯吟诗之好,吟而不得,风吹桃花雨,枕书自眠。这是诗人的抒情式自传,是对其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诗人“和自己在一起”,尽情地享受春日的美景,一人独得其乐,耽于吟咏,如同鸟儿享受春光而纵情鸣唱一般。
而在程颢的诗中,我们仿佛看见一类人的自得,自得到可以作为一种精神范式。这一点可以从“与人同”“男儿到此”的语气中得到证明,“与人同”,自不必说。“男儿”,在此指的是一类人。这类人的从容自得类似于《论语·先进》中曾皙描绘的那个“浴沂咏归”(10)《论语·先进》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页。的诗意境界。朱熹发明此境云:“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10]涵泳于理性,从容于生活,如此而已。
三、诗酒风流的人生逸趣,颇似陶潜
观《全金诗》可知,金代作家在诗歌中称咏最盛者莫过于陶潜、白居易,尤以陶为最。称陶者,多以“拒宋之节”及“悠然任真之趣”为主(11)不事二姓如郦掖《题献陵梁氏成趣图》云:“渊明耻折腰,眷然歌归欤。”白华《题靖节图》云:“咄哉灵运辈,危坐衣裳辱。何如五柳家,春雨东皋绿。”赞其道趣如高士谈云:“巷陋颜子乐,地偏陶令心。”赵沨《新凉》云:“可人陶靖节,随意葛天民。”庞铸《漉酒图》云:“我爱陶渊明,爱酒不爱官。……望望孤云翔,羡羡飞鸟还。”金诗中涉及以上两方面的诗句众多,兹不赘举。。史肃作为金代作家的一员,自然也会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现存30首诗中,明确提到陶渊明1次,《放言二首》其一云:“莲社从来说陶远,竹林今不数山王。”[2]388其《澹轩遗稿》已佚,全貌不可得见,但称咏陶潜当不会少。就现存诗看,其中所描绘的生活隐隐然有陶渊明的影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一系列意象的使用有陶之印迹;其二,其诗入理处颇与陶相似。
(一)“黄花”“飞鸟”“酒”等意象的使用
这几种意象都是陶渊明所惯用且生活中常见或必须(12)酒、菊,是其生活所必须;飞鸟,是其生活中常见;倚南窗,是其自适之状态。如《归去来兮辞》中所描述:“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1页。,于史肃亦然。如果单言一种意象,或不能判定其有陶的影子。若这几种意象同时出现,再加上其所描绘的生活状态及自然情态,就有理由怀疑其中有陶渊明的影子,且亦如陶氏所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1]89。
孙康宜认为陶渊明自传式的诗歌叙述于自然物中有隐喻,在特定的自然物和陶氏本人之间可以画等号[9]26。而史肃诗中“飞鸟”的意象运用,也是如此,甚至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状态的写照。如:
午梦初回乌鸟乐,小亭斜日柳阴阴。(《山阴县》)[2]386
忘形沙鸟知人意,窣地山云不世情。(《宿睦村》)[2]386
晴云入户团倾盖,飞鸟随人作好音。(《偶书》)[2]388
“午梦初回”感受到“乌鸟乐”,其实就是诗人自己内心之乐的反映,上文提到不管南窗北窗,随所“眠”而皆可乐,乐是因这种自适自得的生活状态而乐,一如禽鸟。“忘形沙鸟知人意”,本该是人知沙鸟意;人“忘形自得”,眼中沙鸟才“忘形”,才能“随人作好音”。
言“黄花”(即菊花)。如《早出遵化》云:“强颜红叶自由舞,野性黄花无赖香。”[2]386红叶自由,黄花无赖,皆仰归自然而生息,或随风轻舞,或迎风飘香。又《杂诗二首》其二云:“迎风紫苋因循老,背日黄花次第开。”[2]388“因循”“次第”,皆依循自然规律而开谢之谓。特别是《放言二首》其一,褒扬陶渊明之节,而以菊花做喻。其诗云:“莲社从来说陶远,竹林今不数山王。家鸡野鹜何须较,秋菊春兰各自芳。”[2]388陶渊明不入莲社,故云“说陶远”;山涛、王戎先避世而后投身司马氏集团,为后世诟病,故云“不数”。诗人内心是想过陶氏一般的生活,像菊花一般拥有“自芳”的品质。约与史肃同时的王特起,其《漫作》一诗云:“北阙上书吾老矣,东篱把菊思悠哉。竹林留得巨源在,莲社招入渊明来。”[2]321可见,陶渊明式的生活状态,确是金代后期诗人的人生理想。
又藏身醉乡的“酒”咏。陶渊明“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12]而史肃亦嗜酒,诗中也多言“酒”,如:
诗书作我闲中地,风月知人醉里天。(《方丈坐中》)[2]386
千克的出生地为法国。1799年,法国科学家提出了千克的最初定义,即1立方分米纯水在最大密度(温度约为4摄氏度)时的质量为1千克。很显然,最初的质量单位千克是由法国的长度单位米推导出来的。
日上南窗已数竿,醉头扶起不巾冠。(《次韵安之饮酒》)[2]386
寒食清明少天色,孤居未要酒杯深。(《偶书》)[2]388
草玄只拟关门坐,好事应从载酒游。(《次张信夫韵》)[2]388
萧统《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寄酒为迹也。”[11]10陶氏寄酒为迹,史肃亦然。故《次韵安之饮酒》云:“玩世惟知酒功圣,藏身无似醉乡宽。”[2]386
(二)入理之处
元好问谓史肃“作诗精致有理”,却未明说其如何有理。观其诗可知,其“有理”之处也似陶渊明。“东坡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13]卷三,507
“采菊”一联,“落世纷深入理窟,但见万象森罗,莫非真境,故因见南山而真意具焉。”[13]卷四,515在《饮酒》诗中,陶氏由“菊”“山”“飞鸟”等意象而悟自然生息之“真意”,描绘出了一个现实参与道的自然人之乐。在史肃的诗中也隐隐然有此番之悟,其《宿睦村》云:“檐马丁东风外响,田车历辘月中行。忘形沙鸟知人意,窣地山云不世情。露草霜筠有幽意,诗题分付候虫声。”[2]386诗人也由“檐马”“田车”“候虫”之响、“沙鸟”“山云”“露草”“霜筠”之态,而悟自然之“幽意”。所不同的是,史肃想将其用诗语表达出来,而陶氏则“欲辨已忘言”。
陶言“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11]90史肃《感兴》云:“一轩吾事了,无意竞纷华。”[2]388此二联皆有寄于一轩遗世远俗,而获独善自得之意。陶氏可赏菊饮酒而遗世,所谓“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11]90史肃欣悦秋果累累、园葵花灿而远俗,所谓“避俗嫌高绝,干荣耻盗夸。树果蕃秋实,园葵粲晚花。”[2]388
陶言“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11]93,史肃《道傍柳》云:“人生非金石,长短百年寿。功名与富贵,于身亦何有。古人随物化,今已柳生肘。”[2]386此诗虽化用《古诗十九首》之《回车驾言迈》(13)《回车驾言迈》云:“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句,却反“荣名以为宝”之意,而与陶氏此诗中的“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11]93意同,这是连番坐事遭贬谪后,对出处进退及人生价值的清醒认识。
四、禅道了悟如此,诗人心性难却
其《杂诗二首》其一云:“禅心已作沾泥絮,诗思浑如上水船。”此句正是史肃老来人生的真实写照,由于颇尚佛老之学,于禅、道已了悟,加之连番坐事遭贬,使得诗人心境豁达,看轻功名利禄,人生通透。所谓“麒麟阁上功名字,不博生前一笑欢”“一轩吾事了,无意竞繁华”“纷纷宠辱人间世,付与浮云任去来”。既然看轻功名,何妨高卧安适、狂歌痛饮,然其偏偏却痴迷于诗。于是,通透人生的涵养遇到动情为之的诗,却便也难脱传统诗人的情结。因而,屡屡“苦吟”,“秋”“枯败”“老”等意象便频频出现在诗人的笔下,无意中投射出一种王朝末世的士人心态及自怜之情。
由歌吟风月诗酒渐成癖瘾,而陷苦吟。其《次张信夫韵》云:“锦囊诗句年来满,供尽闲花野草愁”[2]388,此意亦如姜夔评诚斋云:“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14]卷下史肃此处虽次韵张信夫,未尝不是自况。其《立秋日》云:“年衰犹健饭,官达也穷愁。……个中诗句在,倚杖得冥搜。”[2]389此处言“官达”却又云“穷愁”,观后句乃知,“穷愁”因“冥搜”诗句而生。又《早出遵化》云:“山好未忘三日雅,诗穷赢得一秋忙”[2]386,直言其穷乃在“诗穷”。“冥搜”苦吟而陷“诗穷”,几吟而成癖、成“病”。其《发脱》一诗云:
年年道路少清欢,处处葵蔬馈薄飡。月色过窗同夜梦,霜华著壁独朝寒。
求医未有诗千首,破老惟消竹数竿。衰发从今不须脱,少留衰白戴黄冠。[2]389
诗人“薄飡”而“少清欢”,根本原因在于“吟病”,从“月色过窗”到“霜华著壁”,由夜至朝,皆诗人所历,从侧面道出了诗人对诗事的执着。种竹为易事,养竹看长可颐养雅趣,展颜破闷,消弭衰颓之气,而“吟咏”这种“吟病”呈“贪”状,乃难事,受诗魔驱使而成“贪病”,非穷吟尽咏不能根除,也因而陷于“诗穷”。
虽然诗人的修习,使得其能从容自处,几乎不直言国事(从现存诗看),但生于人间世,终逃不出传统诗人所特有的多愁善感、一叶知秋的敏感心性。除“边愁故未已,不敢恨长途”[2]385“丰年不救两河饥,腊尽才看小雪飞”[2]390两联,余诗皆不及国事忧患,似乎已看透兴亡争战,如其《杂诗二首》其二所云:“世事翻腾只如此,吾生弃置已焉哉。”[2]390然而传统诗人吟咏的惯题却无法回避,如闻一多先生所云:“黄昏与秋是传统诗人的时间与季候。”[15]因而诗人在吟咏风月时也不自觉地偏重秋意清幽、鸟虫鸣寒、霜月冰冷。如:
今日山前无过客,数株衰柳管秋风。(《过九里山》)[2]386
秋虫已息又还吟,晚雨初晴又作阴。(《晚兴》)[2]389
夜风喧马枥,秋露冷鸡栖。(《河上》)[2]385
秋霜一何严,凋此道傍柳。(《道傍柳》)[2]386
月色过窗同夜梦,霜华著壁独朝寒。(《发脱》)[2]389
在诗人笔下,风喧柳残、虫吟鸡栖、露冷霜严,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凉寒”。虽未明言身世处境,这一切却隐隐约约透着诗人对王朝末世的哀怜及自怜之情。故而其诗中屡用“残”“破”“败”“荒”“折”等字眼营造枯败意境,如:
破垒残星没,寒城晓角孤。(《别张信夫》)[2]385
南皮城下荒秋草,说是当日燕支台。(《杂诗二首》其二)[2]390
败井劳深汲,荒庭阙近寻。(《物化》)[2]387
寒蝉高鸟清愁外,折苇枯荷小景中。(《北潭》)[2]389
大千世界荣枯皆有,而在诗人眼中看到的却多是“破垒残星”“荒秋草”“荒庭”“败井”“折苇”等景象。亦如国势日坠、人之将老。故而诗人眼中除却秋冷霜严、物色枯败,更兼叹老。诗人感慨吾生老矣,除了物换时移、人生代谢使然之外,往往也总与国势飘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秋霜一何严,凋此道傍柳。残枝几叶在,其势不得久。……
别后遽能几,忽忽成老丑。人生非金石,长短百年寿。(《道傍柳》)[2]386-387
岁月吾生老,关山客梦迷。故园桃李树,摇荡不成蹊。(《河上》)[2]385
畏景流庭过,凉飔即坐来。物随时共换,人觉老相催。(《立秋日》)[2]387
国势亦如道旁之柳,残枝败叶,“其势不得久”,亦如“故园桃李树,摇荡不成蹊”。而这种衰落颓势正如夏去秋来的自然规律一样,不可逆转,“畏景流庭过,凉飔即坐来”,国势盛极而衰,人生忽忽将老。
“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16],在不经意间的抒写中,外物亦无非“老”矣。《杂诗二首》其二云:“迎风紫苋因循老,背日黄花次第开。”[2]390《登悯忠寺阁》云:“聚土闲童子,移山老比丘。”[2]387“紫苋”是老的,“比丘”亦是老的。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诗人尚有不俗的意趣可供“破老”消遣。《发脱》云:“求医未有诗千首,破老惟消竹数竿。”[2]389“竹”可免俗“破老”、“诗”可医心遣愁。
综上所述,史肃生前,有“闻人”之名,而其身后却诗名不彰。观其现存诗,“有理”“用事”的特点明显,尤善于属对,即元好问所谓“精致”。五言如:“夜风喧马枥,秋露冷鸡栖。”[2]385“移床就佳月,引袂纳凉风。”[2]387“树鸟依依宿,檐萤细细流。”[2]387,尤其“树鸟”一联颇可媲美元好问名句“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8]卷1。七言如“强颜红叶自由舞,野性黄花无赖香。”[2]386“知有高亭堪眺远,惜无佳客共登临。”[2]388“迎风紫苋因循老,背日黄花次第开”[2]390。“强颜”“知有”二联,置于平行时段的宋诸家卷中,亦不遑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