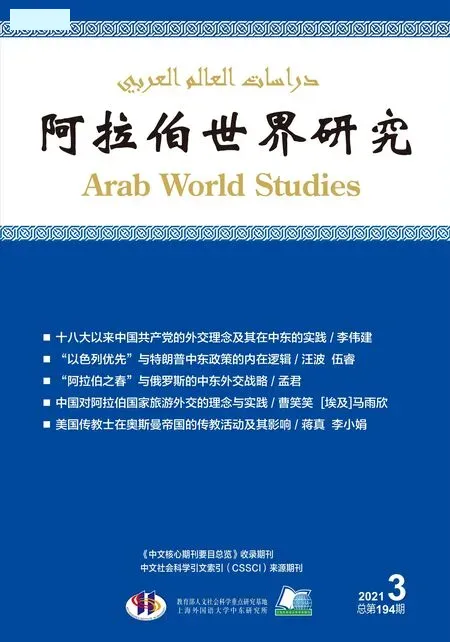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蒋 真 李小娟
2020年7月初,土耳其欲将圣索菲亚大教堂(1)圣索菲亚大教堂修建于公元6世纪早期的东罗马帝国,最初是一座基督教教堂。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将其改为清真寺。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圣索菲亚清真寺被改为博物馆。该教堂在基督教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备受基督教世界的关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2019年的竞选中流露出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为清真寺的意愿,引起了基督教世界的反对。2020年7月,改造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风波再起。从博物馆改为清真寺的消息引爆了基督教世界的舆论。美国和俄罗斯一齐发声“劝阻”土耳其,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一世(Kirill I)称,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基督教文明最伟大的纪念碑之一”,“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威胁就是对整个基督教文明的威胁。”(2)“World Reacts to Turkey Reconverting Hagia Sophia into a Mosque,” Aljazeera, July 11, 2020,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0/7/11/world-reacts-to-turkey-reconverting-hagia-sophia-into-a-mosque, 上网时间:2021年4月14日。这一事件折射出千百年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互动的历史与现实。
近代以来,为适应殖民主义时代的价值观,西方基督徒发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传教运动。基督教的传教运动在英语中为“mission”一词,源于拉丁文“missio”,意为差遣。后来经过不断扩展,传教一词指的是“西方教会系统延展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活动”(3)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1, pp. 227-228.。近代西方的传教运动在基督教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时间上跨越几百年的历史,空间上遍布世界各地,基督教也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宗教。(4)唐逸主编:《基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页。16世纪,奥斯曼帝国步入极盛时期,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辽阔疆域。在强大的穆斯林近邻的“阴云”笼罩下,西方对奥斯曼帝国形成了“东方主义”式的想象,奥斯曼威胁一直潜伏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明血液里。基于“十字军东征”以来形成的政治背景,以及奥斯曼帝国特殊的地缘和宗教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传教运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备受西方传教士的关注。由此,西方基督教世界与“最后的穆斯林帝国”——奥斯曼帝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气势恢宏的文明互动。这场互动是对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互动的继承和延续,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16世纪以来,基督教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生根发芽。到了19世纪,西方的传教活动在奥斯曼帝国广泛存在。其中,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活动最具代表性。传教理念是美国对外文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帝国主义利益的日益增长,美国传教士基于西欧传教活动的早期成果,在奥斯曼帝国开启了一个空前的基督教传播的时代,生动诠释了以冲突与融合为基本特点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互动的内涵和外延。
国外学术界对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活动研究起步较早,尤其以美国学者为代表。他们基于一手档案、游记和传教士日记等历史资料,主要从美国传教士在美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传教士建立的教育系统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等方面着手,对该问题进行了精细的考察,相关论著颇丰。(5)相关成果参见 Emrah Sahin, Faithful Encounters: Authorities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Hacer Bahar,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he Role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US-Ottoman Empire Relations and Their Educational Legacy,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GmbH, International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19; Hans-Lukas Kieser, “Mission as Factor of Change in Turkey (Nineteenth to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Vol. 13, No. 4, 2002, pp. 391-410; Faith J. Childress, “Creating the ‘New Woman’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American Collegiate Institut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4, 2008, pp. 553-569; Devrim Umit,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Network in Ottoman Turkey, 1876-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Vol. 4, No. 6, 2014, pp. 16-51.但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互动角度的探讨却十分罕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大多具有基督教背景,他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免带有宗教情感的倾向和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起步晚,缺乏重视且鲜有探讨。(6)国内尚无针对该问题的系统性论述,涉及相关问题的著述主要包括: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20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2020年;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美]戴维·A.霍林格:《海外传教活动对20世纪美国的影响》,郭擎川译,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在某种程度上,该问题是当前国内美国与中东关系研究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关注该问题对于文明交往视野下多文明群体之间的互动研究也大有裨益。因此,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文明互动交往的视角探究美国传教士(7)美国传教士主要是美国基督新教福音派,由公理会、长老会和归正会等教派组成。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以期深化对几百年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认知。
一、 权益之争: 美国传教士与奥斯曼帝国的博弈
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简称美部会)(8)1806年的某天,美国波士顿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以小塞缪尔·J.米尔斯(Samuel J. Mills, Jr.)为代表的学生在草地上举行了祈祷和冥想的仪式。这时突然下起阵雨,他们躲在干草堆的背风处避雨时萌生了向海外传播福音的想法。两年后,一个名为“兄弟会”(The Brethren)的大学生秘密社团成立,决心完成传教使命,这为美部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810年9月,美部会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来自公理会、长老会和归正会等教派,致力于实现“全世界的福音化”。1819~1850年是美国传教士海外活动的拓荒期。印度是美国新教传教士登陆的第一个目的地。然而,由于1812年英美战争和英美传教士在加尔各答遭遇的种种问题,他们很快将注意力从南亚转向中东。于是,中东成为美部会最重要的传教基地之一。的组织和领导下,美国拉开了与奥斯曼帝国百年互动关系的序幕。事实上,在美国传教士之前,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早已在奥斯曼帝国开展传教活动。(9)法国主要集中向叙利亚地区的马龙派教徒传播基督教,而英国则注重在埃及科普特人中间传教。美国传教士在他们的基础上将传教工作扩展到整个奥斯曼帝国。在短短20多年间,他们为美国打开奥斯曼帝国的门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传教活动的缘起
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活动受到新教“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运动的影响。19世纪初,美国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推动了福音派的发展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兴起,这使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国家的特殊使命是向全世界传播基督教的福音。(10)Devrim Umit,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Network in Ottoman Turkey, 1876-1914,” p. 20.奥斯曼帝国是中东主要的政治体,其整体实力虽然在下降,但仍统治着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美国传教士对奥斯曼帝国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基督徒对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情感。19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深信前往奥斯曼帝国传教不仅是出于“对异教徒的义务”,更是一个特别的关于对“《圣经》之地”的责任。在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一个传教目的地能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得到如此长期和有力的支持。(11)Edward Mead Earle, “American Missions in the Near East,” Foreign Affairs, Vol. 7, No. 3, 1929, p. 398.
1819年,美部会派遣传教士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和普林尼·菲斯克(Pliny Fisk)前往奥斯曼帝国传教。1820年2月,这两位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士麦拿(Smyrna)(12)士麦拿(Smyrna)是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Izmir)的旧称,它是奥斯曼帝国著名的港口城市,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爱琴海沿岸地区。登陆。(13)Clifton Jackson Phillips, Protestant America and the Pagan World: The First Half Centu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10-1860,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69, p. 31.帕森斯在寄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看到一个系统在运作,在神的祝福下,将彻底摧毁这个强大的罪恶帝国。”(14)“一个强大的罪恶帝国”后来成为一个常见的短语,尤其为基督教传教士普遍使用,主要指奥斯曼帝国。他感到悲伤的是,“有多少灵魂被挡在福音的光明和祝福之外!”(15)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1, p. 6.早期,美国传教士主要分布在奥斯曼帝国的大城市士麦拿和伊斯坦布尔等地,他们专注于学习当地语言,分发《圣经》和宗教书籍,创办出版社,并尝试建立教会学校等任务。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最初10年里,由于缺乏系统思考和制定有关传教的详细计划,导致传教活动的成果微乎其微。
19世纪30年代,鉴于向穆斯林和犹太人传教非常艰难,美部会将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即所谓的“名义上的基督徒”(16)“名义上的基督徒”是一个笼统的术语,传教士用来指那些声称信仰基督教,但没有皈依经历的人,通常包括亚美尼亚人和聂斯脱利派等。确定为传教任务的重心。1831年,针对不同的基督教社团,美部会设立了君士坦丁堡布道站(17)布道站(missionary station)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地建立的传教点,用于联络和组织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平时居住饮食也都在其中。1831年,美部会指派威廉·古德尔(William Goodell)前往伊斯坦布尔建立布道站。他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将《圣经》翻译成亚美尼亚—土耳其语,并用20年时间对其进行修订。1867年,古德尔在费城去世。、士麦拿布道站和贝鲁特布道站。(18)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8.1850年,奥斯曼帝国迫于西方的压力,授予新教徒米勒特(Millett)(19)米勒特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种宗教自治制度。米勒特为音译,意为“民族”或者“国民”,它要求非穆斯林宗教团体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捐税的基础上,可以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享受内部的宗教自治权。米勒特制度的主要作用是维持民族和宗教的稳定。合法地位。从1850年到1876年,大量的传教资金和人员源源不断地从美国输入奥斯曼帝国,推动传教活动迅速发展。美国传教士的兴趣不再局限于像士麦拿和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都市,开始关注奥斯曼帝国遥远的省份及其周边地区。(20)Devrim Umit,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Network in Ottoman Turkey, 1876-1914,” p. 29.这一时期,介绍奥斯曼帝国的出版物在美国风靡一时,这些出版物强调了在奥斯曼帝国生活和工作的浪漫之处,吸引着美国传教士、探险家和商人。19世纪70年代,美国新教徒对改造“罪恶的穆斯林帝国”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新来的传教士更具宗教扩张意识,他们推动了新一波的福音传播浪潮。
(二) 美国传教士与哈米德政府的冲突
1876~190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的统治给美国传教士带来空前威胁。因此,美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集体记忆往往不是正面的,他们有如“可怕的土耳其人”和“红色苏丹”等类似的概念。(21)Devrim Umit,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Network in Ottoman Turkey, 1876-1914,” p. 16.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与其说是对奥斯曼帝国的记忆还不如说是对哈米德二世的记忆。(22)Edward Mead Earle, “American Missions in the Near East,” p. 403.哈米德二世即位时,奥斯曼帝国内部经济衰落,政治统治摇摇欲坠,民族问题丛生,外部面临俄国、英国和奥匈帝国等国家的入侵,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哈米德二世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极力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他认为传教活动会引发帝国民众对法国和美国革命的效仿,导致其政权的崩溃,因此对美国传教士在帝国境内广泛的活动保持警惕。(23)Ibid., p. 402.
出版、教育和医疗是美国传教士常用的传教形式,其中,他们在出版和教育领域与哈米德政府的冲突最为频繁。1822年,菲斯克在马耳他建立了第一家教会印刷厂,在短短9年内用希腊文、亚美尼亚文和阿拉伯文等语言出版了35万册宗教书籍。(24)Cagri Erhan, “Ottoman Official Attitudes Towards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Turkish Yearbook, Vol. 30, 2000, p. 208.1852年,印刷厂迁至伊斯坦布尔的布道中心,被称为“《圣经》之家”(Bible House),它为整个安纳托利亚和其他中东地区提供出版材料,影响深远。印刷出版业在塑造民众思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美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成为帝国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传教士的努力,一些穆斯林皈依了基督教,这引起了哈米德政府的注意。哈米德认为美部会“煽动性的书籍和小册子”粉碎了穆斯林社区的信仰和忠诚,美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可能会扰乱公共秩序,污化土耳其—伊斯兰形象,因此加强了对传教士出版物的限制。(25)Emrah Sahin, Faithful Encounters: Authorities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p. 104.哈米德政府要求外国出版商接受审查,正如“《圣经》之家”的编辑亨利·德怀特(Henry Dwight)在他的书中总结的那样,“如果没有审查人员的签字批准,印刷工就不能印刷书籍、报纸和图片。几乎所有的出版商都在某个时候遭遇过官方审查。”(26)Emrah Sahin, Faithful Encounters: Authorities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p. 100.1891年,奥斯曼帝国颁布了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在公共场合发表的论文和书面讲话都必须事先经过审查。从1878年到1907年,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审查员人数增加了10倍,但这些审查员在大部分时间里仍然超负荷工作。很多传教书籍因未通过审查而被列入了黑名单。此外,哈米德政府模仿美国传教士采用印刷技术,出版有关反对传教活动的宣传物,与美国传教士相抗衡。奥斯曼帝国对美国传教如此敏感,以至于海关人员对含有“美国”一词的出版物保持高度警惕。(27)Ibid., p. 118.美国传教士向奥斯曼帝国请愿,要求减少对出版物的审查,但哈米德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认为一旦放宽限制,相关出版物会迅速传播到普通大众,进而影响帝国的稳定。
另外,美国传教士与哈米德政府的冲突还体现在他们创办的教会学校上。1850年,奥斯曼帝国境内有7所基督教教堂和7所基督教宗教学校,1880年分别达到97所和331所,1913年达到163所和450所。(28)R. L. Daniel,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the Near East: 1820-1960,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94.哈米德二世对此高度警惕,但忌于传教士背后的美国政府,他并没有驱逐美国传教士或者取缔他们的机构,而是采用一系列措施遏制和反击美国教会学校。他改革帝国的教育系统,尤其针对小学和中学设定以伊斯兰宗教教育为内容的课程,要求教师采用官方语言教学,并在帝国境内建立哈米迪学校(Hamidian school)。这类学校注重伊斯兰传统文化教育,抵制美国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1899年1月9日,他颁布了一项法令,明确了教育改革的紧迫性,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叛教行为。哈米德政府还要求私立学校必须持有官方认定的执照才能正常运作,教师则“必须获得证书”。除非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奥斯曼政府保留关闭这些机构的权利”。(29)Emrah Sahin, Faithful Encounters: Authorities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p. 76.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大量美国教会学校实际上处于无证办学的状态,它们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后才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三) 美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干预
“传教士所关心的道德和宗教问题可能会引起外交官和政府的同情甚至支持,但这只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30)④ Jeremy Salt, “Trouble Wherever They Went: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Anatolia and Ottoma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Muslim World, Vol. 92, No. 3-4, 2002, p. 310.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传教士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工具之一,正如一位美国基督教史学家所说,“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是一项家长式的统治事业,是一种宗教帝国主义”。(31)任继愈主编:《基督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271页。19世纪80年代,美国为支持其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开拓性活动,试图借助亚美尼亚问题牵制奥斯曼帝国。因此,亚美尼亚问题一度成为美国与奥斯曼帝国互动的关键。1895年,美国的两所教会学校幼发拉底河学院(Euphrates College)和中央土耳其学院(Central Turkey College)在帝国镇压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中遭到破坏,美国传教士要求奥斯曼政府赔偿10万美元损失,后者拒绝了这一要求。1895年12月4日,美国总统克利夫兰(1837~1908年)向参议院通报有关奥斯曼帝国损坏美国公民财产的信息。他还告知参议院,他已指示圣弗朗西斯科号(San Fransisco)、马尔布黑德号(Marblehead)和明尼阿波利斯号(Minneapolis)等战舰在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巡航,以防止帝国对其公民的任何攻击行动,并确保奥斯曼帝国赔偿损失。赔款问题直到1901年才得以解决。1901年6月,美国的肯塔基号(Kentucky)战舰被派往士麦拿港,奉命向奥斯曼帝国施压,帝国政府最终支付了10万美元的赔偿金。(32)Cagri Erhan, “Ottoman Official Attitudes Towards American Missionaries,” p. 207.这说明美国传教士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他们作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既有秩序和社会稳定。为此,双方的矛盾不断被激化。
此外,“埃伦·斯通(Ellen Stone)事件”是美国政府干预传教活动的又一重要案例。1901年9月,美国女传教士埃伦·斯通和她的同伴卡特琳娜·切尔卡(Katerina Tsilka)被一伙匪徒伏击并绑架。这一事件震惊了美国政府和民众,全国各地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大约在受害者落入绑匪手中一周后,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年)总统宣誓就职,他指示美国国务卿要“不遗余力”地解决此问题。为支付绑匪要求的天价赎金,埃伦·斯通的亲属与新英格兰教会组织以及一些记者合作,设立了国家大赎金基金(National Great Ransom Fund)。经过数月努力,1903年2月23日,绑匪接受了72,500美元赎金,释放了埃伦·斯通及其同伴。(33)Emrah Sahin, Faithful Encounters: Authorities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p. 40.“埃伦·斯通事件”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声誉,导致帝国当局卷入一场与美国政府的争端当中。其间,美国十二艘战列舰以“友好合作”的名义驶过地中海,其中半数装备精良,随时准备冲锋陷阵。奥斯曼帝国当局将该行动解释为美国在传教问题上向帝国施压的一种外交手段。在伊斯坦布尔和华盛顿的各种会议上,美国代表要求奥斯曼当局承担起保护美国传教士的责任。他们还要求帝国当局针对传教士被起诉、驱逐出境、袭击或谋杀的司法程序做到完全透明。奥斯曼帝国当局认为他们对美国传教士的保护是一种恩惠,而不是义务。但随后在多重压力下,帝国重组了国家安全网络,并动用大量国家资源来惩治地方犯罪,保护美国传教士的人身安全。(34)Emrah Sahin, Faithful Encounters: Authorities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p. 51.
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了反对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革命。革命成功后,立宪政府对美国传教士在革命活动中的热情给予肯定,对美国传教士的态度也发生了积极变化。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约翰·利什曼(John Leishman)在报告中写道,“立宪政府不仅会对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还会缓解包括传教士在内的美国公民的压力。”(35)Cagri Erhan, “Ottoman Official Attitudes Towards American Missionaries,” p. 211.1908年9月下旬,立宪政府宣布废除对书籍印刷、发行以及对传教士旅行的限制,为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活动提供了便利。1913年,奥斯曼帝国的美国教会学校入学人数高达25,922名。(36)R. L. Daniel,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the Near East: 1820-1960, p. 94.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殖民体系的逐步解体导致新教外交的优势地位和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英雄时代走向终结。美国传教先驱帕森斯和菲斯克怀揣的关于改造奥斯曼帝国的英雄梦最终没能实现。(37)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304.
二、 冲突与融合: 美国传教士与帝国主要宗教群体的互动
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了独特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以及物质对象。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传播着他们的个人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所表达的特定文化价值观。(38)Jerzy Zdanowski, “In Search of the Supracultural: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Gulf in 1920s-1930s,”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Vol. 30, No. 3, 2019, p. 385.他们在传教目的地致力于形塑基督教的话语,努力在传教实践中凸显其话语的合法性,因此会不断与其他相异的观念产生摩擦和冲突。(39)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0页。正是在这种相互冲突和对抗中,美国传教士所带来的基督新教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之间实现了多文明的互动和交往。在此过程中,美国传教士始终以实现新教在奥斯曼帝国最大程度的传播为目标,不遗余力地推进传教实践。而这看似美好的宗教关怀掩盖着谋求美国国家利益的本质。
(一) 美国传教士与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艰难对话
美部会的传教士接触到了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在内的奥斯曼帝国穆斯林,他们与穆斯林的对话异常艰难。穆斯林的宗教观念融合了宗教和政治思想,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但美国传教士则持政教分离的宗教观念。另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一神教的成员,比起多神论者,他们的信徒更加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作为普世主义者,他们都声称全人类应追随真正的信仰,并试图说服对方皈依。(40)[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合法性建立在以苏丹为统治者的基础之上,帝国政府不能容忍以任何形式对伊斯兰真理提出质疑,帝国的一些官员建议传教士在与穆斯林打交道时谨慎行事。如果穆斯林愿意冒险,美国传教士甚至为他们施洗。但总的来说,穆斯林不愿接受他们的观点,“这一切都把传教士置于宴会上守夜人的位置,他们饥肠辘辘地凝视着那些被禁止吃的食物。”(41)Jeremy Salt, “Trouble Wherever They Went: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Anatolia and Ottoma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306.奥斯曼帝国警惕美国传教士及相关机构对其核心意识形态,即伊斯兰国家的威胁,将美国传教士及其活动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即使在这种境况下,19世纪末的伊斯坦布尔传教士依然可以偶尔与穆斯林学者进行神学讨论。1879年,阿里·埃芬迪(Ali Effendi)阿訇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做讲座期间,他邀请美国传教士阿维迪斯·康斯坦蒂安(Avedis Constantian)参与讨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问题,两位神学家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宗教对话。(42)Emrah Sahin, Errand into The East: A History of Evangelical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ir Missions to Ottoaman Istanbul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Bilkent University, 2004, p. 80.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建立立宪政府。美国政府期待与之合作,试图为传教士的活动创造良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在美国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年轻穆斯林”特别适合参加“目前在土耳其推行的具有深远政治和社会改革意义的运动,我们非常同情这一努力。”(43)Hans-Lukas Kieser, “Mission as Factor of Change in Turkey (Nineteenth to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p. 398.从1911年开始,美国传教士抓住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爆发战争、极度衰弱的时机,重启对帝国境内穆斯林的传教工作,试图促进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穆斯林的皈依。鉴于宗教学校可以直接接触到穆斯林学生,他们对教会学校的工作大为重视。1909~1914年,伊斯坦布尔和士麦拿美国教会学校的穆斯林学生人数在逐步增加。传教士希望《圣经》和基督教知识的学习成为穆斯林学生的必修课,唤醒他们“精神上的饥饿”。(44)Devrim Umit,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Network in Ottoman Turkey, 1876-1914,” p. 43.即使如此,对穆斯林的传教成效仍然不显著。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土耳其人内心一如既往的虔诚,穆斯林还是穆斯林……。”(45)Jeremy Salt, “Trouble Wherever They Went: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Anatolia and Ottoma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89.但美国传教士始终坚持将“奥斯曼”土地“永久基督教化”的目标,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的心脏”,帝国穆斯林的皈依关系到基督教的全球传播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46)Devrim Umit,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Network in Ottoman Turkey, 1876-1914,” p. 49.
(二) 美国传教士与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互动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最初的传教对象之一。对圣地的依恋延伸到美国家庭、信仰模式和教育等各个领域,是美国基督教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促成了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交融。美部会向耶路撒冷派遣传教士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在古代以色列的所在地建立美国前哨站的浪漫前景”的影响。(47)Clifton Jackson Phillips, Protestant America and the Pagan World: The First Half Centu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10-1860, p. 135.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美国人相信“千禧年主义”,认为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重建锡安是建立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全球和平王国的先决条件。这些都加剧了美国传教士对犹太人以及他们在末世论中所起的预示作用的关注。(48)Hans-Lukas Kieser, Nearest East: American Millennialism and Mission to the Middle Eas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5-6.在美国传教先驱看来,将中东布道站的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和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无疑是传教活动的首要任务之一。美部会认为,比起欧洲基督教传教士,美国传教士在促进犹太人皈依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因为美国是“唯一没有迫害过犹太人的基督教国家。”(49)Eleanor H. Tejirian and Reeva Spector Simon, Conflict, Conquest, and Conversion: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82.1819年,帕森斯被美部会派往奥斯曼帝国传教,在动身前的几个月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去朱迪亚(Judea)(50)古代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包括今以色列南部及约旦西南部。的使命上。我要利用每一刻,利用每一种方式,向圣地发起一场精神上的‘十字军东征’。”(51)Hans-Lukas Kieser, Nearest East: American Millennialism and Mission to the Middle East, p. 38.1830年至1850年间,伦敦犹太人协会的一个分支——波士顿女性协会(Female Society of Boston)资助美部会的威廉·肖夫勒(William Schauffler)前往伊斯坦布尔向犹太人传教。(52)Ibid., p. 26.
美国传教士在与犹太人的互动中遇到了多重挑战。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将其臣民划分为不同的宗教团体,它定义了帝国在整个19世纪的社会、宗教和法律组织。(53)U. Makdisi, Artillery of Heaven: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Failed Conversion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3.奥斯曼帝国承认犹太人组成的宗教米勒特,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宗教法庭,以及在他们的社区内进行礼拜的自由。犹太人米勒特的宗教领导阶层——拉比担任民法法官,并在帝国官僚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54)Aimee E. Barbeau, “Religious Voluntarism, Polit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Secular: Nineteenth-Century Evangelical Encounters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3, No. 3, 2017, p. 456.他们极力反对美国传教士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新约》内容,并在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会堂里谴责美国传教士,禁止犹太人购买美国传教士的出版物。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传教士开设了犹太人小学,并试图以《新约》为教材教授学生阅读,但最终失败了。犹太青年将传教士印发的《新约》内容剪下,在集市上当作废纸售卖。(55)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8.在犹太社区,拉比不仅反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而且反对犹太人在美国教会学校学习,他们通过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学校加以抵制。19世纪末,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犹太人团体成立了以色列大学联盟(The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致力于为伊斯兰国家和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提供现代教育,以此抵制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56)Eleanor H. Tejirian and Reeva Spector Simon, Conflict, Conquest, and Conversion: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pp. 149-150.
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是美国传教士与犹太人互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早期的美国传教士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持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战前,伊斯坦布尔“《圣经》之家”的领导层原则上欢迎犹太复国主义,“《圣经》之家”的评论员写道:“所有希伯来民族的真正朋友都强烈同情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古老家园的计划。”(57)Hans-Lukas Kieser, Nearest East: American Millennialism and Mission to the Middle East, p. 110.然而,他们认为在没有精神复兴和皈依的境况下,犹太民族主义者返回巴勒斯坦是对先知的“嘲弄”。(58)Paul Charles Merkley, Christi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State of Israel,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1.在巴黎和平会议上,传教士代表对犹太人返回家园的计划表示同情,但他们并不支持犹太人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59)Hans-Lukas Kieser, Nearest East: American Millennialism and Mission to the Middle East, p. 108.石油利益的增长使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变得更加敏感。(60)John A. Denovo, Americ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1900-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3, p. 344.在传教士的渲染下,美国政府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开始大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众很难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公正的看法,许多美国人甚至无法理解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愤怒。阿拉伯人觉察到,当他们挣脱英国和法国殖民枷锁的时候,一种新的、更微妙的、打着保护犹太人旗号的西方帝国主义正在形成,并不断蚕食他们的领土。(61)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308.美国传教士及背后的美国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举措关系到阿以和平进程的推动,尤其对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影响深远并持续至今。
(三) 美国传教士与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互动
奥斯曼帝国基督教会源于五六世纪的少数民族教会,包括东正教会(如科普特教会、亚美尼亚教会和叙利亚东正教会)、天主教会(如马龙派和麦勒卡教会)和聂斯脱利派教会等。(62)Aimee E. Barbeau, “Religious Voluntarism, Polit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Secular: Nineteenth-Century Evangelical Encounters in the Middle East,” p. 456.起初,美部会将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作为传教的主要目标,基督徒并不是重点关注的对象。然而,传教士很快意识到这一目标缺乏可行性。由于奥斯曼帝国对穆斯林皈依的严厉惩罚和来自犹太人内部的极力排斥,美部会感叹“上帝似乎对我们关上了门”。(63)Ibid.对此,美部会决定改变传教策略,集中向所谓的“堕落的东方教会”进行精神启蒙,复兴当地的基督教教会,侧面使穆斯林和犹太人向基督徒自然转换。(64)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8.因此,美国传教士的工作转向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但挑战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天主教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其成为第一个反对美国传教士的基督教教派,“皈依商人的店铺遭到抵制;皈依者在街上被石头砸死,然后被吊起来,人们朝他们的脸上吐唾沫。”(65)Edward Mead Earle, “American Missions in the Near East,” p. 401.1823年,马龙派大主教发布通谕,谴责新教徒印发《圣经》,并禁止他的子民与“英国传教士”(66)1831年,美国在伊斯坦布尔建立美国公使馆,正式与奥斯曼帝国确立外交关系。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民众一般将美国传教士误认为是英国人。交往,梵蒂冈的红衣主教索马格里亚(Somaglia)则指控这些“《圣经》信徒”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67)Aimee E. Barbeau, “Religious Voluntarism, Polit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Secular: Nineteenth-Century Evangelical Encounters in the Middle East,” p. 460.此后,东正教信徒也掀起了反对美国传教士的浪潮,东正教学生从各地的美国教会学校退学;新教教师被禁止在东正教教会机构任职;传教书籍、小册子和《圣经》遭到烧毁。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牧首谴责美国传教士的“异端邪说”书籍,呼吁信徒要防止他们将“毒药”倒进孩子们的耳朵里。(68)Heleen Murre-van den Berg, New Faith in Ancient Lands: Western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Boston: Brill, 2006, p. 217.“而穆斯林则用困惑和幽默的目光看着这场不体面的斗殴。”(69)Edward Mead Earle, “American Missions in the Near East,” p. 401.
美国传教士与当地基督徒的诸多冲突并非偶然,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牵绊。奥斯曼帝国给予基督徒米勒特半自治地位,这些米勒特的宗教领导层并不认同美国基督教具备先天优越性。作为宗教领袖,他们希望加强信徒对其教会的忠诚;作为世俗统治者,他们担心部分社区脱离其教会管辖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减少他们的收入。为维护教会的权威和传统,当地米勒特领导层决心抵制美国传教士的“异端邪说”。美国传教士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他们被描述为“魔鬼的仆人”“披着羊皮但内心贪婪的狼”和“觅食的狼”等。(70)Jeremy Salt, “Trouble Wherever They Went: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Anatolia and Ottoma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92.另外,传教士和当地基督徒在宗教观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天主教徒认为,个人只有“在教会的传统仪式和权威中”才能实现皈依和救赎,而美国传教士要求独立的个人在皈依之后才能自愿加入教会,参与宗教仪式。正如菲斯克所说,皈依者需要通过“圣灵来更新心灵”。只有在这个更新的经历之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然后参加洗礼,并加入教会。(71)Aimee E. Barbeau, “Religious Voluntarism, Polit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Secular: Nineteenth-Century Evangelical Encounters in the Middle East,” p. 461.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传教士将《圣经》放在宗教观的中心位置。对于他们而言,在精神上唤醒“名义上的基督徒”的主要方法是带给他们《圣经》。对于当地的基督徒,尤其是对天主教徒来说,允许个人自由阅读和解释《圣经》将是有害和破坏性的。(72)R. L. Daniel,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the Near East: 1820-1960, p. 24.菲斯克和一名马龙派信徒之间的一段对话很好地证明了这一论断:“我们问修道院长,关于他对《圣经》的信仰情况。他说,‘我相信教会的信仰’。我回答说,‘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对于前者来说,传统的宗教等级是信仰的中心;而对于后者而言,《圣经》和个人的理解才构成信仰的核心。(73)Aimee E. Barbeau, “Religious Voluntarism, Polit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Secular: Nineteenth-Century Evangelical Encounters in the Middle East,” p. 459.
如果说美国传教士与上述基督徒的交往是以冲突为基本特点的文明互动,那他们与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的交往则主要表现出以融合为特点的文明互动。根据美部会的统计,他们在帝国的传教工作对亚美尼亚基督徒的影响最为深远。(74)Muhammet Avarogullari and Ozgur Yildiz, “Role of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Ottoman Education System,” Turkish Studies, Vol. 10, No. 9, 2015, p. 69.19世纪60年代以来,受美国教会学校提供的优质教育和工作机会的吸引,许多亚美尼亚人接受了新教教义。美国的传教活动扩大了亚美尼亚人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同。实际上,美国传教士与亚美尼亚人之间也存在冲突。在传教初期,美国传教士与亚美尼亚人因宗教观和布道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了矛盾。美国传教士致力于促进亚美尼亚教会的改革,进而促使亚美尼亚人皈依新教,这遭到了亚美尼亚教会的强烈反对。另外,美国传教士带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优越感来到奥斯曼帝国,他们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关于物种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定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和国家,与自然界进化过程中的优胜劣汰相似,认为只有社会上的优胜者和国际舞台上的优胜国家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强烈的竞争意识和生存、成长的欲望,很好地契合了美国对外传教工作的态度,却掩盖了侵略性和傲慢本质,为帝国主义提供了辩护。(75)Devrim Umit,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Network in Ottoman Turkey, 1876-1914,” p. 34.一些美国传教士凭借这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所谓优越感,对亚美尼亚人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例如,在1900年,当美国女传教士特雷莎·亨廷顿(Theresa Huntington)面对当地一位亚美尼亚医生的求婚时,她认为这是对她的一种侮辱。(76)Heleen Murre-van den Berg, New Faith in Ancient Lands: Western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 257.
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亚美尼亚问题”一直是传教士用来影响美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主要筹码。一战结束后,美国传教士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亚美尼亚人,这使亚美尼亚人与威尔逊政府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联盟”。(77)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247.但这种“联盟”关系并不牢靠。凯末尔主义者谴责美国传教士是“麻烦制造者”,而亚美尼亚人因危及美国的战略利益而最终被抛弃。由此可见,美国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就是“通过他们的存在及其传播的价值观,服务于一般意义上的自身国家利益。”(78)Jeremy Salt, “Trouble Wherever They Went: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Anatolia and Ottoma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310.
三、 世俗工作的成效: 互动实践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美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活动影响力广泛,尤其是在世俗工作方面颇具成效。从1819年美国传教士渗透到奥斯曼帝国开始,一直到一战后美国传教活动的衰落,美国在奥斯曼帝国社会的传教工作并未获得想象中的成功。美国传教士试图传播的福音在当地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社区并未被广泛接受。实际上,美国传教士在包括教育、妇女事业和促进民族主义等世俗工作方面的努力比传教更为有效。
(一) 对奥斯曼帝国教育和妇女事业的促进作用
奥斯曼帝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使美国传教士转变了传教形式,从强调宗教布道变为重视世俗教育。美国传教士所提供的现代教育,特别是他们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比其他传教形式更为成功。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开设了多所教会学校,以便通过教育使学生接受新教价值观,最终达到促进皈依的目的。美国教会学校一般选择欧式建筑风格,具备实验室,学校周围放置着体育运动器材。(79)Heleen Murre-van den Berg, New Faith in Ancient Lands: Western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 268.由于教会学校大多采用寄宿制管理,因此增加了传教士与学生的接触机会,有利于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最大限度地对学生施加影响”。(80)Muhammet Avarogullari and Ozgur Yildiz, “Role of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Ottoman Education System,” p. 60.
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校是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和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它们在中东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864年,罗伯特学院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成立,以建校资金的捐助者——纽约富商克里斯托弗·罗伯特(Christopher Robert)的名字命名。该学院不仅是奥斯曼帝国,更是整个中东地区由美国教会建立的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师资力量雄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1866年,贝鲁特美国大学成立,其前身是叙利亚新教学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成为当地重要的高等学府和教会学校的典范。到1968年,该校3,500名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和550名教职工中的70%都是阿拉伯人。在1.4万名校友中,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阿拉伯世界。(81)Ibid., p. 307.1965年,有7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国大使都是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友。(82)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308.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奥斯曼帝国的妇女成为美部会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美国内战的结束缓解了美部会面临财政困境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妇女的自信心。她们在战争期间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和医疗事务,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她们在奥斯曼帝国设立多处妇女布道站和教会学校,促进了妇女教育的发展。这也是凯末尔政府成立后为数不多的得到承认的美国传教成果之一。美国女传教士常常发现当地的妇女太过繁忙,根本无暇顾及宗教学习。一位女传教士到一户人家朗读《圣经》故事,这时一名妇女打断了她的话:“你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你可以读书。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缝补、孩子和牛怎么办呢?”美国传教士还试图将当地女性的结婚年龄提高一些。(83)Heleen Murre-van den Berg, New Faith in Ancient Lands: Western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p. 253-254.但他们尽量避免破坏当地的社会传统以免给布道站带来损失。传教士循序渐进推广女性教育的方式收到了成效,女性教育逐渐受到重视。
女性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她们的知识水平和收入水平,使其家庭和社会地位也得到相应提高。19世纪70年代,美部会传教士建立了伊兹密尔的美国大学学院(American Collegiate Institute)和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女子学院(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这两所学校为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的土耳其妇女地位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女子学院起源于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Constantinople Woman’s College),于1890年获得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特许成为美国学士学位认证机构,它也被视为中东妇女教育的典范。(84)Faith J. Childress, “Creating the ‘New Woman’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American Collegiate Institut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for Girl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4, 2008, pp. 553-554.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美国教会学校吸引了越来越多奥斯曼帝国的年轻女性。她们入学的主要动机与其说是为了皈依基督教,还不如说是为了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另外,对于传教士来说,教会学校是“为社区带来聪明、虔诚和高效女性助手”的最佳方式。这些年轻的女性一旦接受扎实的新教价值观教育,就很有可能根据基督教原则建立家庭并成为“有教养和智慧的基督徒的妻子或母亲”,最终推动基督教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85)Heleen Murre-van den Berg, New Faith in Ancient Lands: Western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 280.
(二) 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催化作用
美国学者罗德里克·戴维森(Roderic Davison)指出,“不幸的是,奥斯曼帝国唯一接受的西方宗教就是民族主义的信条”。(86)Hans-Lukas Kieser, “Mission as Factor of Change in Turkey (Nineteenth to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p. 406.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促进了阿拉伯人对其文化和政治的认同,推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87)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305.年轻的阿拉伯学生试图发扬阿拉伯传统文化和政治秩序的优势,积极参与阿拉伯复兴运动。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阶层更愿意与美国展开合作,他们利用美部会提倡的独立、自由思想向英国和法国殖民者施压。阿拉伯大起义期间,麦加谢里夫(88)阿拉伯文“Sharif”的音译,原意为“高贵者”“贵人”“圣裔”。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后裔的尊称。近代麦加的统治者、伊拉克和摩洛哥的国王,均冠此衔,代表法蒂玛长子哈桑的世系,受一般穆斯林的尊敬和爱戴。后泛指伊斯兰国家中出身高贵或有政治地位者。侯赛因之子费萨尔谴责盟军之间的秘密条约和英国的《贝尔福宣言》,拒绝法国的托管,并给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发了电报:“我恳切地请求您不要把我留在吞食者的两爪之间。”(89)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201.
美国传教士的活动激发了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导致民族主义运动愈演愈烈,最典型的例子是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运动。1860年,第一个美国福音派的亚美尼亚教会成立。1865年,哈佩特福音联盟(Kharpert Evangelical Union)成立,拥有11个教堂、6个牧师和325名成员。到1890年,在哈佩特福音联盟成立25周年之际,美国传教士已经在亚美尼亚人中间建立了25个教堂,拥有近2,000名成员。(90)Heleen Murre-van den Berg, New Faith in Ancient Lands: Western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 247.美国传教士还帮助亚美尼亚人创办报刊,推动了亚美尼亚方言的发展,这成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觉醒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国传教士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的阿拉维派被卷入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之路。19世纪50年代,新教米勒特获得合法地位后不久,美国传教士便开始接触奥斯曼帝国的阿拉维派。阿拉维派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边远地区,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封闭,美部会的传教士可能是第一批进入这一社区的人。(91)Hans-Lukas Kieser, “Mission as Factor of Change in Turkey (Nineteenth to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p. 395.美国传教士被这个“独特的民族”深深感动,因为他们自称是新教徒。然而,美国传教士并没有改善这些阿拉维派的处境,反而因为新教倾向,使他们受到当地民众的孤立。
此外,美国传教士还对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人和保加利亚人等群体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起到间接的助推作用。在奥斯曼帝国的坦志麦特改革时期,库尔德人已经对自己所扮演的社会和政治角色感到不满,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美国传教士试图与库尔德人合作,虽然两者的合作并不成功,但传教士带来的阿拉伯—库尔德语传教书籍间接助长了库尔德人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92)Ibid., p. 396.美国传教士还积极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保加利亚人接触,他们将《圣经》翻译成保加利亚语进行传播,还出版了第一部现代保加利亚语语法书,间接推动了保加利亚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93)Joseph L. Grabill, Protestant Diplomacy and the Near East: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cy, 1810-1927, p. 19.
阿拉伯大起义和亚美尼亚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其他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给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带来巨大损失,导致当地美国教会学校和福音教会经费不足。1915年,在奥斯曼帝国镇压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期间,美部会投资的约2,000万美元和150名员工减少到大约一半,大量教会学校被迫关闭,不少传教士死于传染病。据估计,到1916年初,奥斯曼帝国的镇压行动导致大约50万亚美尼亚人逃往高加索、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大量亚美尼亚新教牧师及其助手遭到驱逐,给传教活动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94)Joseph L. Grabill,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the Near East, 1914-1923,” The Muslim World, Vol. 58, No. 2, 1968, p. 47.可见,美国传教士在间接引发奥斯曼帝国分裂的同时,也被分裂主义的“黑洞”所吞噬,其传教活动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而终结。
(三) 对奥斯曼帝国社会分化的间接助推作用
美国传教士带来的“第二次大觉醒”所提倡的价值观对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宗教系统是一种威胁,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分离主义”的后果。事实上,在整个中东地区,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人数很少。但是,美国传教士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传教士是西方入侵势力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西方对中东的殖民统治,成为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杠杆。美国传教士将以美国文化为特征的价值观输送到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角落,破坏了帝国传统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强调社会的同质化和各民族的团结才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美国传教士则希望强化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建立多元化的社会。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宣称建立多元社会,可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95)Hans-Lukas Kieser, “Mission as Factor of Change in Turkey (Nineteenth to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p. 397.美国传教士经历了诱发奥斯曼帝国分裂的社会分化和民族主义深渊的打开。
随着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帝国的大片领土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相继被分裂出去,美国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助推者的角色。帝国政府虽然对传教活动进行了干预,但效果有限。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显然意识到美国传教士传播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可能会“对一个多民族帝国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地方官员也将美国传教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几乎一致认为传教士传播的信息很可能“混淆人们的思想”,在公众中“播下不和的种子”。(96)Emrah Sahin, Faithful Encounters: Authorities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p. 10.
即便如此,奥斯曼帝国仍然低估了美国传教士的影响。帝国对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缺乏足够批判,导致民族主义价值观与传统的帝国价值观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美国传教士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谴责奥斯曼帝国的专制之外,还不断宣传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这些都使奥斯曼帝国的统一纽带更为脆弱。美国传教士诱发了奥斯曼帝国各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却对其中释放的苦难选择了袖手旁观,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美国对待亚美尼亚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美国传教士向亚美尼亚人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使他们对自己的宗教身份产生强烈的优越感。这是导致亚美尼亚人坎坷命运的直接诱因,面对奥斯曼帝国的镇压,亚美尼亚人指责美国传教士“鼓励煽动叛乱,却并未履行他们所承诺的一切”。(97)Edward Mead Earle, “American Missions in the Near East,” p. 405.
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事务,传教士的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同步。当传教士面临威胁时,美国当局采取的干预措施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分化。美国传教士所扮演的殖民扩张先锋的目的逐渐暴露后,奥斯曼帝国对其活动的打击和遏制也不断上升,这引起美国政府的强力施压。在美国总统的指示下,美国军舰先后六次被派往奥斯曼帝国的港口维护传教士权利。例如1904年,奥斯曼当局关闭了几所美国教会学校并逮捕了一些归化为美国公民的亚美尼亚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遣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前往士麦拿港,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约翰·利什曼在会见奥斯曼苏丹时提到了美国轰炸士麦拿的可能性。(98)Cagri Erhan, “Ottoman Official Attitudes Towards American Missionaries,” p. 207.结果,这些亚美尼亚人获释,美国教会学校获准重新开放。这种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民众对国家和君主的不信任,进而危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合法性,增加帝国社会分化的诱因。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奥斯曼帝国逐渐丧失了控制境内民众的能力,并最终在外国势力的干预下解体。当然,尽管美国传教士的影响因素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但也不能将奥斯曼帝国出现的整体性变革完全归咎于传教士的影响,其内部的变革因素十分复杂。
四、 余论
19世纪以来,美国海外传教运动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教活动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均形成空前之势,成为美国近代殖民主义扩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美国对外扩张的先锋,美国传教士受其自称的“天命”所激励,前往奥斯曼帝国传教,代表着基督教文明的美国和代表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在历史的转折点相遇,展开了一场跨越百年的、以冲突与融合为基本特点的文明互动。这场互动是千百年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一个缩影,代表着“基督教的美国”与“最后的穆斯林帝国”之间的文明碰撞。前者的国际主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表达出福音的天命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主义基调,而后者则“努力保持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以免迅速衰落”(99)Devrim Umit,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Network in Ottoman Turkey, 1876-1914,” p. 16.。“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一对长期互相伴随的矛盾统一的交往环节。”(100)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7页。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文明互动中,这一特征始终如影相随。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进行了多次文明互动。首次大规模的互动发生在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人征服时期。公元7世纪,随着穆斯林的对外扩张,那些曾经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人口大批改宗。公元1096年到1291年爆发的“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第二次大规模互动,这也是历史上两者互动最为频繁的时期,双方的互动表现为激烈的战争。15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的扩张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另一次大规模和长时间互动。西方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先行者和开拓者的角色。然而,西方对中东的传教活动既没实现促进穆斯林转信的宗教目标,还反而给中东基督徒的生存增添了不确定因素。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安纳托利亚基督徒遭遇重大挫折以来,该地区的基督徒人口一直在减少,而这一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所加速。(101)Eleanor H. Tejirian and Reeva Spector Simon, Conflict, Conquest, and Conversion: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p. 207.“9·11”事件之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中东地区的宗教冲突被不断激化,致使该地区基督教社区持续衰落。由此可见,当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的基调更多地凸显出冲突的一面,而文化的融合则表现得若隐若现。“从交往哲学上讲,宗教冲突源于将己方奉为主体,将他方视为顺从和受支配客体的‘主—客’式的交往观。”(102)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499页。西方基督教在与伊斯兰教的互动中往往陷入将他者排除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交往观中。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交往观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影响持续至今,也反映到西方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