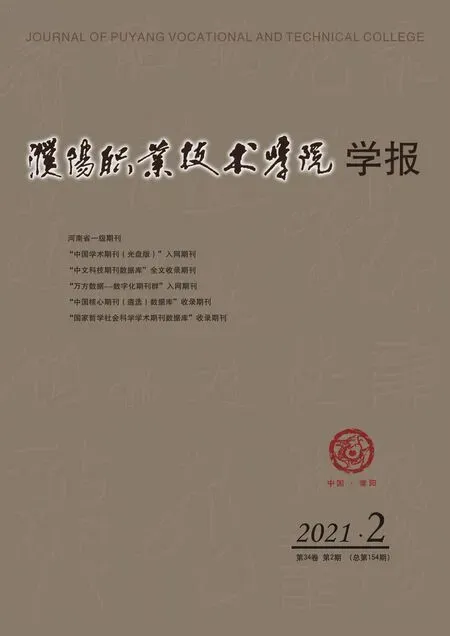论狄金森诗歌中的精神生态
吴业清,敖倩影
(1.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100;2.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谈及中国的隐居诗人大家一定能想到陶渊明,而说到文学史上的“阿默斯特的女尼”却有很多人忽略了艾米莉·狄金森。她孤独迷人、桀骜不驯、清心寡欲,二十几岁之后便呆在家中潜心创作,生前仅发表了7 首诗歌, 却为世人留下了1800 多首诗歌作品,主题丰富,涉及自然、人生、信仰、爱情、死亡、时间与永恒等方面,具有谜一般的神秘色彩。她酷爱乡野森林,亲近自然,善于用文字的组合和符号的衔接表达她内心的追寻,聆听来自万物的消息,她就是大自然的器官。她时常把自己当作一个“男孩子”,可以自由平等地徜徉在牧歌田园, 用性别身份的越界性表达对社会生态的思考,对民主平等的认同。同时,死亡、孤独、痛苦等主题亦是她精神的内省,表达出她对罪恶、自私、无情的灵魂的抗争。 一身白衣的素气的弱女子却是一名绿色的战士, 达到人生物我两忘的境界,时刻散发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为世人展现出她的生态智慧。
一、人性本真的呼唤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曾经在《岳阳楼记》中强调人要面对功名利禄保持一种恬淡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在狄金森的诗篇当中很容易看到她忘却功名利禄、泰然处之的心态。世间的人大多数都喜欢快乐、愉悦,而她却是反叛的,是一股逆流,她喜爱痛苦,就像费尔巴哈所说:“痛苦是诗歌的源泉。 ”痛苦更能反映人性的本真。 《我喜爱烈痛的脸孔》是狄金森刚刚隐居时的一首诗, 一张看上去不舒适的面孔呈现却是最自然的姿态,诗歌内容如下:
我喜爱烈痛的脸孔,
因我深知其真实。
人不假装抽搐,
或佯装剧痛。
当目光呆滞,
即是死亡。
无从伪装,
额上汗珠,
真朴的苦闷成串。[1](23)
诗人对“痛苦”的情有独钟正是对人性本真的追求,当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笑容反倒是成了人们出门最虚伪的面具,人们利用这个面具换取名利,获取欣赏,成为伪君子。诗人的语气表面上看起来幸灾乐祸,更厌恶丧失真诚之人的微笑的矫揉造作。因为这样的笑容背后无法探察人真实的感情。 这是一首看似消极但却渴求人性回归的诗歌, 暗示出人即使是处在黑暗中,也该明白心中的光明会到来。作者批判了人心灵的拜物化。 所谓心灵拜物化指的是在本来属于精神空间、 心理空间的活动领域却被物质与金钱填充[2](157)。 人只有在极度痛苦的时候才能呈现出自己的真诚,这是一件多么讽刺的事。狄金森把人性比作机器, 只有在断裂那一刹那才能听到人内心真实的呐喊,这样的“人”,她不屑一顾,所以诗人写到痛苦遭遇之时,并没有给与任何安慰,甚至眼睁睁看着这类人在烈火中灼烧。 诗人感叹人们在“物”的丰收中却丢失“心”的意向[2](156)。 丢失了心的人,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庄子在《逍遥游》中核心句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狄金森也喜欢用“无名”来诠释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无名”时常意味着隐逸、平和、宁静、淡泊。 人类不能沦落为社会的工具,更不要把别人当作工具,不偏执于自己,更要超越自己。 她生前出版的7 首诗歌没有一首是经过她本人同意。 作为意象派的先驱,她表达大胆、生动、充满智慧,却从未引起重视和注意,更别说给她带来什么声名。她有一首诗是这样呈现她的心灵暗语:
我是个无名小卒! 你呢?
你也是无名小卒吗?
竟然还会有两个!
做个名人多无聊啊!
多暴露—像只青蛙,
对着钦羡你的一方沼泽,
在长长的六月喧嚣你的名字。[1](65)这首诗大概是写于狄金森31 岁时,此时狄金森渐渐厌恶了泡沫般的声名。她很幽默、淡然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名者,她也很自信! 诗人又发出疑问,你呢? 是对他者灵魂的拷问, 诗人渴望得到肯定的回答。紧接着诗人很欣慰竟然会有两个无名小卒。说明诗人找到了知音,在这个世俗间还是有人敢于诚实、坦然地接受自己。“不要说!他们会张扬你该知道!”这是诗人对哪些精神真空化的人的鄙夷。 所谓精神真空化就是人类已经丧失了动物自信的本能, 失去了文化传统价值尺度, 而对生活产生了一种无聊或者绝望的态度[2](152)。 诗人甘愿做一个无名之徒,生怕“你”的声张引来声名显赫之人所有的麻烦,并且诗人经历美墨战争和美国内战, 曾经被视为崇拜偶像的父亲和哥哥也渐渐疏远于她, 这样的生活经历让她更看重生命价值,而名利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诗人述说到做个名人多无聊像一只聒噪的青蛙,“青蛙”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政治要人,而“沼泽”只不过是附和着青蛙的一群乌合之众, 是对过分招摇之人的一种讽刺。 “青蛙”整日喧哗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沾沾自喜也有大片随波逐流的“沼泽”盲目的羡慕迷失了自己。 诗人从社会形态上用比较的视角说明凡人和权势之人的区别,前者无权无势任人宰割,后者有权有势,仗势欺人,这就是一种平民和国王的对比,也是一种对权利的抗争。从文化层面看,诗人批判了灵魂空虚的人盲目崇拜着所谓的文化名人或者潮流先锋,没有自己的主见和风格,丧失了自己的信仰,也憎恨“有名”之人用符号话的权利、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去控制他人的人生。六月本就是炎热的夏季,诗句中,青蛙仍然在六月喧嚣,说明这种精神压力的可怕, 这种精神霸权主义暴力的可怕, 而诗人只能用“无名之辈”告诉世人,她仍旧是一个坚强的反叛者,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在这场战争中找到自我, 才能挖掘心灵中自由的空间。
二、存在感的疏离
周国平《在生命本来名字》中是这样说的:“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只是人们随着我们的成长,头衔、身份、职位等俗物琐事使人沉沦,反倒忘了‘无名’的事实。人们在社会为了一个称谓活着,忽略了生命中温暖和平和、健康的意义,精神陷入萎靡缺少幸福感,而幸福感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需求和体验的满足。人们过多关注商业消费、物质性消费、工业性消费却更多的忽略了时间性消费、精神性消费。[3]而狄金森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中早就发掘了人性存在感的疏离,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社会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2](155)。 《爱》这首诗一定戳中了无数读者的心。
爱像其他东西,我们长大了就不再适用。
所以把它收进抽屉里,
直到古老的方式再度流行,
类似祖父母的服装。[1](83)
这首诗中把爱定义为被收拾起来放在抽屉的衣服。因为它看起来过时不再流行,衣服只不过是被人穿在身上,长大了可以被经常更换的物品,是人的附属品。等到流行复古时才又把它拿出来展示。爱彷佛是在我们受伤的时候,就用它来抚慰内心,等到我们的伤痕修复好了,却把身边的关爱搁置一边。当我们在生活中历经千难万险,经历时间的磨砺之后,发现你珍爱的人和事情却并没有用心好好地珍惜。 这便是人生的遗憾。 人性往往是这样,童年的你天真、善良,敢于爱他人,青年时期你可能也曾奋不顾身地爱过某个人(某个思想、某个物件)。这里的他人泛指的是“个人、自然、社会”。 你拥有爱自己和爱他人的能量,而到了中年之后,反而那份热烈的“爱”的能力逐渐消退,最后自然地冷却下来,甚至如烟消失殆尽。当老年之时,蓦然回首,才发现“爱”所承载的回忆才是打动我们思想、撼动我们灵魂、寄托我们乡愁、燃烧我们青春之光的力量。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身体成长,智力的成熟却换来了灵魂的萎缩,爱的能力的丧失,到了中年阶段甚至找不到精神的归宿。诗人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存在感的疏离, 这是一种人与内心世界的疏离。曾几何时,亲人的温情还存留在我们的内心,青春的欢笑还在我们耳边荡漾,那朵珍爱的蝴蝶花,我们只肯远远的爱慕。这种疏离可能源于一些为了功名利禄的恶性竞争, 在争权夺利的环境下,关爱、同情、人际间的真诚合作之花再也无法开放。 大千世界,铺天盖地的物质主义,让你在面对他人痛楚时,你会冷漠,甚至有人会窃喜。 你再也听不到你内心发出的声音,更感受不到被爱的温度,认为被关切可能是另有目的。 当你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自我认同时你变得愈发弱小, 选择在强大的物质主义中放弃自我,拒绝被爱,更没有爱他人的能力。 生命中所有的坚守,由于你自我的放弃被统统瓦解,这正是一种精神的污染。
狄金森拥有饱满的生命和纯洁的灵魂, 她的爱依旧保持恒常、保持任性,她用自己高尚人格诠释自己的精神世界。 一首《友谊》表达她精神世界的丰富和爱人的功能。
万一看到你在——
汪洋中——沉下——
或快被命运打败——
隔天——将死——
或叩敲——天堂之门——无人来开
我会亲自骚扰上帝
直到他让你进来
诗中主人翁好似非常忧心将出门的挚友旅途的安危,于是写信或者面对面跟他说,若你搭船沉溺于海中,或突遭意外奄奄一息,或离开人世来到天堂口敲门无人应,我会用尽各种手段——包括骚扰、唤醒上帝不让你被遗弃、孤立无援。诗人甘冒大不韪去到上帝面前与之争论,足见两人友谊的深厚。诗句的口气带着玩味的意味, 这让我们看到这个充满爱的能量的女诗人为了生命中关心的人不顾一切, 这样的态度是认真但又带着真诚的感情, 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美学距离。 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中强调人一旦满足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就需要得到精神上的需求, 这个精神上的需求包括社会需要和尊重的需要,他们来自得到家人、朋友、同事的认同,来自自尊、自重和他人的敬重,友情便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精神需求。 狄金森时刻保持着孩子般未经污染的眼睛细微地观察人性中的真、善、美。精神不仅仅是“理性”的,它还是宇宙间的真实的形而上的真实存在,是自然的法则、生命的法则、生命的意向,人性中的一种向着完善、亲近、谐和的意绪和憧憬。爱、友谊是人类永恒的价值, 精神价值判断和情感价值判断是一致的。人需要在与自然、社会的接触和交往中形成自身精神的能量,获得生命的意义。
三、人性的自我和谐
一个人的自我和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形”与“神”的和谐。“形”指的是身体,而“神”指的精神。天人合一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的精神境界。精神中包括人性的多个层面, 弗罗伊德德精神分析法曾经论述到人格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本我、自我、超我。其中“本我”是原始的自己代表着原始的欲望、享乐,不受理性和社会欲望的驱使。 “自我”代表了个人意识,表现出人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受社会伦理和规范制约。 “超我”是人格中最高层次,他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内化而来的,也是调节“自我”的重要机制,是理想的自我。 所以人的精神层面的和谐只有在这三层意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做到人格的合理化。 狄金森的自我精神层面一直在寻求自我的和谐与完善。 她超凡的文学素养一直让她抑制住自己的“本我”、提升“自我”、推进“超我。 ”《幽灵》这首诗歌正表达出她善于倾听内心的声音,敢于压抑恶的“本我”,敢于做一个反叛的幽灵,与自我抗争,促成人性的和谐。
不只是寝室———有幽灵出没——
不只是房屋——
脑子里拥有的走廊--胜过
有形的地点——
安全多了,在子夜遇见
外在的幽灵
千万不要在内心遭遇——
那个更冰冷的群众。
安全多了,快跑穿过教堂的墓园,
铺石鸣响,
千万不要没带武器,当自己遇到自己——
在凄凉的地方——
自己藏在自己的背后——
该是最吓人的——
刺客躲藏在屋内。
算不上恐怖。
肉体借了一支左轮手枪——
他关上门——
没看到一个更可怕的鬼——
或更多——[1](241)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念和恶念, 这些罪恶感和懊悔感以及各种怪念头、幻想、本能常常会在夜深人静中显现。 当一个人独自在家中,躺在床上,寂静无声,这时幽灵们便会踏入你的心头。不怕鬼的人真的不多,内心的鬼其实是最吓人的,也是最难破除的梦魇,因为那是你人性的一部分。这些幽灵穿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即使你加快双腿的步伐也躲不过它游走的长廊。当我们与它迎面相见,我们蜷缩着身体不敢抬头。 那是我们的创伤、悔恨、私欲、占有、罪恶感, 或是我们充满黑色的忧郁和那些无法从容面对的哀伤。也许忧伤仅仅只是面目狰狞的小幽灵,而那些看似温和亲切的幽灵才会对你造成极大的伤害,最后甚至占据你整个意识,控制你的肉体,让你精神分裂甚至失常, 整天沉浸在恐怖与幻想当中无法自拔。 诗人神秘色彩的黑色的主题,用幽灵、鬼象征自己内心遭受威胁的秘密,恐怖源于恐惧本身。这种身心分离,灵与肉的分离,人我对立,正是人性异化的表现。人性只有处于和谐状态才有自我,才会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五味协调谓之和, 五音协调谓之谐,这便是和谐的本义。 人必须走出自我矛盾、自我分裂的怪圈, 让人格中不同的自我意识达到平衡发展的状态,才能走向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自我和谐意味着有拥抱自我能力,不走同质化,不人云亦云,限制人性中冷漠、贪婪、懒惰、羡慕、嫉妒等,摆脱人格中的困境,摒弃人格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工具主义思想。用人性中的爱心、同情心、责任感、乐观等积极的因素去打倒一些消极因素, 时刻反省人格自我意识的多维性,做到知、情、意、行间的统一,促进心理人格、道德人格、法律人格、主体性人格的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用崇高的整体性人格去塑造健康的人生观。
四、结语
本文从生态诗学的角度解读了艾米莉·狄金森的五首代表性的诗歌。 诗歌内容反映出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遭遇的精神危机,是精神真空化、心灵拜物化、存在疏离感的表现。 诗人更是世界的先知,能够运用素朴的语言唤醒他人的意识, 告诫世人远离世俗化、物质化、功利化的观点。 在迅猛发展的信息化社会,有很多人都面临着精神的困境,或是因为科技产品的方便快捷造成了情感疏离, 或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大肆捕杀野生动物造成人类的疫情, 又或者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对自己身边的人不择手段。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放下高能量的物质欲望, 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消除主客二分的思想,重拾人性本真,用爱的花朵去浇灌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