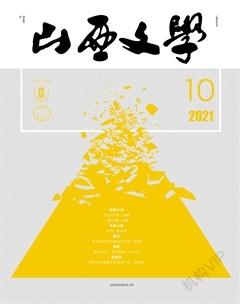邢小群老师与我的处女作
1983年,我二十岁。
在家里憋了一个暑假之后,9月初我又返回山西大学,开始了大三阶段的学习。那个学期开设的课程有古代汉语、唐宋文学、外国文学、当代文学、政治经济学和形式逻辑,这是必修课。选修课只有一门,名曰诗词欣赏。
操练了两年之后,我对大学生活似已轻车熟路。上课,读书,不时看场电影,偶尔会会老乡,就把每天的日子塞满了。在那种单纯得很单调的生活中,上什么课读什么书自然是重头戏,但课程是早就被设置好的,不需要我们操心;任课老师也已事先配置到位,容不得我们选择。我们那一届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分成了甲、乙两班,每班45人,又基本上是小班授课,所以,哪位老师教我们什么课,是缘分,也是命中注定之事。如今,我在当年的大学毕业纪念册中发现,当代文学课那里写着两位老师的名字,但王振华如同天外来客,根本不在我的记忆系统之内。我只认识邢小群,因为她被派到乙班,教了我们一学年的当代文学。
就这样,在1983年的秋天,我们与邢老师相遇在一起。
那个时候,邢老师只是三十岁出头。她个子不高,衣着朴素,梳短发,戴着一副深色宽边大框眼镜,显得很潮很飒爽。但一开口说话,又显出知识女性的大气沉稳,是大家闺秀范儿。此前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大都说不周正。邢老师不仅普通话字正腔圆,而且还京腔京韵,一下子就把原来的老师甩出了几条街。加上她又是女中音嗓子,一句句话飘过来,仿佛谱上了乐音,瓷实,悦耳,好听。这样的老师走进课堂,立刻就抬高了我们的期待水位。
学生对老师的身世总是充满了好奇,但消息灵通人士打探过来的情报却十分有限。那时候我们只晓得邢老师是工农兵学员,北京人,插过队,却不知道她是诗人、作家、《平原游击队》的编剧邢野之女,更不知道她小时候曾与闻捷、李季、公刘、郭小川、赵树理等诗人、作家住过邻居,有过交往。许多年之后,我在她书中读到这些掌故,不禁感慨:邢老师所讲述的那些当代作家,有许多她是见过真佛的,怪不得当代文学被她讲得那么贴心贴肺,为什么她当年没在课堂上显摆一番呢?
后来我读汪曾祺文章,看到沈从文教给他的小说秘诀是“贴住人物写”,方才明白讲作家作品,也是需要贴住人物的。莫非邢老师在那个年代已悟出了这个道理?
邢老师的这种“贴住”很有讲究。1990年代中期,我在一所地方院校曾经客串过两三轮的当代文学课,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要想把五六十年代那些没多少意思的诗歌讲出点意思,把“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类的“红色经典”讲得不像经典,还是需要相当大的本事的。那时我已读过陈思和的《民间的浮沉》等著名文章,好赖还可以凿壁偷光,现炒现卖。但1980年代初期,连像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都没一本,一切都得筚路蓝缕,这课可如何往下讲?我以前写文章,曾对邢老师的课有过一句话点评:“她分析作品时常常能化腐朽为神奇,让神奇更神圣。”如今在其回忆录中,我则看到了她自己的更多说法:“我讲郭小川重在强调他作为一个诗人在个性上、思想上的矛盾,从而更能发现一个优秀诗人的人性深度和思想矛盾。”“我仍然承认《创业史》的现代的、诗性的写法。在当代长篇小说中,它达到了最高点。可惜,它所宣传的合作化道路,没有经受住历史的筛选。”很显然,那个时候的邢老师已注意到了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她在课堂上,绝不是要么好得很,要么糟得很,而是面对众口叫好的作品一声叹息,面对挨批被整的作家充满质疑。记得初上大学,文学概论课的老师就把《苦恋》剧本的油印稿发放下来,人手一册,供我们批判。1983年后半年,“清除精神污染”的警钟又开始长鸣。这些举动一惊一乍的,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但邢老师似乎镇定自如,我行我素。她的课离当下意识形态最近,却并没有成为“松紧带”政治的晴雨表,反而像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许多年之后,我在其回忆录中看到了她的那篇惊心动魄的“审父”之文,忽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邢老师当然是在对她那个充满了暴戾之气的父亲进行反思,但又何尝不是对那种“革命使男人雄壮,使女人粗糙”的革命文化刨根问底?而她那颗怀疑、清理、反思乃至批判之心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早在1980年代的课堂上就开始萌动了,只不过那时候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我们限于年龄、阅历和知识结构,也不一定能听出更多的弦外之音。邢老师在她的回忆录中说:“那时,我在讲台上努力挣脱着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禁锢,总希望比别人大胆一些,讲出作品的新意所在。開顶风船虽说有风险,但深受学生欢迎。”而我则想到了马克思的那个著名说法:“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旦从“后头”思考,邢老师的当代文学课就获得了新的意义,那是对我们的全面启蒙——文学的,人性的,政治的,甚至人生格调的。后来我写文章,不时会提及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而实际上,这种新启蒙是全面展开、遍地开花的。现在想来,邢老师的课堂于我而言,就是新启蒙的一个重要场所,比如朦胧诗。
大学时代,我对诗歌一度极为痴迷,于是读诗、抄诗然后试着写诗便成为例行功课。我曾经以为,我的那种迷狂是青春、时代和校园风尚的产物,与课堂教学关系不大,但邢老师的回忆录纠正了我的看法。那里面有她讲授朦胧诗的内容,甚至她还引用了我的同班同学赵雪芹的几句感言,以作证语。赵雪芹说:“当初,你的课激发出了我们空前绝后的学习热情,我们一个班的学生集体攻占了南边报刊阅览室,‘三个崛起等热文被我们争相传阅。朦胧诗抄了一本又一本,以至于许多人到现在对诗歌的欣赏接受只到朦胧诗便戛然而止。”
说得好!我就是那种既抄朦胧诗又把朦胧诗当作新诗标高的学生。如今,我打开大学时代的一个笔记本,发现其中抄写的大都是诗歌。而诗歌中朦胧诗抄得最多,朦胧诗中北岛、舒婷的诗又位居榜首。记得那时候买不到《双桅船》,我就把舒婷的这本诗集从图书馆中借出,几乎全部搬运了一遍。还有北岛的《云啊,云》《路口》《睡吧,山谷》《明天》《枫叶和七颗星星》《雨夜》……“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即便今天来读《雨夜》,我依然忍不住会隐隐激动。时代的铁幕,沉重的爱情,飞扬的意象,组合成青春与自由的誓词,唤醒了我对没有委屈的天空的向往。我觉得这才是诗,这才配得上诗歌这种高贵的文体!而这样的诗篇,也塑造了我欣赏新诗的审美旨趣。这种旨趣显然无法适应后朦胧诗的松松垮垮,更会在黏黏糊糊的下半身诗歌面前败下阵来。赵雪芹说得没错,我确实没有与时俱进。
但是,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16开的笔记本是“三好学生”的奖品,于1983年6月发放到我手中。这就是说,我抄诗的时间重叠在邢老师授课期间。莫非我是听了她对朦胧诗的解读才有了那种疯狂的举动?我喜欢新诗的天眼是不是那时才被她突然打开?
三十八年过去,往事已如烟,我的记忆模糊了。
没有模糊的是一些细节。我在1983年11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当代文学课的邢老师给我们推荐了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读完以后感到非常好。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统一在一起,苏联文学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一斑。作品描写了……”刚读完这部小说,我就听说电视台要在周日的晚上播放这部电影,大喜过望,但中文系没电视可看,我与几位同学只好跑到对门的省委党校碰运气,结果吃了闭门羹。又赶快折返到校园里四处打探,最终才在工程队那里找到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饱上了眼福。
邢老师的课堂就是这样,她当然是在讲中国当代文学,但外国文学的好作品也不时被她广而告之。近水楼台,我们便成了最早的受益者。
邢老师也喜欢旁逸侧出。讲到戏剧部分时,她忽然就对地方戏发开了感慨:“许多地方戏啊,听得让人无法忍受。比如上党梆子,一会儿唱得很低,一会儿声音又猛地窜上去了,用的是假嗓子,听着难受。”刚说到这里,大家就笑起来,我笑得似乎更加放肆。上党梆子是晋东南一带的地方剧种,我从小听戏看戏,对上党梆子版的革命样板戏不可谓不熟悉。但经年累月,并没有培养起我对家乡戏的爱心,反而觉得其行腔运调直眉楞眼的,吵得慌,很土。现在,邢老师居然也对上党梆子直撇嘴,说出了我的心中所想,岂有不开心之理?许多年之后,我见邢老师写有《思缕中的赵树理》,记录其少年时代与赵树理家比邻而居的生活琐事,就想看看是不是赵树理老唱上党梆子,影响了她的视听感受。但邢老师并未写到这里。
一学期的课很快就到头了。邢老师说,她这门课要考试,同时还要写一篇评论,作为课程论文。那个时候,我已读过路遥的《人生》,又读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分析了一番男主人公,提交上去,题目是《谈高加林性格的典型性》。邢老师看后给了我58分,并写批语道:“人的价值是由什么确定的?作者创造这个形象要想说明什么?能把这层意思讲出来就更好!对这个形象把握得较准确,评价也适度。文字明快,很好!”那个学期,当代文学这门课我得91分,应该说分数还不错,但第二学期初邢老师讲评我们的作业,我却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她说:“你们的评论五花八门,但写来写去,都离不开‘典型二字:不是典型人物,就是典型性格,要么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你们就不能从其他角度入手写点别的?理论太贫乏了!从感受出发,端出你自己的体验,也是一种写法。阅读也讲究生命体验……”这番话虽然是被皱着眉头的邢老师说出来的,却并不怎样威严,而是同情中有惋惜,惋惜中有不解。于是大家就笑,仿佛邢老师的批评与自己无关。而我一尬笑起来,就觉得自己的小脸发烫了。
许多年之后,我在《遥想当年读路遥》中记录了这件往事,又顺便写道:“那还是一个理论和理论术语乏善可陈的年代。由于刚学过‘文学概论不久,由于这门课又反复念叨典型,我们自然便活学活用,把典型看作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后来每每想起这件往事,我便觉得自己当时刚刚舞文弄墨,基本上还是文学评论的门外汉。我只想着如何套用理论,如何让理论装潢门面,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读作品时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如今,我更想说的是,邢老师的这番点拨,很可能让那时候还懵懵懂懂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写文章不一定非得穿靴戴帽,“惟陈言之务去”才最重要。而这个道理在我心中发酵半年,肯定也影响到了我第二篇课程论文的写作。
第二学期邢老师都讲了些什么,其实我早已记不清晰。大学时代的听课笔记被我保存了二十年,后来举家来京,书已太多,只好精兵简政,丢弃了那些本子。当代文学方面,我只是保留了一套上下册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此书由十八所高等院校当代文学教材编写组编写,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以作纪念。许多年之后,大学同学陈树义为我提供了他的听课笔记,我才约略想起了邢老师的授课框架。但是,也有一些内容是印在我脑子里的,根本不需要借助笔记提醒,比如张承志。
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親》获奖(1978)到《黑骏马》再度获奖(1982),张承志早已蜚声文坛,但我却对他一无所知。是邢老师对这位知青作家的介绍和分析,才让我初步领略了他的风采。讲“十七年文学”时,邢老师还适当搂着,好处说好,差处说差,一分为二,辩证到家。但讲到“新时期文学”,她往往就hold不住了,于是喜上眉梢、神采飞扬就成了她的惯常表情,激情澎湃、语重心长又成了她的话语风格。“张承志的小说写得太棒了……你们去看看他的《黑骏马》,像叙事诗,沉重,苍凉……他最近刚又发表了一篇《北方的河》,中篇,写了五条河,没什么故事情节,主人公孤傲,坚韧,百折不挠,小说仿佛抒情诗……苏联有个作家叫艾特玛托夫,写过《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永别了,古利萨雷!》等等名作,浪漫风格,底层情怀,写得特别棒!张承志显然是受了他的影响……”
好嘛,邢老师又开始实时播报了!
肯定是被她那种声情并茂的分析所感染,我立刻奔赴南馆那个期刊阅览室,先读《黑骏马》,果然写得好,那就干脆把张承志的作品一网打尽。《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青草》《黄羊的硬角若是断了》 《阿勒克足球》……《绿夜》,我先把20篇左右的中短篇小说按发表时间顺序整理成目录,然后一篇篇寻找,一篇篇阅读。《北方的河》在《十月》杂志上读过后意犹未尽,适逢《小说月报》(1984年第4期)出刊,见上面转载了这篇小说,立刻买回一本,以供我反复阅读。小说全部读过后,我又开始读关于张承志的评论,以便丈量我的感受与评论文章之间的距离。读到精彩处,又忍不住摘抄起来——《大地与青春的礼赞》(王蒙)抄了三五段,《〈黑骏马〉及其它》(曾镇南)则抄了三五页。还有贺兴安的《雄浑深沉的琴声》,陈骏涛的《人生的搏击者》,周政保的《走向开放的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邢老师说艾特玛托夫写得好,要不要读他的小说?当然需要读!邢老师的鉴赏力高,判断力强,她推荐的作品早已是信得过产品,不读岂不是要抱憾终身?于是《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上下册(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我先借后买,挨个儿阅读其中的中短篇,然后又扩展到他的长篇《白轮船》和《一日长于百年》。
现在我必须承认,那是一次奇特的阅读之旅,从张承志到艾特玛托夫,我读着、想着、感动着也思考着,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张承志的作品中有一种孤傲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是很容易征服年轻人的心的。当然,我也承认,“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往往很傻很天真,我们常常通过文学看世界,文学也就成了我们反观现实世界、进入理想世界的秘密通道。它整合着我们的经验,塑造着我们的精神,也实实在在地参与了我们对现实人生的建设。因为《北方的河》,我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那期《小说月报》。大学毕业后的好几年里,我都会不时去温习这篇作品,从中汲取着浩然之气。于我而言,它是比《平凡的世界》更励志的作品。因为这次的大面积阅读,我对张承志的兴趣又一直延续到他那个“以笔为旗”的年代。读过他的随笔集《荒芜英雄路》和《无援的思想》,尤其是读过他的《心灵史》之后,我又一次热血沸腾起来。面对一些人对他的文化围剿,我甚至还写了一篇《保卫张承志——〈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批判之一》的文章,发表在陈树义主持的内部刊物《上党学刊》上。2007年,应《南方文坛》张燕玲主编之邀,我又写《〈心灵史〉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一文,算是对1990年代的张承志的一次迟到解读,但实际上,那也是对我自己青春阅读往事的一次清理。我还想写一篇《重读张承志》的随笔文章,把我彼时更复杂的感受诉诸笔端,可惜写了两千字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那些感受也终于风流云散。
1980年代的感受幸好已被记录在案。当邢老师说第二学期不用考试只需提交一篇论文作为考查成绩时,我的选题实际上已经有了:就写张承志!这回我不用“典型”,不信就写不出一篇好作业。我在期末忙活一番,终于完成一篇自认为还不算短的长文——300字的稿纸写了整整30页,名为《足球·马·河——谈张承志的小说创作》。那时候我还不会提炼标题,只好以张氏三个中篇小说名代之,以暗示其中的象征手法。仿佛是觉得此文来之不易,我在文后还煞有介事地署上了写作日期:1984年6月16日。
1984年秋,开学不久,当代文学课的作业就返回到我们手中。我见自己作业的封面上打了“优”,心里便踏实下来。打开看,发现其中几处论述都被旁批为“好”。翻到末页,那里不仅有个大大的“好”字,而且还有一段批语:
这篇文章基本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你应当投稿。当然,发表一篇文章,除了文章本身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因此,要想成功,也得拿出《北方的河》里‘我的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祝你成功!
心花怒放,秋高气爽!本来我也就是想摆脱“典型”困扰,让邢老师看看我有没有长进,却万没想到她会给我这份作业如此高的评价。基本达到了发表水平?投稿?说心里话,反复看过几遍评语后我又有些恍惚。那个时候,虽然我也读过一些文学评论,但对评论文章的“发表水平”根本没有概念,“投稿”更是从未想过。我总觉得,大概只有曾镇南们才有资格“投稿”或“发表”,与他们的生花妙笔相比,我还差着行情。但邢老师却说到了火候,她的判断力一向精准,我岂有不听不信之理?读张承志的书,听邢老师的话,照邢老師的指示办事,没准儿就能成为一枚好战士。思前想后几日,“北方的河”开始在我心中呼啸,我禁不住跃跃欲试了。
但往哪里投稿呢?那时候,我对评论刊物所知甚少,对投稿之事更是两眼一抹黑,如何走出这一步,于我已是困难重重。仿佛是猜透了我的心思,有一天邢老师忽然找到我的宿舍,她先是评点一番我文章的优劣,然后说:“这样吧,我给你列几个刊物。成都有个《当代文坛》,辽宁有家《当代作家评论》,陕西还有个什么来着?”她一边说着,一边把这几个刊物的名称写在我作业的背面。“对了,河北还有张专业性报纸,叫《文论报》,里面有个‘青年评论家栏目,要是往那里投,我正好认识一位编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说到这里,她略加思考,便在我找来的一张白纸上写起来了。“不过,”邢老师说,“报纸发不了长文章,顶多三四千字。要是给《文论报》,你得好好压缩一番。”
接过邢老师的那个短笺,只见上面写道:
王斌:
你好!现有我的学生的一篇评论张承志的文章,我感到不错,你看能否用?不行就给他退回。余言再谈。
祝
改革成功!
邢小群
我很感动,也一下子如释重负。想不到在我这里大发其愁的事情,邢老师三下五除二就帮我搞定了。我去南馆侦察了一番《文论报》,发现该报由河北省文联主办,预告中说:从1985年1月起将改为对开大报,每月两期。我抄下地址,又去浏览一番《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等刊物。随后,我又打开这篇作业,从头看起,琢磨着怎样删减字数。
但刚删几段,心里就犯开了嘀咕:缩写、扩写、改写是我高考时就操练过的作文类型,掐胳膊去腿并无多大难度。待缩写成功,再配上邢老师的推荐信投稿,发表虽不能说十拿九稳,但估计也八九不离十吧。可是越往下删,又越是心疼,心里也越就不是滋味:我啃啃哧哧写了那么多,为了发表却不得不拿掉一大半,这就好比一个农民种了一亩三分地,收了九百斤玉米棒子却只有四百斤算数,那五百斤怎么办呢?愁眉苦脸了许多日子,忽然有一天我开窍了:既然邢老师说基本达到了发表水平,那就意味着我的文章到哪儿都能基本发表吧,既如此,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豁然开朗之后,我立刻把自己的稿子略加润色,再誊抄一遍装信封,寄到了成都市布后街二号——《当代文坛》编辑部。为什么寄往那里?道理明摆着嘛,这是邢老师推荐的刊物,而且她把此刊列在了最前面。
许多年之后,陈树义给我发来一张图片,上面是邢老师写在他期末论文后的批语,占多半页稿纸。这张图片激发了我的寻找欲,于是翻箱倒柜一番,我也终于找到了我的那篇作业。拍过图片后,我把我俩的批语一并转给邢老师。不一会儿,她喊着我的微信名说话了:“山药蛋 ,你注意到你文章后面批语的字了吗?是丁东写的。当然是我们的共同想法。”
天哪,原来是这样?丁东是邢老师的丈夫,著名的文史学者,这么说当年他也参与了对我这篇习作的审读?然后他们又商量一番,由丁东执笔,写出了那段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批语?
我将信将疑,立刻找出被我保存多年后来又被我扫描成电子文本的推荐信,比对了一下笔迹:邢老师的字端庄清秀,丁老师的字清秀端庄,很有夫妻相。但仔细看,丁老师行书的幅度要大一些,怪不得我几十年都没有发现这个秘密!
于是我把推荐信的图片也转给邢老师,说:
“明白了邢老师,这才是您的字。”
“哎呀!都留着哪!”邢老师立刻回应。
“哈哈,革命历史文物!以后我写您就有证据了,以前只是捎带着写过。”
“我不值得写什么。”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事件啊,怎么能说不值得?”
是的,确实是重要事件!回望我的1984,依稀记得听过一次山西五作家的文学讲座,看过一场长达八小时的电影《解放》,全班同学去迎泽湖划过一次船,周峰的《夜色阑珊》成了我们初学跳舞的伴奏带……然而,所有这些都已如烟似雾,漫漶不清,青春的往事也越来越变得空空荡荡,流失了许多细节。但唯有这件事情——张承志、作业、邢老师的批语、当面写出的推荐信——却长留在记忆里。它真真切切,嘀嘀嗒嗒,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接通了我的来路,响彻在我的进程。有时候我会想到,那时的我就是找不着北的吴琼花,邢老师(以及她背后的丁老师)好比那党代表,“常青指路”之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能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又一直与笔墨为伍,很可能都与这个事件有关。记得萨义德说过,只是因为回溯,“开端”才有意义。如今我遥想自己的写作“开端”,那一刻忽然变得灯火通明。
邢老师的做法也让我油然生出效仿之心。许多年之后,我在大三学生提交的期末论文中发现有两篇写得不俗,基本上达到了发表水平,便让他们修改一番,直接推荐到我们主办的《文化与诗学》上。编务会讨论时有人说,我们的刊物从未发表过本科生论文,鉴于种种考虑,此头不可开。我唯唯,才意识到物换星移几度秋,1980年代早已一去不回。
但是,我那篇今天看来稚嫩得一塌糊涂的习作却发表出来了。1985年2月的一天,我收到了《当代文坛》的用稿通知。通知中说,我的文章将在第3期刊发,“为了怕耽误时间,使你担心,同时为了避免一稿两发的现象,特此通知。倘不同意我们的处理意见,望速告。”我高兴都来不及,怎能不同意呢?不久,样刊寄来,打开看,发现编辑只是修改了标题,原题被改为《一个青年作家的足迹——略论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内文则几未改动。——哈哈,玉米棒子全卖光,《扬鞭催马送公粮》,我的耳边顿时响起那首欢快的笛子独奏曲。
随之到来的还有百十来块钱稿费。
2012年5月,在《当代文坛》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我讲述了这篇文章的幸运之旅,然后便开始感慨:“这个故事也许能反映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种风貌:一个大学生把自己的处女作投给了一家刊物,他没有关系,没有得力的人举荐,而作者本人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名气。用编辑的话说,这是属于自然来稿。而编辑部收到这篇稿件后,没有在意这个作者的身份和名气,也没有说让这个作者出多少钱的版面费,而是认真对待,仔细审稿,并很快给他发出了用稿通知。不久,他不仅收到了样刊,而且还得到了平生的第一笔稿费。他用这笔稿费请班里20位左右的同学吃饭喝酒,之后还略有剩余。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只可能发生在我所经历的80年代。如果放到今天,也许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会出现问题。”
岂止是文章,就连房子都出了问题。2020年严冬的一天,听说邢老师所住的那个香堂新村遭遇强拆,我便拽上张巨才老师,驱车50公里一睹究竟。那是一幢三层小楼,我们随邢老师、丁老师走到顶层,只见一百平米的大房间转圈放着16个书架,书架的每一层都码满了书。“当时就是因为书太多,没地方放,我们才买了这里的房子,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情。”邢老师平静地讲述着这个房子的来历,那时她已年近古稀,头发花白,但依然健谈,还是当年给我们上课的嗓音。“这些书我们得处理一大半,要么送人,要么卖掉。你需要什么书,可以随便拿。”
我们开始聊天了。张老师不清楚我那篇处女作的故事,我便借机讲了几句。说起当年的那封推荐信,邢老师插嘴道:“你知道那個王斌后来干嘛了吗?他成了张艺谋的文学策划,是《英雄》的编剧。”不知道,我当然不可能知道。王斌于我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但是一提到这个名字,我还是感到一种温馨。
准备告辞时,两位老师送了我一兜子他们自己写的书,而我则挑选了一套邢老师购于1978年的《创业史》,留个念想。
回到家来,打开这套《创业史》,见里面勾勾划划处甚多,旁批眉批也不少,不由得感叹:邢老师当年读得可真是细啊!翻到第十五章,看到开头那句话被邢老师用铅笔划住了:“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她在旁边批注道:“哲理!”而这句话因被路遥题写在《人生》的扉页上,早已广为人知。弱冠之年的我留意过这句话吗?我又想起我为邢老师提交的那篇很“典型”的作业了。
也把邢老师送我的书——《凝望夕阳》《我们曾历经沧桑》《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置于案头,准备复读和新读。我早已知道的情况是,大概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邢老师就转向了口述史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采访了许多文化名人,抢救了一批宝贵资料。那是她回京之后做的主要事情。她在书中说:“我内心总是有一种还原历史真实的冲动,而不愿仅仅局限于当下的价值判断。”是的,真实常常隐藏在当事人的心中,访谈便是打开历史皱褶、让记忆说话的一种有效方式。
读着邢老师的书,我仿佛又回到了1980年代的课堂。只是,这一次多了更加丰富鲜活的历史细节,我可以好好补补课了。
2021年7月31日
【作者简介】赵勇,山西晋城人,现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著有《赵树理的幽灵:在公众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等。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看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