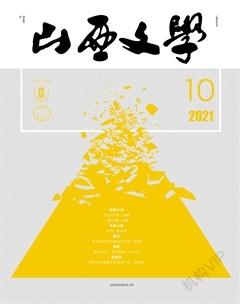寒夜守光,君子豹变
晚清七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真正具有天崩地坼意味的大变革时代,中西交冲之中涌现出无以数计的显宦重臣、士子文人、变法志士、革命党、清流派、绅士、流氓与军阀……璀璨彪炳的烂然星辰之中,孙诒让(1848-1908)算不上光彩照人,相较于那些纵横捭阖的治世能臣或者命运跌宕起伏的阴谋家与冒险者,他的大儒乡贤的经历过于平淡,谈不上具有特别的戏剧性和传奇性。但他也并非籍籍无名的普通士人,从父辈戚谊到同侪友朋,都可称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尽管中了举人之后,数次会试皆未中,然而终究能以治经注疏、实业教育闻名于世,成为学术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书写这样一个人,无疑是艰难的:受限于史料中的真实存在,无法向壁虚构、踵事增华,起伏不大的人生也很难找到一个切入点,容易流入到浮泛的流水账之中。
胡小远、陈小萍的《蝉蜕——晚清大变局中的经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后文简称《蝉蜕》)则将孙诒让置入近代变局的精英士人群体之中,以他的生命轨迹为连线,贯穿他的师友圈,实际上是期望通过这个个案勾勒出整个精英士人群体在晚清时候的生命依归与价值取向。因而虽然作者和为本书写“导言”的赵柏田都将之称为“长篇历史小说”,那也仅仅是因为它在史料基础上增添了为数不多的想象性细节,整体而言可以视作为一本颇具学术性的传记。其实,“历史小说”這一提法原本就充满了内在的悖论:一般而言,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梁启超畅言“新史学”之后,“历史”与“文学”分属二途,这是现代学科分类的必然结果:一是倾向于实证求真,一则是以审美为中心的形象塑造。虽然在后现代史学之后,两者都被视为一种“叙事”,但现代以来形成的认知范式大体并没有逾越这种规制。回首现代以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尽管在不同的史观之下诉求不同,但总是以人物的命运遭际与形象性格来折射、反映时代与社会的转折与变化,叙述者即便有插入议论,但往往不会喧宾夺主。《蝉蜕》则不然,它尽管以孙诒让的一生行迹为中心,但并没有特别塑造其形象,而侧重于对于晚清变局时代与其生命史相重合的一个甲子(1848-1908)时间里诸种社会思潮与人物的关系纠葛。
孙诒让在这个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处于中西碰撞里执守儒学元典的抉择,看上去似乎颇有保守主义的倾向,然而正如先秦儒家从来都有一种“以复古求革新”的精神,他在事功与立言之间的徘徊以及最终投身经典和教育,显现出晚清思想与精神中的焦灼与试图坚守文化的努力。他的成就固然有目共睹,然而无论是对于周礼的正本清源还是墨子的诠释训诂,在现实层面都已经不再能发挥理想中的功效(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使得他的尝试烙上了一层悲怆的色彩。有意味的是,这个在当时当地不曾有效发挥社会功能的学术事业,在时过境迁之后反倒日益显示出其拭旧如新的熠熠光华。从长时段看,孙诒让一生的精神历程确实如同蝉蜕,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这中间或许有“寒蝉凄切,对长亭晚”的凄惶,但更多是“韬精殊豹隐,炼骨同蝉蜕”(李颀《谒张果先生》)的想象,最终他的成果如同蜕变后留下的晶莹剔透的壳,作为急剧变化时代的象征性物象之一,成为后学可以不断回首与汲取的遗产。所以,《蝉蜕》更多的意思体现在其认识功能,而非美学功能,因此倒不必恪守“小说”的陈规,径直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历史写作类型,体现出某种意义上的“真”——这个“真”不是实证主义的真实,而是时代运行的走向和趋势的真实。它当然无法被归结为某种必然的历史“规律”,却是时过境迁之后以“后见之明”呈现出来的历史脉络图。它所涉及到的事情必有出处,与纯然的文学创作不同,进而也带来阅读期待视野的差异——人们更愿意从中得到通达的见识,正如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1]。
孙诒让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一般的历史叙述中,这个时间节点被视为近代史的开端,海国图志、富国强兵、开眼看世界之说已然兴起,但这只是少数先知先觉之人,大多数人依然处在盲目躁动之中,如同在凛冬暗夜听闻雷声隐隐,心中怵惕,却茫然无措,不知来处与去路。这一切不是纯然外来刺激的反应产物,也是中国文化与学术自身内部发展的结果,如同陈来所说,在十八世纪儒学的精英世界已经面临真正的挑战,挑战恰恰来自于理想的失落和考据学及礼学的兴起,也就是说乾嘉之学是以理学的退场作为前提的。乾嘉之学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是从儒学史和彼时的时代社会而言,都是一个远离理想、脱离理念、没有思想的时代。[2]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对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学术研究提出所谓的“学术职业化”问题,认为文人职业化是对儒家正统出身的祛魅,而考据学在18世纪知识话语中的主导地位撼动了儒家信仰体系的基础。这是一个充满了内在冲突的场景:一方面考据对于理学的空疏心性之论是一种反拨,而后者正是统治者所依恃以愚民的观念与方式;另一方面考据本身具有与近代科学方法的接近性,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结果上都促成了关于儒家学说的再认识和重构。[3]其结果是经学地位下降而史学地位提升[4],孙诒让时代的经学家们正是内在于这个中国思想与学术大转型的过程之中。
在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中,文人和科举制度的崩坏显示了18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转变,那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最终解体。乾嘉学派强调考据和儒家礼仪制度的研究与实践,是彼时思想学术与精英文化的关怀所在。礼仪被转化为道德权威,并通过科举制度兑换成政治资本、身份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在这个知识的分化、衍生、改组、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士人的身份认同、生存方式、职业选择、学术范式、权力和权威诉求、自我呈现都相应发生了改变。商伟通过对《儒林外史》的分析提出了彼时两种不同类型的儒家礼仪,一种是二元礼,它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工具性的;既是基于神圣道德律令的规范性制度,同时又提供了社会交换、利益协商和维系社会政治利益关系的合法手段。一种是苦行礼,体现为重建儒家礼仪的努力,一方面试图在儒家思想所允许的范围内,退出或超越世俗世界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则将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绝对化,并通过行动贯彻到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去,强调以实践代替已经泛滥堕落的言述。[5]这种提法未必得到广泛认同,却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礼学的日益脱离生活实践而成为意识形态。
晚近的儒学研究指出,明代的礼学主流是家礼学,家礼学不是研究王朝礼、聘礼,是落实在社会民间的礼的体系,真正能够落脚于社区、宗族和民间实践当中。而清代正好相反,把家礼学作为礼学的杂类排除出去,转到仪礼学,而仪礼学是最容易脱离实践的。比如礼的功能,最重要的礼学应该是守族、互助、正俗、宗法秩序的重整,而通过仪礼,则很难下沉到这个世界。这种仪礼学在乾隆初中期还有点经世致用的意味,但到了乾嘉之学,特别突出复杂繁琐的仪礼,跟社会实践已经渐行渐远,积极用世的通经达用,一转而成为不及物的经典研究,这倒正迎合了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
通过发现与还原古代圣贤奠定的礼乐制度和仪式典章,乾嘉之学重新彰显了一种礼仪主义。但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考据学者的思路已经因为两方面的影响和刺激而发生了变化:“一是对主流社会中空谈义理之学的疑惑,对于这种义理中严厉的道德标准和高调的理想主义,他们看到它由于过分压抑人的情欲,而与社会生活实际的背离,便试图用另一种约定俗成的道德共识和形诸仪节的规则来代替它,于是有‘以礼代理的思路;一是对上层文化中思想与学术各走极端的忧虑,由于高蹈空疏的‘理和过于琐细的‘事的分裂,使它们或成为无所依附的教条,或成为细碎繁琐的考据,于是希望用类似西洋学问中的‘公式或‘法则来重建知识和思想的共同基础,于是重新寻找‘通例成了乾嘉后期的风气……人们便渐渐在原本古典的学问中,羼入了现代的意味,或者也可以说,在面对现代的学术困境时,引入了古典的依据。”[6]作为“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孙诒让接续的正是朴学、汉学、小学这种失去了现实效力,但内在里已经悄然发生范式转移的学问。此时,这种学术由于其自身逻辑的必然发展,走向了对自己守护对象的悖反:学者们斤斤计较于文本的细节详实,但实证主义必然会带来否定宋学文本中元典真实性的结果,也就是对得意忘言的完整性理解的抛弃,因而实际上是瓦解了经学大义。因为经典并非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不断的流传中衍生叠加,成为一种历史产物。所以主观上孙诒让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够经世致用,但客观上却是日益脱离实际。
与此同时,今文经学的崛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虽然名为“经”,事实上已经成为“术”,因为“经”作为意识形态的依托和价值来源,是不证自明、不假思索、不可置疑的,一旦“经”都能够被考证为“伪”,那就意味着价值观已经潜在地发生了变化,尽管当事人也许主观上并不这么想,革命在实践上却已经发生。这是关节所在,无怪乎孙诒让会对康有为(1858-1927)大加挞伐,连带对好友黄绍箕(1854-1908)也不假辞色(黄绍箕曾受业张之洞,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孙诒让合称“二仲先生”,都是“瑞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现在的瑞安小城还可以看到两家旧居遗址相距也不远)。因为作为一个敏锐的士人,他察觉到了康著的极大危害性——这种变法触动的是道统的根本,已经不仅仅是器、末、技的层面了。
经学家在晚清以来的命运折射了中国古典文化在晚清遭遇西方现代文化冲击时候的命运,经世致用可能会自然引向经变从权,当然也可能导致离经叛道。在这个“权势转移”的大时代,一切都在迅疾地发生变化,潮流汹涌,有人喧嚣弄潮,有人伫守灯塔,有人激流勇进,有人徘徊不去,有人溺于深水,更多的人则被泥沙裹挟前行。孙诒让及其后几代士人都处于这个缓慢但又毋庸置疑的蝉蜕过程中。这个过程里,经学家们蜕变的痕迹显现出士人群体的分化,一方面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以学术为志业”的专门知识分子产生,另一方面也有葛兰西所谓“有机知识分子”的萌生。孙诒让及其同侪们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很难归于其中任何一种,他们属于过渡时代的人群,内在与外在都在不停地经历天人交战,“今日之我”和“旧日之我”可能保持连续性而更加稳固,也可能天翻地覆,完全抛弃此前信奉的价值观念体系。
这个大转型的过程与此前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系列文化交流与革故鼎新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断裂式的,人类文化轴心时代所形成的一系列文明成就在此际将遭遇根本性的转折,本土的传统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海纳百川地自然而然将他者文化融汇入自身之中,因为河流本身改道了,如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说,这是一种语法意义上的转换,而不再是词汇意义上的增补:“只要一个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那么,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但是,当由外国势力的侵入而引起的社会瓦解开始后,外国思想便开始取代本国思想。”[7]关于“词汇”的变化我们在中国文化系统历次扩容之中尚可看到,比如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而被吸收到体系之内,而晚清中国所面对的是旧有文化再也沒有能力兼容异质而强大的西来新事物,经学家们所面临的外来挑战是“现代”与“传统”的战争,也即人们常谓的“中西古今之争”。在现代性分化之后的文化场域中,政教分离,自然、社会与主体都经过全面改组,而这一切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支撑下衍生为一种普遍模式,流播到世界各地。中华帝国此时被硬性拉入世界史,不得不内在于此种“迟到的现代性”之中:观念层面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阶层意识形态遭受到的失败;学术上在乾嘉之精的主流旁侧衍生出边缘驳杂的“新学”;军事与现实政治层面,是中央集权的溃散、地方军事化和社会固有结构的分崩离析。
混乱之局召唤中流砥柱,然而孙诒让仕途无成,只能在精神上希求障百川、立表率。他虽然继承的仍然是乾嘉朴学的路数,但在通经博物、遍搜穷讨中仍有时务的关怀。他的学术活动,在考释注解先贤经典中让人生的意义找到落脚之处,《周礼》寄托的是失落家园的乡愁,《墨子》想象着精进利他的刚猛精神,《契文举例》考释甲骨文固然有纯学术的乐趣,其旨归未必不在找到中华文化源头的意味,而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的《温州经籍志》则隐隐然有着“礼失求诸野”、留存地方性文化血脉的念想。显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在最初并没有全然丧失文化的自信,因而可以看到“中体西用”的替代性方案,事实上孙诒让就在这个脉络之中,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服膺于张之洞及其幕僚的主张的。
当然,孙诒让也有一个缓慢而坚定的成长过程,这是《蝉蜕——寂寞大师孙诒让和近代变局中的经学家》通过文学虚构的手法所加意强调的。书中特意安排了一场年轻的孙诒让与容闳(1828-1912)和盛宣怀(1844-1916)的会面争论:盛宣怀称在雅致的地方上不必拘礼。孙诒让却道:“正是雅致的地方,偏还得要讲个‘礼字。”[8]按照情节,这固然有年少气盛、血气方刚的因素,换个角度而言,也显示出他的迂腐。容闳从现实情势的角度认识到礼利之变,必然要学习西方技艺,开拓贸易商业。这在孙诒让看来则是丢了国本,道德礼教在他那里比细民生计更为重要。面对容闳的务实与观念,孙诒让其实无言以对。这个扬州梅园中的场景显然是虚构的,作者刻意为之,是要在冲突中确立孙的立场与形象。“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事太实则近腐,可以说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9]本书过于拘泥于史实,时常有手脚难伸之感,唯独这为数不多的段落,显示出虚构的匠心。
以虚构的情节衡诸于历史上的事实,永嘉学派的影响无疑深着于孙诒让身上。永嘉学派在宋代周行已(1067-1124)、薛季宣(1134-1173)时初露端倪,到陈傅良(1137-1203)、叶适(1150-1223)时根深叶茂。宋代儒学,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占统治地位,永嘉学派与注重心性的心学和喜谈义理的理学不同的是,重事功,其主导思想是“弥纶以通世变”,注重经济利用。“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10]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1814-1894)、叔父孙锵鸣(1817-1901)都服膺永嘉学派的理念,孙衣言更是多方搜求抄本,命孙诒让校勘后编成《永嘉丛书》。永嘉学派的复兴与道光之后汉宋之学对立的局面有关,“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以史学补汉学之短”。永嘉学派反对空谈义理,重视货币、田赋、盐茶、地形、水利、转输、吏役、兵制、济贫等社会、经济问题,体现在孙诒让身上是其实业救国的行动,但从义理上来说,在因袭已久的话语体系中,孙诒让无法发明出一种更新的语言和表述,来把握、描述和应对所经历的现实和经验,这使得他的努力多少带有一些逃避的意味。
从梅园争论的少年到中年之后洋务失败,维新兴起,孙诒让逐渐接受了一些变革改良之说,但他尊君重礼的底线始终无法突破。这种等级制观念无疑在民权日益普及、下层民众逐渐启蒙的时代失去了其合法性。因而避免不了在士人内部发生分化,孙诒让与陈虬(1851-1904)的矛盾就集中体现了士绅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无法化解,也幸亏孙诒让1908年就去世了,在他死后不久,大清王朝就被颠覆,到来的是一个更为滂沱骛乱的军绅政治的时代,用陈志让的说法:“中国从所谓的绅士或地主政权建立之后,实际的政权基础是绅士和军人的联合,那是绅-军政权。但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后,军人的势力壮大,中国的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却变成了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北京的总统,总理,国务院,国会受军人操纵;各地方的县长,乡长也受军人的操纵。这种政权我们叫做‘军-绅政权”[11]。乡贤这一联结官府与乡民的中介在军事地方化的局势中迅速败坏,成为与暴发户和强权者结合欺压民众的土豪劣绅,再也不是维护乡里空间的社会基础柱石了。
胡小远、陈小萍二位作者整体而言是以体贴之同情站在孙诒让的角度来展示他应对内外部情势的变化——这在孙诒让与陈虬的矛盾处理时尤为明显,叙述者经常采用鄙夷的议论指斥后者的偏激与狭隘。对于历史文学书写而言,这种情感倾向于显然过于明显了,但也正因此可以看到当下时代文人知识分子对过去的再评价。陈虬出身贫寒,是近代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和造诣很深的医师,1885年创办了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客观而言,陈虬的社会与思想贡献高于孙诒讓,而孙诒让学术影响强于陈虬,但因为陈虬贫病而亡,著作散佚,无法与高门望族的孙诒让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虬的政治思想一度受到重视,但特定年代的话语转变后,乡贤重新成为晚近这些年文化怀旧的中心角色,在这种背景中胡、陈二人的写作态度受大环境影响折射出世风之变。书中还连带同时将与陈虬合称“东瓯三杰”的陈黻宸(1859-1917)、宋恕(1862-1910)贬低了一番,显然是站在孙诒让的角度,也即以“世家官绅”的角度指斥“布衣士绅”,以空洞的仁义道德抨击平民的奋斗抗争。
孙诒让理解不了“布衣党”陈虬、陈黻宸、宋恕,因而翻来覆去地念叨:“世间之事不可思议,都在图谋富国强民,都在探求变法自强,为何同道者不相与谋?”[12]但是,他们本非“同道”,这涉及到近世以来平民阶层地位的提升,打破了他这样的世家子弟所习惯了的伦常秩序,但他终究不是一个思想前沿的士人,毋宁说是一个恪守古典的士大夫。我读过这本书的初稿,原先的副标题是“寂寞大师孙诒让和近代变局中的经学家”,似乎要突出孙诒让的独特之处。其实,孙诒让的“寂寞”也并非特例,像他这样在历史与情感、理性与感性之间发生巨大冲突的人物在晚清民国并不在少数。就在他去世前一年,王国维就曾直言:“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13]此种“可信”与“可爱”之间的矛盾,孙诒让亦是感同身受,而他之无法超越自我认知的局限也注定是一个鲁迅所谓“历史中间物”般的必然宿命。
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中,孙诒让对于墨子的钟情到恰显示出一种先秦儒家的奋进精神。对于墨子的诂解,意义并不在证明光学、力学、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宇宙学、逻辑学的古已有之——这在现实情境中并无意义,并且也与现代体系化、实证化与制度化的科学理性相去甚远——关键在于其中体现出的对于中国古典的信念。胡小远、陈小萍二位敏锐地拈出他的《光不灭说》可谓颇具慧眼,在“光不灭,墨学不灭”的倡说中,孙诒让把治学和为人熔铸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指向于一种蜕故孳新、生机不断的文化精神。此前此后的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文化确实屡遭播迁、颠沛、离乱、消沉,而终究气息犹在,总能在奄奄一息之际吐故纳新,接续生命,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就此而言,孙诒让在古典文化的寒夜,取薪笼火,培育种子,如同守夜之人,适足以留名后世。《蝉蜕》平实铺展,描摹行状,让这一形象凸显于世,也称得上是功德一件。
诚如赵柏田所说:“古典时代已经终结,无论历史中,还是小说中的人与事,皆已无可奈何花落去。断裂一次次地发生,昨日的世界如同一块旧大陆渐渐飘移出现代人的视线。即便今日的孙家后人,也大多移民海外,对先祖于一部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意义,对昔日里的文化辉煌,亦大多不明就里,今人视昔,已如高山不可登,如孤岛不可渡。《蝉蜕》以学人性命为其性命,以学人心魄为其心魄,神魂与之,梦寐思之,为今人勾勒出了那个渐渐漂远的昨日世界的隐形轮廓,为逝去的文化英雄重铸今生,今人若要重返,《蝉蜕》便是渡海的舟楫,登山的步道。更何况,时代是这样的亦新亦旧着,‘蝉蜕固属无奈,却也心甘情愿,因此有蝉衣焚去的青火,有蝉翼毁去的焦味,也有终于明白世界大道后的欣然,此是书中人的悲欣交集,亦是著书人的悲欣交集。”[14]这也是《蝉蜕》一书最终给出的带有普遍意味的隐喻:哪怕最坚硬的礁石也会在时间巨浪的冲刷下发生些微的变化,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物总是处于行进着的历史之中,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历史与人并没有某种静止而凝滞的本质存在于某处等待人们去发现,它总是在实践中获得自己的定位与意义。
注释:
[1]培根: 《培根隨笔集》,曹明伦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2]陈来: 《二元礼、苦行礼的概念成立吗》,《中华读书报》2013年4月10日。
[3]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0页。
[4]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341页。
[5]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严蓓雯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2年,“导论”。
[6]葛兆光:《清代考据学:重建社会与思想基础的尝试——十八、十九世纪之际考据学的转向》,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132页。
[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8]胡小远、陈小萍:《蝉蜕:晚清大变局中的经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
[9]谢肇淛:《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第446-447页。
[10]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1735页。
[11]陈志让: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4页。
[12]胡小远、陈小萍:《蝉蜕:晚清大变局中的经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8、350页。
[13]王国维: 《自序二》,作于1907年7月,原载《教育世界》第152号,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静庵文集续编》,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胡逢祥分卷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14]赵柏田: 《古典的终结》,胡小远、陈小萍:《蝉蜕:晚清大变局中的经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作者简介】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著有《从后文学到新人文》《文学的共和》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