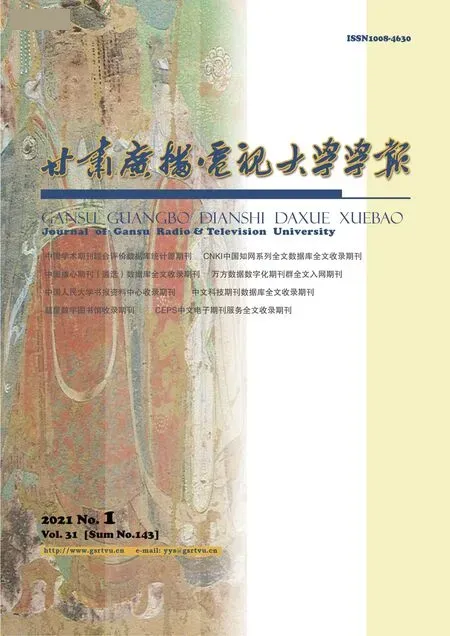西王母“生死”之辨
——以不死药为中心
崔皓羽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生死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同理,未知死,焉知不死?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吉尔伽美什正是目睹了友人的死亡,才决定去探寻不死的秘密。而所谓不死药,正是融汇了生与死的产物。“‘不死药’,其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哲理概念。‘不死’的前提是‘死’,因有‘死’,才有对‘死’的否定物‘不死’出现,因有‘死’与‘不死’,联系这二者的中介‘不死药’才有了意义。”[1]262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掌管不死药的神明是西王母。但这位女神是否自诞生之初便执掌不死药,则是一个未解之谜。目前最早记载西王母的典籍是《山海经》,所涉三处都未言明西王母是否拥有不死药。直到《淮南子·览冥训》才明确提及“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2]217《文选·祭颜光禄文》注引《归藏》:“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3]但《归藏》原文已佚,似乎也无法作为明确的证据。但无论不死药是西王母先天有之,亦或是后来所得,这位神明都与生死这两种概念脱不开关系。西王母成为中国神话中不死药的归属,必有其因。
一、昆仑“天堂”的示灾鬼母
不死药与死亡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哲学范畴,在具体神话中也有所反映。如希腊罗马神话中,阿喀琉斯获得不死之身的说法有诸多版本,其中流传甚广的一种是通过浸泡冥河之水来达成刀枪不入之躯[4],这正反映了一种朴素的观念: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死的秘密也应从死亡中寻找。
而西王母所居之地就是一处“魂归之所”。《山海经》中明确提及西王母的居处有三:昆仑山、玉山和西王母之山。玉山因盛产玉石而得名,不具有地理倾向。而关于西王母之山,在《穆天子传》卷三中有所提及:“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郭璞注曰:“弇,弇兹山。日所入也。”[5]意为太阳所落之处,与位于西北部的昆仑山隐隐相关。总而言之,西王母居于昆仑,大体是无误的。
而昆仑的具体性质曾经历过一次变化,这在典籍中有迹可循。《山海经》中对昆仑的记载有如下几处: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6]55-56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6]466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昆仑南渊深三百仞……[6]344,349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到昆仑存在两种说法:昆仑之丘(大山)与昆仑之虚,均为“帝之下都”,当属同物异名。关于后者,《淮南子·坠形训》中有更详细的描述:“禹……掘昆仑虚以下地,中又增城九重……”[2]133所谓“虚”即“墟”,根据《坠形训》的描述,不难看出昆仑之墟位于地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昆仑究竟是山上神都,还是地下城市?其实《山海经》并非一时一地所作,成书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昆仑丘向昆仑墟的转变,正体现了先秦两汉之际人们对死后魂归之所的认知由山上转入地下的过程。
在远古先民的眼中,死后世界并不在地下,而在山上。山高则连天,顺着高山扶摇而上,魂魄就可以到达生前遥不可及的神明之所。而昆仑“高万仞”,又位于西北。“从典籍记载、考古资料来看,原始先民观念里的幽冥世界最初出现在西北方向。”[7]26这样一来,昆仑便成为了魂归之所。而这种“魂归高山”的死亡观念,在后世文献中也隐约可见。如《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乌桓传》云:“……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8]岱山即泰山,“泰山作为鬼山替代古昆仑的地位,发生在秦汉之际。这是政治东移的结果,同时也得归功于术士儒生的极力推崇渲染,将东岳泰山列为五岳之首。”[7]294直到后来土葬的流行将死后世界带入了地下。在《左传·隐公元年》中,郑庄公立言与母亲断绝关系时,誓词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可见当时已经将位于地下的黄泉当做死后归宿。许地山曾考证黄泉的原型似乎出自昆仑“黄水”,末了说:“……到神仙思想发达,便从鬼乡变为仙乡,或帝乡,以致后人把在昆仑底九井黄泉忘掉。”[9]而东汉佛教地狱观念的传入,更是加深了“魂归地下”的观念,逐渐取代了魂归高山的信仰。但《山海经》中对昆仑性质的矛盾书写,仍是隐约记录了先秦两汉之际人们对死后魂归之所的认知转变。
西王母作为昆仑神国的重要一员,《山海经》记载她“是司天之厉及五残”[6]59。对于“厉及五残”,历来有不同的解释,郭璞注:“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6]60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厉及五残,皆星名也……郑注云:‘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是大陵主厉鬼。昴为西方宿,故西王母司之也。”[10]这个说法是将“司厉”解释为西王母司掌西方昴宿中的大陵、积尸之气,以此控制厉鬼。而《〈山海经〉西王母的正神属性考》则是直接将“厉”解释为厉鬼,“天之厉及五残”即为天上厉鬼与“见则五分(方)毁败之征,大臣诛亡之象”的五残星[11]。如此来看,司掌鬼物的西王母出现在作为“魂归之所”的昆仑算得上是合乎情理。
需要注意的是,西王母本身并非凶厉,否则只会一味引起恐惧,她的职能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即控制厉鬼,并预示灾祸,因此具备一定程度的神圣性。而她所在的古昆仑作为“魂归之所”,也与后世所称的地下冥界又有不同。与其说是“地狱”,更像“天堂”。首先,昆仑是难以抵达的:“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6]466这就与常世拉开了距离,具备了神圣的意味。其次,昆仑“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6]345通过昆仑可以去往百神所在之处,这也符合魂归高山的信仰。通道由神兽看守,可知来往不易;而“开明西有凤皇、鸾鸟……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6]350神木神兽皆在此云集,其中甚至还有不死之树,也无怪乎《山海经》毫不吝啬地称昆仑“此山万物尽有”[6]466。
不死药这种神奇且难得之物,应被置放在仙境福地,而非阴森可怖之所。而昆仑符合这类条件:一则此处虽能容纳死后魂魄,但并非是掌刑地狱,也不必承担惩恶扬善等一系列教化功能,更适合人们寄托神明赐药的愿望。《海内西经》云:“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郭璞注:“言非仁人及有才艺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冈岭巉岩也。羿尝请药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羿一或作圣。”[6]345-347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不死药遥不可攀,但是仍需要存在成功获取的例子,否则无法为人所信。这时羿请药昆仑的事迹就能成为有力的佐证;其次,昆仑有通天之路,令求药于神明成为可能。上古之时,巫觋是神与人往来的媒介,如《大荒西经》中所提及的:“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6]453-454所谓“升降”,是指通过天梯于天地之间往返。而昆仑“方八百里,高万仞”,就是一座伫立在北方的巨大“天梯”。巫觋们在沟通神人之际,还能向神明讨要灵药,这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百药爰在”。而坐镇昆仑的神明中,掌控厉鬼的西王母无疑是与“死亡”这一概念关系最为紧密。人们遵循在死亡中寻求不死之秘的思维模式进行想象,西王母也就成为了昆仑众神中不死药的执掌者。
总之,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同时拥有“魂归之所”与“世外仙境”两种特性,前者与西王母司掌厉鬼的神格相呼应;后者则与地狱相区别,并赋予了西王母神圣的属性。这就使西王母最终成为神话中司掌不死仙药的神明。
二、执掌日月的生命女神
如果西王母仅仅是西方魂归之所的神明,那只能说明她掌管死亡,尚不足以与不死药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不死药的持有者还要拥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特质——延续生命。而西王母之所以拥有此种特质,首先得益于她是一位女性神明。同样作为西方之主的少昊没有成为不死药的持有者,除了他诞生于战国时期,时间较晚外[12]103,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这一重女性身份。
当先民试图解释女性某些生理现象时,会将之与世界中的某些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比如把经期、生育带来的身体变化与月之阴晴圆缺相关联。“凡与周期性相关的事象,如死亡与复活、生育、发端,等等,都与月亮取得了对应,经过原始思维的‘互渗’,这本来不相干的种种就俨然合一了。”[1]267月亮与女性成为了生死循环的的象征,先民在塑造不死药持有者时,也会不自觉地偏向于女性。
不仅是月之盈缺满亏,日之东升西落也代表着周而复始,死而复生。“对生的祈盼是原始初民关注万物的原动力。最初他们以太阳的东升为生,以太阳的西入为死。”[13]由此,就不得不提到西王母的另一神格——日月神。这一形象是从西方神的神格中演化出来的。殷代的祀典就出现了“东母”“西母”“王母”,虽不敢遽定所谓“西母”“王母”是否为西王母,但“东西母与日神有密切的关系”,而推断的重要依据就是日月行次与地理方位的对应[12]102-104。据前文所述,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又有“弇山”之名,即所谓“日入所也。”西方不仅是日之所憩,也是月之所出,既代表了昼夜交替的时间变化,又代表了日月运行的空间变化。那么西王母也拥有了成为日月之神的资格。两汉时期关于西王母的出土文物中,常常可以见到玉兔、蟾蜍、三足乌、九尾狐等从属图像[14],这也是西王母身为日月之神的佐证。玉兔和蟾蜍都是月中精魄,而三足乌是太阳的象征。西王母作为日月神的神格以这样的方式被保留在了具体图像之中,从而流传了下来。
西王母作为女性神本身具有孕育生命的特性,而其西方神的神格演化出了日月神的另一种形态,日月之周而复始便是死而复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女性神、西方神、日月神三重身份使西王母由冥神迈向了生命神,而与不死药建立起了真正的桥梁。
三、长生不死与死而复生
对于集生死为一体的西王母而言,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她所持有的不死药的功效,究竟是长生不死,还是死而复生(或效果更进一步,能使人死后复生并成仙),抑或是两者兼有?
日月轮转象征着生死交替,那么拥有日月神格的西王母似乎也应该拥有同等能力。一些学者以此为前提对两汉时期墓葬中西王母图像进行分析,从西王母在图像中所处的位置、从属玉兔的捣药行为等方面,推测墓葬中西王母图像可能是表达墓主人死后成仙的愿望。“刻画西王母等神仙只是表明这里是神仙的世界,也是墓主将要去的地方。”[15]
但奇怪的是,最初西王母的不死药似乎只是令人长生不死,而非死而复生或死后成仙。同为西汉时期的文献——《淮南子》所记载的是:“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注曰:“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末及服之,嫦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2]217可见嫦娥是生前服药而奔月,不死药的效果应为长生不死,而非死而复生。不能令人死而复生或死后成仙的西王母出现在人们死后的墓葬中,这种现象如果只用墓主人希冀死后成仙,在墓中绘制西王母图像来解释,似乎是不够妥当的。
当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不死药的功效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泛化,囊括了长生不死和死而复生两种功效。墓主人其实就是为了在亡故后向西王母求取死而复生的仙药,所以才在自己的墓葬中绘制了西王母图像。而这种能令人死而复生的仙药,被后世称为“尸解药”。
但西王母对“尸解药”的态度是值得玩味的。在《汉武帝内传》中,上元夫人反感汉武帝,于是建议西王母赐给汉武帝“尸解药”:“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但西王母是这样回答的:“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帝不得复停。”[16]言谈之间,似乎都很看不起“尸解”这种成仙方式。虽然《汉武帝内传》据考证是魏晋时期拟托班固或葛洪之名所作,但西王母对于成仙方式的矜贵态度或有缘由。如《抱朴子·内篇·论仙》谈及:“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17]天仙的成仙之法更类似于《淮南子》中嫦娥食西王母之不死药而飞升的描述,与尸解仙“先死后蜕”形成明显差异。可知古时成仙之法亦有高下之别。或许正是这种差别影响了人们心中西王母及上元夫人对尸解之法的态度,故才有《汉武帝内传》一说。
由此可见,西王母的不死药至少最初并不同于“尸解药”,不具有令人死而复生或死后成仙的功效。这种观念在魏晋时期的《汉武帝内传》中仍有存留。而两汉时期墓葬之所以会大量出土西王母的图像,恐怕并非是出于墓主人死后成仙的愿望。倘若追溯源头,就可以发现西王母所处的昆仑在远古就是魂归之处,神仙世界与死后世界并不是矛盾的。墓主人在去世后前往幽冥,拜谒死后世界的女神西王母,似乎更为合情合理。由此来看,西王母之所以会出现在两汉时期墓葬中,应是偏向于作为冥神而非复生神的神格。
不死药是神话中连接生死的道具,而西王母作为不死药的持有者,神格中糅杂了“生”与“死”两重特性。这两重特性都可以追溯至她作为西方神的原初神格。昆仑因地处西北而被赋予了“魂归之所”的含义,而居于其中的西王母因拥有控制厉鬼以及预言灾祸的能力而为人所敬畏,并与“死亡”这一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西方作为日落月出之地,又使得西王母拥有成为日月神的可能。日月之流转不息让先民们看到死而复生的可能,而将这种愿望寄托于西王母身上。两汉之际西王母崇拜的风行正是这种愿望被放大的结果。而不死药这种将生与死的概念融汇在一起的物品,也被拥有同样属性的西王母所吸引,最终落入了这位神明的手中,并拓展了西王母的神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