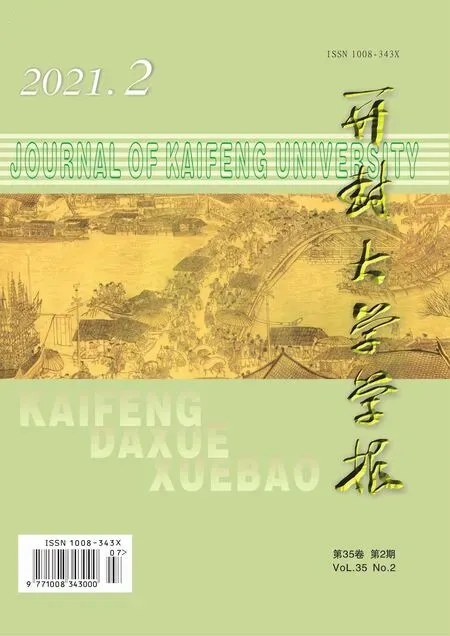路翎创作对“人格”塑造的突破
唐明明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路翎认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根本是在于描写人物,与具体的历史相联的、社会的人物,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1]P295正是对“人”的生动描写和细致表现,才使得作品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更为丰厚。在路翎的文学世界里,主要有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小心翼翼而又具有探索精神的知识分子;一类是身处社会底层但富有抗争精神的贫苦群众,他们中有矿工、流浪汉、村妇等。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他们无一例外,都在挣扎,都在反抗和斗争。社会传统、惯性思维和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具有巨大的牵制力量,他们迈出任何一步都万分艰难。在路翎作品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传统对人的个性的戕害和扼杀,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具有个性的人与传统的顽强斗争,听到了路翎在探索人性过程中的呐喊。
一、对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开拓
新文学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在“五四”时期这样一个追求思想解放的时代,知识分子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这是理所当然的。郁达夫、郭沫若、丁玲等大批作家都在按照自己的个性来创作,为“个人”主体的确立而呼喊,反映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鲁迅的挖掘更为深入。通过孔乙己、狂人、夏瑜、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一系列人物的境遇,我们清晰地看到“个人主义”面前存在的重重障碍,加深了对“知识者、清醒者如果不有所作为,在黑暗罪恶的社会中就必然走向灭亡”的认知,更加钦佩那些先知先觉者为自由而奋战的勇气。路翎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在精神气质上靠近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自觉承接“五四”传统。经历了抗击侵略者的残酷战争,这使路翎对知识分子形象塑造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相较于前人的创作,他的作品显示出一些异质。在《财主底儿女们》中对蒋家三子形象的生动刻画,反映了路翎在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的深入探索。
蒋蔚祖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也是一个行将没落的封建家庭的长子。维护家庭传承的责任、现实生活的重压使他喘不过气来。在父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与较量中,他徘徊、隐忍、犹豫,始终没有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最终疯狂而死,成为旧文化的牺牲品。但是,与高觉新、祁瑞宣们处处忍让、软弱妥协、牺牲自己不同,蒋蔚祖如同鲁迅笔下的狂人,对社会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有着对自由的渴求,他知道,不抗争、不改变就没有未来,所以他在极度压抑下,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出自己的反抗,只是他的反抗最终陷于虚无的境地,刚刚挣脱父亲的锁链,又沦为妻子的“囚徒”。从这个意义上说,蒋蔚祖是个有些许追求但最终被现实湮灭的悲剧人物。在妻子出轨、父亲去世之后,他避开所有的人,开始自我流放。他在幻想中享受主宰一切的快乐,直至自己灭亡。路翎通过蒋蔚祖的悲剧告诉人们“什么是封建的中国底最基本最顽强的力量,在物质的利益上,人们必须依赖这个封建的中国,它常常是仁慈而安静的,它永远是麻木而顽强,渐渐就解除了新时代底武装”[2]P1。
蒋少祖是以蒋家第一个叛逆者的形象出现的。他16岁便离家到上海读书。他受到时代的影响,阅读了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新杂志,最终他背叛了家庭。这是那个时代青年们的一个普遍的行为,是一种流行的做法。这种背叛也带给他意想不到的收获——“姊妹们底秘密的温柔的关切,大量的金钱,以及蒋家底叛逆的儿子的光荣的名誉”[2]P321。然而,他对传统的背离并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彻底。很快,蒋少祖就感觉到了这种叛逆背后的无聊,崇敬的感情慢慢淡了下去。心理变化催生具体行动,他很快就在时代的风潮中向后转,逐步退回自己的安乐窝。值得注意的是,蒋少祖不仅是路翎塑造的一个从时代潮头渐渐退下来的知识分子形象,还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和较强敏感性的思考者形象。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生活态度,但不能否认他的理性。突显蒋少祖的理性,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路翎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巨大突破。对1937年的青年来说,“人民”“生活”是必须拥抱的伟大词语。而蒋少祖明确地指出,“你应该首先懂得,然后再信仰”。暂且不论这个人物是消极还是积极,单说作者在当时文学人物好坏分明的创作模式之外给予我们第三种体验,就值得钦佩。
在对蒋蔚祖、蒋少祖等旧一代知识分子进行描写后,路翎推出了蒋纯祖这个保持奋勇向前、毫不妥协的战斗者姿态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形象。蒋纯祖是蒋家最小的儿子,与他的大哥、二哥比起来,他与家庭要疏远得多。同二哥一样,他接受着新式的学校教育。但是,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更为严酷。家庭和社会中呈现的是这样的场景:在家里,他看到父亲死后亲兄妹姑嫂为分财产而明争暗斗;在南京,他看到天空轰鸣的敌机、街头飞扬跋扈的士兵、被炸死的房东老太太以及饥寒交迫的难民和无依无靠的孩子。现实生活给他以极大的震撼,同时也给予他深刻的警醒,他不会有任何回归传统的可能。在演剧队、石桥场,他对那些假借革命的名义攫取利益的行为嗤之以鼻,他看不惯权力集团的斗争,他对旧的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反抗。路翎对蒋纯祖形象的刻画,并没有止步于突显其革命精神的彻底性,他在蒋纯祖形象塑造上的探索,是对“彰显个性与开展革命工作发生冲突”这一旧有创作套路的反拨。他没有通过让个体服从集体来证明革命的感召力和更高价值,而是试图通过个性的充分张扬来提升革命的合理性,通过个人对时刻面临的压迫的反抗来探讨进行革命的正确途径以及革命的最终目的。在以全民族抗战为主题的时代,作为作家的路翎看到了个人与集体之间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他显然更关注人如何在最大程度地保留棱角的同时进行革命。蒋纯祖便是作家艰难探索的成果。
通过塑造蒋家三子的形象,路翎展示了在封建传统压迫下个体知识分子的曲折经历以及他们所选择的不同道路,说明知识分子只有走出家庭,在精神上彻底与封建传统决裂,才有可能实现自我的真正解放。这是路翎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极大开拓。路翎在个人主义文学观念上的新开拓催生了新的文学实践,他注重展现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时的行动力与彻底性。除了蒋纯祖,明和华(《人权》)、林伟奇(《谷》)等人也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进行了实际的反抗。吕纬甫、魏连殳以及子君等人反抗的结果都是个人毁灭,而蒋纯祖、明和华、林伟奇等人不同于他们,这些人积极地、永不停歇地进发。
二、对底层人物形象塑造的突破
路翎一方面关注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关注劳苦大众的生活,在对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独特的贡献。简单梳理一下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众多作家笔下的底层人物,不难发现,艰难困苦、备受欺凌、精神麻木、反抗不足是他们共同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是他们共同的标签。如鲁迅塑造的阿Q、闰土、祥林嫂、华老栓等人物形象,他们均丧失了自我。旧中国沉重的封建枷锁让人窒息。《丰收》《春蚕》《骆驼祥子》等作品同样反映了农民遭受沉重压迫的现实:从贫困到被逼堕落,过程令人痛心。到了20世纪4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作家笔下的人物,生活更加艰辛,灾难更为深重,但是他们慢慢觉醒,并纷纷通过参加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改变,在路翎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路翎在深刻揭露和批判封建势力对贫苦农民的压迫的同时,充分展示农民身上反抗压迫的原始强力,并肯定农民的复仇行动。如孙其银(《卸煤台下》)、石二(《黑色子孙之一》)、张振山(《饥饿的郭素娥》)、朱谷良(《财主底儿女们》)等流浪汉形象,他们远离故土,没有尊严地活着,然而依旧遭受压迫,只能一次次地“走”,这也是他们共同的选择。他们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虽然还是从贫困到贫穷,但毕竟生存了下来,在当时,能生存下来就是奇迹。他们艰难生存,这本身就是强大生命力的体现。鲁迅叙写复仇时重在精神剖析,而路翎展示的是在遭受沉重压迫情况下实实在在的顽强抗争,是贫苦农民对自我生存权利的维护。
路翎在作品中反映了穷人所遭受的奴役,同时也展现了他们所进行的激烈反抗。郭素娥这个人物形象就是一个典型。她没有祥林嫂的逆来顺受,有的是面对流氓的迫害决不妥协的坚韧性格;祥林嫂被逼改嫁时誓死不从,而郭素娥有着改变自己生活的主动性,她会有意识地吸引一个男人来帮助自己实现对目前生活的颠覆。所以,她们的结局完全不同。可怜的祥林嫂死在新年前夜,还落得鲁四老爷一声“扫兴”;郭素娥虽然也死了,“但她却扰动了一个世界”:张振山终于远行,魏海清也因为她的死而起来反抗了。通过郭素娥这个形象,路翎对底层人物身上“原始的强力”进行了充分诠释:懦弱无力、逆来顺受并不是他们的天性,在其灵魂深处,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反抗精神,当外界的压力大于他们的心理“燃点”时,他们就会爆发、就会抗争。这种抗争精神存在于路翎小说中的很多人物身上,如何德祥(《在铁链中》)、何秀英 (《燃烧的荒地》)、朱四娘 (《爱民大会》)、王家老太婆(《王家老太婆和她底小猪》)等,他们并不是什么大英雄,都是备受压迫的小人物,但他们均以自己的方式在斗争,争取自己的尊严和解放。
在路翎作品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化的倾向明显。这使路翎饱受指责,尽管它有利于对底层人物内心深处的挖掘,有利于彰显底层人物坚强的意志品质,有利于表现底层人物精神的升华。这样描写和处理是作家极力想象的结果。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有着先知先觉的痛苦:一方面期盼大众的觉醒,另一方面又深知现实的困顿和革命要走的路还很长。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存在着,既悲天悯人又痛苦不堪,饱受内心的折磨。“以后时期的作品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那样,深刻的悲悯与明确的批判倾向结合在一起。”[3]P34然而,在路翎的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和底层人民已不似以前那样完全隔阂、对立,他的底层人物形象具有知识分子的部分特征。当然,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创新。路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经苦恼于自己把一个工人写成了知识分子甚至诗人,但同时他坚信自己的创作原则是正确的:“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但因为羞怯,因为说出来费力,和因为这是‘上流人’的语言,所以就很少说了。”[4]我们暂且不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化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斗争形势和文学创作规律,单就创作手法来讲,它是路翎表现底层民众觉醒的一种方式。
三、结语
在文学的审美选择上,路翎以表现“个人”为追求,“人”始终是他创作的核心。路翎通过“蒋纯祖”“郭素娥”这些拥有强大原始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告诉人们应以怎样的主观意志、精神和勇气去和封建传统战斗,去彰显个性,追求自我解放。路翎的文学创作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