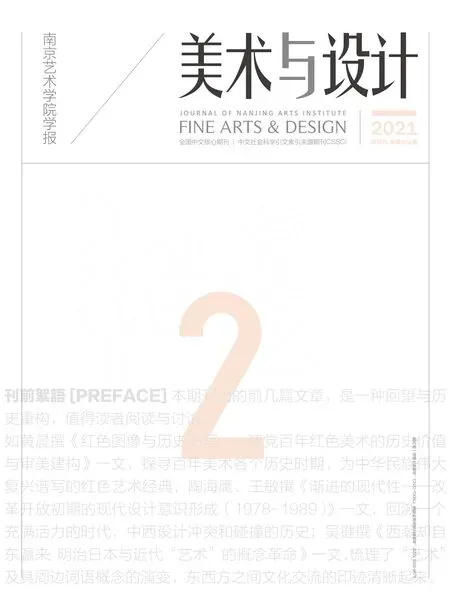张僧繇四题①
韩 刚(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610021)
张僧繇是与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齐名的“中古四大家”,学界从各个方面论之者甚多。在僧繇生平履历方面,则以素有“六朝痴”“林六朝”之称的林树中先生所撰《张僧繇年表》(2002年完成)等工夫甚深,然今天看来,仍有不确处。述之于下,希望对前贤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有所补正和推进。
一、张僧繇官职与家世
有关张僧繇的官职,以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张僧繇评传记录较早、最详,谓“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1]90另外,唐代刘长卿《张僧繇画僧记》有“梁直阁将军”记载。[2]1544则张僧繇曾官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直阁将军、右军将军与吴兴太守等,依次考述如下:
(一)武陵王国侍郎
张僧繇“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中,“武陵王”为梁武帝萧衍第八子萧纪(508—553),天监十三年(514)封为武陵郡王,故张僧繇任该职当在天监十三年之后。
《隋书·百官上》载南梁官班:
“扬南徐州西曹祭酒从事,皇弟皇子国侍郎,嗣王国常侍……为一班。”②(唐)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百官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732—733页;另,唐杜佑《通典》卷第三十七《职官十九·秩品二·梁》所载同。
谓“皇弟皇子国侍郎”为一班。南梁官班主要有地位从低到高的三套系统:一为自十八班至一班的流内官系统(即流内十八班,以班多为贵),地位最高;二为自七班至一班的流外官系统(流外七班,班多为贵),地位次之;三为三品蕴位(或三品勋位),地位最低。分别对应不同层级之人群:士族(世族)靠门第从流内十八班入仕;寒门凭才学从流外七班起家;一般庶民从军人或胥吏做起,积累军功、吏绩或年劳从三品蕴位(或勋位)做起;三品蕴位迁转至流外七班,流外七班迁转至流内十八班,三者等级分明。[3]故张僧繇天监十四年官“武陵王国侍郎”为流内十八班中最低者(一班)。一般而言,随吏绩、年劳的增加,会从流内一班至十八班依次向上迁转。
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张僧繇曾画《宝像》(详于下文);宋代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七记,天监二年(503),张僧繇曾奉梁武帝诏画僧宝 像,表明张僧繇至少天监二年已以画艺侍奉于南梁宫廷,至天监十三年(514)已十一年。如此,张僧繇在南梁武帝宫廷依靠画艺业绩、年劳等自三品蕴位至流外七班、流内十八班之一班“武陵王国侍郎”费了十一年光阴。因而,林树中《张僧繇年表》:
“武陵郡王国侍郎职位很高,仅在郡王萧纪之次。”
“六朝的出仕讲究品位(分九品),士族无下品。张僧繇在‘释褐’之际即奉梁武帝敕画高僧宝志像,30岁上下即官王国侍郎,并直秘阁事,除了他本身非凡的才能而外,出生世族也是可以肯定的。”[4]359
谓张僧繇职位很高、出生世族看法应不确。因为,若其出生世族,当时一般会通过国子生、策试,于青少年时代入仕,起家官应为流内二班之“秘书郎”等甚至以上。如《梁书》张缅(489—531)本传:“天监元年(502),弘策任卫尉卿,为妖贼所害,缅痛父之酷,丧过于礼,高祖遣戒喻之。服阕,袭洮阳县侯,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太守,时年十八”;[5]491张缵(499—549)本传:“缵字伯绪,缅第三弟也,出后从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赠廷尉卿。缵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阳公主,拜附马都尉,封利亭候,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5]493萧乾( —567)本传:“萧乾,字思惕,兰陵人也。祖嶷,齐丞相豫章文献王。父子范,梁秘书监。乾容止雅正,性恬简,善隶书,得叔父子云之法。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十五,举明经,释褐东中郎湘东王法曹参军”;[5]278王承本传:“王承,字安期,仆射暕子。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5]585等等。
当然,当时也有寒门子弟入仕,起家官为王国侍郎的。如《梁书》卞华本传:“卞华,字昭丘,济阴冤句人也……华幼孤贫好学。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既长,遍治《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蒨同业友善。起家齐豫章王国侍郎,累迁奉朝请、征西行参军。”[5]676齐豫章王为萧嶷(444-492),字宣俨,齐高帝萧道成次子,齐武帝萧赜弟,萧道成即位(建元元年,479),封为豫章郡王;该书徐勉本传:“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人也……勉幼孤贫,早励清节。年六岁,时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笃志好学。起家国子生。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每称勉有宰辅之量。射策举高第,补西阳王国侍郎。”[5]377西阳王为萧子文(485-498),字云儒,齐武帝萧赜第十七子,永明七年(489)封蜀郡王;明帝建武二年(495年)改封西阳王。“幼孤贫好学”的卞华“起家齐豫章王国侍郎”“幼孤贫,早励清节……笃志好学”的徐勉“补西阳王国侍郎”均为王国侍郎,且均是通过“好学”“国子生”与策试而得。
而迄今未见张僧繇孤贫好学、为国子生与参加策试等信息。故知其得王国侍郎既非士族子弟通过国子学、策试途径入仕(流内十八班序列),亦非寒门子弟通过好学、国子学与策试入仕(流外七班序列),而是属于胥吏等通过积累业绩、年劳途径入仕的(三品勋位或蕴位序列)。在南梁官班三品蕴位中,有“染署丞”“太乐库丞”“清商丞”“太医二丞”“正厨丞”等与画工性质相当,这也说明,僧繇凭画艺由三品蕴位序列晋升是有可能的。
(二)直秘阁
张僧繇“直秘阁,知画事”始于天监十三年(514)。其“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中“秘阁”为汉武帝以来宫廷重要图书收藏机构,从南齐画家毛惠秀“永明中待诏秘阁”来看,[1]88张僧繇“直秘阁”职责当与之相近,即“直”与“待诏”略同,这是往前看。往后看,也可以得到一些可凭推想的信息。唐长孺认为,唐代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诸方面变化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6]流外官制度应该也是如此。①南梁流外七班,唐代与之相应的是流外七品。杜佑《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制定流外七品“勋品”(相当于一品)自注“勋品自齐梁以来有之”,表明其与南朝流外官品之间有衔接关系。唐代无三品蕴位,盖因隋唐科举制兴起,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制度衰微,“士庶天隔”局面被打破,南梁三品蕴位被扬弃、整合到唐流外七品中。《唐大诏令集》卷二中宗即位敕云:“诸司有品直司,宜加一阶,无品直司,赐勋一转。”[7]说明唐代作为官制的直官有有品直官与无品直官之分(这里的“品”指的是流内官品)。《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郎中二人条:
“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原注:诸司诸色有品直……秘书省图画一人、丹青五人、造笔一人……外官直考者,选同京官。其前官及常选人,每年任选。若散官、三卫、勋官直诸司者,每年与折一番。)[8]
以上讲的是唐代诸司所置定额有品直的员额等情况。秘书省有品直官“图画一人”“丹青五人”与绘画相关,为额定编制。《唐会要》卷六十五《殿中省》:
“(开元)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殿中监奏:‘尚食局无品直司六人,并是巧儿,曹司要籍,一任直司,主食十年,考满,同流外授官,仍补额内直驱使。”[9]
其大意是说,尚食局有无品直六人,都是烹饪巧匠,要在“主食”(唐代为流外第三品)工作岗位上工作十年,考核合格以后,根据“流外官品令”授予伎术官,补为额内直(相当于有了编制)。这为推想南梁三品勋位、流外七班入职、年劳、考核与晋升提供了想象空间。若从张僧繇天监二年进入宫廷算起,至天监十三年,已经凭出色画艺工作了十一年,才做到流内十八班最低者“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与唐代无品直授官情况差不多。
“武陵王国侍郎”与“直秘阁,知画事”职任时间应同。或许,这对以画艺侍奉宫廷的胥吏张僧繇而言,已经相当理想了,因为“王国侍郎”已是寒门子弟通过读书入仕的起家官(如上文所引,寒门子弟卞华、徐勉均以“王国侍郎”起家)。当时,这种胥吏从三品蕴位至流外七班再到流内十八班,虽不多见,但并非绝无仅有,如《梁书》孔子祛本传:
“孔子袪,会稽山阴人。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初为长沙嗣王侍郎,兼国子助教……累迁湘东王国侍郎、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又云麾庐江公记室参军,转兼中书通事舍人……中大同元年,卒官,时年五十一。”[5]680
其中“长沙嗣王侍郎”为流外七班(即流外最高班),“湘东王国侍郎”为流内十八班之一班(流内最低班,与张僧繇武陵王国侍郎班次同)、“常侍”为流内十八班之二班,“员外散骑侍郎”为流内十八班之三班,“中书舍人”为流内十八班之四班。孔子祛少孤贫好学,通过读书仕进,由流外七班至流内一班、二班、三班、四班依次晋升,有助于类比说明张僧繇由画艺晋升的一般情况。而之所以僧繇三品蕴位、流外七品吏职未见记载,迄今所见其最早官职为流内一班,盖由于其画艺杰出,知遇于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等,影响至大,后世画史为尊者讳,悉数勘落之故。
(三)直阁将军
唐刘长卿《张僧繇画僧记》记:张僧繇“直阁将军”官职应为梁武帝左右侍卫之官,虽与帝王甚为亲近,但不见于当时正式官班令,应为临时临事所设,具有后世差遣使职性质,①南朝“直阁将军”学术界多有考述,可参考张金龙《南朝“直閤”将军制度考》(《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胡小明《南朝直閤将军再探讨》(《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等。其级别、待遇等仅可从与之相近的“朱衣直阁将军”推想。《隋书·百官上》记:梁武帝天监六年(508)“又置朱衣直阁将军,以经为方牧者为之。”[10]726其中“方牧”为古代统治一方军政的方伯、州牧之并称,引申为地方长官。“朱衣直阁将军”为正式职官,掌宫内侍卫,属中领军(流内十四班),在南梁官班制中为流内十班。则张僧繇“直阁将军”待遇、级别应在流内十班以下。
(四)右军将军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记:张僧繇“右军将军”为宫廷侍卫武职,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定为流内九班。[11]1011唐余知古《渚宫故事》:“张僧繇避侯景之乱,来奔湘东王绎,承制,拜右将军。”其中,“右将军”当为“右军将军”省称,是知张僧繇获该官应在梁元帝承圣(552—554)年间(详于下文)。
(五)吴兴太守
《历代名画记》所记:张僧繇“吴兴太守”一职当为“吴兴郡太守”省称。南梁“郡置太守,置丞。”[10]729虽郡太守官班不见于当时官班令,然可从他人任此官职情况稍作推测。《梁书》柳恽本传:
“恽善奕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二年,出为吴兴太守。六年。征为散骑常侍,迁左民尚书。八年,除持节、都督广、交、桂、越四州诸军事、仁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征为秘书监,领左军将军。复为吴兴太守六年,为政清静,民吏怀之。”[5]332
天监二年(503)柳恽为吴兴郡(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六年(507)征召为散骑常侍(流内十二班)、迁转至左民尚书(即后世户部尚书,南梁为流内十三班)任上,八年征为秘书监(流内十一班),领左军将军(流内九班,与张僧繇右军将军官班同),复为吴兴郡太守。同书蔡撙本传:
“蔡撙,字景节,济阳考城人……梁台建,为侍中,迁临海太守,坐公事左迁太子中庶子。复为侍中、吴兴太守。”[5]332—333
蔡撙在南梁的“侍中”为流内十二班,“左迁”意为降低官职,“太子中庶子”为流内十一班。综合曾任吴兴太守的柳恽、蔡撙管职变化来看,南梁“吴兴太守”由他官兼领,就二人当时其它有明确官班之官职而言,兼领“吴兴太守”之官当在九班至十三班左右。
如上文,张僧繇拜“右军将军”在梁元帝时,而从《历代名画记》所记:“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来看,僧繇任“吴兴太守”应在“右军将军”(九班)之后,亦应在梁元帝萧绎在位(552—554)期间。
张僧繇以画艺晋升,最终做到吴兴太守,在崇重士族门第,“士庶天隔”的南朝看似有违常规,实则又是符合南梁实际情况的,如梁武帝天监八年(509)五月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5]49《隋书·百官上》记:“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10]723等等。这也为后世宫廷画家出职补官准备了先例。
陈传席《六朝画家史料》:“张僧繇乃是梁武帝的御用画家,从天监中为侍郎直秘阁知画事至太清初,他大约六十岁了,仍然是武帝的御用画家。他大约不会是右将军、吴兴太守,官至太守者史当列传,张彦远恐怕弄错了。”[12]此话应不确。如上引“善奕棋”,梁武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的柳恽(擅长棋艺,与僧繇擅画,均属艺术行业),天监二年,“出为吴兴太守”,八年,“领左军将军(九班)。复为吴兴太守六年”,表明僧繇“历右军将军(九班)、吴兴太守”应不误;而揆诸当时史传,官某某将军、吴兴太守者非仅柳恽、僧繇而已,而是大有人在。故唐代张彦远、刘长卿、余知古等所记僧繇官职当有所本。
上引柳恽“复为吴兴太守,为政清静,民吏怀之”;《梁书》临川靖惠王萧宏(字宣达,梁武帝第六子)世子萧正仁:“为吴兴太守,有治能”;[5]341同书张缵本传:“服阕,出为吴兴太守。缵治郡,省烦苛,务清静,民吏便之”;[5]493等等,表明“吴兴太守”班次虽不见于当时官班令,却是实职,应为吴兴郡最高军政长官。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太守”条:“又,三国以来有遥置之制,亦置官属,给俸禄,本用以赏功臣。梁末以来,京官文武月给唯得廪食,多遥带郡县官而取其禄食。”[13]考虑到张僧繇在南梁宫廷50余年,深得梁武帝、简文帝与元帝知遇,所得“左军将军”为流内九班正式职官,其“吴兴太守”一职当非属此“遥置之制”。
综上述,张僧繇当出生于一般庶人家庭,凭画艺高超于天监二年(503)年奉梁武帝诏画高僧《宝 像》,由普通技艺胥吏做起,通过十余年业绩、年资积累,天监十三年(514)入流,即流内一班(王国侍郎),为武陵郡王萧纪王府官,且为梁武帝宫廷图书收藏机构“秘阁”直官(“直秘阁”),主管绘画事务(“知画事”);“直阁将军”应为梁武帝宫廷侍卫官,为非正式官职,差遣性质,应为梁武帝授;“右军将军”为梁元帝萧绎宫禁宿卫武职(流内九班),“吴兴太守”为吴兴郡最高军政长官,均为梁元帝授。
值得注意的是,“直阁将军”“右军将军”均属宫廷宿卫武职,授予杰出画家张僧繇,盖主要是表示爱好画艺的梁武帝、梁元帝等的知遇,与保证僧繇在君王有绘画等事务需要时出入宫廷方便,以及获得相应的俸禄和其它待遇,应不会履行实际职务(即不带兵履行宫内侍卫职责)。此盖为后世帝王授予宫廷画家武职传统之滥觞。
二、张僧繇师承
姚最《续画品》张僧繇评传:
“善图塔庙,超越群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14]
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七:
“置一乘寺,西北去县六里,邵陵王纶造,在丹阳县之左,隔邸,旧开东门,门对寺。梁末贼起,遂延烧至,陈尚书令江总舍书堂于寺,今之堂是也。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15]
《历代名画记·论顾陆张吴用笔》:
“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1]22
学者多据这些文献史料认为,张僧繇之所以在绘画上取得杰出成就,主要是因为师法天竺画法“凹凸花”并卫夫人书法用笔,创新为与顾恺之、陆探“密体”相对的“疏体”画风。①参见陈传席《六朝画家史料》四十《张僧繇》,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64—265页;周积寅《“六朝三杰”是什么?张家样的特色是什么?》,载《古代艺术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3—214页;林树中《六朝艺术》第二章第三节《张僧繇的绘画》,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138—141页;等等。
《历代名画记·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述晋唐画家师资传授最为详审,却未见张僧繇师资,而实则除师法上述“凹凸花”、卫夫人书法用笔外,他还师法曹不兴。同书张僧繇评传:
“初吴曹不兴图青溪龙,僧繇见而鄙之,乃广其像于武帝龙泉亭,其画草留在秘阁,时未之重。至太清中,震龙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1]90
其意为:起初,三国吴曹不兴画清溪龙,张僧繇见后感觉画得不好而鄙视之,于是将这幅龙扩展放大(即临摹放大)画到梁武帝龙泉亭壁上,画稿留在秘阁,当时没觉得宝贵。直到太清(547—549)年间,雷电震动龙泉亭,壁上扩放的龙腾云而去,才知道曹不兴所画清溪龙的神妙。
由此可知,张僧繇曾师法曹不兴《清溪龙图》,而陆探微师法顾恺之,顾恺之通过卫协师法曹不兴,吴道子师法张僧繇。是知中古四大家实际上出自同一系统,张彦远谓顾、陆为“疏体”、张、吴为“密体”之划分,仅是顾陆系统内部分化而已。
现存日本大阪的《五行二十八宿神(真)形图》,北宋《宣和画谱》著录为张僧繇作品后,多为后世认同,如明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吴诗初《张僧繇》:“从影印本看,作者是以细画见长的,这虽然不能使张僧繇的艺术特征完满地再现。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必然体现了原作某些方面的特点,对研究张僧繇的技法风格,仍然不失为现在所能占有的唯一资料”;[16]30—31林树中先生认为:该“作品属‘密体’,与传记所载张画‘疏体’不同”,[4]140二位先生均认为该图为张僧繇“密体”风格作品,与张彦远以来僧繇疏“疏体”风格的传统认知不同。对于这一不同,吴诗初的解释是“创造疏体画法的张僧繇,在艺术实践中并不排斥密体画法的存在,而是以疏体为基调与密体结合运用的”;[16]6林先生的解释则是“一个人一生可以有不同风格作品”。[4]140实则如果对上引《历代名画记》中天监十三年(514)后张僧繇临摹放大曹不兴名作《龙图》之文献有正确理解,便可明白,僧繇“密体”画风实当源于曹不兴,且属于30岁以前的早期风格。这也符合画家青少年时期临摹学习传统流行画风,而后自创风格的一般成长历程。
三、张僧繇《宝 像》
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除著录张僧繇七处寺院画壁外,尚有:
《汉武射蛟图》一卷,《吴王格虎图》一卷,《羊鸦仁跃马图》一卷,《行道天王像》一卷,《维摩诘像》一卷,《宝诘像》一卷,《摩纳仙人像》一卷,《朱异像》一卷,《梁宫人射雉图》一卷,《醉僧图》二卷,《咏梅图》一卷,《横泉斗龙》一卷,《杂人马兵刀图》一卷,《昆明二龙图》一卷,《青溪宫水怪图》四卷(已上诸画《太清目》皆无)。
右十九卷张僧繇画,九卷,隋朝官本。(张彦远《名画记》又有《梁武帝像》《定光像》《田舍儿舞图》)。”②(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于安澜编《画品丛书》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38页。按:《贞观公私画史》现存最早版本当为南宋书棚本,括号里的注释文字“张彦远《名画记》”云云应为南宋刊刻时所加。
此外,《历代名画记·张僧繇》尚著录有《梁北郊图》。惜乎唐代著录的这二十三卷无一卷留存至今。其中《宝诘像》值得特别重视。今存宋书棚本、《王氏画苑》本、《说郛》本、《古今图书集成》本、四库全书本、美术丛书本等《贞观公私画史》虽均作《宝诘像》,然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本《贞观公私画史》作“《宝 像》”;[17]清刘世珩《南朝寺考》:“《贞观公私画史》:张僧繇画《 公像》于梁开善寺。(案即今之三绝碑也)”,[18]15加之张僧繇时代及以前并无宝诘其人,故“《宝诘像》”当为“《宝 像》”,“诘”“ ”盖因形近而讹。“宝 ”(418—514)世称 公、宝公等,为南朝高僧,深得梁武帝等知遇。天监十三年(514),宝 卒。《梁书》王筠(482—550,字元礼)本传谓其“奉敕制《开善寺宝 大师碑文》,词甚丽逸”;[5]485唐李白(701—762)《 公画赞》: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锦幪鸟爪,独行绝侣。刀齐尺量,扇迷陈语。丹青圣容,去住无所。”[2]1567
唐寒山(约691—793)《诗三百三首》:
“余见僧繇性希奇,巧妙间生梁朝时。道子飘然为殊特,二公善绘手毫挥。逞画图真意气异,龙行鬼走神巍巍。饶邈虚空写尘迹,无因画得 公师。”[19]
唐李顾行(元和五年进士,官监察御史)《上元县开善寺修 公和尚堂石柱记》:
“ 公和尚者,实观音大士之分形者欤!然迹见于近代,《梁书》具载其事……初 公之未迁灭也,梁武帝命工人审像而刻之,相好无遗,俨然若对。建窣堵坡于金陵之开善寺,圣功冥化,历代瞻敬。人钦其神者二百余祀……长庆四年(824)三月十一日记。”[2]3652
这些史料表明,张僧繇奉梁武帝敕画当时高僧宝
之像后,武帝又令工人将《宝 像》刻于石碑上,且敕令王筠制碑文。碑成,于金陵开善寺内建塔(即宝公塔)置之,以供后代瞻仰。北宋志磐《佛祖统计》卷三十七记,天监二年(503),梁武帝“尝诏张僧繇写 真,以指剺破面门,出十二面观音相,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写。”[20]明确了张僧繇画《 公像》的时间,王筠撰碑文,工人刻碑当在宝 卒后不久。
这一南梁武帝时代围绕僧繇作《 公像》而展开的艺术活动影响广大深远。在后代佛教典籍中,此事被作为典故反复运用,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良工幻出兮不许僧繇知,虚堂张挂兮梁宝公犹迷”等;[21]在后世山水游记、地方史志中,则作为与唐李白诗、颜真卿书法齐名的三绝,如明宋濂《游钟山记》(1361年作):“复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数辈。中有张僧繇画大士相,李白赞,颜真卿书,世号三绝”;[22]葛寅亮(1570—1646)《金陵梵刹志》:“三绝碑(唐张僧繇画大士像,李白赞,颜真卿书,为三绝,下有赵孟頫书《 公十二时歌》)”;[23]甚至被作为艺术再创作的素材,如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李太白赞宝公画像(李伯时画《梁武命张僧繇为宝公写真》,米芾书赞云)”;[24]明嘉靖《江阴县志》:“广福寺西庑藏殿后壁,有嘉祐(1056—1063)间惠天师昙素画《梁武帝召张僧繇写 公变相图》,笔力遒徤,神气欲生,见者惊悚”;[25]等等,涉及政治、宗教、文学、书法和绘画人物梁武帝、宝 、张僧繇、李白、颜真卿、李公麟、米芾、赵孟頫等。影响远远超过上列唐代著录张僧繇二十三卷传世画作中的任何一卷。而当代学者研究颇多的《五行二十八宿神(真)形图》最早为《宣和画谱》张僧繇评传著录,一说为唐梁令瓒作,作者归属迄今仍有诸多争议。或可以说,僧繇《 公像》已成为后世中国文化史的一道靓丽风景。
四、张僧繇生卒年
张僧繇生卒年不见于载籍。
袁有根先生推测,僧繇约生于497年;[26]谢巍谓僧繇:“约建武年间(494—498)生,太清年间(547—549)卒,年五十多”,[27]均属推测,未予论证。林树中《张僧繇年表》谓:约生于“萧齐永明二年甲子(484)。”[4]359论证大致为,据《佛祖统纪》记天监二年(503)张僧繇奉敕画僧宝 像,《名画记》记:张僧繇“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梁书》记:萧纪于天监十三年(514)封为武陵郡王等信息,认为:
“……而奉敕画高僧宝志像是最早有纪年的张僧繇事迹。六朝士族子弟20岁行成人礼并出仕,称‘释褐’。如以天监二年为20岁,则约生于萧齐永明二年(484年)。天监十三年(514年)任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时约31岁,也是合乎常理的。”[4]359
谓“六朝士族子弟20岁行成人礼并出仕,称‘释褐’。”应不确。当时世族、寒族子弟入仕主要通过入国子学成为国子生,经过一定时间学习后,参加策试。南齐时规定国子生入学年龄为“十五以上,二十以还”,[28]南梁时国子生入学年龄还小一些,如《梁书》记:王锡“十二,为国子生。十四,举清茂,除秘书郎”,[5]326上引卞华“年十四,召补国子生”,萧乾“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等,均可证。齐梁成为国子生后学制为几年才能参加策试、授官,未见明确令式规定,但上引王锡两年,萧乾、张缵六年,王承八年,而王锡、张缅、张缵、萧乾、王承等“释褐”均在20岁以前。
林先生的论证虽有一些问题,但张僧繇天监十三年(514)约31岁的论点却是可取的。《隋书·百官志上》:“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10]748(意为通常情况下,除士族或寒门子弟通过国子生、策试入仕年龄可在30岁以内外[如上引王锡、张缅、张缵、萧乾、王承、卞华等均是],其他人入仕均得年满30岁)这样的令式来看,张僧繇应是通过三品蕴位序列(即胥吏通过积累业绩、年资晋升)获“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的,须要满足已满30岁的年龄条件。故袁有根先生推测,僧繇约生于497年,谢巍谓,僧繇约生于建武年间(494—498),生均当未契,当以林树中推断,僧繇约生于484年为当。
林树中《张僧繇年表》谓张僧繇卒于天保元年(562),享年约79岁。论证所依据的两条文献史料为:
一是《历代名画记》:“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毁拆”;
二是唐代道宣《续高僧传·释慧耀传》:“慧耀(525—603年)晚年十数年间,为江陵导因寺住持。此导因寺即今(初唐)之天皇寺”。“天皇寺现柏殿(《名画记》作‘柏堂'),五间重层,梁之右军将军张僧繇亲笔所图”。“殿其工(?)正北,卢舍那佛相好威严,时发光明。”
针对这两条史料,林先生给出了三点解读:
一是认为张僧繇“画《卢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图于江陵天皇寺。(后梁)明帝萧岿异之”;
二是“按:明帝,在南朝刘宋有刘彧;萧齐有萧鸾;后梁有萧岿。当是萧岿”;三是僧繇“此年或是年后卒”。[4]376
林先生所据两条史料虽基本无误,但对其解读却有误。失误的关键点在认为《历代名画记》中所云:“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中,“明帝”为后梁萧岿,而实当为简文帝萧纲。宋蔡梦弼笺《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三十五:
“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画图(此寺有大王右军书,张僧繇画《孔子十哲》形像。按《渚宫故事》:张僧繇避侯景之乱,来奔湘东王绎,承制,拜右将军,僧繇工画,为南郡之冠。常于天皇寺栢堂图《卢舍那佛像》,夜有奇光,发自屋壁。又于堂内图《孔子十哲》,识者谓右军绝笔。湘东记室鲍润岳曰:‘释门之内,写素王之容,虽神异无方,岂可夷夏同贯。’僧繇笑曰:‘吾诚偶然,安知不利于后。’闻者莫晓其意,及后周灭二教,梁为附庸,荆楚祠宇莫不尽撤,惟天皇寺有宣尼像,遂为国庠。时人叹其先觉。”[29]
这是宋蔡梦弼引唐余知古撰《渚宫故事》相关内容笺,杜甫“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画图”诗句。引文对僧繇画江陵天皇寺《卢舍那佛像》及《孔子十哲》的时间、人物与地点等要素有较明确交代。时间在“张僧繇避侯景之乱,来奔湘东王绎,承制,拜右将军”前后,“侯景之乱”在公元548年八月至552年四月之间。而萧岿(542-585,字仁远)为后梁(或西梁)第二位皇帝(562—585年在位),谥号孝明皇帝。可见:
一是《历代名画记》张僧繇评传所记“明帝置”中“明帝”不当是后梁萧岿,而应为南梁简文帝萧纲(503—551,字世缵,549年五月即位,551年十月为侯景所杀,伪谥号明皇帝,庙号高宗。551年三月,王僧辩灭侯景,湘东王萧绎追尊为简文帝,庙号太宗),如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梁天皇寺(张僧繇、解倩画,在江陵)。”[30]表明天皇寺为南梁寺院;清刘世珩《南朝寺考》:“天皇寺,梁简文帝所建也。”考证:“《景定建康志》:天皇寺,明帝所置也。陈云:南朝惟晋、宋、齐有明帝,而皆与张僧繇不同时,盖此时侯景弑简文帝,初谥……”[18]41—42其中“初谥”意为侯景弑简文帝萧纲后所给“明皇帝”谥号。
二是针对僧繇画《孔子十哲》于天皇寺,发出“释门内如何画孔圣?”之问者,《历代名画记》记为“明帝”(即“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帝怪问……”),宋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引唐张鷟《朝野佥载》也记为“明帝怪问……”[31]那么,从这里看,“明帝”究竟为谁?应为萧纲。因为上引《渚宫故事》“常于天皇寺栢堂图……”中“常”古与“尝”通用,《(绍定)吴郡志》引为“尝画江陵天皇寺栢堂……”可证。尝:曾经。则《渚宫故事》所记意为张僧繇“来奔湘东王绎”之前即已画《孔子十哲》等,故只能是在萧纲在位时画的,而不可能是11年之后即位的后梁明帝萧岿时。
三是发出“释门内如何画孔圣?”之问者,《渚宫故事》记为:“湘东记室鲍润岳”,“湘东记室”为湘东王萧绎(514封湘东王,至552年十一月即皇帝位,为湘东王38年)王府官,而萧绎547年任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天皇寺在江陵[即荆州]),故僧繇画《孔子十哲》等应发生在547年至552年十一月间。而简文帝萧纲549年五月至551年十月在位,在时间上也是与“一是”“二是”推断吻合。
《渚宫故事》《朝野佥载》《历代名画记》等所载张僧繇于江陵天皇寺画《卢舍那佛像》及《孔子十哲》在简文帝萧纲时,是有关僧繇记载之较晚者,但不是最晚者,林先生以此作为张僧繇卒年依据应误。
《历代名画记》:“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应是张僧繇生平信息最晚者,而僧繇任“右军将军”的时间《渚宫故事》明确记载为:“张僧繇避侯景之乱,来奔湘东王绎,承制,拜右将军。”“承制”意当为即帝位,如《梁书》鲍泉本传:“鲍泉,字润岳,东海人也……少事元帝,早见擢任。及元帝承制,累迁至信州刺史”;[5]448该书张缵本传:“防守缵者虑追兵至,遂害之,弃尸而去,时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赠缵侍中、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简宪公”;[5]503等等。如此,张僧繇官“右军将军”则在梁元帝萧绎即位(承圣元年[552]冬十一月)后。而任“右军将军”之后所任“吴兴太守”,亦应在梁元帝时。萧绎承圣元年(552)至三年(554)在位,故承圣三年当为张僧繇卒年上限。若依林树中先生谓,僧繇约生于484年,则其享年当在71岁左右。
五、结语
张僧繇约生于公元484年,由寒微胥吏做起,天监二年(503)奉武帝诏画《宝 像》,天监十三年(514)后,历官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直阁将军、右军将军、吴兴太守。在绘画上,天监二年所作《宝 像》影响深远;天监十三年“直秘阁”后,曾师法曹不兴《龙图》;约卒于梁元帝时代或稍后,享年约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