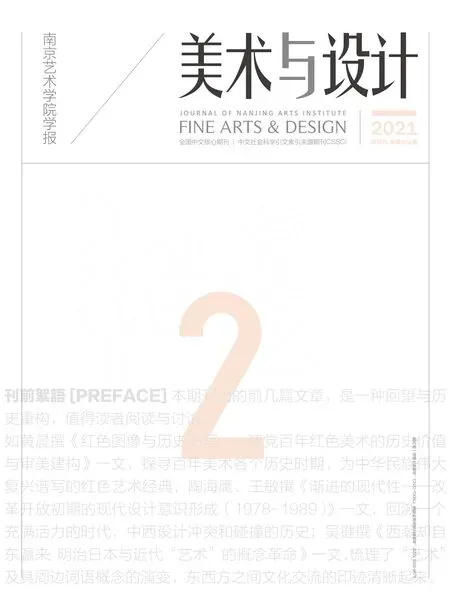想象与行动的伦理学:面向新兴技术的设计思辨①②
张 黎(广东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62)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林格里奇”困境
未来具能高力的人工智能及其自主系统,将对世界产生像工业革命一般规模的变革性影响。然而,与每次生产力革命一样,繁荣背后的风险与问题,同样值得重点关注。在 AI 技术逐渐主流化的当下,需要确保这些技术与人类在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则方面保持一致,已成为当代技术伦理学的主要议题。2017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机器人伦理报告》,建议各国制定 AI 伦理准则。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于 2016 年启动发布的“关于自主/智能系统伦理的全球倡议”及其《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白皮书》,并于2017年12月发布第二版“合乎伦理设计(Ethically Aligned Design,简称 EAD)”的指南,已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同。人工智能这类新兴技术的伦理问题得到世界性关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被描述为“科林格里奇”困境。
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在其1980年的著作《技术的社会控制》中提出过一种“控制的悖论”,[1]即当一项技术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时,虽有较大可能去干预其发展方向,但由于尚未充分了解技术将如何影响社会以及将会产生哪些影响,从而无法实施干预。然而,一旦技术完成深度的社会嵌入,人们虽已确切了解其结果和意义,但已很难再去改变它的发展方向和程度。这一难题被称为“科林格里奇”困境,也是技术伦理学面临的经典挑战之一。
当代技术伦理学已发展出了几种策略用于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比如针对创新结果的“前瞻性评估(prospective evaluation)”,[2]以及针对创新过程规范的“技术道德变革(techno-moral change)”[3]、“道德物化(materializing morality)”[4]和“技术调解(technological mediation)”[5]以及“社会技术实验(sociotechnical experimentation)”方法[6]等。其中,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及其提出的“道德物化”理论,以人工物作为道德主体的思路突出了技术设计过程中的伦理诉求,尤其值得关注。
人工物伦理是当代技术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日常化,我们正进入一种“后人类”的状态,这种后人类状态一方面表征着人的机器化趋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机器的具身化态势。在伦理学领域,人工物是否能像人类一样成为道德主体并发挥伦理价值,是技术伦理学的争议之一。受到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霍特斯(Gilbert Hottois)的“技术伴随伦理学”思想、唐·伊德(Don Ihde)的“技术现象学”取径等影响,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顺应了技术哲学的物转向和后人类主义趋势提出了“道德物化”概念,指的是在设计过程中把抽象的道德规范“写入”具体的技术物,人们通过使用这些被道德化的技术物来履行或遵从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从而在行动中对使用者的行为形成道德引导。比如公路上的减速带、公共卫生间的感应式水龙头和限量纸巾盒、地铁里的限流管控设备等。人们在使用这些技术人工物或曰设计的时候,需要遵守已经预设了道德伦理规范的行为准则,才能获得物的全部可用性。“道德物化”作为当代技术伦理学新思潮的代表,有助于克服技术伦理学面临的“外在主义”(externalist)诘难,[4]4即传统的技术伦理学把伦理道德看作技术活动之外的“外在”规范力量,仅对技术的后果进行伦理反思和价值批判;“道德物化”的提法将技术伦理的评估对象从结果前移至设计过程,将结果反思调整为实践干预,突出技术设计伦理的建构型特征。
然而,“道德物化”等策略也存在“短板”,比如仅考虑了设计情境中的利益相关者即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等专业人群,由于新兴技术固有的认知门槛,使用情境中消费者与用者,仍然无法参与技术伦理评估。除此之外,面对新兴技术无法预判的社会影响,传统伦理研究从原理到个案的演绎逻辑已然失效,如何在动态的价值框架之中去想象、虚构、推测并思辨新兴技术的伦理后果,从而主动影响甚至干预技术选择与应用的决策权,也是当代伦理学面临的主要难题。
思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①思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是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与菲奥娜·雷比(Fiona Raby)在其2013年的新书《思辨一切:设计、虚构与社会梦想》(Speculative Everything: 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s)中提出的概念,中文版2017年12月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关于该概念的历史、释义、案例等,也可参见拙文:从激进到思辨:设计如何催化社会梦想[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4):14-19,187.从时间、知识和权力三个维度试图解除前述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从时间轴看,思辨设计强调想象力的运用,并采用设计未来(design futures)、设计虚构(design fiction)、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等方法,将技术伦理评估的时间点前移至尚未完成商业化应用之前;在知识生产方面,思辨设计以道具和场景取代抽象的文字语言对可能的技术后果进行视觉化呈现。在权力层面,本着“智识平等”的预设,以想象力这种人类通识能力为催化剂,思辨设计以提问取代回答,以荒谬感和歧感引发好奇和关注,以期激活观众主动求知的意志和动机,“到底要不要接受或改变这种技术未来”,将技术选择与使用的决策权留给观众。综上,思辨设计要发挥其作为实践伦理学的行动潜能,其核心在于基于技术现实的想象。一方面,设计师要运用想象力去构筑出一种虚构的未来;另一方面,观众要运用想象力去理解这种不同于常识、有别于现实的另类未来。科林格里奇本人也曾指出,要克服未知技术结果应保证技术的可改正性、可控制性和可选择性等三种属性。[1]11思辨设计则是以想象力维护了人们关于未来技术发展选择的决策权。
思辨设计充分发挥和调动设计师与观众的想象力,以道具和场景构建出某种技术原型载体的伦理叙事,以可视化的优势增益了道德物化的影响力机制,并邀请观众一起想象,从而影响其技术决策权,引导技术人工物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相适应。本文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语境中论述思辨设计如何以想象发挥出实践伦理学的行动潜能,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回答思辨设计如何以想象力为核心动能体现其作为实践伦理学的优势;其次将说明思辨设计如何通过设计虚构和思想实验等方法展开并推动想象,从而将观众/用户纳入到技术伦理的决策环节;最后将解析思辨设计如何通过想象力实践“智识平等”的预设,以共同决策的未来选择去落实兑现技术人工物的伦理价值,从而以设计实现赋能。
二、作为实践伦理学的思辨设计
当代新兴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且作为一种支配力量对个人微观生活和社会全局正发挥着显著影响。然而,学界对这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技术及其前提缺乏足够的审慎与反思,其深层原因在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论。面对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颠覆性伦理影响的新兴技术,比如基因编辑、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其伦理影响十分复杂,目前对这类“会聚技术(NBIC)”可能引发的伦理挑战暂未形成有效预案,也加剧了技术发展结果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新兴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前提与路径必须得到“伦理先行”的谨慎研判。另一方面,随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7]“理论已死”与“理论无用论”等说法甚嚣尘上,再加之图像转向,理解语言的门槛似乎越来越高,理论对行动的说服力也越来越弱。新兴技术的“潘多拉魔盒”效应让人们进退两难,关于“这些技术将会对人类未来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受限于语言的理论讨论干瘪且抽象,很难引起主要技术受众的关注与理解。
思辨设计以创新的非现实美学策略,一反主流的技术乐观主义,对新兴技术与未来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进行可视化地推测与虚构。邓恩曾认为,当今智能产品设计在商业机制的主导下已经只剩符号学层面的操作了,智能技术内置的风险被包裹在黑箱之中,成为看不见的秘密。传统智能产品的所有属性均以“优化”为唯一考量,使得人工智能携带的伦理问题被束之高阁,最终将导致人工智能的发展“脱轨”。因此他提出将智能产品设计为“后优化物件(Post-optimal object)”[8]的可能性,寄希望于思辨设计能够重新唤起人类对新兴智能技术伦理问题的意识与反思。
借助人工物发挥出语言的文本性与启发性,使得设计有望在未来伦理学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设计师式的未来探索模式是一种更具物质性的、视觉性的并具有操演性的方式,能有助于各种可能性的具化与阐释”。[9]设计师需要重新审视其输出物,包括产品、介面、图像、环境、服务,与系统等对于未来世界的影响力。无论未来如何变更,人的日常生活无法离开物(object),如前所述,通过物来发挥道德影响和伦理干预,也是近年来技术哲学荷兰学派的主要思路。在所有的设计实践类型当中,思辨设计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未来研究(future studies)方法论,它能对尚未发生的技术伦理议题进行想象与推测,并通过创建的平行世界及其另类未来观,引发关于人与技术异化关系的反思,在思维与行动层面唤醒人们“身体力行”地去解决因技术引发的存在困境。近年来,在技术哲学物转向的趋势下,思辨设计凭借着其独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优势,已展现出另类且巨大的伦理潜能空间。[10]
实践伦理学与传统的理论伦理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实践”二字。首先,实践伦理学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原则为轴心。由于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实践伦理学并不照搬既有的伦理学原则,而是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按照动态价值框架去理解并灵活地运用原则。传统的价值判断原则及其规范体系,只作为动态价值框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且随着技术实践的展开,结合具体情境对其进行具象的价值评估与理性反思并调整相应决策。与以解决问题为核心任务的传统设计方法不同,思辨设计充分认识到新兴技术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重在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从而引发讨论,并以道具和场景来架构出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平行世界,在其中展开相关技术困境的具体讨论。在提出“思辨设计”之前,邓恩还曾提出过一种“为了辩论的设计(design for debate)”的方法,[11]以“如果……会……(What-If)”设问方式,对技术的可能后果进行既合理又大胆地推测,供大家对其进行辩论,并充分了解技术后果,从而对观众的技术应用决策施加影响力,这一方法可视为思辨设计的早期原型概念。另外,实践伦理不仅导向实践,且伦理本身也有赖于实践来实现。结合思辨设计提供的关于未来技术叙事的想象、理解与反思之后,观众以其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伦理观念等去兑现自己的技术决策权和话语权,充分体现了实践伦理学的作用机制。
早在2014年5月,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曾与另外几位顶尖科学家,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同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等,在为英国《独立报》撰文时表达过对人工智能这类新兴技术潜在危险的忧虑,并呼吁人们去“想象(imagine)”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被广泛应用之后的可能后果。[12]可以看到,为了让大家正视新兴技术的潜在风险,科学家们使用了一个常见但十分精准的动词——“想象”。然而,这里的难题实则是“如何想象”,尤其是如何邀请大众一起想象新兴技术的未来。对于科学家等精英群体而言,这样的“想象”显然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但对于普通人而言,这种想象是有门槛的。换一种提问方式更容易理解上述难题,即如何借助想象,将讨论新兴技术及其影响力的话语权从专家拓展到大众?思辨设计通过设计虚构与思想实验对上述难题提出了可行思路。
思辨设计动用想象力,基于思想实验的逻辑,对某种新兴技术的可能影响进行推测,以日常生活作为语境,以道具和场景作为媒介,谨慎地虚构出某一技术可能引发的后果。可以看出,为了让普通人参与到技术后果的想象与讨论中,思辨设计不是基于抽象的文字或口头语言进行提问,而是选择对新兴技术的伦理风险实施“降维”地视觉表达与故事化预演,邀请普通大众基于可视、可感、可知的道具和场景及其叙事展开想象与反思。想象力既是设计师启动思辨的主要助力,也是观众理解与参与讨论的重要触媒。
三、伦理如何想象:设计虚构与思想实验
荷兰设计研究学者多勒斯汀(Dorrestijn)和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曾提出过一种“后乌托邦设计”(postutopian design),[13]与传统乌托邦设计运动的主旨不同,后乌托邦设计结合助推(nudge)方法和劝导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等当代技术伦理学框架作为方法,在人类福祉和自由意志之间保持平衡,以设计引导(而非强制)人们通过改善自身决策和行为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面对技术伦理难题,思辨设计“只问不答”,以非现实的美学策略,引导大众对新兴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想象与反思,以谨慎的技术伦理观为准绳以期影响人们的技术决策权,从而引发行为层面的改变,继而进一步调整现实与未来的关系,推动实现以人类福祉为愿景的社会梦想。从这一操作逻辑来看,思辨设计的伦理价值从想象中开始,在行动中完成。
如前所述,如何克服进退维谷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是技术伦理学的经典难题。当技术尚未被大规模应用,如何能够知晓其可能的潜在危险;一旦技术被大规模运用,如果真的存在危险,又无法撤消其影响。面对传统技术,从伦理学理论与原则(或规则)可借助演绎逻辑推导出关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演绎逻辑无法解决因新兴技术引起的伦理争议。[14]技术是全新的,影响将是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也是从未遭遇过的。在这种未知因素远远多于已知因素的问题语境中,知性和感性都需要让位于想象力,想象力在康德看来亦是具有超越性和无限性的人类灵魂性能。[15]
对想象力的强调与运用,是思辨设计在方法论层面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来自于思辨设计的认识论基础,即未来锥体(future cone)及其对多重未来的区分。[16]面向未来可能而不是当下现实,是思辨设计的价值取向。思辨设计的主要设计对象是技术,尤其是那类影响甚大,但对其反思极其欠缺的新兴技术。思辨设计动用想象力,实施两种类型的技术思辨,一是对尚未现实化技术进行的思辨与推测,以期提供反主流未来的可能面貌;一是对现实新兴技术的批判与反思,以期呈现出另一种(alternative,也可译为“另类”)当下的可能。因此,思辨设计实践主要有两种类型且都与想象力相关:一是对可能未来的思辨;一是对另一种/另类现实的虚构。而且,维持当下与未来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也是思辨设计的显著特点之一,[17]然而要维持两者的互动,想象力是关键所在。
“思辨”一词来自于英文单词Speculative。①其名词形式为speculation,动词形式为speculate,该词除了“思辨”之义之外,还有“臆想的”“带着疑问的”“推测”“思索的”“好奇的”等释义。关于SpeculativeDesign的翻译问题,可参见拙文:从激进到思辨:设计如何催化社会梦想[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4):14-19,187.很多人看到思辨设计的第一印象大多是“天马行空”“脑洞大开”“想象力‘爆棚’”等印象,因为虚构(fiction)确实是思辨设计发挥想象力的主要方式之一。虚构的特征主要包括诗性语言的运用,叙事的建构以及突出的另类审美。[18]也因此,思辨设计常被误解为设计虚构(design fiction)。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误解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即思辨设计确实采纳了设计虚构作为具体的设计方法。美国科幻小说作者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曾将“设计虚构”定义为:“有意使用故事原型来悬置对变化的怀疑”。[19]这一定义非常适合解释思辨设计以物理道具及其虚构美学来讲故事的做法。之所以如此倚重虚构,是因为思辨设计处理的母题均来自于尚未现实化的未来时空或不同于现实的平行世界,既然如此,不虚构便无法展开讨论的可能。
实际上,任何设计都带有某种程度的虚构性,都是希望说服利益相关者共同实现或接受某种技术调解的未来版本。然而,思辨设计并非设计虚构,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如设计虚构以较为中立的价值立场呈现未来,而思辨设计的态度则更具批判性。且正是这种差异性反而突显出了思辨设计基于技术人工物的伦理性优势。对于设计虚构而言,虚构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但对于思辨设计而言,虚构只是工具,其目的是建立多方对话,从而导向良善的技术未来。具体而言,思辨设计刻意摆脱了受限于市场导向的商业惯例及其约束,动用虚构并推测未来世界的产品、服务和系统,反思性地探索新兴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可能作用和潜在影响,从而启动专家人群与新技术主要受众之间的对话。通过多方对话,去推动那个符合多数人意愿的未来能够成为现实。思辨设计主要依赖于思想实验开启的问题意识去推动虚构与推测,从而讨论那些尚未发生、然而一旦发生后果却非常严重的未来。如前所述,思辨设计的虚构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虚构的方式,让观众发声才是其主要目标。思辨设计应该“将此种风险构成的过程明确地展示出来,从而才能真正引发多方面的讨论。”[20]
思辨设计以“如果……会……”的思想实验作为开端引发讨论并建立对话。设计师利用虚构的手法推测出一个尚未存在的问题空间,“如果……会……”这种假设性提问方式来自于哲学领域的思想实验,思辨设计采纳思想实验的提问方式,目的是通过虚构出极端的伦理困境,从而放大或突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可能张力,尤其是新兴技术可能在社会中释放出的负面影响力。类似的问题有:“如果基因编辑这种技术被全面地商业化,人类社会会发生什么”“如果可以选择,你会为自己的后代设计哪些特质”“如果生物燃料技术被深度市场化,你会用动物或敌人的血液作为原料为自己生产电能吗”“如果未来人类需要与动物形成共生关系才能存活下去,你会选择与哪一种动物共生以何种方式共生从而尽可能维持目前的生活质量”“如果COVID-19这类病毒将不断变异、疫苗失效,人类社会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等。这些假设性问题要么涉及的是尚未市场化的技术原型及其社会后果,要么引导人们关注到那些很有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且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问题领域。思辨设计重点考虑的正是一旦这些技术被深度市场化,将会产生哪些严重的伦理影响。为了避免“科林格里奇”困境,思辨设计将讨论技术伦理的时间点前移至技术尚未被市场化之前,并采用道具和场景将尚未发生的技术后果进行可视化的故事化表达,让人们可以实在地“看到”这些来自于“近期未来”(near future)的技术以及一旦当它们被深度嵌入社会生活时将可能发生怎样的结果。
从苏格拉底的伦理观、伦理即美好生活的要义来看,人类所有的技术选择都关乎伦理,都是关于如何通过某种技术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除此之外,技术不仅关乎目的,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与价值判断。[21]如果关于这些涉及到人类未来取向的讨论仅停留在抽象的语言层面,能够参与其中的人必定是少数精英。思辨设计以物为媒,将技术应用可能的未来后果以虚构化的视觉方式“提前地”呈现出来,将原本以语言为载体进行的思想实验,转变为通过视觉化的具象方式进行,从而将局限在专家之间的技术讨论话语权扩展到技术的直接受用者——大众手里。这便是思辨设计以想象力推动伦理实践的行动机制,结合设计的可视化操作,以虚构的设计推动思想实验从抽象的思维层面“降维”到具象的视觉层面,从而实现技术伦理话语权的大众化普及。
通过设计虚构与思想实验,思辨设计才得以维持从现在到未来,从现实到科幻,从日常到无常之间的沟通。以想象力探秘未来技术的伦理可能,使思辨设计比传统的技术伦理学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当下与未来,在思辨设计的认识论框架中,因想象力的润滑始终保持着联动状态。思辨设计为大众提供的是那种很有可能实现,但却未经民意充分商讨过的未来。要理解思辨设计基于未来的虚构叙事,并对这种悲观的、负面的、反乌托邦的未来叙事保持警醒,需要观众想象性地主动介入。思辨设计以想象力启发大众动用技术决策权对它呈现的“反”未来版本进行反思、改造或规避,从而参与到对当下现实的改良行动中,以期实现那个大多数人“想要的”(perferred)未来。
四、思辨设计的伦理优势:以想象为行动赋能
激进民主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empower”,中文可译为“赋权”“赋能”或者“赋予力量”。“赋”这个字的使用,特别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即力量(power)的实现似乎来自于外界,来自于他人的给授。如果接受这种力量来自于外界的赋予机制解读,便“不仅承认给予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不平等且在事实上也制造了这种不平等”,因此力量只能借助于“行动者自身的实现与实际化过程”。[22]换言之,力量隐形地存在于每个人,就像隐藏在脂肪下的“马甲线”。解放者的功能不是给行动者提供任何现成的东西,比如知识、技能、理解力等,而是帮助行动者“减脂”,当脂肪(障碍)移除之时,便是肌肉(力量)显形的时刻。人们缺的不是力量(知识或理解力)本身,而是去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志和动机。思辨设计以想象启发的正是观众愿意去改变的意志和动机。所以朗西埃认为,解放关乎意志,不在于“解释”(提供答案),相反,解释恰好是造成受奴役状态的主要原因。[23]
思辨设计重在以想象发问而不是以知识解惑,背后的动机是在启蒙。启蒙的难题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使用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后者正是意志管辖的范围。朗西埃在《无知的教师》一书中确定了教师的作用并非在于占有知识而是驱动意志,不是去解释教师知道了什么而是下达指定,因为在其“智识平等”的预设中,每个人的智力能力(capacity)是相当的,只是当处于结构的不平等境况当中时,才有了差异化或等级化的智力表现(manifestitations)。[23]解释与提供解答等行为会不断重申并落实技术专家人群的优越与技术受众的无知,从而再次确认现有社会结构的不平等。
因此,真正的解放,便是要克制这种“好为人师”的解释冲动。思辨设计确实在回避“解释”或“提供解答”这件事情。除了不提供答案之外,思辨设计通过刻意减少细节和真实感的方式塑造场景,采用虚构感十足的道具取代真实的产品,都是为了移除“现实世界思维惯性”的阻力,帮助人们释放思维本身的动能。思辨设计不提供现成的知识,它提供的是促进以不同于现实的思维模式去展开想象的场景。想象虽然是大脑内部的事情,但需要从外界获取符号的意义,并经由道具作为媒介的物质性转变为内部的符号意义,转变为自己的理解。获得新知是关于意志和注意力的事情,思辨设计以另类美学唤醒注意力,时刻在言说自身与当下现实世界的差异,并标明自身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刻式描述,而是提供了一幅关于未来的简笔画,以全新的陌生感引发想象力、激发兴趣和意志力,以期推动观众的自我解放。
思辨设计以想象力作为激活人工物伦理性的认识论逻辑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前提预设,即智识平等(intellectual equality)。[23]需要指出的是,智识平等并非思辨设计追求的结果,而是它预设的前提。[24]只有在智识平等的前提之下,不同利益人群之间的对话才有可能搭建起来,沟通才有可能实现。从这一点看,思辨设计的政治性也许并不如对抗性设计那般清晰和直接,而是选择了设计在美学和伦理方面的潜力,由其指向未来的诗学气质和另类虚构的美学特征,完成其政治功能的表达,即解放人的思考和沟通能力,进而选择某种能够实现善的生活方式。
任何沟通的发生都需要借助媒介。要实现有效的沟通,则需要精心选择用以沟通的媒介。朗西埃将实现激进民主的“宝”押在了诗学和美学,主要是看中两者相对宽松、不设限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思维空间。“人在说话的时候……是在作诗。”[23]65然而,作诗的前提是有话可说,面对新兴技术的认知门槛和“科林格里奇”困境,思辨设计对其进行三重处理,让人们对技术伦理的问题有话可说:一是从时间维度上,将尚未发生的事情以设计虚构的方法挪移到眼前;二是从知识层面,将抽象的技术后果具象化为每个人熟悉的日常叙事;三是从权力方面,激活其想象力促使观众以行动实现自我赋能。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能力对科技的社会化未来发挥其话语权与决策权。设计师是在以想象力作诗,也在邀请观者以自身的想象力来读诗,这种诗性体验的高潮将出现在观众自我赋能的行动中。综上,思辨设计作为方法论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实现了从设计师到用户、从技术到社会、从未来到现实、从想象到行动的伦理跨域及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