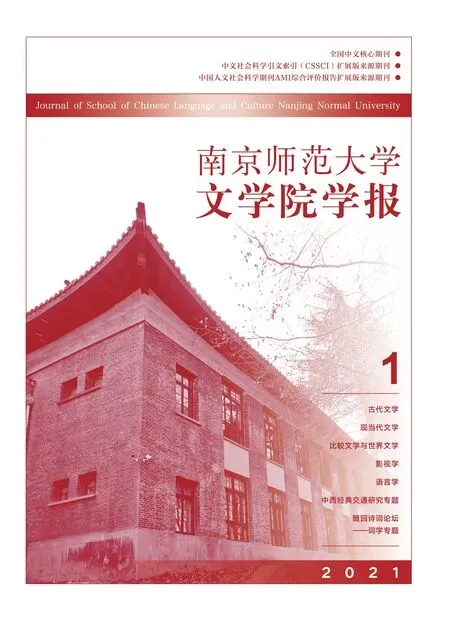亚瑟·韦利《诗经》英译的版本考究与文化翻译新辨
朱云会 胡 牧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孔子教化弟子的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自1871年第一部《诗经》英译全译本(理雅各译)出版发行以来,迄今为止,已经产生了将近20部全译本。[1]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的《诗经》英译本是20世纪以来从文化视角全面解读《诗经》的第一个译本。检索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学界探讨的韦利译本均为1937年译本,研究视角多为文化人类学视角,没有学者梳理韦利《诗经》英译本的版本、分析版本的变化,也鲜有学者对韦利译本的语言特点、韦利对“经学解经”观点的接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根据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华语译文研究馆馆藏的韦利英译《诗经》过程中存留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本文着重剖析:1、韦利《诗经》英译的多个版本;2、韦利对诗歌语言考证的深度与限度;3、韦利“经学解经”观点新探。
一、韦利《诗经》英译的版本考究
检索Worldcat网站,(1)Worldcat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联合目录,由在线电脑图书馆中心(OCLC)提供。检索时间为2020年3月25日。输入“The Book of Songs”和“Arthur Waley”,检索出60个译本(包含信息重复录入),共分为10个版本,出版时间分别为1927年、1937年、1954年、1960年、1969年、1978年、1987年、1996年、2011年、2012年。其中,1927年版本为非公开出版版本;1960年、1969年、1978年、2011年、2012年版本为重印版;1937年、1954年、1987年、1996年版本有变动。仔细阅读四个版本,参阅译本中的注释、题解、附录等副文本资料,以及韦利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参考资料,可以探讨韦利《诗经》英译版本的历时性变化,总结变化特点。
1937年,韦利的《诗经》英译本由伦敦的乔治·艾伦和安文(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社正式发行。该版本是韦利《诗经》英译本的首发版,由序言、引言、译文、附加注释(additional notes)、附录、参考文献、列表(finding list)、索引组成。《诗经》包含305首诗,但是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韦利删减15首诗,认为“这些诗都是对政治的哀叹,与其它诗歌相比,显得枯燥乏味,内容腐败、毫无意义”[2](P11)。这15首诗已经刊登在《天下》月刊1936年第三期。1937年版本的注释较少,为了方便专业读者的阅读与研究,韦利出版了与该版本相对应的《补编》(1937),详细列出翻译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及诗歌中较难理解的字词。由《补编》可以看出,韦利参考了四家言论,受毛氏的影响最多。譬如,韦利参阅了《诗三家义集疏》、《诗毛氏传疏》、《毛诗异文笺》、《说文通训定声》等资料,并在注释中多次提及“Shuo wen”和“Mao”。翻译第125首(《毛诗序》第156首)诗歌时,韦利参照“Mao”的解释,认为“枚”即为“徾”,并参照“Shuo wen”将“徾”译为“secret going”(2)“”字不见于《说文》,根据参考文献等判断韦利或据清代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在翻译的过程中,韦利同样受到国外汉学家的影响。通过译本的《后记》可以看出,韦利评价最高、对其影响最多的汉学家是法国汉学家顾塞芬和葛兰言。
韦利1937年译本以文化译介为主,“经过深思熟虑后,韦利认为根据主题安排诗歌的顺序,其优势远大于原有顺序”[2](P18)。为了方便研究者查找资料,韦利在译本中以表格的形式将译本与源语文本的顺序相对照。此外,韦利还将一些诗歌改编成对话体,他认为有些诗歌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因此需要用引号加以标注。[2](P17)
1941年,由于燃烧弹引起的大火,1937年出版的《诗经》成为绝版。[3](P7)几年后,韦利决定重新修订《诗经》。1954年,原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诗经》的第二版。对照第一版和第二版可以发现,新版本没有较多、较大的修改,修改之处主要包括增添注释五处、修订句子三处、订正音译词两处。增添注释之处分别为第27首(《毛诗序》第100首)、第77首(《毛诗序》第43首)、第96首(《毛诗序》第67首)、第139首(《毛诗序》第263首)、第286首(《毛诗序》第206首)。在翻译第27首中的“东方未晞”时,韦利将其翻译为“The dew of night is not yet dry”,并增添注释“另外一种解释见1946年出版的《中国诗歌》,我至今仍然不能确定两者中哪种正确”。查阅1946年出版的《中国诗歌》,[4](P21)韦利将之翻译为“the cock has crowed”。在译介第286首诗歌时,韦利增添注释介绍这首诗的句式风格和第49首一致。在句子方面,韦利修订的三处分别为第20首(《毛诗序》第88首)、第261首(《毛诗序》第179首)、第184首(《毛诗序》第175首)。第20首将原文本“叔兮伯兮”由“Oh, sir, oh my lord”改译为“Oh uncles, young and old”。第184首,将原译文中的“springy”改译为“unstrung”。第261首,将“help us to fire the brushwood”改译为“help us to lift the game”。此外,韦利还指出第一版专有名词的翻译存在问题,忽略了一些不规则的发音。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新版本在处理这些发音时参考《哈佛燕京索引》,选择了较权威的发音方式。譬如,将第183首(《毛诗序》第161首)中的“sheng-pipes”改译为“reed-organ”,将第278首(《毛诗序》第131首)中的“An-hsi”改译为“Yen-hsi”。韦利指出新版本的修订参考了葛兰言1942年至1946年间出版的相关书籍中的翻译及注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权衡再三,我发现自己的观点与他的观点不一致,但是又不能确定他的观点是错误的”[3](P7)。
1987年美国纽约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重新出版1954年版本,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为新版本作序。宇文所安认为,时至今日,《诗经》对现代人仍有重要的影响。“儒家学者发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社会道德观念。二十世纪西方读者亚瑟·韦利发现了一种民间诗歌,证实了现代西方对古代社会的观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社会历史版本。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诗歌的每一种解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还保留着人性的最原始核心。”[5](Pxiii)宇文所安认为在《诗经》的翻译过程中,无论是一个单词、句子还是整首诗的翻译都充满了困难,“亚瑟·韦利既是一位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翻译家;在译作(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属于阐释)中,他尽最大努力,使这些诗歌恢复了周初时的清新。”[5](Pxxiv)
1996年格罗夫出版社出版了“亚瑟·韦利翻译,周文龙(Joseph R. Allen)编辑并补充翻译,宇文所安作序,周文龙作《后记》”的新版本。该版本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亚洲语文学系教授周文龙在韦利1954年版本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目前,该版本已经成为美国亚马逊在售《诗经》英译本中的主要译本之一,是美国《诗经》英译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重新整理韦利的译文时,周文龙坦言“我尽可能多地保留了他的注释和解释,必要时将它们重新改写以适应新的格式;删除不再适用的注释,代之以自己的阐释;保留韦利的诗节,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更改他的翻译”。[6](Pvvvi)此外,新版本增加了:一张周代封国地图,一个人物表(文本中出现的重要传奇人物和历史人物),一篇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刊后语,以及精选的参考书目。刊后语中,周文龙总结和整合了学者们对《诗经》的研究,从“起源:从歌到诗歌”“文本从何而来?”“走进孔子”“传统训诂”“新儒学修订”“考证与《诗经》”“《大序》的诗学”七个方面概述了《诗经》的文学史,包括文本的起源、诠释学传统和诗学。
与1954年版本相比,1996年版本具有以下特点:1.不再将诗歌分为17类,而是按照《诗经》原有的顺序排序;2.补全韦利译本中舍弃的15首诗。翻译这15首诗时,周文龙同样参考了葛兰言1942年至1946年出版的相关书籍,并在用词、语气、风格方面尽量与韦利保持一致;3.为每一首诗添加题目。中文标题通常取自诗歌的开头几行,在创作英文标题时,周文龙参考了韦利的译文(少数例外);4.所有的中文名字和术语都使用了国际标准的拼音。为了便利不熟悉中文的读者阅读,除常见地名外,译者在音节间使用了连字符。该译本提供的资料,既适用于希望了解更多有关《诗经》历史信息的普通读者,对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也是绝佳的参考资料。
韦利的《诗经》英译本经历几次重印和版本变迁,其中,1937年译本为公开发行的首译本;1954年译本是基于1937年译本的细微变动;1987年译本是在1954年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序言;1996年译本则为美国学者周文龙在1954年版本基础上的编辑与补充。只有1937年译本没有其他译者或学者的参与,最能体现韦利《诗经》英译本的原貌。文章将以1937年版本为例,分析韦利译本对诗歌语言的深度探索,以及韦利在翻译过程中对“经学解经”观点的接受度。
二、韦利译诗的语言考证
爱德华兹认为韦利《诗经》英译本最独特的两个特点为:文学价值与语言的准确性。[7](P1063)语言在文化探索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只局限于宗教文化、农业文化、民俗文化等狭义的文化范围,忽略了语言研究在韦利《诗经》英译研究中的重要性。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华语译文研究馆(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rchive)馆藏的《补编》(TheBookofSongs:SupplementContainingTextualNotes)是探究韦利《诗经》译本语言特色的重要资料。《补编》是与韦利1937年《诗经》英译本同步出版的补充资料,在此之前,鲜有学者对此引起重视。翻阅《补编》发现,韦利将全部篇幅用于探究汉字的本源,解释汉字的演变,对专业读者有很大的帮助。在英译过程中,韦利对诗歌中字词的考究非常深入,对译文的选词也极为严格。韦利始终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提倡查阅古典文献、参阅第一手资料,认为即使在参考《说文解字》时,也应该使用早期版本,避免因版本删减而造成意义的遗漏。这种追根溯源的字词考究精神,保证了译文语言的准确性。
在韦利看来,欧洲学习中文的学生们的主要缺点在于“只阅读古文献的现代标准版本,或参照经现代文字体系完善的版本,没有意识到古汉语中的一个字会有多种不同的书写方式,这些书写方式完全不同于《康熙字典》中的书写方式”。[8](P3)此外,韦利还在《补编》的《引言》中明确指出没有一本参考资料可以像毛氏的资料一样,保留着如此多的古代用法[8](P4)。
韦利认为《诗经》中的字词之所以难于翻译,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字词的含义发生了改变,以至于“搜集记录诗歌的官员可能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记录的是什么”[8](P15)。《诗经》中的许多汉字都有多种正确的书写方式,随着文字改革以及文字标准化的推进,即使在《说文解字》中也很难查找到文字的变化轨迹。参阅《毛诗序》中的记载,韦利将古汉语的特征总结为两种:省略不发音的部分;同音异义词的使用。因此,在阅读中国古代文献时,韦利提出应该通过读音来判定字的含义,而不是通过字形。[8](P6)譬如,“養(养)”与“恙”。韦利认为第44首(《毛诗序》第61首)中的“養養”不是“抚养”的意思,而是“恙”,“忧伤、伤心”的意思。[8](P6)此外,韦利还探究了中国古代汉字偏旁的变化过程,指出“说”为“悦”的古代表达。[8](P6)
在译介《诗经》的过程中,韦利不仅参考了汉代评论家的观点,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挖掘。在1937年译本的附录中,韦利详细探讨了“德”与“万”的翻译。韦利认为“德”是《诗经》中重要且难于把握的概念,因为“德”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美德(virtue)”,而是有好、坏之分。[2](P346)特雷格尔(Tregear)在其撰写的词典《毛利语—波利尼西亚语比较字典》中,将“德”定义为“魔力、威信、影响力”。[2](P346)参考该解释,韦利将“德”翻译为“Power”、“inner power”、“virtue”。在解释“万”的涵义时,韦利梳理出历来对“万舞”的五种不同解释,又分别指出五种解释的不合理性,并提出将“万舞”音译为“Wan dance”。爱德华兹认为要想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就要必须保证词语的一致性、不生硬;要有能力探索词语的含义,尽管有些词语的含义早已不再清晰;此外,还要能够发现汉字之间的互换与通假现象。[7](P1063)爱德华兹赞赏韦利的《诗经》英译本,因为该译本没有停留在批评已有译本的层面,而是能够在指出已有译本缺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诗经》英译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翻译感叹词时,韦利认为“译者要做的就是判定该词是否影响句子的理解”,[2](P14)“并删除‘式、亦、以、思、斯’等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8](P9)。韦利提出在替换同音词之前,译者首先应该做的是将两者所代表的意象进行比较,试着探寻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任何其他的方法都会使学术陷入无根据猜想的深渊”[2](P15)。葛兰言对这种翻译方法提出异议,认为“……在汉语这样的语言中,如果我们可以随意地把一个汉字变成另一个具有相同读音的汉字(韦利偏爱这种方法),原文的意思就可能发生改变。替换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除非是必须,而且修改的内容显然是可信的,否则千万不要修改文本”。[9](P76)
在英译《诗经》的过程中,韦利从字词入手,逐根溯源,细致分析《诗经》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内涵,指出中国古代汉字在同音异义词、感叹词等方面的变化特点。词源的探索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步骤之一,韦利探源式的译介方式为后来的研究者与译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与译介模式。
三、韦利对“经学解经”的接受度
目前,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诗歌韵律等方面对韦利及其《诗经》英译本进行了深入探讨(李玉良 2007;陈惠 2011;张保红 2020;等),指出:从诗歌的编排结构来看,韦利根据主题将诗歌分为17类,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从译介的内容来看,韦利舍弃经学阐释,注重中国文化的挖掘,在《诗经》英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研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华语译文研究馆的馆藏资料发现,韦利对传统《诗经》研究中的“经学解经”持有辩证的观点,充分肯定了经学涵义的重要性。在译本的《前言》和《后记》中,韦利多次肯定顾塞芬(Couvreur)译本中经学解经的重要意义,指出顾塞芬法译本在其研读《诗经》的初期,对自己解读《诗经》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诗的过程中,韦利立足现实,认真区分传统习俗、神话传说、经学内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借助经学注释澄清史实、挖掘道德阐释中的事实,有效防止了过度的经学解经遮蔽诗意的本真,却又陷入中西文化过度对比的泥潭。
韦利1937年《诗经》英译本“吸收了古汉语研究的新进展,首次再现了290首诗歌的原意”。[2]其中,对韦利影响最深的当属葛兰言的汉学研究。翻阅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诗经》研究著作,可以发现,韦利对《诗经》中许多中国文化的阐释都受到葛兰言的影响,称赞葛兰言在《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中揭示的《诗经》本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P337)然而,葛兰言批评顾塞芬对经学家传统注释的笃信,指出“若要证明经学家道德教化式注释的不良后果,只需将我逐字翻译的版本与顾塞芬神父忠实于传统注释的译本对比即可”。[10](P532)与此相对,韦利充分肯定了顾塞芬译本的意义与价值,认为在已有的译本中,最佳翻译当属顾塞芬的法译本,该译本忠实地遵循了朱熹的评论,清晰地指出诗歌的寓意,“像这样的翻译直到今天也必不可少。因为,只有知道这些歌曲在过去是如何被寓意化的,否则你不仅无法理解后来文学作品中无数的典故,甚至连日常语言中仍在使用的表达(从对歌曲的道德解读中提取)也无法理解”[2](P337)。与此同时,韦利反对将各家观点混为一谈,批评理雅各译本“将朱熹的观点与汉代学者的观点混为一谈,并加入了译者自己的观点,其翻译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2](P337)。
韦利对“经学解经”持有辩证的观点,肯定经学涵义在理解《诗经》文化内涵时的重要性,认为“有些诗歌,从其表面涵义来理解,确实具有说教的涵义”[2](P336)。但是,韦利又指出,过度的经学阐释限制了《诗经》的阐释范围,因为“正如词语具有多种含义一样,社会实践也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2](P337)。譬如,在翻译婚姻诗与求爱诗的过程中,若只探求诗歌中的寓言涵义,则会阻碍诗歌内涵的探索,这些诗歌也只能用于道德指导,难以探求诗歌中蕴含的中国古代婚俗。[2](P336)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韦利以经学阐释为知识积淀,立足现实,从文本中提取事实、获取诗歌中的中国文化。
在译本中,韦利阐释中国文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一首诗歌的注释中谈论诗歌包含的文化习俗;另一种是在《前言》、《后记》或者某种主题的题解中,整体概述《诗经》中某一类文化习俗。譬如,《后记三》中,韦利概述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婚嫁习俗、继承习俗、祭祀习俗方面的体现。第二种阐释方式与葛兰言的汉学研究极为相似,都是立足文本,从字里行间探寻事实,并将这些事实串连起来,试图呈现一副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景图。
韦利指出,在研读《诗经》的入门阶段,顾塞芬译本中的“经学解经”观点对其理解《诗经》起到了重要作用。[2](P326)随着阅读量的增加,韦利对《诗经》的理解逐渐现代化,开始将“经学解经”观点作为理解诗歌的背景知识,着重探索诗歌中的文化内涵。譬如,在翻译祭祀诗《诗经·周颂·载见》时,韦利没有提及诗歌的祭祀对象周武王,而是以周代为背景,讲述了周代严密的宗法制度。在译本的《附录》中,韦利对“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中体现的“昭穆制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昭”即为古代的“昭穆制度”。“昭”指“明亮的”;“穆”指“安静的、庄严的”。[2](P333)因此,在译文中,韦利将之翻译为“Then they showed them to their shining ancestors/ Piously, making offering”。在“昭穆制度”中,始祖居中,左昭右穆,父子分属于“昭”与“穆”,不可属于同一“昭”或同一“穆”,以此来区分宗族内部的长幼次序和亲疏远近。父子属于不同的氏族,这是昭穆制度的根本意义。韦利指出,“昭穆制度”暗示了两个母系氏族之间交换婚姻的原始婚姻制度,同时也成为周代曾有过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见证。
在译介“宫廷诗”、“宫廷传奇诗”的过程中,韦利也指出了诗歌中蕴含的故事与传说。例如,在翻译《诗经·国风·鸱鸮》时,韦利解释到“该诗与成王和周公之间的传奇故事有关。……鹰象征邪恶、叛逆的叔叔们……”[2](P235)。韦利的解释与《毛诗序》相仿,“《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曰《鸱鸮》”。对比韦利与《毛诗序》的解释,可以发现,韦利没有对成王与周公之间的故事进行详细叙述,而是将重点放在解释诗歌中的意象。在最后,韦利还指出“这首诗歌的解释不够清楚,诗歌的创作可能另有其它用意,后来才被学者们用来阐释成王的传说”。[2](P236)由此可见,韦利将经学解经视为诗歌的背景知识,是理解诗歌内涵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翻译的过程中,韦利常常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类比,以寻找文化之间的相通性。但是在类比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类比的现象,过度强调相似性,造成对中国文化的曲解。在译文中,韦利将《诗经·大雅·绵》的第一句“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且土沮漆”,翻译为“The young gourds spread and spread. The people after they were first brought into being/ From the River Tu went to the Ch’i”。韦利认为在中国古代,葫芦常常会起到救生的作用,这与原始诺亚方舟的作用相同。因此,诗歌的第一句是在“暗示一种被遗忘的信念,暗示人类‘起源于葫芦种子’”。[2](P247)韦利还指出,北美洲和非洲也有“人类起源于种子”的传说,因此,可以证明人类文明的相通性。此外,韦利还在“宫廷传奇诗”中,将女子因奇迹而怀孕,生下英雄儿子的故事类比于《圣经》中撒拉的故事,以及许多有关国王和王后历尽艰辛、喜得贵子的民间故事。[2](P239)
在译介的过程中,韦利反对将诗歌的内容过度依附于经学研究,却没有完全放弃“经学解经”,而是在探索诗歌含义的过程中,以经学为背景,从现实出发揭示诗歌的文化内涵。译本中,韦利在译介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横向对比早期的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既有利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又不乏对中国文化的过度阐释与误解。尽管如此,韦利的译本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总 结
通过反复研读韦利翻译《诗经》过程中留存的第一手资料,文章爬梳出韦利《诗经》的多个版本,研究了每一种版本的特点;并以1937年版本为例,分析译本中的语言特色,探究韦利对“经学解经”的接受度。自韦利译本出版以来,几经改版,仍备受西方读者的青睐。检索美国知名图书分享网站Goodreads(3)Goodreads是一家图书分享型社交网站,注册用户可以在网站上推荐新书、推荐书单、进行图书评价。检索时间为2020年3月20日。,韦利《诗经》英译本的评分达3.96分(满分5分),69%的读者给出了四分以上的评分。读者们指出“韦利把这些诗译得栩栩如生”、“翻译是阅读它们最简单的方法。译本解释了当时的时代,谁是掌权者,以及人的重要性。还提供了关于诗歌如何通过隐喻、图像、文字相互联系的细节”。还有读者认为,韦利的译本“使现代读者能够读懂并享受《诗经》的乐趣。对于任何对中国历史、文化、诗歌或儒家思想感兴趣的人来说,韦利的《诗经》英译本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同样,美国亚马逊网站(4)美国亚马逊网站是美国做大的购物网站,也是美国最大的图书线上销售平台之一。检索时间为2020年3月20日。的读者也给出了好评,认为“这几乎是最好的《诗经》英译本”。韦利的《诗经》英译本在《诗经》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深入探究韦利的《诗经》英译本,对《诗经》翻译研究及经学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