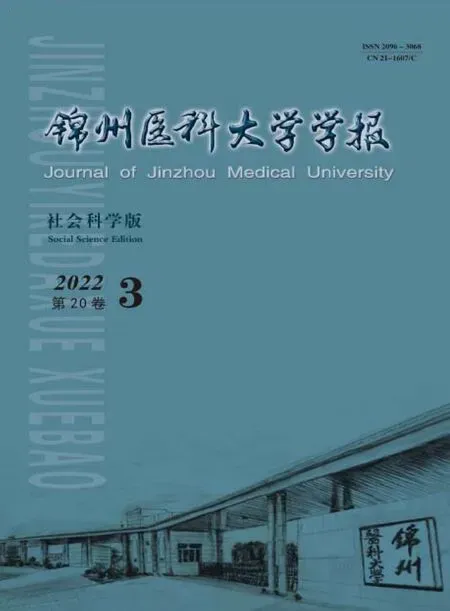关于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的历史考察和思考
刘依平
(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珠海 519041)
中医在中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自诞生至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宏大的医学传统,涌现出了很多重要的医家和著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中医的发展及其地位不仅关系到百姓身体健康,还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密切相关。但在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后果之一表现在中医方面,却是西医对中医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甚至在民国期间中医到了被政府下令打算废止的关头。虽然经过中医界的抗争,中医得以留存,后续通过设置国医馆、尝试使中医科学化来谋取其应有的地位,但其抗争逻辑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以西医为圭臬的社会意识以及既成的公共卫生制度。总括来说,近代社会对中西医学之优劣比较与民族社会之康健与否之间的认知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西学剧烈冲击和全面影响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的过程中,对中医本身以及怎样改造中医的看法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一、问题:为什么是中医?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历史悠久的中医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不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医在医界的重要性和大众的认可度无论如何也都是稳固而又持久的。然而,同样令人瞩目的是,近代以来中医的不利处境日益严峻,原本治病救人的中医,其社会地位已经沦落到自身成为被救治的对象,以致于其存废问题成为了近代中西医论争的核心问题。那么,中医在近代缘何就成为了问题呢?这与西医的东渐和发展密切相关。
明代后期,西方医学经由天主教士传入中国。按照熊月之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国人接受西医是有一个过程的,从疑忌、接触、试用到对比、信服共经历了五个纠缠交错的环节。[1]从该判断可以得出:面对西医在中华大地上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后世一些人物希望采取“断然手段”废止中医、取缔中医等吁求,自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期间势必也经历了一番过程。实际上,比如在清代宫廷中,西医与中医是“和睦相处”的,甚至还在药物、治疗等方面有过不少合作。[2]同时,早期也有一些中医学家、思想者持中西医汇通的观点并付诸实践。另外,在一些中西医对比尤其醒目的地域,比如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港英政府在鼠疫暴发时不得不应对中西医疗观差异所带来的管治危机。[3]但随着形势的风云变幻,近代中国总体上处于落后挨打的现状迫使先进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思考个中的缘由。
由于医学既与国民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又与传统历史和文化高度结合,因此受到瞩目。另一重要方面,西医在非西方国家的生长总是与帝国殖民扩张关系紧密。因此,在各种正、反合力之下,中医受到医界内外人士的共同关注和省思,甚至成为了思想交锋和行为决策的战场。言汇通者有之,言改造者有之,言废绝者亦有之。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世风慕西、政府“偏重外医”的情形之下,废止中医的诉求竟上升到了行政决策的高度。可见,在一些人物的心目中,作为负面对象的中医曾经到了必须被除之而后快的境地。
二、观点:质疑或否定中医的理由
延续几千年的中医是继续保存还是应该被废止的疑问之所以产生,除了与近代以来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之外,还必须考虑质疑或否定中医之主张者的思想和趣味。这部分人往往都是所谓的“名人”,即近代思想家和学者。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潮流,对知识界和政府的影响也最大。赵洪钧就曾专门在其著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再版序中大篇幅地介绍了吴汝纶、严复、梁启超等人对中西医问题的看法。[4]
据赵洪钧介绍,吴汝纶对待中西医问题是非常“言行一致”的,表现于吴氏不仅言语上极度贬低中医,而且还至死都不愿让中医来医治。在吴氏笔下,整体观之,中医为含混医术,西医则“理凿而法简捷”;在医治原理、依凭技术以及方剂药性等方面,吴氏对中医信奉的“阴阳五行之说”“用寸口脉候视五藏”及“本草药性”等均提出质疑。至于一些具体病症,吴氏在与亲友书信中表示,中医既无医治咳嗽这样的“小疾”之药,也不如西医知晓咳嗽与大病之间的关联;之于肺病,中医亦“不解,亦无征效之药”;其孙患眼病,也不宜服用中药,因为“中医不能深明药力之长短”,只是“以一药医百人”的“妄”术而已。由于吴氏的个人名望和社会地位,所以,晚清政府在1902 年和1903 年制定的教育制度中出现了废止中医的倾向。那么,吴汝纶为何如此贬中褒西,竟至于形成一种“偏执到了极点”的医药观呢?
有论者将吴氏的上述表现归因为两点:一是受到特定环境和人际因素的影响,二是源于其个人的文化素质条件。[5]更有论者提出,吴氏之所以一方面视桐城古文为文化瑰宝,另一方面却又拒斥传统中医,根源在于其“中体西用”的文化观。[6]
与吴汝纶相似,严复是深植于中国传统学养的佼佼者,也同样深受19 世纪末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状况的影响。相较于吴汝纶在对西学的皮毛之见基础上形成的中西医药观,严复作为“认真地、严格地、持久地把自己与近代西方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中国学者”[7],他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将医药与堪舆、星卜之学一同视为“中国九流之学”,且都“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可见,严复虽不主张“中体西用”,但如果从更科学的西学比如西医来看,中医属于“迷信”一端,会随着“学术”的扩展而消失,所以自然只能算作为“九流之学”。
放在今天来看,毋庸置疑的是,中、西医各具价值,且在不少方面相互不可替代。上述在对中医的抨击声浪中担纲的名人知识分子所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眼光,肯定不能作为医学史上的结论。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他们与中医相关的言行宣告了中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衰落。同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功能方面,中西医在这些名人心目中的等级和次序,以及他们看待中西医固定化的视角,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时人的价值偏好。
三、抗争:以1929 年“废止中医案”为例
在中医废存的争议史上,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废止中医案”可以说是“一场撼动全国的政治大地震”[8],也是国内中医界发起抗争的一次高潮。甚至,有各种资料显示,东南亚中医界都因此发起抗争以呼应国内情势。[9]说到底,该案引发的社会风潮实则是中医界寻求生存的一场深刻的自救行动。
如前所述,清末主张废医论者不多,相反有不少开明人士主张中西汇通。以中医学家张锡纯为例。张锡纯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其组方用药也体现出“衷中参西”的理念,敢于尝试,创立了不少中、西药的合方,比如石膏阿司匹林汤等。[10]这些人物对西医没有太多的疑虑,但也并非完全信赖西医,而且对中西医汇通的尝试不尽相同。然而在近代社会风潮中,这一流派未能成为主流,而是衰退、最终被取代。[11]经历过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之后,国内中医界的抗争拉开序幕,但中医的地位更趋低落。到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卫生体制看,中医医务者在有关政府机构中人数寥寥,而西医却随处可见。当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开会时,出席会议的代表没有中医的身影,尽数西医界人士。而此次会议的主题却攸关中医的生死存亡。
会上提出四个提案,全与废止中医有关。这几个提案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 《制定中医登记年限》 《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知名人士章太炎的学生、被称为近代以来“废禁中医”头号人物的余云岫提出。余氏曾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废止“汉医”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不久,余氏就发表了一本彻底批判中医原典《黄帝内经》的著作,从此声名大噪。在此次提案中,余氏提出,中医的废止关乎民众思想、国家卫生事业和民族进化、民生改善等国族大事。因为其他三个提案的内容实际上与余云岫的提案多有重复,所以,会议最后在余氏提案的基础上提出合并,拟定并通过了一个《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史称“废止中医案”。该案限定了中医的登记年限,提出禁止开办中医学校以及取缔通过报刊宣传中医等事项。汪精卫当时是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院长,他也持废止中医的意见,因此,该案得以在行政院通过。
自然,由于“废止中医案”的内容无疑是要将中医置于死地,因此,该案一出即引发轩然大波。以上海中医为代表,全国的中医界人士纷纷起来表示抗争,发起各种请愿、集会的活动。后经多方努力,部分得益于国民政府高层内部意见的分歧,蒋介石发表了支持中医的言论。最终,1929 年“废止中医案”宣告暂不执行。可见,在当时南京政权根基尚不稳固的情形下,将中医设定为官方规制和取缔的对象时,非但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还将全体中医界、传统医界秩序、文化保守势力塑造为共同敌人,并引发了意料之外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此后,中医的抗辩一直未能结束,争议仍在持续。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中医的存废问题总是无法从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大背景中单独抽离出来。但实际上,中医废存之争对各方而言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和用途,以致于每次争议的原始语境和含义在现实中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更为宏大的国族命题往往遮蔽了这一本应属于医学界的问题,“中医的废存之争最终变成了中国政治家们应对近代危机的一个突破口”[12]。而要想理解这幅争议的图景,就必须厘清个中的纠葛、氛围和目的,特别是如何理性对待争议中出现的各种上纲上线的论辩。
四、转型:从中医到“国医”
自1913 年北洋政府“漏列中医”事件后,中西医之间在称呼上逐渐做出日益明显的界分。中医被西医称为旧医,西医自称新医,中医则自称“国医”。相对于中医,“国医”是相对晚出的概念和词汇。有研究者指出,“国医”的概念与清末医界中的“国粹保存论”相关。[13]起初,医学是被视为中国传统学术而被包含在“国粹”之内的,但“国医”两字的连用当时还未出现。[14]
随着“五四运动”的展开,与国粹相结合的中医对西医的成见增多,“国医”一词崭露头角。关于“国医”的论述大概是在1920 年代中后期出现,特别是借由对孙中山这样的政治人物谈及中医与政治之关联的言论的阐发,中医基本上完成了向“国医”的身份转换。将中医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尊严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考量,因此构成为民国期间中医界至为重要的一个抗辩基调。
然而,中医的抗辩逻辑始终受制于西医及其已然形成的以西医为主导的相关医制。比如,中医的科学性问题,中医有无资格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医学”,中医如何获得与西医同等的地位,诸如此类。以《医界春秋》为例。该杂志社人称“中医界之喉舌”,在1927 年年中,拟参照国民革命成立一个“中医革命团”。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个革命团体,该社认为中医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下若要发生改进,也需要来一次“革命”不可。然而,除了提出组织架构、中医权利等方面的诉求之外,该社的“革命”话语体系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是:一方面试图通过排斥西医,谋求提高中医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整顿和改革中医学说的“必经”之路是必须“采西学”。[15]又以行业组织为例,虽然中医团体古已有之,但1929 年“废止中医案”之后,中医行业组织也开始仿照西医学术和职业团体,在各地成立了不少中医学会和中医公会。但这些医界团体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分化和对立,融合并未能成为主流。[16]
在中西、新旧之争的基础上,“国医”的出现颇具意涵。因为从中医到“国医”,名称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医本身的变革,更隐含了中医在特定时期的地位及其对所处社会背景的回应。到前述1929 年“废止中医案”而引发的社会风潮之时,中医的这种地位和回应可以说各自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因此,有必要检验“国医”这一称谓的产生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趣味,将其复原为特定的历史概念和医界潮流。概而观之,“国医”这个称呼及后来其他国学研究的兴起,都表明了以西医为代表的西学是如何刺激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医学等事业和领域,同时也更表明了西学是如何制约了它们的发展趋向。
在今天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应该没有人会去听信废止中医的言论。相反,中医在如今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下大放异彩,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未来中医的发展已成为国家规划的重要内容。但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中医不仅被认为在医理、医术、医制等方面存在问题,甚至其生存都受到质疑和挑战。部分趋新的精英人士公开的言和行,当时南京政府的行政手段,矛头都指向中医。1929 年“废止中医案”及其后中央国医馆的成立都清楚地表明“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17],中西医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就一目了然。可以说,历史的合力在近代中医发展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而要解释和理解中医的这番际遇,就必须联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之特殊状况。这些状况构成了中西医论争史和中医界求存思变的深刻背景。无论是对西医的信仰或盲从,还是对中医的质疑或偏见,都必须放在由国家、民族危机所造成的背景中来观察。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但其中一些问题仍可以继续深入探讨,比如疾病与社会治理、医疗史与政治史、疫病知识的生产和社会应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