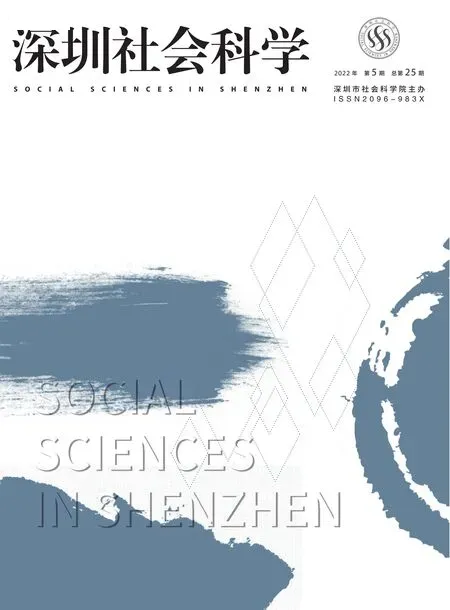列奥·施特劳斯隐微学说指谬*
朱海坤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1930年初,在《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出版前夕,列奥·施特劳斯在给克吕格的信中坦言自己“不可能相信上帝”,因为对理智的诚实要求他“必须弄明白‘为什么’”。[1](P8)在此前的斯宾诺莎研究中,他已然否定了理性战胜启示的现代神话,但在此时,他本人却面临着理性与启示的冲突。这种矛盾心理的一面是对自身民族宗教传统的传承意识,另一面则是理性探究的哲学使命。为此,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古世界,打算从迈蒙尼德那里找到化解冲突的方法。然而,迈蒙尼德让哲学向神学低头的妥协并未彻底获得施特劳斯的信赖。不久之后,来自伊斯兰哲学家阿尔法拉比的启迪使他彻底摆脱了疑虑——哲学家的独特写作方式保持理性与启示各守畛域、互不侵犯。
施特劳斯将隐微写作看作是从古希腊延续到中世纪伊斯兰-犹太哲学的历史事实,隐微写作与古典哲学息息相关,正是古典哲学与政治或宗教信仰的矛盾性催生了隐微写作的技艺,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的二重性化解了古典哲学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施特劳斯对隐微写作的阐释离不开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结构。
一、哲学的处境与隐微写作的必要性
在一篇为自己的隐微学说作辩护的文章中,施特劳斯开宗明义地提出了需要隐微写作的理由:
在研究某些早期思想家时,我渐渐意识到理解追求真理(哲学或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方式:哲学或科学,作为人的最高级活动,试图用关于“万物”的知识取代关于“万物”的意见;但意见是社会的基本要素;因此,哲学或科学的努力就会瓦解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于是便危及到了社会。所以,哲学或科学必须保持在极少数人手中,哲人或科学家们必须尊重社会所依赖的种种意见。尊重意见完全不同于把那些意见当作对的而加以接受。那些在哲学或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持上述观点的哲人或科学家,就被迫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使他们能够把自己视为真理的东西透露给少数人,而又不危及多数人对社会所依赖的各种意见所承担的绝对义务。这些哲人或科学家将区分作为真实教诲的隐微教诲与有益于社会的显白教诲;显白教诲意味着每个读者均能轻松地理解,而隐微教诲只透露给那些小心谨慎且训练有素的读者。[2](P215-216)
施特劳斯将哲学与社会的永恒矛盾视为两类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哲学(或科学)是一种致力于探索真理的思辨生活,只属于拥有完美理智的少数哲学家;社会则是建立在习俗或道德观念基础上的政治生活,属于绝大多数缺乏理智思考能力的庸众。施特劳斯以《理想国》中的“洞穴之喻”来证明哲学家与众人的区别:只有少数哲学家能够走出洞穴,生活在真理的阳光之下,大多数人必然困居于洞穴,生活在阴影的幻象之中,以虚假的意见为真实的知识。由于缺乏理智,即便哲学家重返洞穴去试图唤醒普通大众,将他们带出洞穴,他们也无动于衷。更有甚者,他们敌视带来真理的哲学家,威胁他们的生命。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仅难以化解,甚至是致命的。
苏格拉底之死是对这一冲突的严峻性和悲剧性的最好证明。在施特劳斯看来,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将古典哲学从自然哲学引向了政治哲学。哲学从原始部族的习俗主义中萌生是以自然代替祖制成为好的标准。最初的哲学以对自然的探求为本职,这种自然哲学对人类事物漠不关心。苏格拉底是第一个着眼于探究人间事物本性的哲学家,因而是政治哲学的创立者。苏格拉底以对政治事物本性的追问,如什么是虔敬、什么是正义等,不断地拷问和否定人们关于这类问题的习俗成见,致力于以对各种错误意见的不断否定逼近真理。苏格拉底对真理的探究是在雅典城邦中进行的,是在与城邦公民的交谈中展开的。他的质疑与拷问不断挑战城邦公民长期固守的意见,甚至危及现存的政治秩序。最终,苏格拉底遭到了城邦的审判,他背负了败坏青年和不信城邦的神这两项罪名,并遭罹厄运。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选择赴死,体现了他坚持真理和抵制虚假知识的哲学品格。他的悲剧命运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哲学家应当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根据苏格拉底的著名格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3](P76)哲学家从本性上不会放弃对真理的爱欲,而求知却面临着性命之虞。这个问题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苏格拉底之死向柏拉图昭示了哲学活动所面临的危险处境,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追求真理必然要否定政治生活赖以为基的共同意见,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秩序的紊乱、道德观念的沦丧和公共利益的损害,而作为这一恶果的始作俑者,哲学家必将受到大众的敌视甚至伤害。如果说,苏格拉底从探究对象上定义了“政治哲学”,那么柏拉图则是在言说方式上规范了“政治哲学”。这意味着正视哲学的政治处境,以社会或大众能够允许或接受的方式来从事哲学。这就意味着,在进行哲学探究和哲学教育时,哲学家必须具备审慎的品格。
所谓“审慎”,绝不是要限制哲学思考的自由,让哲学回避对某些敏感问题的探究,而是要保持言辞上的克制,在大众面前隐藏具有颠覆性的哲理,在必要的时候要将普通民众引向对城邦共同体有益的意见上去。审慎的哲学家要具备两种不同的教诲:一种是真实的哲学教诲,只能传授给少数哲学家或潜在哲学家;一种是为大众准备的富有教益的政治教诲。这双重教诲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施:口传和书写。口传的便宜之处在于,哲学家能够根据对象的不同天性自由选择教育内容,对同行或潜在哲学家传授哲学教诲,向普通人或不具备哲学禀赋的人传授政治教诲,不便之处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有碍传播的广度。与此相反,书写的优势在于不受时空的限制,哲学家的真实教诲能够对未来哲学家产生影响,但一个既定文本是向所有读者开放的,无法针对具体对象选择教育内容。哲学家由此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技艺,他们运用“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在同一文本中表达两种教诲,其中,哲学教诲是隐藏在文本深处的,既要瞒得过群氓的眼睛,又要给哲学同行们留下路标,政治教诲则是浮露在文本的表层,属于显白教诲,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它是一种公开的面向自己人的隐秘交流,“通过自己的著作对少数人说话,同时又对绝大多数读者三缄其口”。[4](P19)
古希腊哲学家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在中古伊斯兰-犹太世界变得更加严峻。在中古时期,信仰成为唯一正当的生活方式,上帝是一切真理和价值观念的根源,启示的权威更为强势,律法的规范更为严格。这种带有教条主义性质的信仰形式使哲学以及作为其方法的思辨理性显得十分可疑,“在伊斯兰世界里,‘哲学’和‘哲人’开始意指一种可疑的活动和一群可疑的人,甚至干脆意指无信仰和无信仰的人”。[4](P12)古希腊政治哲学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是由习俗所形成的共同意见,而中古伊斯兰-犹太哲学的现实处境则是超验的神学及其统摄下的宗教意识形态。哲学家触犯神法的后果可想而知。因此,中世纪哲学家必须谋求哲学活动在宗教社会里的正当性。施特劳斯通过迈蒙尼德展示了证明哲学正当性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让哲学向神学低头,利用哲学认识和荣耀上帝。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使哲学成为证明上帝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辨自由。第二种方法是,在表达方式上做文章,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在表面上是为律法的主要根基提供辩护,却在暗中认可了哲学的智慧。
施特劳斯区分了中世纪两大哲学传统——基督教经院哲学和犹太-伊斯兰哲学之间的根本差异。总的来说,这一根本差异体现在基督教经院哲学强调神学与哲学的糅合,或者说,神学收编了哲学,哲学成为神学的支撑,而犹太-伊斯兰哲学家则保持了神学与哲学的本性上的矛盾,使两者处于微妙的平衡之中,并把这种平衡状态看作西方文明发展的密钥。在启示与理性之间存在必要的张力,施特劳斯坚持“离则双美,合则两伤”的看法,认为无论宗教驯服哲学还是哲学压制宗教都会导致西方文明的危机。依他之见,神学与哲学的对立,亦即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对于西方文明的生存来说具有根本性意义。它们是试图对整全作出终极描述的两种基本方式。对于人类的生活而言,人的理智与神的启示,谁更具有指导能力,这是一个难以遽然做出决断的问题。从整个西方哲学史来看,无论是以神学压制哲学,还是让哲学消灭神学,都不是恰当的解决办法,保持二者的张力才是西方文明焕发生机的动力之源。作为维持双方的张力与平衡的基本手段,隐微写作担负着文明兴衰的使命。
二、人性、诗艺与隐微写作的充分性
以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传达双重教诲须以一个基本预设为前提,即“人类被严格地分成有灵感、聪明的少数人和没有灵感、愚蠢的多数人”。[4](P52)这一前提使施特劳斯遭到现代学者的广泛批判。加拿大学者莎迪亚·德鲁里将他视为自由和民主的死敌,认为隐微写作“关乎哲学家的秘密王权”。[5](P103)施特劳斯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上述论断所隐含的危险,他至少两次反思在聪明与愚蠢之间是否存在“一条延续的道路”或“过渡群体”,但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在《显白的教诲》一文中,施特劳斯否定了施莱尔马赫针对柏拉图的教诲是否隐秘所作的如下假设,即在极粗心和极细心的读者之间存在一条延续的道路,并断言这二者的差别“不在程度上,而在类别上”。[6](P120)此后,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一文中,施特劳斯再次断言“智者”与“俗众”之间有一道鸿沟,“这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根本事实,不管大众教育取得怎样的进展,都不会对它有丝毫影响:哲学或科学根本上是‘少数人’的特权。”[4](P28)他执意将哲学家与常人的差异视为人性的基本事实,并且认为人与人之间天生的不平等不仅不会消弭,反倒会“通过不同的教育或习惯以及城邦的不同部分所享有的不同生活方式而得以强化和深化”。[7](P41)这样的论断固然为隐微写作的产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基础,但同时埋下了荒谬的种子。倘若隐微写作果真基于人性的天然差异,那么隐微写作在近代哲学中的骤然消失就变得匪夷所思,为什么现代哲学家普遍地把这个古老而重要的传统抛之脑后了?难道哲学家与常人的天性差异会在经历了一场启蒙运动之后就被消弭?另外,隐微写作的目的是引导潜在哲学家远离俗见、追寻真理,若哲学家天性如此,隐微写作岂不是多此一举?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并非所有人都乐于将生命投入于对真理的追求,大多数人的生活都需要道德、法律或宗教的外在约束。但是,在这两类人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应该加以审问的。对智慧与愚蠢的绝对区分是一种虚假的二元论,把它作为隐微写作得以成立的根本支撑,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证明哲学家及其职责的特殊性,施特劳斯提出了德性问题。在众多的德性范畴中,哲学家独具智慧与审慎。而在城邦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虔敬、勇敢、节制、正义等道德规范实际上却遭到了他们的否定。因为对神祇的虔诚、对敌人的杀戮、对欲望的克制或对法律的服从,在智慧的审视下都是谬误和愚蠢的,从理性的眼光来看都显露出意见的本色。哲学家的智慧以真理为目标,体现为思想的癫狂,其审慎是对言辞的节制,是对真理教育的现实境况的警惕。在施特劳斯看来,智慧与审慎是互为表里的统一体,真正的智慧必然表现为言语上的节制。施特劳斯认为“是否懂得区分对外与对内的教诲是哲人的标志”,[8](P255)智慧与审慎的结合保证了哲学交流的隐秘性。施特劳斯说:“使这种著述(指隐微写作)成为可能的那个事实可用一个公理来表示:没有思想的人都是粗心的读者,有思想的人才是细心的读者。”[4](P19)这一论断颇有点铤而走险的意味。在有思想与细心之间是否存在排他性的对应关系?不可否认,一个有思想的人理应具有缜密的思维能力,但倘若认为所有细心的读者都在哲学的意义上是有思想的,尤其是在涉及写作问题时,则未免过于武断。中外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文字或修辞的敏锐与思想的缜密深刻之间不能轻易地划等号。就隐微写作来看,作者隐藏自己的真实思想要借助一定的修辞手段,或制造某种文本的反常特征,这些修辞或反常对于一个谙熟诗艺的诗人来说,本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①关于隐微写作的诗艺特征,可参见朱海坤.隐微写作的文本艺术结构与功能论析——以列奥·施特劳斯的经典阐释为中心[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 101-108.诗人虽不具备哲学的智慧,却拥有高超的文学技艺。诗人使他们的隐微术面临被识破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哲学家构想的理想国容不得自主的诗人。“自主的诗人受自己的爱欲操控,在诗的主题和表现方式上与哲学城邦的目标大异其趣。为了建立哲学家理想中的城邦政治,诗必须臣服于哲学,受哲学家支配。哲学家要求阉割自主的诗,使之降格为附属的诗,变成哲学的言说方式。”[9]在《城邦与人》中,施特劳斯提出,真正的哲学家绝不会与一个诗人成为真正的朋友,尽管哲学家需要诗人那般高超的诗艺,但他宁愿与色拉叙马霍斯结盟,也不愿让一个诗人留在正义的理想国中。然而,诗人与语言具有天然的亲缘性,无论是柏拉图还是施特劳斯,都不能真正把诗人驱逐出去。哲学家的“高贵的谎言”始终面临着被诗人拆穿的风险。
那些天资聪颖的读者是否会泄露哲学家的隐秘教诲呢?施特劳斯坚信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他的依据是苏格拉底的著名格言:德性即知识,“有思想的人本身就值得信赖”。[4](P19)这里的知识特指古典政治哲学所追求的关于整全的知识,凡以此类知识为目标的人都是哲学家,他们与城邦或政治共同体之间存在必然冲突,因而不会行此不义之举。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知识与美德,尤其是忠诚、值得信赖一类的美德相等同,是否符合苏格拉底的本意?从《美诺篇》中苏格拉底与美诺关于美德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拒绝以某一种或几种具体德性作为讨论对象,而执著于从本质上定义美德。在不断追问什么是美德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引导美诺认识到须以区别善恶作为美德的标准。下面的这句话是“美德即知识,恶即无知”的直接来源:“那些不知道什么是恶的人并不想得到恶,而是想得到他们认为是善的事物,尽管它们实际上是恶的。”[10](P501-502)人人都向往善的事物,但时常在什么是善的或恶的问题上缺乏正确的理解,因此,获得关于事物本性的知识,是追求美德的前提。在古希腊语中,德性(arete)一词的本义是指“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性”,[11](P75)苏格拉底这句格言的真实含义应当是,以认识人的本性作为知识的目标。这与德尔斐神庙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相契合,苏格拉底以之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这与施特劳斯的理解相去甚远。
在一个文本中包含显白的与隐秘的双重教诲,且让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读者对象,这就要求作者在遣词造句上达到炉火纯青般的功力。他不仅能够施展修辞技艺使双重教诲安排得恰到好处,而且要保证哲学家能够从中读出潜藏的微言大义,还得保证不向常人泄露半点机密。施特劳斯断言,哲学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精心而周密的,其文本中的一切特征都是作者意图的表现。即便隐微作者在写作时要达到表意的完美精当并不是没有可能,那么他又如何能够控制或保证双重教诲泾渭分明地传递给不同读者群体呢?施特劳斯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隐微写作向大众隐瞒真理的奥秘。哲学家利用大众的惯性认知行为,反其道而行之,向他们展示某种行为习惯,使之形成刻板印象,如此一来,当哲学家偶尔以异于往常的方式行事时,就能瞒过他们的眼睛。施特劳斯借助阿尔法拉比关于虔诚修道者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一个虔诚信奉上帝的修道者,为了禁欲和谦卑放弃了尘世生活,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他以正直笃实、得体合宜、苦行修持且虔心敬神而闻名于世,却遭到了城邦统治者的仇视。暴虐的统治者下令拘捕他,为了防止他逃跑,还命令所有城门严加盘查。这位修道者出于恐惧,想办法逃出城区,于是找来一套常服,换下自己的僧袍,穿在身上。然后手里拿着铙钹,装出一副醉醺醺的模样,边走边唱,在夜幕时分来到城门前。面对守门人的盘问,他以嘲弄的语调说自己就是他们要找的修道者。守门人却认为他在开玩笑,就让他出城去了。作为诚实正直而行事得体的僧人,他以醉酒和滑稽的方式骗过了守门人。或者说,正是对僧人的习惯性看法误导了守门人,使他们忽略了在特殊情境下的特殊行事方式。公众在面对反常或特殊的话语时,总是对之加以合理化的阐释,使反常现象得到符合其既有认知的阐释。这就为作者在写作时设置矛盾或反常现象留下了余地,并为见识卓越者的洞幽烛微提供了空间。施特劳斯对大众阅读心理的分析符合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一个外部的刺激信息要引起反应,那么接收这一刺激信息的主体必须具备反应刺激的能力,亦即相应的心理图式。只有受到主体心理图式同化了的外界刺激才能引起反应,也就是被理解。庸众对文本的理解倾向于将接收到的信息纳入已有的认知图式,他们所能注意到的只是常规性的共同意见。与之相反,哲学家理解力的特别之处恰恰在于,面对非常态现象所做的不是忽略它或将之常规化,而是思考该现象背后所蕴藏的独特意义。然而,如果把这种反思和审问的能力视为一种先天能力,否认后天习得的可能性,无疑是武断的。
施特劳斯从书报审查制度的程序合法性角度提供了隐微写作得以成立的另一个充分条件。他指出,若是依照法律程序对某一哲学著作加以审查,审查官必须提供明晰的证据才能断定作者隐含地发表了异端思想。但是,此类证据常常带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含糊性特征,因为审查官从文本中发现的悖逆之处既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也可能是由于审查官杯弓蛇影式的多疑造成的。对于审查官而言,作者的有心之过或无心之失,像泥鳅一样狡猾,难以确当地把握,因而无法断定作者是否真的传达了异端思想。正如施特劳斯限定的那样,这个条件只有在迫害不超越法律程序时才有意义。但实际的情形是,凡有书报审查制度的地方,威权往往伙同法律采取疑似从有的处置方式,即便审查官不能证实著作中确有异端思想,若有可疑之处,作者也未必能够幸免。这样的事例在中外历史上都不鲜见。
综上所述,哲学家与常人的天性差异被认为是隐微写作得以成立的充分条件。但施特劳斯对二者的绝对区分也使隐微写作面临不少逻辑漏洞。隐微写作对修辞技艺的依赖激化了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矛盾,诗人及其技艺对哲学家的双重教诲的隐蔽性构成了挑战。隐微作者对聪明读者的德性信赖与哲学家对此类城邦美德的否定自相矛盾。对庸众阅读心理的分析和把握是隐微教诲取得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确保不能通过一定的哲学教育破除心理图式的封闭性。施特劳斯在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内,为隐微写作的可行性提供了有效的论证,但若要保证双重教诲的严密性滴水不漏,似乎有些难以自圆其说。
三、历史主义与隐微写作的消失
令施特劳斯感到遗憾的是,隐微写作的古典技艺被现代人遗忘了。他将莱辛看成这一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位继承者,“在他之后,显白论问题似乎完全被忽视了”。[6](P119)然而,隐微写作缘何被人遗忘?施特劳斯并未给予充分的解释。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作为20世纪的哲学家,施特劳斯何以在隐微写作消失一百五十余年后重新发现它的踪迹?这得益于伊斯兰哲学家阿尔法拉比的启示。阿尔法拉比在总结柏拉图关于城邦公民教育的思想时,将色拉叙马霍斯视为苏格拉底的必要补充。这是因为,苏格拉底“只具有对正义和美德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12](P51)缺乏必要的和适当的教育方法去培育青年人和大众的品格,而作为修辞术师的色拉叙马霍斯在这方面却拥有卓越的才能。因此,哲学家应当运用两种教育方法:对智识精英运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对青年和大众运用色拉叙马霍斯的方法。施特劳斯将阿尔法拉比的阐述重心从教育方法的调和与互补转移到哲学探究与政治社会的严峻冲突,并在此意义上把苏格拉底之道定性为对真理的执着以及对大众的虚假意见或错误生活方式毫不妥协,而色拉叙马霍斯则能够应承和安抚大众。这一阐释与阿尔法拉比从柏拉图那里继承的思想相去甚远。阿尔法拉比认为,面对完美的人和高尚的人在大多数人中间岌岌可危的处境,柏拉图的做法是“制定一套方案,让他们脱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见,去追求真理和高尚的生活方式”。[12](P52)在他看来,柏拉图并未主张哲学家与大众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向他们敞开哲学的大门,让他们进入真理的世界。施特劳斯将阿尔法拉比视为隐微写作在中世纪的传人以及自己的领路人,但阿尔法拉比对隐微主义所做的提示并不像施特劳斯揭示的那样明显和可靠。
上述疑难并非要否定隐微写作本身。在宗教和政治迫害的时代,以一种字里行间的方式表达某种异端思想,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有历史的根据。但是,施特劳斯将隐微写作作为古典政治哲学的言说和教诲形式,在逻辑上变得难以自圆其说。这在“被遗忘”的表述中现出端倪。施特劳斯将隐微写作当成哲学与社会的本质冲突的必然产物。而且,这一技艺的有效性以智者与俗众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为前提。其言下之意是,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不可化解,智者与俗众的区分也是永恒的。那么,隐微写作的消失或被遗忘就变得疑窦重重。反过来说,隐微写作被遗忘所拷问的正是施特劳斯的上述两个基本论断的正确性。因为“遗忘”正是“冲突”或“鸿沟”消解之后的结果。因此,施特劳斯把隐微写作的消失归咎于现代政治哲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现代政治哲学取代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要义在于,将哲学与社会的本质冲突反转为二者的和谐一致,“他们坚信能够、且必须直接把思想变成行动,并用行动来检验思想”。[13](P234)促成这一转变的,是历史意识的觉醒。施特劳斯说:“现代历史意识的兴起与隐微教诲传统的中断正好同时发生。”[4](P52)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具体关联在他的表述中含糊不清。
历史意识的觉醒对近代哲学的影响体现为两个方面:历史的哲学化和哲学的历史化,前者是将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内容,即历史哲学,后者是将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方法,即历史主义。作为方法的历史主义改变了政治哲学走向和思维方式,引起了施特劳斯的格外注意。批判历史主义是他的重要工作。历史主义的历史性预设强调知识的经验性和差异性,否定一切永恒的观念和整全的描述,与施特劳斯的哲学观互反。
首先,历史意识造就了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然人性论不同,现代哲学家强调历史对人性的生成作用。在剥离了上帝对人的宰制后,现代哲学需要重建人之为人的根基,霍布斯与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具有代表性。霍布斯把对暴死的恐惧或自我保全的欲望视为自然权利的真正开端,是人类一切道德法则和社会秩序的起点。其意义就在于,将历史意识融入了新的政治哲学之中。这是因为,由人的自我保全欲望为起点的社会秩序始终处于历史生成的过程中,它是由人类意志推动的,而非自然而然或一成不变的。其后,卢梭带着对自然的乡愁反思霍布斯与洛克的现代政治方案,纠正他们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错误观念,进而提出以“公共意志”作为公民社会的立法原则,作为公正或正义的基石。现代政治哲学接纳了历史范畴,解决了古典政治哲学所遭遇的哲学与社会的永恒冲突,但是,在实现社会生活层面上的有效运用的同时,政治哲学也失去了对本源性问题加以追问和探求的品质。施特劳斯说“发现自然乃是哲学的工作。”[14](P82)然而伴随着自然的遗失,双重教诲以及作为其必要方式的隐微写作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其次,历史主义将人类的一切思想都看作历史性的,是某一民族、某一地域或某一时代的独特产物,注重思想与历史的内在关联,历史是思想产生的源泉,而思想则是该历史事物的镜像或写照。施特劳斯将由思想与历史相统一的知识类型称为“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强调某一具体学科知识对社会与人生的实际效用,它将知识当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因而缺失了对社会意见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能力。现代哲学谋求思辨理性与历史经验的结合,借以实现对人生实践的具体指导,使原先的真理探求沦落为某种实践伦理的技术指导,哲学因而变成了意识形态。最为根本的问题是,知识社会学不再以自然作为求知的目标,丧失了独立探求真理的品质,不再具有颠覆政治的危险性。现代哲学摧毁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二重性张力结构,隐微主义失去了它赖以为继的根基。
其三,历史主义的方法在阐释学问题上肯定理解的历史性,而施特劳斯的隐微学说却要求超越阐释者的历史性,以实现“如其所是”的理解。这引起了学界对施特劳斯文本阐释程序合法性的广泛怀疑。①关于隐微主义的质疑,可参见朱海坤.论辩中的隐微主义[J].深圳社会科学, 2019(4): 125-133,159.从逻辑上看,历史主义挑战甚至否定了隐微写作的根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施特劳斯之所以回归古典世界,正是为了应对历史主义所引发的现代价值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隐微学说是施特劳斯为克服历史主义而构设的一套方案。历史主义与隐微学说的逻辑冲突呈现“二律背反”。这就意味着,历史主义与隐微学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是一个抉择问题,而不是逻辑问题。亚瑟·梅尔泽认为,施特劳斯的隐微主义是对整个现代历史主义范式的重要挑战,并取得了胜利。然而,他的论述是在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以承认施特劳斯的逻辑和立场为前提。[15]
换言之,施特劳斯的隐微学说在知识大众化和以自由平等为基本价值的时代若要赢得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无异于痴人说梦。自由社会在两个方面取消了隐微主义的合理性。首先,自由意味着否定人与人之间的高低之分,古典哲学对哲学家与非哲学家之天性差异的基本假定在18世纪以后不再受到认可,大众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均等的机会使每个人接受哲学教育,哲学不再只对少数人开放。更何况,哲学本身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后现代语境下的西方哲学注重差异性和个体性,不再以整全的知识为对象,因而也就没有拣选少数心性特异者的必要了。其次,自由社会意味着迫害的减少和消失,哲学家解除了被大众敌视或伤害的危险,充分自由的政治甚至鼓励他们的大胆写作与直言批评,因而不再需要以隐微的表达方式来自保了。
四、结语
隐微学说是列奥·施特劳斯重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脚手架。作为犹太裔的施特劳斯旨在维护希伯来文明的神学正统与希腊文明的哲学传统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对隐微写作传统的发掘和塑造,施特劳斯绘制了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谱系,找到了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张力共存的可能性,并声称为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危机找到了一条回归之路。然而,施特劳斯的隐微学说并不完全具备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借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来化解神学与哲学的本性冲突,在本质上是把哲学问题归结并混淆于伦理问题或诗学问题。这种做法无疑过分夸大了哲学家在思想、道德和修辞方面的能力。施特劳斯把哲学思辨视为少数哲学家的专属生活方式,具有超越社会历史生活的特点,认同隐微写作作为一种“高贵的谎言”对大众的愚弄。这种哲学观否定了哲学的真理追求和启蒙精神,不仅与现代哲学精神南辕北辙,也完全背离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待真理的谦逊态度。
施特劳斯之所以用隐微学说来重绘西方古典哲学的图谱,是为了反驳和超越西方现代哲学的历史主义倾向。他认为,隐微写作这种独特的哲学写作和传播方式有效地规避了思想的历史化问题。但是,现代哲学并不会因隐微写作的重新发现而改变其历史主义倾向。相反地,正是由于施特劳斯的隐微学说倡导的是一种“教外别传”式的宗派哲学,再加上施特劳斯身上消抹不掉的民族意识,它自身也就打上了历史主义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