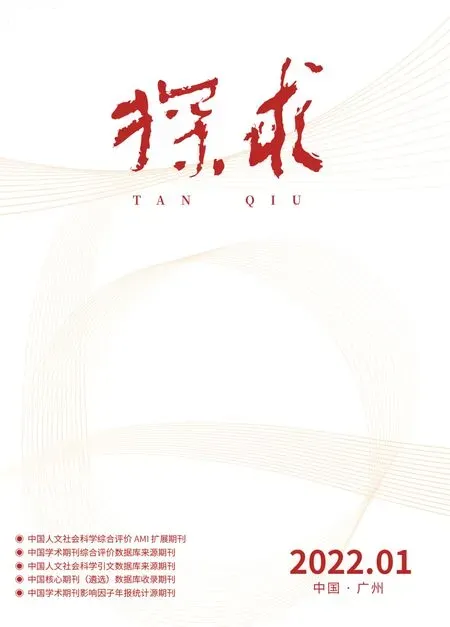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新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胡晓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同时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且同时提出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首次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并再次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这为我们深刻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指明了方向。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新生与人类文明形态的积极扬弃具有历史的逻辑统一性,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人类文明形态的价值指向具有理论的逻辑统一性,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追寻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合理探索具有实践的逻辑统一性。讲明二者在历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统一性,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代中华文化与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学术担当。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新生与人类文明形态的积极扬弃具有历史的逻辑统一性
在中国哲学史上,“新”有着特殊的意义,《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针对《大学》原本“亲民”“新民”之争,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应是“新民”,而王阳明则主张“亲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公案。[3]实际上,“亲民”更多指向君子圣人之治理去亲近百姓,而“新民”则有使民“自新”之意,而“自新”是“新”的真正涵义。“新”是“亲”与“斤”的形声字,“亲”的本义在指涉亲属亲戚的涵义前,亲身、亲自都是向内之义,而“斤”与斧斤劈木有关,“新”表达的是一种刀刃向内的状态,与时代新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积极扬弃与辩证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着深刻的致思关联。
文明就历史视域而言,可分为古典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就空间视域而言,可分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等;从社会形态发展而言,可分为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从生产的基本方式而言,可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马克思正是在对以往诸文明的深刻分析,尤其对资本主义文明方式及其内在要素的全面批判中,指出了人类文明的新方向,在思想上完成了文明自身的自我革新。而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的当代演进,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植根于中华文明,立足于中国实际,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资本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基础上创造的新的文明形态,是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迈向共产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4]。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本质规定性——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资本意味着“价值增值”,现代形而上学意味着资本的思想形态的“进步强制”,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研究指明这种文明的形态蕴含着瓦解自身的力量,必然在历史展开过程中表现出与自身的对立与矛盾,它必然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实现改弦更张,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方向,即共产主义文明[5]。共产主义文明是在超越工业文明基础上,向人类历史上优秀文明成果的更高程度的复归,是人向自身的复归。而中华文明的现代遭遇,首先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现代性的缓慢敞开并怀疑自身的价值,进而触动其限度、反思此“文明”,从而开始对自身传统价值的迷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现和社会革命论”,而“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6][P698]。新文化运动后,一大批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道路历史地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首先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辩证否定环节,与中华传统文化在缺少现代性却反思现代性的维度上,所指向的对现代性与自身传统的双重超越的逻辑一致性,二者必然表现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转型的辩证统一过程。
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新生与人类文明形态的积极扬弃具有历史的逻辑统一性。中华文明的新的转化需要自我革新,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吸收西方现代性的积极因素,实现时代新生;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的特质并没有被代替,它在吸收的同时进行择取反思,因之融合而成的更新的文明在实现中华文明自我新生的同时,实现人类文明的新生。它并不在历史时间的逻辑上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为席卷一切“旧文明”与“异文明”的借口,而是在应然的唯物史观真理逻辑上让所有文明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展示一种最为典型、更为合理的人类文明实现形式。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人类文明形态的价值指向具有理论的逻辑统一性
文明的本质是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诸关系的全面和谐。[7]新文明观是“五位一体”的总体的、全域的、多维的文明新形态。就物质性的超越而言,新文明观建立在物质生活的丰富基础上,却不以物质水平的丰富为唯一评价标准,从而对现代价值体系大厦的资本逻辑、商业逻辑、科层管理体制予以全面的反思和超越;就精神性的超越而言,新文明观并不以“启蒙”的姿态对“野蛮”民族进行文化和价值殖民。它具有普遍性和指向性,但并非强制的和征服的;就生态性的超越而言,新文明观并不与“自然”相对立,而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它指向一种基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属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整全的支撑体系,是在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否定的基础上对工业文明的辩证否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或新形式,是现代生产力与自然和谐理念二者的辩证统一。文明新形态是对何以为文明的反思,文明不应是历时性的、独占性的,而应是共时性的、普遍性的属人关怀。在西方式现代化模式所产生的知识分化下,新的文明形态扬弃知识的界限,而达到对人类智慧形态的整体性理解;在西方现代文明观价值所理解的价值冲突下,新的文明形态超越单一的智慧传统,整合各个文明的多元智慧来推进对存在的整全理解;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奠基的自然与人的对立下,新的文明形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吸收中华文化古典宇宙论与存在论的合理内核,在更高程度上指向人与自然的“两大和解”。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是人与自然的“两大和解”,也是双向生成,“自然向人的生成”与“人在对象化的过程中确认自身”是同一理论逻辑的两个方面,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对此人类文明形态的指引有着深刻的理论自觉,其说,“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其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矣。”[8][P163]“顺应”指传统农业文明人因应自然的生存形态,“改造”指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人对自然的征服形态,而“创造”则是共产主义文明将会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两大和解、双向生成,互相实现更高程度的“天人合一”。
而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的时代精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的深刻统一。在文明的进程中,由中国哲学所原理化表达的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与生命情怀,涵括了丰富差异的关联结构,包括人与天地万物、人与人、身与心的总体而齐全的和谐关系,这是一种对待而一体的交互性关系,而非严格的统一秩序,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智慧。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强调宇宙与人生的统一,人具有深沉的宇宙关怀,在通达天地万物的过程中开显自身,成就物我、人己、身心的统一;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又说“参赞天地之化育”,人既是宇宙演化过程的结果,又参与、提升、欣赏这种造化,是自然、道德与审美的人生在根源意义上的统一;强调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张载说“为万世开太平”,人作为历史和未来之维的当下联结,应尽到继往开来的责任,而责任是根源的、行动是内生的,便是感动与行动的统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文明”之思,它包括天下文明、光批四表的价值指向;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情怀担当;文明以止、光而不耀的辩证智慧;内质外美、文质相合的美质理想,这些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特质可以超越特定的民族与时代,成为各个文明共享的价值资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因而,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时[9],它一方面说明了生态与文明之间的根源联系,是将生态议题上升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作出的重要表述,另一方面又不仅指示生态文明这一个维度,而是包含了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五大领域的整体性说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文明的统筹布局,着眼于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是对单一维度发展追求的文明类型的超越,从根本上突破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框架内诸领域之间,进而影响到的人类心灵诸能力的整全性之间的对立、割裂、强制的逻辑。这是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同时是中华文化核心精神的时代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飞跃。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人类文明形态的价值指向具有理论的逻辑统一性。中华传统文化内源于“天人合一”的古典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真理性予以现代化一度的转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超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更高程度上指向的都是属人的应然存在——“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0][P185]这是二者理论内涵的高度统一。当今世界,面对现代性的问题,提倡交互伦理、关联社群、合作政治、共生和谐,而以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的整体性、关联性思维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正可以为借鉴,而这正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的核心要义。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追寻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合理探索具有实践的逻辑统一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游历欧洲一战的废墟后写下了《欧游心影录》,他主张以“中华传统文明为体,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以创造新文明”。[11][P349]张岱年先生曾提出,在21世纪,中国文化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主题,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大创新,创造大器晚成、现代复兴的中华文明新形态,以熔铸21世纪的新型世界文明。[12]实际上,近代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思索一直与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从而更为合理的现代性、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的反思相联系。
与古典时代相比,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演进情实表现出一种对另一种文明形态的认识、吸收、反思、与超越的过程。这里的“另一种文明形态”先是被理解为西方文明,其与东方尤其是华夏文明相对,而再被理解为“现代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相对。有学者将其中的思想史称为“中西之争”向“古今之争”的转变。[13]就其实质而论,中西之别,更多涉及认识思维之异,就哲学思想而言,则是两希文明尤其是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及其近代发展出的科学精神,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顶峰;而古今之争,更多指向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区别,而就哲学思想而言,其后是由历史观所开始的存在论、本体论、与伦理观的深刻变革。[14][P11-21]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实际是“文明”问题的两个方面,近代中国与西方碰撞的阵痛在哲学上来说,是两种文明类型的较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但是这个“公共”实际是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独家”,是以其工业文明的思想原则为唯一正确的依归,并在资本、权力、军事的保障下强加于一切文明与一切民族之上,于是那些“民族和地方的文学”虽然成为“世界文学”,但只是在形式上进入了现代世界,而在实质上却失去了自我。这一套话语体系与西方近代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相联系而获得了一种“世界性”与“合理性”,也曾一度席卷中国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心灵,引起极大的阵痛与迷茫。时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把西方的进化论系统介绍到中国来,就是认为只有实现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用“力今胜古”“日进无疆”的进化论思想,才能树立民族的自主、自立、自强之信心。这是救亡之悲;但是,另一方面,当学习的意识从“其用”转向“其体”,从而触碰到民族精神的核心问题时,他们也强烈感受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两副面孔”,[15]对以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资本运作及其后的“科学”思维的攻击性、异质性的困惑,对中华文明核心理念的“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的统一性与文明的包容性的一种“非怀古”的指向应然的反思,构成近代知识分子的核心关切。这是启蒙之思。这种启蒙之思是文明之思,不仅针对“落后”的中国向何处去,也是对“前进”的西方向何处去,从而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整全性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应然形态的具有系统化思考与实践性指向的哲学思想得以引进学界、征服人心、适合国情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华文明的新转型与人类文明的新的形态的一体性关联。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拓展,必将在更本质的层面上触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会通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是在文明的类型上的一种选择,它反思的正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世界”,[16][P276]是一种看似合理的文明类型。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就是指向文明类型在思想和实践上的更高程度的形态,从而在根本上扭转“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17][P300]以全人类获得普遍的最高的自由王国为根本信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者、创造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文明的新文明,一种不同于以往历史的新历史,它肇始并开启了一种新文明的实现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迈向共产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深刻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这一思想深刻反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梦想和追求,特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在有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的同时,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指明了道路,这就是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在中国新时代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18][P34]唯有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可以超越民族的更迭而指向新的历史,唯有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可以真正让现代性这一人类发展现阶段的定向特征具有属人的完整的一度,它从存在意义出发、立足人类命运、涵括自然万物、包容不同文明,以建立人与人、人与物、文明与文明共生、共在、共享的生命共同体为目的,在这里,所有人、所有物、所有文明都能够获得其生存发展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特定的民族精神保持它的本质特性,它的具体的特殊性并不会被溶解到抽象的普遍性之中,但会丰富普遍性的内涵,从而在保持自身特殊性的同时提升对普遍性的理解。
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追寻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合理探索具有实践的逻辑统一性。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是一个文明凝结成了一个国家,这是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不仅关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是呈现给诸后发国家的价值理念,国家指向的是精神而非疆域、文明指向的是和谐而非冲突。因而共产主义文明的首先探索并最终实现又注定在中华文化的大地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以铁的必然性呈现出来。
《决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用中国人民命运的改变、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展示、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的锻造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转化与这五个方面紧密相关,关涉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精神,关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与开放性、时代性的统一,关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色与实质内涵,关涉共产党人的文化先进性,关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所具有的强大而持久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与新时代的主题相适应,中华传统文化的位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从近代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即应当被现代化超越的传统,到新时代被看作是继承发展并重塑现代性的文化资源,其意义正是在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实现自身传统的日新又新。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也唯有在寻回自身归家之路的过程中才会指引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如果说中华文明的精神必然具有并必定会引导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一度,这种内在固有属性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践中、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充分展开中,才能真正实现。也正因为时代任务深化带来的理解中国哲学的深度和角度的变化,作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事融贯的中华传统文化,必然加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辩证法,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融汇成为中国当代哲学史、中国当代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新阶段,并具有生生不息的开放性和发展性。
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转化根本指向的是人的更为合理、幸福的生存样态,它对外指向人与自然的共生,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共存,对内指向人性的真善美的统一和身心和谐的统一,具有历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统一性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植根于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以马克思基本原理为真理种子,面向、反思、吸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性要素,探索出一条新的文明的实现道路,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新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实现五千年中华文化的青春新生。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定向,是风华正茂的百年大党对千年沧桑的中华文明的新生再生,是新生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新形态提供的新的致思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