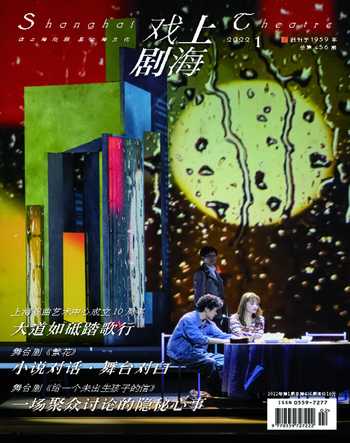戏曲年轻态需要创新
费泳
最近粤语戏曲电影《白蛇传·情》引起了影迷及业内同仁的高度关注,在电影院线上映也有不俗的表现。从《白蛇传·情》的观众观影人数、口碑等相关信息分析来看,都有让人倍感惊讶的现象,根据“猫眼”对《白蛇传·情》的用户画像,对该片感兴趣的观众中多达33.5%为20岁至24岁的年轻人,25岁至29岁的观众占了22.7%,两者相加有超过五成的《白蛇传·情》受众在30岁以下,这就更加令人刮目相看。这种现象的溢出效益已经超出了此影片的本身,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
戏曲电影能够吸引年轻观众,这绝对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戏曲艺术还是戏曲电影就一直在费尽心思地考虑如何吸引年轻观众走进戏曲剧场,因为这将决定着中国戏曲艺术的未来。那么今天戏曲电影《白蛇传·情》“突降”会是这一趋势的先兆吗?或者说会是一個发端吗?因为当前,对于中国戏曲艺术本身来说,的确是到了“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刻。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曾拍摄的京剧《白蛇传》在当时就非常引人注目,客观分析此片,较之当时的戏曲电影有了很大的不同和发展。一方面是电影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是80年代初中国电影观众还是有庞大的群众基础。因为经历过特殊年代,精神文化产品远没有今天这么丰富和发达。所以京剧《白蛇传》上映时,观影人数亦是空前的。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议论这部戏曲电影,尤其是电影中“惊变白蛇”“水漫金山”等特技段落的精彩处理按照当时国内电影技术条件来说,已经有一定的高度。
一晃4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把目光再聚焦到《白蛇传·情》,这部电影为什么会在当下院线电影票房竞争如此残酷的环境下杀出一条“血路”来,尤其是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呢?是情节吗?《白蛇传》是一个老故事了,中国百姓几乎妇孺皆知,显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是流量明星的加入助阵吗?非也!这部电影的主演全都是广东粤剧院的当家演员。那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这部戏曲电影注入了电影导演的“自觉意识”。正是这种自觉意识使这部戏曲电影区别于以前的戏曲电影。此戏曲电影与彼戏曲电影也产生了“基因突变”。这就如同电影在成为电影艺术之前,在它的幼年期只是一个记录者,当摄影机“运动起来了”,电影产生了自己的叙事语言,随之诞生了电影艺术。今天这部戏曲电影《白蛇传·情》有了电影导演自觉意识的注入与“觉悟”,或许是《白蛇传·情》成功的关键。或许我们这样比较会把这部戏曲电影的成功抬得过高,兴许是不恰当的,但是,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是由看似简单的小事情为引子。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电影技术高度发达,今天这部《白蛇传·情》里同样“水漫金山”“断桥”等画面的特技处理就更有视觉震撼力,是过去戏曲电影难以企及的。但是技术问题不是关键所在,这也不是我们今天探讨这部戏曲电影的主旨,笔者认为该片导演在创作这部戏曲电影的初始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成熟的故事、完整的戏曲舞台演出,就认为电影只是用来记录的,顶多放在实景里拍摄或者搭景拍摄,或者用简单的电影语汇来表现而已。恰恰相反,这部戏曲电影深深地注入了导演的自觉意识,尤其是电影导演的意识。例如对人物的解释,法海的定位、青蛇的定位,尤其是男女主人公对待爱情的态度,都做了一层新的解释和诠释,而且这种解释和诠释契合了当下年轻人对人、情、世、故的审美心理。在这个思维的推导下,导演又充分调动了电影的技术手段,对一些场景做出了电影化的处理,而不只是舞台化的处理。目前这部戏曲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结果,使得观众纷纷涌入影院探索其究竟,然后在观影审美心理上得到了一种满足的原因所在。这跟先前戏曲电影的观感审美心理是有所不同的。而观众的反应也很直接,观众认为此片音乐美、画面美、唱腔美,在观众的心里自然产生一种评价:原来粤剧戏曲电影可以如此浪漫,如此好听、如此好看又是如此柔情蜜意。
面对这种文化现状,戏曲界是喜还是忧呢?如果我们要去问广东粤剧院的艺术家们:面对这么多观众喜爱这部电影进而喜爱粤剧有何感想呢?他们的回答自然是喜上眉梢。令人感叹的是大量年轻观众涌入影院,他们热切地观看与讨论,这对于粤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自然是一件美事、乐事,但是粤剧会不会凭借这一部戏曲电影就此走上发展的康庄大道呢?似乎还不能这么乐观。
如果一部戏曲电影的成功能让戏曲艺术走出困境,那我们就太天真了。一部优秀的戏曲电影可以推广某个剧种,可以把部分年轻观众吸引到剧场,但是只靠戏曲电影就能把戏曲推上守正创新的坦途,这显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知道舞台艺术的魅力在于它的剧场性,而非电影化。剧场艺术是戏曲的出生证明,离开了剧场的观演关系,戏曲何谈发展呢?
前面讲的《白蛇传·情》是电影导演在戏曲艺术中注入了电影导演的自觉意识,或者说得再直接一点,是电影导演偶尔“跨界”戏曲电影,让戏曲艺术在这儿与电影艺术有了一次短暂的“亲密接触”,对戏曲艺术本身而言,得到的只是一种暂时的“欢娱”,而非马拉松般长久的“爱情”。那么我们戏曲艺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破圈”?笔者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就是戏曲艺术家自己才是戏曲艺术的“拯救者”。
今天的戏曲艺术依然面临这个世纪之问。十几年前,白先勇先生尝试着推出了青春版《牡丹亭》,获得了成功,遗憾的是白先勇一个人毕竟人单势孤,白先生年事已高,这种探索努力很可能日渐衰微。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从目前来看,中国戏曲界一直在倡导中国戏曲艺术要守正创新,广大戏曲艺术家们为此也付出了汗水,取得了成绩,但是就目前的结果来看,似乎还是守正多一些,创新方面是乏力的。笔者认为,我们的戏曲艺术要发展,必须要大胆革新,甚至有时候要刀刃向内。
首先戏曲院团要开门办剧院,要与外界——特别是要同文学艺术界等诸多领域广泛接触,要同文艺界的不同领域的学者、艺术家们广泛交朋友,取长补短,目的是要让剧团这潭深水活起来。
其次,当其他门类的艺术介入时,难免会触及到自身艺术的特性,甚至是要害处,戏曲人不要惧怕失败,不能因为一个剧目的失败而拒绝向其他艺术的借鉴,不要因为固守一些老传统而失掉一些新机会,传统文化不应全盘继承,我们要继承的是有活力的、带有我们民族优秀灿烂文明基因的文化种子,一句话,就是面对传统文化后人要扬弃旧的、陈腐的东西。
再次就是戏曲艺术要普及,要走出去,要发现新天地。我们的戏曲艺术无疑是伟大的,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我们要让戏曲艺术乘风破浪,势必要革新,不革新就会走向没落。这次《白蛇传·情》的热映充分证明了我们传统戏曲艺术的发扬光大大有可为,年轻观众是非常喜爱戏曲艺术的。
但是,我们如何让我们年轻观众打心底彻底爱上戏曲艺术,而非只是一时兴起呢?戏曲艺术的革新,如何才能够持久推动下去,而不停留在浅尝辄止呢?文化艺术界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应该持续地关注戏曲艺术、戏曲从业人员,不能单纯地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而是要关注生活、拥抱生活、放眼世界、拓展视野。只有这样,戏曲人才能真正扛起创新大旗。梅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止步于自己已取得的成就,而是博采众长,有跨时代意义的是他使我们的传统戏曲京剧艺术走出国门,将中国的国粹扬名于海外。这样的气魄和胆识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得益于他对戏曲艺术的守正创新的勇气。
这次《白蛇传·情》就是一次成功的电影导演跨界,我们是否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尤其是在当下,我们的年轻人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是自豪自信的,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敬意。这些审美心理的变化,都在告诉我们,本民族的东西就是最具时尚魅力的。就像笔者坐在影院里看《白蛇传·情》时,看到一对对年轻人三三两两相约而至,看到他们观前观后的喜悦神情时,由衷地感叹:只要我们持久地自信,持久地去创作,克服固步自封,坚持守正创新,中国的戏曲艺术一定会迎来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