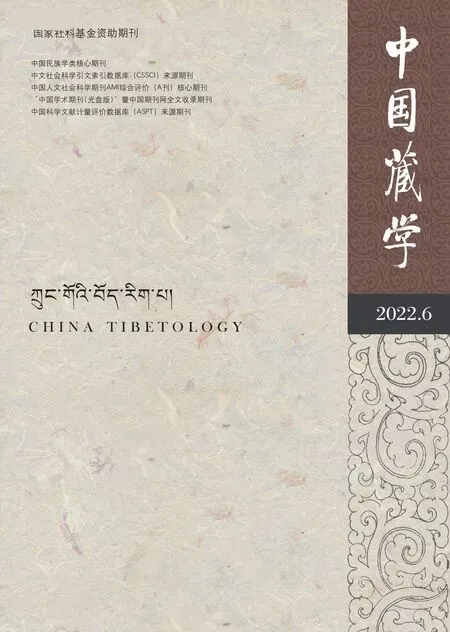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下新图像样式的出现
——青海玉树吐蕃佛教石刻再研究①
卢素文
川青藏交界地带已发现多处吐蕃时期佛教石刻,主要分布于今西藏自治区昌都芒康①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昌都芒康县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昌都旅游局:《西藏芒康嘎托镇新发现吐蕃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第233—251页。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査果西沟摩崖造像2009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第16—21页。张建林、席琳、夏格旺堆:《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和察雅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第7—14页。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昌都察雅县向康吐蕃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7—42页。、四川石渠③故宫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第27—70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第3—15页。和白玉④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等:《四川白玉县加瓦仁安石刻调查与研究》,待刊。、青海玉树。从现今公布的材料和相关研究来看,昌都、石渠、白玉以及玉树的石刻点,存在以毗卢遮那佛⑤毗卢遮那佛,藏文名称为 ,又可译为“大日如来”,关于其定名,目前未统一,毗卢遮那佛和大日如来皆在使用。考虑到汉译文献中一般称为毗卢遮那佛,因此,本文统一称为毗卢遮那佛。相关图像为主的共性,但又存在其他不同的图像类型,从各个地点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存在与其周边的文化交流融合的现象。昌都察雅和芒康的图像基本与毗卢遮那佛相关,石渠和白玉则出现了《恶趣经》相关题材,玉树的石刻出现了佛传、十方佛等题材。
目前在玉树发现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共5处,基本位于勒巴沟和贝纳沟内,分别为古秀泽玛石刻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古秀泽玛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第63—94页。、恰冈石刻⑦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省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藏学学刊》 (第16辑),第148—163页。艾米·海勒:《公元8—10世纪东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国外藏学研究译文》 (第十五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9—206页。、吾娜桑嘎石刻⑧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省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第95—146页。和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石刻⑨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第1—68页。及其西侧崖壁石刻[10]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摩崖石刻及线刻佛塔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第69—101页。。其中恰冈石刻题材为毗卢遮那佛与二菩萨,大日如来佛堂内石刻为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皆与毗卢遮那佛有关。当前学界对于吐蕃时期的毗卢遮那佛图像研究成果颇丰[11]主 要有以下研究: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第123—141页;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第353—384页;席琳:《吐蕃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组合图像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第41—48页;张长虹:《藏东地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图像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20页等。。另外3处石刻点的图像不同于常见的毗卢遮那佛相关题材,如古秀泽玛石刻的两组图像,一组为初转法轮图,一组为礼佛图,皆与释迦牟尼佛有关,在已发表的简报中探讨了礼佛图中的释迦牟尼佛可能与菩提瑞像有关[1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古秀泽玛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第63—94页。,菩提瑞像在唐代的敦煌、四川等皆有出现。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的石刻题材为十方佛和《普贤行愿王经》,勒巴沟内的吾娜桑嘎石刻题材为佛传故事与《无量寿经》《心经》等。对于这两处石刻,除了已发布的简报《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和《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摩崖石刻及线刻佛塔调查简报》之外,研究相对薄弱。
本文在已有简报的研究基础上,对吾娜桑嘎石刻和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的图像和经文作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两处图像是将吐蕃本土的毗卢遮那信仰和汉地华严、法华信仰结合而创作出的新的图像样式,表现了唐朝汉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一、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毗卢遮那佛+二弟子+十方佛+《普贤行愿品》”
该图像位于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的一整块崖壁上,同刻十方佛与《普贤行愿品》,上方为十方佛,下方为《普贤行愿品》(图一),该处的《普贤行愿品》早在《贤者喜宴》中就有记载①巴俄·祖拉成瓦:《贤者喜宴》(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447—448页。。石刻最上方刻有汉式屋顶,其保存状况虽然不尽人意,但依然可以看到屋顶上装饰有花朵、垂缦等图案。屋顶下方刻一方形框,框外侧刻一周莲瓣,框内中间刻一佛二弟子,下方刻一世俗人物形象,周围刻十方佛。简报中认为图像题材为中间刻毗卢遮那佛与二弟子,下方刻世俗人物,周围为十方佛。将其与大日如来佛堂内的石刻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年代相近,为9世纪初期。②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摩崖石刻及线刻佛塔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第69—101页。简报中辨识出了“毗卢遮那佛+二弟子+十方佛”的图像配置,但是对于为何出现这种配置以及所反映的信仰则未予讨论。

图一 大日如来佛堂西侧石刻线描
(一)毗卢遮那佛与二弟子
中央主尊为毗卢遮那佛,其两侧胁侍为二僧人形象,应为二弟子。其他地方已经发现的吐蕃时期毗卢遮那佛图像,其组合为毗卢遮那佛、观音和金刚手菩萨,或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其胁侍皆为菩萨,此处发现的毗卢遮那佛与二弟子的组合为首例。从中央主尊头戴宝冠、饰臂钏、双手施禅定印来看,毫无疑问这是胎藏毗卢遮那佛,与《大毗卢遮那现等加持经》(简称《大日经》)有关。二弟子一般作为释迦牟尼佛两侧的胁侍出现,此处存在由胎藏毗卢遮那佛替换释迦牟尼佛的可能性。
在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也发现有以胎藏毗卢遮那佛替换原来主尊的现象,从榆林第25窟和法藏敦煌绢画CH.0074①关于榆林第25窟和法藏敦煌绢画CH.0074的主要研究如下,郭祐孟:《敦煌石窟“卢舍那佛并八大菩萨”曼荼罗初探》,《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45—63页;赖鹏举:《中唐榆林25窟密法“毗卢遮那”与佛顶尊胜系造像的形成》,《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第18—23页;刘永增:《敦煌石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解说 (上)、(下)》,《敦煌研究》2009年第4、5期,第12—23、8—17页;陈粟裕:《榆林25窟一佛八菩萨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5期,第56—82页;田中公明著,刘永增译:《敦煌出土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像》,《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第59—67页;沙武田:《榆林第25窟——敦煌图像中的唐蕃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便可窥见。对法藏敦煌绢画CH.0074的研究往往关注绢画上方的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对该幅绢画作进一步观察,注意到在其下方绘有宝池,内有两只鸟各立于岩石 (或山顶),宝池下方有两身吐蕃供养人,左侧供养人着吐蕃装,饰缠头,呈跪姿,右侧供养人同着吐蕃装,牵一棕色马。宝池中的两只鸟,田中公明研究认为属于鹅鸟,表现了阿弥陀佛净土②田中公明著,刘永增译:《敦煌出土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像》,《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第59—67页。,中央主尊根据图像特征判断为毗卢遮那佛。如果不去考量中间的毗卢遮那佛,单从绢画中的宝池和宝池下方的两身吐蕃装供养人来看,该幅绢画应该是表现了某种净土世界,暗含宗教仪轨的寓意。结合在敦煌的佛教绘画中经常出现由不同的宗教信仰融合而产生新的样式的情况,可以大胆推测,这幅绢画是将阿弥陀佛净土的主尊替换为毗卢遮那佛,以阿弥陀佛净土来表现毗卢遮那佛的相关信仰。
至于榆林第25窟正壁的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图像,以往研究也是将关注点置于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图像上。而在主体图像之外还能观察到一些细节,自毗卢遮那佛莲座下方伸出一莲茎,莲茎向上升起,依次承托各尊菩萨,该种表现方式可能借鉴了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的表现方式③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粟裕副研究员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2018年举办的青年藏学家藏学讲座中告知。。赖鹏举认为:“榆林第25窟正壁的主尊代表南传中印胎藏及佛顶尊胜系 ‘毗卢遮那佛’的仪轨,而其榜题 ‘清净法身卢舍那佛’及本窟四壁的造像则表现北传华严密法的主尊,两者在本窟的对应关系,开启了尔后南、北系密法的互动。”④赖鹏举:《中唐榆林25窟密法“毗卢遮那”与佛顶尊胜系造像的形成》,《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第18—23页。榆林25窟正壁表现的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八大菩萨的排列和手中的持物与在玉树地区所发现的不同,应不属于同一系统,更多的是受到敦煌造像的影响。用来表现净土世界的莲茎承托佛像以及“清净法身卢舍那佛”的题记等是北传华严密法的象征,但是其图像风格以及整个图像所要表达的则是吐蕃地方的毗卢遮那信仰。因此,榆林第25窟正壁的图像是吐蕃毗卢遮那信仰和汉地华严信仰的结合,借助华严的净土世界来表现毗卢遮那信仰。从榆林第25窟与法藏敦煌绢画CH.0074将原来的主尊替换为毗卢遮那佛的现象来看,将原净土世界的主尊替换为毗卢遮那佛并非个例,这种替换现象表现了两种信仰的融合。
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所刻的毗卢遮那佛与二弟子,是以毗卢遮那佛替代了原来的主尊释迦牟尼佛,现在再来看毗卢遮那佛与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有研究认为《华严经》中的“华藏世界导师有所谓 ‘三佛’之名以及 ‘三身’的说法。三佛就是异名同尊的释迦佛、卢舍那佛、毗卢遮那佛,‘三身’就是内尊佛都可从 ‘本体、相状、作用’三个方面来说明其究竟圆满的境界,用佛经专业术语来说就是 ‘法身、报身、化身’”⑤释见辟:《华藏世界:华严学的净土信仰》,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8页。。在《华严经》主导的华严信仰中,释迦佛为法身,毗卢遮那佛为化身,二者为同尊。①曹郁美:《〈华严经〉中的毗卢遮那佛》,《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2007年第9期,第55—74页。如果将此处的一佛二弟子组合放在华严信仰的体系下,其互换替代则成立。当前发现的吐蕃时期造像基本为毗卢遮那佛相关题材,《大日经》相关汉、藏经文也在吐蕃时期流传,艾米·海勒 (Amy Heller)研究认为吐蕃时期将王权与毗卢遮那信仰结合,以毗卢遮那佛象征王权来实施其统治②A my Heller,“Ninth century Buddhist images carved at lDan ma brag to commemorate Tibeto-Chinese negotiations”, pp.335-358;“Early ninth century images of Vairochana from eastern Tibet”, pp.74-79;“Eighth and ninth century temples&rock carvings of Eastern Tibet”, pp.86-103.。吐蕃主要流行毗卢遮那信仰,在同一时期的敦煌则以华严信仰等为主,此时的敦煌由吐蕃占领,二者存在往来交流。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上所刻图像以毗卢遮那佛替换释迦牟尼佛,有可能是毗卢遮那信仰与华严信仰结合的一种表现。
(二)十方三世佛
毗卢遮那佛与二弟子外侧刻十方佛,共10尊。所施手印共3种,第一种为双手施禅定印,第二种为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说法印,第三种为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法华经》《华严经》等皆记载“礼敬十方如来”,十方佛有代表十方净土之意。从3种手印来看,可能代表了3种佛:左手禅定印、右手触地印,可能为卢舍那佛;左手禅定印、右手说法印,可能为释迦牟尼佛;双手禅定印推测为毗卢遮那佛。《华严经》体系中释迦佛为法身、卢舍那佛为报身、毗卢遮那佛为化身。
《华严经》最早由东晋的佛驮跋陀罗于420年译为汉文,即《大方广佛华严经》,共34品60卷,简称《六十华严》。其后实叉难陀于699年译有《八十华严》,共39品80卷;般若于798年译《四十华严》,共一品40卷。同一时期,胜友 (Jinamitra)和智军等藏译《佛华严大方广经》,共45品,收录于《甘珠尔》中。因此,吐蕃时期《华严经》的汉、藏译本皆已出现,推测吐蕃也出现了华严信仰,但是要讨论其传播程度及在吐蕃佛教信仰中所占地位则需要更多的材料支撑。
吐蕃时期既已翻译有《华严经》,贝纳沟此处的十方三世佛则很有可能与华严信仰有关。二弟子一般与释迦牟尼佛组合出现,如果是“释迦牟尼佛+二弟子+十方佛”的配置,则为华严信仰中常见的图像,而此处将释迦牟尼佛替换为毗卢遮那佛,并且十方佛中的8尊佛的手印与主尊手印相同,皆为双手结禅定印,可推测这是毗卢遮那信仰与华严信仰的结合。
此处的十方佛石刻是迄今为止在涉藏地区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例。11世纪以后在西藏寺庙壁画中也有十方佛的绘制。杨鸿蛟在《白居寺祖拉康内殿壁画图像考释——兼述般若佛母与十方佛组合图像在藏地的传播》一文中对十方佛进行讨论,认为“十方佛图像成为藏地《般若经》信仰密教化的重要表现方式,《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 (梵atasāhasrikā-Prajāpāramitā, 藏)即详细描绘了十方佛国世界,其《缘起品》(Nidāna-parivarta)中记载: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鹫峰山顶,放光照十方佛土,一切世界上首菩萨各以千叶金色莲花来献,佛散花遍诸佛界,花台化佛演说大般若经”。③杨 鸿蛟、魏文:《白居寺祖拉康内殿壁画图像考释——兼述般若佛母与十方佛组合图像在藏地的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10期,第37—57页。谢继胜对居庸关佛塔进行研究时,对其中的十方佛题材进行论述,认为三种手印代表了十方三世佛④谢继胜:《居庸关过街塔造像义蕴考——11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图像配置的重构》,《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5期,第49—80页。。十方佛常与其他题材组合于一起,表现十方佛土。
要讨论贝纳沟的十方佛,需将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敦煌。此时的敦煌壁画中大量绘制净土变,十方佛一般绘制于净土世界中,表现十方净土。如郭祐孟对榆林第25窟的研究,认为正壁以菩萨身戴冠、双手结法界禅定印的卢舍那佛,与八大菩萨结合为一铺曼荼罗,本身已经是独立密法,却又假借左、右两侧壁代表十方、三世的两铺净土变,来作为实践卢舍那境界的方便法门,显、密法门各自独立却又相互增益。①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主尊的毗卢遮那性格——以莫高窟第14窟图像结构为主的分析》,郑炳林主编:《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24—46页。说明在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已出现将毗卢遮那为主尊的密法与以十方三世代表的净土世界相结合的图像配置模式,而这种模式充分体现了在敦煌原有图像基础上增加新元素,创作出新的图像样式的现象。
(三)供养人或善财童子
在主尊下方还绘有一世俗人物形象,双手合十,跪坐,面向上方的毗卢遮那佛,做礼佛状。关于其身份,推测有两种可能性,一为供养人,二为善财童子。在同一河谷内的勒巴沟古秀泽玛石刻中出现有吐蕃供养人形象,共4身像,最前方为一童子形象,跪坐,双手捧香炉,后面为戴高缠头、着三角翻领袍服的吐蕃王室成员形象。与其相比,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的人物形象为单尊,所着服饰非吐蕃王室成员所着的三角翻领袍服,未戴高缠头,而吐蕃时期的佛教造像活动往往与吐蕃王室的出资支持有关,因此可以排除这一形象为供养人的可能性。
敦煌石窟中出现有唐五代时期《入法界品》相关图像,所绘制内容为善财童子参访情节。陈俊吉对敦煌石窟中出现的唐代《入法界品》进行研究,认为唐五代时期《入法界品》中善财童子的造型,可以分为“菩萨形”和“世俗人物形”两大类,“菩萨形”着菩萨装,配置莲座和头光等,“世俗人物形”则着世俗的服装。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的这身人物形象,虽后期受风化影响,部分细部不清,但是从其残存服饰特征来看,应为世俗人物形象,且与“世俗人物形”的善财童子接近,因此推测可能为善财童子。
据前所述,善财童子的绘制与《入法界品》有关,入法界品为《华严经》中的一品,吐蕃时期已有藏译本《华严经》。建于11世纪的塔波寺壁画中也发现有一处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的故事情节②Klimburg-Salter D.E.Tabo:A Lamp for the Kingdon:Early Indo-Tibetan Buddhsit Art in the Western Himalaya, Skira Editore,1997,p.54.,其构图及形象与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的世俗人物像存在差异,但是塔波寺善财童子形象的出现,说明《华严经》当时在西藏已经具有一定的信仰基础。在敦煌所发现的唐五代时期的《入法界品》相关图像,其故事情节与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图像也存在差异,单从图像构图来比较,未发现完全一致可供参考的图像。从经文内容来看,《入法界品》中记述了如何行菩萨道证入法界,即由善财童子的普贤行来实践,最后圆满证入法界。③陈俊吉:《唐五代 〈入法界品图〉中善财童子的造型与特色》,《书画艺术学刊》第19期,第151—204页。因此,结合上文推论的该处崖壁中“毗卢遮那佛+二弟子+十方三世佛”的配置为毗卢遮那信仰与华严信仰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图样的创作,在此背景下,此处的人物形象可能为善财童子。
(四)《普贤行愿品》
图像下方刻藏文普贤陀罗尼和《普贤行愿品》,考古调查简报中已公布了藏文原文和汉文翻译。在吐蕃时期已经认为修行念诵《普贤行愿王经》可达到证悟成道的目的。《贤者喜宴》中也有修行时念诵《普贤行愿王经》的记载,说要在释迦牟尼佛前念诵《普贤行愿王经》,从而达到修行的目的,《普贤行愿王经》在当时的佛教仪轨中应是配合佛像来使用的。
将十方佛外侧装饰的边框及最上方的屋顶样式,与敦煌的净土变壁画相比较,发现建筑样式接近,而且十方三世佛常见绘制于净土变中。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上“毗卢遮那佛+二弟子+十方三世佛《普贤行愿品》”的图像与经文的配置,表现了吐蕃本土的毗卢遮那信仰与当时汉地流行的华严信仰的结合,《普贤行愿品》本身又具有发愿的功能,常常配合图像使用,在礼拜佛像时可念诵《普贤行愿品》来达到发愿及证悟成道的目的。
二、吾娜桑嘎石刻:“释迦八相+骑象普贤+骑狮文殊”
吾娜桑嘎石刻位于勒巴沟沟内,该处石刻由图像和藏文组成,图像主体为佛传,目前可辨识出猕猴奉蜜、佛诞生、佛降自三十三天说法、佛降伏外道、佛涅槃等情节,《简报》中认为属于“释迦八相”。藏文题记的内容包括讲述佛传的情节和单独的《无量寿经》《般若心经》等,《简报》认为《无量寿经》和《般若心经》皆与吐蕃高僧法成的译本较为接近,但存在几处差异。①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省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第95—146页。张长虹将吾娜桑嘎石刻的佛传与在敦煌第76窟、东千佛洞、榆林窟第5窟、五个庙第1窟等发现的同类图像进行对比,得出以下结论:“随着吾娜桑嘎这批石刻图像的发现,尽管目前仅辨识出 ‘六相’,并非完整的 ‘八相’,但是从其所刻内容与北宋至西夏时期完整的 ‘释迦八相’图像大体吻合来看,这批图像显然是后期释迦八相出现的先声,敦煌宋代蓦然出现的具有 ‘印度波罗样式’的八塔变的图像来源还是应该在吐蕃佛教图像系统中去寻找来源。”②同上。笔者赞同其观点,敦煌出现的同类题材与吐蕃有关联,且其来源可能为吐蕃。
吾娜桑嘎摩崖石刻D组上方为佛降自三十三天说法,在其下方为一菩萨坐于大象上,为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右侧为一坐于狮子上的菩萨,应为文殊菩萨 (图二)。因石刻受风化影响,不确定在其周围原来是否刻有眷属。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组合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常见,关于文殊、普贤二圣信仰的形成,赖文英研究认为,至迟在6世纪前后,文殊、普贤二圣信仰已经形成,并且是佛教徒发愿礼忏以求佛道的菩萨行者之代表③赖文英:《普贤行于文殊愿——文殊、普贤二圣信仰探源》,《2015华严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财团法人台北市华严莲社,2018年,第255—279页。。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出现有与《法华经》《华严经》相关的净土变,法华信仰和华严信仰在这一时期占据重要地位。
唐宋时期的文献中也有高僧对文殊、普贤与华严、法华的探讨。如《宋高僧传》中的《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对文殊、普贤、毗卢遮那与华严的记载:“大历十一年 (公元776)暂游五台……居大华严寺,专行方等忏法。时寺主贤林请讲大经,并演诸论。因慨华严旧疏文繁义约,惙然长想,况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大华严》之义也。”④[宋]赞宁:《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5页。
隋朝吉藏的《法华义疏》中认为普贤、文殊和法华、华严皆有关系。云:《华严经》七处八会,普贤、文殊善其始;《入法界品》流通之分,此二菩萨又令其终,所以此二人在彼经始终者,世相传云:究竟普贤行、满足文殊愿故。普贤显其行圆,文殊明其愿满,故与诸菩萨中究竟具足,显《华严》的圆满法门。今说《法华》亦明文殊开其始,普贤通其终,亦显《法华》是究竟法。所以二经皆明两大士者,欲显《华严》即是《法华》。为直往菩萨说令入佛慧故名《华严》;为迴小入大菩萨说令入佛慧故名《法华》。约人有利钝不同,就时初后为异。古两教名字别耳,至论平等大慧清净一道,更无有异,是故两经皆明二菩萨也。①[隋]吉藏:《法华义疏》,[日]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631页。

图二 吾娜桑嘎石刻文殊与普贤菩萨线描
《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与《法华义疏》说明文殊、普贤与法华和华严皆有联系。殷光明研究认为敦煌石窟中结跏趺坐佛与骑狮文殊、乘象普贤组合的3尊像,尤其是中唐以前与法华有关的,称释迦三尊像;中唐以来与华严有关的,称华严三圣像;图像与义理归属不明确者,则二者皆可称。②殷光明:《从释迦三尊像到华严三圣的图像转变看大乘菩萨思想的发展》,《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0页。那么再来看吾娜桑嘎石刻中文殊、普贤出现的位置,二者位于佛降自三十三天说法附近,整个石刻所在崖壁刻“释迦八相”,主尊应为释迦牟尼佛。文殊、普贤和以释迦牟尼佛为主尊的“释迦八相”的同绘可能与《法华经》有关。谢继胜对扎塘寺发现的法华图像进行研究,同时梳理了吐蕃译经目录,认为吐蕃时期已翻译有藏文《法华经》③谢继胜:《扎塘寺壁画法华图像与11—14世纪中国多民族艺术史的重构——文殊弥勒、释迦文殊与藏汉佛教义理的图像形成史》,《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第130—146页。。扎塘寺出现的法华图像并非凭空出现,又加上吐蕃时期已翻译有藏文《法华经》,说明吐蕃时期很有可能法华相关图像已有绘制。
骑狮文殊和骑象普贤二者与法华、华严皆有关,而究竟是属于法华还是华严,则要看其主尊为释迦牟尼佛还是毗卢遮那佛。张长虹将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等与榆林第25窟、敦煌藏经洞所发现药师经变相绢画中的同类菩萨进行对比,认为吾娜桑嘎石刻点的图像与敦煌的吐蕃样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可能是受到敦煌的影响。①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省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第95—146页。吾娜桑嘎将骑狮文殊、骑象普贤与释迦八相一起绘制,而吐蕃时期已翻译藏文《法华经》,又有一定的信仰基础。因此,吾娜桑嘎石刻的图像为一种新的图像样式,将文殊、普贤和释迦八相组合配置可能与《法华经》有关,是敦煌的净土信仰融合于吐蕃佛教艺术的表现。
三、结 语
玉树位于唐蕃古道上,是从青海进入西藏的重要通道,《贤者喜宴》《柱间史》等藏文史籍中记载文成公主入藏的路线,玉树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有学者甚至认为玉树发现的吐蕃佛教石刻为文成公主主持凿刻。霍巍早在其《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提出“来自汉地佛教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四川、敦煌等地与来自吐蕃本土的藏地佛教相互交流、融合,在佛教造像艺术上产生新的流派与风格。在藏东遗存下来的这批摩崖造像上既可以观察到源自吐蕃本土的印度—尼泊尔风格的影响,也可以观察到浓厚的汉地文化因素 (如刻工中的汉人工匠、造像当中的唐氏风格、题铭当中残存的大量汉文等),也正是唐蕃关系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不必拘泥于唐文成公主进藏这一长期以来的传统模式来看待这批吐蕃遗存,而应当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才会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②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对于川青藏交界地带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的出现,霍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认为这批造像很可能是在吐蕃与唐朝积极酝酿再次会盟的历史背景之下,益西央僧团为配合和促进唐蕃之间的友好会盟而刻写的石刻,其核心价值在于“以佛证盟”③霍巍:《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第92—101页。。
玉树石刻中所能直接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因素,如大日如来佛堂东侧崖壁所刻的梵、汉、藏3种语言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藏文题记中所记载的汉、藏工匠组成的造像团队,在大日如来佛堂、察雅丹玛札石刻、扁都口等石刻藏文题记中皆有出现的兼修汉地禅宗的益西央等,学者们所持观点趋于一致,认为这些表明了吐蕃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④霍巍:《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的考古调查与新发现》,《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第4—9页;霍巍:《论藏东吐蕃摩崖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西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63—69页;张延清、杨本加:《唐蕃和平与文化交流的使者——吐蕃僧团》,《藏学学刊》(第15辑),中国藏学出版社,第33—50页等。。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所刻的“毗卢遮那佛+二弟子+十方佛+《普贤行愿品》”的组合表现了毗卢遮那信仰与华严的结合,吾娜桑嘎石刻中“释迦八相+骑象普贤+骑狮文殊”则与法华有关。这两处图像的出现,体现了吐蕃时期流行的毗卢遮那信仰与以敦煌为代表的汉地法华、华严信仰的结合,是汉藏佛教交流中出现的新的图像样式。这两处图像的发现为研究汉藏文化在佛教信仰方面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