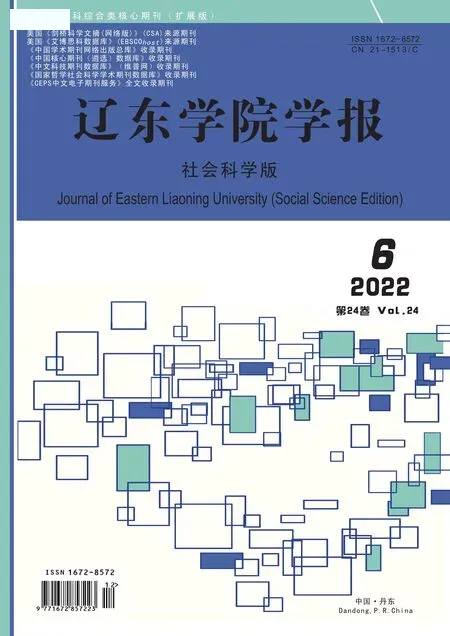《郑志》与《郑记》关系新诠
罗 永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郑志》是一部记录郑玄及其门人弟子之间互相答问的著作,自《后汉书·郑玄传》始著录以来,《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通志》等均有著录,该书大约在唐以后渐渐散佚,南宋后亡佚殆尽。由于《郑志》中保存了大量郑玄的经学思想,故诸经《正义》《通典》及类书中屡屡征引。《郑记》一书始见著录则是在《隋书·经籍志》,题为“《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1]938,亡佚时间应与《郑志》大致同时。有关两书的关系,《唐会要》载刘知几《孝经注议》云:“郑玄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所著述及应对时人,谓之《郑志》”,“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记》(1)《唐会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引本节作:“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志》。”考《文苑英华》《孝经注疏》等均作“郑记”,知此“郑志”乃“郑记”之讹,中华书局1955年版沿而未改,今改正之。”[2]1406。据此,则《郑志》唯载郑玄语录及其与弟子、时人互相问答之语,《郑记》唯载郑玄门人弟子之间互相问答之语。清代学者辑录《郑志》《郑记》,各家关于两书的安排也有所不同。以袁钧辑本为界,袁本之前的辑本唯称《郑志》,而将今《郑记》之文杂厕其中;袁钧始依刘知几的区分标准,将《郑记》别为一帙,以为“各还本名,庶几稍见当日之旧焉”[3]卷一,后世学者亦以此为袁钧辑佚之功,以为诸本粗疏,袁本最善。
依据传统观点,《郑志》《郑记》应判然有别,各是一书。然而从唐人注疏征引两书的情况来看,两书却常被混淆:有据刘知几所言应属《郑记》之文者书作《郑志》,也有同样的内容,本篇书作《郑志》却在别篇标作《郑记》的。清人校勘,往往仅据各史志目录的著录及刘知几的划分予以辨别,认为之所以出现混淆,是因为引用者将两书混为一书,始终没有学者尝试从源头上去厘清两书的关系。以至于迄今,学界的认识都停留在刘知几的陈述上,简单地认为《郑志》《郑记》从成书开始直到亡佚都是没有交集的两本书。但是笔者通过考查各史志目录著录两书的篇卷变化,结合对唐人书中征引混淆之处的辨正,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郑志》与《郑记》并非如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判然有别,而是在成书之后的流传过程中,出现过内容上的分合,正是这种分合导致了唐人书中对两书征引的出处上出现混淆,以及刘知几对两书的区分与这种混淆的矛盾。大致来说,最初的《郑志》八篇应纯为郑玄语录及其答弟子、时人问五经的内容,此后经郑小同及郑门弟子不断增补,《郑志》由八篇变为十一卷,其中就掺入了《郑记》的内容,而两《唐书》所载之九卷本,又是在十一卷本基础上剔除掉其中的《郑记》之文而成的。《郑记》一书出现则应是在十一卷本《郑志》成书以后,由郑玄再传弟子们汇集郑玄弟子间互相问答之语而撰集,最早为杜台卿于隋开皇初年献上的《玉烛宝典》一书所征引,故其成书当不晚于隋初。以下笔者将从史志目录著录《郑志》的篇卷变化入手,探讨《郑志》的成书和流传情况,及其与《郑记》一书的关系。
一、从“八篇”到“十一卷”:《郑志》的成书、增补与《郑记》的混入
《后汉书·郑玄传》云:“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4]1212此处的“八篇”,一般认为是以内容起讫划分,即将郑玄与弟子、时人讨论的内容分属各经,每经划为一篇。如袁钧就认为《郑志》是“以经为次”[3]卷一,胡元仪《北海三考》也说:
按“八篇”者,以《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七经分篇,得七篇,又《杂问》一篇,共为八篇也。[5]
此说应当是可信的。唐人《正义》引《郑志》,有时不书“郑志”而直接引作“春秋志”“杂问志”“易志”等,如《周礼·保章氏》疏引《春秋志》[6]707,《周礼·大司寇》疏引《易志》[6]907,《毛诗·桧谱》疏[7]457及《甫田》疏[7]836引《尚书》《郑志》,《采芑》疏引《周礼志》[7]644,诸经《正义》引作“杂问志”者更多至十二条,而其所引内容均是《郑志》中语,说明《郑志》确实是以内容分篇的,《正义》在引《郑志》时直接标明了其所引篇名。八篇本《郑志》的内容,据《后汉书》所说,应该只有“玄答诸弟子问五经”,即郑玄与弟子及时人相互问答之语,并没有羼入《郑记》的内容。
及至初唐,《隋书·经籍志》著录《郑志》已变为十一卷,多出三卷。关于多出三卷的原因,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以为“按《隋》、《唐志》载《郑志》十一卷。九卷者,皆魏侍中郑小同重订别本”[8]93。郑珍也认为《后汉书》所载八篇本《郑志》是郑玄门人弟子所撰,而《隋书》著录之十一卷本则为郑小同增编而成:
必是康成之殁未久,诸弟子即各出所记,分五经类而萃之,为《志》八卷;后来小同更有所得,增编为十一卷,自题己名,如朱子据二程弟子尹焞、张绎等记编为遗书之比,故《隋志》归之小同撰耳。[9]
胡元仪则在此基础上认为之所以多出三卷,是因为原来的一篇分为了多卷:“八篇而为十一卷,多出三卷,则篇帙重者,或分为二卷耳。其多三卷,盖《诗》与《礼》欤?以今所存者,《诗》《礼》较多推之也”[5]。以上诸说不无道理,《郑志》由郑玄门人弟子依《论语》而作,其成书当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代,中间必经增删及修订,而从《后汉书》著录的“八篇”,到《隋书》之“十一卷”,期间很可能就历经数次增补并重新分卷。作为郑玄之孙,且“学综六经,行著乡邑”[10]142,郑小同在其中理应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最终是否由郑小同完成了十一卷本《郑志》的编定,则实在没有确据可征;而且以袁钧辑本《郑志》来看,八卷中《毛诗志》55条,《周礼志》《仪礼志》《礼记志》分别为36条、6条及31条,《毛诗》及《三礼》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三。以今窥古,八篇本《郑志》很可能也是“《诗》《礼》较多”的格局,又经后世增补,则《毛诗》与《三礼》的四篇或已多至不得不分为七卷,遂与其他四篇合为十一卷。而增补进十一卷本《郑志》的,除了之前漏收的“玄答诸弟子问五经”的内容,是否还有《郑记》,即郑玄弟子之间相互问答的内容呢?增编《郑志》时,虽然还没有《郑记》一书,但这些弟子间的相互问答实际已经由再传弟子们记录了下来,如果这些再传弟子此时参与了增编《郑志》的工作,他们是很有可能把这些内容添加进去的。有关《郑记》的内容,刘知几说是“唯载《诗》《书》《礼》《易》《论语》”[2]1406,与《郑志》八篇相比,仅多了《论语》而少一门《春秋》。而实际上,《郑志》中也提到了《论语》,《毛诗序》孔疏曰:
《论语》注云:“哀世夫妇不得此人,不为灭伤其爱。”此以哀为衷,彼仍以哀为义者,郑答刘炎云:“《论语》注人间行久,义或宜然,故不复定,以遗后说”。[7]22
而《郑记》中也并非不载《春秋》,如《礼记·曲礼下》孔疏:
焦氏问:“案《春秋》君在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无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当何称?”张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称未闻。案称嗣子某,或殷礼也。”[11]107
并且从古书征引及后世辑佚看,《郑志》《郑记》二书在内容上相差无几,主要都是关于五经的阐释,那么在增编《郑志》时,将如今《郑记》中的内容也“以经为次”编入其中也是合乎情理的,而这正与袁钧之前的学者辑录《郑志》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正因为在不断的增编中补充了大量《郑记》的内容,才使得编撰者不得不将其重新分为十一卷,而这十一卷本《郑志》,也就同时囊括《郑志》《郑记》两书的内容,与《后汉书》的八篇本有了很大的不同。十一卷本《郑志》编成之时,《郑记》尚未成书,当时并没有“郑记”之名,应是郑门的再传弟子们在增编《郑志》之后不久,又汇集各自手中的郑玄弟子及其与再传弟子间的相互问答之语,依之前自己的老师们编撰《郑志》之例,将其编为一书,并命名为《郑记》,与十一卷本《郑志》并行于世,《郑记》之文于是两见,一见于《郑记》本书,一见于《郑志》。这种猜想并非无据,考辨《正义》当中征引“郑志”“郑记”的混淆之处,可以为我们的观点提供文献材料的支撑。
唐以前征引《郑志》之书,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齐魏收《魏书》和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所引数量很少,而且内容都是郑玄答弟子及时人问,没有混淆。到了唐代,唐人诸经《正义》开始大量征引《郑志》,其中明确标作“郑志”者一百余处,不书《郑志》而作“某某问,郑答”“郑答某某问曰”,或直引篇名如《杂问志》《春秋志》者亦有数十条,实际上均为《郑志》一书的内容,而标作“郑记”者仅一条,见《毛诗·生民正义》:
《郑记》王权有此问,焦乔答云:“先契之时,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盖以玄鸟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于上帝也。娀简吞鸟乙有子之后,后王以为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谓之高媒。[7]1059
本段引文还见于同为孔颖达疏解的《礼记·月令正义》,文有小异而标作“郑志”:
《郑志》焦乔答王权云:“先契之时,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于南郊,盖以玄鸟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于上帝也。娀简狄吞鸟乙子之后,后王以为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谓之高禖。”[11]474
这是郑玄弟子之间的问答,按刘知几所说应当是《郑记》之文,而孔颖达于《生民正义》引作“郑记”,却在《月令正义》引作“郑志”,殊堪注意。清代学者浦镗认为《生民正义》有误,他在《十三经注疏正字》(2)《四库提要》著录此书,题为“沈廷芳撰”,然阮元引据此书时则作“浦镗云”,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云:“案廷芳为浦镗作传云:‘《正字》书存余所,故人苦心,会当谋诸剞劂,芳得附名足矣。’而镗弟铣《秋稼吟稿序》云:‘《正字》书,沈椒园先生许为付梓,今已入《四库全书》,而非兄之名也。’据此,则是书为浦镗撰,非出沈廷芳”。据改。中指出此处“‘记’疑‘志’字误”[12]239。然而阮元以为不误:
案此不误。浦镗云“记”疑“志”字误,非也。考《郑记》与《郑志》非一书。《郑记》六卷,康成弟子撰;《郑志》十一卷,郑小同撰,并见于《隋书·经籍志》,浦失考。[7]1059
孙诒让亦以为《生民正义》作“郑记”不误,而《月令正义》有误,于是在《月令正义》引《郑志》此条下加校语曰:
《诗·生民》正义引此作“郑记”,又云“此是郑冲弟子为说以申郑义”,则作“记”是也。《郑志》与《郑记》本是二书,后人多混为一。[11]474
阮、孙二人所据,无非是《隋志》等书对《郑记》的著录和刘知几关于《郑志》《郑记》内容的区分,却没有考察两书的成书及其相互关系,实难服人。实际上,《礼记正义》中尚有两条引文是郑玄弟子之间的问答,被袁钧辑入《郑记》,而《正义》中均标作“郑志”而非“郑记”:
按《郑志》,焦氏问云:“仲秋,乃鸠化为鹰。仲春,鹰化为鸠。此六月何言有鹰学习乎?”张逸答曰:“鹰虽为鸠,亦自有真鹰可习矣。”[11]509(《礼记·月令正义》)
故《郑志》崇精问焦氏云:“郑云三王同六卿,殷应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与五行其取象异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大宰,即为六官也。”[11]130(《礼记·曲礼正义》)
这两条引文与上引《月令正义》一条,照刘知几的说法,均应为《郑记》之文,而孔颖达却标作“郑志”。如此,我们便不能不怀疑,孔颖达撰《正义》时是否并没有见过《郑记》一书?他征引的郑玄弟子间的问答又究竟出自何书呢?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解释是:
刘知几《史通》亦称:“郑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谓之《郑志》。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不问答,谓之《郑记》。”案《通典》及《初学记》所引《郑记》,均有王赞答词,与知几所云更不问答者不合。考《孝经疏》引此文作“各述师言,更为问答”,知“不”字乃“为”字之讹。王应麟《玉海》、朱彝尊《经义考》并沿用误本,殊失订正。又《通典》所引《郑志》,皆玄与门人问答之词,所引《郑记》,皆其门人互相问答之词,知《志》之与《记》,其别在此。《曲礼正义》引《郑志》,有崇精之问,焦氏之答。《月令正义》引《郑志》有王权之问、焦乔之答,焦氏之问、张逸之答。疑本《郑记》之文,校刊者惟据《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改为《郑志》也。[13]855-856
按,《提要》此说不确。首先,《提要》以为刘知几此言出自《史通》,但这其实是四库馆臣误记,《史通》中并没有提到《郑志》和《郑记》的区别,这些话实出自刘知几《孝经注议》,这篇文章如今可见最早的出处是《唐会要》,此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孝经注疏》等亦有载引,而此四书中,除了《孝经注疏》引作“更为问答”外,余皆作“更相问答”,故其所谓“校刊者惟据《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改为《郑志》”自是无稽之谈。其次,《玉海》《经义考》的确误作“更不问答”,校刊者也可能会据此二书将《正义》中作“郑记”之文改为“郑志”。但考影印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上引三条均已作“郑志”[14],绍熙乃南宋光宗赵惇的年号,而《玉海》成书已是元代,《经义考》更是清代之书,不可能据未出之书以校改前代之文。因此,《提要》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据刘知几所言,《郑志》《郑记》各是一书,而孔颖达多处引《郑记》之文却均标作“郑志”,合理的解释是,孔颖达作《正义》时所据的本子正是经过增编的混《郑志》《郑记》为一书的《郑志》本子。而孔颖达在贞观年间曾参与编撰《隋书》,所以他所据的本子,应当正是《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十一卷本。如此,我们便从文献材料的考辨上证明了十一卷本《郑志》已经因为后世增补而包含了《郑记》的内容。当时《隋书》已著录《郑记》六卷,是《郑记》虽已单行,十一卷本《郑志》仍流行于世,孔颖达《正义》所据即是此本。所以《正义》中所引,自然只书《郑志》之名,不见《郑记》,《礼记正义》三处引文正应标作“郑志”。进而可以推知,《生民正义》作“郑记”者为讹误,应据《月令正义》改为“郑志”为妥。之所以误作“郑记”,或是后世因见《郑记》《郑志》两书已分,又据刘知几所言两书之别,臆改“郑志”为“郑记”,失孔氏本意。
二、从“十一卷”到“九卷”:《郑志》的整理与《郑记》的剔除
如上所述,十一卷本《郑志》既已包含了《郑记》,若刘知几所见为《隋书》著录的版本,何以仍能够言明《郑志》《郑记》两书之区别如此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所见的本子并不是《隋志》著录的十一卷本《郑志》,而是另外的已经不包含《郑记》内容的《郑志》本子。而《隋志》以后,两《唐志》著录《郑志》变为九卷。从十一卷到九卷,又少两卷,四库馆臣认为“已佚二卷”[13]856,胡元仪也以为“有所残阙”[5],然而事实恐怕还并不如此。按,《隋书·经籍志》原稿为《五代史志》,编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此后官府曾组织过多次对经籍的搜检刊正,据《唐会要·经籍》所载:
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严、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
文明元年十月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
景云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2]643-644
可见《隋志》编成之后,官方对经籍的整理修缮并未停止,并且除了搜罗遗书以补缺漏外,还曾对传写讹谬之处予以刊正缮写。开元初,唐玄宗又诏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开元三年,褚无量、马怀素与玄宗言及经籍,玄宗就因内库图书“篇卷错乱,难于检阅”令两人重加整理,“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15]1962。而实际上,早在开元七年之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旧唐书·褚无量传》:
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纵观焉。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15]3167
因此至迟在开元六年之前,这次整顿已经开始,并且成果斐然,“数年间,四部充备”。不久马怀素、褚无量相继去世,诏令元行冲总代其职,开元九年,殷践猷、王惬、毋煚等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由元行冲奏上。毋煚在此基础上“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15]1962。《旧唐书·经籍志》即是直接抄录的《古今书录》,只是删去了原书所附的小序,《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开元以前书籍,也是以《古今书录》为底本。因此,两《唐志》记载的“《郑志》九卷”其实是毋煚著《古今书录》时的见在书目,也就是说《古今书录》已著录《郑志》为九卷。此九卷本《郑志》,很可能就是在高宗至玄宗期间的数次经籍整理中由十一卷本删削而成的。刘知几上《孝经注议》是在开元七年,因此他所据《郑志》,极有可能正是此本。虽然《古今书录》撰成时刘知几已经去世,但九卷本《郑志》问世则在此之前,即便是在开元初这一次经籍整理工作中重整得来,也很可能早于开元七年奏上《孝经注议》时,所以刘知几仍及见之。总之,经过数十年间的多次整理,《郑志》已从《隋志》著录的十一卷变为九卷,刘知几所见即是此本。而刘氏既已明言《郑志》是“其弟子追论师所著述及应对时人”,与“郑之弟子,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的《郑记》有问答主体上的区别,反过来又证明九卷本《郑志》中确已不含《郑记》。这种内容上的变化,不太可能是因散佚所致,更可能是人为修订剔除的结果。只不过这次修订不是简单地增删或分卷,而主要是将原本混入其中的《郑记》的内容剔除出去,致使其内容减少从而略为九卷。至此,《郑志》《郑记》两书才真正如刘知几所说,已经各是一书了。从此以后,唐人书中征引《郑记》之文,遂不再有标作“郑志”之例。
至于此本《郑志》何以为九卷,与《后汉书》所言八篇之旧不合,盖重整时将《郑志目录》别为一卷欤?按,刘知几《孝经注议》云:“《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五经之外,有《中候》《书传》《七政论》《乾象历》《六艺论》《毛诗谱》《答临硕难礼》《驳许慎异义》《发墨守》《箴膏盲》,及《答甄子然》等书”[2]1406。《郑志目录》之名,首见刘知几此《议》,而《目录》之内容,此亦为仅见,后人辑《郑志》佚书,多将此条附于最末。然而此条并非问答,也不是郑玄语录,大概是弟子编《郑志》时为每篇所作的简介性质的文字,与郑玄《三礼目录》相类,原本或散见全书各篇,后来被集中到一处,别为一卷,遂成九卷之数。然此说证据不足,在此姑且算作一种猜想,留待有识君子证之。
另,两《唐志》以后,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又著录有《郑志》十一卷、《郑记》六卷[16]762,但《通志·艺文略》的著录特点,正如郑樵在《校雠略》中所说,是“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即不论是否见在,统统著录,所谓“总古今有无之书”[16]831-832也。所以,《通志》所载“《郑志》十一卷”,大概只是郑樵照《隋书》直录,并非《郑志》在宋代又从九卷增编为十一卷。其实从《新唐书》以后,官方目录均已不再著录《郑志》与《郑记》。郑樵之前,北宋时编修的《崇文总目》即不载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此判断两书“全佚于北宋初”[13]856,皮锡瑞也认为“历五代、宋而遽亡佚”[17]149,而南宋罗泌作《路史》,其子罗苹注其书曰:“郑答赵商与昭皆以为三皇至道,故举南比正夏冬,而春秋自正,五帝中道,故又命羲和于春、秋、夏详人事,乃合而一之”[18]146。此条佚文,《路史》之前各书均未见引,至清人辑佚时方将其辑入,似乎在南宋罗苹注《路史》时《郑志》尚有残存,全佚或当在南宋以后。
三、结语
自从《后汉书·郑玄传》著录《郑志》以来,《郑志》卷数屡次变化。从八篇到十一卷,是因为后人增补致其数量增多,故增加三卷,而此次增补进之内容就包含了郑玄弟子间的互相问答,这部分内容后来被汇集成《郑记》一书。而从十一卷到九卷,前人多以为是散佚二卷,实则是玄宗开元初以前重新整理所致。这次整理,在十一卷本基础上,将原先羼入其中的《郑记》之文剔除,重新分为九卷。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所据为十一卷本《郑志》,故其所引《郑记》之文均作“郑志”;刘知几上《孝经注议》时所见乃九卷本《郑志》,故其能叙《郑志》《郑记》的内容区别如此。清代学者唯据刘知几所说,以为两书泾渭有别,绝不混杂,不惟校勘诸经《正义》时据以断其所谓讹误,辑录《郑志》《郑记》佚书时也以两书是否分别以评其优劣,却从未真正厘清过两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书既已久佚,其中成书、流传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只能依据有限的文献记载加以推理、求证,以期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结论,“庶几稍见当日之旧焉”。笔者不揣简陋,妄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