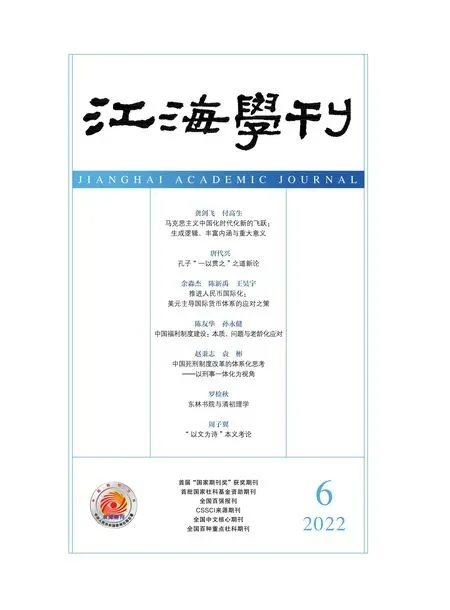东林书院与清初理学*
罗检秋
明清鼎革之后,程、朱理学逐渐成为民间学术主流,也是构建庙堂儒学的主要资源。清初学术潮流是如何发生转变的?清代学者及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顾炎武、王夫之等名儒的学术反思。康熙帝晚年曾赞誉中州理学家孙奇逢、关中理学家李颙、山西理学家范鄗鼎等人,而对江南民间理学,包括著名的无锡东林书院罕有提及。一定程度上盖因清初东林书院缺乏孙、李那样的学术名家,但也在于清廷禁止士人结社,忌讳东林遗风。在此背景下,清廷及理学官僚多对东林书院的理学传统避而不谈。
民国年间,钱穆先生认为:“余观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他提到清初东林学术对陆世仪、李颙、孙奇逢等名儒及皖南施璜、吴曰慎等人的影响,认为“即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亦无不可”。(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0页。钱说语焉不详,未能引起研究者注意。他所谓“清初学风”不仅是指经世关怀,而且在于尊崇程、朱理学的取向。谢国桢、小野和子等学者论述了明末东林党人与明清之际会社的关联,但忽略了东林书院与清初理学脉络的关系。(2)关于清初理学的代表性专著有,龚书铎主编、史革新著:《清代理学史》(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朱昌荣:《清初程朱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关于晚明东林书院及东林党的主要论著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事实上,鼎革之后,东林书院成为清初理学的重要渊源,对朝野理学趋向都有相当影响。
以理学倡导士林
宋代杨时传二程之学,曾在无锡东林讲学。明代万历年间,东林书院圮废已久,仅存一片柳树林及几间旧屋,原址成为僧舍。万历二十二年(1594),削职回籍的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倡修东林书院。其后,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学其中,砥砺气节,阐扬理学。东林书院岁有大会,月有小会,一时有志之士,闻风兴起。他们生当阳明学盛炽之时,却开“由王返朱”之先河,被誉为“心程、朱而脉孔、孟”,“使程、朱之学晦而复明”。(3)周彦文:《东林景逸高夫子论学语序》,高廷珍等编纂、《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东林书院志》卷一六,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34页。顾宪成的《东林会约》遵循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以“知本”“立志”“尊经”“审几”为“四要”。其“知本”一目申述孔、孟、程、朱的性善论,强调“本体工夫原来合一”,而王阳明以“无善无恶”为本体,实与“为善去恶”工夫“自相矛盾”,非圣人之道。(4)顾宪成:《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东林书院志》卷二,上册,第19页。顾、高等人长期主盟东林,宣讲《四书》主题,编刻程、朱著作。其中高攀龙的《朱子节要》掇取朱子《近思录》大指,择其精粹,在明清之际的江南士人中广泛流播。
东林书院传承儒家的经世理念,其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明东林学子的心志。高攀龙彰明程、朱的“居敬穷理”,阐明“穷理尽性”之旨,又指出,“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所以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为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5)高攀龙:《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东林书院志》卷五,上册,第89页。这显示了东林学者的社会关切。万历三十二年(1604),东林书院建立后,江南士人闻风而起,金坛的志矩堂、宜兴的明道书院、常熟的虞山书院、桐城的崇实书院等均请顾宪成、高攀龙前往讲学,书院间密切往返交流。有论者认为,明末形成了以无锡东林书院、江西江右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为中心的全国性书院网络,而东林书院又发挥着主导作用。(6)参见[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第149—162页。但东林党人惨遭宦官魏忠贤镇压后,东林书院仅存瓦砾,而后东林弟子“日趋书院旧址讲习不辍”。(7)张夏:《黄日斋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53页。崇祯年间,书院得以修复,“虽未获复旧观,而仲丁释菜,历数十年不废”。(8)高世泰:《施旷如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59页。书院也成为明末士人的精神寄托。
清初东林书院一度衰微,而高攀龙的从子高世泰(1604—1676,字汇旃)成为重兴书院讲学的关键人物。他少侍东林讲席,高攀龙“即以道器许之”。高世泰于崇祯十年(1637)成进士,授礼部主事,随后奉命主广东乡试,曾任湖广按察使司佥事、提督学政,期间修复濂溪书院等,编纂三楚文献,刻《楚衡述风》一书,崇祯十六年(1643)任满回籍。他认为明清易代与东林书院的兴衰密切相关,“讲学盛衰遂与国运盛衰相始终”。(9)陆世仪:《论学酬答》卷前“高世泰原序”,《续修四库全书》第9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67页。故在顺治十二年(1655)主持修复东林书院的道南祠、丽泽堂,又捐赀建燕居庙及三公祠,以延续东林学脉。他笃守朱子及高攀龙之学,尤以朱子《大学格物补传》为要领,指出,“舍格物而单提良知,终非圣门之正的,为其与致知在格物之旨不符耳”。(10)熊赐履:《高汇旃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68页。
高世泰于顺治十二年(1655)重开东林讲会,申订规则,定于“每年春秋上丁日开讲”,“依古礼三斋七戒之期,为十日讲习之实”。据载:“维时四方之来游者,云集响应,无异曩时。迄今春秋释菜,俎豆依然。几十年来,寒家罔敢或替,皆守先学宪之遗训也。”(11)高廷珍等编:《高汇旃先生申定讲会规则·跋》,《东林书院志》卷二,上册,第33—34页。高世泰主讲东林书院三十余年,建止水祠祀高攀龙,并纂辑《高子节要》等书,“孳孳焉笃守忠宪之道,以待后之学者”。(12)熊赐履:《高汇旃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68页。有论者考察皖南的紫阳、还古书院时认为,清初书院会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民间理学士人之间的会讲;另一种则是民间理学士人与理学官僚之间的会讲。”(13)朱昌荣:《清初程朱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8页。东林书院不仅二者兼有,且规模较大。高世泰曾作“再得草庐”诗,有朋友和诗云:“道南方启君家派,学北欣观大国风。廿载孤蓬谁汉节,千秋衰草尽吴宫。虽嗟一线如丝缕,私淑几希正未穷。”(14)张能麟:《再得草庐和韵》,《东林书院志》卷一八,下册,第750页。这是他在清初修复东林书院,重兴讲学的写照。高世泰与祁阳刁包、休宁汪学圣、关中李颙等交往论学,也对后者的学术倾向有所影响。
无锡张夏少时师事明末东林学者马士奇,潜心理学,以朱子为宗,排斥王学。清初他与高世泰等讲学东林,“每竖一议,必原本六经,参以心得,往复回环,极尽理趣”。巡抚汤斌曾在东林书院会讲,赏识张夏治学,“延至吴郡学宫讲《孝经》《小学》”。时人谓东林“三十余年讲席不尽废者,以先生为鲁灵光也”。张夏治学笃守“居敬穷理”,编著《洛闽源流录》,将明儒分为“正宗”“羽翼”“儒林”三等。列入“正宗”者都是程、朱一脉人物,陈献章、王阳明等人则贬入“儒林”,表明其学术取向。(15)秦松龄:《张菰川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二,下册,第513—514页。张夏又著有《五经四书述》《朱解孝经问业》等书,大体阐发朱子之学。
此外,高世泰的堂侄高愈,十岁读高攀龙遗书,有志于圣贤之道。平生不好帖括文字,功名止于诸生。他每日研习儒经及程、朱性理之书,尤深于《周礼》,与从游者顾栋高等讲说经义,常娓娓忘倦。张伯行抚吴时,延请其主东林讲会,因病只能不时参与。他为学“务躬蹈力行,不尚议论”,著有《小学纂注》等。(16)秦缃业等纂:《无锡金匮县志》卷二一《儒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369页。当时“县中人好以道学相诋諆,独于紫超,佥曰‘君子、君子’云”。乾隆中,督学尹某“以小学取士,颁行其书”。(17)彭绍升:《高先生愈传》,钱仪吉编:《碑传集》卷一二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版,第929册,第6091页。
东林书院在顺、康、雍时期历经数次修葺,成为当地传播理学的中心。比如,高世泰的同年进士、无锡人胡慎三,明末曾在江西、福建等地为官,著有《圣学源流录》。顺治十年(1653),他与高世泰等讲学东林,以高攀龙的著述教学。无锡人严瑴,明末诸生,自谓“读书以理学为主,吾自得《高子遗书》,方知有归宿处”。清初,他不再参加科举,而“惟理学是究”。他在东林书院讲学,被高世泰推为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记》,又相与辑《高忠宪公年谱》《高子节要》《东林志》诸书”。(18)龚廷历:《严佩之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二,下册,第482页。
康雍年间,江苏地方官汤斌、宋犖等人“视学讲道必于东林”。于是,“东林之光焰浩浩煜煜,炳耀宇宙。无论豪杰之士,感愤激发,下至屠沽负贩,莫不抵掌摹绘。群喜群愕,艳称东林遗事者”。(19)任兰枝:《东林志序》,《东林书院志》“东林书院志序跋”,上册,第2页。有的官员后来且认为,“东林盛衰”“系于道统”。(20)胡慎:《东林书院志》,《东林书院志》“东林书院志序跋”,上册,第10页。事实上,东林书院的理学脉络不囿于苏南,还延伸到江南数省,波及北方。
东林书院与江南理学传衍
江南民间理学家的学思虽不尽同,却不能忽视东林学脉的影响。鼎革之后,东林书院与皖南书院的关系更为密切。清初皖南学者纷纷游学东林,使之与歙县紫阳书院、休宁还古书院间频繁交流。从学于高世泰的休宁汪学圣有诗云:“愿学生平孟是随,而今仰止赖吾师。庐成人醉春风里,草绽予惭夜雨时。”(21)汪学圣:《再得草庐和韵》,《东林书院志》卷一八,下册,第752页。之所以如此,盖因汪氏早年参究禅宗二十余年,闻高世泰“讲道东林,野服造门”。高氏告知“阐发程、朱,是为正宗,厌薄程、朱,是为乱宗”,“留语数十日,而学圣遂悟从前所学之非”。此外,皖南学者“汪知默、陈二典、胡渊、汪佑、吴曰慎、朱弘、施璜辈讲朱子之学于紫阳书院,因汪学圣游(高)先生门,相次问学”。(22)熊赐履:《高汇旃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66—467页。
歙县吴曰慎少时以文名,家贫而好理学。闻高世泰讲学东林,因往游学。“从东林诸君子后,虚心请益,研求下学上达之旨。析疑问难,时出谠论。”他回皖南后,“益向学紫阳、还古两书院中,会讲不辍”。他与胡渊、施璜等人长期在紫阳书院、还古书院讲习程、朱理学,遵循白鹿洞书院学规。吴氏读濂、洛、关、闽之书终身不倦,精研《近思录》及“四书五经”,治学强调“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著有《周易粹言》《大学章句翼》《中庸章句翼》等书。论者谓康熙以后“紫阳、还古之间,学者郁起,知所指归,先生汲引之力居多”。(23)施曾:《吴徽仲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二,下册,第502、503页。就清初皖南学术来看,所谓“知所指归”大体是指独尊程、朱的取向,还古书院由崇陆、王而转尊程、朱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
休宁施璜初为举业,在歙县紫阳书院听讲后,心向理学,遂弃举业,专心读书讲学。康熙十一年(1672),施璜负笈东林,以高世泰得高攀龙家学渊源,遂师事之。他“登东林讲堂,慨然有吾道复兴之志”。高世泰雅重之,“每会辄推为祭酒”。施璜治学修身极重“诚信”二字,著有《思诚录》《五子近思录发明》等。据载,他辞归后曾与高世泰相约某年月日再来会讲。将届期时,世泰设榻以待,有人说,两地遥隔千里,施君未必如约。高世泰说:“不然,施生笃行君子也。如失期不来者,君不复交天下士矣。”“言未竟,先生果携其子担囊而至。”(24)秦源宽:《施虹玉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二,下册,第506—507页。施璜长期主讲紫阳、还古书院,为皖南理学的主要传播者,其祭孔文有云:“自道之南,有此东林。群贤踵接,循宋迄今。高忠宪氏,再造功深。犹子世泰,国宝家琛。”(25)施璜:《祭告先师孔子文》,《东林书院志》卷一七,下册,第691页。于此可见东林学脉在施璜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施璜卒后,东林同人公举祀于道南祠。
此外,游学东林书院的皖南新安学者汪璲,少遭丧乱,家道中落,而治学不懈。他深于《易经》,注重阐明《易》理,贬置象数,主张《易》学当于平实切近处用功,著《读易质疑》等书。熊赐履称其“辨志既勤,卫道复力。立言端以洛、闽为宗,而其才足以发明之”。汪璲中年以后以高世泰等人为师友,晚年归里讲学。高世泰赠诗云:“游吴握手皆奇士,还里论心有硕儒。”时人认为“盖纪实也”。(26)陈鹏年:《汪默庵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二,下册,第504页。
东林书院对江、浙学者同样有所影响。太仓陆世仪(1611—1672)较早转宗程、朱,对顾宪成、高攀龙的气节和学术推崇备至。他认为在王学之后,顾氏“能以性善之旨破无善无恶之说,小心二字塞无忌惮之门”,“可谓豪杰之士”。(27)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版,第297页。他指出:“或以忠宪偏于气节者,非也。圣贤立身行事,只是因时而起……忠宪之气节亦因乎时而已,于学问何加损哉!”(28)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298页。他还认为,顾、高等人使“孔、孟、程、朱之正学焕然复明”。(29)陆世仪:《高忠宪公年谱序》,《桴亭先生集外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页。他赞同朱子“理先气后”说,阐述宋儒的性、命、理、气等主题,认为“居敬穷理在圣人为一贯之学,在学者为入德之门,即此下学,亦即此上达,初无有二”。(30)陆世仪:《论学酬答》卷二《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气才情问》,《续修四库全书》第946册,第81—82页。陆氏拒不仕清,甚至拒绝地方官的讲会之请,但“顺治十五年(1658),应学政张能麟聘,为辑《论学酬答》《儒宗理要》《治乡三约》等书。十七年应诸生请,讲学东林。康熙五年之讲毗陵,既又归讲娄中”。(31)江苏研究社编:《江苏乡贤传略初稿·陆世仪》,江庆柏主编:《江苏人物传记丛刊》第1册,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72页。他与陈瑚、江士韶、盛敬等人共倡程、朱理学,人称“太仓四先生”。“闻风亲炙者,皆感动奋发”,门人私谥为尊道先生。(32)王祖畬等纂:《太仓州志》卷一九《人物三·陆世仪》,《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1273页。全祖望曾谓,清初儒者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最有名,而陆世仪“少知者,及读其书,而叹其学之邃也”。(33)全祖望:《陆先生世仪传》,钱仪吉编:《碑传集》卷一二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版,第929册,第5966页。
类似学者,不一而足。如吕留良(1629—1683)自云“幼读朱子集注而笃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34)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潘用微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3册,第319页。吕留良极重华夷之辨,曾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的博学鸿儒之荐,以行医及授徒为生。他与黄宗羲、黄宗炎、高世泰、施闰章、陆世仪、高旦中、何商隐、施璜等学者游,自称“足迹不越江南,交游不及名位。荷锄村畦,穿穴故纸”。(35)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戴枫仲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3册,第329页。综上可见,东林书院作为清初江南复兴、传播理学的重镇,与著名理学人物交往频繁,也对江南学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东林书院与北方名儒
清初中州、关中的理学家孙奇逢、李颙也与东林书院密切相关。从学术上看,孙、李长期带有王学色彩,不似清初东林学者完全取法程、朱,但不宜如有的论著那样看作王学宗师。他们的本体论仍有王学烙印,而涵养功夫多遵循程、朱,可谓宗程、朱而兼容陆、王。他们从陆、王转重程、朱的过程中,曾受东林理学传统的启发。
孙奇逢(1585—1675),直隶容城人。年十七举于乡,居京师,与鹿善继、周顺昌、周起元、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交好,自称为高攀龙、顾宪成的私淑弟子。天启末年,魏忠贤擅政,左光斗等被诬坐赃,奇逢与鹿善继之父鹿太公为左光斗等募金营救。事虽不果,但表明他对东林党人的气节推崇备至。针对清初非议东林党人的说法,他指出:“阴晦之时,孤阳一线,则东林实系绝续之关。乙丙死魏逆诸臣,甲申殉国难诸臣,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乎?……泾阳之气魄精神度越诸子远矣,岂向俗儒曲学问毁誉、定是非者耶!”(36)孙奇逢:《理学宗传》卷一一《顾端文公》,《续修四库全书》第514册,第401页。孙奇逢屡被清初地方官荐举、征聘,皆不出,继承了东林学者的精神传统。
顺治七年(1650)后,孙氏移居河南辉县,在苏门夏峰村讲学25年之久。孙氏早年“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37)方苞:《孙征君传》,钱仪吉编:《碑传集》卷一二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3辑,第929册,第5985页。主张“学以圣人为归,无论在上在下,一忠于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38)孙奇逢:《理学宗传叙》,《理学宗传》卷前,《续修四库全书》第514册,第205页。康熙五年(1666),孙奇逢撰成《理学宗传》,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11人列为宗传人物,详述其学行;其余从汉代以至明代数十位儒家人物,则入“补考”简介。可见,其理学系谱虽然兼容程、朱和陆、王,但在清初最先确立了顾宪成的理学地位。孙奇逢认为顾宪成的著述“开豁洞达,晰义甚严,而持论甚正。评人处不狥不刻,自是迩来诸儒之冠”。(39)孙奇逢:《夏峰集》卷五《读十一子语录书后·顾文端》,《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册,第453页。孙奇逢治学以理为本体,归宿于以程、朱修正陆、王,他宗奉程、朱的主敬说,故有针对“道本于心”的说法云:“心何以得也……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惟敬始能凝聚此理于心而无所放逸。”(40)汤斌:《清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5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影印本,第16页。他不像顾、高那样从本体论上区分朱、王之学,但内圣功夫则与东林学者大致相同。故刁包收阅孙氏书后,表示:“不肖敬信如神明,乃知洙泗、濂洛之传近在咫尺”,并期待有“笈游立雪时”。(41)刁包:《用六集》卷一《答孙容城征君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册,第433页。
孙奇逢讲求躬行实践,一生笃学力行,又享高寿,故海内仰宗数十年。他不反对弟子出仕,其及门弟子百余人,不仅包括民间理学家费密、耿极等人,还有后来入仕清廷的魏裔介、魏象枢、汤斌、耿介、张伯行、崔蔚林。其中魏裔介、魏象枢独尊程、朱,而汤斌、崔蔚林长期倾向王学。孙奇逢曾规劝崔蔚林:“子嗜阳明,须知阳明与程、朱相剂为用,非有抵牾也……若存一说废一说,是有春夏而无秋冬矣。”(42)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一一《师儒传二·夏峰弟子》,天津徐氏1912年刊本,第17页。崔氏的王学偏好一直未变,一定程度上招致了康熙的贬黜。尽管如此,孙氏门生中的理学官僚仍是传播程、朱之学的重要媒介。汤斌评论:“今天下理学烝烝而起,诐行淫辞之习渐以消磨,谓非先生倡率鼓舞而然欤?”(43)汤斌:《汤子遗书》卷三《征君孙先生九十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2册,第322页。“二魏”、张伯行等人将夏峰之学引入朝廷,使之引起康熙帝注意,彰显了孙氏的学术影响和地位。
关中学者李颙(1627—1705)17岁读冯从吾的《冯少墟先生集》,恍然有所得,被人称为“少墟高弟”。冯氏为万历十七年(1579)进士,曾从学于顾宪成,是明末关中书院的中心人物。他视讲学为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谓“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讲学者,正是讲其所以躬行处”。否则,“躬行君子终未之有得矣!”(44)冯从吾:《少墟集》卷七《语录·宝庆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版,第142页。他和东林书院声应气求,与顾、高二人及钱一本被称为“东林四君子”。冯从吾批评佛老为异端之学,又针对陆王心学云:“吾儒论心都不曾丢过理字,若丢过理字可以言心,则先儒之说皆诬。”(45)冯从吾:《冯少墟集》卷一《辨学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3册,第8页。高攀龙称赞冯从吾学问好,“是吾儒之极纯者”。(46)高攀龙:《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东林书院志》卷五,上册,第93页。据载,明末“都御史邹元标、冯从吾等建首善书院于京师,攀龙时与讲会,被目为朋党”。(47)江苏研究社编:《江苏乡贤传略初稿·顾宪成高攀龙与周顺昌》,江庆柏主编:《江苏人物传记丛刊》第1册,第44页。高攀龙曾致书东林学友:“连日会冯少墟,云我辈除却锻炼心体,更无别事,其言简而尽矣。”(48)高攀龙:《东林在会诸友》,《东林书院志》卷一七,下册,第678页。受冯氏影响,李颙仰慕高攀龙的风节,“每遇吴人,即访其履历之详及所著书,而卒无从得”。(49)高廷珍:《轶事一·东林轶事》,《东林书院志》卷二一,下册,第806页。这些言行无疑反映双方的情谊和学术认同。
李颙于康熙九年(1670)冬受常州知府骆钟麟之请讲学江南,期间特意拜谒忠宪公祠,与高世泰会晤并在东林书院会讲。讲学中,高氏阐明朱子“习静不如习敬”之旨,李颙完全认同,并指出“是敬乃工夫,非本体也”。高世泰又云:“言满天下无口过”者,只有朱子;“六经皆我注脚”,是陆九渊之口过;“满街都是圣人”,是王阳明的口过。李颙认为,朱子之言“粹乎无瑕”,而陆、王之言“犹药中大黄、巴豆,疏人胸中积滞,实未可概施之虚怯之人也!”(50)李颙:《二曲集》卷一一《东林书院会语》,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5—98页。可见高、李尊朱抑王的倾向大体相同,唯李颙对陆、王仍有几分肯定。据载,李颙“临别尤以会讲切磋,兴复东林遗绪三致意焉”。二人会讲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51)秦松岱:《梁溪应求录跋》,李颙:《二曲集》卷一一,第102页。李颙将高世泰之言“语其从游,谓宜奉为典型”。(52)熊赐履:《高汇旃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67页。在学术交往中,东林之学对李颙不无启示,对其转重朱子学有所推动。李颙晚年以朱学救王学之弊,其《四书反身录》主要阐发宋儒《四书》学主旨,“以理学倡导关中”。(53)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李颙》,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页。他倡导“明体适用”之学,而其“悔过自新”说皈依于程、朱,尤重朱子的“居敬穷理”。他认为:“‘穷理’即孔门之‘博文’,‘居敬’即孔门之‘约礼’。内外本末,一齐俱到,此正学也,故尊朱即以尊孔。”(54)李颙:《二曲集》卷一五《富平答问》,第126页。这方面大体契合东林书院的理学取向。
直隶祁州人刁包(1603—1668),天启朝举人,早年治学不分程朱、陆王而讲求“吾日三省吾身”,初闻孙奇逢讲王阳明良知之学,心向往之。顺治十五年(1658)读高攀龙遗书后,数十年疑团涣然冰释,大喜曰:“不读此书,几虚过一生,遂为主奉之。”(55)彭绍升:《刁先生包传》,钱仪吉编:《碑传集》卷一二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3辑,第929册,第5958页。后以私淑弟子礼祭祀高氏,“塑望焚香展拜,或有愧心惰行,必稽首自责”于位前。在刁包看来,高攀龙“为濂、洛、关、闽之后一人而已”。他以未能从学于高攀龙为憾,又致书高世泰,“敬伸北面之忱,愿敦异世之好”。(56)刁包:《用六集》卷四《与高锡山学宪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册,第476页。刁包在著述、书信中推重顾、高二人的理学见解,又辑《辩道录》四卷,汇集罗钦顺、顾宪成、高攀龙、冯从吾四人的辩学言论。在他看来,四人都是辩明朱、王之学而传承宋儒正学的人物,高攀龙不当谥为“忠宪”,当用“文正”易名,与罗钦顺一起从祀孔庙,(57)刁包:《用六集》卷二《答孙北平少宰书·其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册,第450页。是为儒家道统的标志性人物。
刁包与孙承泽、魏象枢“缔为神交。各以所得遥相质正。每有疑义,必往复辨论,不苟雷同”。(58)高廷珍:《轶事二·诸贤轶事·刁蒙吉先生》,《东林书院志》卷二二,下册,第903页。刁包强调“天下莫大于穷理”,“舍穷理而言致知”,“又安有入手时哉!”(59)刁包:《用六集》卷四《答王介祺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册,第481页。像程颐一样,他重视“穷《春秋》之理”,撰有数篇《春秋》“书法论”。他赞同朱子“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二语,认为“静坐,所以居敬也。读书,所以穷理也。两者内外夹持,而天命之性庶几旦暮遇之矣!”(60)刁包:《用六集》卷四《与杨光起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册,第485页。刁包于“居敬穷理”缺少新见,其“性善论”也与宋儒及顾宪成、高攀龙无异,不过,他有关历史人物的论说不乏己见。尤有价值的是,他于顺治十八年(1661)提出:士子“往往以有用之精神,耗敝于无用之八股……欲求真学问,其可得乎?”针对废八股文将导致儒经消亡的说法,他认为:“八股,小技也,假借四子五经以为文,而其名始存;四子五经,大业也,附会八股以为题,而其实始亡……一存一亡,势不两立,是安可以不议变易乎哉!”(61)刁包:《用六集》卷一一《废八股兴四子五经说》,《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册,第573页。他深刻认识到八股文对经学的危害,反对士人沉迷于科举八股。这种认识在清前期乃至19世纪都不失为真知灼见。刁包病逝于康熙八年(1669),次年高世泰等具呈无锡县令,将其从祀东林道南祠。
崇祯四年进士孙承泽(1592—1676)曾入仕清朝,顺治十年归田后隐居京郊。他与东林党人的政治态度不同,却是东林理学的传播者。他重视阐明儒学道统,著《道统明辨录》,对宋五子,尤其是朱子的经注及性理主题多所阐发。像高攀龙一样,孙氏笃信儒家思孟学派的性善论,认为发于舜、汤的“心传”道统,至孔子而详尽,即“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祖之,则曰性善,则其旨已洞达而无余蕴矣。”(62)孙承泽:《藤阴札记》,《续修四库全书》第944册,第43页。他阐扬高攀龙之学,认同其对阳明学“病虚”的批评,指出:“不言性善而言无善无恶,不言知能并重而偏言致良知,不师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师心自用之陆子静,近世学乱于虚也,实始于文成矣!”(63)孙承泽:《藤阴札记》,《续修四库全书》第944册,第50页。孙承泽对陆、王表现了鲜明的排斥立场,也赞同罗钦顺对王阳明《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的驳斥,认为“此忠告也,而阳明不受也”。(64)孙承泽:《藤阴札记》,《续修四库全书》第944册,第62页。孙承泽与刁包等人交游论学,也对清初魏裔介、魏象枢等理学名臣产生了影响。孙承泽卒后,魏裔介致书无锡地方官,“谓北海先生之学,其得忠宪高公之统者也,于是锡邑后学群举而入道南祠”。(65)钱肃润:《孙北海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二,下册,第489页。
此外,北方名儒与东林书院交游者还有不少。山西范鄗鼎于康熙六年(1667)成进士后隐居不出,所辑《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汇集辛全、孙奇逢、熊赐履、张夏、黄宗羲诸家理学史精要,辨明理学脉络,兼容程、朱、陆、王之学。(66)关于范鄗鼎纂辑《明儒理学备考》及《国朝理学备考》,参见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第八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66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撰书过程中曾与魏象枢、党成等人“往复讨论”,也得熊赐履、张夏、陆陇其等人推许。张夏谓其“辨论取舍,直是程、朱复生”,一时朝野讲学君子,莫不走字商榷,奉为吾道干城”。(67)范翷:《先征君墓碣记》,范鄗鼎:《五经堂合集》次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1册,第314页。
康熙中叶以后,清廷已注意到民间理学趋向,虽不能如愿诏征绝大多数在野学者,而朝野间的学术交流并未隔绝,东林书院则是顺康年间影响理学官僚的学术渊源之一。
东林书院对理学官僚的影响
清初东林书院与理学官僚的关系复杂而密切。修葺东林书院得到理学官僚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康熙中,巡抚汤斌亲诣会讲,尚书熊赐履、巡抚宋犖、学使许汝霖倡捐缮治,复重建依庸堂。”知县董其事,“悉复旧观”。(68)秦缃业等纂:《无锡金匮县志》卷六《学校》,《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15页。但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后,江苏学政发布了整顿书院的告示:为防避“意见横生,是非蜂起”,强调书院“务延真诚学道之儒”来讲学,“宁朴毋伪,宁质毋华”,摒斥“党同伐异之辈”;学徒则“咸宜各备实心”,开口时“莫争朱、陆”,而应“入孝出弟”,“主敬致知”。(69)《整饬书院檄文》,《东林书院志》卷一四,下册,第577页。显然,官方学者在认同东林书院的理学传统时,又严禁明末士人的党争风气。在此背景下,康熙中期以后的东林书院无疑受到一定限制。而在顺治及康熙初年,东林书院对理学官僚的学术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魏裔介(1616—1686)自云早年读宋儒书“味如嚼蜡”,顺治初年才觉得“字字皆性命之奥,孔孟之蕴也”。(70)魏裔介:《静怡斋约言录》外篇,《续修四库全书》第946册,第136页。这种转变实与东林同道孙承泽不无关系。尊崇顾宪成、高攀龙之学的孙承泽著《考正晚年定论》,否定王学。魏裔介曾从孙氏问学,读其书“不胜叹服”,也撰有《王阳明之学是非辩》一文,否定王氏“良知”说,谓其“非圣人之学”。(71)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一四《王阳明之学是非辩》,《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册,第61页。魏裔介善读宋人书,张烈尊朱辟王,“其端皆自(孙)先生发之”。(72)高廷珍:《轶事二·诸贤轶事·孙北海先生》,《东林书院志》卷二二,下册,第908页。因其学术渊源,魏裔介认为顾宪成不仅气节高尚,而且“理学足以发圣贤之蕴”。(73)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二《小心斋札记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6册,第244页。魏裔介晚年撰《圣学知统翼录》,起自伯夷、柳下惠,下迄顾宪成、高攀龙,将顾、高纳入上接程、朱的道统,而二书均将王阳明排除在外。事实上,他推崇顾、高之学,谓顾宪成讲学,“阐明性善、气质之说,深辨无善无恶之谬,虽其议论亦时有出入之疵,然认的性字明白”。(74)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二一《圣学知统翼录·顾宪成》,《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册,第275页。而高攀龙主张治学由格物而入,认为“穷至事物之理,穷至于至善处也”。魏裔介指出:“观此,则先生博学笃至,切问近思,而无近日学者之失,可知矣!”(75)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二一《圣学知统翼录·高攀龙》,《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册,第276页。他曾致书高攀龙之子:“阳明见道未真,遂流于虚浮……而泾阳辟之尤力。忠宪公资学清淑,自当继文清之后。私心窃慕,无日忘之,况通家谊重乎!”(76)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一六《答高忠宪公长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册,第102页。可见魏氏重视东林学脉。魏裔介的同年进士魏象枢(1617—1687)不像魏裔介那样表现出对顾宪成、高攀龙的崇拜之情,却维护了东林书院的学脉和讲学传统,认为所谓“理学以东林为鉴”的流言,将“遗臭万年”。他指出:“既欲做人,便欲明理;既欲明理,便欲讲学;既欲讲学,便欲交正人君子……东林之人,今日如生;东林之言,今日犹芬。”(77)魏象枢:《寒松堂全集》卷九《答左翼宸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册,第546页。推重东林学术传统于此可见。
熊赐履(1635—1709)官至尚书、大学士,既传承家学,根本上又直承东林书院之学。其父熊祚延少时补博士弟子,推崇曾子传圣人之道,编《希曾录》,又作《弘毅解》篇。“自经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礼制、乐律,一切经济书,靡不洞悉原委。”(78)钱肃润:《熊祈公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69页。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司佥事、提督学政时,“修复岳麓书院、石鼓书院与濂溪书院,并行课艺,理学文章,卓然为一时文衡之冠”。(79)高廷珍:《轶事二·诸贤轶事·高汇旃先生》,《东林书院志》卷二二,下册,第905页。熊祚延以高氏为东林嫡传,遂携其弟熊祚永入濂溪书院受业,为高氏入室弟子,“精研《高子遗书》,得东林先贤洛、闽一脉”。(80)钱肃润:《熊祈公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70页。故熊赐履云:“先公受知实最深,尝拔置濂溪书院,命主讲席。先公感先生之教,遗训家庭必毋忘东林一脉。然则先生之教思不私吾楚,而吾楚之被泽亦弘且远矣。”(81)熊赐履:《高汇旃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68页。熊祚延曾将《高子遗书》授赐履,并曰:“东林为道学正宗……儿曹能服膺是编,便是圣贤路上人也。”赐履“嗣后历官禁近,诸所讲述,一本东林旨趣为宗”,为圣祖讲《大学》《中庸》,“每发一言,上未尝不点首称善”。(82)高芷生:《熊敬修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二,下册,第497页。熊赐履晚年作《学统》一书及《闲道录》,时人认为是阐明其父之学也。(83)钱肃润:《熊祈公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一,下册,第470页。此说或许不无夸张,但熊赐履独尊程、朱而又注意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可谓继承父志。
熊赐履早年随高世泰研习理学,后世视为“世泰之徒所成就者”。(84)徐珂编撰:《无锡学派》,《清稗类钞》第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84页。熊氏又与执教东林书院的钱肃润等交游。钱氏学古穷经,多有诗文。熊氏少时即知其名,后来“书问不绝,时时以近著见示”。他认为,钱氏学宗程、朱,讲求“存诚主敬”,东南士子多“愿得及于其门,而东林、扶风两书院坛席尤盛”,道南梁溪之绪因之一振。(85)熊赐履:《经义斋集》卷四《钱础日七十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9册,第99页。钱肃润所编《文瀫初编》将熊赐履的《遵谕陈言疏》置诸卷首,谓其“事事本帝王之治,事事本圣贤之学,而其心惟以正心诚意为主,故所言具见本原”。(86)钱肃润辑评:《文瀫初编》卷首《遵谕陈言疏·识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73册,第22页。
康熙二十六年(1687),有感于讲学常遭“时君时相之怒”,熊赐履明确指出:“讲也者,讲明所以为圣为贤之理,俾知所从事也。”“讲学一事,顾可以终废乎?是盖有道矣!”如今讲学盛行,“此诚斯道昌明之一大机会也。则愿吾党有识之士,以默识为真修,以笃行为至教,勿口舌轧击以矜能,勿意见纷挐以长傲”。(87)熊赐履:《经义斋集》卷五《重修东林书院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9册,第102、103页。宋犖任江苏巡抚时,又修葺东林书院,时任吏部尚书熊赐履捐银支持。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高世泰之子高芷生及东林后学秦源宽、高嶐等人呈请无锡县令,并经江苏巡抚张伯行批准,以熊赐履入祀道南祠。
少无师承的汤斌(1627—1687)早年泛览诸家,后得孙奇逢等人启发,经“反复审择,知程、朱为吾儒之正宗”。(88)汤斌:《汤子遗书》卷四《答陆稼书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2册,第367页。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出任江苏巡抚后,三至东林书院,支持修葺书院。尤其是二十五年四月,汤斌以礼部尚书内招北上,途中驻节东林书院,“先谒道南祠,悬‘伊洛正宗’匾额,香案设供,行四拜礼。旋登讲堂,拜燕居庙,坐再得草庐。是时官僚云集,府厅县学及远近绅士皆来观礼”。针对当时入祀道南祠学者名单的纷争,汤斌批示:原祀道南祠者,皆传杨时之学的门人,“顾、高诸先生皆兴复东林,同堂讲习,其祀于东林固宜”。但启、祯以后东林党人遍天下,“而与书院无与也”,故不当入祀。“游此地者,要当讲求龟山、端文、忠宪之学”,而不必“启门户之争可也”。(89)高廷珍:《轶事一·东林轶事》,《东林书院志》卷二一,下册,第807—808页。汤斌区分了东林学者和东林党人,赞同发扬东林理学传统,主张摒弃党争习气,代表了理学官僚的基本主张。
康熙九年进士陆陇其(1630—1692)久任知县,为官清廉,其《三鱼堂文集》等书均立足于独尊程、朱,而指斥阳明学外儒内禅。他认为,朱子“所谓诚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为诚正,亦就处事接物之际而诚之正之焉耳”。(90)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四《读朱子白鹿洞学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7册,第357页。这表明他与东林书院的讲学内容不无差异,故在他看来,顾、高的心性之学未脱王学樊篱,非朱子正脉。对此差异,一般论者多所注意。不过,钱穆认为陆氏所辨“似严而实妄。若论朱子正脉,则其学必求体大而思精……高、顾东林讲学,意欲挽王返朱,其所以纠王之失而求重发朱子之是者果何在。能从此发明,则朱子正脉益张,而王学之与东林,要皆非无所取。何事乎坚立门户以拒人,必取正脉于一线乎?”(91)钱穆:《陆稼书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127页。钱穆不认同陆氏“朱子正脉”的狭隘观念,可谓一语中的。不过,陆氏的真实意图不在贬评东林,而是针对清初的阳明学余波。他曾致书汤斌,强调“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92)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五《上汤潜庵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7册,第377页。这也蕴含规劝汤斌摒弃王学之意。事实上,陆陇其也承认,明代的薛瑄、胡仁居、曹端、罗钦顺,“朱子之正脉也,此外则阳儒阴释之学,创为新说,叛道离经。梁溪顾泾阳、高景逸起而正之,为功于学者甚大”。(93)王材任:《陆稼书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二,下册,第500页。显然,他仍肯定东林学者复兴理学之功。故在复兴理学方面,陆陇其与东林书院可谓同道,只是后起的陆氏在独尊程、朱的轨道上走得更远。他自称官江南时,“时与东林过从,知祁州有刁蒙吉先生者,介节士也……予之所尝服膺于先生者,一如先生之于梁溪也”。(94)陆陇其:《刁文孝先生生平事实记》,《用六集》“附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册,第417—418页。康熙二十九年(1690),居官御史的陆氏为刁包入祀道南祠亲撰“生平事实记”,从侧面反映了对东林学术的认同和置重。
此外,素慕陆陇其之学的理学官僚张伯行也重视东林书院。康熙四十六年(1707),张伯行以江苏按察使赴福建巡抚之任,四十九年移抚江苏。“首葺东林书院,躬诣讲学,剖析朱、陆异同,娓娓不倦”。其后,无锡士人请于江苏巡抚,将其“从祀书院之道南祠”。(95)华希闵:《张孝先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一二,下册,第511、513页。这些看似与东林书院比较疏远实与东林书院仍有某些学术关联。
清初理学官僚在独尊程朱的取向、践履理学的途径、彰明道统等方面,曾受民间学者启发,而东林书院是其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源头。而这些理学官僚自顺治年间就反复疏请开经筵、刻经书,推动清廷建立了以程、朱为根本的庙堂理学。
结 语
清初理学家大体缺少学理的创新,其重兴理学的根本取径是阐发程、朱旧题,走出阳明学藩篱,或者调和朱、王,重释其本体论和修身工夫。东林书院的学术成就不像黄宗羲、孙奇逢、李颙等人引人注目,但其学术实践基本相同。当晚明王学盛行之时,顾宪成、高攀龙已开启“由王返朱”的趋向。鼎革之后,高世泰、张夏等人在东林书院倡兴程、朱理学,排斥王学,成为江南理学的重镇。北方名儒孙奇逢、李颙、刁包等人的学术转向也体现了东林学术的影响。清初民间理学呈现江南、中州和关中三个中心,是为不争之事实。而东林书院作为江南理学的传播中心,在顺康之际于理学有续绝兴亡之功,实为开先河的潜流。
清初,东林书院没有引起朝廷注意。清廷既认同民间理学,包括东林书院的理学传衍,却又忌讳东林党人遗风,并通过地方官修葺书院、亲临讲学等举措,将书院理学纳入官方轨道,防范士人结社。康熙中期以后,理学复兴的格局已经形成,理学官僚往往成为清廷双重政策的实行者。然而,参加东林书院会讲者既有李颙、陆世仪等民间学者,又包括熊赐履、汤斌、张伯行、陆陇其等理学名臣。后者会讲实际上有裨于朝野学术的交流和互动,东林学者借重于理学官僚刊刻宋儒著述,传播程、朱理学,对清廷尊崇理学的趋向不无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当时一般书院所不具备的。东林书院在清初理学格局中的地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