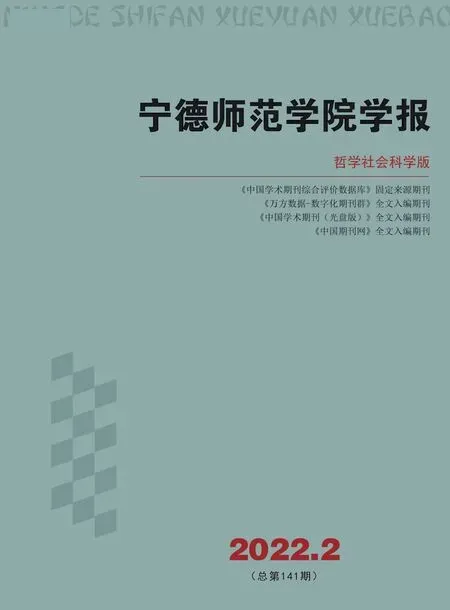从对渡文化到文化对渡 :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的历史记忆与当代使命
王振亮 邓丽娟 高晓丽
历史记忆代表着个体或群体对过去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累积,展现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印记。[1]历史记忆不仅仅是人类的心智活动,更是一种情感,它往往与认同紧密联系。王明珂认为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2]民俗体育的源起往往与特定历史息息相关,在岁月不断更迭中逐渐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3]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源于清初,每逢端午节,福建蚶江和台湾鹿港对渡船只都会在蚶江海边追逐泼水,人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互祝吉祥,交融情谊,祈求大家来年平安兴旺。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承载着两岸人无法磨灭的历史记忆,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见证。近年来,因“台独”分子的操弄,两岸交流面临困难,台胞对大陆原乡的文化认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台胞原乡文化认同逐渐式微。新时期,蚶江海上泼水习俗在形塑台胞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中发挥那些价值?在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又担当何种使命?构成了本研究的缘起。
课题组分别于2018 年6 月15 日至20 日,2019 年6 月3 号至8 号,2020 年9 月10 号至12 号,三次对蚶江古镇进行实地调查,对来福建蚶江镇参加海上泼水节活动的多位台胞、蚶江镇文化站站长林文裕先生、蚶江镇参与泼水习俗的多名群众等相关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并将收集的资料认真进行梳理,尝试运用记忆的视角探究答案。
一、记忆贮存: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缘起
蚶江古镇位于福建省石狮市北部,泉州湾南岸,海岸线长17 公里,扼泉州湾咽喉门户,因古代沿海滩涂产蚶而得名蚶江,蚶江镇现辖有19 个行政村,常住人口88507 人。[4]福建蚶江与台湾鹿港海上距离仅130 海里。蚶江早在宋元时期便是“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泉州)的门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5]清代,蚶江作为“泉州总口”,是大陆对台贸易的中心码头。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清廷因蚶江港所处位置重要,“乃移福宁府通判(俗称泉州海防府属正五品)官衙于蚶江青莞,封验巡防,督催台运暨近辖词讼,与台湾鹿仔港对渡。”[6]
(一)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源起的民间传说
传说是一个社会群体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公共记忆。[7]蚶江百姓口口相传,流传着一个关于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源起的传说:两岸通航,商人长期在海上漂泊,每到端午,五毒横行,瘟疫滋生,船上之人往往怪病蔓延,众人身上长满痱子和不知名的的脓包,奇痒无比,忍不住用手抓挠,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大家纷纷跑到海边放“王爷船”--祈求“王爷”保佑,有人不小心把海水溅到身上,说来奇怪,顿觉身上奇痒消失大半,遂自己弯腰从海上舀起一桶海水,从头上一灌而下,奇痒病痛更轻,随后大家相互泼水庆祝。于是就诞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蚶江海上泼水习俗。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历史记忆,这则传说不仅道出了两岸对渡人的苦难,彰显了闽台“王爷”的灵验,同时也包含了我国端午“恶月恶日”的民俗文化。
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认为:传说是一种虚构性的作品,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同时他也强调了传说的意义,认为传说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所以传说“不仅是当地民众的文艺作品,同时,也蕴含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8]两岸对渡,并非一帆风顺,暗礁、迷雾、疾病、海盗、极端天气随时可能导致船毁人亡。人们在苦难面前,求助神灵,寄托信仰;因此,“王爷信仰”在闽南和台湾地区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源起的民间传说无疑是两岸民众为了坚定“王爷”信仰而进行的美好想象,同时也暗含了历史上,两岸对渡之艰辛。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源起的民间传说经过两岸民众代代相传已经成为人们坚定的文化共识。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扬·阿斯曼所说:传说是这样一种历史,人们讲述它,是为了让自己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可以找到方向,传说是历史中被放大的部分,是被人们敬仰的部分,是获得了信仰力量的部分。[9]
(二)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源起的官方叙述
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离不开两岸对渡贸易的繁盛。在官方的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蚶江海上对渡的记载。康熙四十九年(1784 年),清政府“覆准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属之蚶江口与台湾府彰化县属之鹿仔港设口开渡”。[10]蚶江港东渡鹿港,航线最短。“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利之所在,群趋若鹜”。当时的蚶江港,专营台湾生意的商号不下数百家。[11]闽南商人把台湾的米粮、食糖、海货等产品运到大陆销售,把福建泉州等地的陶瓷器、家具、药材、茶叶、布匹、竺麻、金褚、烟叶则源源不断运往鹿港。[12]《石狮市志》记载:每年端午节蚶江港进入休整期,两岸对渡的船商要祭拜保护神“五王爷”,维修船只。大小船只尽回港洗船、补灰、画船等维修整理。有些船靠得比较近,洗船时水常常泼到别人身上,引来大家笑声阵阵,喜欢开玩笑的人则趁洗船时故意拿水去泼邻船的人,邻船的人也不示弱,提起水就反击,在洗船中大家互相泼水嬉戏,后来越来越多的船只加入到泼水嬉闹中,逐渐形成了端午蚶江海上泼水的习俗。
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官方叙述,它们的本质都是历史记忆。[13]传说与正史文献传达的历史在价值上是平等的。[14]蚶江作为“泉州总口”,商船林立的特殊环境为海上泼水习俗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华端午节传统习俗与闽台“王爷”信仰共同催生了蚶江“海上泼水”习俗,这是闽台两岸商贸密切联系的产物。每年的端午节,通过这场酣畅淋漓的海上泼水习俗,蚶江与鹿港两岸对渡的历史被一代一代的传承,闽台两岸地缘、商缘、血缘、神缘、俗缘等五缘关系不断被强化,正如我国民俗学家乌丙安在蚶江海上泼水节的的开幕式上所讲:“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是福建蚶江与台湾鹿港独一无二的对渡文化,两岸“对渡”其实是“共渡”,海峡两岸的人民,共渡一片海域,共度中华民族的节日,在危难面前两岸同胞共渡难关。”
二、记忆激活: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的消亡与复苏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开放厦门为通商口岸,蚶江港地位逐渐被厦门港所取代。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台湾被日本侵占,蚶江与鹿港对渡通商几近绝迹。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退守台湾,海峡两岸完全隔离。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信仰一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受到严厉批判,作为“五王爷”信仰仪式——“蚶江海上泼水习俗”被严厉禁止,流传近300 年的地方特色习俗——“蚶江海上泼水习俗”彻底消亡。
1986年10 月8 日台湾解除“戒严令”,两岸交流迅速升温,大批台胞来到原乡寻根祭祖,投资办厂。大陆侨乡为了吸引海外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往往通过传统民俗让远方的亲人有所皈依,一度蛰伏几近消失的传统习俗获得有力的刺激而开始复苏。[15]在此背景下,蚶江古镇从民间到政府积极行动,挖掘历史古迹,恢复优秀传统习俗。“对渡碑”、“五王爷府遗迹”、清代黄树珍的《自记年谱》、六胜塔、海关厘金遗址、鹿港行郊、台胞祖祠等一大批两岸对渡历史古迹、文献重现天日。古碑、族谱、古迹是两岸对渡历史记忆的重要文本,这些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为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的复苏打下坚实基础。蚶江鹿港对渡历史记忆被重新唤醒。
1988 年6 月28 日,蚶江民众为了纪念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205 周年,自发举办了规模盛大、别开生面的海上泼水活动。29 名鹿港台胞特地从台北经香港到北京,从北京到福州坐火车两天一夜,再从福州到泉州,最后再到蚶江古镇坐汽车又花费了7 个小时,终于在端阳日赶到蚶江共襄盛举。拍胸舞、公背婆、火鼎公、火鼎婆、大姑凉山、踩高跷、唆啰嗹等各种各样闽南特色民俗表演再次汇聚在蚶江古渡口,“五王爷”搭载“金再兴”号王爷船下水巡海……。
文化认同不是一种既存的状态,而是在对话、交流、融合中实现的过程。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的复苏不仅仅是一场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它不是回归到旧有的文本,而是通过对共享文化和历史记忆的重新调用,不断构建新的记忆文本。鹿港台胞克服重重困难来蚶江参加海上泼水习俗,本质上是台湾同胞眷念原乡故土、认祖归宗的寻根情怀,是闽台民众血缘亲、俗缘同的自然表现,是对蚶江泼水习俗背后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感,是加强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增强两岸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重要基础。
三、记忆传播: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的文化对渡
习俗穿越历史、见证历史,同时也激活历史、见证未来,从而使得“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16]“记忆传播并不仅是传递信息,还是传递一种特定的情感”。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承载着“两岸对渡”“王爷信仰”“端午恶月”等丰富的文化内涵,用身体活动再现历史的记忆,并成为鹿港台胞的原乡符号,具有强烈的情感感召功能,维系着鹿港台胞原乡文化认同。
(一)从原乡文化到“反哺”原乡
连横在《台湾通史》记载:“台湾原名埋冤,为福建闽南人所号。明代闽南人入台者,每为天气所虐,居者辄病死,不得归,故以埋冤名之,志惨也[17]。”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入台的先民们需要来自原乡文化的慰藉与精神支持,于是原乡的神灵、风俗、语言、建筑甚至原乡地名等纷纷被移植而来,成为台湾先民思乡怀祖的精神寄托。《鹿港奉天宫志》:“鹿港与蚶江对渡以来,出入船舶无数,往返两岸者商户频繁……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鹿港船户由蚶江打铁街五王府传苏府王爷之香火至鹿港,供于本宫……,端阳日,王爷巡海,鼓锣炮竹震云霄,大船小舟伴左右,竞舟戏水乐逍遥……”。[18]蚶江与鹿港,相同的村名,相同的端阳习俗,相同的王爷巡海,相同的竞舟戏水……,太多的相同,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血脉在台湾的延续,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蚶江是鹿港的原乡,福建是台湾的原乡,台湾主流文化属于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支系。
“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不良影响,很多传统习俗一度被看成“四旧”而被禁止。蚶江古镇的王爷神像、“金再兴”号王爷船、碑刻、匾额、典籍等统统被毁坏或焚烧,蚶江海上泼水等众多传统民俗活动也一同消亡。1988 年两岸恢复交流后,蚶江海上泼水习俗虽然部分恢复,但是两岸同胞欢喜之余又难掩失落。他们无法到“五王爷府”祈福,也看不到“金再兴”号王爷船巡海。没有“五王爷”金身,没有“金再兴”号王爷船,没有“神将”“狮阵”“宋江阵”等阵头护驾,蚶江海上泼水习俗就不算真正的复活。然而要想完全恢复中断近半个世纪的传统习俗又谈何容易。
两岸恢复交流之后,蚶江海上泼水习俗迅速从台湾地区获得“反哺”。1994 年,蚶江籍台胞林为兴捐资100 万元重建蚶江“五王爷府”并撰赠“闽台同根”匾额。在鹿港信众的帮助下,蚶江“王爷府”从鹿港“奉天宫”分灵王爷金身。随王爷金身来蚶江古镇的还有“王爷巡海”仪式所需相关道具、典籍等;多位台湾“阵头”师傅来蚶江表演并传授“金狮阵”、神将、宋江阵等台湾阵头技艺。鹿港文教基金会委派1 名“王船”师傅来蚶江协助打造“金再兴”号王爷船……。台湾地区民间活动尤其是民间庙宇的组织与管理经验丰富,蚶江借鉴鹿港奉天宫的做法成立“澈汉五王府董事会”负责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的组织运作。蚶江海上泼水习俗在台湾“反哺”下,重新找回台胞原汁原味的原乡记忆。
(二)从蚶江海上泼水习俗到两岸对渡文化节
自1988 年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恢复以来,由两岸民间自发组织。随着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不足、组织混乱、封建迷信、安全隐患等问题日益凸显。2007 年福建省各级政府因势利导,筹办首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活动时间也从一天延长为三天,台湾参访团成员也不再局限于鹿港地区。台湾体育界、教育界、餐饮界、企业界代表纷纷来蚶共襄盛举。文化节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包括祭王爷、游王爷船、王爷船巡海、海上泼水、龙舟竞渡等传统民俗内容,还增加了民俗摄影、两岸太极拳邀请赛、两岸文化产业论坛、两岸青年歌会,两岸龙狮大赛等内容。文化节蚶江的南音、北管、高甲戏、布袋木偶戏、南拳表演让来蚶江参会台胞如痴如醉,鹿港的雷音三太子、家将、宋江阵的登场也让蚶江乡亲大呼过瘾。经过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蚶江海上泼水习俗已经发展成为内容丰富,两岸参与人数众多,影响力巨大的两岸对渡文化节。
(三)从单向交流到两岸互动
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恢复以来,台湾同胞从未缺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台湾当局种种限制,蚶江同胞却无法到鹿港参与活动。动力源于目标,一次又一次的申请,一道又一道的手续,在两地同胞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2009 年端午节,715 名蚶江民众护送“蚶江澈汉五王爷”金身到台湾鹿港,参加首届蚶江“五王爷”赴台巡守暨两岸对渡文化交流。鹿港乡亲万人空巷迎接来自原乡的神灵和亲人,地缘近、血缘亲、神缘承、商缘连、俗缘循,让来鹿港的蚶江乡亲倍感亲切。鹿港溪中两岸乡亲龙舟竞渡,文化论坛两岸学者追忆对渡历史。鹿港镇长王惠美说:我从出生之后,就没有回过泉州,我知道爷爷是从泉州来的,泉州蚶江对我来说,也就是爷爷成长的地方。”蚶江“五王爷”赴台巡守,台湾近百家媒体争相报道;五王爷信仰、蚶江海上泼水习俗、蚶江与鹿港的对渡历史不断被提起并广为传播。数万鹿港乡亲在场体验,通过身体性的实践很好地完成了原乡文化的操演与维持,并产生一种“情绪”,唤起和感染参加活动的每一位台胞,在纾解老一代台胞思乡之情的同时,又向年轻一代台胞传递原乡的文化记忆。
蚶江端午海上泼水节与鹿港端午龙舟邀请赛遥相呼应,两岸同胞在交流互动中唤醒历史记忆,并建立起新的记忆。正如闽台对渡交流协会会长林清阔所说:“蚶江端午“海上泼水习俗”已经成为维系两地同胞情谊,守护两岸精神家园的重要纽带。”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正从“对渡文化”迈向“文化对渡”。两岸同胞通力合作,取长补短,互利双赢。它再次生动地诠释了两岸中国人同根相系、同命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四、记忆价值: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的当代使命
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真实写照,守护这一段历史记忆,一方面要重视传统习俗的激活与发展,另一方面更要思考历史记忆如何与新时代有效对接,发挥其当代价值。心理学家巴特莱特认为:“记忆不只是历史‘痕迹’的重新兴奋,而是服务当今社会反复推敲的‘构念’”。[19]日本著名民俗学者寒川恒夫教授认为,民俗有助于形成人们特殊的文化身份。[20]
(一)对抗原乡文化遗忘
台湾居民约98.3%的人口为大陆移民,其对大陆的原乡记忆依然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台独分子”鼓噪的“去中国化”,台胞原乡记忆处于不断重构和失忆的过程,并呈现出复杂心态。[21]民进党当局通过修改课纲、建构“台湾史观”,企图切割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联结。此举弱化了台湾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中国”情结,并严重撕裂台湾青年人的历史文化认知。这种割裂是残酷的,很多台湾年轻人关于大陆,关于原乡的情感已远不如老一辈强烈。受“台独”史观和“台湾主体意识”散布的影响,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台湾同胞的祖国认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逐渐把“中国”形塑为非我群的“他者”。[22]如何唤起更多台胞尤其是台湾年轻人对原乡、对中国的记忆,成为两岸中国人当前迫切的历史任务。
台胞通过参加蚶江海上泼水节和鹿港的端午龙舟赛,老一辈会向子女传递:“蚶江是老家,是你们爷爷成长的地方”,从而让台湾年轻一代对原乡故土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将那些沉潜在历史深处逐渐被台湾青年一代淡忘的历史通过身体仪式得以重现,并以此对抗台湾年轻人的原乡遗忘,重建台湾青年一代处于断裂危机中的记忆脉络。其次,在台湾当局大肆“去中国化”的背景下,台胞突破“台当局”权力阻隔,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子女亲朋来蚶江参加海上泼水节,并把原乡的特色文化引入到鹿港。这也是反抗台当局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联结的一种方式,通过民间自发的文化记忆来对抗台当局对“原乡”乃至对“中国”的遗忘。
(二)强化两岸文化认同
认同是心理学范畴,核心是讨论归属问题。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个体在情感或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23]“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所属的文化体系形成的一种内在情感,表现为一种归属感和文化情结,并以此形成“我群”与“他群”的社会区分。[24]认同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所以“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者不定期来加强其集体记忆。”[25]
蚶江海上泼水习俗,肃穆的“王爷船”巡海仪式,海上泼水的集体狂欢,不断丰富的文化事项,每年吸引台湾地区数十个参访团来蚶江参加文化节系列活动和十几万群众观看。两岸同胞的体验参与,建构了一个基于民间信仰、地方节日和身体展演于一体的闽南地域文化节,其作为一种隐性的精神纽带,既穿越历史又指向未来,积极地促进了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正如麦克·费瑟斯通指出:“操演纪念仪式和庆典,其实就像充电池一样,它们储存着共同体的感觉,并定期把它充满。这些定期的文化仪式强化着我们的家庭、地方和民族的集体认同感”。[26]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两岸对渡文化、王爷信仰文化和端午习俗文化是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的根,突显两岸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并使之成为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助力两岸关系朝着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
(三)共享对渡文化品牌
品牌一词源于古挪威语的“brandr”,意为“打上烙印,原指烙在犯人身上的印记或牲口所有权的标记。如今“品牌”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主要指能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无形资产。[27]文化品牌,是指那些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并且有独特标记的文化事项或文化产品。[28]文化品牌的打造对提升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有效激发当地群众的文化自豪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可以让外界更好地了解本地区的文化,推动本地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从而有力地提升地方文化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2005 年,“蚶江海上泼水习俗”被列为福建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08 年,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纳入国台办对台交流重点项目,并在原蚶江海防官署建成“闽台对渡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上千件蚶江与鹿港的对渡文物。2011 年,蚶江端午海上泼水习俗被评为中国最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节庆,并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蚶江海上泼水习俗已经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品牌。蚶江镇借助蚶江海上泼水文化品牌,建立文化产业创业园。截至2020 年共有18 家台企入驻,年产值破亿元。鹿港依托两岸对渡文化节,打造国际休闲文化小镇。蚶江海上泼水习俗品牌化,有效带动了蚶江、鹿港旅游业、娱乐业及文博会展业等相关产业的壮大发展,为两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蚶江,鹿港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
(四)筑牢两岸命运共同体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是一种亲密的共同生活。[29]人类共同体最早见于血缘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我们会感到安全,而在共同体外,我们会感到处处潜伏着危险。在共同体中,人们互相依靠、互相帮助。[30]共同体最基本的特征为利益共同,这种利益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团体被称为“利益共同体”。当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联上升到命运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最高阶段,则被视为“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13 亿大陆同胞和2300 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是两岸交融的产物。在地缘、血缘、商缘、神缘、文缘关系的感召下,蚶江海上泼水习俗不仅讲述历史,而且成为当下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依托蚶江海上泼水节,蚶江每年举办两岸“同名村、心连心”交流活动、闽台龙狮大赛、两岸灯谜展猜、闽台美食节、蚶江侨乡谜会、“海丝情”国际南音大会唱等各种文化活动,台湾文创、动漫、传媒等文化产业的助力不仅让蚶江海上泼水文化节内容更加丰富,同时也让台湾优势文化产业在闽南迅速生根发芽。闽南传统文化南音、北管、拍胸舞、唆啰嗹通过海上泼水节再次闪耀鹿港,并被引入台湾华岗艺校课程。依托蚶江海上泼水节两岸经贸交易会、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两岸农洽会、台湾农产品展销会等两岸经贸活动如火如荼,蚶江成为众多台胞来陆旅游、交流、投资的第一站。
蚶江海上泼水习俗传递的历史记忆生动地诠释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这种命运共同体也不同于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31]它是存在于闽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闽台民众的实践交流互动得以强化和巩固。这种命运共同体是滕尼斯“血缘共同体”的延续与升华,是在闽台民众互动交往中型塑和建构的,并通过象征性的身体运动——蚶江海上泼水不断呈现。
五、结语
历史记忆凝结着一个族群所特有的情感联系,并由所属的族群及其成员所分享和传承。[32]蚶江海上泼水习俗是祖先留给蚶江鹿港两岸中国人的文化遗产,记录着蚶江与鹿港的交流、迁徙、融合的历史,再现了两地人民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历史发展轨迹,承载着闽南文化爱拼敢赢、重乡崇祖的厚重基因,它是两岸历史的记忆,也是闽台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闽台两地人民通过对蚶江海上泼水习俗的传承,闽台共同的血缘、信仰、历史、文化、习俗和语言不断被巩固强化,两岸文化不断交融,构成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对于台湾民众而言,参加蚶江海上泼水寄托着他们对原乡的眷念与遐思之情,通过重温历史得到精神慰藉,是一种自我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传承。正如台湾鹿港文教基金会会长蔡雨亭所说:“蚶江是鹿港的原乡,当年蚶江先民跨海到达鹿港,将技术和文化带到鹿港,从而形成了今天的鹿港,如今我们来蚶江是文化交流,更是文化返乡。”正是凭借着这种文化认同,两岸人民经历一次次分离,总能冲破重重困难险阻一次次重新聚集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海上泼水的欢歌中寻求生命归属和精神家园。
眉山,是沉积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广袤的土地。据《眉山县志》载,自汉及宋,眉山文庙香火不断,进而文脉悠长,“古者,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眉山县志》民国十二年版校注本,眉山市东坡区党史方志办公室编2008年8月),明代的邓克明在《重修文庙记》中也说道:“敦崇教化,尊礼耆耇……若人才蔚起,相望不绝,苏氏父子其最著也”,可见传统儒教对苏轼政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注释:
[1]王彬:《台湾居民大陆记忆及其情感分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1 期。
[2]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 年第5 期。
[3]郭学松:《仪式、记忆与认同:“三公下水操”中的身体运动研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7 年第6 期。
[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9》(乡镇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年,第228 页。
[5]石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编:《石狮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年,第162 页。
[6]陈支平:《明清港口变迁史的重新解读——以泉州沿海港口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6 期。
[8]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194 页。
[9][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8 页。
[10]林水强:《蚶江志略》,香港:华星出版社,1993 年,第92 页。
[11]黄杏川:《蚶江郊商之兴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88 页。
[12]吴承祖:《论清代郊商之义利并举——以日茂行林振嵩为例》,《闽商文化研究》2014 年第1 期。
[13]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 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2 期。
[14]刘灵坪:《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思想战线》2018 年第5 期。
[15]郑一省:《华侨华人与当代闽粤侨乡的民俗活动》,《东南亚研究》2003 年第6 期。
[16]张兵娟:《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传播与文化认同建构——以大型电视文博节目<国家宝藏>为例》,《新闻爱好者》2019 年第1 期。
[17]连横:《台湾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8-19 页。
[18]清·周玺:《彰化县志·规制志》,1900 年,第199 页。
[19][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214页。
[20]陈利红:《论民族传统体育对族群建构的文化意义——以仡佬族、彝族和傣族为例》,《体育文化导刊》2017 年第11 期。
[21]王彬:《台湾居民大陆记忆及其情感分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1 期。
[22]孙云:《从“我群”到“他者”: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台湾民众认同转变的成因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3 年第3 期。
[23]任曼等:《文化共同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第178 页。
[24]郑晓云:《文化认同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68 页。
[2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31 页。
[26]麦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51 页。
[27]欧阳友权:《我国文化品牌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 年第5 期。
[28]罗坤瑾:《从传播人类学视角看民族文化品牌的塑造——以贵州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2 年第2 期。
[29][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45 页。
[30][美]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 页。
[3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16页。
[32]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