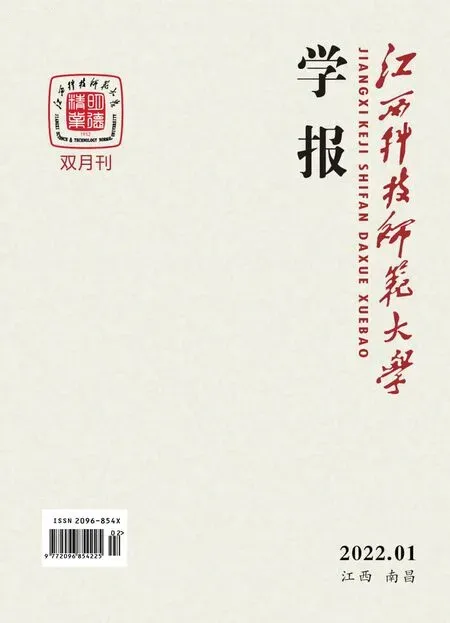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历史渊源探究
王军伟,周祥云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云南昆明 650504)
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国际法通常被理解为调整现代国家体系之间关系的法律;现代国家这个概念包含的时间跨度也只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惊鸿一瞥,不过短短数百年的光阴。正如J.G.斯塔克(J.G.Starke)指出的那样:“伴随着现代欧洲国家相互交往对话的社会现实,国际法得以不断发展完善。其起源可以溯及到16、17、18 世纪的学者、法学家,他们率先制定了国际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1]可以说,国际法是具有自主意识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主权国家间行为规范的准则,它既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时也为我们走向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提供了指南。
格老秀斯作为现代国际法当仁不让的理论权威,是我们在当代继续思考有关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所绕不开的丰碑。如果说他的国际法理论在今天已然硕果累累,那么笔者则试图从其思想的根须理清脉络,从而驱散笼罩其头上的迷雾蒙昧。
一、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古希腊历史渊源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诞育着人类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时,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古希腊是实质意义上国际法的开端吗?对此,有些学者认为,鉴于古希腊独特的政治环境,该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法产生的社会背景有赖于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的建立,而古希腊的诸多所谓“国家”的政体,有着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构成实际意义上相对自成一体的主权权威,故而以城邦的名称谓之更恰如其分。对此,T.A.沃克(T.A.Walker)妥帖地指出:“古希腊国家之间交往的历史,是城市间独立和屈服更替的历史,这些城市的居民事实上是有着共同祖辈的家庭的成员。存在于这些人之间的国际法更确切地来说是城际法。”[2]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对上述看法不予苟同,他们断言,如果是从自治的角度来理解国际法,那么古希腊人也确实地参与了国际法的历史进程。该观点建立在如下事实之上:这些希腊国家有着自己的领土;征服其它地域的国家及其民众;建立殖民地;达成政治协约。诸如此类,都只能是自治自决的主权国家才具备的权威,这和今天的民族国家没有什么分别。菲利普森(Phillipson)认为:“国际法依赖于独立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但并不必然要求其在于民族、语言、宗教信仰上的差异。”[3]除此之外,他还给出了造成上述错误认识的原因。因为有些人过度执迷于现代主义这个词汇,从而忽视了古希腊国家间的既定事实,未曾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总而言之,此类学者是为专业词汇所迷惑,成为了拘泥于形式字眼的奴仆。
尽管对于国际法真正的开端存在着异议,但并不影响格老秀斯从该段历史中汲取思想的精华。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诸多引述,无一不在宣示着他对于这个时期思想理论的深根细作。比如,这两人都在国际法体系中为宗教保留了席位。他指出:“因此,亚里士多德将宗教的关心和支持作为公共利益的首要之物。”[4]其本人的表述为:“除了独立国家的内部福祉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区域留待宗教发挥作用。”[5]
除此之外,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探讨使节权问题时,他指出国际法赋予了大使两种权利,其一是大使有权获准进入他国;其二是他们相应地有权受到保护,免受人身伤害。关于前者,格老秀斯举例论证其观念的合理性:“迦太基元老院议员汉诺(Hanno)猛烈抨击汉尼拔(Hannibal)不接纳代表盟国的大使进入他的营地,因为他这样做违背了国际法。”[6]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释道改规则并未强迫各国无条件接纳他国使节入境,理由是国际法仅仅禁止无充分缘故而拒斥使节的行为。有多种动机为其提供辩护:有的是不喜与之交涉的国家,当然亦有不悦派遣而至的大使,或是抵制使团来访的目的。与此相关,格老秀斯又给出了一个例证:“根据伯利克里的建议,雅典人把斯巴达使者梅利西普斯(Melesippus)驱逐出境,因为他来自没有和平意图的敌国。”[7]
由此可见,格老秀斯本人的国际法思想的历史渊源有一部分来自于古希腊时期,该时段所积淀的丰厚政治实践智慧,以及该囿域所凝练的伟大哲学思想精华都为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孕育提供了温床,包括在国际法的领域为宗教保留了一席之地,并且就使节权利这个卓著的国际法议题展开了鞭辟入里的解析。
二、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罗马历史渊源
当历史转轴的指针指向古罗马时期,没有人会否认其在国际法演化进程中的显著地位。古罗马作为一个疆域囊括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其统治辖区内的民众不仅仅囿限于罗马公民本人,还有数以万计的外邦人。对此,该帝国的统治者拒绝用一套法律标准去规制罗马公民和外邦人,于是市民法(jus civile)和万民法(jus gentium)就诞生了,后者更是古今学者探究国际法渊源的必经之路。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随着古希腊自然法概念在罗马人的思想中普遍流行,一种信念在罗马法学家的观念里蔚然成风,即旧的万民法事实上是自然丢失的法典,而他们自己的衡平法则是其唯一可以寻回的契机。罗马法对于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影响在《格老秀斯与国际正义》一书中可见一斑:“将自然法理论运用于‘万民法’的过程中,格老秀斯的论证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古代罗马法学家的著作基础上的。”[8]
古希腊的自然法理念对于罗马人的影响在西塞罗的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在其叙述中,他并未直接阐明万民法的有关内容,也没有试图对万民法施加任何评论,仅仅在市民法和万民法之间作出了区分,指出后者表明了那些法律机构是为所有人共有的、同时应该被包含在独立国家的市民法之中。对此,他指出:“联合体之间的纽带会在同属于相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变得更加紧密,正因为此,我们的先辈选择在市民法和万民法的两个层面上理解不同的事物。市民法并不像万民法一样具有存在的必然性,但是万民法同时也应该是市民法。”[9]西塞罗规定了自然法的内涵,使其浸润到罗马法思想之中。
格老秀斯对于西塞罗观念的引用生动地体现在其本人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在探讨通过行使征服权而获得领土和财产时,他认为战争中的取得物一经捕获便可成为最初捕获者的财产。这一点首先源于国内法的规定,然后推而广之到国际法的层面,这一点和西塞罗的“万民法同时也应该是市民法”的看法如出一辙。格老秀斯提出:“在这一关于战争权利的问题上,各国已经确定。”[1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为:“在这些方面万国法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人和物。”[11]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罗马法对自然法的借鉴吸收并非完全系统化的照搬。对此,T.A.沃克指出:“希腊哲学使罗马法学家对自然法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他们最先进的公法概念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法律观念,这种观念源于万民法和自然法的融合。”[12]柏拉图很早就提出:“只有充分服务于人类自然本性发展的国家才能称之为善。”[13]正如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认为的那样,罗马的法学家同时也是熟稔的哲学家,他们关注到万民法作为“法”是适用于全人类的,这一点区别于国内法。同时,该法是人类自然理性的产物,也是人意法与自然法姻缘缔结的结晶。在此基础上,詹姆斯·布赖斯进一步指出:“万民法与自然法相契合,西塞罗的评述暗示了这一点,他认为所有国家的同意必须被视为自然法,关于西塞罗该论点的正式宣告可以最早追溯到哈德良(Hadrian)的时代。”[14]
将国家间的共意视为自然法赋予的权利为后继者格老秀斯所吸收采纳,他意识到当神圣罗马帝国和教会不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公共产品,逐渐退出人类政治社会的舞台,人们开始呼唤真正的国际法充当国际性的权威机构。权威来源于权利的认同,格老秀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并从人类文明的卷帙浩繁中找到了亟需的权利基石,即由契约缔结的权利共同体。毫无疑问,契约建立在缔结者之间的共意之上,而这种共意则是自然法赋予人类理性的产物。戴维·J.希尔指出:“国法不仅仅由从正义的一般原则抽象出来的某些纯粹的结论所构成,它还包括一个以同意为基础的理论体系,而正是这个自愿认可性的义务体系将国际法学与伦理思想和道德理论区别开来。”[15]尽管民族国家的兴起标志着疆域界限的明确划分,但为人类所共有的普遍理性则没有任何囿域,因而其约束力是对所有人类都具有效力的。我们说法律只有对自愿受其规制的人有拘束力,那么显然国内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只能适用于其公民,倘若我们寻求国家间的法律规范,唯一的选择就是依据人类共通理性的国际法。对此,戴维·J.希尔指出:“市民法只是适用于和平时期的法律,而在战争状态中,市民法却无法发挥其效力。而那些源于人类本性而非出自特定的民事关系的法律,即使在战争中仍应发挥效力。战争法就来源于这些永恒的法律。”[16]自然法的权威和上帝的权威早已赋予了我们权利和义务。
在此不难看出,格老秀斯对于国际法的理解是基于自然法和制定法的两个维度。前者代表着国际法的公平正义,后者则寓意着国际法的普遍拘束力。因为格老秀斯并不将国际社会仅仅视为民族国家的联合体,他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更高层面意义上的法律共同体,不仅关系着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规范,更是独立的个人与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如果用当代比较通俗的话术来表示,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亨德里克·范·埃克马·霍姆斯(Hendrik van Eikema Hommes)有着相当精彩的论述:“由自然血缘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社会,完全符合人与国家之间的个体间或彼此间合作的关系,这是格老秀斯的自然法概念,以及后来的自然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人意法理论的特征。”[17]至此,我们可以稍稍领会到为何这位学者至今仍然被供奉在圣坛,不单单是他天才般的锐思,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深处始终闪耀着人性的关怀,因此无论跨越多少个世纪,都会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
讨论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在自然法和万民法中间存在着一个特例,即奴隶制。众所周知,万民法中允许该种制度的存在,但其要义显然是与自然法相悖的。詹姆斯(James)为此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将奴隶制视为法律体系中的“一种更加自由和进步的因素”,因为其具有普遍适用性。为了进一步说明其观点,詹姆斯提到:“在自然法和万民法交互的进程中,这两种法可以从大致意义上被看作是同义语。”[18]他本人想表达的意思是,万民法与自然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可供调适的弹性空间。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格老秀斯在其自然法理念中承认了奴隶制存在的条件性,即奴隶制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因而当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也就随之失去了“暂时的合法性”。这一点显然并不违反自然法的本性。对此,佛德(Steven Forde)也指出:“这个体系考虑到在万民法上反映出来的历史上不停变动的国家实践,因而表现出了充分的弹性,同时,它也为那些自然法的永恒的道德原则保留了一席之地。”[19]
三、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中世纪历史渊源
伴随着罗马帝国的陷落,万民法也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此时的欧洲文明则开始向中世纪封建制度过渡。在该种制度之下,封建主及其附庸之间是互助互惠的义务性关系。国王将其领土划分给附属,保卫他们的安全,确保附庸彼此之间的正义;而附庸则拥护其封建主的统治。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领导与服从,而是某种程度上的互相制约,任何一方都并非至高的权威。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封建主及其附庸之间大大小小的摩擦从未间断,也因此需要主教在精神领域的权威化为现实世界中的权杖,以此来平衡各方的矛盾与纠纷。教会法(Canon Law)的诞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此前万民法的作用,为所有封建国家共有,以此来调整彼此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对此,吉尔克(Gierke)作出了经典的描述:“如果说这里只有一个国家,并且包含了全体人类,那么这个国家只能是上帝自己创建的教会,所有现实世界的土地主都必须先成为教会的一员才能具有效力权威。”[20]
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自然法和万民法之间搭建了理论的桥梁,使得二者互通有无。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在罗马帝国时期,沟通自然法和万民法的倾向就已经出现,并且一度接近于完成,但两者之间依然无法达成完全的一致性,而这个愿景在托马斯那里得以最终实现。他最初的做法与罗马时期的相同,也是将万民法看作是人的自然理性在生活习俗和社会实践中的外化表现,并进一步认为两者之间并无任何分歧,乃是和谐一致的。他指出自然法具有为人类理性所认知的基础性原则,而人意法则是直接从该原则推绎出的次级原则,其具体论证为:“既然所有归属于神圣上帝的事物都由永恒法支配,很显然所有事物也都享有该法的品质,也就是说,事物具有永恒法所赋予的正义品质,并落实为正当的行动及目的。”[21]
托马斯认为国际法是基于演绎的方式,即以自然法本身的原则为前提条件推理出来的行为规范,这一点不同于依据特定人的共意而形成的国内法准则。上述观点与托马斯对法的来源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他认为全部的法都来自于理性和立法者的意志,自然法产生于上帝的理性意志,人意法来自于人的意志,这种意志受理性的约束。
格老秀斯本人也借鉴了托马斯与此相关的理论,在讨论到战争中的哪些行为是合法行为时,格老秀斯探讨了这一命题,即战争中的欺骗行为是否违背自然法的精神,亦或国际法的原则。对此,他通过说明历史上存在数不胜数的对敌人实行的欺骗的例子,来证明战争中的欺骗行为在今天也是正当的。“这些行为都是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的,尽管这样做背离了他从属的军事体制中的惯常做法。因为这些制度和纪律受到每个国家军事指挥官的意愿和想法的影响,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所有国家具有拘束力的习惯。”[22]依据特定人的共意而形成的国内法准则只对特定的国家有效,因此,我们不能说战争中存在欺骗行为就违背了国际法的普遍原则;相反,它是国际法的衍生物,也是国内法与国际法原则相符的佐证。
托马斯对于国际法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引入了关于习俗问题的思考,也就是习俗是否具有和法律一样的效力,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际法的空白。首先,托马斯提出所有的法都来源于立法者的理性和意志;自然法和神意法(divine law)来源于上帝的理性意志(reasonable will),人意法来源于人的意志,此种意志受到理性的支配。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人的理性和意志在实践层面上不仅可以表现为语言,还可以通过行动来彰显。因此,习俗作为不成文法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书面表达,但从法的本质来源上考究是具有效力的。最后,他指出习俗作为一种得以重复出现的行为,是理性和意志的自我充分彰显,“因此,习俗具有法律效力,同时也是法律的延伸。”[23]基于该理论,托马斯对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奴隶制也有了更合理的阐释:其一,奴隶制是自然理性推演(rational derivation)的衍生物(addition);其二,对一切共同东西和普遍自由的拥有可以说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奴隶制不是自然带来的,而是人类为了其生活的福祉而设计的制度。”[24]他以此论证道,自然法则在这方面没有改变,除非通过附加衍生的方式。正是在该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托马斯完成了罗马法没有实现的伟业,也远远超越了其先驱者们,即协同了自然法和国际法的一致性。
在协调自然法与国际法的一致性方面,格老秀斯的成就可谓是无人能出其右,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他的论使节权一篇。在他看来,外交大使作为国际法体系的鲜明象征,应该拥有更多的特权,即比自然法允许的范围要广。比如衡平法和自然公正要求对所有有过错的人施以惩戒,但是国际法却允许例外,也就是说,有利于大使和保护有公开诚意者的例外。所以,审判或处罚大使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国际法禁止许多自然法允许的事。“因此,偏离了自然法的国际法就引起了解释和推测,而这些解释和推测给予了公正原则比自然法所严格允许的更大程度的特权。”[25]
四、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近代历史渊源
当西方的伟大制度,即教会与帝国成为过去式,而新的神秘体——诸民族刚经历了分娩的阵痛,尚未发展出足以支撑政治思想的框架时,在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人被孤独地遗留下来。更糟糕的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即借着爱的纽带将不平等的人团结在一起的夙愿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正如沃格林在其《政治观念史稿》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城邦衰落之后,紧接着的是世界城邦的兴起,以及一神论宇宙观的黎明。现在,这个宇宙已经崩溃,随之而来的也不是一个新世界,而是支离破碎之域,亦即个别的人类体——诸民族。”[26]在基督教这个公共产品被驱逐出社会生活之后,此时的人类不仅面临营养不良疾病的困扰,还有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对秩序的毁灭性打击。诸国各自为营,皆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在竞技场上角逐,当彼此之间出现意见纠纷之际,再也没有一个公共的权威为其裁决,于是战争成为了“法官”,弱肉强食成为了民族间的主旋律。但是,频繁斗争使得当时的人们身心俱疲,于是便转头向人类经过长期历史演变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寻求秩序规范。值得庆幸的是:“古代的海事规则和一些非系统的战争和商业法律在任何方面都可以被视为等同于国际法。”[27]但是遗憾的是系统的国际法还音信渺茫。
当人类的命运处于十字路口的转折点之际,马基雅维利手持“君主论”的火炬为16 世纪的诸民族驱散了重重迷雾,并指明了此时的民族国家所要奔往的方向。需要指出的是,他使自己的理论跳脱出传统理论的框架,他对绝对价值的那种古典守旧的认知方式嗤之以鼻,并且摒斥基督教的思想观念,这种看法基于其对于那种猜测性认知的不以为意。正如他自己声称的那样:“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28]首先,他把一个非常低级的人作为一个基本前提,并认为由于人类天性趋向于社会性的生活,所以会招致混乱,乃至无政府状态。其前提建立在这样一个认知之上,即人性的堕落,以及社会的腐朽。倘若在人类尚未没落之前,那么共和制的国家再合适不过,鉴于人性的腐坏,具有强力意志的君主就显得极为必要了。他不再对教会抱有幻想,寄希望于信仰的复苏,而是渴求君主的权利凌驾一切,从而为使国家摆脱无政府的混乱局势,赢得尊严与荣光。也因此,作为最高主权权威的君主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法律本身,甚至可以从外部施加强制力于个体自身,以此约束其行为。
这种政教分离的观念在格老秀斯《论海洋自由》一书中也得到了体现,在论述葡萄牙人无权以教皇馈赠的名义取得对东印度的主权时,他毫不犹豫地指出:“耶稣基督,当他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时他因此放弃了世俗世界的权力…有人就大胆地断言——我使用的正是这些作者们的话——教皇既不是全世界政治方面的,也不是世俗方面的君主。”[29]他将教会的权力囿限于精神的王国,拒斥教皇的权杖干预人类世界,为世俗政务的君主划定了自由权力的疆界。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即将最高权威诉诸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随着欧洲君主们在逐权斗争中的肆无忌惮所爆发的弊端,渐渐变得黯然形秽。于是,冀求一部国际法的愿景于16 世纪晚期和17 世纪初期在人们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毫无疑问,此刻的人们亟需一部具有普遍约束力和效力的法律来规制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是马基雅维利所忽视的一点。
之前我们说教会逐渐退出了大众生活的公共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教皇完全销声匿迹了,而是形成了教会国家这样一个带有双重主权性质的政体。因此,以国内法、教会法以及神意法为基础的自然法原则就成为了即将以国际法形式出现的法律规范的胎盘,孕育着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规则。也就是说,所谓的国际法不再仅仅是主权者之间的合意,同时也是基于共意的自然法、万民法原则的体现。
针对上述思想观点,格老秀斯一并吸收并运用到其理论中。他认为在发出宣战声明后立即施加实际的敌对行动是合理且正当的,对此,他试图用罗马人对迦太基人的做法引为例证。这是因为万民法需要对自然状态下的不确定时间,即宣战和战争开始的时间进行干预,也就是说,需要制定法对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但是,格老秀斯同时也指出:“确实也有一些情况,使得这样的延迟根据自然正义是适当的。”[30]例如,一方当事人要求损害赔偿时,给予对方适当的考虑期限是必要且合理的,因为需要知道对方当事人的意愿,即同意与否。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法为何需要同时具备制定法和自然法的双重效用。一方面,它为人类社会的秩序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制度本身留下了弹性空间,兼顾了制度的稳定性与原则的可调适性。
随着教会退出世俗生活的领域,国际社会交往的行为准则所倚仗的公共权威也不复存在。正如我们之前探讨过的那样,仅仅将权威赋予至高无上的君主身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其个人意志的各自为营使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身处于该境况下的人开始思考寻求一个普遍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的紧迫性,于是以西班牙神学家为代表的苏亚雷茨(Francisco Suarez)为国际法找到了新的理论基点,那就是自然法的原则,也就是基于共爱和仁慈的自然戒律(natural precept)。国家不单单是由特定种族组成的联合体,苏亚雷茨在此处更强调国家是一个政治和道德的实体,并由自然法所支配。因为自然法的共善原则,所以对全人类都有拘束力,各个民族国家都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苏亚雷茨旗帜鲜明地指出:“尽管一个主权民族国家、联邦或者王国可能就自身而言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公共体,并由它自己的成员构成,但无论如何,每一个民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人类息息相关。”[31]至此,他为国际法找到了新的基石,不再是上帝的意旨将人类联合起来,而是人类自身的理性为个体间的交往制定了准则。显然,不同于国内法是基于特定种类人的共意而建立的政体,国际法是自然法的延伸,或者说是表现于人类社会的外在化的自然法,当然也是制定法。也因此,国际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律规范的拘束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基于一种道德必然性(moral necessity),所以从内在责成人们去遵守其必然性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苏亚雷茨在罗马的万民法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之间做出了区分。他认为万民法包含两重含义:其一,它是建立在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相互交往的既定事实上的法律,也是这些缔结法律的人所必须遵守的;其二,它是作为个体的国家在其疆域内所要遵守的法律实体,万民法之所以有此称谓,是因为这些国内法彼此之间相似,并为人们普遍接受,或者可以说,万民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内法,只是其适用范围极其广泛,因而具有了国际法的外在性特征。同托马斯一样,苏亚雷茨也将万民法与自然法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补充,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基础性原则。
格老秀斯对于苏亚雷茨观点的承继突出表现在他本人对于国际法的定义之上。在界定国际法的内涵时,他指出国内法来自于国内权力,与此类似,国际法则是相对更为广泛的法律:“万国法是一种在适用范围上更加广泛的法,其权威来自所有国家,或者至少是许多国家的同意。”[32]这与苏亚雷茨的所持立场不谋而合。同时,格老秀斯还将国际法与自然法联系起来:“除自然法外,很少能够找到任何其他法律是对所有国家共同适用的,所以自然法本身常常被称作‘万国法’。”[33]不言而喻,格老秀斯同苏亚雷茨一致认为,自然法的普遍适用性原则是国际法的内在特征,国际法则是自然法的外在表相。
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分析博丹的相关思想理论。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博丹的观点是以马基雅维利带有独断论色彩的君主论为参照物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基督教的统一体已然支离破碎,为政治义务寻找新的基点的任务迫在眉睫,因此,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家自身及其建立的方式。对此,他采用了经验和归纳的方式来研究。首先他身处在饱经内忧外患的法国,他看到造成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根源是中央权力的分散,唯有建立统一的政府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的目光最终锁定在应该体现在统治者身上的权力(power)和主权(sovereignty)。他指出主权是统治者发布命令的权利,而法律则是君主发布的命令。为了保障主权的绝对性,统治者的这种权利是不能下移委托的,因为委托就意味着权利的分散,任其发展就会招致混乱。
同马基雅维利带有独断论色彩的君主论相比,博丹显得更为现实理智,因为他看到了将绝对的主权权威置于君主的个人意志上的极端危险性,这并不能为国家和整个人类带来希望的曙光,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无序的状态。自然,博丹的主权理论也绝非无源之水,这里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念。第一点,主权权威不能存在于政治共同体的民众之间,换句话说,人们所达成的共意不能成为具有义务性强制力的来源方式。
针对君主权力的相关思考,格老秀斯显然是借鉴了博丹的理论,同马基雅维利的独断论相比较,显然前者更为理智。对此,格老秀斯除了承认战争的合法性以及正当性以外,进一步表明要谨防贸然发动战争,即便是在具备正当理由的条件下。他在此想要说明的一点是,作为统治者也不能肆意霍权,继而罔顾自然正义的法旨。他率先指出:“通常我们承担了一种对国家和自身的义务,即避免寻求武力解决。”[34]毋需多言,这是自然法的正当理性命令。身为一国之主的统治者在被迫同他国操戈兴兵之际,所应之举并非不加考量地点将以待,乃是静心凝神斟酌国家现状。倘若敌军胜己数倍,此战是否可行便须细掂慢撂。“而如果他发现自己无法通过这个考验,那么在敌人进入他的领土之前,应该派出使团提出和平的条件。”[35]
纵观上文,我们不难发现,16 世纪晚期、17 世纪初期的思想理论可以说是为更加体系化的国际法蓄势赋能,并揭开了格老秀斯走上国际法舞台的帷幕。在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里程中,人类一直跌跌撞撞地摸索前行,但是心中的那团圣火却从未止息。当教会权威里的上帝被流放到世俗社会之外的孤岛,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政治体制也随之崩塌。此时的神学家、理论家开始负重前行,试图从破碎的片甲残胄中找到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从而将零落的各个国家和民族重新聚合在一起。庆幸的是,人类终究没有被遗弃,因为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光,并找到了在失去上帝庇佑后的新的根基——国际法。即便没有了上帝赐予的圣火,我们依然可以在宇宙间行走的坦然且自豪。该法以与自然法相契合的人类共通理性为基石,并为全体人类所共享,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拘束力。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又为公共领域的必需品找到了新的可替代物,并且更加稳固可靠。
结语
综上所述,古希腊卓越的政治理念是其思考使节权利等诸多具体国际法问题的清源;罗马法所蕴含的融通自然法与万民法的法律实践,使其怀揣国际法得以在近现代民族国家扎根的愿景;中世纪阿奎那的理论建设让此夙寐终成现实;及至近代博丹等学者的思辨激撞为其君主权力的设定开辟了鸿蒙。若将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历史渊源比作浩荡淼茫的长河,上述的每条支流都流淌着熠熠生资的涓淙澄水,时至今日仍于格老秀斯的萃思中恒生不息。通观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历史脉络,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日益觉醒。它在人类文明的摇篮里积蓄力量,在文明交融碰撞的帝国中茁壮成长,尽管遭受了中世纪神学的排挤打压,但是却在现代民族国家惶恐无助之际重焕光彩。值此之际,人类不再是等待上帝救赎的祈祷者,而是从自身发掘到了力量,自发地参与到世界符号秩序的重建。此刻,我们不再是静思的旁观者,而是热思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