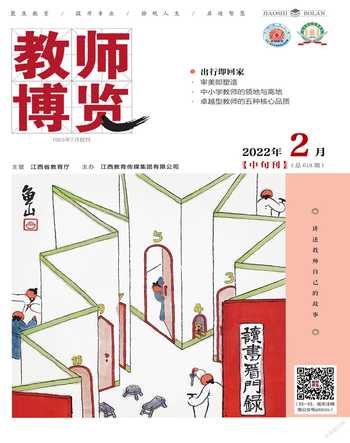审美即塑造
徐林
檀传宝老师说:“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如果可以处理成一幅美丽的画、一曲动听的歌,那么与这幅画、这首歌相遇的人就会在‘欣赏’中自由地接纳这幅画、这首歌及其内涵。道德教育的价值引导与道德主体的自主建构两个方面就可以在‘欣赏’过程中得以统一。”与学生的相遇其实就是与美的相遇,但这种美显然不等于完美。我们不能苛求学生完美,就像我们不能保证我们自己完美一样,否则,诸如“你们是我遇见的最差的一届学生”这类话的潛台词也就可以解读成“我是你们遇见的最差的老师”。没有完美的学生,也没有完美的老师,但这不应该影响我们要拥有审美的眼光,并用这种眼光去无限追求和塑造完美。一个学生其实就是一部作品,而参与这部作品的塑造的不仅仅有学生,还有我们。如果我们能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作品,那么,“作品”也会向我们敞开他们的神秘大门,让我们领略其内部的风景。
而对话时常为我们提供了通达这种审美境界的最佳路径。我喜欢与学生对话,尤其是那种没有任何实际目的的对话,这种对话会让我流连忘返。2009年,我遇到一个学生,曾和他进行过从教以来最酣畅淋漓的一次对话。事后,我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了这次对话,其中的一段我是这样写的:
事后回忆这次难忘的对话经历,我惊喜地发现,整个的对话过程,都是由他“掌控”着话题的选择,推进着对话的节奏,我只是充当了一个参与者的角色。此外,对话过程中还伴随着争论与辩驳,而这种争论和辩驳平常只会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师生的对话中。整个对话过程是非功利的,这不是一次“有预谋”的思想工作。于我而言,对话不是我因握有他的某个把柄而逼其就范的工具;于他而言,对话也不是因为贻人口实而寻求开脱的表演。这里既没有“斥责”“安抚”或“拉拢”,也没有“坦白”“屈服”或“狡辩”。我们真的是在一种没有“私心杂念”的情境中进行着一种心灵与心灵的沟通。
习惯了约谈式交流的老师或许不太适应这样的对话方式,因为在约谈式的交流中,老师可以掌握绝对的话语权。正因为这样,约谈经常是在一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中进行的。因为在约谈中,老师经常是有备而来,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某一问题的发话者,学生似乎也只能在老师的发话中进行着或积极或消极的防御性回应。很多时候,这样的师生交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中所遭遇的问题,因为交流本身存在着问题,“口服”不等于“心服”。实际上,我们需要基于爱、谦逊和信任的对话,正如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写的:“真正的教育不是通过‘甲方’为‘乙方’,也不是通过‘甲方’关于‘乙方’,而是通过‘甲方’与‘乙方’一起,以世界作为中介而进行下去的——这个世界给甲、乙双方留下了印象并提出了挑战,产生各种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想法。”
完全由教师主导的对话实质上是一种野蛮的灌输。我以为,为避免师生交流中教师主导权的滥用,也为寻求真正有温度的师生对话,我们有时应该让渡我们的“话语权”,让学生成为师生交流的主导者。此刻,于教师而言,倾听是最好的对话参与方式。我碰到过很多不善言辞甚至不愿言辞的学生,走进他们的内心就成为我孜孜以求的目标。而要走进他们的内心,我需要“撬开”他们的嘴。我曾遇见一个不善言辞的学生,几乎每一次和他聊天都成了我的个人演讲。起初我以为可能是因为我紧握话语权,限制了他的“发挥”。于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有意让渡了我的话语权,让他尽情“发挥”,但结果并非预想的那样,他只是支支吾吾且断断续续说了些话。他没有尽兴,我亦觉得不爽。原因何在?话题不对?场合不对?还是时机不对?面对这样的“作品”,读懂都难,又如何欣赏?但事情终于还是迎来了转机。我与其父母商量,准备进行一次家访,并交代其父母不要事先告诉他。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敲响了他家的门,门外能隐隐听见他母亲叫他开门的声音。这样,他为我打开了门。面对我的到来,他看上去有些紧张。我说:“今晚我是来向你讨教的,并看看你父母。”他似乎更紧张了。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我和他父母谈论了一些教育之外的话题,并用触龙的迂回聊天法,不经意间过渡到他的身上。我不时瞥了他几眼,他眉头渐渐舒展。我提出要到他的书房请教一个问题,他就领着我进入了他的书房。他的书房不大,但里面堆满了书,除了一些教科书和教辅资料外,还有大量的课外读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然科学类的。我随手拿起一本《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问他:“你看的?”他点了点头。书桌上有很多草稿纸,有几张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我拿起来,问他:“你这是在演算什么呀?推导公式吗?”他的回答顿时让我惊讶:“这是我最近发明的一种数学公式。”我接着说道:“好厉害!你能跟我讲讲吗?”于是,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的“发明”。在我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口若悬河地“演讲”。说句实在话,我着实听不太懂,但我知道,此刻,我根本不需要听懂,只需要倾听,因为,此刻“听”比“听什么”更重要。讲完后,他突然问我:“老师,你不是要问我问题吗?”我会心一笑,说:“你已经解决了。”
这次交流让我倍感兴奋,但兴奋之余,我也在反思: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刻意地与学生对话,有的时候,学生的沉默也是一种美。正如帕克·帕尔默所说:“一名优秀教师甚至能倾听学生尚未发出的声音。这意味着宽容他者、关注他者、尊重他者;意味着不要匆忙地用我们可怕的言语去充塞学生沉默的时刻,不要迫使他们说出我们想听的话;意味着体贴入微地走进学生的世界,使他们将你看成真心实意地倾听他者真心话的人。”我想到上面我提到的那位学生。当我和他父母聊天时,他作为旁听者始终在一旁,但实际上他心里也一直在参与着我和他父母的对话,只是没有发声而已。这就如课堂发言,没有举手站起来的学生不等于他没有发言,其实他可能用他内心的语言在参与着课堂讨论,因为我们有时太过在乎嘴里说出来的有声的东西,而忽视了课堂上那些无声的语言。
真正有温度的对话体现的是一种教育的关怀,对话的温度就是关怀的温度。美国心理学家吉利根认为,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一种是“公正取向”,注重原则、规则、权利和义务;一种是“关怀取向”,注重关心、照顾、直觉和情感。但现实是,很多老师自以为本着“公正”原则做事,就觉得无愧于心。而“公正”有时就像一把尺子,有刻度却没有温度。比如教室排座位,我们可以搞出很多的所谓公正原则,却唯独少了真正的人性原则。其结果,排座位真的就搞成了在教室里的一种利益分配,这种分配似乎就是一件最没有人情味的事儿。
但关怀就是一种审美!吴非老师在《永不凋谢的玫瑰》一文中,曾讲过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经历过的一件事:小女孩在校园花房摘玫瑰花,苏霍姆林斯基发现后,并未劈头盖脸痛斥她,而是耐心地询问原因。当得知小女孩摘玫瑰花是为了送给病重的奶奶时,苏霍姆林斯基在花房里又摘下两朵大玫瑰花,并且说,一朵是奖励给小女孩的,一朵是送给小女孩妈妈的,感谢她养育出了好孩子。如檀传宝老师所言,德育工作者只有眺望德育对象的未来人格时,才能对德育对象的道德成长做出积极肯定的审美评价。而在师生对话中,不管这种对话是出于何种目的,教师只有改变“谈判”或“审判”的立场和心态,让对话成为一种审美活动,对话才会真正拥有关怀的温度。
德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关怀与审美的事业。汉语中的“德”字由三个部分构成:彳、直、一心。那么何为“德”?我想,它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意思:心之所想,目之所向,行之所至。
首先,心之所想,想什么呢?我想,最核心的问题是,学生是什么?每一个学生都是一部作品,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教师既是这部作品的读者,也是这部作品的作者。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读者或作者,一定是一个有情怀、会审美的人。学生是千姿百态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学生,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尊重学生的差异。怀特海说:“在教育中如果排除差异化,那就是在毁灭生活。”而排除“差异化”,进而毁灭生活的人一定是不懂得审美的人。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一千次地确信,没有诗意的、感情的和审美的源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智力发展。”
其次,目之所向,面对学生这样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你能看到什么?能看多远?英国教育改革家坦普尔说:“问题不在于他们18岁时怎么样,重要的是他们之后将成为怎样的人。”凯洛夫也说过:“教师站在人们未来专业的摇篮边。因为他应当是第一个能够看出和发展学生能力的人,他应该首先看清楚学生当中未来的设计师、飞行家、工程师、医生、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或科学和文化的活动家。”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吗?我怀疑我们的“近视眼”令我们无法看清远方的风景,就算我们有的人佩戴上了“眼镜”,视野所及,看到的也是我们心里早已设置好的东西。许倬云说,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的未见。教育真的需要远见,因为一代可能影响三代,三代可能影响无穷代。
而远见需要我们有正见。“死亡课”是我多年坚持的一门课程,因为我认为,课堂就是一个生命场。至于这样做的意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然,一次死亡对话不可能提供关于死亡问题的标准答案,一次“死亡课”也不可能完成死亡准备,一次死亡教育也并不一定能彻底唤醒学生的死亡觉悟与生命意识。因为教育从来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但教育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课也是一点一点上出来的,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做多少做多少。正如布莱克所说:“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恒纳进一个时辰,把无限握在自己手心。”我想,一堂课带给学生这种生命视野的拓宽,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把一粒种子真正培植成参天大树,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在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要做的绝不应该是轻描淡写,也绝不可以守株待兔,更不能无所事事,应该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但真正的“守望”绝不是置身事外,而是置身其中,用参与、用对话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在心里逐步筑成一道“活着”的生命意志的防线。
或许在有的人看来,我这样做是典型的理想主义。但正如吴非老师所说:“教育没有了理想,没有了追求,也就变得猥琐无比。”爱因斯坦曾把那种追求“实惠”的人生观斥为“猪栏式的理想”,他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为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态度,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教育的损害。但我认为,所有理想的追求其实都是以现实为参照并在现实的世界里被唤醒的美。就如“死亡课”,它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了解“死亡”,更是要唤醒他们去发现生活和生命的美。
最后,行之所至,即德育究竟要做什么?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想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课堂除了教给学生知识,更应该交给学生价值判断。因为,“每一节课,都和未来有关”。多年来,我和许多学生对话,这些对话中有很多涉及价值判断的“大问题”,如:如何看待尼采的“超人哲学”?读鲁迅有什么意义?读文科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人生的终极价值?读大学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读书?
我把这些问题称为学生向我提出的“天问”。能够以“天问”示人的学生总归是有情怀的。而要想发现和引导他们,老师不能没有审美的眼光,否则你就会轻易判断这个学生是不务正业,甚至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我虽然并不能完全保证,对每一个提出“天问”的学生,都能给他完全满意的答案,但我一定会给他们提供一条继续寻找答案的路径,那就是阅读。作为老师,带学生读书是天职!钱理群老师说,教育就是爱读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让学生进行海量阅读,并主张他们多读一些“难啃的书”。我的口头禅是:“不读几本难啃的书,不能算是读过书。”为此我还专门成立过班级读书会。在某一次班级读书会结束时,我在札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的班级读书会已经走过两年的历程,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我无法预料,或许会因为高考的即将来临而告一段落,但我坚信:命运的门已经叩响,读书会在学生心中所植下的精神种子永远不会埋没,它将生根,发芽,吐枝,有朝一日,气候成熟,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阅读是师生共有的命门。博尔赫斯说过:“这世上如果有天堂,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以为,伴随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应该也有一座图书馆,这样的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天堂;而在这样的天堂里,老师和学生之间、师生和书籍之间,都在进行着精神世界的审美与构建。
所以说,真正的德育是美学的,真正的教育是美學的事业。正如帕克·帕尔默在《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中写的:“教育犹如人类自古有之的一种舞蹈,教师和学生历来就是这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共舞舞伴,教学的一大好处就是它每天给师生提供重返舞池的机会。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两全其美的舞蹈:年长者给年少者以经验,年少者给年长者以活力,他们在一起翩跹起舞,共同塑造着休戚与共的人类社会。”
是的,作为教师,我们要懂得审美,因为审美即塑造。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
3945501908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