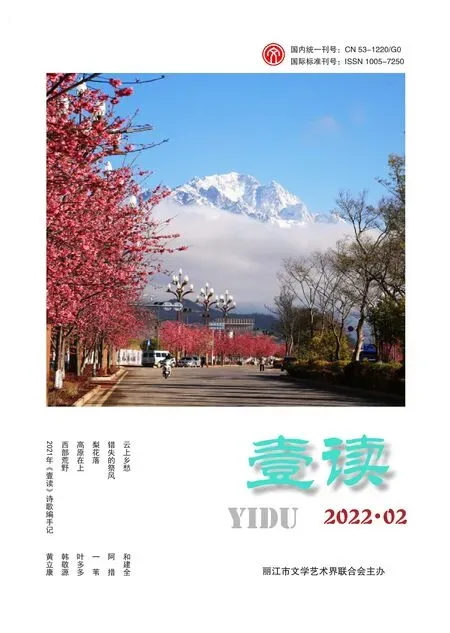草木香
◆李丽琴
灯盏细辛
“牙疼,把‘青花子’捣成一小团放进龋齿洞里,一下子就不疼了。”
“青花子”是家乡人对中草药灯盏细辛的白族语名称。姨奶奶去世多年,但一看到灯盏细辛,她给我们敷药的情景就历历在目。
灯盏细辛还有灯盏花、短茎飞蓬、灯盏草等别名,有散寒解表,止痛,舒筋活血等作用。除了能治疗牙痛,还能治急性胃炎、高热、跌打损伤、风湿痛、胸痛、疟疾、小儿麻痹后遗症、脑炎后遗症之瘫痪等疾病,但它们开的小花朵是青紫色的,能最直接有效地终止牙疼,我的父老乡亲们就习惯以“青花子”来称呼它们,并经常拿它们来治疗牙疼。事实上,灯盏细辛是常用药,入很多中草药书籍,《全国中草药汇编》《云南中草药》《昆明民间常用草药》等均有记载,在这些医书里,灯盏细辛可煎汤,可蒸蛋,可外敷。比如治疗感冒头痛、筋骨疼痛、鼻窍不通、小儿疳积、蛔虫病、感冒、肋痛时可用水煎服,治小儿麻痹后遗症及脑炎后遗症瘫痪可研沫蒸鸡蛋吃,治疔毒、疖疮时把灯盏细辛捣烂外敷。但在我的印象里,治牙痛并不是捣烂加红糖外敷痛处,而是把鲜灯盏细辛茎叶捣烂直接塞进龋齿洞里,比如姨奶奶给我们用灯盏细辛的时候多在野外放牛羊,她听谁说牙疼就直接从地上扯一株,经常把灯盏细辛扯断,扯出来的部分不带泥土,用两颗石头砸烂,塞进去一小团,牙很快就不疼了。
现在提灯盏细辛,很多人心中会有成片种植、植株肥壮的印象,但小时候我们常见的灯盏细辛是长在荒坡上的小植物,东一株西一株,自由生长,枝单叶薄,较为瘦弱,让人一眼能认出它们的特征是紫色的小花朵。那些荒坡远离村庄,大都有坟,因土壤不肥,湿度不够,即便夏秋披满了杂草,也都长得不茂盛,灯盏细辛也不例外。我生长的村庄在坝子中央,村庄没有属于自己的牧场,但田地多为水田。那时都用水牛来耕犁,即便每年用来耕田的时间很少,但每家每户都养着水牛,农忙季节,自家没有水牛,有钱也要等别家耕犁完才能借到耕牛,有的人心疼自家的耕牛,给钱也不借。农忙季节一过,那些荒坡就成了牛群和小伙伴们的天地。荒坡上的草很短,牛啃半天也填不饱大肚子,但灯盏花却一朵一朵开着,牛群不去吃它们,它们就在山坡上自然而然开着,保持着自己的一份优雅安静。有的牛企图一下子填饱肚子,就不安分地往庄稼地东张西望,趁人不注意就跑到玉米地里偷吃两口,遇到主人在地里的时候,小伙伴们就遭骂。人家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哪里是畜生能糟蹋的!小伙伴们知道理亏,不敢还口,也收不住贪玩的个性,就轮流看管着牛。男孩子们喜欢玩打扑克、打水枪等游戏,我们女孩子就采灯盏细辛紫色的小花朵玩。姨奶奶见不得村里的孩子们遭别人骂,也似乎理解我们的贪玩和主人爱护庄稼的心情,就一边到玉米地里割草,一边帮我们看管牛群。因为牛羊不吃,灯盏细辛就在草坡上自由地生长,活到开花,活成药材。
后来有药材公司收购,人们一闲下来便背着篾篓,用小锄头去采挖,因为长得弱小零散,挖一天也卖不到多少钱,但勤俭的乡亲们还是去采挖,积少成多,挖一段时间卖完时也能补贴家用。姨奶奶是其中之一,她早年丧夫,听父亲说她吃过不少苦,但我几乎没听过她讲述生活的苦难。在我们的印象里,她不仅勤劳,干活还非常卖力,用今天的话说,是女汉子,说话做事都很有魄力,也一直是她们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有时懒散一点的人干一天的活她半天就干完,如果跟谁同在一丘田里割水稻麦子,她割出的肯定超出一半。就算和我们一起去放牛羊,也是背个蔑篓在荒坡边的庄稼地里割一篓草背回家。不仅如此,她还常常给我们讲故事,为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教我们一些生活经验,遇到电闪雷鸣和陌生人恐吓还给我们壮胆,让我们免去了一些童年的恐惧和尴尬。现在想来,一个女子挑起家庭重担,抚养大一双儿女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姨奶奶就如一朵灯盏花,不招摇,不诉苦,安静从容。生活中不乏无病呻吟者,但她把生活的苦难咽进肚子里,纵然无人解语,也在生活的缝隙里兀自芬芳。那时我们都喜欢跟着她,不只是她的坚毅带给我们的安全感,更多的是她给了我们轻松愉悦。毕竟,安全感和快乐都是童年的必需品。
我能看到灯盏细辛成片生长,且长得很肥壮的时候,它们已经长到我家门前的一大片田野里。那些田曾经是两季田,每年都要消化掉大量的农家肥,比起荒坡,不知要肥沃多少倍。不过种植灯盏细辛之前,它们已经陆续荒着了,随着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务工,大部分田没有人管理,长满荒草。有车前草、蒿草、鸡脚稗等,更多的是灯芯草,那些草代替庄稼在田里长了几年,长得很茂密,让人不敢随便走进去,即便冬天在田埂上行走,也感觉提心吊胆,好像一下子会从杂草间蹦出来几个魑魅魍魉或鼠蟑蛇虫,给人猝不及防的袭击。后来有个公司来用土地流转的名义来租那些田,家乡人就以每亩六百元的价格欢天喜地地把它们租了出去。经过机械打整后,没有外出的人便以打工的形式早出晚归地替公司在那些田里种植上灯盏细辛。那些种植灯盏细辛的人有我认识的,夫家聋哑的表姐是其中之一。表姐和姨奶奶的命运有些相似,不同的是姨奶奶是年轻时丧夫,表姐是嫁给了一个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丈夫,生了儿子后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回娘家居住生活,和没丈夫的人一样,儿子也一直由娘家人抚养长大。儿子初中毕业后读了个私立学校的五年制大专,虽然是特殊贫困学生,却也和别的学生一样该交多少学费伙食费就要交多少学费伙食费,她不知道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别,只知道儿子上了个毕业后能发工资的大学,便四处打工挣钱供儿子读书。表姐同样是做事卖力的人,做事不磨洋工,手脚麻利,非常尊重她所从事的劳动,她一直是个虔诚的劳动者,不管是种植庄稼还是工地干活,都力求把事情做得标准化,对她来说,比起在工地提沙灰水泥,种植灯盏细辛相对轻松一些。一天七十块钱的工价虽然不高,但一个月下来,也够儿子的生活费了。然好景不长,没几个月,那个租种了我们田的公司撤走了,没有付给帮他们种植灯盏细辛的人几个月的劳动报酬,表姐虽然是弱势中的弱势,却也没拿到工钱,只能用她自己的语言向熟人控诉她遭遇的种种事情。
我现在还经常遇到灯盏细辛,不过已经不在山坡田野,更多时候在书本中和药店里。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又常常用电脑写字,就免不了与各种中草药的缘分。之所以同时想到姨奶奶和表姐,是姨奶奶能说生活的种种是与不是而保持沉默,表姐虽然说不了话,却是整天咿咿呀呀用肢体语言表达她的种种心思看法,让人懂得她的思想看法,从而不敢触犯她。我有时候想,这大概是上天给人的佛性,让她们在生活的缝隙里拥有一种自己的生存方式,一丝丝人该有的尊严。
我需要向她们学习,沉默或者表达。
杨属
多年之后,我才确定那些一直在我们生产生活中有着密切关系的植物就叫杨属。
它们在我母语里的名字是“白沼”(白是汉语“白”的白族语译音,“沼”是借汉语读音),除了小孩,家乡人几乎都知道这种植物。写作中,我就无数次提到它们,但跟很多人一样陷在民族语言的瓶颈里,我问过很多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也问过很多汉族文友,有的人叫桦树,有的人叫白杨,他们这么说,我有时也这么写,但心里终究没有确定,我所知道的桦树跟白杨的生长属性和相貌特征明显没有跟它们对上号。
多年后才知道“白沼”学名杨属,其实应该怪我粗心,它早作为一种标本贴在沙溪兴教寺大门内的墙上,我也无数次进出寺院大门,但都没有注意那些植物标本,反而是几年后偶然间在一个废弃的围墙中见到几块彩色植物图谱才明白我们经常挂在口上的“白沼”学名就是杨属。那个废弃的围墙在另一座三教寺里,里面曾经搭建过简易住房,据说是云南某大学一个植物学研究生来到这里,对与白族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植物本草产生浓厚兴趣,得到同意后在里面搭建了简易棚子住下来,暂居的他不时到周边村寨采访,并拍摄了大量图片制作成植物图牌挂在墙上搞研究。研究生在那寺院住了半年后离开了,那些牌子便留了下来,因无人管理收藏,便在风雨中破败残缺,我见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有些不知去向。
听到这个故事,看着那些残缺不全的植物图谱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感到遗憾,研究生作为科研人员,完成了他所需要的工作后是要离开的,但那些图文并茂的植物图谱对于我们白族人来说,可是一份珍贵的科普资料。从小说白族话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熟悉的很多植物的汉语名称,让我们忽略了它们在生活中的很多作用,表达起来也是言不达意,不能不说是一种欠缺或遗憾。很多出现在我文字里的植物,我都是费了很多周折才进一步去认识它们。杨属就是其中之一。
杨属作为一种在山中自然生长的植物,于我们来说一直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它们喜生于山间相对潮湿一些的沟洼或路旁的冲积土上,与其它植物相比,它们生长迅速,皮光滑,是人们喜欢与之亲近的植物。新世纪之前,家乡人一直用柴禾烧饭取暖,每到冬季,家家户户都要上山砍柴或捞松毛。那时评价一个家庭主妇是否能干,人们就看她家院子里有几剁好柴,房前屋后有几堆松毛。家乡人首选的柴禾是材质较硬、耐烧和火力较大的栗木、橡木和榛木,这些树木不多时,也会取杨属和其它杂木当柴禾。通常,他们先到山上砍伐一些大的树木,用刀或斧断成三尺左右长,再用斧劈成碗口粗的条子,堆起来晾晒一段时间,待这些柴禾减掉一些水分重量,再去背回来。杨属材质较脆,砍或劈都要比其它柴禾轻松,但水分重,不耐烧,晾晒的时间也要比栗木长一些。
除了柴禾,杨属于我们来说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不知何时传下来的习惯,传了多少时候,每到立夏日前夕,家乡人就在门上插一些杨属枝条,说是辟邪。有一年我特地去问家在县城周边的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乡间传说过去曾有盗贼勾结村中不务正业之人在繁忙的夏天潜入百姓家中行窃,为了防止盗贼误入他家,就商量好在他门口插上杨属枝条为记号。此事恰巧被邻居听到,告诉了全村人后大家都在门口插上杨属枝条,盗贼看到连夜潜逃。此后每到立夏百姓就在门口插上杨属枝条,祈愿平安吉祥。
家乡人主食大米,种植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农历七月十五,正是水稻出穗扬花的时候。那一天就常见到家乡的老奶奶们拿着柱香、冷食和杨属枝条去田野行走,白族话称“观赕”,“观赕”直译汉语就是“逛甸”,外人看着词意像是到草甸闲逛,但家乡人一听就不是闲逛,那“逛”中有着浓浓的“巡”意,那些去“观赕”的人都是带着虔诚敬奉的心意去的,她们到自家的每一丘田地,在田间地头插上柱香和杨属枝条,放一些食物,用自己的方式祭拜一下天地,表达对农作物的敬意,再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出生地在滇西盐路山下一个小坝子中央,离生长杨属的山有些距离,我们需要提前一天走七八公里去山中折杨属枝条。那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但村里的老人们都没有忽略此事,每到这些日子前就把杨属枝条折回家备用。他们的习惯和坚持,让生活充满了仪式感。让离开家乡的游子在心中永存一份对家乡的思念和怀想。
杨属通常是成片成林生长,除了与我们的这些关系,它们还经常作为一种景观树吸引我们去山里观赏。春天,它们还未长出叶子时,花序就排成葇荑挂上枝条,嫩叶呈褐红色,在蓝天白云下远远观看,一片褐红色缀在笔直的白色树干上,极美。深秋,它们宽阔的叶片变得鲜黄清丽,无论是近观远看,都非常赏心悦目。春去秋来中,我们总要安排几个日子,特意去城外观赏杨属,观赏大自然的同时,收获一份内心的安乐祥和。
生活平凡,热爱它,也常常有意料之外的收获。某一年立夏前一日我们都忙,没有时间去山上折杨属枝条,回到家门口时一看不知哪家邻居用透明胶布帮我们在门上贴了两枝杨属枝条。大约是此前心中对此有一丝遗憾,小女儿看到门上的杨属枝惊喜得大声欢呼,我们也觉得很温暖。邻居的友善之举给小女儿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对她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她开始细心起来,在那年农历七月前夕我们去折青刺果枝条时看到她多带了几枝,回来也用透明胶布贴到了邻居家的大门上,并年年如此。
柴胡
或是这株药草可用别的来代替,在我们白族语言中并没有其它名称,我知道它能治病的时候,就一直以柴胡的名义称呼它了。
柴胡长在我们的田埂上,是大伯父教我们认识的。大伯父生前在县医药公司工作,认识的中草药多,每回老家都会教我们认识一些,柴胡是我小学毕业那年认识的。
那年仲夏,把所有该栽种的农作物栽种下去之后,父亲带着母亲去昆明看病,大伯父就受父亲之托回老家照看我们。因家中养有牛羊,栽种的农作物较多,大伯父在安排我们每天要做的一些农活之外,也每天去帮我们放牛羊。在滇西北高原,村庄田野地势都有些坡度,虽然坡度不大,但需要一条田埂才能保持田块的平整。我们村子田多,田埂大多宽厚,人和牲畜都能在上面稳稳当当行走,大伯父为了牛羊能吃得饱一些,就经常单独把牛羊牵到田埂上放,通常是贪玩的小朋友们放的牛羊到黄昏也没吃饱,他没等日落西山就和吃得饱饱的牛羊回家了。
大伯父和牛羊回家的同时,通常还带回点植物,并问我们认不认识是什么,可是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我们常见的植物是药草。于是他就一种种教我们认识,要是我们两三次都说不出药草的名称,他就直接带我们去田野里找,让我们从它们生长的位置、株形、花朵的大小、颜色、和我们的关系等等去认识它们,于是我们就认识了蒲公英、续断、柴胡、九里光等十几种生长在我们房前屋后和田野荒坡的药草,并知道怎样在生产生活中使用它们。
大伯父和二伯父、父亲、叔叔为同父异母兄弟,但一直相互关心着。他的工作轨迹是从滇西的乔后盐矿到县药材公司,但我想如果他是老师,一定也很称职。他教我们东西不是口头说教,而是现身说法,让我们通过实际操作来掌握。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无疑是最牢固的学习方式。
虽然都为我们常见,但这些药草都有自己的生长秩序,它们不像人,哪里热闹就往哪里挤,而是分别长在属于它们的旮旯里,同属于一个村庄,却又互不干扰。就如续断喜欢湿润肥沃的闲置土壤,而柴胡只在种苞谷的田埂上见到。和高大的续断相比,柴胡显得单薄细弱多了,整株只有两尺左右高,那大约每隔五六寸便分枝张叶的茎秆,要十多株才能用手握成一小握。让我们最快速度确认它们的,是那些黄色的小花朵,开得多时,每根枝条上能有十几枝花,每一枝花上有几十朵微小黄花。
百度查找一下,看到柴胡为《中国药典》收录的草药,有和解表里,疏肝升阳之功效。用于感冒发热、寒热往来、疟疾、肝郁气滞、胸肋胀痛、脱肛、子宫脱垂、月经不调。但我们全家人牢牢记住的只有感冒发热,因为有大伯父教我们,我们就常在夏末秋初采摘一些回来,在感冒发热时煮汤水喝,清热解毒。除此,我还认识以柴胡为名的几种中成药。读初中的时候感冒,村里的赤脚医生就给我打了“柴胡注射液”,我还因为认识柴胡得意地跟他讨论起柴胡的各种药用。前些年家中老人患胆囊炎,就常用柴胡舒肝丸、柴胡舒肝颗粒,去年还看到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她因工作不顺导致情志不舒天天吃柴胡舒肝颗粒,别人问她只是情绪不好吃什么与肝有关的药,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医学类书籍时,还看到柴胡出现在很多药方里。
不仅柴胡,很多药草就长在老家的乡村田野,是大家都见惯了的事物,但我发现村里人自己利用得不多,大家用药都喜欢去药店买现成的西药或中成药,即便需要吃中药,也是去医院开几副那种很方便的粉剂冲服,而很少自己去采摘。这让我觉得很可惜。
老家远离城市,缺医少药,有些疾病隐藏在体内,不痛不痒,发现往往已经晚了。如果长在我们身边的药草能被熟知懂得和合理利用,生活应该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蒲公英
相对于其它药草,蒲公英是老家男女老少都认识的一种植物。它们不仅生于路边、田野、山坡,有时还以极快的速度长到院子里的草坪和花坛里。阳春三月,蒲公英的叶子一片片从根上长出来,然后长出花茎,开出圆盘似的黄花,吸引一只只蜜蜂,也吸引了一群小孩子。蜜蜂在这朵蒲公英花上急速跑一圈,又飞到另一朵花上。小孩子们拿着小棍子蹲在花旁,目光随着蜜蜂们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仿佛那是他们。小棍子是他们用来防身的,但蜜蜂并没有时间跟孩子们捉迷藏。它们在花间来回穿梭,腿上沾满了花粉就飞走了,根本没有把孩子们放在眼里。这样的时间持续一个月左右后,那些黄色小花朵便全部变成一个个有白色冠毛的花冠,接着,蒲公英种子上的白色冠毛便结为一个个白色的松散绒球。到秋季,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那群小孩子又经常把它们摘来用口吹,比着谁吹的花朵飞得高飘得远。那些花坛里的蒲公英,就是这么让那群孩子吹来安家落户的。
蒲公英为多年生草本,除此还有婆婆丁、黄花地丁、金簪草等名称。每株高10~25厘米,有叶子较宽少齿的,也有叶子较窄齿大深的,即便没有开花的时候也非常好认,因其叶型像公鸡尾巴,父老乡亲还给它一个好记的名字:公鸡尾巴菜。
有资料介绍,蒲公英对金黄色葡萄球耐药菌株、溶血性链球菌有较强的杀菌作用,对肺炎双球菌、脑膜炎球菌、各种杆菌及卡他球菌均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急性乳腺炎、结膜炎、淋巴结炎、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还可治胃炎、肝炎、胆囊炎及泌尿系感染等各种感染性疾病,但父辈称它们“公鸡尾巴菜”时它们并没有以药草的性质进入生活。作为父辈人生中的一种菜,蒲公英给了父辈人深刻的口感记忆,他们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饥荒,凡是能吃的野菜都拌着米糠咽进过胃里,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去体会野菜的种种好处,听他们说起那些把蒲公英当菜吃的年月,总能听出一种惧怕。
没有经历过就不同了,我们很容易接受对我们身体好的东西。记得以前中学的赵老师住我们隔壁,当时我没有把蒲公英当成药草的意识,但赵老师有。每到秋季,她会到田野里连株带根挖回很多蒲公英,然后拣出烂叶子,洗干净晒干,袋装后和柴胡等一起送给她的亲友们。我还常见她隔几天就煮一锅蒲公英,让全家人都喝一点。后来见到老君山中学的几个草坪里都长有蒲公英,三月开出黄花朵时常见蜜蜂忙碌采蜜的身影,那成了一群在学校里生活的小孩子们的深刻记忆,至今还能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他们对那些日子的怀念。
蒲公英可生吃、炒食、做汤,是药食兼用的植物。区别于其它药草,蒲公英能入菜谱,它的花、花蕾、叶子和根都可食用。将蒲公英的嫩叶或花茎洗净后可炒可蒸可煮,若是火锅,放入即可食用。我们做过蒜蓉蒲公英,将蒲公英嫩叶洗净,入沸水锅焯一下,捞出放入凉水中洗净,挤干水分,切碎放盘内,撒上蒜蓉、芝麻油、精盐、味精,拌均即成一道美味。除了做菜,我们还用蒲公英给孩子治疗过淋巴腺炎,把整株挖来洗净,煮汤内服,捣烂外敷,效果还真不错。
也有些人很是聪慧,善于在生活中利用植物。记得刚到县城生活的那几年,栖居的院子里长了很多蒲公英,一位大姐就经常用镰刀割来蒲公英的叶子,剁碎拌上玉米面、米糠等喂自家养的鸡,说是预防疾患。几年过去,还真没有见过她家养的鸡得过病。
即便蒲公英生长在我们的房前屋后,又有这么多的功效,但据我观察,蒲公英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应用得远远不够。因为它曾经是父辈人贫苦时期吃的菜,是贫苦生活的一种象征,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他们就忽略了蒲公英的药性功效,认为吃蒲公英就象征着生活条件差,碍于面子,感冒发热,宁愿到医院输液十多天,也不愿意吃点蒲公英。反而是城里的饭馆酒店懂得利用,大部分的火锅店都备有蒲公英、板蓝根嫩叶,吃饭时,客人都会吃点这种健康生态蔬菜。最让我觉得遗憾的是一个亲戚,年纪轻轻就得了乳腺癌去世,也许经常吃些蒲公英,生命不会如此短暂。
蒲公英可以炒食也可以煮食,不过味道稍苦,怕苦的时候可将其洗净后在开水或盐水中煮几分钟后捞出,漂洗数遍再煮汤或熬粥、炒吃,也就没那么苦了。不过,日子好过的今天,在众多的蔬菜中有一盘带点苦味的菜,也是一种不错的调剂。
老家房后有一个园子,土壤不是很肥沃,以前里面种着果木和蔬菜,我们到城里生活后就一直荒着,几年后里面长满了杂草,还有几棵松苗和野蔷薇、青刺果的幼株,让人看了很是堵心。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替换,对于土地来说,应该是要生长一些植物的,它们需要人来打理装扮,没有果木,没有庄稼蔬菜,它们很快就被杂草霸道无理地占据,这种自然规律有点弱肉强食的味道。有一年春季婆婆看着看着就把干草给点燃了,没想到风大火势蔓延,幸好及时被扑灭,不然就会蔓延到后面的山坡。
我老觉得应该在园子里种些什么,作为它的主人,我有管护它的责任,我曾经用手把里面的小石头一个个拣出去,在园子外围种刺生植物阻拦牲畜,在里面种上生活所需的瓜果蔬菜。让桃花在园子里盛放,让辣椒在园子里慢慢变红,让青葱和芫绥在里面散发香气,现在让杂草去替换一种曾经的生活味道,心里说什么都是不情愿的。再说,让自己的家园荒芜,纵然有千般理由,反映出的也是人的一种散懒和消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的生命力早被唐代诗人白居易一语道尽,生长于农家,我知道让那些杂草自动退出的最好方式是用另一种植物来替换它,想到蒲公英的繁衍速度和在生活中的多用性,便让孩子从网上购买了一包蒲公英种子,我自己则在野外采撷了波斯菊的种子,计划着在哪一个回家的时间把它们播撒在园子里,找回满园清香。
清明节当天晴天丽日,天气干燥而灼热,我们一家上完坟后回家便拿出锄头、铁耙去收拾园子。园子外围的梨花和桃花开得正好,但多年不耕作,院子里的土壤都板结了,没法用锄头翻起,我们就把干草铲掳起来,在第二天清早把园子里的松苗、野蔷薇、青刺果幼株移栽到外围,把干草在园子里一小块一小块铺开,乘着无风把它们烧成草木灰,浇水后后在园子里分别播撒了蒲公英和波斯菊的种子。值得一提的是,当日下午天空便下起雨来,连续两三天的阴雨天气,让我们的劳动成果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巩固。到谷雨,蒲公英和波斯菊都陆续长了出来。看着它们一点点长高、长大,想象中秋波斯菊会开满园子的外圈,而来年三月成群的蜜蜂将在蒲公英花香中浅吟低唱,我们都感到了一种幸福。
红蓼
知道它们的学名叫红蓼时,我已经跟它们打了几十年交道了。数十年来,我们都一直用白族话叫它们“欠锅枝”,我用它们的茎叶做了豆瓣酱,要写有关味蕾的文章时想知道它们的汉语名,就把拍摄的图片发到一个QQ群去问,记得是楚雄作家余老师告诉我它们学名是红蓼。
它们为野生,小时候见到它们,就生于房前屋后的水沟边和庄稼旁边的沼泽潮湿处,非常普遍,为给牛和猪吃的一种饲料。它们生长迅速,割过不久就长出新叶子让我们割第二茬了,但牛和猪并不喜欢吃,我常看到它们在有别的食物时都不怎么去吃红蓼。
红蓼花在每年六七月份开,花序呈穗状,每枝上有三五穗,穗长跟株形有关,长得好的红蓼枝叶肥嫩,花序会有六七厘米长,数十朵玫红色的小花紧密地簇在一起,很是好看。而生长在土质较差之处的红蓼长得比较瘦弱,花序也只有三四厘米长。小时候没有玩具,有时,我们也会采摘一束插到玻璃瓶里玩,但是它们存在得太普遍了,在生长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它们几回,即便可以做饲料,我们对它们的需求性又非常小,以至于在我知道它们可用来做酱菜之前,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来说,它们仍然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植物。
用它们做豆瓣酱是到城里之后知道的事情。老家人做的豆瓣酱有很多种,黄豆、芸豆、赤小豆……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每一种在滇西北剑川生长的豆子都可以被做成豆瓣酱,但用红蓼做豆瓣酱的豆类却限于蚕豆,而且还分季节性。剑川人用来做豆瓣酱的蚕豆有两种,一种是绿皮绿心,一种是黄皮黄心,据说前一种比后一种好,我就常用绿皮绿心的那一种。家里没有蚕豆,每做之前我都先到农贸市场选购颗粒饱满、无虫蚀的蚕豆。同样地,红蓼生长在县城周边一切可以生长的地方,城西景风公园里曾有一块没有利用的水洼地里就长满了红蓼,没有牲畜的亲近,它们保持着干净和茂盛,但都是以杂草的样子在洼地里胡乱生长,我几次都是穿着雨鞋从那里采割回需要的红蓼茎叶。戊戌年春天去采访,看到那块水洼地已经被建设成一个活动广场,剑川“四·二”武装暴动纪念碑也从公园的另一边搬到了广场上。
我用红蓼蚕豆做豆瓣酱是这样完成的。在农历七八月红蓼还没有出穗开花的时候,把采割回来的红蓼茎叶洗净,晒干表皮沾水,把蚕豆浸泡一夜后剥皮晾至半干后一层红蓼一层豆瓣装进箩筐或纸箱,待十多天蚕豆瓣上产生一层厚厚的绿茸时捡去红蓼茎叶,用簸箕把蚕豆瓣晒干收好。到霜降时令,又把收好的蚕豆瓣取出,用香茹煮的汤水浸泡煮软,再放进精盐搅拌好,晚上拿到院子里霜冻,白天收放到阴凉处。大约一周后就加香油和辣椒、花椒、茴香的粉末拌匀装瓶装罐食用。这样做出来的豆瓣酱味道极好,存放时间长,吃起来甘甜回味,无论是炒菜炒杂酱还是单独使用,都非常美味。这个过程也很考验人的悟性,要掌握一个度。若用红蓼敷豆瓣时其中一种带着水或湿度高,都能让豆瓣起霉。而最后搅拌过程中汤汁过多也将减少酱的色泽和味道,最好是所有程序和用料都适度适量。
一种事物,能在生活中长期保存延续,有它的各种价值和实用性。酱菜的味道来自于调料和做法,而这些调料都生长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在收集和制作的时候,都能感受到时间的美好。红蓼对我们来说非常普遍,即便它们有好看的花穗,大多数人还是将它忽略。相对于味道,我更想弄清楚红蓼的性质,于是便知道红蓼是调配食用香精的母体香料,在香辛料中是基础原辅材料,其果实还可以入药,有活血、止痛、利尿等功效。这样看,除了做豆瓣酱,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应用得更广泛一些。
我写红蓼的初衷是想让更多的家乡人了解它,而它们能在诗画中风姿绰约,与名人之名一道留存古今,同样是我没有想到的。新浪有家博客专门发了有关红蓼的诗文贴,除了有宋徽宗的《红蓼白鹅图》和徐崇矩的《红蓼水禽图》,还有很多唐宋诗人的诗词。那《红蓼水禽图》上,三穗蓼花盛开在一枝红蓼上,红蓼枝被飞落的水鸟压弯,梢头、叶尖浸入水中。水鸟全神贯注波中青虾,对画家的关注浑然不觉。《红蓼白鹅图》表现的则是一只白鹅在红蓼花下陂畔,引颈回眸,安闲的梳理自己的羽毛。我一看到这两幅画也非常喜欢,虽然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但人到中年,我们更需要一种昭然物外的心境,来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看与红蓼有关的诗词,唐宋明清各个朝代都有,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秋波红蓼水,夕照青芜岸”、 宋代诗人陆游的“老作渔翁犹喜事,数枝红蓼醉清秋”和清代杨芳灿“红蓼滩头秋已老,丹枫渚畔天初暝”。他们描述的场景,也是我常见的。
从熟视无睹到在生活中应用,再欣赏有关它们的诗与画,我认识红蓼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有大理州最高峰雪帮山的雪常年映衬着,我希望家乡的红蓼也能入诗入画,让生活呈现出更多的滋味和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