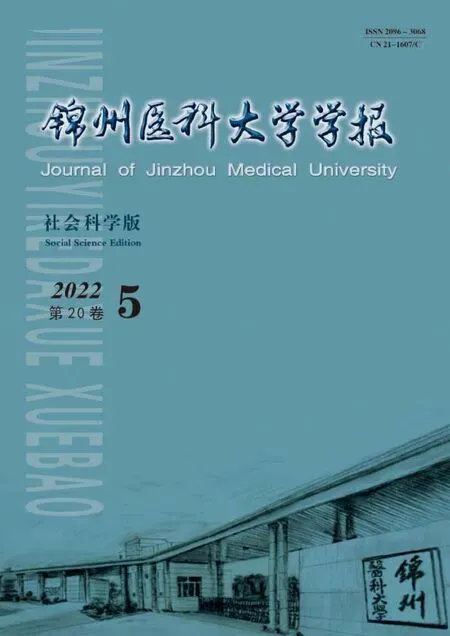2000 年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综述
刘雅仙,赵成彬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自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疾疫史在我国作为“新史学”的一项逐渐兴起,并吸引着越来越多学者的目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由于史料以及现实联系的原因,对于疾疫史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明清时期,而在2000 年以来,关于疾疫史的研究更是有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进展,因而对这一时期相关研究文章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比较分析,既有其必要性又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学界最新的研究情况和研究趋势,从而能够令我们对当前疾疫史的研究重点和热点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把握和认知。除此之外,通过对不同研究方向和研究学科横向与纵向的对比评价,也能够让我们跳出自身固有的局限,学习新的研究技术、研究思路和研究手段,以便更好地取长补短,推进学界对于疾疫史研究的发展。目前,已有不少有关我国疾疫史研究的综述和总体研究,医学界有赖文、李永宸等人的《近50 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1]、邓铁涛的《中国防疫史》[2]等,就史学界而言,有余新忠的《20 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3]以及他同陈思言合作写的《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4]、王小军的《中国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5]、郑言午的《近20 年隋唐疾病问题研究综述》[6]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各自从疾疫史研究的学科分类、途径材料、热点问题、研究成果、反思展望、影响作用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经纬角度的时空研究
较为传统且多见的是以时间和空间为主要内容展开的疾疫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时间因素又可细分为通史研究和断代史的研究,在断代史中又有以具体某年、某皇帝、某一事件为标志进行的研究;空间因素又可分为大区域和小区域的研究,大区域包括全国、几省或一省的范围,而小区域则为市县镇乃至村户或是某一特定环境。
本世纪以来,围绕时空展开讨论的研究层出不穷,如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7],这是我国较早对瘟疫展开研究的专著之一,该书从生态社会背景、瘟疫的时空分布和种类、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瘟疫的成因,重点关注了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的整体互动情况,运用了翔实的史料分析得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论断和观点。李玉偿的《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8]探讨了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历史,并对公共卫生制度在传染病传播流行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另外,曹树基、李玉尚合著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状况与社会变迁:1230-1960》[9]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针对国内历史上的鼠疫作出的具有科学性和宏观性的学术著作,该书不仅对研究鼠疫发生历史的方法论进行了梳理,还对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及环境变迁与鼠疫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对政府层面在医学方面的投入也有一定的关注。张志斌的《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10]收集了八百多条我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关于疫病流行的史料,时间跨度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两千多年有余,为我国疫病的发生情况做了较好的梳理,也为社会各界探讨传染病的防治提供了历史借鉴。赖文、李永宸的《岭南瘟疫史》填补了中医学史中较为薄弱的疾病史研究板块,弥补了岭南地区的空白[11]。
而针对时空因素的研究常常将二者结合起来,如:闵宗殿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讨论了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疫情、疫病种类、瘟疫暴发的原因及对社会影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相关研究的不足[12]。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分别就不同时期的大区域环境和时间跨度较长的瘟疫流行情况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林汀水从地方志和医疗史记载的基础上更为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明清两代发生在福建的疫病记录,便于学者更好地开展研究[13]。在较小的区域范围或者是时间跨度较短的瘟疫流行的研究方面,浅川的《万历年间华北地区鼠疫流行存疑》[14],余新忠的《大疫探论:以乾隆丙子江南大疫为例》[15]等都是其中较为优秀的研究成果。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其中不少文章仅是对该地区该时间段内的瘟疫进行史实的罗列、特点和原因的分析模板化及对社会影响的叙述,内容单一且缺乏新意,但依旧不可否认其价值。
二、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
时空因素仅仅是疾疫史研究中最为基础的两点,更多且更为常见的研究则是将时空因素与其他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进行更加细化而有深度的发掘,从而使疾疫史的研究成果能够涉及更多领域,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
1.从疾疫本身出发的研究。中国疾疫史的研究最初的主力军就是医学界,直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史学界才逐渐将目光投入此中,而在医学史的研究中,疾疫史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几种:首先,针对疾疫的起因、传播、表现的研究。如徐素娟等人就发生在康熙三十至三十一年陕西的瘟疫成因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主要与旱灾、社会风俗、治疫政策等因素有关[16]。赵现海则是以鼠疫为例,对当前有关瘟疫的研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包括要进行多文本互证来开展瘟疫科学史研究、改变僵化的叙述模式,从地域特征出发对瘟疫区域史加强研究,以及从传统而非现代的瘟疫观念出发开展瘟疫观念史的研究等[17]。以上都是以某一地区和某一类型的瘟疫为研究对象展开的相关探讨。
其次,相关的医家医案及文献的整理研究。如徐超琼、杨奕望主要对青浦名医陈莲舫在治疗瘟疫过程中的高超本领和巨大贡献进行了讨论[18]。钱高丽、周致元则以明代徽医汪机为切入点,分析了明代徽州疫病带来的影响以及当时民间医家的瘟疫应对机制[19]。张蕾则是以疫病为背景,研究了古代山东医者医派的治疗方式和应对不同瘟疫不同医者之间手段上的区别[20]。杨继、张、张春阳等人都是通过整理研究明清的医家文献总结相关的防疫治疫的方法和规律[21]。刘希洋则是从防疫方书上探寻清代疫情防控的措施和效果[22]。王翰飞[23]、张献忠[24]等人从中医治疗疫病的特色和理论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此外,翁晓红[25]、魏岩[26]等人还从我国古代防疫思想入手,探析了其内容和变化并试图将其中的可取部分嫁接到当今社会中来。林明欣、朱建平、丁曼旎等人则从非口服中药这一中医学方面的内容开展了对疫病防治的研究[27]。
2.从社会应对和影响出发的研究。疾疫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在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在促进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进步,向更好的一面完善。许多学者对疾疫相关的卫生设施、赈济组织等社会应对做了值得肯定的研究。既有对疫情影响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讨论,如李孜沫、陈丹阳二人从卫生防疫制度引建的角度分析了清代疫病对促进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的积极影响[28],也有关于政府及社会各界应对疫病的措施手段的研究,如田澍以明朝瘟疫多发期为背景,开展了对明政府官方层面应对瘟疫措施的梳理[29],余新忠不仅从国家层面,还从不同的社会力量方面整理了相关的防治手段,认为国家和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以合作为主,而非对立,而社会力量的活跃能够较好地填补行政力量所未能覆盖之处[30]。当然,疾疫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余新忠就试图以战争的视角来看待疾疫的作用和影响,通过讨论咸丰同治时期江南发生的瘟疫,剖析其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突破性[31],吴娅娜、易法银对湖湘和中原地区的研究也证明了在疫病影响下的民俗迷信活动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与改变[32]。此外,余新忠[33]以及苏基朗、谭家齐[34]还分别研究了明清江南和松江地区瘟疫发生对人口产生的影响,王宏治注意到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法律手段防疫治疫的记载,而在应对瘟疫的过程中总能看到巫术的身影,统治者不仅注重环境的保护,还对医药行业实行强制性管理,遭遇突发大疫时也会采取延医施药、减免赋税、发粮赠款等手段[35]。这些都是由瘟疫衍生而来的一些学术问题,颇具新意。
3.从拓展学科出发的研究。疫疾史的研究从最开始医学界的一枝独秀,到后来史学界的并驱争先,再到如今进入21 世纪,越来越多的学科也将疾病史的研究纳入其自身的行列来,互相争奇斗艳,如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环境学乃至心理学等等。地理学方面,在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教授的领导下,涌现了一大批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的研究成果,涉及不同时期的全国多个省份,如安徽、山东、福建、河南,山西、云南等地,单丽针对赣南周边霍乱重疫区的形成与变迁进行了探讨[36],张小敏试图通过地理空间角度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进行阐释,并认为疾病在人类社会中的静态和动态流动都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影响[37]。社会学方面,陈旭的《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38],讨论了明代瘟疫的特点、官方及民间的救助以及社会的变迁等,内容虽然不多但不少部分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环境学方面,朱浒、黄兴涛的《清嘉道时期的环境恶化及其影响》从灾荒视角出发,揭露了嘉道时期中国环境恶化的总体态势和社会由盛转衰的内在因素[39]。心理学方面,陈旭[40]和胡勇[41]分别从明代和清代讨论了瘟疫之下民众的心态,总体上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发现民众的心态会随着瘟疫的发生情况、控制效果而变化并反过来影响着瘟疫的流行和控制。政治学方面,胡成以发生在1910 年10 月上海公租界的一场鼠疫为背景,探讨了这一事件下暴露的种族歧视问题、中外关系紧张问题以及此事件与华人参与租界政治的信心增加之间的联系,认为由此引发的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对于打击英国在上海租界的权威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2]。当前,还有许多学者往往将疾病作为一种隐喻,以疾病的应对为切入点,将疾病与政治挂钩;另一方面,疾病流行要求建立更为全面、科学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卫生机构体系。此外,更多的技术手段和统计方式也在疾病史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如萧凌波的《基于核密度估计的清代中国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43],蔡婉婷、李新霞、陈仁寿的《基于Apriori 算法的古现代疫病用药比较与分析》[44],都是通过将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应用到疫病的研究之中,使其更具有专业性和说服力。
三、史料来源与搜集研究
由于中国古人对于疫病的认知缺乏科学性,对疫病的发生机理了解有限,且较之于其他的自然灾害来说,疫病的发生频率相对较低,因此,在古文献中疫情资料的分布也较为散乱,尚未发现成体系的记录疫情的专书。而到了明清时期,这一现象得到了改善,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由于接触到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学科体系,关于疫病的记录也得以不断完善,如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瘟病学派使得专研疫病的医书数量大增,而后报纸、方志上有关疫病的记录从数量和内容上都有了很大提升,便利了学者对这一时期瘟疫的研究。疫疾的研究资料除了传统的史书、地方志、报刊、官府文牍等,还有如杂记、碑刻、宗谱、日记、书信、传记、医书、档案资料等。周邦君[45]、哈恩忠[46]、冯志阳[47]等人就分别利用了笔录、档案、报纸等材料开展了各自的研究。另外,也有学者针对文献本身进行了探索梳理,张萌谈及了疫病文献研究的方法和现状[48],认为厘清概念、细化研究、完善文献质量评价体系,在深入整理研究古今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总结具有必要性。李文林、屠强、彭丽坤等人经过研究发现,疫病主要以“热邪”为致病因,容易损伤气血、消耗精气。在明清医家的病案里,“清热”类药物占疫病用药的绝大多数[49]。刘雪松主要研究了清代云南地区大规模发生的鼠疫,通过对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关于“疫”的不同描述,分析史料中“疫”情与鼠疫之间的相关关系,认为造成鼠疫的外在环境条件离不开云南独特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并揭示了鼠疫在清代云南逐渐从单一疾病发展成环境灾害现象这一历史事实[50]。
四、疾疫史研究趋势与反思
尽管有更多的学科与技术手段加入并运用到了疾病史的研究之中,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其研究的薄弱和不足,仍需继续深化、扩展。
1.从总的研究而言,疾病史研究发展未能跳出原有的研究框架。当前疾病史研究队伍虽在壮大,但专门从事疾病史研究且水平较高的学者仍少,除曹树基、余新忠、李玉尚外,其余学者影响力均有限。研究成果方面,近年来,虽有文章不断发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但数量屈指可数,平均一年仅有少数几篇。专著、博硕论文方面也未见别具创新性的大作。研究群体的大部依旧以医学界为主,研究凭借的文献以传统的医家医案、正史和地方志为主,对于其他史料的利用较少。而此类文献中往往较少记录到民众个体及个别社会现象,因此使得社会心理和文化史的研究较难开展。新史学强调泛史料化,然而在常见的研究作品中以日记、家谱、报刊、笔记小说、诗歌等为主要依据的成果并不多。此外,研究内容多烈性瘟疫而少温和型瘟疫,常常以时间加地区、史实加特点等要素的模式进行阐述,而结论却近乎大同小异,缺乏创新。
2.从研究对象而言,疾疫史研究的地域、时间与内容不平衡。从前文中我们能够看到,在明清疾疫的研究中存在地域的倾斜,相对来说,经济较为发达或者历史文化较为深厚的省份,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就较多,例如华北地区、江南地区、华南地区等,而东北、西北、青藏地区的疾疫研究就显得较为薄弱,客观来说,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与当地史料的不足、学者数量较少有一定的关系,而藏医、蒙医、壮医、苗医等古老的民族医学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其在防治瘟疫中的成果亟待我们发掘。此外,在对疾病史的研究中还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平衡,由于明清遗留史料较多,同其他朝代的疾疫研究相比,明清有关疾疫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表现得较为出色。但即便如此,依旧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学者们对以明清两代或明、清某一朝代为限的研究在史料上往往略显单薄,以某一皇帝在位期间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对短时期和小范围(乡县乃至村户范围)的某一瘟疫发作前后的生动叙述则近无,这也使得疾疫史的研究往往陷于一个较大的宏观层面上,而极易忽略疫病下小群体、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活动。曹树基、李玉尚等人都是研究鼠疫的知名学者,鼠疫研究的文章也很多、质量也最高,而地方病研究则无人问津。例如,血吸虫病广泛存在中国南方,流行时间长,危害大,被喻为“瘟神”,而这方面研究却很少。血吸虫病已是广为人知的疾病,其研究力度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病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3.从研究视角而言,加强学科合作的同时还需做到“走出去,引进来”。瘟疫史的研究主要以医学界和史学界为主,虽然逐渐有从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环境学等学科视角出发的研究,但目前来说还是缺乏能够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视角的出现。目前,学术界针对疾疫的研究视角主要有“医疗社会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生命史”等,其中“生命史”和“生态环境史”视角为新近发展起来,是从国外引入的相关概念,还处于一个摸索探求阶段。尽管相关学者们在试图将这些新概念、新视角与国内的传统疾疫史研究融合,但观察他们推出的研究成果后,我们还是能够十分明显地感到这些成果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并未完全为国内学者所用。此外,国内的许多学者囿于语言和文化的限制,其发表的一些疾疫史优秀的理论研究成果不能为国外学者所见,虽然国内也不时举行相关的会议和研讨会,但这样的“闭门造车”以及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匮乏无疑会导致国内的研究氛围缺乏生机和刺激,使总体的研究水平无法得到较快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