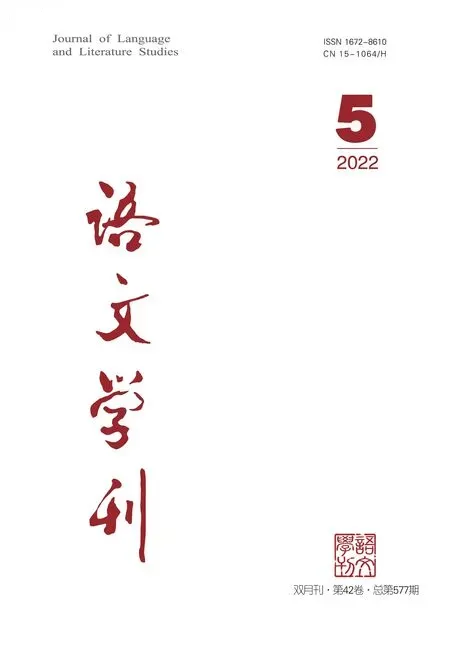传统文论语境中的《文心雕龙·神思》主旨新探
○ 陈沁云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神思》篇作为《文心雕龙》“剖情析采”的首篇被讨论得非常多,“想象”是大家在理解此文时离不开的话题,或是以此为讨论的主旨,或是附带谈到。在此之中,直接将“想象”作为《神思》理论内核的学者亦不在少数①。事实上,以“想象”阐释《神思》是以今释古,带有时代特色,故而并不能将之冠以误读之名。但不可否认的是,刘勰在写作《神思》的时候一定有着自己的目的,对这部分进行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还原作者的创作思路,进而也能让《神思》与《文心雕龙》的关系进一步清晰起来。
一、“想象”:当代《神思》主旨研究的核心观点
当代《神思》篇的主旨研究结论基本集中在“想象”论、“形象思维”论、“灵感”论、“思维活动”论以及“艺术构思”论等方面②,研究论文大致随着这几个方向深入剖析。事实上,通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虽然学者们的结论分为这几大类,但总体而言都可以将它们归于“想象”论之列。在《神思》的研究史中,“想象”一直是被讨论最多的,其他的观点或是与之息息相关,或是以其为母体生发。
首先,可以考察一下“灵感”与“想象”之间的关系,即使抛开《神思》不谈,二者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西方美学中,“灵感”与“想象”是密不可分的,比如黑格尔就认为“要煽起真正的灵感,面前就应该先有一种明确的内容,即想象所抓住的并且要用艺术方式去表现的内容。灵感就是这种活跃地进行构造形象的情况本身”[1]364。朱立元先生认为黑格尔的这段话指出了“灵感”的活跃性,“艺术家一旦进入灵感状态,他的想象就特别活跃,各种久储的形象像潮水般刹那间都涌流到他眼前,迅速地组合融化成新的形象”[2]165。笔者十分同意朱先生的观点。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灵感”是基于“想象”活动而产生的。应该说,二者都是人的思维意识中的活动,“灵感”具有突发性、易变性,甚至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并非主观意识可以控制。而“想象”却略为不同,基本上主体可加以把控。从一定程度上说,如果不进行“想象”活动③,活跃思维,就很难获得“灵感”爆发。通过对于潜意识当中两者活动模式的研究,可以发现“灵感”的产生需要依托“想象”活动。当回归《神思》时,二者的关系仍是如此,认为此篇主旨是“灵感”的学者们主要关注点在于《神思》中第一段话④的部分内容: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3]173。
站在当代文论的视角来看,将这部分内容阐释为对于“灵感”的描述应该说问题不大,充分体现“灵感”的特点。与此同时,不得不说这样的“灵感”是依托于“想象”的能力。贺天忠先生认为这段话“既是想象的特征,也是灵感来临时的重要特征”[4]。在讨论二者的关系时他指出:“灵感应是想象的高级形态,特殊表现形式,比想象更具独创性。”[5]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充分体现二者之间的联系。将此段话释为“想象”非常契合当代文论,“灵感”存于其中亦合乎情理,特别是“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这句话,与当代对“灵感”的认识十分相似。笔者认为,在人的思维意识当中,首先应当由主体自发进行“想象”活动,以此来刺激大脑思维,并使之活跃起来,在不断的“想象”过程中,“灵感”会突然出现。“想象”是思维活动,“灵感”是“想象”这种思维活动的结果。虽然有学者认为《神思》的主旨是“灵感”,但本质上仍然是在“想象”的基础上做出的更加深入、细致的解读。无论是客观上二者的关系,还是在《神思》中它们的交织,脱离后者而单纯依托前者来概括《神思》,似乎较少见到学者如此讨论。
其次,“形象思维”论、“艺术构思”论、“精神活动”论与“想象”的关系,笔者将此三者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较小,甚至相互关联密切,故不宜再做细分。詹锳先生将“形象思维”与“想象”几乎画等号,其在《文心雕龙义证》的《神思》题解中讲道:“可以说:‘神思’一方面是指创作过程中聚精会神的构思,这个‘神’是‘兴到神来’的神,那就是感兴,类似于现代所说的灵感;另一方面也指‘天马行空’似的运思,那就是想象,类似于现代所说的形象思维。”[6]975詹锳先生认为《神思》是“灵感”与“想象”,而“想象”也就是“形象思维”。事实上,“想象”与“形象思维”的关系是比较好理解的,“想象”的产生须有“表象”的生成,没有“形象思维”又何来“表象”?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再看牟世金先生的观点。牟先生是持“艺术构思”论的,可事实上他与詹锳先生的观点大同小异,其在《文心雕龙研究》中谈论《神思》时讲道:“文学创作是一种凭虚构象的精神生产。这种生产的完成,必须通过特殊的精神活动:想象。没有必要的想象,就不可能有艺术创造。刘勰所论,就是完成这种艺术创造的想象……艺术创造所须完成的,自然不是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虚无缥缈,而是绘声绘形的具体艺术形象。”[7]317牟先生将《神思》的主旨概括为“艺术构思”,这就扩大了此篇的内蕴,因为构思涵盖的内容很多,绝不只是某一具体的思维活动,应该是综合性的。可是,牟先生也承认“想象”是艺术生产的必经之路,同时必须创造出具体的艺术形象。此处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作者用了“凭虚构象”一词,已经将自己的观点概括得十分精要了,“想象”和“形象”是密不可分的。总的来说,牟先生认为《神思》是“艺术构思”的论点,其核心是“想象”,目的是产生艺术形象,这是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做出的精准、细致的思考。在“思维活动”论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王运熙和杨明两位先生。王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译注》中认为“神思”是指人们进行创作时的思维活动[8]272,杨明先生亦持如此观点⑤。“思维活动”论无疑再一次扩大了《神思》的内涵。当然二位前辈的落脚点都是写作中的“思维活动”,但仍然比“艺术构思”的内涵与外延要广阔得多。无法否认的是,刘勰的《神思》一定是谈写作的“思维活动”,可是如果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此篇的主旨和神韵,则应该会更贴近作者的想法。王运熙先生对《神思》开篇一段文字的解释是:“先是说明人们在进行创作思维活动时,思路异常开阔,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头脑中仿佛展示了自然界鲜明生动的形象,并考虑如何运用美妙的词句来加以表现。”[8]272可以看到,虽然作者以“思维活动”统筹《神思》,但是在理解上还是回到了“形象思维”,头脑中产生了生动的“表象”,并且这样的思维活动不受时空的限制,这仍然与“想象”理论比较相似,也就是说即使以“思维活动”这样的大概念来把握《神思》,最后也可能会不自觉地朝“想象”论靠拢。
综上所论,当代对《神思》主旨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想象”展开的,或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无论是直接以“想象”阐释《神思》,还是在思维、构思层面进行挖掘理解,最后大家似乎都很难避开以“想象”来讨论此篇内蕴。总体而言,“想象”论是当代《神思》主旨阐释的核心观点。
二、原始表末与释名章义:对刘勰《神思》主旨“言尽意”的考察
虽然在当代《神思》研究史上“想象”具有核心地位,但笔者却认为刘勰作此篇的目的可能与“想象”关系较小。那这篇文章所作为何呢?笔者认为,《神思》是为了通过对“言尽意”的研究来建构起文章理论的地基,也就是说刘勰要在这篇文章中贯穿他的“言尽意”思想,并且将之作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后续的“剖情析采”部分大多是在论述具体的风格与写作问题,是在《神思》“言尽意”大框架下进行的局部研究,所以“言尽意”是整个文章理论的基础。在刘勰看来,只有竭力消除思维与创作之间的壁垒,那么其余有关文章写作的讨论才有了相应价值,如果语言文字无法贯穿思维想法,那后续所谓的“体性”“风骨”“通变”等又怎么体现出来呢?本文将尽力还原刘勰《神思》的写作意图。
我们需要明确的第一点就是,刘勰的思维中应该不存在“想象”观念,这个词颇似舶来品,传统文论较少出现“想象”这个概念。问题在于,虽然刘勰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是在一千五百多年之后的当代仿佛可以看出《神思》所论十分符合“想象”理论。这就可以看作是古今之契合,以后者阐释前者并非不可行。事实上,因为我们在阅读《神思》之前基本上已经有了“想象”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比较了解它的理论内蕴,如此一来,可能会有先入为主之弊,那就很有可能不是刘勰的《神思》。此时放弃先入之见来考察这篇文章就变得很重要了。首先来看第一段的部分内容,刘勰说: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3]173!
虽然引用了《庄子·让王》中公子牟的故事,但刘勰赋予了它不一样的含义,即是要指出“形”与“心”可以分开很远,也就是说精神活动不受时空限制,并且以此为例来帮助自己给“神思”下定义。后面的几句话正如上文所言,是学者们将《神思》作为“想象”论的一大证明。事实上,刘勰此处所论之核心应该是“文之思也,其神远矣”。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笔者认为如何阐释 “文”与“思”的关系至关重要。张灯先生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作家创作时的思绪,能使心神走得很远很远”[9]241,这是比较符合刘勰本意的。也就是说,刘勰在讲《神思》的时候思路是十分明确的,虽然作家的思维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可是它必须要与创作相连,所谓的“神思”之“远”,那是针对“文”而言的,也就是说思维的活跃要为创作服务。如果脱离了这一点,那刘勰的讨论也就离开了对文章理论的思考。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便可以理解作者的用意:他的目的是在探索主体的思维意识可以去到的极限空间到底有多远。所谓的“寂然凝虑”至“卷舒风云之色”之语是刘勰对这个极限空间的设置和形容,如何可以证明呢?关键就在于“思理之致”的“致”的阐释。参考诸家译本,将之译为“导致”居多,这并不是非常符合彦和之意。此处应该是对于“思理”这个活动的进一步加强说明,刘勰用了那么多的形容文辞,为的就是彰显出这种极致的思维活动,强调主体思维所能达到的极限空间。如果只是说明正常的“思理”,为什么需要安排“形”与“心”的分离,以及“思接千载”和“视通万里”的空间跨越呢?所有的这些应该都是为了表达出一个观点,即思维可以去到无限遥远的空间。台湾的李曰刚先生就认为应该将“致”训为“极诣”,指出“此句总摄上文(其思理之致乎),言此乃思想理致之极诣,换言之,亦即思维活动之最高境界也”[10]1130。笔者认同李先生的观点。张灯先生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这种微妙的、变幻无穷的景象,显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理’也即理性思维,‘思理之致’自应指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故‘致’宜训为极为当。”[9]686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刘勰的目的,便可看出,这些所谓的极致空间都是刘勰主观设计出来的,他就是要探索人的极限思维模态。这样的设置并非随性而为,其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拉大思维与创作之间的距离,他希望这样的距离是无限大的,至少是他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最大程度。所以,《神思》是刘勰给自己设置的难题,当思维与创作面对如此大隔阂、壁垒、距离时,是否还能够做到“言尽意”?是否还能准确地用文辞表达出思维内容?换句话说,如果创作主体的思维与创作不处于同一时空,后者是否还能完美地表达出前者的模态?可以说,刘勰的尝试十分大胆,非常具有挑战性。他的整篇文章都是在极力磨合二者。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刘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从各个角度去消除“言”与“意”的距离,当然,彦和要衔接的不是普通的“言”“意”矛盾,而是创作与极限思维之间的壁垒。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3]173。
刘勰在此处将“神”与“物”放在一起讨论,好像他把话风转向了另一边,事实上并非如此。王运熙先生对这个问题有着非常准确的见解,他指出“因为这是以诗赋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对象来讨论问题的缘故。汉魏以至南朝,人们一般以诗赋为文学作品的主要样式,这在创作和评论方面都是如此……状物是辞赋的一个重要内容”[11]81。文中的所言“物”其实是刘勰避不开的,古代文章作品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无法离开“物”,特别是景物,这是寄托情感的最佳载体,也是作家普遍的选择,所以不能因为此处讲到了“物”就认为刘勰转变了话题。明白了这一点,就了解刘勰仍然在完成自己设置的挑战。可以看出,他意识到“志气”与“辞令”之间的关系,在创作时思维不能堵塞,文辞必须通畅。刘勰始终将“神思”与写作联系在一起,他的落脚点是没有变化的,由思维到创作实践,二者不可分割,既不是单纯的构思,也不是纯粹的摆弄文辞,而是两者的统一。刘勰只有对“言”“意”问题做出思考,才能搭好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其他细节问题,他想要完成的目标是:
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173。
此段话便是真正的《神思》主旨,意在强调文章写作需要对“言”与“意”进行完美衔接。刘勰希望文章作者可以用心感受,了解自己的想法,然后谋划文章结构,最后落笔成文。这是对首段的总结,也是全文的主题。文章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得保障“言”可以尽“意”,顺利完成由思维中的“意”至笔下之“言”的整个过程。有学者将此处的“意象”作为“想象”论的有力证据,这是不太准确的。刘勰虽然用了这两个字,但是他想要表达的只是“意”,没有“象”,与当代文论中的“意象”不同。钱锺书先生曾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认为:
应该说明的是“意象”作为一个组词虽然被刘勰第一次提了出来,但他所说的 “意象”和我国文论史后期所说的“意象”,或西方所说的“image”含意并不尽相同,比之要广泛得多。《文心雕龙》由于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意象”实属一个偶词,其含意实际上只是一个“意”字[12]。
钱先生的认识是在回归传统文论语境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此处的“意象”就是指“意”。当我们联系上下文的时候,也可以发现,刘勰说得最多的是“意”,他要表达的也是“言”与“意”的关系,如果突然出现 “意象”,那就太突兀了,并且也将主旨转移了。《文心雕龙》每一篇的主旨都很明确,逻辑条理也十分清晰,突然的主旨转移并且插入无关话题,这是不会发生的。对于这一点,杨明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神思》的主旨应该是对于“言尽意”的考察,并且刘勰加大了这个过程的难度,他希望完成的是用语言文辞来言尽极限思维空间中的“意”。笔者认为,刘勰相信如果连如此困难的“言”“意”壁垒都可以消除的话,那就解决了根本问题中最艰难的部分,所以这是他在创作理论中首先要做出的回应,将之形容为“驭文之首术”,的确再合适不过了。
三、解决模式与选文定篇:“言尽意”的方法与例证
虽然刘勰有着“言尽意”的观念,但是在实际的写作过程当中总会遇到无法消除“言”“意”隔阂的情况,刘勰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并且将可能出现的令人不满的情况表达了出来: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3]173。
简言之,就是头脑中所规划的内容很美好,主体的情感也十分丰富,因而希望表达出来的东西有很多,但是最后却发现呈现出来的文章可能只打了对折,还有很多想法没有阐发出来,不尽满意。这是典型的“言不尽意”。语言文辞与思维之间存在着隔阂,用刘勰的话说,就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3]173。可是,刘勰是“言尽意”论者⑦,他必须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刘勰的解决方法也是沿着“言”“意”关系来进行的。他首先在思维意识层面提出“虚静”“养心”,然后强调通过后天学习来提升语言表达的水平。从思维贯彻到具体写作,这样的认识是十分科学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可以看出,他始终将“言”与”意”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讨论。在思维层面,刘勰基本秉承着传统“养心”“养气”的特色,其曰: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3]173。
前一句作者是引用了《庄子·知北游》中的话,但此处的引用和开篇所引《庄子·让王》的目的是一样的,要为《神思》的主旨服务,因此刘勰的意思是在创作前需要保持内心的虚静,清空杂念,洗涤精神,然后投入写作,他的意图应该是非常积极的。诸译本对此句的阐释大多比较准确,笔者选取李曰刚先生的译文作为一例兹以说明,其曰:“是以欲运转文思,其要诀贵在虚静二字:临文之际,应洒濯五脏内之勃缪累塞,以力求其清虚;拔除精神上尘埃滓垢,以务臻于洁净。”[10]1132这样的阐释不仅对原文进行了解读,同时并没有忽略全篇的基调,围绕主旨探索了刘勰的想法,将“虚静”紧密与创作结合,厘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虚静”是创作前对思维的调试,目的很明确,让内心专注于文章创作,心无杂念⑧。刘勰的后一句话更是直接将“养心”之术与写作联系在一起。虽然前后两句话并不在一段中,但后者实际上是对“虚静”“养心”之术的具体落实。在前一句中,刘勰从思维入手,提出方法,而在后一句话中点明了思维必须实践至写作。较多学者认为《神思》中所言之“虚静”论应该与《养气》篇合而观之,这是非常合理的见解。《文心雕龙》诸篇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刘勰都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探究思考。他在《养气》篇中说得更加清楚:“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条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3]239由此可见,在刘勰看来,创作之前的思维清理十分重要,如果认为意识混乱,烦扰过多,尚可“言尽意”,想必不太准确。与此同时,应该要明确的是,如果希望大脑中的思维去到很远的地方,和现实拉开巨大的距离,那就一定要让思维活跃起来。也就是说,刘勰明白当设置极限的思维距离与空间时,人的意识、精神活动非常活跃。可是,这样的模态虽然利于思考,但却碍于落笔成文。文章写作时需要冷静,所以他借用了传统文化中的“虚静”,用来制约写作中的思维跳跃。刘勰对人的思维模式和具体写作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在哪一层面该如何操作了如指掌,相互之间该如何衔接亦是心如明镜。他把哲学层面的“虚静”加以改造运用至写作理论中,为缩小“言”与“意”的距离开了一个好头。
紧接着,刘勰谈到了“学”的作用,这也是达到“言尽意”的主要方法。在对“意”的层面进行宏观把控之后,如何具体落实到文章写作就是他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彦和认为此时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学”上,“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3]173。这四个短语就是刘勰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关键是学什么?怎么学?笔者认为需要对此进行仔细剖析。前面两个短语基本上争议不大,意思就是学习优秀的经典作品,酌辨事理丰富才学;而“研阅以穷照”和“驯致以绎辞”却是诸说纷纭。首先,“研阅以穷照”该如何理解,特别是刘勰说的“研阅”到底指的是什么?部分学者将之阐释为参考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就是说“阅”是“阅历”的意思。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比如吴林伯先生就认为此处应该解释为“研究、阅读有关材料,其目的是‘穷照’——彻底认识事物”[13]475,王运熙先生则将之译为“阅览、钻研前人或他人的文章”[11]84。笔者认为刘勰主要强调的应该还是学习与精研,至于诸家所解之“阅历”,虽不能直接说是错误,因为正如詹锳先生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古人增进阅历的方法之一”[6]982,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都是精研学问与文章。可是我们仅通过刘勰的“研阅以穷照”这五个字就得出其中有“阅历”的含义,也许略为冒险,更何况从全文与此四个短语之间的关系来看,作者在这里要说明的应该就是勤学文章,精研学问,故而吴林伯、王运熙先生的解释比较保险并且贴近原文。其次,在“驯致以绎辞”中关于“致”的训释也存在着不同看法,诸多译本将之释为“情致”。事实上,在我们完成前述对“研阅以穷照”的理解之后,此处的解释就应该清晰很多,并且也只能跟随上述“学”的路径接着分析,也就是说,将“致”译为“情致”可能就不太准确了。那应该如何解释呢?“致”应释为“达到”⑨,这个短语意思就是说要掌握文辞写作的规律。通过这部分的解析,可以觉察到刘勰极其看重“学”作为“言尽意”方法的重要性,这也符合古代学者勤学苦练的特点。不仅如此,刘勰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运用了具体的例证加以说明,也就是下文关于历代作家写作过程之迟速的评说,其曰: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沉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鞌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3]173-174。
在部分研究者看来,这段话内容是在分析历代作家构思的快与慢,将“灵感”论、“想象”论引入讨论的也有不少。事实上,刘勰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列举不同作家的“言尽意”的情况,有的作家思维与创作较难在短时间内完全磨合,有的则不然,可以马上“辞达意”。在此之中,虽然刘勰没有直接道出“学”对于“言尽意”的关键作用,但是从他采用的例子就能看出学养是十分重要的。写作疾速之人定不用多说,没有足够的学养肯定无法做到“言”“意”的无缝衔接。那些所谓“思之缓也”的作家们是不是才学不够,不如曹植、王粲他们呢?对此,刘勰给出了解释:
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3]174。
在彦和看来,这两种模式虽有迟速之分,但并无优劣之别。也就是说,这只是在创作中的两种思维模式,写作疾速之人,是因为他们十分机敏,所以“言”和“意”基本上是同步的;而沉思之人,偏好思虑良久,所以思维与写作会有前后时间差。但是无论是哪种类型,都需要勤学苦练、博学多才。事实上,当我们深入考察刘勰所列举的作家,我们就可以发现,司马相如、扬雄、桓谭、王充不可能没有才学,他们若构思的是鸿篇巨制,想要速成实在是天方夜谭,即使果真疾速而为,恐效果不佳,又如何流芳百世。王充《论衡》皇皇巨著20万余言,难道可以速成?更不可能以“想象”来写作。这是必须积累学养,精思研虑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衡与左思的赋,更需要学养的支撑,正如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云:“案二文之迟,非尽由思力之缓,盖叙述都邑,理资实事,故太冲尝从文士问其方俗山川,是则其缓亦半由储学所致也。”[14]88此二者之文涉及山川河流,需要到实地考察,积累资料,也就是季刚先生所说的“储学”,特别是左太冲的《三都赋》,最是如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此赋《序》中的一段话: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15]178-179。
左思为了写好《三都赋》,做了很多实地考察,这些都是为创作所积攒的材料。因为在他看来,文章写作必须切乎实际,只有这样,读者才会相信。如此便可清晰明白刘勰所说“练都以一纪”其实是左思在“储学”,为写作打基础,所谓的“思之缓也”应该不仅是指创作前的构思,更是包含了学习的成分,在丰富的材料支撑之下,也许才可以“言尽意”。在完成例证之后,刘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3]174。
没有学问,却想要写好文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无学养之人作文必定会思理不畅而内容贫乏,文辞泛滥而杂乱无章。因此,优秀的文章写作一定是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之上,这样方能主旨一贯,说理晓畅。
刘勰提出的“虚静”和“学养”较好地应对了他给自己设置的难题,前者针对思维,后者服务写作,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虚静”可以很好地控制住思维的跳跃,当然这种跳跃本身就是刘勰自己预想设置的。当思维要去到极限的距离和空间时,它一定是非常活跃的,可是作者落笔成文时必须保持冷静、理性,所以“虚静”就显得很有必要。“学养”的问题自然不必多说,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刘勰看来,若要“言尽意”至少需要做到这两点。
四、敷理以举统:对《神思》“言尽意”之“理”的总摄
在《神思》的最后一段话中,刘勰似乎话锋一转,表达了他在“言”“意”关系上还有很多无法说明的问题。虽然最后一段内容不多,好像刘勰没有再多讲什么观点,但事实上,这部分却仍贯穿着作者对“言”“意”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一下作者的意图,原文是: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3]174!
在《神思》研究史上,对“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的阐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大多数译本基本上是按着黄侃先生的理解⑩来进行的,但左东岭教授提出了异议,他指出:“黄侃先生在这里有两点重要的失误:一是把两句话的被动语态改成了主动语态,二是把原本是谈构思的‘神思’内容换成了‘修饰润色’。”[16]季刚先生的理解应该说是比较通顺的,可是不符合刘勰本意。左东岭教授一语中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可以通过改变语态来实现。那该何解呢?虽然左教授没有尝试翻译此句,但学界已有论文得出了研究结果,比如刘尊举将“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貌”和这句话连在一起翻译为“如果情理杂乱,体要不明,那么即使有奇思妙想,恐怕也只能出之以拙陋的言辞和平庸的典故”。而将“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阐释为“若有精心的组织安排,便能写成令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17]。再如王晓娜将前半句释为“即使构思时文章有了一些‘巧义’和‘新’,但倘若写文章时不能‘博而能一’,那么落笔成文后,因杂乱无序也只能使文章沦为一堆平庸的文辞”[18]。可以看出,两位学者都已经纠正了语态颠倒的问题,译文也比较贴近原文。事实上,在他们的论文中都强调了“博而能一”的重要性,同时二者也对“若”进行了阐释,训为“假如”。王文还强调了“于”为“在”之解,这是引用李逸津先生的解释。他们的译文大同小异,较为符合刘勰本意,可是也存在着两个问题,亦是非常容易误解的地方。首先,“若”不能解释为“假如”,应该理解为转折。关于这一点,张灯先生的解释是比较准确的,他指出:“‘若’相当于‘若夫’‘若乃’,任联词,表示意有他转。”[9]247为何?张先生没有解释。联系上文来看,刘勰在前面的四段话中基本上已经把他能讲的话都讲完了,他的观点已经表达完毕,其先是引出主旨,然后把解决方法和证据都摆上台面。在第五段中,刘勰没有再进一步要表达观点的意图,他想要说的可能就是“言尽意”很难,有的时候构思得很巧妙,而写出来的文辞却很糟糕,这是再次呼应前文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换句话说,此处他已经开始总结全文,再次回顾《神思》的主旨。虽然他提出了解决“言”“意”矛盾的方法,但是彦和内心还是充满了担忧。担忧什么呢?那就是以他的学识只能把《神思》讲成如此了。刘勰明白在“言”“意”问题上还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或者有待解决之处,自己所说的一切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要消除“言”“意”之间的壁垒太困难了,可是基于自己的认识水平,他无法再深入窥探里面的门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引用“伊尹”和“轮扁”的故事来结尾。其次,所谓的“博而能一”对“杼轴献功”的核心意义较难得出。当我们明白了对“若”的阐释之后,就可以了解第五段话是与前面几段存在转折关系的。同理,此处不会再对“博而能一”之论进行单独展示。关于“杼轴献功”的理解,我们只能认为是刘勰将所有能“言尽意”的方法都纳入其中了,包括他自己所提出的方法,由此来尽量缩小思维与创作的距离,故而可以认为“博而能一”是“杼轴献功”中的一种方法,但无法得出前者是后者所言之核心的结论,如此略有过度阐释之嫌。通过对第五段话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刘勰转移了话风,但他并没有脱离主旨,“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这句话道出了“言”与“意”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可是刘勰希望能够“言尽意”,所以“杼轴献功”就代表了可以达成目标的所有方法,至于其中到底具体包含了多少方法、哪些方法,恐怕在彦和看来,他是无法言尽了,故曰“言所不尽,笔固知止”。
从《神思》的内容看来,刘勰所进行的应该是对“言尽意”的讨论,全篇内容基本上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的。刘勰首先让思维去到最极限的空间中,然后再试图用语言文辞将之拉回到写作之中,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笔者认为这是彦和给自己设置的挑战。当最困难的“言”“意”壁垒都可以消除的时候,那写作基本上也就完成了最核心的部分。如何才能消除二者的距离呢?刘勰提出“虚静”和“研学”的方法,他始终保持思维与创作的统一。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将此二者作为解决方法并非创新性很大,但事实上,笔者却认为刘勰最大的成就即在此。因为在他的脑海中,思维与写作既有先后顺序,也有连贯性,如果不首先从构思层面提出解决方法,那写作就失去最核心的方针,这样“虚静”的提出就很有必要;可是,若只对思维提出应对方案,而忽略具体的实践环节,那么再巧妙的“意”也会无法现形,所以“学”可以帮助文章表现。但是在科学认识中,首先要从思维入手,然后才能延伸至写作。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刘勰对文章理论已经有了非常科学的认识观,《神思》体现了他对文章的讨论是与普泛意义上的人类学紧密结合的,即“言”与“意”的关系是文章理论层面的思维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虽然刘勰在最后说“言所不尽,笔固知止”,但可以认识到,即使在当代,我们对“言”“意”关系的认识也无法超出他太多,所以把《神思》作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充分体现了作者超高的文章理论格局,这是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可谓高屋建瓴,抓住了文章写作的关键。
《神思》所采用的叙述方法基本上是按照刘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3]287的模式来进行的,虽然在《序志》篇中作者说得很清楚,这是“论文叙笔”的行文逻辑,但笔者认为同样适用于“剖情析采”部分,在《神思》篇中也是能够得以彰显的。在《文心雕龙》中,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相应固定的主旨,并且一以贯之。《神思》篇也是如此,那么所谓的“想象”“灵感”论就比较难站住脚了。也许可以说此篇开端两段是“想象”,可是从第三段开始,就很难再以“想象”冠之了。从上文对第三段诸作家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写作的主旨是比较明确的,王充《论衡》无法通过“想象”作成,张、左二者更是无法将他们的作品直接冠以“想象”之名。况且刘勰引证诸家的目的很明确,他想说明的就是“人之秉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然后引出“博而能一”。因此,根据刘勰对主旨一以贯之的写作特点,《神思》较难以“想象”论来贯穿。
《文心雕龙》的整体基调应是朝着“言尽意”发展的,可是哪一篇才是真正完全贯彻这个主旨,并且将之作为最核心的方向舵呢?笔者认为就是《神思》。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此文的导向性极强,对整体理论框架的指导价值也非常大,《神思》之所以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其根本就在于刘勰是以“言尽意”来总摄整个文章理论体系的。
五、结 语
通过还原刘勰的写作目的,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神思》的主旨可能是“言尽意”,作者给自己设置了巨大的难题,最大程度上拉开了思维与创作的距离,然后探索二者进行榫合的方案。在刘勰看来,只有首先消除了“言”“意”之间的壁垒,其他关于文章理论的问题才能一步步迎刃而解,所以作者将这个问题冠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之名。自古以来,“言”“意”之间的错位一直是困扰作家们的重要问题,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也不免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写作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彦和自己认识到他也无法完全消除“言”“意”之间的壁垒,只得尽可能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即便如此,刘勰的理论仍然是高超的。
【注 释】
①将《神思》阐释为“想象”的学者较多,比如范文澜、王元化、刘绶松、李曰刚、李泽厚、詹锳、吴林伯、穆克宏、祖保泉等,人数众多。当代将《神思》解读为“想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站在当代文论语境中来看,这是不误的。
②这几种是对《神思》主旨阐释的主流结论。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在研究探索过程中,对此文的解读越发细致,但总体上的主旨辨析基本呈上述之态势,变化不大。本文接下来会对持这些观点的代表学者做出简单介绍评述。
③胡伟东在《也谈直觉、想象与灵感》一文中对“想象”与“灵感”在潜意识层面的活动关系做出了研究思考,指出“想象是灵感的源泉,而灵感正是根植于无边的、川流不息的遐想之中。想象的基础是一种潜意识活动,是在显意识之外的一种人脑的机能。现代脑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表明,潜意识在人脑内的活动范围和能量都是很大的,甚至超过意识活动,意识活动停止,潜意识活动反而更强烈。当连续思考问题时,思维处于高度激发状态,而当这种激发状态略微松弛时潜意识即开始活动。当潜意识孕育成熟之后,一旦接到某种信号,受到某种刺激,与此有关的现象显现出来,涌现于显意识,即出现所谓灵感。在心理状态上表现为波涛汹涌、思绪万千、突然的领觉,获得启迪,导致科学上的发明和创新”(胡伟东:《也谈直觉、想象与灵感》,《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这段话的分析是十分清晰的,也在科学层面将二者的关系描述得非常仔细,可以看出“灵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想象”产生的。
④本文对于《神思》的分段采用(梁)刘勰《文心雕龙》,戚良德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的分段模式,全文分为六段(包括赞词),参看此本第173-174页。
⑤杨明先生在其专著《文心雕龙精读》和《刘勰评传》中都是认为《神思》是指写作时的“思维活动”(参看杨明《文心雕龙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5页;《刘勰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⑥杨明先生在《文心雕龙精读》中引用了钱锺书先生的原话,并在此基础上追根溯源,认为《周易·系辞》中所言的“圣人立象以尽意”也与所谓的“形象”无关,《文心雕龙》中用“象”字,并无明确地指今日所谓“形象”的意思(参见杨明《文心雕龙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2-125页)。这也提醒对《文心雕龙》本意的理解需要回归传统文化语境。
⑦关于刘勰到底是“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论者向来有争辩,不过笔者认为他是“言尽意”论者。《文心雕龙》虽然不是每篇都与“言尽意”有关,但其理论体系就是为了“言尽意”而生的。在此不得不提的是王元化先生,他在《文心雕龙讲疏》中认为刘勰是“言尽意”者。王先生通过对《神思》《物色》《夸饰》诸篇的理解,指出在刘勰看来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参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⑧虽然笔者将“心”与“思维”混用,但本质上是一回事,所谓的“心”也就是指大脑中的思维模式,古人对大脑思维较少有很准确的认识,以“心”指称居多,所以笔者在论述时尊重这样的习惯,全文皆是如此行文。
⑨持这样观点的有周振甫(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张灯(参见张灯《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88-689页)、吴林伯(参见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页)等。
⑩黄侃先生的解释是“此言文贵修饰润色。拙辞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文心雕龙札记》,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9页)。